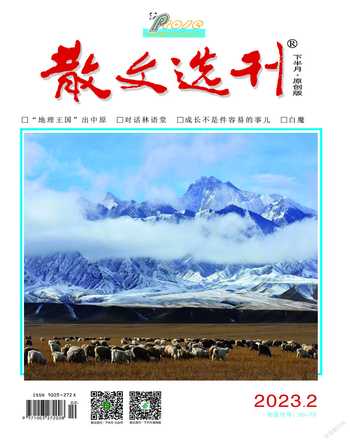偷月亮菜
舒维秀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侗寨里一名少年时,就曾和小伙伴们多次“贼偷”过月亮菜。
那时候寨里人家日子都过得很紧,平时除生产队畜牧场杀猪,每家分得几斤肉外,是很难吃上荤菜的,连糖果也很少得吃,每每听到货郎担吆喝着从寨子走过,我们都挨在屋里不出来,不然出来见了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买了糖果,而我们家却买不起的话,心里更不是滋味。上小学前,我曾有过从本寨一小姑娘口中抢过水果糖,放进自己口中尝几下甜味,又吐出来退给她的“丢丑”经历。那时的中秋节,有些年父母亲会想办法给我们买来月饼(当时叫饼子糖),每人至少一个,多则几个,我们吃得可香了。有些年却因手头紧而买不起饼子糖。也许是月饼吃得不满足,也许是为了一年一次的放纵吧,中秋夜月亮升上山坳后,我们出动了。
“岑横屋背的柑子林,是大队的,我们今年去那里偷”,上坎小明比我大两岁,主意多。“我白天去认真看了,柑子大个哩!”下坎老银讲。我们几个踏着月色,从田埂上出寨,经过阴溪寨时,先听见一条狗叫了,接着满寨狗都叫了起来,我们不但不躲避,反而在寨外喊:“老全,快出来,我们偷月亮菜去。”于是又多了几个偷月亮菜的人。偷得柑子后,就在柑子林边席地而坐,剥下的柑子皮,铺白了脚边的草地。
我们寨子对门坡路口,有个小小白土地,白土地边,有块小小土,是阴溪寨人家的,有年种了一土的葛苕。这年中秋,月亮老是藏在云里不怎么出来,月光时明时暗的。白土地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心理害怕物,但我们还是抵挡不住葛苕的诱惑,我和弟弟摸过小路来到了白土地边的葛苕土里。一边用手扯苕藤,一边用手刨土,好不容易才偷刨出一个葛苕。偶有夜风吹来,土地边的树叶哗哗轻响,我俩心头还是一紧,匆匆偷了几个就回家了,这是最担惊受怕的一次偷月亮菜,后来我们再也不去那里偷了。
最难忘的是姑妈家几个老表那年中秋节和我们寨里小伙伴一起偷月亮菜的事。那晚我们几个和上坎小明、老川,下坎老银等人相约去偷月亮菜,但偷哪个家的好些呢?“我家的花生今年长得好,去偷我家的”,“我爹妈今年做得好,葛苕大个大个的”,“前天我尝了一个,我家的柑子变甜了,去那里偷”……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开了腔,后来大家一起行动,先偷老银家的柑子,再偷小明家的柚子,最后偷老昆家的葛苕和花生。老川家的葛苕,因那年他爹妈身体不好,农活做不到位而小个小个的,大家决定不偷他家的了,弄得他脸上不好意思起来。哼!明年要我爹我妈好生种块大葛苕,看你们去偷不!老川在一旁小声嘀咕着。偷来月亮菜后,大家集中去寨子对面的小山岗上分吃,再玩藏猫猫游戏。众人躲藏在茶叶树下,轮流由一人去找,后因老川踩到一条蛇而于惊险中游戏收场。回家后,我们几老表意犹未尽,拿起斧子柴刀,去屋背剩粮湾一家土坎边偷砍了一根杉木树扛回来,把偷月亮菜行为升级为偷月亮材。
偷月亮菜有个规矩,叫“ 许吃不许辗”,即当时偷当时吃完,不许带回家吃。这也许是在物资匮乏年代,既要滿足小孩子们玩乐的天性,又不至于对菜主人造成较大损失的一种平衡吧。
——小明篇——请假
——上课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