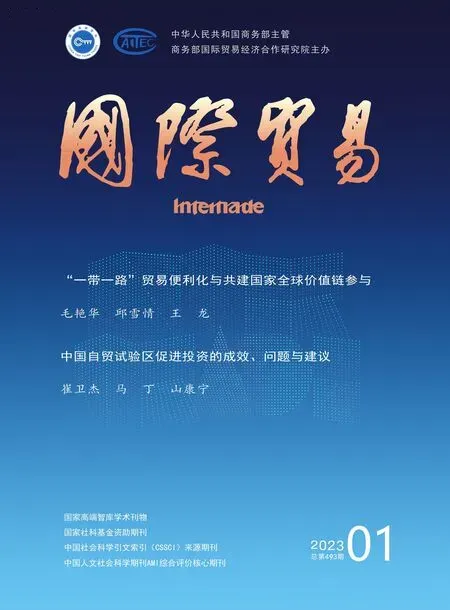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 杨 任财君
一、问题提出
由于WTO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一些成员纷纷转向区域和双边服务贸易规则构建,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负面清单应用于跨境服务贸易管理,从而成为区域贸易协定(RTA)服务贸易开放的主流。WTO的RTAs数据库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全球生效的356个RTA中,188个涵盖服务贸易,其中2000年之后生效的超过90%①参见RTAs in force,http://rtais.wto.org/UI/PublicAllRTAList.aspx,访问日期:2022-09-28。,近年来的RTA中大多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对中国来说,目前尚未在RTA中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2018年上海市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08年)》(以下简称《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2021年7月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2021年版)》(以下简称《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无论是框架结构和还是清单内容都与FTA中的负面清单存在较大差异,仍不是真正意义的负面清单。同时,2022年1月1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要求中国在协定生效6年内将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由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2021年6月中国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工作,这不仅是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需要,也是推动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重要举措。
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框架
(一)跨境服务贸易与负面清单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服务贸易定义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四种提供方式。RTA实践中,服务开放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按GATS四种提供方式以正面清单形式开放;另一种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形式,服务开放包含除“商业存在”之外的其他三种提供方式,“商业存在”被纳入投资章节。采用NAFTA形式的RTA通常以负面清单来管理跨境服务贸易,如《美墨加协定》(USMCA)、CPTPP等。虽然跨境服务贸易也包括部分金融服务等,但由于该部门的重要性,大多RTA会单独成章,另行规定开放规则和内容,因此本文的负面清单暂不包括金融服务。
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是与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相对应的一种管理模式。正面清单模式中,政府列出允许的市场准入主体、范围、领域等,没有列出的原则上属于禁止进入领域,即“法无列明不可为”;负面清单模式中,政府列明不开放的领域,未列入清单的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即“法无禁止皆可为”。
(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国际规则框架
NAFTA是第一个对投资和跨境服务贸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RTA,此后越来越多的RTA开始参照NATFA框架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作为NAFTA的升级版,USMCA的负面清单文本相比NAFTA有较大改进,代表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最新的规则框架。
USMCA第15章为跨境服务贸易,由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组成:正文包含跨境服务贸易定义、适用范围、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当地存在、不符措施等内容;5个附录分别是对快递服务、交通服务等的专门说明。其中,跨境服务贸易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等三种提供方式,同时强调不适用于金融服务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当地存在是与不符措施相对应的4项正面义务。
USMCA第15.7条不符措施规定了负面清单制度,各缔约方在负面清单中列明其跨境服务贸易与4项正面义务中一条或多条不相符的不符措施,并按对缔约方约束力强弱将其分别列入附件I或附件II。其中,附件I为中央和地方层级下现行不符措施,通常包含棘轮条款,即缔约方更新承诺时这些不符措施的限制程度要维持不变或降低,附件II为缔约方可以在未来维持现有措施或采取新限制措施的领域。其中,附件I中每条不符措施包含限制性行业、分部门、不符措施违背的正面义务、政府级别、相关国内法律依据和不符措施具体描述等部分,附件II一般不包括政府级别。
三、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比较
美国是NAFTA倡导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已相对成熟。日本是CPTPP主导国,且在CPTPP和RCEP中均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因此,对美国和日本在FTA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进行比较研究非常必要。
(一)美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践与特征
WTO的RTAs数据库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美国共签署14个FTA,其中13个同时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除与约旦的FTA美国采用正面清单外,其余12个FTA美国均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通过比较这12份负面清单,可以总结出美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数量较少。美国服务业发达,跨境服务贸易竞争力强,对负面清单依赖程度较低。美国签订的FTA中,无论是附件I还是附件II,不符措施数量都在8项或以下。附件I中,除与新加坡FTA和USMCA中分别包含8项和7项不符措施外,其他FTA不符措施都只有6项。原因在于:美国—新加坡FTA涵盖3项针对所有行业的水平不符措施①水平不符措施是负面清单中的一种特定称谓,指负面清单中某一项目的限制针对所有行业,而非特定行业。,其他FTA只包含1项;由于美墨加三国的特殊地理位置,USMCA新增1项独有的陆地运输服务不符措施。附件II中,除美国—新加坡FTA、USMCA分别包含5项和8项不符措施外,其他FTA都是6项。原因在于:美国—新加坡FTA不涵盖水平不符措施,其他FTA都包含2项,即美国—新加坡FTA后,美国将附件I的2项水平不符措施转移到附件II中,并取消了美国—新加坡FTA中1项针对通信服务-有线电视的不符措施;USMCA新增针对陆地运输和博彩业的2项不符措施。
二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涉行业延续性较高。美国FTA签署对象涉及国家和地区复杂,但美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涉行业保持了高度一致性。除美国—新加坡FTA和USMCA所涉行业存在差异外,其他FTA不符措施涉及行业和条数均一致:附件I涉及商业服务(2条不符措施,下同)、航空运输(1条)、运输服务(1条)和专业服务(1条);附件II涉及通信服务(1条)、社交服务(1条)、少数民族事务(1条)和运输服务(1条)。
三是不符措施违背各项正面义务情况基本一致。无论是附件I还是附件II,美国FTA违背正面义务的情况相似。附件I中仅美国—新加坡FTA不符措施涉及市场准入,即美国保留采取或维持不违反GATS第16条规定的义务的任何措施的权利。此后该项不符措施被移到附件II中,因此只有美国—新加坡FTA附件II不涉及市场准入问题,具体不符措施违背证明义务情况详见表1。
(二)日本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践与特征
根据WTO的RTAs数据库,截至2022年8月底,日本生效的FTA共有19个,其中18个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的FTA有9个。通过比较这9份负面清单,可以总结出日本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较多。日本签署的FTA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附件I和附件II不符措施数量平均为42.6条和14.7条,且后期FTA不符措施数量并不比早期的少。相反,最早签署的日本—墨西哥FTA,无论是不符措施数量还是违背正面义务数量均最少,签署时间最晚的RCEP却最多。从不符措施类型看,除日本—瑞士FTA附件I有1项水平不符措施外,其他FTA均不涉及水平不符措施;附件II均有至少2项水平措施,详见表2。

表2 日本现行FTA跨境服务贸易不符措施分布及违背正面义务情况
二是不符措施涉及行业具有一定延续性和集中性,不同缔约对象差异较大。就延续性看,9个FTA中,附件I的汽车维修服务、建造服务、测量服务、医疗健康和福利、采矿业、房地产、房地产评估、航海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相关服务、调查服务、语言能力测试、批发零售贸易等部门都只有1项不符措施;商业服务、收集代理服务、教育及学习支持、船籍服务和专业服务也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其中,收集代理服务、教育及学习支持除与墨西哥、智利签署的FTA中没有不符措施外,其他FTA都有1项;商业服务除与欧盟、英国签署的FTA有2项不符措施外,其他都有1项;专业服务除与墨西哥、智利签署的FTA有11项外,其他都有12项。附件II中,航天业、武装爆炸业、能源业、渔业、信息和通信、安保服务等部门均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除与瑞士、秘鲁的FTA在航天业各有2项不符措施,在能源业各有5项不符措施外,其余FTA在这些行业都只有1项不符措施。
就集中性而言,附件I的不符措施主要集中在专业服务和运输服务。专业服务不符措施最少的有11项,运输服务最少的有7项,是与墨西哥、智利、欧盟、英国的FTA,与秘鲁的FTA和CPTPP都有9项,与瑞士、澳大利亚的FTA是12项,RCEP是14项。附件II中除涉及所有行业的水平不符措施外,其他不符措施集中在能源业和航天业。
就差异性而言,附件I不符措施中,只有与瑞士、澳大利亚的FTA和RCEP涉及农林渔及相关服务(1项)、热力供应(1项)、信息和通信(2项)、油业(1项)、水供应及水务(1项);只有与智利的FTA涉及信用管理和收集商业(1项);只有与墨西哥、澳大利亚的FTA和RCEP涉及安保服务(1项);只有与欧盟、英国的FTA及CPTPP、RCEP涉及航空业(1项);分销服务中,与英国的FTA和RCEP不符措施为1项,与瑞士、秘鲁、澳大利亚、欧盟的FTA及CPTPP为2项;制造业服务中,与秘鲁、欧盟、英国的FTA及CPTPP不符措施为1项,与瑞士、澳大利亚的FTA为3项,RCEP为4项。附件II不符措施中,仅与墨西哥的FTA涉及社交服务(1项),仅与瑞士、秘鲁的FTA涉及制造业(1项),仅与秘鲁的FTA涉及商业服务(1项),仅RCEP涉及视听服务、私人经济、电话销售等(各1项),仅与欧盟的FTA涉及运输服务(1项),仅与欧盟、英国的FTA和RCEP涉及运输服务/商业服务(1项)。同时,仅与墨西哥的FTA不涉及公共执法、惩戒服务及社交服务(其他均为1项),仅与墨西哥、智利的FTA不涉及教育及学习支持服务(其他均为1项),仅与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的FTA不涉及土地交易服务(其他均为1项)。
三是不符措施违背正面义务差异明显,更多集中于市场准入。附件I中,日本不符措施违背国民待遇和当地存在情况差异较大,违背最惠国待遇的情况较为一致,数量较少,附件II的情况基本相似,详见表2。
四、比较视角下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问题
为更好地适应服务贸易开放模式转变,中国最早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尝试以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如《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目前正在制定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将《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美日签署的FTA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进行比较,其异同点详见表3。

表3 美日签署的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比较
(一)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美日等国家签署的FTA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属于国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是与其他国家通过谈判签署的协定的一部分,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仅对签署缔约方生效,负面清单调整需要与缔约方协商,非缔约方不享有同等权利,也无须承担相应义务。无论是《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是《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都是国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是中国政府颁布的在某一区域范围实施的管理与所有贸易伙伴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在国内仅分别适用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二)跨境服务贸易概念一致,涵盖范围存在差别
美日等国签署的FTA中,跨境服务贸易指除商业存在外的其他三种服务提供方式。在清单说明部分,《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明确清单适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等三种服务提供方式,《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强调“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服务的特别管理措施不列入本负面清单”。可见,这些负面清单中跨境服务贸易的概念一致。
从涵盖范围来看,由于金融服务的特殊性,美日等国签署的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包括金融服务,而是将金融服务单列章节,单独规定开放规则和领域。如USMCA第17章是金融服务,CPTPP第11章是金融服务,即便日本在RCEP中以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也是单独确定的。由于是国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没有将金融服务排除在外。
(三)负面清单规则框架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国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都包含两个附件,即附件I和附件II,分别列出中央和地方层级现行不符措施和未来保留进一步限制的不符措施。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只包含一份列出现行特别管理措施的清单,没有明确未来可能保留或加强的限制措施。
其次,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没有列出特别管理措施涉及的正面义务、政府层级和法律法规依据。美日等国FTA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均规定了限制措施违背正面义务的类型,是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还是本地存在,同时各项限制措施均列出相应的国内法规。相对而言,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仅是特征性描述,不仅没有详细的正面义务违背说明,也缺少具体国内法律的支撑。
(四)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数量和内容差异较大
首先,负面清单行业分类差异较大。美日等国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限制的行业部门虽各有侧重,但都重点考虑涉及国家安全、核心技术的行业,注重对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部门实施限制,如航空行业。比较来看,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几乎涉及所有服务部门,《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涉及行业门类分别为13类和11类,不符措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0条和13条),金融服务业(31条和17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1条和12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2条和11条)。美国主要集中在通信服务、少数民族事务、运输服务部门,日本主要集中在专业服务和运输服务。
其次,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条数较多。虽然《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缩减了各门类特别管理措施的数量,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服务业”分别缩减21条、17条、14条,不符措施最终由159条缩减至70条,但相对于其他国家FTA中的不符措施条数依然较多。比如,美国FTA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附件I和附件II)一共仅15条左右,日本FTA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中不符措施数量平均约为57条,虽然与《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数量接近,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说明部分均包含了“兜底”条款。例如,《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文化、金融、政府采购等相关措施”,《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金融审慎、社会服务、人类遗传资源、人文社科研发、文化新业态、航空业务权、移民和就业措施以及政府行使职能等相关措施”,都按现行规定执行。这意味着,除负面清单列出的不符措施外,不符措施还大量存在于诸多现行规定中。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相对于美日等国家FTA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非真正意义的负面清单,不仅在规则框架方面与FTA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存在较大差异,缺乏详细的行业分类、限制措施程度分类、不符措施违背正面义务类型、政府层级和国内法律依据,而且不符措施条目较多,在考虑“兜底”条款后数量更多。这不仅会影响到跨境服务贸易发展,增加跨境服务贸易的管理难度,也无法适应RCEP将正面清单转换为负面清单的要求和中国加入CPTPP谈判的需要。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正在制定全国版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也提出了加入CPTPP的申请,结合国内与国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差异,未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高度重视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工作
从美日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体内容看,各项不符措施所涉行业均保持了较大的延续性,虽然会根据不同FTA签署对象进行相应调整,但总体差别不大。由于首份负面清单内容对后续其他负面清单有极强的参考指导意义,因此中国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极为重要,不仅会为未来中国签署FTA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起“打样”作用,而且能进一步彰显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决心。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早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开放程度过大、限制不足的问题,后续FTA限制程度有一定提升。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服务贸易额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整体竞争力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仍需相对谨慎,要为未来进一步扩大开放预留空间。
(二)负面清单制定与调整要以全面梳理兜底条款为基础
目前,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主要问题就是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面清单,因为除清单列出的不符措施外,现行规定中还存在大量的不符措施,这些措施散见于各类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金融审慎等相关政策法规中。因此,首先要全面梳理这些政策中可能涉及的不符措施,将其作为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的基础;其次要结合现有上海和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内容,确定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包含的全部范围,制定不符措施削减步骤和路径,为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和FTA谈判提供指引。
(三)调整负面清单框架结构,明确不符措施的指向性
相对而言,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结构不完整,应遵循国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对成熟的框架结构,对不符措施的表述不仅要包括限制性行业明细分类、政策层级、国内法依据等内容,还要根据服务业特点和重要性考虑其限制程度差异、违背正面义务类型等。在对不符措施涉及行业进行细分时,美国在NAFTA中同时使用SIC(北美产业分类体系)和CPC(联合国核心产品分类),此后一直使用SIC,其他大部分国家采用CPC,日本和墨西哥则采用本国的产业分类代码。由于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RCEP投资负面清单都使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于已有管理经验,可考虑继续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明确不符措施适用行业的细分代码,使适用行业更具有指向性。
(四)负面清单制定和谈判要坚持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跨境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政府管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经验相对匮乏,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谈判需要在坚持开放的同时保持相应的灵活性。
第一,充分运用两个附件来管理不同行业不同重要程度的不符措施。国际上通常将跨境服务贸易不符措施根据约束力程度分为两大类,形成附件I和附件II,附件I是允许保留的现有限制措施,附件I通常设置棘轮条款,缔约方不得在未来的更新中提高不符措施的限制程度。附件II不但允许维持现有限制措施,缔约方同时保留对相关行业现有限制措施进行修订或设立更严格的新限制措施的权利。因此,附件II中主要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业态增加保留措施,如日本在附件II中更多地增加对本国航天业、能源业和渔业等战略行业以及安保服务、武装爆炸业和公共执法等公共安全行业的保护。因此,中国要充分利用两个附件对跨境服务贸易进行适度保护,尤其需要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金融审慎、民族问题、文化遗产等问题的不符措施列入附件II。
第二,对正面义务的违背要有所取舍。从不符措施对正面义务的违背情况看,日本负面清单较少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不仅体现了对各国平等开放的姿态,也有助于降低负面清单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难度。且相对于其他三项正面义务,减少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对整体限制程度的降低有限。因此,在同时考虑负面清单更简洁和不过分降低限制程度的情况下,可考虑减少违背最惠国待遇正面义务。违背市场准入的措施相对较严格,美国虽然在NAFTA后的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中增加了该项正面义务,但应用较为克制,仅与新加坡的FTA在附件I中有1项措施违背该项正面义务,附件II中最多有2项措施违背该项正面义务。相对而言,日本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较多地违背市场准入正面义务,有效地保护了重要或弱势行业。美国较少违背市场准入正面义务与其强大的服务业竞争力分不开,中国需要通过更多地运用违背市场准入正面义务来保护相对弱势的服务细分行业,为未来的开放预留空间。
第三,根据缔约对象适度调整负面清单所涉行业。在保持负面清单内容延续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缔约对象,需要对不符措施涉及行业和适用领域进行调整。例如,USMCA中美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新增一项独有的针对陆地运输服务的不符措施;日本也根据不同缔约对象调整不符措施的适用领域,如针对热力供应的不符措施,在日本与澳大利亚的FTA以及RCEP中均为同时适用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在与英国的FTA中被移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仅适用于投资领域。同样,中国FTA谈判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需要根据缔约各方在不同服务细分领域的竞争力强弱调整所涉行业、限制程度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