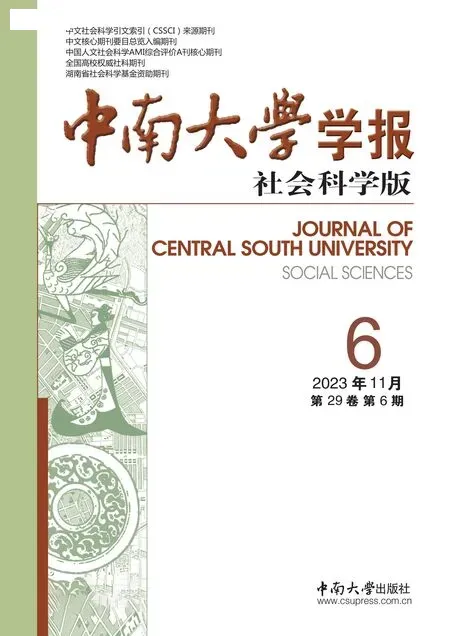现象学视角下“情感认识论”的“现代性”意义
聂建松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36)
谢文郁先生于2017 年在《“敬仰”与“信仰”:中西天命观的认识论异同》一文中提出了“情感认识论”,认为“情感”是一种稳定的认识器官,不仅能够认识经验的对象,也能够认识诸如“天命”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随后,他又写下了《情感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一文对其“情感认识论”的主体、认识对象和命题真值问题都做了系统的阐述。他的理论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其中张俊老师先后写了《儒耶终极信仰该如何比较—— 与谢文郁教授商榷》《情感认识论:一个反现代性的知识学方案》等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两位前辈学者的思想交锋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张老师提出的“现代性”问题。通过重新梳理哲学史,我形成了一个与两位前辈学者皆略微不同的新看法:在众多“情感”之中,尤其是其中的“爱欲”,应当相当于现象学中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那么我们通过参考一些现代哲学家,比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盖勒·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以及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等人对于胡塞尔的理论的反思,或许就可以对“情感认识论”这一问题进行重构,顺便解决在胡塞尔的理论中的一个难以调和的现代性矛盾。
一、从古典的“爱欲”至现代的“意向性”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已经提示“爱欲”和“认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第五卷中就区分了两种人的倾向:哲学家是“与智慧亲近的人”(φιλoσόφoυς),普通人则是“与声音和视觉亲近的人”(φιλήκooι καὶ φιλoθεάμoνες)。柏拉图表示只有前者能够亲近“美本身”(αὐτὸ δὲ κάλλoς),后者则与之无缘,只会关注“各种美的事物”(καλά πράγματα)。二者不同的爱欲倾向也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状态,前者拥有“各种认识”(γνώμην),后者则只拥有“各种意见”(δόξαν)。至于古典晚期更加系统的关于爱欲与认识的学说,我们则可以参考柏罗丁(Plotinus)《九章集》中的《论认识的“各种实在”和其上的存在》(“Περί τῶν γνωρίςτικῶν ὑπoστάσεων καὶ τoῦ ἐπέκεινα”)对《斐德罗篇》的“马车喻”的诠释:灵魂的“主体”(τὸ κύριoν)存在于“精神/感觉”这两股好坏力量之间,因此凡人沉溺在感觉和欲求中,而哲学家则能保持在精神阳光的沐浴之下[1](V.3.9.5-10)。柏罗丁认为后者的灵魂要比前者更为根本,因为人类灵魂本身就有“要把握精神的观视的渴望”(τό γε πoθoῦντες λαβεῖν θέαμα τoῦ νoῦ.)[1](IV.3.12-13)。Lloyd Gerson 认为这两类爱欲与两类认识活动相对应,即灵魂对身体的爱欲对应其感觉活动,而灵魂对精神的爱欲则对应其精神活动[2](136)。Dimi trios A.Vasilakis 更是指出,柏罗丁所谓的爱欲就是“灵魂”自我构成的活动,以及低级存在对于高级存在的追寻,二者都表现为对精神的沉思[3](41)。因此,在柏罗丁的理论当中爱欲与认识是密不可分的。不过,我要强调的不只是这二者之间的统一性,而是这背后蕴含的一个逻辑,即灵魂在进入身体之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存在,它天然地就与精神世界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故而在进入身体之后,灵魂仍然会保持着对于精神世界的“爱欲”,因此它才产生了朝向精神世界的冲动(ἔφεσις)。从这个角度来说,灵魂对于精神世界的“爱欲”是先于其认识能力的,并且也是它的出发点。
按照Dmitri Nikulin 的看法,柏罗丁的认识论一直延续到了笛卡尔[4](146-170)。从整体上来说,笛卡尔同样也是将灵魂先在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他也认为人的灵魂是“神的形象和相似”(imaginera& similitudinem Dei)[5](VII.51,57),并且灵魂是先于身体的存在①,故而灵魂也可以被称为精神(mens/animus)、理智(intellectus)和理性(ratio)[5](VII.27),而其最基础且最初的精神活动就是对自我的“认识”(connoître)[5](VI.33)。但从应用术语的细节上来说,笛卡尔没有如同柏罗丁一样使用爱(l’amour)去描述那种认识的冲动,而是继承了奥古斯丁对“意欲”(voluntas)的使用②。他认为意欲有两类:一类作用于灵魂,它由“感知”(perception)所引发并控制着精神(pensée)朝向非物质的存在(如神或者灵魂自身);另一类则作用于身体,它由身体对外界的感知和“情绪”(passion)所引发[5](XI.343)。
随后,胡塞尔又通过对笛卡尔认识论的反思开启了现代的现象学。他批评笛卡尔将“自我”视为“思维着的实体”(substantia cogitans)或者独立的“精神”(animus),认为应当将所谓的“心灵生活”(Seelenleben)统统排除在外,由此还原出一个先验的“唯独的自身”(solus ipse)。既然“自我”是先于“我思”(cogito)的,那么“我思”就不是“自我”存在的证明,而是“自我”朝向“思考对象”(cogitatum)的意识,即“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6](13)。从这一角度来说,胡塞尔的“意向性”与柏罗丁的“爱欲”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是先于各种具体的认识活动而存在,而且各种具体的认识活动都是建立在它们之上的。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柏罗丁的“爱欲”是基于一种“灵魂先于身体存在”的古典灵魂观,而胡塞尔则出于其“无神论”的信念放弃了对认识主体的本体论构建。不过,梅洛·庞蒂在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时候就提出了人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亲密无间的,但胡塞尔却将认识主体视为是纯粹的精神体,将之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7](9)。因此,如果从这个批评角度来看的话,胡塞尔的认识主体倒与柏罗丁的灵魂有几分相似。
此外,胡塞尔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修正为“我生即我在”(Ich lebe:cogito),并且指出了“意向性”构成“自我”的生命本质[8](97)。这一看法也被Dmitri Nikulin 认为是与柏罗丁的认识论不谋而合的,因为柏罗丁也认为认识主体必然是先有(灵性的)生命才会表现出(朝向精神的)“爱欲”,进而才会表现出其认识能力[4](152-157)。
二、对笛卡尔的“爱欲”的剥离的反思
虽然谢、张两位前辈都不否认现代意义上的“情感”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知觉活动,但是古典时期的“爱欲”(ἔρoς)却不仅仅是一种与身体相关的情感。在柏拉图的笔下,他谈到了两种不同的爱欲:一个是拥有“神”的身份的美神之子(《斐德罗篇》242d-e),另一个则是贫乏神与丰饶神所生下的“精灵”(《会饮篇》203b-e)。此二者又被认为是与柏拉图笔下的两位“美神”相对应的,即天上的美神和“世俗的”(πάνδημoς)地上美神(《会饮篇》108d-e)。在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的诠释中,这两位“美神”象征着不同状态的灵魂:前者指纯粹的灵魂,后者指进入身体的灵魂。这两类灵魂有着与之相配的两类“爱欲”:前者拥有纯粹的精神爱欲并追随着天上的无形之美,后者则有身体的爱欲并追求着地上的物质之美。从现代的定义来看,后者的爱欲与身体上的情感更相似,前者则可以被定义为是后者的“原型”。
按照这一类的古典哲学观念来说,灵魂是先于身体的存在,故而其本质当中并不包含肉体的情感,但是灵魂拥有某种近似于“情感”的精神活动,即纯粹的精神爱欲。笛卡尔打破了这一从柏罗丁到奥古斯丁的观念思路,他将爱欲(l’amour)降格为一种身体上的情感[5](II.79),从而将“爱欲”逐出灵魂的最初状态之中,因为他认为灵魂本身是一个纯粹的“思维的存在”(res cogni tans),故而其存在之中应当是不包含任何情感或者情绪的。胡塞尔虽然将“生命”重新引入“自我”当中,但他也未将“爱欲”重新拾起,因此他应当是认同笛卡尔对于爱欲的定义。
笛卡尔将爱欲剥离出灵魂的理由在于,爱欲是一种身体的情感,而情感是由灵魂进入身体之后所引发的次生品,因此情感是要被排除在纯粹的精神活动之外的。不过,这背后是有一个哲学前提的,那就是从柏罗丁至笛卡尔的哲学家,他们都认为灵魂是先于身体的独立而存在的,因此“自我”才有可能成为不受到身体感染的纯粹存在[9](41)。但是胡塞尔出于对其立场的坚持,以及对于“纯粹的自我”(reinen Ich)的坚持,反而让其“意向性”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学说:它一方面身处于物质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必须是与之相隔的纯粹精神活动。梅洛-庞蒂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矛盾,即胡塞尔希望以“不参与的方式”(ohne mitzumchen)注视世界,可事实上我们却是在世的存在,而非超凡脱世的精神体[7](10)。
对于笛卡尔和胡塞尔的反思也正是由此开始的。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就认为,笛卡尔和胡塞尔都遗忘了“自我”存在的哲学前提,那就是“自我”是与身体等价的,只有拥有身体才能拥有自我[10](127)。马里翁也认为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笛卡尔在构建自我的时候排除了“一种爱欲方式的调和”(la tonalité d’une disposition érotique),而他则希望达成一种“爱欲之中的理性”(une rationalité érotique)[11](14)。我们可以看到,马里翁正是希望借助古典“爱欲”概念的特殊性(作为横跨身体和精神两个领域的存在[12](49-52)),去打破笛卡尔对于精神和身体的分离,并进一步解决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中的内在矛盾。
三、对爱欲和情感的现象学重构
在马里翁之前,米盖勒·杜夫海纳就已经开始将情感和意向性联系起来了。他认为感觉(feeling)是对一种情感的品质(an affective quality)的了解,并且情感不是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而是作为客体的属性来被主体所感受的。因此,情感的对象虽然不完全是客观现实的,但也是为了主体存在的客体。客体只有通过情感才能够成为一个被主体感觉到的存在,而主体也只有在此之中才能完善“自我”,因此情感反而是“先验的”(a priori)。杜夫海纳认为知觉有两种意向性:一种是普通的知觉;另一种则是对知觉的知觉,即美学的知觉。前者联系着自身和外物,后者则属于“深层的我”,即由情感构成的“自我”[13](480-485)。杜夫海纳认为,“美”就是“感觉者”在感觉“被感受者”的时候所体验到的完满,这种“完满”就是指“深层情感”,它构成了一个与现实相关却不相同的“美的世界”。不过,在我看来,杜夫海纳仍将“美”局限在感觉范围之中,因此他也没有突破笛卡尔对“爱欲”的规定。他也谈过“爱欲的诞生”的柏拉图神话,但他认为美应来自“丰饶”而非“缺乏”[14](62)。这恰好证明了他与笛卡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立场上是颠倒的。
马里翁的“爱欲的意向性”理论的灵感源自列维纳斯的理论。列维纳斯批评胡塞尔的“意向性”隐含着笛卡尔的“无限”观念(即“意欲”是上帝的形象),但真正的“无限”应当属于“他者”(Autrui),意向性本身不是无限的,而应当是介于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存在[15](37)。既然人作为意向性的发出者其本身是身体的存在,那么他必然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而他的意向性则是朝向无限的世界的。不过,这种意向性不是胡塞尔拒绝了对自我进行“自然主义”解释之后的“纯粹的意识”(reinen Bewusstsein)[16](103),而是一种由身体的“自我”向外发出的“爱欲”。
马里翁认为,哲学家们如今对于现象和主体发出的意向性之间的关系只设想过“匮乏”和“相等”,但没有设想到还存在“超越”(surpasse)的第三种关系,即超出意向性的“充溢现象”(phénomène saturé)。简而言之,“充溢现象”在以下四个方面都超出了有限的意向性:其“量”体现为意料之外;其“质”体现为超出感性视域的显现;其“关系”(relation)体现为身体和精神的先后关系,即人的身体是在被影响(s’effecte)之后,“自我”方才能够继续感觉(affecter)后来的内容;其“模态”(modalité)体现为一种迎面而来的“面容”(visage)或者“圣像”(l’icône)[17](89-92)。这四者之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第三点:既然“充溢现象”超出了意向性之外,那么“自我”也就必然处于身体之中,对外的求索也只能是基于身体的“爱欲”,而非纯粹的意识。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马里翁的“爱欲”并不是参考了柏罗丁一脉的理论,他应当参考的是“伪狄奥尼修斯”(Psuedo-Dionysius)的理论④。伪狄奥尼修斯的爱欲理论不同于柏罗丁一脉的古典理论在于两点:其一,伪狄奥尼修斯主张“感觉爱欲”(ἔρoς)与“精神爱欲”(ἀγάπη)是一体的,他反对柏拉图式的二元爱欲学说;其二,他更强调一种“神性的爱欲”与人类的认识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二者集中体现在伪狄奥尼修斯的“象征神学”(Symbolic Theology)的思想当中。在伪狄奥尼修斯看来,人的灵魂的爱欲运动有三类:前二类是类似于柏拉图的二元爱欲,分别朝向身体和精神[18](709a-713c);第三类则较有特色,灵魂能够降入“感觉”去寻找已经“延伸”(ἐκτείνεται)至其中的精神[18](816b)。柏罗丁认为灵魂在感觉中无法找到精神,因此指向精神的活动需要屏蔽“感觉”,但狄奥尼修斯氏则认为这样的方式反而能更好地刺激灵魂的精神活动[19](1103c-d)。这一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前文提到的“至一/神”的不同看法:柏罗丁不认为“至一”或者精神会下降到物质世界,伪狄奥尼修斯则认为“至一之神”会对物质世界发起充满爱欲的行动(ἐνέργεια),即神会按照符合观看者的“尺度”(ἀναλoγία)显现[20](180c),因此人类是能够通过对可感的“象征”进行沉思(θεωρία)感知到其中蕴含的不可感的精神的。
我认为伪狄奥尼修斯的爱欲理论从两个方面为马里翁的“爱欲现象学”理论提供了支撑:一是通过将灵魂中的两类爱欲合一,马里翁将“身体”重新引入到“自我”当中。二是通过将世界视为神圣的主动的爱欲显现。马里翁可以将一个无限的“大他者”重新引入,并且创造出一种双向的凝视,即人可以设想来自他者的凝视来对抗人类自身的凝视。在这种双向凝视的交错中,人类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克服对“偶像”的单向的不良偷窥欲,而将他人和世界视为迎面而来的“面容”(visage)或者“圣像”(l’icône),而非是肆无忌惮的窥视对象。
四、“情感认识论”的现象学意义
杜夫海纳和马里翁都向我们展示了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反思,并且将“情感”和“爱欲”重新又引入认识主体当中。这种重新引入与谢、张两位先生的争论不完全是同一个轨道的事情,两位先生的争议在于情感究竟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认识或者知识。准确地说,这样的讨论谈不上是现象学的方式,因为现象学的方式是从认识主体和其意向性出发的。张俊老师虽然提到了现象学的方法,但是受限于篇幅,他没有充分论述现象学的发展。我认为至少按照梅洛-庞蒂开启的“知觉现象学”的现代路径,肯定是不能再回到将认识主体视为是胡塞尔式的“纯粹的自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将认识主体视为是具有身体的存在。因此,我认为谢先生的“情感认识论”虽然受到了张老师的批评,但也有正逢其时之处和可取之处,那就是他将身体和情感重新领回到认识主体之中,故而“情感认识论”或许可以沿着如下的路径继续发展。
首先,如今对于笛卡尔和胡塞尔式的认识主体的批评其实已经不再局限于哲学理论的思考,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就从心理学和生物学上对此提出过批评,他认为在人的心理当中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理性状态,而笛卡尔哲学所谓的认识主体的理性状态仍然是一种“情感”。达马西奥认为情感可以分为基本情感和次级情感:前者基于我们的本能;后者则包含了更加复杂的认知功能。次级情感具有理性或者说理性也是一种次级情感的状态,理性不应是“无情”(ἀπάθεια),而是顺从、服从和维护自尊等情感内驱力的结果[21](106-115,152,200)。虽然从柏罗丁至胡塞尔都将理性和情感视为是相异且相斥的存在,但是生物实验却表明次级情感与基本情感实则出于同一生理通道[21](112),因此“情感”是认识主体不可能摆脱的必然要素。这可以说明人的意向性的本质应当是“情感”或者“爱欲”的,我们无论是在理性状态下还是在激情状态之下探索世界,其实都是处于一种情感之中。譬如,儿童具有生理性的嗜甜并且本能地反感酒精刺激,但成人则可以陶醉在美酒中去寻找复杂的甜味。成人不是感受不到烈酒的刺激,而是他能克制由酒精对舌头和鼻腔的刺激所引发的生理反感(基本情感),享受其背后蕴含的复杂风味(次级情感)。
其次,如同前文中的马里翁所说,我们一旦将身体认定为“自我”的基础,那么就等于打破了胡塞尔式的超然自我,也就等于承认在“身体的自我”之外必然存在“他者”,因为凡具有身体者必然是有限的存在。不过,马里翁这样的理论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既然“自我”是有限的,那么就需要说明超出“自我”之外的充溢现象是如何拥有综合统一的秩序。从马里翁所参考的伪狄奥尼修斯的古典哲学理论来看,最大的“他者”(神)会在人类的感官里呈现为“美”,它将自身全都“慷慨地给予”(ἐπιδίδωσιν)了物质世界[18](664a-c),因此物质现象的“秩序”(τάξις)就是其神性的形上之美的展现③。我们当然不需要恢复这样的古老立场,因为曾作为形上之美的内容在如今已经失去了资格[22](6)。可我们若做一次反向思考,其实仍然能够通过现象学的方式发现其踪影。胡塞尔虽然将“显现的世界”(Die erschein ende Welt)的形而上学前提进行了悬搁,但是他也没否定现象的“秩序”的客观性,只不过他不认为这种客观性超出了自我的范围之外。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如果按照马里翁的方式去承认自我是身体的,那么也就等于直接恢复了自我之外的“他者”,也就不必同笛卡尔和胡塞尔一样试图建立一个上帝一般的无限“自我”,然后试图在它当中解决一切的认识论问题[15](39)。
最后,爱欲或者情感的意向性也不一定就影响由此得来的知识的客观性。这一概念是意在说明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总是难以避免身体带来的局限。为此,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位受到伪狄奥尼修斯影响的哲学家费耶拉本德(Paul Feyerabend)的理论。他就认为知识的对象乃是各种“展现的实体”(manifest reality),而这些实体都属于一个“最终实体”(Ultimate Reality)[23](314)。这一“最终实体”不能简单地被悬搁,因为其本质拒绝被简单地界定,它所流露出来的只有“行动”。虽然为了避免落入庸俗的智能设计论可以悬搁其“神圣的爱欲”(我们可以不相信其行动是有意图的),但是依旧很难否认我们的科学活动是建立在其行动之上的,而非仅凭我们自身的思考[23](233)。令费耶拉本德感到遗憾的是,尽管“最终实体”的行动引发了极为丰富的现象,但是科学一元论的简单还原法却过滤掉了大部分,只保留符合其观念的一小部分[23](315)。鉴于他与马里翁之间的思想亲缘关系,我认为完全可以借鉴他的理论来解释马里翁的“充溢现象”,即“最终实体”向众人无差别地展现出了“充溢的现象/美”,但个人却只是根据自身的“爱欲”接受属于自己的“侧显”(Abschattung)[24](81)。
这样一种理论实际上没有否定世界作为一个大“他者”的客观性,只是说我们每个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如果我们将马里翁的“爱欲的凝视”认定是来自世界的,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反过来成为凝视我的存在,并且由此体现出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天命”或者“神意”(πρόνoια)。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成为“经验中的超出经验者”,因为基于有限的人的构想必然受限于其经验,但“全体”又远超了其经验的范围,而一旦“世界”引发了意外就需要人们以“理性”的情绪来安抚自身。其他类型的“侧现”的意义也可以赋给全体,譬如爱因斯坦就视之为是无情的“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创造者”,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世界”其实始终都是“次级情感”的对象。如果我们从这样一种现象学角度出发去看待情感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必如同两位先生一样去争论情感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更应当去说人类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怀有一种情感。
综上所述,我认为通过对谢先生的“情感认识论”进行现象学重构,可以从中发现至少两点现代性的意义:一是它提示我们应当将人视为是身体的存在,而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存在。这不意味着要将人降格为动物,相反是要说明,即便是“理性”,也是一种情感状态。二是它应当表明人是有限的,“他者”不能被简单地还原至只有“自我/表象”的纯粹环境中,因此现象只能给有限之人,而“自我”只能是其“沉浸者”(l'adonné)[17](89)。正是由于“自我”是有限的,故而人对世界的“全体”(τό πᾶν)的理解就只能依赖其自身所见的“侧现”。由此观之,我认为谢先生开启的“情感认识论”其实蕴含了一种现象学上的可能性,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足以成为胡塞尔代表的现代哲学的有力批评者。借着对“爱欲”的笛卡尔式的剥离,我们虽然可以认识到人类是超越本能的存在,但是这也是对人的“非人化”的改造,并且会鼓动他去僭越“世界”的位置。总而言之,我认为谢先生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现代意义就在于抵抗对“爱欲”的剥离,将人的本性恢复为是身体的“爱欲”的存在,而且他是在对“他者”的爱欲中建立自身,而非仅仅爱欲其自身。
注释:
① 更准确地说,笛卡尔采纳了奥古斯丁类似的关于anima/animus 的区分。他也认为animus 是不包含身体的灵魂,而anima 则包含了身体和物质的含义。参见《笛卡尔全集》(OeuvresdeDescartes)一书中的III.362、VII.27 和VI.33.
② 奥古斯丁的理论虽不同于柏罗丁,但也有继承他的方面,除了意欲一词,他也使用过“爱”来描述灵魂的认识能力,譬如他就说过“因为精神若不能辨识自身,那么它则不能够爱自身”(Mens enim amare se ipsam non potest,nisi etiam noverit se),也说过精神“在认识自身之前就爱其自身”(se amat antequam noverit)。参见他的《论三位一体》(DeTrinitatelibriquindecim)中的IX.3.3.和XI.343.
③ 狄氏引用《罗马书》1:20 来说明物质世界是神性之美的力量的展现。参见《论神名》(DeDivinisNominibus)的592b 和700c。
④ Sarah Coakley 和Charles M.Stang 在二人合著的《重思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Re-thinkingDionysiusthe Areopagite)的216—222 页中,详尽介绍了马里翁是如何通过巴尔塔萨转向狄奥尼修斯氏的学说。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