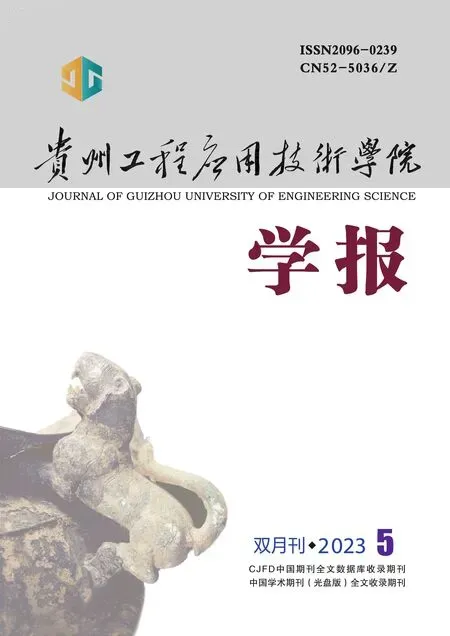事例确证理论的建构与问题
段天龙
(南京大学 1.哲学系,2.当代智能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确证理论”(confirmation theory)不仅是现代逻辑在科学哲学中应用的典范,更是当代形式知识论的核心议题。这一理论主要探究证据(E)“是否”或“多大程度”对科学假说(H)具有“证据性支持”关系,从而形成了定性和定量两条研究进路。
定量研究以“贝叶斯确证理论”(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ies,BCTs)为主要代表。该理论通过概率函数对认知主体的信念进行建模,并将确证度解释为H 在面对E 时所获得的可信度的提升。随着BCTs 的出现和成功,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确证的定性维度的研究已经过时。然而,BCTs 很难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确证理论。首先,BCTs不能描述量子力学之前物理科学中非概率的确定性论证的结构;其次,包括“信念函数理论”(Dempster-Shafer theory,D-S)[1]和“排序函数理论”(ranking function theory,RF)[2]等在内的所有基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主观认知态度的定量确证理论,都不能有效解释BCTs所面对的诸如“为何科学实验结果往往构成特定理论主观上令人信服的证据”等基本问题[3]728;再有,“要确定经验证据对某一假说给与多大程度的支持,首先要知道该证据是否构成该假说的支持性或确证证据”[4]38。所以,对H和E之间定性的逻辑研究——用精确的逻辑语言为确证概念构造明确的定义—仍然必不可少甚至更为根本。
确证理论的定性逻辑研究主要有两大传统[3]727:“假说-演绎主义”(Hypothetico-Deductivism,H-D)和“事例确证理论”(instance confirmation theory,I-C)。H-D最初被看作科学发现的方法,后被改造为科学确证的方法,当代事例确证理论就是在批判H-D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事例确证理论的假说-演绎雏形
二十世纪初,作为科学发现方法的H-D被逻辑经验主义者改造为一种科学确证的方法。[5]这一方法的最初版本记为H-D1:
H-D1:E确证H,当且仅当:(i)H├E;(ii)⊬E。
然而,H-D1甚至无法说明最常被讨论的确证关系。由于∀x(Ax→Bx)⊬Aa∧Ba,所以根据H-D1,形如“Aa∧Ba”的观察报告不能确证形如“∀x(Ax→Bx)”的假说。而这显然有悖于日常的“枚举归纳”(induction by enumeration)直觉:
所谓的归纳推理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从特例到一般性假说的过程,其中每个特例都是一个“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特例符合一般性假说,并因此构成了该假说的确证证据。[6]5
可见,H-D的任何精确构述都应该允许某概括的事例确证该概括,吉姆斯(Ken Gemes)将这一要求称为“事例确证问题”(the problem of instance confirmation)。[7]即便我们认为Aa∧Ba确证∀x(Ax→Bx),对于Aa ∧Ba 和∀x(Ax→Bx)来说,二者之间既不满足∀x(Ax→Bx)├Aa ∧Ba,也不满足Aa ∧Ba├∀x(Ax→Bx)。我们该如何在Aa∧Ba和∀x(Ax→Bx)之间建立演绎关联从而刻画确证概念呢?基于经典逻辑,有两种可能的基本模式:
(a)因为∀x(Ax→Bx)├Aa→Ba且Aa∧Ba├Aa→Ba,所以Aa∧Ba确证∀x(Ax→Bx)。
(b)因为Aa∧∀x(Ax→Bx)├Ba,所以Aa∧Ba确证∀x(Ax→Bx)。
事例确证理论的提出者亨佩尔(Carl Gustav Hempel)选择了模式(a)而非(b)作为构建I-C 的基础。在谓词逻辑中,由于全称量化条件句没有存在含义,&x(Ax→Bx)⊬Aa∧Ba,如果前提中引入Aa,即预设&Ax,会有xAx∧∀x(Ax→Bx):&xBx。也就是说,在模式(b)中,E被划分为前提和结果两部分,并预设&前提成立,再通过前提和H共同演绎得到结果。由此不难发现:(i)模式(b)在证据中体现出一定的历时性,从而更符合尼科徳(Jean Nicod)在《几何与归纳的基础》[8]一书中对确证条件的原始表述——“对于形式为‘所有的A都是B’的假说,当在A发生的情况下B也发生时,那么该假说被确证”;(ii)由于证据被划分的两部分在确证关系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模式(b)也不自觉地从形式上体现出一种“三元”确证关系。正是基于上述特征,假说-演绎主义者提出了H-D2,通常被称为“预测标准”(prediction criterion,PC):
PC:E确证H,当且仅当:(i)E≡E1∧E2;(ii)E1∧H├E2;(iii)E1⊬E2。①
亨佩尔认为,PC虽然可以作为确证的充分条件,却太狭隘且会导致确证的(恶性)循环定义。而相较于狭隘性,循环性似乎是不能容忍的。为此,亨佩尔精心构造了一个假说H1“(x)[(y)(R1(x,y)→(z)R2(x,z)]”。亨佩尔认为,在依据PC确证H1之前,需要先确证H2“(y)R1(x,y)”。因此,我们在使用PC时就已经使用了确证概念,从而确证定义在这里是循环的。然而,如梅里尔(Gary H.Merrill)所指出的,PC是通过明确地“基于某条件”来凸显确证的基本特征的。所以,如果要根据PC说明对H1的确证,固然需要以对H2的接受为前提并且整个过程将是递归的,但基于对H2的接受,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对H1的相对确证。再者,对H2的接受基于类似{R1(a,b),R1(a,c),......}的观察报告,此过程并不需要H1的参与,因此并不存在循环。所以,如果亨佩尔的控诉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将得到——所有的递归定义都是循环的——这样荒谬的结论。[9]
不难看出,亨佩尔之所以指控PC具有循环性,根源于他坚持认为“确证应被视为表示证据和表示假说的两个语句之间类似于逻辑后承关系的二元关系”[6]22。也就是说,亨佩尔没有“相对于T被确证”的直觉,而这种相对确证的概念通常与三元确证关系相伴随。如此一来,亨佩尔拒绝(b)而选择(a)作为构建I-C的基本模式就不足为奇。
二、亨佩尔的满足性标准事例确证理论
基于模式(a),亨佩尔借助于“展开”实现了对事例概念的形式说明。在模式(a)中,亨佩尔将Aa→Ba 称为∀x(Ax→Bx)在Aa∧Ba 所提及的对象类{a}上的展开,将Aa∧Ba 称为∀x(Ax→Bx)的事例。将H在E所提及的对象类{a1,......,an}上的展开记为dev(H,E),则dev(H,E)递归定义为:(i)如果H不包含量词,那么dev(H,E)是H 本身;(ii)如果H 的形式为¬ψ,那么dev(H,E)是¬dev(ψ,E);(iii)如果H 的形式为∀xψ,那么dev(H,E)是合取式dev(ψ[a1],E)∧......∧dev(ψ[an],E);(iv)如果H 的形式为xψ,那么dev(H,E)是析取式dev(ψ[a1],E)∨......∨dev(ψ[an],E)。如此一来,观察报告E是H的事例,当且仅当,E蕴含H 在E 所提及的对象类上的展开。亨佩尔关于确证的“满足性标准”(satisfaction criterion,SC)进而可以表述为:
SC:E确证H,当且仅当,E├dev(H,E)。
之所以称为满足性标准,是因为它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某假说在观察报告所提及的对象的有限类上被满足,那么该假说被给定观察报告所确证。”[6]37这样,亨佩尔将E与H之间的确证关系转换成E和dev(H,E)之间纯粹句法上的逻辑后承关系。这不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演绎主义诉求,也避免了H-D所面临的一个典型难题,即“非相干合取问题”(the problem of irrelevant conjunction)。为了更深入地说明亨佩尔的事例概念,本文将这一问题细分为“非相干假说合取问题”和“非相干证据合取问题”。
(一)非相干假说合取问题
对于PC来说,非相干假说合取问题(该问题与“包含有新颖参数的假说如何被确证的问题紧密相关”)是指:如果已获知H被E所确证,那么根据PC,H∧∀xCx也将被E确证,而C可以是任意不出现在H中的谓词。但根据SC,E不确证H∧∀xCx。因为E不衍推H∧∀xCx在其所提及的任何对象类上的展开,也就是说E并非H∧∀xCx的事例。因此,与H-D相比,格兰莫尔(CLak GLYmour)认为SC更接近于抓住E和T之间的结构关系,是理论检测的核心。[10]
值得一提的是,非相干假说合取不仅是H-D确证理论的核心困难,也是贝叶斯确证理论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在贝叶斯确证语境中,非相干假说合取问题体现了贝叶斯确证标准——数据E确证假说H当且仅当Pr(H|E)>Pr(H),即数据E确证假说H当且仅当H在给定E时的条件概率超过其先验概率——和日常直觉之间的冲突:对于每一个被数据E确证的假说H 来说,我们可以给H 缝合一个未被E 确证的、概率上独立于H和E∧H的假说H`,这样H∧H`根据贝叶斯确证标准也被E确证,但H`有可能和E不相干。也就是说,确证达尔文进化论的数据也将确证达尔文进化论和神创论的结合,这似乎非常违反我们关于真实确证(genuine confirmation)的基本直觉。
(二)非相干证据合取问题
菲特森(Branden Fitelson)认为由SC 可以得到“单调性条件”(monotonicity condition,M)这一推论:如果E确证H,那么对于任意K,E∧K确证H,前提是K不能提及任何在E和H中都没有被提及的个体常项。[11]M中的前提是必要的,因为根据枚举归纳直觉,任何关于新的个体常项的观察报告不仅与已有观察报告一致,而且存在否证假说的风险。令E为“Aa∧Ba”,H为“∀x(Ax→Bx)”。根据M中的前提,K 不能为“Ab∧¬Bb”,这样就合理地避免了“E∧(Ab∧¬Bb)确证H”的情况。然而,M 仍然过于宽松。根据M 中的前提,K 可以为“Ca∧Da”。根据M,E∧(Ca∧Da)确证H,但此时K 和H 明显是非相干的。如果我们像要求假说那样也要求证据在确证关系中没有多余部分,那么可以将这种状况称为“非相干证据合取问题”。显然,SC将会面临这一问题。因为SC和M一样,都只对个体常项而没有对谓词进行限制。如果我们对M再增加一个限制条件——“E中不能出现任何在H中没有出现的谓词”,那么SC可以避免非相干证据合取问题。
区分并强调非相干证据合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法案件中要求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是相干的,对案件事实具有某种实际意义。反之,与案件无关的事实和材料都不能成为证据。也就是说,证据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是否相干以及相干的强弱程度。在具体案情分析中,我们需要指认出构成违法犯罪事实的确切证据,即被指认的证据对于案件事实来说既是充足的也应该是不冗余的。在确证理论语境中即是说,作为证据的数据不仅应该足以能够使得假说得到确证而且相对于假说不存在不相干的部分。
无论如何,由于确证关系是垂直的,即“H受限于实质上出现在E中的个体常项的集合”[3]731,SC天然地避免了非相干合取问题。但这种避免是以切断假说之间或证据之间的横向关联为代价的,从而致使其具有一个根本的局限性——不允许对其词汇超出证据词汇的假说的确证。
三、格兰莫尔对满足性标准的修正
考虑这样一个场景:令H为“法国国王会骑自行车”,E为“亨利会骑自行车”;但即使我们知道“法国国王就是亨利”,也无法根据SC得到E确证H,因为SC只适用于不带等词的一阶语言。在解决SC的根本局限性之前,格兰莫尔首先扩展了SC所基于的一阶语言。亨佩尔的确证条件等价于以下形式:
满足性条件:如果在任何结构
其中,E 是一致的、无量词的语句;D 是定义域,f 是函数;f 用Dn的子集取代语言中每个n 元谓词符号,并将每个个体常项固定到定义域的一个元素上。“正如亨佩尔所做的,只承认满足性条件下的个体常项是可能的,却不切实际地狭隘,似乎更好的做法是允许我们的证据和理论既可以描述个体,也可以命名它们。”[12]129为此,格兰莫尔将分析扩展到带等词和描述算子i 的一阶语言。当然,在传统描述理论中,通过:I(ix L(x))#&x(L(x)∧(&y(L(y)“y=x))&I(x))可以消除算子i。也就是说,引入描述算子i 并不是必要的。但对于格兰莫尔来说,一个语句中有较多的术语总比太少要好。如此一来,不仅“等值条件”(equivalence condition,Eq)被自动满足,满足性条件也可以修改为下述更一般的形式:
满足性条件*:如果在任何结构
至此,I-C能够方便地在带等词的一阶语言中进行分析。而相较于一阶语言,以方程式形式表示的科学假说似乎更为常见。因此,格兰莫尔使用“量”和“量的值”等概念定义了满足性条件*中的基本术语:量指的是开原子公式,例如P(x)、B(x,y,x)等;量的值是与量具有相同谓词的原子语句或其否定,或者是用个体常项或定义描述替换量中的变量而获得的语句,例如P(a)、P(b)、¬P(a)、P(ixG(x))都是P(x)的值;说两个量是相等的,当且仅当它们具有相同的一组值。在此基础上格兰莫尔使用计算②一并代替了亨佩尔的衍推和展开:如果Qi表示出现在H中的量,那么在E上相对于理论T对Qi值的计算,便是作为T的后承的一个语句Ti;如果在计算中使用的所有假说都是T的后承,就说该计算使用了T。有了满足性条件*和计算概念,格兰莫尔基于三元确证关系提出了以下满足性标准*:
SC*:根据满足性条件*,在E上使用T计算得到的H中的量的值确证H。
比较SC和SC*不难发现,在亨佩尔理论中,事例是通过实验或观察直接获得的报告。但在格兰莫尔理论中,事例是一个量值集,它由给定的初始数据的值(E1)和在初始数据集上相对于T计算得到的其他出现在H中的量的值(E2)共同组成。也就是说,格兰莫尔所说的“E相对于T确证H”,实际上可精确表述为“E1相对于T计算出E2,E1∧E2确证H”;对于事例“E1∧E2”与H之间的关系,格兰莫尔只是模糊地使用“事例与假说相符(accord with)”来表示。③如果使用亨佩尔的术语,则相当于“事例衍推假说在事例所提及的对象类上的展开”。所以,本文认为SC*也可以表述为:
SC*:E相对于T确证H,要求:(i)E1∧dev(T,E1)├E2;(ii)E1∧E2├dev(H,E);(iii)E≡E1∧E2。④
如果E2=∅,那么SC*将坍塌为SC。可见,亨佩尔理论只是格兰莫尔理论在“假说词汇没有超出证据词汇”时的特殊情况。
四、格兰莫尔的拔靴带事例确证理论
SC*通过语言扩充使得以受限语言陈述的证据能够检验、确证以更广泛语言陈述的假说,从而克服了亨佩尔事例确证理论的根本性缺陷。在此基础上,格兰莫尔对SC*进行限制,这些限制与SC*共同构成了他所谓的“拔靴带条件”(bootstrap condition,BS)。
在SC*的基础上,格兰莫尔认为这样一些确证情景应该被拒绝:(i)在以方程式形式表达的理论中,对于假说A=B,设A是可直接观察的实验量,B是理论量。我们可以先确定A,再通过A=B确定B。但认为由此得到的A和B将确证A=B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无论A具有怎样的值,都不可能相对于A=B而计算得到A=B 的一个否定事例;(ii)在一阶语言中,根据SC,¬Ra 确证∀x(Rx→Bx)。但在格兰莫尔看来,这种确证关系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3]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借助于“分析真”而构建的确证关系一样是平凡的,因为不存在Rx的值可以计算得到∀x(Rx→Bx)的否定事例。此外,任何数据都不能确证重言式假说,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否定事例。所以,为了检验假说,我们必须能从给定的初始数据中计算得到H的否定事例。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一种使假说(暴露于)有被证伪的风险的方法,数据才能被视为是支持假说的证据。如果我们事先就知道收集数据的过程确保了数据符合假说,那么我们通常不会认为数据支持该假说”[14]。这一思想通常被称为“可证伪性条件”(the falsification condition,FC):
FC:初始数据的值集E相对于理论T而检测假说H的必要条件是,存在初始数据的可能值集E`,在其上使用T能计算得到H的一个否定事例。
其中,E`被称为E的“替代”,可以通过否定E的某些合取肢得到。结合SC*和FC,可以得到BS的核心思想:“H相对于T而被E所确证。条件是,我们能够使用T从E中推导出H的一个(肯定)事例,并且这一推导过程不确保无论我们已经具有什么E都将获得H的一个事例”[12]127。
格兰莫尔将BS 称为“拔靴带条件”,是因为“理论中假说的事例,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是以‘拔靴带’的方式(计算)获得的。也就是说,(事例)是使用理论自身的假说(或其他可想象到的)从实验、观察或独立的理论考虑中获得的值中进行计算得到的”[12]122,而该过程恰好类似“拉动靴带从而扯动所有该靴带穿过的靴眼的过程”。进一步,如果想扯动任意两个靴眼之间的一段靴带,显然需要这段靴带和其他段的靴带是相连的从而一起被扯动,就像“H的词汇表与E的词汇表之间的联系不是由一类特殊的分析性假说提供的,而是可以由包括H 在内的任何假说提供的”[12]150一样。所以,如果计算使用了H,即H∈T,也即是说理论T 包含着若干个正在探索中的假说,那么这样的确证关系便具有“拔靴带特性”。
为了构建合理的三元确证关系从而确保严格的证据相干性(rdle vance),格兰莫尔进一步指出,“证据相对于理论检测假说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假说中出现的所有量都可以相对于理论从数据集中的量计算得到”[12]120。这一思想被卡勒(Madison Culler)明确称为待检测假说中“量的可详尽计算性”(exhaustive computability of quantities,Q-EC):
Q-EC:初始数据的值集E 相对于理论T 而检测假说H 的必要条件是,在E 上使用T 能计算得到所有在H中非空(实质)出现的量的值。[15]566
其中,如果一个变量出现在每一个和H逻辑等价的假说中,那么就说它实质性地出现在H中。然而,Q-EC只是要求H中量的值都应该是可计算的,却没有对T中的量作出限制,以致BS仍会面临非相干假说合取问题的困扰。说明如下:如果E相对于T而确证H,并且E和H都不包含谓词M,但T包含或衍推语句∀xM(x),那么,E将相对于T而确证H∧∀xM(x)。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三元确证关系自身的特性——为了避免“不允许对其词汇超出证据词汇的假说的确证”这一局限性,需要借助于一个基本词汇足够丰富的T,但同时也可能由于过于丰富而引入非相干量。所以,格兰莫尔认为,为了确保只检测H所断言的部分而不包括除H外T中的其余部分,有必要增加一个条件使得T中的量对于计算H中量的值都是必要的。本文将这一条件称为理论中“量的可详尽利用性”(Q-EU):
Q-EU:初始数据的值集E相对于理论T检测假说H 的必要条件是,在E上使用T计算所有非空出现在H 中的量的值时,不应该存在T 的逻辑后承包含(或衍推)某些量,这些量不出现在E 或H中。
此外,为了避免相同证据相对于相同理论而确证不一致的假说的情况,格兰莫尔要求E、T和H应该是一致的,即“一致性条件”(consistency conditions,C-C)。至此,基于C-C、SC*、Q-EC、FC和Q-EU,格兰莫尔在《证据与理论》[12]130-1中提出的确证标准可以简洁地表述为:
BS:E相对于T而拔靴带确证H,当且仅当:(i)C-C;(ii)Q-EC;(iii)SC*;(iv)FC;(v)Q-EU。
需要强调的是,按照格兰莫尔的意思,当满足BS时,是量而非量的值是假说的确证事例。因为对于确证假说的量来说,它的某些值是假说的肯定事例,另外一些则是否定事例。
五、拔靴带事例确证理论的主要难题
不难看出,从SC到BS,I-C由于更强调方法论原则而非纯粹的演绎主义诉求,因而“更接近于研究实践的泥潭和血液”[10]34。然而,BS不仅没有完全摆脱SC所遭遇的亨佩尔悖论并面临“克里斯滕森(David Christensen)反例”,更会导致由“卡勒反例”引发的其他问题。
(一)亨佩尔悖论
格兰莫尔认为,任何把某种事例化作为支持理论基础的确证解释,都必须处理事例化关系所特有的某些困难,这些困难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亨佩尔悖论。在《确证之逻辑研究》一文中,亨佩尔明确地将由于同时承认尼科徳标准(NC)和Eq而导致的逻辑悖论指认为“确证悖论”。顿新国表明,仅依赖SC和经典逻辑演绎规则就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即“¬Ra∧¬Ba”确证“∀x(Rx→Bx)”,即这是亨佩尔自己的SC确证理论中的悖论,并将其称为“亨佩尔确证悖论”。[4]64本文将这两者统称为“亨佩尔悖论”。格兰莫尔认为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亨佩尔悖论,即“Ra∧Ba”而非“¬Ra∧¬Ba”相对于T 确证∀x(Rx→Bx)。试考虑:
(E1)H:∀x(Cx→Dx);T1:∀x(Rx→Cx)∧∀x(Dx↔Bx);E:Ra∧Ba;E`:¬Ra∧¬Ba。
格兰莫尔认为,E`并不像E 那样能够相对于T1计算得到H 的肯定事例,即不满足SC*,故E`不确证H。然而,格兰莫尔自己在这里违反了拔靴带特性,因为根据简单的演绎推理,E`实际上可以相对于H∪T1计算得到H 的肯定事例。首先可以由¬Ba∧T1得¬Da,再由¬Da∧H 可得¬Ca,故得到!Ca !Da,而¬Ca∧¬Da├dev(H,E),即“¬Ca∧¬Da”是H的肯定事例。所以,(E1)并没有体现出BS对亨佩尔悖论的限制。我们可以重构亨佩尔悖论所讨论的情景:
(E2)H:∀x(Rx→Bx);T1:∀x(Wx→¬Bx);T2:∀x(Sx→¬Rx);E:Wa∧Sa;E`:¬Ra∧¬Ba。
其中,H为乌鸦假说,T1为“所有白色的都是非黑色的”,T2为“所有鞋子都是非乌鸦”,E为“一只白鞋子”,E`为“非黑色的非乌鸦”。显然,根据BS,E不确证H。同时,E也不确证¬H,即E不否证H。所以,对于格兰莫尔来说,“一只白鞋子”和乌鸦假说是非相关的。在此意义上,BS确实限制了亨佩尔悖论的出现。然而,问题仍然在于,E`是否确证H,即“形如‘¬Ra∧¬Ba’的观察报告是否确证形如‘∀x(Rx→Bx)’的假说”。[4]65如果我们接受E*确证H,即E`是H的肯定事例,那么“几乎所有的缺陷都是原始满足性标准的缺陷,不应该归咎于拔靴带模式”[12]133。
除此之外,亨佩尔提出SC所诉诸的枚举归纳直觉也是很不精致的。根据SC,形如“Ra∧Ba”的观察报告将确证形如“∀x(Rx↔Bx)”的假说。也就是说,一只黑乌鸦将确证假说“是黑色当且仅当是乌鸦”。本文将这一状况称为“主题悖论”,因为它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缺乏背景信息时,我们可以对具有不同属性的某对象选择不同的谈论“主题”(subject matter)而得到不同的假说。例如,当仅面对几只是黑色的并且是乌鸦的对象,我们既可以归纳得到“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也可以得到“所有黑色的都是乌鸦”。
(二)卡勒反例引发的问题
卡勒认为FC太强。试考虑:
(CE1)H:∀x(Ax→Cx);T1:∀x(Bx→Cx);E:Aa∧Ba。[15]570
卡勒认为,根据BS,E 不能相对于T 而确证H。因为对于量Ax 和Bx 来说,不存在替代证据E`,在其上可以相对于T而计算得到H的一个否定事例。然而,FC所强调的是——如果存在在E`上的计算,那么就应该能够计算得到至少一个H 的否定事例。但在(CE1)中,根本不存在E`上的计算。所以,(CE1)并不构成FC的反例。但是,由此可以引发其他值得考量的问题。
1.如何在一阶语言中表达“替代证据”
不难知道,在(CE1)中之所以不存在在E`上的计算,是因为否定前件式在经典演绎逻辑中是无效的,从而无法由¬Ba和∀x(Bx→Cx)进行进一步的演绎推导。在以方程式形式表达的理论中,无论量具有何值,我们总可以将其带入方程式进行计算。但在由一阶语言表达的理论中,并不是所有量值都可以和理论中的假说结合进行演绎推导。也就是说,因为演绎规则的限制,¬Ba和∀x(Bx→Cx)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隔阂。再有,科学实验中的数据通常不能简单地以“Ax”或“!Ax”的形式进行表达。所以,如何在一阶语言中表达替代证据有待进一步研究。
2.如何说明理论中的“同形异释问题”
卡勒对(CE1)作了这样的解释:T1为“所有加斯康人都是勇敢的”,E为“达达尼昂既是加斯康人又是火枪手”,H为“所有火枪手都是勇敢的”。然而,我们可以对(CE1)作另一种解释:T1为“所有乌鸦都会飞”,E为“a是一只黑乌鸦”,则H将表示“所有黑色的都会飞”,而这显然是违反直觉的。这似乎意味着,当对同一结构的某部分作不同的但均符合直觉的解释后,由这一解释所决定的对剩余部分的解释则有可能是反直觉的。本文将这一状况称为理论中的“同形异释问题”。
(三)克里斯滕森反例
与卡勒认为FC太强不同,克里斯滕森认为BS太弱,并借助拔靴带特性和一阶逻辑的演绎封闭性提出了一系列反例,本文只列举其中的两个。试考虑:
(CE2)H:∀xGx;T1:∀x(Rx→Bx);E:Ra∧Ba;E`:Ra∧¬Ba。[16]472
其中,H表示泛神假说,即“万物皆神”;T1表示乌鸦假说。由于T是演绎封闭的,故可以得到其逻辑后承T2:∀x[(Rx→Bx)↔Gx],进而不难得到BS被满足。这样,我们将会有“一只黑乌鸦确证万物皆神”的反直觉结果。为此,格兰莫尔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
R:对于任何语句R都有,H⊬R↔Ti且R的非逻辑词汇是Ti的非逻辑词汇的真子集。[17]627
通常将条件R和BS一起记为“BS+R”。但BS+R仍会遭遇新反例。试考虑:
(CE3)H:∀x(Fx→Gx);T1:∀x(Rx→Bx);T2:∀x(Wx→Fx);E:Ra∧Ba∧Wa;E`:Ra∧¬Ba∧Wa。[18]
其中,假说H 声称“只有上帝才能飞翔”;T1和T2分别表示乌鸦假说和“所有有翅膀的东西都会飞”。和(CE2)的情况相似,BS+R被满足。所以,我们再次得到反直觉的结果:一只有翅膀的黑乌鸦是只有上帝才能飞翔的证据。
六、事例确证理论的启示与发展趋势
面对格兰莫尔的批判[19],假说-演绎主义者展开了对H-D的语义模型、自然公理化、非经典逻辑框架以及与BCTs的比较和综合等多维度的研究,而I-C在克里斯滕森反例出现之后少有实质性进展。对以下问题的考量将为重构I-C提供基本思路。
(一)实质性标准:构建合理的三元确证关系
正如本文指出的,为了解决SC的根本局限性,三元确证关系是必要的。而怎样的三元确证关系才是合理的,将关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1.“拔靴带特性”是否必要
卡勒认为,克里斯滕森反例之所以成立是因为BS 具有拔靴带特性[15]565。在(CE2)和(CE3)中,如果要求H∉T,那么克里斯滕森反例将不成立,因为计算H 的事例所必需的双向条件句将不会得到。要求“H∉T”也符合其他常见的三元关系的确证理论:(i)在大多数版本的H-D 中,都要求H∧T├E 且T⊬E。如果H∈T,则将得到T├E 且T⊬E,矛盾;(ii)在标准贝叶斯解释中,0
但是,如果H∉T,将意味着所有实质上出现在H中的量都应该已经出现在E∪T中,否则将存在H中的量的值得不到计算,这将致使BS 退回到SC,以致不允许对其词汇超出证据词汇的假说的确证。所以,除非我们有其他方法可以修复这一缺陷,否则H∈T将是必要的。但即使H∈T是必要的,“允许使用理论自身的某些假说来检测理论自身”势必会导致认识论上的循环。所以,根本任务将是如何理解格兰莫尔的拔靴带策略是一种可以促进我们认知目标的“构造性循环”而非破坏性循环。[20]而这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
2.如何理解“相对于T被确证”
由于坚持三元确证关系,格兰莫尔似乎走向了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相对于不同的T,E和H之间将具有不同的确证关系。也就是说,E是否确证H完全取决于相对于哪个T。然而,只有当T满足某些条件时,相对于它的确证才会给理性主体提供相信H 的理由。伊迪丁(Aron Edidin)[21]和米切尔(Sam Mitchell)[22]等人因此主张我们应该从相对确证走向真实(或实际)确证,并认为添加从相对确证转换到真实确证的条件,可以避免克里斯滕森反例。也就是说,在克里斯滕森反例及其类似情形中,由于理论所包含的假说(例如泛神假说和乌鸦假说)之间是如此的松散,谓词又是如此的奇异,很容易把这些例子看作是不合理的并且在任何科学理论中都不是可能的。对于如何才是“相对于T”的真实确证,目前主要的观点有:(i)真理要求:T是真的;(ii)确证要求:T被确证;(iii)信念要求:T被相信;(iv)独立确证要求:T独立于E被确证。[23]
但这些对真实确证说明的合理性,似乎都以如何避免无穷倒退或恶性循环为前提,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与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和融贯论之争相关。克里斯滕森甚至认为,“选择何种对相对确证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眼光”[23]382。
3.两种定性确证理论传统的综合
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应该通过定性确证理论两种传统之间的互补性来寻求更合理的三元确证关系,斯普伦格(Jan Sprenger)就自觉地将亨佩尔理论和H-D进行了综合[3],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I-C和H-D是两种互斥的定性确证理论的观念。但是,他所基于的条件“¬E∧T⊨¬dev(H,E)”并没有真正体现亨佩尔事例确证理论的基本观点即“数据陈述衍推假说陈述的展开”,而只是歪打正着地和FC这一限制性条件保持形式一致。当然,斯普伦格的工作启发了我们可以回归对演绎关系的再探讨,而将I-C和H-D进行综合显然是一种可能的尝试。
(二)结构性标准:选择合适的逻辑系统
虽然事例确证者们已经尝试对I-C的实质性标准进行了修正,但他们始终坚持同一个结构性标准,那就是在经典逻辑框架内刻画证据相干性。以至于问题仍然是——“这种失败是由于对形式理论的疏忽,还是由于证据相干性存在结构性标准这一想法的错误”[17]626。
I-C的主要难题有力地表明,基于一阶语言的经典方案很难合理地刻画证据相干性,“如果我们把理论简单地看成是演绎封闭的语句集,那么一个理论就不会有一整套内置的确证关系”[16]480。也就是说,亨佩尔悖论、克里斯滕森反例等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对事例的计算依赖于导致实质蕴含怪论的条件引入规则“B衍推A→B”,而显然A在这里是非相干的。所以,虽然亨佩尔和格兰莫尔想方设法通过事例概念刻画证据相干性,但他们在得到H的事例进而将E和H关联起来的逻辑推导却是非相干的。可见,放弃基于一阶语言的经典方案而选择非经典逻辑来重构I-C似乎是必要的。甚至有人认为“经典逻辑不足以作为令人满意的确证理论的基础,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可以单独胜任该任务”[24]。
值得一提的是,假说演绎主义者同样意识到由条件引入规则和附加律“B衍推BVA”等有效演绎推理规则所引起的非相干性问题,所以他们对经典逻辑衍推关系进行了相干性限制,使得前提的逻辑后承能够真正成为前提的部分内容(partial content)[25][26]42。
七、余论
综上,作为定性确证理论之一的I-C,其主要任务仍是使用经典演绎逻辑刻画确证概念,但由于经典逻辑只确保推理形式上的“有效性”(validity)而非“内容”(content)上的“相干性”,故始终会面临亨佩尔悖论和克里斯滕森反例等所凸显的相干性问题,即如何保证证据与待检验假说在内容上具有相干性。从对这些相干性问题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I-C的目的是刻画确证这一归纳概念,但实现过程实质上是基于“演绎推理”(deduction)的。也就是说,包括I-C在内的定性确证理论实质上试图——基于给定的证据并通过某种推理模式——来实现对某给定假说的确证。
由此,对“确证模式”的刻画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对“推理模式”的探究。如我们已知的,推理通常因其形式而被视为有效,即使是“归纳推理”(induction)也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某些参数模式来评估的。但科学推理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实质推理”(material inference),即由前提和结论中包含的概念所体现的经验内容而合理。[27]当然,推理不仅存在于科学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因为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我们总是基于已知的信息和各种推理模式不断地进行新的活动。
可见,对“推理模式”的研究就应该成为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的基本前提。试想,是什么让人工智能成为每个人的难题呢?归根结底是因为:鉴于我们自己的思考不是“计算”而是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具有猜测性的推理,那么我们怎能指望对它进行编程呢?[28]所以,本文认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重心目前应该转移到对包括作为整理论证方法的演绎、作为探索发现方法的归纳(包括机器学习和类比等)和“溯因推理”(abduction)以及“反事实推理”在内的各种推理模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为了避免类似本文提到的相干性问题,使得人工智能更符合人类的日常思维,便需要研究能够保证前提和结论之间相干性的推理模式。
注释:
①其中,E2≠∅且E1∧E2=∅。如果E2=∅,则意味着E和H是非相干的;如果E1∧E2≠∅,则有可能E1衍推E2,从而使得E与H非相干;此外,如果E1=∅,则PC退回到H-D1。
②格兰莫尔另一方面也将计算视为一个分级的有限图,图的零级节点和最大节点上都是量,中间节点可以是任何复杂度的开公式,而每个节点之间是通过辅助假说连接的。由此,格兰莫尔也将整个确证过程看作一次计算。
③在以方程式形式表达的理论中,方程式的一组解就是该方程式的一个肯定事例。
④与PC相比,之所以将“E≡E1∧E2”作为SC*的条款(iii)是因为,使用PC时,E1和E2均为已有数据,而使用SC*时,已给定的数据只有E1,E2是相对于T计算得到的新数据,当T不同时,E2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