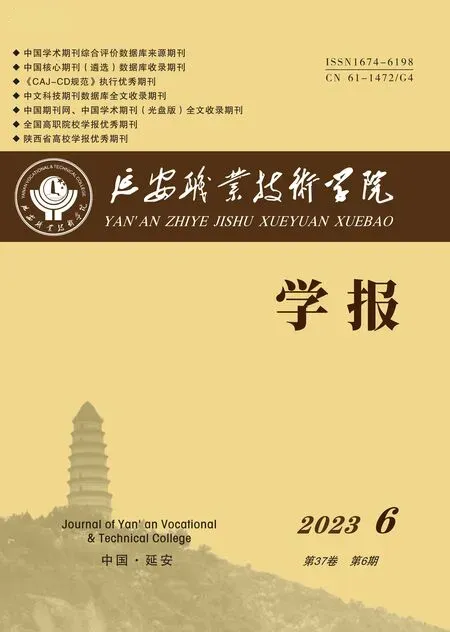论庄子天下观的系统特征
化贯军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天下,原始意思即天之下。“天下”一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最具概括力、最独特的概念之一,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已是言必称“天下”了。这时的天下观念,涉及地理、文化、政治等意涵,可以说它影响了中国人对宇宙和文明秩序的理解。然而,先秦诸子由于各自逻辑不同,天下秩序到底是什么,给出了不同的解读。美国哲学家拉兹洛认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把世界作为整体来思考,蕴含着系统思维的范式[1]88。庄子基于对所见、所闻、所感的不同事物联结方式的认知,提出了独特的天下观,即:天下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人与物按照一定的连接,组成一个个小的系统或者组成不同的天下面相。人人关系体现的是社会层面,人物关系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层面,物物是人与人关系的另类体现。
庄子,战国时人,年龄和孟子相仿。现存本《庄子》包括内、外、杂篇共33 篇。一般以为,内篇是庄子思想的反映,外篇和杂篇有反映,有继承,当然也有偏离,但通篇内容是成体系的[2]12。因此,本文所引用《庄子》文章,内容主要引自内七篇(为了行文方便,引用内七篇时只说篇名,不再说是内篇,仅引用外、杂篇时才特意说明),材料经过爬梳剔抉,是能够反映庄子哲学思想的。
一、天下的不同面相
(一)天下是有限和无限的空间集合
一是表示宇宙自然界、天地之间或引申为(统治的)领域。它不纯粹是一个空间概念,已经引申有政治的含义,“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逍遥游》)[3]32,这里天下与海内相对,表示统治的地域,意思相同,当为庄子受了战国中期天下观念的影响,认为天下是“四海之内”面积三千里的地域,由天子统辖。
二是表示无限之境。“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3]93;“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3]279。这些所游之处,皆是无限之境。这个无限之境比有限纯粹政治共同体意义涵盖更要广。可以说庄子的天下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概念。在这里,天下的所指在庄子心目中显然不限于统治者所统治的有限区域,而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即宇)。
(二)天下是一种政治共同体
即国家或统治权。尧让天下于许由,认为许由是日月、及时雨,而自己是多余者,治理天下不够格,曰:“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逍遥游》)[3]23“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德充符》)[3]198这两个地方的天下,实指政权。“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外篇·在宥》)[3]338只有尊重、珍惜生命的人,才可以委以重任,被托付天下,天下之意也主要指国家政权。
(三)天下是一种社会共同体
即人世间、社会上。庄子认为人世间有两个世俗的规则:子女敬爱双亲,为命;臣下侍奉国君,为义。如何去做,乃是让双亲或君主心安。尽管子女或臣子都有不得已之处,但仍然要安之若命,忘却自我,这才是真正的德性。可以看出,庄子赞成源自自然情感的孝(命)和忠(义),但反对将忠孝模式化。另《人间世》中“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3]145,是说楚国叶公子高出使齐国,请教孔子,孔子告诉其传递国君间喜怒无常的言语,是人世间非常不容易的;“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3]169,圣人建功立业或保全性命,是基于天下有道与否。这里的天下都是人世间或社会上的意思。
(四)天下是人、事、物的单个或集合
天下指天下人,如:“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外篇·骈拇》)[3]291-292。世间的俗务,如《逍遥游》中“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3]32《大宗师》中“吾犹守而告之,参(三)日而后能外天下”[3]231,都是表示世间的俗务或事情。天下之物。《外篇·骈拇》中“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3]292,意思是天下的事物都自然而产生,却不明白其为何而生,各有所得而不知如何而得,天下是指天下之物。
(五)天下是一种综合和抽象相结合的共同体
整个社会的礼乐、政治及社会秩序。《外篇·胠箧》中“上诚好知(智)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3]328作者认为,很难说是指上述四个意义的哪个,应该是上述意思的一个综合和抽象。作者以空中鸟、水中鱼、林中兽为例,认为,智巧繁多,连这些动物都乱成一团,如果人们崇尚智巧、圣言,人的淳朴本性被毁坏,天下将有大乱。这里的“天下”,很难说是指上述四个意义的哪个,应该是上述意义的一个综合和抽象。
二、庄子天下观的系统思维
(一)整体性
西方人以原子式的视角分析事物,而中国人非常重视综合,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思维视野,中华文化孕育甚早,《易经·艮卦·卦辞》有:“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我们观察一个人,只看到其背部并不能知道全身的状况,就好像走到一个院落,却看不到主人在家。整体性是系统论的核心观点,是系统的重要存在形式。这种整体性,意味着系统不是由部分简单叠加或堆积而成。系统的永恒存在,意味着这种整体性不容随意破坏,不能任意割裂,否则,系统将不复存在。
世间万物休养生息、混而为一的地方,就是天下。万物在这一点是相同的、一体的,即万物一体。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永葆人的真性,不会因小失大,不会与世沉浮。柏矩跟着老聃悟道,希望师父允许自己周游天下,老聃却说:算了吧,天下就是这里,到处都是一样(《杂篇·则阳》)[3]791。“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3]176就是说我们观察事物,如果聚焦于相异的一点,肝胆之间也会形同楚越之遥。如果聚焦于相同的一点,万物都以一体的。
《应帝王》最后一段谈的是“浑沌之死”。南海、北海和中央的帝王,分别为儵、忽和浑沌。儵与忽在浑沌的地盘见面,浑沌对它们很好,它们就想着要报答浑沌,可如何报答呢?它们以人为标准,认为人都有七窍以生活于世,而浑沌没有,于是它们每天忙碌,凿了七天,浑沌终于有了人形,却一命呜呼[3]281。浑沌即是庄子的天下认知,在庄子看来,浑沌本来是混一的,不容人为分割,否则,浑沌就不复存在。
(二)多样性
不论宏观抑或微观,事物都是一个个网格状的联结,每一个联结点就凝结成一个小系统。庄子的天下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集合体,这种多样性一方面是源于万物的“内在之德和内在之理”,另一方面,源于人们观察和看待事物的方式、眼界和价值观等[4]39。
庄子提及事物,总是以万物代称,意指事物的种类繁多。《齐物论》中多次提到“万物”:“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3]65“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77“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3]95。《齐物论》在谈到是非的相对性时,以人、泥鳅和猿猴的不同习性为例,侧面说明了多样性存在是合理的。人睡潮湿之处,腰就会出毛病,动弹不得,泥鳅却优游自如。人攀到树的高枝就会心惊肉颤,猿猴却应付裕如。就居处而言,何者才是真正的宜居之地、人以肉为佳肴,麋鹿流连于草间,蜈蚣可以吃蛇,猫头鹰和乌鸦偏爱老鼠。就美味而言,也是多种多样。毛嫱、丽姬是绝色佳人,然而,鱼儿看到就会迅速潜入水中,鸟儿看到就会窜入空中,麋鹿看到就狂奔躲避。就美色而言,何者才是正色?[3]88
鲁侯把郊外的海鸟供奉在太庙,敬上等的好酒,奏高雅的乐曲,用祭祀的牲畜作膳食,然而,海鸟不敢吃喝,惊恐万状,三天即亡。这是典型的,以养人的方式养鸟,不是以养鸟的方式养鸟,鸟的天性是回归自然。人鸟习性不同,不可强之为一(《外篇·至乐》)[3]551-552。对于事物多样性,就要一视同仁,忘却是非之心,顺遂事物的天性,“是不是,然不然”,是与不是,然与不然,都不强做争辩,以此,我们才能逍遥自在、畅游于无穷的境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无是非,就是无为,“无为可以定是非”,“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外篇·至乐》)[5]544。无为是天地的自然之性,正是因为这样,万物才得以滋生,实现无中生有。
庄子非常宽容宇宙之中的不完美,鲁国有个叫叔山无趾的人,拜见孔子,被责备后,说道:“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天地是无所不覆盖和承载的(《德充符》)[3]186。人要勇敢面对自己的不完美,要“自得其得”“自适其适”,要自己使自己有所得,有所适,以符合自然之道(《外篇·骈拇》)[3]298。
(三)层次性
层次性是指构成系统之物不是胡乱杂糅、乱七八糟的,而是有序的、分层的,有层次高的,有层次低的,总起来是一个协调的动态的平衡。自然科学家发现,非常微小的跳蚤,吃的是更小的同类,而更小的跳蚤,又会搜寻极小的东西,以此类推,无有穷尽[5]113。层次性使系统更加稳定和更具应变能力。
系统的结构在不断地优化,不断地形成不同的层次,即子系统,各子系统的关系是包含和派生的,它们既要维持本身的生存,同时,一个小的整体服从于更大的系统,以此类推,直至总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关联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同子系统的关联,可以构成更高一点的系统层次,由此,系统的恒定性才得以在这种动态中得以平衡和存续。
在庄子哲学中,万事万物其实是有层次之分。由于子游有成心,所以只能区分“地籁”和“人籁”,“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南郭子綦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所以能通达“天籁”,“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齐物论》)[3]50道生万物,但长而不宰,万物是“自己”“自取”,是自己如此。
南伯子葵问怀道之士女偊,为什么年龄这么大了,还“色若孺子”,答曰“吾问道矣”,女偊认为,要悟得大道,就需要不停地修炼。首先,三天,能够遗忘天下,七天,忘却外物,九天,忘掉自身,然后通达万物,逍遥于世,没有时间之别,没有生死之分,一切都处于不将不迎的“撄宁”状态,乱中宁静(《大宗师》)[3]230-231。
尧想禅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父,舜想禅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被让者借以治身为由,没有接受。治身即养生,不然养护自己的生命,也不损害别人的生命。周始祖太王亶父统治邠地时,无论富贵和贫贱,皆不会伤害自己和臣民的生命。面对狄人的侵犯,没有抵抗,而是放弃所在土地,愿意跟随自己或留下的,静听其便。“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天下乃“千仞之雀”,身体是“隋侯之珠”,轻重可知!(《杂篇·让王》)[3]851庄子之道的真谛是治身,其次才是国家,再次才轮到天下。
《外篇·在宥》中,治国者面对世间万物,依次为:物、民、事、法、义、仁、礼、德、道、天等,从具体之物到抽象之物,这是一个层次的递进。至于什么是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得道者应该以无我之心对待它们,顺从天道,合乎人道,天道是主,人道是臣,相辅相成[3]361、364。《杂篇·外物》中,称呼得道者为神人,按照儒家标准,所称呼的小人、君子、贤人、圣人,在庄子看来都是凭主观行事者。但是这些得道也好,不得道也好,按照《外物》的标准:小人、君子、贤人、圣人、神人,以此类推,都是在自己领域里做出一定的成绩,别人不去干预。《逍遥游》中,知了、斑鸠和麻雀,囿于自身的局限和偏见,而无法逍遥快活。而那些智力能够担任一定官职,行动使乡里人亲近,德性合于君主的意愿,乃至一国百姓都信赖的人,也不过像这三种小鸟罢了,它们处处在意世俗所谓的成功,嘲笑别人的无能[3]18。这里官职、乡里、君主、国家,层层递进,显示了一定的层次性。
可以看出,庄子之天下观,论述天下万物,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层次性非常明显。假若没了一定的层次性,那么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就会无法协调,系统的生命力和活力就会丧失,系统的功能就会失调,最终整个系统也可能不复存在。
(四)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系统各要素之间,以及各系统与系统之间,是开放的、转化的,不是封闭的、凝固的。长梧子认为:圣人以没有分别之心,与日月相邻,心怀宇宙万物,与之混为一体,没有分际,把是是非非抛掷一旁,贵贱一样。众人忙碌不已,圣人淳朴悠闲。世间万物莫不如此,因而相互积聚相容而不排斥分离(《齐物论》)[3]52。
没有事物不是或不可,就如植物的茎和房屋的柱子,丑女和西施,各种古古怪怪的东西,以及事物的毁灭与生成,生成与毁灭,等等,如果基于道而论,都是通而为一的。山中的猴子为什么会为吃三个还是四个栗子而发愁,是因为,人为地将栗子分开而再去追求所谓的一体。事物本来是浑然一体的,即使是口中所说的“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看来也是人为地把我和万物分别开来了,这些分割都是徒然耗费精力罢了。万物互相依赖、相互转化,《齐物论》曰:“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3]64-65“彼”“我”之别并不固定,可以说是互为彼此。
在《外篇·至乐》还谈到了万物在一定环境之下相互转化的思想,物种由十分细微的“几”(又称为“机”)产生,㡭、蛙蠙之衣、陵舄、乌足、蛴螬、蝴蝶、虫、鸲掇、鸟、斯弥、食醯、颐辂、黄軦、九猷、瞀芮、腐蠸、羊奚、不箰(笋)、久竹、青宁、程、马、人,这些事物都是他物转化而来,“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3]555庄子看来,一切都是应时而生灭,变动而不居的,尧舜禅让而帝业存,燕王姬哙禅让却灭亡。汤武奋起而王,白公奋起被杀。栋梁、名马、猫头鹰有时作用或能力非常神奇,有时却废物一个。为什么?一切应时与否而已(《秋水》)[3]515。
在《外篇·田子方》中,讲述了一个如何了解和接纳异质文化的例子,有一个楚国怀道之人,叫温伯雪子,他要到遥远的齐国去,风餐露宿,途径礼仪之邦鲁国。有鲁国人祈求拜见之,他却拒绝,认为鲁国所谓的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后来使齐归来,又途径鲁国,那个先前要拜见他的人再次求见,温就答应了。见面之后,回到住处及途中,不停地感叹。他的仆人疑惑不解,温解释道:“见我的那个人,进退若规矩,从容若龙虎,给我提意见如儿子对父亲,开导我如父亲对儿子。”[3]623-624这种从有成见到感叹不已的变化过程,双方的见面,是关键点,只有交流开放,才能真正了解对方、认可对方。
在道的主宰下,天下万物盛衰消长、有沉有浮,时时刻刻无有止息。从《逍遥游》中,可以得知,鹏是由鲲蜕变而成,事物是变化不居的。商汤讯问贤臣棘,天下有没有极限,棘认为没有极限,不毛之地之北,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3]15。
在《外篇·秋水》中,借海神北海若之口,中国、四海、天地,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彰显了中国的有限性和天下的无限性。如果受制于时空、见识的拘束,就无法洞彻天下万物。河伯看到了大海,才认识到黄河的渺小,望洋兴叹,其实,在北海若看来这只是认识的第一步,北海若指出,北海确实比黄河要大,然其之于天地,就像山中一粒小石块,一棵小树苗;四海之于天地,就像大泽中的蚁穴;中国在海内,就像谷仓中有个小麦粒;人之于万物,就同马身上的一根毛。如此展眼,相对于天地的无垠,没有什么称得上大的。“五帝、三王、仁人、能士”在这毫毛大小的地方折腾,何足为言![3]500-501
三、庄子天下观的内在之“道”
系统的奥秘就在于结构,仅有各种要素,没有一定的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就仍然是散乱之物,就不会有任何功能,因而不是一个系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是观看角度的不同,并没有深入事物的内部。因此,要想了解一个系统,必须深入探究系统的结构。结构是系统要素的联结方式,此系统之所以区别于彼系统,就在于其联结方式的差异。从系统结构的视角看,所谓天下,就是在天之下生活的人和其他诸要素,基于一定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庄子天下观的联结方式就是:“道通为一”。 西方哲学强调一切皆一,一即一切。其实在中国哲学、在庄子哲学中,也同样有这种认识。这个一就是“道”,道是系统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道通为一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的气是指心寂的状态,大道呈现于其中。“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外篇·知北游》)[3]649天下万物,生生死死、方方圆圆,亘古而存,天下虽大,不出于道,秋毫虽小,道使之生。天下从不停息地变化,万物自然有序地盛衰,其中的根本就是道的存在。
《大宗师》认为,道真实而无形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般人也不可接触,它自古就存在,赋予“鬼”“帝”以神性,天地也是它生。在四方上下,古往今来面前,也无所谓高深久老,然而它是孕育万物之本。得道者不是为了得到好处,当然也不回避好处,狶韦氏、伏戏(羲)氏、维斗、日月、堪坏、冯夷、肩吾、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彭祖、傅说,庄子举出了一连串人物以说明之。[3]225
庄子谈到看待事物的标准和界限问题,如果人们认为天下小于秋毫的末端,那么泰山就是小地;如果认为长寿之命小于早夭的婴儿,那么八百岁的彭祖也是短寿的。假如从不同之处观察事物,肝胆之间也会如楚国和越国那么辽远;假如从相同之处察看,万物就是一体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3]176
外篇《秋水》更具体发挥了这一思想,我们应该用平等的眼光、道的角度看待世俗中的事物,事物自身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从“物、俗、差、功、趣”等不同视角看待万事万物,就会有贵贱、大小、有用无用、是非等各种自以为是的标准,所以才产生了区别。在《齐物论》中,庄子把这些标准称为人们的成心:“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 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 愚者与有焉!”[3]56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以自己的成心来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聪明之人抑或愚笨之辈都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标准。而且这些所谓的是非标准,在庄子看来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以栖息地、美味、美色而论,人和各种动物各有所好,但是不能互通其“好”。即是说作为个人色彩浓重的是非标准不可以强加于人的,不然,就会带来纷争混乱。“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3]68“然”是说物的存在,“可”是说物的价值,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自然价值的。只有从道的角度,才能真正通达万物,与万物为一。庄子认为,“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我们应该追求“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的境界[3]72。
基于道的视角,观察事物之名,无为之君恰如其名;观察职守,君臣之别分明;观察能力,则天下官治;观察万物,万物完美。人的德性是与天地相通,天下之道覆盖万物,治理天下曰事,做事的专长是技能。技能要与事相配,事情顺从大义,大义要合乎德性,德性顺乎大道,大道合乎天(《外篇·天地》)[3]366。
综上可知,天下包罗有差别、具个性的万物,虽千差万别,却自有存在的理由,没有大小、长短、贵贱、有无及是非的不同。天下涵有的万物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依存,变动不居,彼此并无截然之分野。总之,天下乃是万物一体的存在,基于道而论,万物会通为一。
(二)何为道?
1.无为即道。尧把老师许由比喻为日月和时雨,只要在位天下就是大治,因此,想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却推辞不受,认为自己对于治理天下的名与实,都毫不在意,“无所用天下为”,尧是“庖人”,是厨师,自己是“尸祝”,是祭祀的主祭者,即使厨师不下厨,主祭者也不可越俎代庖。古代统治天下者,虽有智慧,不显示;虽有口才,不自夸;虽才能跨越海内,不盲动;无为则天子自治。忘天下[3]25。
俗人习惯于纷纷扰扰,神人则与万物混而为一,不会竭尽心力追逐于天下之事。因此,可以远离各种灾害。治理天下,对于尧来说,居功至伟,对于神人来说,是“尘垢秕糠”即可成之,毫无意义。因此,尧见了神人之后,也恍恍惚忘记了天下,终达逍遥之境(《逍遥游》)[3]32。有一个官居大宰的人,向庄子询问什么是“至仁”。庄子认为至仁就是无所偏私,儒家的孝是不合于道的,真正的合道行为是“忘”,忘我忘物,甚至“我”和天下也要两相忘(《外篇·天运》)[3]446。泉水干涸,鱼儿相互吐着唾沫以苟活于陆地,哪能逍遥于水中,自由自在。因此,合乎自然的生存才是合乎大道的。人类应该与万物一体,与大道一体(《大宗师》)[3]221。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庄子同样崇尚自然,“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只有空空如也的房子,才会有光亮的显现;空虚寂静之心,才会有吉祥的凝聚。所谓“虚”,就是“忘”。忘掉成见,忘掉自我,忘掉有用无用(《人间世》)[3]139。匠人所见的“栎社树”、南伯子綦所见的“大木”,不能用于祭祀的白颡牛、高鼻猪、有痔疮的人,以及在俗人眼中形体智力有问题的支离疏,都是因为所谓的“没用”,才得以保全性命。而楸树、柏树、桑树等,因为是所谓“有用”之材,一旦成型,就会死于斧头之下。鲁侯敬鬼尊贤,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片刻没有休息,但是仍然祸不单行,忧愁万分。在鲁国隐士熊宜僚看来,这种鲁侯除患的方法是非常肤浅的,大狐狸和花豹虽然谨慎行事,但是仍然被杀,因为他们皮毛值钱,鲁国就如鲁侯的皮毛,再执着于除患也无济于事。因此,真正的做法是,放心一切,忘我顺物,与大道同游,方可无患(《外篇·山木》)[3]595-596。
2.忘我顺物。领悟大道还要做到忘我,卫灵公的太子天性喜欢杀戮,颜阖将要做太子的师傅,请教于蘧伯玉怎么办。蘧伯玉认为,颜阖应该忘却自我的存在,“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表面迁就太子,暗中不露声色地引导它,方可既保全自己,又能够教育太子(《人间世》)[3]152。
所以,在庄子的眼中,圣人处世的原则是,“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顺遂自然,天下道兴,建功立业,天下道亡,保全性命,莫要矜夸德行或一心要出人头地,这样只会使自己遭遇不测,甚至徒遭刑戮。庄子是要告诫众人,要放弃主观之用的成见,不要仅仅知道有用之用,而忽略了不用之用。
治理天下者不但要端正自己的本性,还应顺从百姓万物的本性。有虞氏虽然得到了民心,但靠的是仁义,仍逃不掉外物的束缚。而泰氏,闲适地睡觉,悠然自得,就是被人称为牛或马,都不以为然,德性纯真,外物莫侵。因此,真正的治理天下之道乃是合乎自然。隐士接舆认为,统治者以自以为是地制定法度是悖德的表现。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就如海中凿河、蚊子背山一样荒诞。真正的圣人治理天下,是顺从自己和百姓的本性(《应帝王》)[3]264-265。
如何顺物呢?就是要合于天性合乎自然之性地对待万事万物。沼泽间的野鸡,十来步才可能啄到吃的,百十步才能喝到水,然而它不会期盼被驯养在樊笼之内,养在笼子之中,虽然吃好喝好,精神旺盛,但是不逍遥自在(《养生主》)[3]117。当然,崇尚自然之道,并不就是一味地无为,庄子并不反对基于自然的忠孝情感,反对的是以这种模式束缚人。叶公子高,还没动身出使齐国,就心神不定、阴阳失调,孔子告诫叶公子高,说天下有两大规则:命和义,前者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比如儿子对父母,后者无法避免的东西,比如君臣之分。前者的最高境界是使长辈安适,后者的最高境界是使君上安。因此,后代或臣子要做到的是:哀乐不为所动,安然对待命运,“忘我而顺物”,这才是真正的有德。
庄子提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但庄子并不反对基于自然而然的情,圣人寄身于常人之中,外在上与常人一样,即“有人之形”。但是圣人会忘却常人那种是非好恶之情,即“无人之情”(《德充符》)[3]198-199。怀道之士秦失,隐迹世间,好友老聃去世,众人皆号啕大哭,他却只是干号三声,弟子问其何故,秦失认为老聃的生死,是顺时顺理的事情,不可过于哀乐,痛哭流涕者皆丧失了人之为人应有的天性(《养生主》)[3]118-119。
与天为徒、合为一体的真人,不孤傲于世,但是不会结党营私;好像缺点什么,但不受外界诱惑;悠闲自在,豁达舒畅,高谈阔论,不浮华,不特立、不矜持。无我无物逍遥自在。真人基于刑法而执法,没有个人好恶于其中;礼仪只是辅助,不过分强求;顺物之自然乃是智慧,不自作小聪明,总之,不掺杂是非好恶地对待人间的法律、礼仪和智慧(《大宗师》)[3]214。
庄子推崇不被事物所羁绊的人生境界,《应帝王》中,“天根”向“无名人”问询如何治理天下,“无名人”认为其是粗鄙之人,问这让人不快的问题。“无名人”推崇的是,与造物者一起,御飞鸟,出六极,至无际之野,逍遥快乐。在“天根”的再次追问之下,“无名人”认为,只要“天根”内心虚寂闲适,抛却自身的成见,顺遂外物自然的本性,天下自然大治[3]266-268。仁义乃身外之物,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人类只有顺遂生命的本性,不追逐外物,天下才能少有困惑而达到大治。天下至纯的德性,是保有性命的真情,鸭脚短,不可人为接长,鹤脚长,也不可人为地截短。骈拇枝手也是一样。仁义本非人之实情,三代以下,仁者愁眉苦脸,心忧天下,而不仁者拼命追逐声色犬马,造成天下嚣嚣不安。“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外篇·骈拇》)[3]293于是三代以下,自俗人至圣人,皆由于外在之物而迁移了自己人之为人的本性。马的真性是“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民的天性是“织而衣,耕而食”,如果圣人自以为是的干预,就会破坏这些自然之性。孜孜以追求仁义就会造成天下的疑惑,过分追求快乐和繁琐的礼仪,天下就会分崩离析(《外篇·马蹄》)[3]307。
在外篇《在宥》中,提出使天下人逍遥自在,而不是治理天下人。治理天下的尧,使天下人不得安静,而桀使天下人忧愁痛苦。都是违背德性的。赏罚使人难于“安其性命之情”,追求明、聪、仁、义、礼、乐、圣、智是违背人性的八种病症,这些都是不可鼓吹的。
3.无为智主。庄子推崇“无为智主”,反对以智巧治理天下,“阳子居”向老聃请教:“一个敏捷、果断、通达、好学之人,可否与明王相比?”老聃认为,这种人只不过如杂役办事,劳心又劳力,没有可比性。明王治理天下,功绩满满,却好似与己无涉,教化施舍百姓,百姓却好似不受依赖,从不称颂自己,使百姓各得其所(《应帝王》)[3]268-270。《外篇·在宥》中甚至提出“绝圣弃知(智)而天下大治”。在《外篇·天地》篇中,要想请啮缺当天子,咨询于许由,许由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啮缺为人聪明机警,天性过人,如果当了天子,他就会把人力的强加给自然,以自身为标准,依赖智巧,“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3]375甚至提出治是乱之源的观点。伯成子高之所以在尧的时候,情愿当诸侯,舜禹是回家耕田,因为尧时不用奖赏,没有惩罚,而天下大治,而舜禹时赏罚并用而天下纷乱。
总之,庄子认为,无为而治是一种天德,是自然的本性。“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外篇·天地》)[3]366统治者养育天下,无所贪而天下自然富足,不妄动,万物自然教化,深渊宁静无澜,百姓自然能够安定生活。
结语
全面深刻地考察一个事物,系统分析犹如一面透镜,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系统是由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体。乍一看,庄子的天下观,好像一味是消极的、无为的,其实,这一天下观处处关怀的是人物、物物之间的相处之道。时人的天下观主要是基于人的立场理解的产物,以文野来分辨文明的不同,而庄子以为,人仅是万物之一。人是人类之一分子,人类是对于天下,是万类之一,无法穷尽。“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外篇·秋水》)[3]512。在庄子的思想深处,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文野看待天下,尽管可以靠拢于某种方式,但其局限性也是必须被超越的。从道而论,万物并无分别,但在日常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辨,是由于人们的视域所致。得道者则应以无分别之心来看待这些现象。一切的不同取决于我们采取的标准、观察的视角。意味深长的是,在《应帝王》寓言故事里,浑沌七窍被凿后,存在状态是“死”而非“亡”,而在《庄子》话语系统中,死意味着隐藏,并不是消亡,《大宗师》是这样描述生死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3]220生死如昼夜轮回,这好似是一种暗喻:浑沌的死,一方面意味着终结,另一方面内含着新生,建构一种新的政教生活、天下秩序可能性[6]116。
内向型超越之典型。西方思想是主客二分式的,是主体逐渐战胜客体的过程,属于外向型的超越。中国思想则是推崇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重视自我的澡雪,是内向型超越。庄子天下观正是这一内向超越的经典写照,天下之中,万物一体,物我一体,《齐物论》中,南郭子綦正是超脱了外在事物的羁绊,才能真正做到形体如枯木,精神如死灰,达到形神分离,物我皆亡之境,这是一种身心皆忘的自我,真正达到了忘物、忘我、与道合一。
总之,庄子天下观的整体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特征,使这一天下之系统更为稳定,更为有活力,而这一天下观的背后之道是自然之道、平等之道、亦是超越之道。
当然,庄子天下观,不可能完美无瑕。这一天下观的核心是道,这道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笼罩,但是这些关系被无限地还原,还原到一种淳朴的至德之世。良好和谐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得以呈现的基础,秩序是有一定规则来维系的,而庄子对规则是拒斥的。这些都带有显著的乌托邦色彩,最终只能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烟雾迷蒙的海市蜃楼。
首先,作为天下的人是孤独的。庄子的“顺应自然”“不失其性”,最终必然导致人类个体之间的孤绝状态。生逢乱世,庄子的内心是孤独的,《齐物论》中隐士南郭子綦悠闲地靠着案几,望着天空,无所事事地吐着气息,“荅焉似丧其耦”[3]44。“耦”是另一个自我,仿佛丧失了自我,这是一种孤独的境界。这种孤独在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生在世,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其次,作为天下的社会是空想的。外篇《马蹄》勾画了一幅至德之世的人间幸福和乐图,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和谐相处,完全自由自在,互不干涉。生活在“绝对自由、安全、幸福地状态之中”[7]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