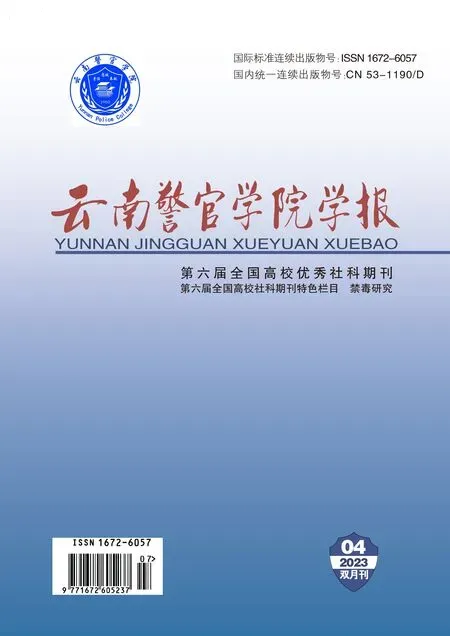社交媒体中邪教思想社会动员研究
赵凌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网络等社交媒体的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拓宽了宣传思想阵地。牢牢占领网络这一阵地,是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否则就可能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同时要清晰地看到,现实存在的各类邪教组织都在利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传播邪教教义、指挥邪教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违法犯罪蔓延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社会危害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如今,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邪教组织也相应调整动员方式,把互联网当作邪教动员的工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也随之成为宣传邪教思想和对潜在信徒进行动员的重要平台,成为实施邪教行为的先决条件;如果能够遏制住这股力量,就能对其造成重创。所以,对社会化媒体中邪教观念的社会动员进行研究,就成了一个亟待面对的问题。
一、社会动员原理
“社会动员”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学科之中,本文对术语中的“社会”与“动员”分别加以阐释。“社会”这一术语,在现代由日本传入我国,泛指除政府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与个体。“动员”作为一个舶来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在近代被引入我国,最初只是用于军事战争范畴。(1)邹奕,杜洋.“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15(05).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社会运动被认为是一种集体行为、一种思想倾向。从其实质来看,社会动员是指国家、政党、社会组织等,以某种形式,有系统地动员人民主动参加社会实践,并对某个问题,在态度、认知、思想、价值观等方面达成一致,从而达到自己的社会目的。(2)甘泉,骆郁廷.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J].学术探索,2011,(06).
社会运动理论主要有资源动员理论、框架建构理论等。从资源动员理论来看,资源被认为是社会运动的一大要素。丹尼尔·克雷斯(Daniel Cress)和戴维·斯诺(David A.Snow)等人提出了社会动员需要四种资源的观点,分别是物质、信息、人力和道德。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动员结构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人际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罗杰·古德(Roger Gould)认为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运动。因为,社会是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组成的网状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运动参与的影响体现在其具有“群体压力”,该功能是指成员的行为会受特定关系网络所影响,迫使其成员遵从群体内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国内学者赵鼎新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种政治行为,并提出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三个维度描述政治行为,将“社会运动”定义为有许多个体参加、高度组织化、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体制外政治行为。(3)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5,(01).此外,鉴于实践中社会运动的多样性,即使同一种社会运动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组织化程度可高可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可大可小,组织化程度高低不等,(4)赵鼎新.社会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这一定义较为符合邪教所追求的“社会运动”的特征。在其中,空间环境是除了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外,构成动员结构的重要一环,而不法组织传播和渗透邪教思想的一大重要虚拟空间环境正是社交媒体。所谓“社交媒体邪教思想社会动员”,即邪教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资源并努力实现诸如宣传邪教教义、动员潜在信徒参加邪教活动等目标的全过程。
在意识形态、共识、观念等方面,框架建构理论相较于前者更为注重。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认为,社会动员主要可分为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前者意在凝聚共识,即说服人们支持该运动的观点和立场;后者意在形成行动,即说服那些支持该运动的人,加入到行动中来。(5)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从大众媒体到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社会运动的形态,赋予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更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使得他们借助最新的通信技术借船出海,成为带有能量的政治力量。(6)Victoria Carty,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Technology,New York:Routledge,2015.上文所说的共识动员是指邪教组织利用社交媒体传播邪教思想,潜在信众便可能会在情感、心理和价值认同上形成共识;而行动动员则是以激进的态度鼓动信徒,深入地参加邪教的犯罪活动。
二、社交媒体邪教思想社会动员的特征
(一)明确的目的性
所有的社会动员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邪教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思想动员具有自身明确的目的性,并且多具有一定政治目标导向。“法轮功”媒体不仅对中国不友善,更显示其强烈的反华情绪,通过社交媒体宣传邪教反动思想,目标在于抹黑中国形象,推翻共产党执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法轮功”邪教组织利用境外媒体《华盛顿时报》发布的“新冠病毒是中国研发的秘密生化武器”文章进行炒作,企图将病毒来源政治化,对我国进行攻击、污蔑。“全能神”通过旗下媒体“寒冬”网站将教义的歪理邪说拍摄成各种视频、影片等,通过在线网络向东南亚各国传播,以其作为隐匿实体的工具,进行反政府政治活动、传播歪理邪说、制造虚假新闻。
除了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之外,邪教组织在宣传其思想时,往往打着“满足需求”的旗号来诱使群众信教。“全能神”邪教组织通过社交媒体声称病毒是“全能神”降临给世人的审判,信徒要营造危机感,努力进行传教活动,不做见证的人将被全部淘汰。约翰·史密斯指出,危机时刻使我们思维狭隘和意识脆弱,充满超越自身的资源依赖性的意识和愿意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意识。(7)[美]肯尼斯·帕尔加门特.宗教与应对的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这也就导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对于这种新型病毒的恐惧和一无所知。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不断有人无端感染、快速死亡的新闻消息,人类自身的脆弱感和无力感凸显,恐惧感被极大唤醒,这时,邪教“适时”奉上的简单“秘诀”就可能被当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应对方法。(8)陈文汉.邪教“防疫秘诀”的心理作用机制与防范对策[J].科学与无神论,2020,(05).邪教这种“满足需求”的目的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使得信徒抓住了“救命稻草”,更易被邪教思想所影响,进而参与邪教活动,走上一条不归路。
(二)严密的组织性
邪教组织一经壮大,其政治意图便暴露出来,企图与党和政府进行对抗,带有险恶的政治目的。为实现其政治目的,邪教组织不断聚财敛财,以庞大的资金规模完善组织结构。随着运动的组织性逐渐增强与手段越来越技术化,其资源动员的效率也随之提高。调查显示,世界各地大约有近万个形态各异的邪教组织,绝大多数邪教组织都利用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9)称职敏,张翔麟.邪教真相[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在全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一百多个专业性网站、三百多个地方性镜像的全球网络体系,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等平台的高效率和巨大影响力,不断升级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堵。“法轮功”组织花费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反华宣传活动上,其媒体体系每年的预算高达数千万美元。
邪教网络宣传的运行管理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邪教网站在技术支持、网络推介、宣传内容等方面的一体化;另一个是各种政治势力整合上表现为一体化的趋势。技术上,不断开发各种破禁软件,应用动态连接技术,并利用各种即时通讯,将宣传内容和破禁软件发送到境内。宣传内容上,组织各方面力量,使其内容更具有欺骗性和吸引力。其媒体网站与各种政治势力网站互相勾结,与境外的一些反华新闻网站相链接,增强了邪教组织的隐蔽性。
(三)效应的广泛性
邪教思想在社交媒体中之所以能够急速扩散,最重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门槛不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互联网上发布和接受信息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并且有相对较为庞大的群体进行传播扩散。(10)张秉楠. 新时期我国邪教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郑州大学,2016.目前,邪教教徒作为网络上的一员,这种新的身份使他们极为容易形成集体意识,并将邪教组织所谓的“理论”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扩散。在网络社会中,成员们若是遇到与自己有相同经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相互之间就会产生亲切感进而盲目信任彼此,这就容易让邪教的歪曲邪说传播开来。同时,由于社交媒体的交易成本低,只要有一个邪教组织的成员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冒充某个团体的追随者,那么这个团体的成员就会被当成普通人,从而让别人放松警惕。互联网上的舆情具有很强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具有共同认同的个人更容易进行信息的传播,一旦传播链被成功构建,舆情的影响力和影响力将会非常大。
“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社交媒体在全球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其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社交媒体将邪教信息大规模传播给数百万人,并在各个国家注册虚假账号大肆传播谣言信息。美化社交媒体“网红”,通过在“油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然后通过某种通用语言轻而易举传播到其他国家。邪教组织只会利用那些模棱两可的照片,或者将它们拼凑在一起,然后用文字来描述,制造出恐怖的数字,以此挑起人们的负面情绪,从而制造一个轰动的社会话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法轮功”邪教人员冒充医护工作人员录制视频,编造“截至当日武汉已有9万人感染”的谣言,试图制造恐慌,在视频中出现“大纪元网”的标志,这则视频是“法轮功”的造谣之作,企图借机混淆视听、扰乱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影响。
三、社交媒体中邪教思想的社会动员方式
(一)塑造社交媒体“动员潜势”
爱德华兹和麦卡锡(Edwards and McCarthy)把运动资源分为五种,其中,道义资源是指外界对运动的支持,具体形式包括同情性、法律正当性、团结性支持等。博得心理上的支持是促使人们参与某项运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来说,社交媒体邪教思想社会动员的第一步是要引起人们的兴趣、博取人们的同情,把普通公众变成运动的“动员潜势”(所有对社会运动参与保持“一般行动待发状态”和“特殊行动待发状态”的人)。(11)哈勒布亚提汉·吾克灭提汉(Wukemietihan Halebuyatihan).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动员及其反制策略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0.在境外的网站、APP,特别是“明慧网”等邪教组织设立的网站上,各种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真相”比比皆是,常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把自己包装成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形象博取同情。
“全能神”邪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其社交媒体“寒冬”网站,对外散布“最近爆发于中国的新冠病毒乃是教主为审判中国而降临给世人的灾难,也是为世界末日来临提供证据,众信徒要营造危机感,努力进行传教活动。邪教组织以“末世论”制造恐慌。宗教心理学认为,宗教信仰的根本原因是恐惧和依赖。这些邪教组织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欺骗和威胁民众,让人们不仅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也对政府、社会、人类、科学、文明等都抱有极大的敌意与失望。社交媒体中等这些“恐吓言论”得到一部分民众的赞同,把自己包装成遭受“迫害”的形象获取西方势力支持,塑造社交媒体动员潜势,进而增加更多被虚假消息影响的社会大众。
(二)社交媒体上的共识动员
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形成真理,这是“戈培尔效应”在邪教组织动员中的运用。他们不停重复群体成员的“共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群体归属感和价值观,令参与者沉迷而不自知。再经历一段时间的填鸭式灌输,人就容易放松心理戒备,从而被组织洗脑。(12)孙瑞.探析邪教滋生蔓延趋势及治理对策[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3).共识动员意在凝聚共识,让外界接受和支持运动所持的观点,说服人们支持该运动的立场和观点。网络社群明显存在着“同类相聚”和极化现象。(13)[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大连接[M].简学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首先,网络社群构建了单一主题下的精准垂直传播,具有开展深度劝服的潜能。其次,即时的互动通讯促使社群的传播信息较为深入,重复强化的互动构成成员之间的群体极化,社群成员在彼此影响中逐渐形成高度一致的价值信念和行为预期。(14)薛鹏,范宝祥.互联网环境下青年群体面对邪教的挑战与对策研究[J].科学与无神论,2020,(05).邪教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构建“新兴宗教”的身份进行邪教思想的共识动员,在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情况下,一些所谓的宗教人士在“包容开放”的幌子下宣扬西方意识形态,人们一旦接受了这种所谓的自由和多元化说辞,便会潜移默化地视邪教为“新兴宗教”。
当人类形成“自我”意识时,便出现了与“自我”相对应的“他者”。随着国家、民族等有界的团体产生,“他者”逐渐走向政治层面,“自我”与“他者”产生了明显的敌对关系。(1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邪教组织依托西方势力,通过社交媒体构筑我国“禁止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他者”身份,在一些所谓“人权报告”的加持下,使得我国逐步与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对立起来,严重破坏我国国际形象。挤压我国发展空间的同时,邪教组织骗取大量支持者,强化其内部凝聚力。
(三)社交媒体上的行动动员
为了将动员潜势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行动动员必须构建一种促进型的框架,来表达手段的有效性、行动的紧迫性与道德上的正义性。包括“法轮功”“全能神”邪教组织在行动动员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往往是精神领袖,他们在社交媒体中打造“网红”进行谣言传播。如2021年《大纪元时报》等“法轮功”喉舌投入高达250万美元,资助数名反华“网红”,伪造所谓的《追踪武汉新冠病毒起源》纪录片,不遗余力地宣传邪教,煽动国内外民众对我国政府的敌视、误解,这些邪教组织“网红”的社交媒体言论煽动性极强,并且拥有大量的“粉丝”群体。
邪教组织社交媒体行动动员具有隐秘性。传播学者库尔特·郎指出:“媒体迫使公众注意力转向特定的议题;他们总是提出一些对象来,建议个体去思考什么,了解什么,感受什么,而脱离其他要素。”(16)[美]希伦·洛厄里.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刘海龙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邪教网站通常分为综合性网站和专题性网站。综合性网站中直接或间接宣传极端思想的报道,常穿插散落在国际新闻中,具有隐秘性和迷惑性。专题性网站中以“有图有真相”的惯性思维表达传递歪理邪说,往往以新闻纪实报道开篇,嵌入传播邪教思想的内容。由于信徒学习都是直接了解信息,不可能直接触及外界环境本身,使其全部沉浸在一个“二手世界”中,因此,这些不实信息容易诱发信徒参与到邪教组织活动当中。甚至,邪教组织从高校网络社交媒体搜寻新生信息更容易躲避防范,拉拢新生入教的效率更高,更容易激发邪教成员参与活动的热情。(17)夏天.日本高校反邪教工作调查研究[J].科学与无神论,2019,(06).
四、社交媒体邪教思想社会动员的应对策略
对于社交媒体上邪教思想的社会动员,要以设置障碍为基础,打破其动员结构,使之动员机制失去作用,进而消除潜在人员参加邪教动员的兴趣和想法,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普通群众向危险群体转变,避免有危险的群体真正地从事邪教犯罪活动,提出不同类型风险防范对策。
(一)预防普通群众向风险人群转化
1.根除异端思想的温床
从根本上铲除邪教意识形态的社会土壤,从根本上瓦解社会化媒体意识形态的动员架构,使其丧失在社会化媒体(空间环境)扎根的土壤,才是最基本的策略。在邪教活动猖獗的地方,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邪教极端思潮作斗争,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开展“去极端化”的宣传和教育,明晰“邪教极端”的表现形式和后果,揭示邪教组织的本质、手段和真实意图,在社会媒体上加大对打击邪教的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力度,建设好主流反邪教媒体,通过主流社交媒体渠道,将反邪教知识传播给民众。其次,适时制定符合国情的《网络反邪教法》,明确界定网络社交媒体中常出现的邪教行为,规定相应处罚措施,不仅可以遏制邪教犯罪行为向网络空间滋生蔓延,而且可以提升民众对反邪教工作的认识,加强反邪教的宣传效果。再次,一些地区教育观念落后、群众风险识别能力不足,导致邪教思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动员和传播,所以要不断提升群众的判断和识别能力,从而弱化邪教思想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力。
2.坚持宗教中国化道路
社交媒体上进行的邪教意识形态社会动员具有严重危害性。我国首先应当从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完善社区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化对宗教的管理,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使其“遵从压力功能”失去作用。其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是幻想地反映超人间的社会意识形态,并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消亡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否认了所谓的鬼神、灵魂以及教主的“神力”“神通”等超自然观念,是应对邪教的重要思想武器。(18)段启明.科学无神论教育是防范抵御邪教的精神法宝[J].科学与无神论,2010,(02).要通过广泛宣传教育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引导民众正确看待生老病死、天灾地变等自然规律,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最后,要加强科学与无神论教育,提供科学的宗教信仰,号召人们在危难面前以唯物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导民众摆脱对牛鬼蛇神等超自然力量依赖,破除封建迷信。
(二)防止风险人群参与邪教活动
1.增强话语可信度,占领舆论高地
面对国外反华媒体对事实真相进行拼贴的虚假报道,我国主流媒体以及网络自媒体要发挥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中的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展现大国形象,旗帜鲜明斥责“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欺骗国际舆论的言论。要针对邪教组织社交媒体的不实报道,及时公开事实真相,曝光邪教组织在社交媒体传播极端主义的实质、不合法和不正当性,回击虚假报道,占据舆论制高点,压缩社交媒体上邪教思想社会动员的空间,争取国内外舆论主导地位。要将邪教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侵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众,让其在国际空间中无处立足。
2.告知参与后果,打消参与兴趣
框架建构论学者本福特认为,为了说服人们采取实际行动,社会动员方往往会阐述采取行动的有效性,诱导风险人群形成采取行动可达成目的的心理。对此,要避免邪教组织利用社交媒体进行邪教思想动员,将危险人群转化为参与者。必须向民众进行宣传,让他们知道加入邪教组织的后果,从而使社交媒体邪教思想社会动员在可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中失去吸引力。要充分发挥电视、报纸、书籍等主流传统媒体的作用,将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可靠性以及积极性与新型社交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充分结合,集中整合资源制作一批优质的反邪教短视频,针对各类反邪教组织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APP客户端,加大移动端的信息传播力度,主动播放科学知识视频,加强正面宣传弘扬正能量,进而提高抵御邪教侵蚀的能力,降低高风险群体的参与意愿,抑制高风险群体通过社交媒体的极端主义思维转变为真实的实施者。
(三)针对参与者的防范策略
1.提升网络技术水平,加快构建网络反邪教围墙
通信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丰富了促进社会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被邪教组织所利用。随着大数据、自媒体等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邪教组织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雇佣了网络技术人才,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进行招募和实施攻击行为,因此,提升网络技术运用能力,能够有效组织邪教社交媒体的思想动员。首先,可以借助大数据等关键技术,强化社交媒体空间的“围堵”。可以与相关运营商、研究团体等协作,及时屏蔽那些能够快速和有效进行信息传播的度量大的可疑节点;及时提醒或屏蔽领袖式的鼓动者发送的有关邪教信息,定位并分析“活跃人物”。其次,加强基于网络地址的网站过滤技术,根据用户所访问的网站地址是否在境内来决定放行或者封堵,重点屏蔽“明慧网”“大纪元”等邪教网站。再次,开发与邪教相结合的移动版网站或APP应用,使用智能分析技术应用在反邪教领域,打造网络反邪教平台,提升反邪教信息的传播效果,通过微信群这样的新型社群,打造新型帮扶模式,以多方发声形成深度说服的线上环境,推动形成邪教成员教育转化的帮扶机制。
2.加强国际反邪教合作,构筑反邪教命运共同体
社交媒体的运用,缩短了全球范围的空间距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邪教治理工作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参与,才能遏制社交媒体中邪教思想的动员。从国际反邪教斗争上来看,一些国家认可中国对邪教组织严厉打击的政策,呼吁学习借鉴我国治理邪教所制定的法律或采取的措施,为我国建立国际反邪教合作网、塑造国家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各国政府和人民对邪教危害性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民加入到反对邪教的阵营,壮大了国际反邪教力量,为构建反邪教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了良好基础。因此,各国应在反邪教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引进谷歌等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经验和技术,与推特等全球性社交平台公司进行直接合作与沟通。
五、结语
本文以社会运动理论为视角,分析社交媒体中邪教思想动员的特征,探讨社交媒体中邪教思想如何通过构建“动员潜势”将普通群众诱变成为风险人群,并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凝聚群众共识,通过社交媒体的优势进行邪教思想行动动员。应对社交媒体中邪教思想的社会动员,要从预防转变、防止参与、行动限制三个方面着手,牢牢掌握社交媒体网络生态主动权,压缩邪教思想滋生、蔓延及发酵的空间,削弱邪教社会动员能力,为群众营造安全的线上线下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