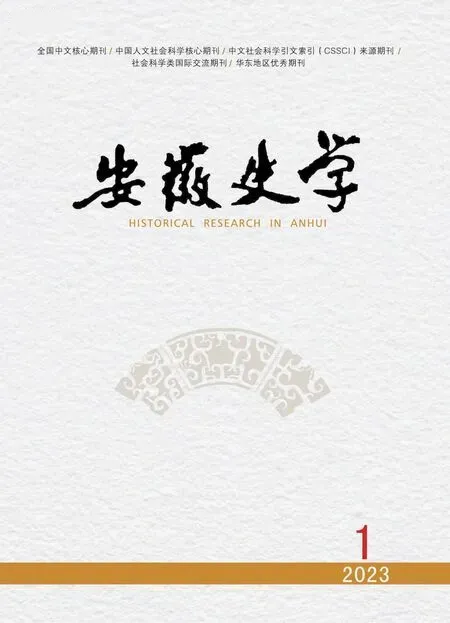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1941—1945)
——基于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考察
曲利杰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新四军在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开展了对日军的瓦解工作。由被俘日军以及主动投诚的日军士兵组成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为活跃在华中敌后开展敌军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相对华北来说,新四军所创建的日本人反战同盟不仅起步较晚,其规模也相对较小,但在俘虏日军士兵和反战工作上却不容小觑,甚至引起了日本军部和统治阶层强烈的反响。迄今为止,有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延安为中心的八路军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国民党地区的活动。关于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相对较少。(1)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徐则浩:《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黄义祥:《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赵新利:《八路军的日语学习培训》,《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赵新利:《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対日プロパガンダ戦術戦略:日本兵捕虜対応に見る2分法の意味》,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2011年;安井三吉:《抗日戦争時期解放区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近きに在りて》3号,1982年;秦郁彦:《中国戦場の日本人捕虜》,《拓殖大学論集》201号,1993年;姫田光義:《趙安博回想録》,《世界》1998年10月。关于华中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曹晋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中的组织与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对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立和活动进行了相关论述。而且在有关方面的研究上以往都区别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鹿地亘(2)鹿地亘(1903—1982),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1938年,鹿地亘经郭沫若引荐,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主要协助第三厅国际处进行对敌宣传,并致力于日军俘虏的思想教育。、野坂参三(3)野坂参三(1892—1993),又名冈野进,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4月到延安,曾以林哲、冈野进为笔名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1946年1月12日回到日本。以及原日军俘虏的回忆录中都显示两党在反战工作上是有联系和合作的。(4)参见[日]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同成社,1982年;鹿地亘資料調査刊行会编:《日本人民反戦同盟資料》第9卷,不二出版,1994年;[日]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此外,日文方面的资料也有待挖掘。(5)[日]藤原彰、姬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收录了原新四军俘虏香河正男、古贺初美、山本一三等的采访和相关人员的回忆资料。日本档案馆所保存的: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組繊系統表》,《外事月報》1942年8月;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内地人)組織系統表》,《外事月報》1944年3月。这些资料记录了新四军中日人反战同盟各支部的具体情况,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的建立和发展、人员组成、活动范围及其影响等,从而尝试更全面地理解华中日本人反战组织的真实情况。
一、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初步建立
1937年10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共领导下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从1938年4月开始,新四军各支队相继挺进华中敌后,创建了包括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省在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新四军开展了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并改造了部分日军俘虏,为华中敌后日人反战组织的兴起,准备了骨干力量。1938年7月,新四军在金坛附近战斗中俘获第一个日军俘虏香河正男;同年8月,在安徽当涂境内俘获田畑作造。之后又在江苏、湖北、河南等地俘获后藤勇、三谷端一、滨中政志、大久保喜二、森田义男等数名日军士兵。随着敌军工作的深入开展,被俘的日军士兵逐渐增多。据统计,1938年7月至1941年7月的3年间,有92人被俘。(6)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在1941年6月的调查报告书中显示:关于日军俘虏,新四军司令部有13人、苏北5人、第一纵队2人、第三纵队1人,大约有20个俘虏。(7)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蘇北共産地区实情调查報告書》,1941年,第130页。根据政策,大部分俘虏被释放回去;对自愿留下来的日俘,则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在新四军敌军工作人员有意识的启发和培养下,留下来的日军士兵不仅转化思想,而且积极投入到各种反战组织中工作。
华中地区日军俘虏最初进行的反战活动,史料上可以确认的是,1938年11月6日,香河正男、田畑作造联名发出的“通知我的兄弟们(第一号)”的传单。(8)即“我か兄弟達二知ラス(第一号)”,参见[日]藤原彰、姬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67、168页。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滨中政志、田畑作造、冈本一利5人在皖南集体加入了新四军,开始真正的反战活动。(9)袁树峰、陈建辉:《在华日人反战纪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这标志着华中敌后日人反战力量已经产生。同年春,日共中央委员、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协助中共指导敌军工作。1940年8月,在野坂参三的指导下,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随后在新四军敌工部门的指导下,一些经教育转化过来的日本士兵,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
1941年11月11日,新四军第五师在其所在地湖北大悟山成立的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是华中根据地的第一个反战同盟支部,也被称为第五支部。(10)华中地区各反战同盟支部的名称,并没有按数字排序,而是按所在地区命名的。这里的第五支部是对应新四军各师的编制序列而定名的,一直沿用下来,未作改动,实际上应称为“鄂豫支部”。支部长是坂谷义次郎,副支部长是森田博美。据鄂中地委敌伪工作部部长黄民伟回忆,主要的盟员有大久保良志、星文治、中野重美、松原秀雄、佐佐木更三、大久保喜二、森田义男、森增太郎等十多人。(11)黄民伟:《我所知道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湖北文史资料》1995年第1期,第199页。该支部成立后,敌军工作发展迅速,1944年初,该支部盟员已增加到100多人。(12)曹晋杰:《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中的组织与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125页。其中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13)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1944年夏,坂谷义次郎在执行任务牺牲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派遣松平于1945年1月到达大悟山,担任代理支部长。(14)黄民伟:《我所知道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湖北文史资料》1995年第1期,第201页。关于该支部的其他盟员,据日本资料记载有:山口清治、水木信幸、板谷义造、藤原勝美、山崎、栗本嘉雄、西川兼一、西部松一、松原良教、古泽秀雄、岩崎操、森川敏夫、林啓二郎、森山善一、安藤久子、小山留吉、水元、金勇南 (朝鲜人)、藤崎勇、永田繁、村山洪用、寺奥定男、岛田一郎、富永勝夫、佐野幸男、高野重一、水野天順、角田一郎、松永一义、杉浦一崇、庄田、高桥、松井、平松啓二、冈岛、北村宪夫、岩崎美佐夫、山本三郎、山本龟太郎、田中、铃木、藤池、佐々木更三、中岛、平崎、川岛、松本、中川、铃木瀨太郎、平尾等,共计60人。(15)⑨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組繊系統表》,《外事月報》1942年8月;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内地人)組織系統表》,《外事月報》1944年3月。
关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活动范围,根据地方文献记载,从1942年春到1945年正月,坂谷义次郎作为支部长的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曾多次在涨渡湖地区活动。常驻地点有汪大房湾、陶家大湾、程底下湾等。(16)张剑南、余文祥:《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在涨渡湖的活动》,《湖北文史资料》1995 年第1期,第202页。亦有资料显示,1944年2月,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在涨渡湖地区的滨湖嘴汪大湾,与当地农民过农历新年。(17)许恺景:《日本反战同盟在新洲》,《武汉文史资料》2003 年第10期,第22页。上述文献所记载的涨渡湖位于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距离鄂豫支部成立的大悟县100公里左右,陶家大湾位于大悟县南50公里左右。可以看出第五支部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大悟县附近。
1942年3月15日,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在新四军第一师的江苏省东台县成立。支部长为香河正男,另外还有滨中政志、田畑作造、横山岩吉、后藤勇等盟员共计5人。(18)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会:《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第231页。之后又增加了松野觉、冈本一利等人。1943年5月,香河正男就任新成立的反战同盟华中地方协议会会长,支部长改由滨中政志担任。(19)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161—162、163页。在1944年3月5日的车桥之战中,出现了很多俘虏。其中,山本一三等14名日军士兵加入了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同盟成员增加到24人。(20)罗宝蔡:《新四軍は日本兵捕虜をどう扱ったか》,《季刊現代史》4号,1974年,第80页。苏中支部成员最多时曾达到70余人。(21)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总政治部联络部1997年版,第38页。根据日本档案显示,除了上述日人之外,另有松田一夫、三谷端一、水野正一、石田光夫、渡边、田井达三、中孝次郎、岩田文雄、林正义(朝鲜人)、任延桓(朝鲜人,日本名丰川秀雄)、吉永八寿秀、粟花落岩、清水鲁吉(本名加藤京一)、梅村政一、宫本一郎、寺尾正、太田正年、水野正一、长绳真二、水谷明、大仓矶市、冈崎周治、久保一男、南乡进、石川芳男、封尾等。(22)⑨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組繊系統表》,《外事月報》1942年8月;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内地人)組織系統表》,《外事月報》1944年3月。关于该支部的活动范围,据相关学者考察,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是在东台县一仓村组成的。1942年春起,新四军第一师驻扎在江苏启东。现在江苏省启东市有“新四军第一师师部驻地”的纪念碑。(2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江苏省革命遗址通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据估计,新四军第一师建立的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活动范围在江苏省东台市和启东市附近。
苏中支部成立不久,日军士兵跟随新四军转移到苏北,在香河正男的参与下筹建日本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1942年7月15日,日本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在新四军第三师所在的江苏省阜宁县正式成立。支部长是古贺初美,同盟成员有香河正男、田畑作造、堀本龙藏、坂桥由五郎、古桥角五、竹田信、林田谦次、村田等。(24)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会:《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第231页。1942年8月,香河正男、田畑作造返回到苏中军区。根据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所刊登的苏北同盟支部在1943年6月8日发出的电报显示,其盟员有古贺初美、古桥角五、竹田信、堀本龙藏、林田谦次、坂本节未。(25)《日人反战同盟苏北分盟电冈野进》,《解放日報》1943 年7月2日。1944年,古贺初美被安排在华中地方协议会,吉春、清水加入。到了1945年,苏北支部又增加青柳坂次郎、森垣等,古贺初美回到了苏中支部。(26)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161—162、163页。
1942年2月26日(27)关于反战同盟淮北支部的成立时间,说法不一。本文根据当事人张文华(时任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宿东敌工站站长)的回忆,见张文华:《攻心战——淮北抗战根据地敌军工作》,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4页。,在新四军第四师驻地洪泽湖附近的泗洪县半城镇成立了淮北支部,从苏中调来的后藤勇担任支部长。(28)④⑩曹晋杰:《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中的组织与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2期,第126、126、125页。成员包括矢口庄司、林博二男、池田太郎等7人。同年末,小井勇、瓦国义、太田延(女)等10人也加入了该部。1943年11月27日,新四军十一旅在灵璧北张大路附近击溃日伪军时俘虏了日军士兵远藤,经教育改造后参加为盟员。(29)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新四军抗战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之后该支部又增加小仓、松田、森垣嘉一。(30)④⑩曹晋杰:《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中的组织与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2期,第126、126、125页。关于该支部成立的具体成员名字,中国方面的资料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日方资料显示,到1944年,除了以上几人外,该支部其他成员有:何某、峰村皋月、野村隆、大泽光子、清水安人、岩崎、森光子、佐治木、平井、大野务等。(31)⑧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組繊系統表》,《外事月報》1942年8月;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内地人)組織系統表》,《外事月報》1944年3月。
同年11月,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军区成立了淮南支部。支部长是高峰红志,盟员有加藤肇、吉春务、清水松田、藤井文章。(32)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会:《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第23l页。1943年,淮南支部在发出关于野坂参三秘密身份的贺电显示,其盟员名字有高峰红志、吉春务、清水、藤井文章、加藤肇。(33)《日人反战同盟苏北分盟电冈野进》,《解放日報》1943 年7月2日。日方档案记载,该支部成员另有田谷春雄、永田正一、中野义雄、森忠等人。(34)⑧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組繊系統表》,《外事月報》1942年8月;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内地人)組織系統表》,《外事月報》1944年3月。根据泷泽三郎的回忆,1945年初到达淮南支部时,该同盟成员曾达到20名。(35)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关于其活动范围,反战同盟淮南支部的成立地点是在新四军第二师驻地天长县。(36)④⑩曹晋杰:《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中的组织与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2期,第126、126、125页。1943年1月到1945年2月28日期间,新四军第二师师部的驻地在江苏省盱眙县城南的黄花塘镇。(37)张传英、张肇俊:《新四军军部变迁》,《党史博采》2007 年第8期,第43页。黄花塘距离天长市北部大约40公里,因此反战同盟淮南支部的活动主要在江苏省盱眙县附近。

表1 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情况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继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后,从1941至1942年,华中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鄂豫、苏中、苏北、淮北、淮南五个支部,其组织名称一般都沿用了所处根据地的名称。盟员人数由1940年的若干人发展到抗战末期的百余人。但是这一阶段,由于各根据地之间的反战同盟缺乏组织上的统一和紧密的联系,日人反战的活动是孤立和分散的,敌军工作效果并不显著。就具体工作而言:“华中日军工作,除了个别地区在进行组织工作而外,一般的还是停留在宣传工作的阶段。”(38)《新四军政治部关于华中反战同盟及日军工作情形致冈野进电》(1944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二、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化
需要强调的是,抗战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新四军各根据地成立的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是重庆西南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的重要一支。早在1939年12月23日(39)关于在华日本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的时间,据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记载,其成立时间是12月23日;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则记为1939年12月25日。但是当时报纸记载以及板本秀夫的回忆录《我们的反战工作》都明确记载是12月23日,而且板本秀夫是西南支部的成员之一,所以12月23日的时间更为可信。,鹿地亘就在广西桂林成立了第一个反战组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开启了国统区的日人反战运动。之后鹿地亘通过周恩来向中共提议在延安也建立这一组织:“前不久得到消息,即向延安日本人反战组织支部提供纲领规约的要求,通过中央送到,成立延安支部。”根据鹿地亘在其著作中所论述:“中共此前将战俘送回日军原部队,对于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的军队来说,带着战俘不断移动是很麻烦的,我们认为教育几个月后再送回的措施是必要且适当的。然而,这些俘虏回到原部队后的消息却无从得知。其中有传言说会给予其严厉的刑罚。鹿地亘曾告诉过周恩来这件事(当时周恩来在武汉),之后冯乃超也报告了同盟活动。周恩来说如果这样的组织运动有可能的话,八路军也要立刻着手。”(40)④⑦⑧⑨[日]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第87、87、228—229、164、204页。
1940年3月,野坂参三到达延安不久,与被送到延安的日本人通过中共发表了规约纲领,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这个过程中,野坂参三是如何与重庆取得联系的,目前尚不清楚。根据野坂参三在鹿地亘《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出版之际,就鹿地亘所在的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曾说:“因为有你们先驱者的经验和模式,所以我们在延安的工作也比较容易着手”。(41)④⑦⑧⑨[日]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第87、87、228—229、164、204页。鹿地亘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消息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传到延安的,这一点暂且不论。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这个名称可以确定的是,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受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启发,组建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42)[日]青山和夫:《謀略熟練工》,妙義出版,1957年,第135页。
1940年7月20日,鹿地亘在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基础上于重庆创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重庆反战同盟总部成立后不久,就收到了新四军内日人反战士兵的来信,“希望与西南同盟总部密切联系,统一接受指令,向革命胜利斗争到底”。(43)鹿地亘資料調査刊行会:《日本人民反戦同盟資料》第9卷,第303页。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1940年10月7日,新四军的日人反战士兵向鹿地亘汇报了近况,内容大意是:“我们五个人正式参加新四军后已经在执行同盟的纲领。我们的工作包括对现有部队的士兵等进行日语教育、喊口号以及反战歌、其他宣传单的撰写等。但我们的工作仍是很不成熟的,尚待今后各位同志的正确指示。”(44)④⑦⑧⑨[日]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第87、87、228—229、164、204页。同一时期西南反战同盟机关报《真理的战斗》也报道了这一消息:“鉴于近来各战区的日本同志陆续有参加同盟的要求,重庆总部等待目前正在出动前线工作队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一举在各战区建立分会(支部)。”(45)④⑦⑧⑨[日]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第87、87、228—229、164、204页。此后新四军反战士兵又多次写信和发电报给重庆总部,希望实现日人反战同盟的统一。
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所在地区的日军反战士兵与鹿地亘都没有了联系:“由于事态的变化,已经没有期待在各地设立同盟支部的可能性。新四军内日本同志的命运令人担忧……只能等待他们在各地的自主创新。”(46)④⑦⑧⑨[日]鹿地亘:《日本兵士の反戦運動》,第87、87、228—229、164、204页。1941年8月鹿地亘组织的反战活动被国民党停止,国统区的日人反战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后虽经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努力,同盟的反战活动得以继续,但成效已大打折扣。(47)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反战同盟成员全部被隔离在贵州省镇远的收容所。只有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重庆允许设置研究室,继续进行形势研究。最后不得不把反战的中心转移到中共方面。关于皖南事变后中共领导下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与重庆之间的关系,野坂参三提到:“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对日军工作,必须作为新四军及八路军对敌工作的一翼,以他们的指示和方针为基础……但是,不能因为这样说,便认为反战同盟在组织上是新四军和八路军敌工部的一部分。日本人反战同盟在组织上仍然属于重庆的同盟总部。”(48)[日]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選集·戦時編》,第306页。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尽管新四军内日人反战组织曾试图与重庆总部取得联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重庆方面的直接指导,总部与各支部的联系基本处于隔断状态。而且华中初步成立的五个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都不是在延安野坂参三的指示下进行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至少在1938—1939年这一阶段,新四军地区的日本俘虏没有从华北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直接接受指示和指导的迹象。虽然八路军的敌军工作方针和新四军方面共有,但双方的日本反战战士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往来。”直到1942年10月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后,延安才终于派出了三个人。约1943年7月开始,华中地区日本人反战组织直接接受延安的指示和指导。(49)[日]藤原彰、姬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68页。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野坂参三开始对日本人反战同盟进行改编。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决定组成日本人民解放联盟。(50)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会:《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第89頁。根据指示,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长的联席会议决定解散日本人反战同盟,组成日本人民解放联盟。(51)《华中日人反战同盟同意组织解放联盟》,《解放日报》1944 年3月25 日。相比之前建立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不仅政治色彩更浓一些,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职责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那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则更进了一步,其中心任务还有“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日本”。(52)野坂在日人解放联盟纲领草案中,共提出了八条:1.结束敌对状态;2.实现持久的和平;3.将使我国强盛繁荣的经济政策;4.推翻军国主义的独裁统治;5.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6.改善人民生活;7.保障士兵和水兵家属的生计;8.组织人民的政府。参见[日]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選集·戦時編》,第365—370頁。工作对象也从日军士兵扩大到在华日本侨民和日本国内人民。
1944年5月5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在淮南正式成立。香河正男担任该协议会委员长,高峰红志担任副委员长(53)[日]藤原彰、姬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170 页。,委员分别是松田谦次、田畑作造、清水鲁吉、加藤肇、矢口庄司。这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领导机构。华中地方协议会之下直接设立各个支部,不再分地区建立协议会。华中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改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支部,分别是鄂豫边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5个支部。(54)曹晋杰:《日本人反战同盟在华中的组织与活動》,《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2期,第126页。同年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浙支部在新四军苏浙军区所在地成立。1945年7月31日,有苏中、苏北、淮北(1945年6月6日,淮南支部并入淮北支部)、鄂豫、苏浙五支部。(55)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356—357页。在重庆的鹿地亘得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的消息,也对此作出了响应,表示“完全赞同在重庆成立类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设置重重障碍,以致重庆和根据地这两大地区的反战组织统一未能实现。(56)[日]鹿地亘:《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闘争資料》,同成社,1982年,第318页。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后,华中、华北两大根据地的日人反战组织也实现了统一,日人反战组织的活动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44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今后的敌军工作,要通过日人反战组织及日人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5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这样,华中与华北的日人反战组织与敌工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敌工方针并依照方针开展对敌工作。在前线对敌宣传中,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已经代替了最初培训他们的敌军工作人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44年12月,约300名日军战俘在中共根据地前线进行反战宣传。(58)[美]埃默森著、[日]宫地健次郎译:《嵐の中の外交官—ジョン·エマーソン回想録》,図書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第157页。到抗战末期,华中、华北共有21个支部,1000多人。(59)关于日人解放联盟的组织结构,到1945年5月为止,在华北、华中各地相继建立了延安支部、晋西北支部、晋察冀支部、晋东南支部、冀中支部、冀鲁豫支部、太行支部、太岳支部、滨海支部、鲁中支部、鲁南支部、清河支部、胶东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等共计21个支部。参见林谷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官兵中的反战运动》,《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71页。
三、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新四军各师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军工作部的领导下,日本人反战同盟华中各支部在争取和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第一,大力开展对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他们通过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战前喊话等形式向日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仅1942年6月至9月,日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就散发宣传品94种、25万多张。(60)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第172页。由华中日人反战同盟创办的日文报刊,如鄂豫支部的《红旗报》《日本军之友》,苏北支部的《日本兵队之声》,苏中支部的《新时代》,苏浙支部的《解放周报》,淮北支部的《士兵之声》等,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军长官对士兵的压迫、日军士兵的思乡和厌战之情,引起日军士兵的共鸣。这些报刊总发行量达20多万份。(6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1942年冬至1943年,苏北支部盟员还在佃湖、八滩、陈集战斗中,靠近阵地前沿向日军喊话,使敌军心涣散,先后有十多名日军士兵投诚。(62)⑩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第39、42页。在反战同盟的宣传影响下,日本官兵有因绝望而集体自杀的,1945年5月至6月,16名驻扎在盐城和东台的日军集体自杀。驻东台独立混成旅团长的亲信、五十四大队大队长坦马,也因对战争绝望选择切腹自杀。(63)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38页。
第二,协助新四军教育转化日军俘虏。例如1944年3月4日,苏中新四军在车桥战役中,俘获日军官兵山本一三、清水鲁吉、梅村政一等共48人。由于这些日军官兵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态度十分骄横,在苏中支部成员香河正男、冈本进等的协助下,终于使其转变了立场,其中有24人留下加入了新四军。山本一三还写了《关于练兵的意见》,对新四军练兵大有帮助,得到了师长粟裕的肯定,并发表在《苏中报》上。(64)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38页。同年6月,新四军第三师俘获以日军警备团长柳板次郎为首官兵六人。在苏北支部成员的感化下,除一人要求返回原部队被释放外,其余五人都加入了反战同盟。(65)曹景文、唐莲英:《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为提高这些日军战俘的政治觉悟,1944年新四军政治部还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该校附设在苏中公学内,对外称作“国际兄弟队”,对内称第20队。“国际兄弟队”共有学员43人,他们大都是反战同盟各支部的成员,主要学习内容是时事政治。学习结束后,这些学员被分配到新四军各部队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线从事敌军工作。(66)⑩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第39、42页。
第三,直接参加对日军的作战。在地方武装队的配合下,第五支队的十几名盟军成员与第五师敌军工作队一起,伏击了从湖北黄冈姚家开往河口的一支日军小部队。其中盟员森增太郎亲自击毙了日军队长,并缴获了队长佩带的军刀。在战斗结束后,森增太郎向李先念师长赠送了这把军刀,李师长亲笔写信给予赞扬。(67)③⑥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第41、40、41页。1944年3月4日,在车桥战役中,反战同盟华中地方协议会会长香河正男亲临第一线,带领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同志配合新四军的军事行动。在激烈的战斗中,盟员松野觉不顾机枪扫射,将两名日军击毙,却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牺牲。(68)⑧[日]藤原彰、姫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176、177頁。日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支部长坂谷义次郎,在应城执行任务时,被日本宪兵队跟踪逮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最后英勇牺牲。(69)③⑥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第41、40、41页。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牺牲的日本反战士兵至少在30人以上。(70)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有34人,其中新四军日人反战同盟盟员5人,他们是松野觉、森增太郎、后滕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等。参见总政治部联络部编:《八路军敌军工作史》上卷,总政治部联络部1998年版,第55页。
第四,主动参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于日寇的野蛮“清乡”和频繁“扫荡”,以及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使得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资极其匮乏。日本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在支部长古贺初美的领导下,参加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其中开荒面积占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的三分之一,生产量占四分之一。因此古贺初美代表苏北支部出席了第三师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之后当选为盐阜区参议会的参议员。(71)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第164页。反战盟员还从发给他们的微薄津贴费中,拿出一部分接济受灾群众。1944年4月2日,苏中支部捐款245元(法币)给四分区灾民。(72)③⑥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第41、40、41页。与此同时,日本人反战同盟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思想改造。根据中央的指示,华中局在发出《关于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后,于1942年6月至1945年8月的3年间,展开了整风运动。(73)王辅一:《新四军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古贺初美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42年,由于他带领指挥的一场战斗中出现了两名负伤者,作为新四军大队长的古贺接受了一周左右的批评和调查,并被要求进行自我坦白和阶级划分。虽然古贺的出身最终被定位为劳动阶级,但据其说这是一项伴随着严厉批评的整风。(74)⑧[日]藤原彰、姫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176、177頁。之后,因为表现良好,古贺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中日人反战组织所开展的反战斗争,引起了日本军部和统治阶层的强烈反响。对于新四军地区的日本人反战活动,日军很早就开始警惕。1939年3月,华中地区的“中国派遣军”报道部制作了名为《对中国宣传实施参考》的文件称:中国方面“利用俘虏进行宣传,我们也应该多加注意”,日本方面也采取了相应措施。(75)中支派遣军报道部:《対支宣伝実施参考》,1939年,第56页。1940年4月29日,日军又发布了《告派遣军官兵书》,指出:不少在华日人为了贪图私利、甘心资敌,成为中国人的工具,并做着有损日本皇军体面的事情。这些“不良日人”甚至让中国人假借自己的名义做出不利于我方之事,为谋求个人利益而违背全面统一领导,并告诫“此种情况如若任其发展”,不仅会使“圣战”毫无效果,而且会导致中日之间永久的抗战。因此训导日军官兵必须“带头遵守纪律、以身作则,促使不良日人反省觉悟”。(76)昭和15年9月大本営陸軍部研究班:《支那事変ニ於ケル支那側思想工作ノ状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蔵資料,C11110754400。为破坏反战组织,日本军部还派遣间谍打入新四军以及日人解放联盟内部。例如,武汉日军宪兵司令部派遣一名日本兵带一名中国妇女,逃到鄂豫边区,但被鄂豫边支部长坂谷义次郎识破。(77)黄民伟:《我所知道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湖北文史资料》1995年第1期,第199页。
由于日军俘虏的加入,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在宣传质量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例如抗战伊始,因为新四军日语人才太少,常常读错了音,以致在喊话的时候,连日本兵都听不懂。(78)《〈每日译报〉报道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和日常生活》(193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此文原载1939年1月22、23、24、29日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题为《自第三战区归来》,署名沙克芳记录。自从反战同盟成立之后,一些标语由他们制作,阵前喊话也由他们执行,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认为1941年3月在苏北收到的传单:“文字、用语、内容等都颇为精炼……这对我军将士的士气有不好的影响”。(79)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蘇北共産地区实情调查報告書》,1941年,第125页。关于日人反战同盟制作和散发的这些传单,虽然效果很难测定,但是长期发展下去,会达到扰乱日本士兵军心、涣散军队意志等效果。1944年新四军政治部在《关于华中反战同盟及日军工作情形致野坂参三电》指出:“估计目前在华中很多日本士兵是见过反战同盟宣传品的,他们并且知道本军中有很多日本同志。”例如,1943年日军在向新四军第四师“扫荡”时,日军士兵问老百姓:太田(女同志)还好吗?临撤退时,在后滕住的房门上写道“日本人后滕勇驻此”。苏中地区滨中等反战士兵的活动,更引起了日军特务机关的注意,日军曾悬赏万元通缉滨中。(8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5),第199页。日军在新四军第三师活动地区也发给日本俘虏传单,叫日军士兵不要再受新四军“欺骗”。1943年,从日军自动逃跑出来寻找新四军,因寻不到而自杀的,在三师地区有三名,一师地区有两名,其他尚有数起未能证实。由此可见,“华中反战同盟进行的宣传工作,已相当深入,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引起了日军大大的注意和憎恨”。(81)《新四军政治部关于华中反战同盟及日军工作情形致冈野进电》(1944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5),第199—200页。据1944年3月在车桥战役中被俘的山本一三回忆说,在日军的阵地上,他知道即使被新四军俘虏也不会被杀,希望回去者可以回去,但是在这个阶段谁也没有想过要自杀。(82)[日]藤原彰、姬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186页。
日人反战组织的影响力甚至达到日本的决策中枢。如第二部分所述,1944年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最终目标从“反战”转变为日本的“解放”,这对日本统治阶层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日本司法省在1945年6月的一份文件中明确强调,“需要警惕国外共产主义分子,尤其是在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军陆军省在相关文件中警告:“从内部离间军民、煽动反战思想,必须采取严厉措施。”(83)《敗戦直前の思想事務家会同記録》,《季刊現代史》,1973年,第86页。同年2月近卫文麿给裕仁的奏折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以日共代表野坂为中心。他们在苏联和中共支持下,以打倒军阀,确立民主政治体制为纲领,在当前展开反军反战活动。他们对在华皇军官兵和日人宣传左倾的失败思想,并且争取他们。还与国内左翼分子接触,如果不提高警惕,等待国内革命时机成熟,他们可能成为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急先锋。”(84)⑦[日]鹿地亘:《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ける中国での日本人反戦運動》,《労働運動史研究》,1965年9月,第262页。文中既指出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动向等,也指出了“败战必至”“该忧虑的是共产革命”,进而向天皇提出应“终结战争”“寻求和平”。从结果来看,近卫文麿的主张并未被天皇采纳,但却成为八月宫中团体的终战工作与天皇“圣断”背后的暗流。(85)⑦[日]鹿地亘:《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ける中国での日本人反戦運動》,《労働運動史研究》,1965年9月,第262页。当然,正如吉田裕指出的那样,这篇上奏文“过于主观,过高评价了革命前提条件的成熟”,但“反映了战争时期巨大的社会变动,这也是事实”。(86)[日]吉田裕:《敗戦前後》,青木書店,1995年,第36页。
如果仅以敌军投降人数来讨论华中日人反战运动的效果,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2022人。(87)在全面抗战八年里,中国共产党共俘获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5096人,新四军俘获2022人。新四军方面,从1938年6月28日在镇江竹子岗孔家迈伏击战中首次俘获日军开始,至1941年5月共俘371人;1941年6月至1942年5月俘158人;1942年6月至1943年5月俘125人;1943年6月至1944年5月俘205人;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俘194人;1945年6月至同年12月底俘969人。参见南京军区政治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卷,第31页。关于新四军地区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人数,日本方面掌握的人数为1942年8月末有45人,1944年2月末有79人。(88)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外事月報》1942年8月、1944年3月。后者的数据与1944年6月叶剑英提出的人数66人比较接近。(89)1944年4月,华北的解放联盟成员有223人,华中的解放联盟成员有66人。参见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社1944年版,第12页。到战败时为止,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总人数为139人左右(参见表1)。(90)数字来源: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組繊系統表》,《外事月報》1942年8月;内務省警保局外務諜編:《在支不逞邦人(内地人)組織系統表》,《外事月報》1944年3月。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方面的俘虏数量、投降者数量、反战同盟成员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即便如此,一百多人的盟员数量也绝对不容小觑,而且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影响到战后。在新四军地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士兵并没有马上结束战斗。很多部队没有解除武装并且在城市和铁路等方面进行警备,与新四军持续交战。在1945年12月19日的江苏高邮战役中,日军不接受投降劝告而进行攻击,在新四军的猛烈攻击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积极配合宣传,最终迫使日军投降,其中1100多名日本兵中有900余人被俘。(91)王辅一:《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171页;[日]藤原彰、姬田光義:《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第188页。
结 语
如前所述,继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后,从1941至1942年,华中地区的日军俘虏也相继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在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建立的过程中,尽管新四军中日军俘虏曾试图与重庆总部取得联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重庆方面的直接指导,也没有从华北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直接接受指示。因此与延安和重庆分别有野坂参三和鹿地亘等核心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指导相比,华中地区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新四军敌工部门的组织和觉醒的日军俘虏的努力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不仅在俘虏日军士兵和反战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军部和统治阶层强烈的反响。
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是作为新四军瓦解日军工作的一环而存在,在军事目的上,体现了尊重俘虏的人格与生命、对战争本质的觉醒等伦理价值,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少有的运动。这种理念,与其说是共产主义思想,不如说是由于中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优待俘虏政策,才促使日军士兵们变成反战战士。此外,日本士兵在本国军队中遭受私刑和屈辱已成常态,日本军部越是对其加强警戒,越是有促生内部解体的可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孕育日军士兵反战思想的土壤。相反,中共不仅恢复了他们作为“人”的自由和价值,甚至为他们构筑了新的希望和理想。为了将该理论付诸实践,1944年他们将组织名称由“日本人反战同盟”变更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这便是考虑到战后的新生日本而实施的变更。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活跃于战后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以东北为中心拯救了许多日本人的生命。并且,包括他们在内被中国共产党救出或者留用的许多日本人,在解放战争中还加入了解放军,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92)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包括技术人员和护士在内的“留用者”有8000人到1万人,其中约3000人成为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见[日]古川万太郎著、张斌等译:《冰冻大地之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另有一种说法:留在东北解放区的日本人,确切数字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万人。其中,解放军留用的日本人数量是:军区卫生部 7200 人,军区军工部 2000 人,军区军需部 900人,军区其他系统 1500人。但笔者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似乎没有这么多。参见王秀英:《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日本友人》,《大地》2001年第20期。之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们先后回国,积极投身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和中日友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