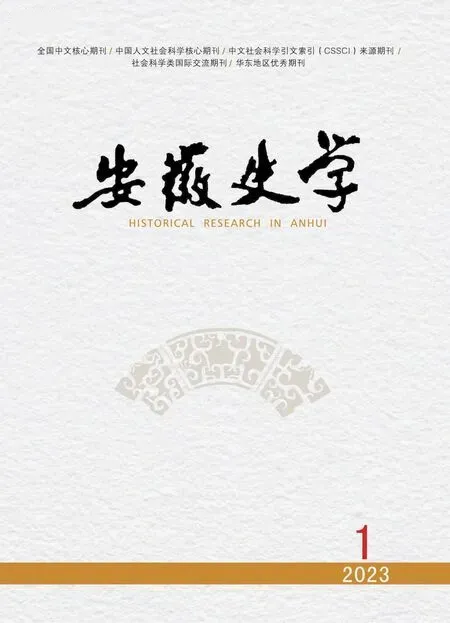《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张海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康有为发起的“联省公车上书”,是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公车上书题名》作为记录此次上书的唯一存世名单,依次开列了各省参与举人的姓名、字号、籍贯和中举科年。然而学界在广泛征引的同时,却忽略了与该题名乃至“联省公车上书”相关的一些关键信息,甚至对不同版本的《公车上书题名》所录举人总数(按:领衔人康有为不计,至少存在602、603、604三说)和各省举人的姓名、籍贯不尽相同,长期视而不见;对许多举人的信息残缺乃至失真,也往往不加考证地全盘照搬。这就不能不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一、四版《公车上书题名》及其记载歧异
此前围绕《公车上书题名》,黄彰健、葛真、茅海建三位学者曾相继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看法。先是黄彰健指出松筠庵谏草堂难以容纳一千二三百人聚会,且如此多人也很难在短短三日内(四月初七日至初九日)将手写疏稿传观完毕,质疑康有为联合千余人集会上书的说法失实,甚至可能在《公车上书题名》中造假,刻意牵涉他人。(1)《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并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728页。随后葛真参照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三》,就该题名中收录的贵州举人信息进行订补。此一研究路径颇具启示意义,只是其研究范围限于贵州,史料来源单一,若干订补也不尽准确。(2)葛真:《辛亥革命前后的毕节》,《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省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243页。2005年,茅海建依据清宫档案将《公车上书题名》与同期其他举人(或举人与官员)的联名上书进行比对,列出其中重复签名人员,并据此分析了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影响力。他注意到《公车上书题名》中存在姓名传抄错误,并以列入福建籍的8位举人中,6人实为贵州籍,质疑该题名有假托或代签现象的存在。稍后茅先生还整理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名录》,列出数十位姓名、籍贯可疑人员。(3)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连载。
本文的研究视角与以上学者有所不同,首先是从《公车上书题名》,或曰《公车上书记》的版本谈起。
今传《公车上书题名》,最早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寻觅不易,多数学者都是参照转载史籍展开研究。(4)主要有中国史学会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166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49—687页;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64页,等等。但实际上,该书于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分别是上海古香阁石印本(简称“古香阁版”)(5)《公车上书记》,上海古香阁石印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索书号:69739。、羊城文升阁木刻本(简称“文升阁版”)(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31—166页。或曰文升阁位于上海,误。、羊城文缘堂木刻本(简称“文缘堂版”)(7)《公车上书记》,羊城文缘堂刻本,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索书号:史620.7/0043。和香港石印书局代印本(简称“香港版”)。(8)康有为:《公车上书记 戊戌奏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影印版。这四版虽然发行商和排版、装帧有别,但内容均由五部分构成,依次为袁祖志《序》,刘锡爵(字斐如)《序》,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简称“未还氏”)《公车上书记》(9)广东的文升阁、文缘堂两版,是将“未还氏”该文和袁祖志、刘锡爵的文章,一并排为《公车上书记》一书的“序”。,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和不著撰人《公车上书题名》。其中,袁祖志、刘锡爵、“未还氏”三人当时都住在上海,古香阁无疑是近水楼台,而三人为《公车上书记》作序或撰记的时间,分别是在光绪二十一年的“天中节”“仲夏月”和“五月朔”,即五月间。又,《公车上书记》一书的广告,最早见于同年闰五月十五日(1895年7月7日)的上海《新闻报》,内称: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为有心世道者所不可不读。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兹觅得全稿并上书姓名,石印成书,托上海古香阁寄售。每部实洋两角。……是书有关世务,故以广销为贵也。(10)《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寄售》,《新闻报》1895年7月7日,第1版。继该报之后,古香阁在《申报》《字林沪报》上也刊登了类似广告。
该广告中提及的“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云云,即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至五月初六日(5月26日至29日),“联省公车上书”事后不足一月,《新闻报》以“奏稿照录”为名,连载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删节本。(11)《奏稿照录》,《新闻报》1895年5月26日至5月29日连载,第2版。同年七月,古香阁还一再登报声明:“原本字画清朗,只有本坊一家出售,购者宜认明书上有本坊牌号,方是原本”;“购者宜认明书上有‘古香阁发兑’字,方是原本”。(12)《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新闻报》1895年9月4日,第5版;《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新闻报》1895年9月16日,第4版。据此,古香阁版《公车上书记》应最早面世,刊行时间在该年五月初七日至闰五月十五日(5月30日至7月7日)之间。广东的文升阁、文缘堂两版,从距离京师的远近和木刻的印刷效率不及石印两点来看,都应晚于“古香阁版”;香港石印书局虽将袁祖志、刘锡爵所称嘱序之人,由“古香阁主”易为“觉世主人”,但明显也是脱胎于“古香阁版”。换言之,《公车上书记》一书应以上海“古香阁版”为祖本。
1990年,汪叔子、王凡两先生已证实“古香阁版”是“康党”自谋刊印。(13)汪叔子、王凡:《〈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主要证据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致康有为函,内称:
《第三书》及《四上书记》前后各事,录副寄上。《第四书》粤中云已开刻,则无须更写。《第一书》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无须更写矣。此间希顾前交与古香阁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车上书记》。彼恐不能获利,请改用小本,如《策府统宗》。此则万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别家,议复同彼。盖尝询之诸书贾,据云: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云云。当直语之曰:《公车记》已销数万部,度买此书之人,亦不过数万人,人有一部,自无购者矣。而彼执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报馆自买机器印之。粤中能刻最佳,刻本必务精雅,若如《救时刍言》,则文字减色矣。(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45页。标点有调整。
具体到“古香阁版”收录的《公车上书题名》,未还氏《公车上书记》云:“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按:联省公车上书)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15)《公车上书记》,清光绪二十一年上海石印书局石印本。所谓“姓名单”,应即《公车上书题名》。“未还氏”,即浙江名士沈善登(1830—1902),是一位翰林出身、家道殷富、常年礼佛、德高望重的居士,他于光绪二十年(1894)结识康有为,且对其学术、政见大为激赏。而将上书经过通告给沈,且将上书副本、题名也抄呈给他的,无疑就包括“康党”。(16)参见张海荣:《〈公车上书记〉作者“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古香阁《公车上书记》广告称:“前代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分赠书中各省列名诸公,并准本坊多印千部发售。”(17)《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新闻报》1895年9月4日,第5版。这里的“都门友人”,显然亦指“康党”。虽然“分赠书中各省列名诸公”,可能只是他们印销该书的托词,却可证实该书附录的上书题名确由“康党”提供,进而还可评估“古香阁版”的印数至少在两千册左右。
据此,《公车上书记》一书应以“古香阁版”为祖本,内附《公车上书题名》亦由“康党”提供。然因辗转传抄和版式调整等原因,继“古香阁版”之后推出的三版《公车上书记》所附《公车上书题名》,皆与之存在不同程度的出入,这不但表现在举人们在上书中的位次、姓名、字号、籍贯和中举科年不尽相同,连人员总数也存在差异。
就举人总数而言,“古香阁版”和“香港版”《公车上书题名》皆登录举人604名;广东的“文升阁版”和“文缘堂版”则登录举人603名。其间所差1人,为广东举人张祖诒。张祖诒,号伯任(一作“伯荫”),肇庆府开平县人,光绪己丑(1889)中举;他与从兄张达瑔,都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参与上书实属情理之中。(18)余棨谋修,张启煌纂:民国《开平县志》卷34《人物》,香港民声印书局1933年铅印本,第15页;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54页。不过“文升阁版”虽然刊落张祖诒1人,却因被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而拥有很高的征引率。(19)《公车上书题名》(文升阁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55—166页。此外,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亦是根据“古香阁版”转载,却将举人总数误计为602名(实载604名),且在转载过程中还增出若干新的错误。(20)如莫如鉷应为“莫洳鉷”,陈端厚应为“陈煓厚”,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649—687页。
然而参与上书的举人总数是否即604名?非也,其中还包括一位重名者,即分别列入福建籍和贵州籍的董玉林,尤其福建董玉林名下,一应信息全无,所以还需结合举人们的省籍再作分析。当年“古香阁版”刚刚印出,该书坊就发现张梦笔、杨绍荣、王鲤、李宗模、邓云卿、李作枢、盛时庚、曾忠上8人,在排版时误被划入广东籍,故于此八人姓名旁均加盖红色戳记,注明籍贯实为“四川”。晚出的“香港版”,不但沿袭了同样错误且未予更正,还很可能因为版式调整而增出成批错误,譬如列入陕西籍的59名举人,实皆甘肃籍;列入四川籍的87名举人,前32名为四川籍,余55名为陕西籍;列入甘肃籍的33名举人,前2名为甘肃籍,余31名皆四川籍。同一年(1895),“邗上草莽书生”辑《谏止中东和议奏疏》所附“各省志士清数”,就是根据“香港版”进行的统计,故而统计结果不可信。(21)邗上草莽书生辑:《谏止中东和议奏疏》卷4,清光绪二十一年香港书局石印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索书号:74742。该书的统计结果依次为:吉林1人,直隶37人,江苏47人,安徽8人,山西10人,陕西59人,福建8人,江西2人,湖北4人,湖南4人,四川87人,甘肃33人,广东95人,广西99人,云南15人,贵州95人。又,茅海建先生曾据清宫档案,指出《公车上书题名》中收录的8位福建举人中,董玉林、任承纪、胡序铨、黄家琮、朱勋、胡兆铨(按:应为胡绍铨)等6人(按:后五人名下同样一应信息皆无),曾在该年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贵州举人葛明远等条陈》上签字。(22)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8页。笔者又查阅了贵州乡试题名录和地方志,可发现董玉林、任承纪等6人姓名。事实上,四版《公车上书题名》都原已登录贵州举人董玉林,内称:董玉林,号竹贤,贵阳府人,甲午。不过这则信息仍欠准确,董氏并非贵阳府人,而是安顺府人。(23)葛真:《辛亥革命前后的毕节》,《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省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41页。再查福建地方志及其历年乡试题名录,清代中晚期举人中皆无董玉林之名。由此可确定,误划入福建的董玉林、任承纪等6人,省籍均为贵州,除去原已在列的董玉林,该题名实际收录举人603名(不含康有为)。
除举人总数及其籍贯存在舛误外,举人名号和中举科年有误,在这四版《公车上书题名》中同样存在。其中有些错误是各版共有的,如陕西举人惠常煋、窦牛虚、似树森、张经寅、刘肇复,分别应为惠常惺、窦中虚、侣树森、张维寅、刘肇夏;甘肃举人苏曜泉,应为苏耀泉;广东举人郭金阳、周恩镐,分别应为郭金汤、周思镐;广西举人杨裕达、周经宗、黄经垣,分别应为阳裕达、周维宗、黄维垣;贵州举人张鸿达、陈明清,分别应为张鸿逵、陈清明。还有中举科年的出入,如贵州举人聂树奇是癸巳(原作“辛卯”)年中举,杨锡谟为辛卯(原作“癸巳”)举人;甘肃王堃棫为乙酉(原作“癸巳”)举人;陕西温恭为辛卯(原作“乙酉”)举人;广西杨书田为甲午(原作“癸巳”)举人,等等。(按:以上有些已由葛真、茅海建两位先生指正)。还有一些举人的名号、科年,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广东举人张恩泽、广西举人杜元春,“文缘堂版”“文升阁版”都分别误作“张思泽”“杜元椿”;广东举人黄心龄号“梅伯”、冯焕章号“拟坡”,“古香阁版”“香港版”都分别误作“伯梅”“拟批”;广西举人朱椿林的中举科年,“古香阁版”“香港版”和“文缘堂版”皆作“己卯”,“文升阁版”则误作“壬午”(按:因笔者未能见到文升阁原版,亦不能排除此一错误是中国史学会转载过程中增出的)。
举人们登记信息不全,在各版中也显而易见。如有的举人籍贯中缺府、缺县;有的缺中举科年;有的只录姓名,字号、籍贯、中举科年并缺;还有的,若干版本曾注明籍贯,其余版本则残缺。如广东举人湛书、冯祥光,“古香阁版”和“香港版”皆未注明籍贯,“文缘堂版”和“文升阁版”则分别注明其籍贯为惠州府连平州、广州府番禺县(按:这进一步佐证了广州所出的两种木刻本,出版时间晚于上海“古香阁”版)。相对而言,吉林、直隶、安徽、江苏、湖北等省名单较为完整,山西、陕西、甘肃、广东、广西、贵州6省举人,信息残缺比较严重。
以上四版《公车上书题名》中举人信息的各种舛误,有力证实“康党”提供的名单原本就颇有水分。当时应试举人大多住在本省在京会馆。从相关史料推断,在松筠庵集会之前,“康党”及其分托的朝士曾赴各会馆广发“知单”,言明上书事由、发起人和松筠庵集会的相关事宜,鼓动举人们联署。(24)吴稚晖回忆当时情况称:“康草一书论改革救亡,遍传各会馆签名,即所谓公车上书是也。”(《中山先生的革命两基础》(1925年7月25日),《吴稚晖全集》卷6,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又,反观1898年春,康有为弟子麦梦华、梁启超等为即墨文庙圣像遭德国人毁坏一事再次发动公车上书,事前亦曾广发知单,内称:“公启者: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人毁去,并将先贤子路像,抉其双睛。……顷者公车咸集,宜伸公愤,具呈都察院代奏,请与德国理论,查办毁像之人,以伸士气而保圣教。……单到,请书姓名,并注科分、省分,以便汇列附上呈稿备览。……麦孟华、林旭、张铣、陈荣衮、梁启超、陈涛、程式谷、张鹏一、龙焕纶、钱用中、况仕任、邢廷荚同启。”(《京外近事:请联名上书查办圣像被毁公启》,《知新报》第55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第10页。)有意参加者,可先在知单上预署,写明姓名、省份、中举科年等,届期再赴松筠庵参加集会,履行正式的署名手续(按:根据清朝上书的有关规定,满汉举人除署名外,还需取具同乡京官的印结或本旗佐领的图片,才算完成联名手续)。但也有部分举人,虽在知单上预署,却并未如期赴会,抑或委托他人代为签署,乃至有中途索回知单者。如未被列入《公车上书题名》的福建举人邱菽园,就是在松筠庵集会前夕索回知单。(25)张海荣:《晚清举人邱菽园对“公车上书”的两次追忆》,《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而列入该题名的吴朓(后改名“敬恒”,字稚晖),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冬才首次见到康有为,应该也是只递交知单而未前往松筠庵。(26)陈凌海编撰:《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吴稚晖全集》卷14,第556页。1943年,吴稚晖甚至称上书题名是康赴各会馆炮制出来的。“三月会试,康有为到各会馆抄录会试举人姓名约一万人,上书于光绪帝,言变法。名曰公车上书。”(27)吴稚晖:《苏报案之前后》,《吴稚晖全集》卷6,第403页。吴氏一生政治立场多变,性格古怪诙谐,其相关记述不能尽信。事实上,受甲午战争影响,该年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总计不到五千人。(28)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山西举人刘大鹏记:“今科会试通共五千人。长班言,较甲午科会试减二千人,倭贼寇边,南省来者遂少。”(《乙未公车日记》,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41页)同年三月初九日,本科会试管理誊录所的官员王清穆也记载:“申刻,到至公堂戳印二场坐号,询悉头场人数共四千七百余名,较甲午科约少二成。”(王清穆撰、胡坚整理:《知耻斋日记(续)》,《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不过结合邱菽园、吴稚晖的相关记述,大体可以认定,《公车上书题名》的形成与各省举人预署的知单存在直接关联。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康有为在京城发动松筠庵集会诚有其事,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相关记述和《公车上书记》一书可兹佐证外,另有三则史料,可证此次集会非虚,且声势不小: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申报》刊登京友消息称:康有为“曾联络同乡公车多人,在松筠庵会集三日”。(29)《谏牍纷陈》,《申报》1895年5月19日,第1版。二、同年秋,广东士人卢庆云致函康有为称:“五月初旬有友自表回□,为言谏草堂之集,一时车马喧阗,宣城道塞,士气之壮,国耻为之一伸。”(30)《卢庆云致康有为》(1895年秋),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三、山东应试举人王丕煦事后赋有《公车上书纪事》诗一首,注明:“时大会于松筠庵,传观书稿。”(31)《公车上书纪事》(乙未三〔四〕月),王丕煦:《韬谷诗存》卷1,民国刻本,第5—6页。不过通过吴稚晖的现身说法,也确可说明《公车上书题名》中收录的部分举人并未赴松筠庵完成正式的联署手续,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此次上书是半途而废。
正如此前茅海建等学者曾经指出的,康有为弟子徐勤、吴恒炜和“未还氏”的相关记述均已证实,“联省公车上书”是以流产告结。(32)徐勤:《杂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吴恒炜:《〈知新报〉缘起》,《知新报》第3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第2页;未还氏:《公车上书记》,清光绪二十一年上海石印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5月26日),《新闻报》首次披露《上清帝第二书》的删节本时所加引言,又提供另一力证,内称:
昨有粤东南海某孝廉递来奏稿,据称拟集十八省公车诸君,合词乞请总署代奏,乃甫起草而和议已成,事遂中止。然其中议论警切,策画周详,方之古人贾生痛哭、杜牧罪言,殆无多让。爰照录之,以告世之留心国事者。(33)《奏稿照录》,《新闻报》1895年5月26日,第2版。
此处的“南海某孝廉”,应指康有为无疑。其时康刚中进士,仍滞留京师,奏稿显然是他人代为送达《新闻报》馆的。引言中说“甫起草而和议已成,事遂中止”,则明确承认“联省公车上书”未遂,并非官方拒接呈文,而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这与康有为后来所称“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明显抵牾。(34)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页。惟所称“乞请总署代奏”一节,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举人们的上书普遍经由都察院代奏,而非总理衙门。也正因为此次上书是半途而废,《公车上书题名》所收举人信息不全和出现颇多舛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相关举人信息的再审视
尽管如此,“康党”提供的这份《公车上书题名》中,绝大多数举人仍可划为上书的支持者(35)如1898年湖南《延年会章程》就规定:“章程分散各友,另用知单,劝其入会。书‘知’者,即作为入会,以后照章程办事。”(《湘报》第4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第14页)(即以送交知单的非正式形式预署,抑或委托他人代签),否则“康党”联系上海古香阁刊印《公车上书记》时,就不会给出“分赠书中各省列名诸公”的说法。(36)《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新闻报》1895年9月4日,第5版。何况该书仅在光绪二十一年就推出四版,印量即便没有“康党”所称“数万部”,至少也有数千册。如此大规模地面向社会公开,“康党”实不可能随意假借他人名义充数。比如中途退出此次上书的邱菽园,就未被收入《公车上书题名》,以致光绪二十六年(1900)康有为避难邱氏在新加坡的府邸时,还赋诗感慨:“最恨邱迟伤故国,题名记上少斯人。(今日乃知菽园本联名,龙华会上,恨少君耳)”(37)《正月二日避地到星坡,菽园为东道主》,《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202页。“龙华会”,农历四月初八日,代指松筠庵集会。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古香阁寄售《公车上书记》的广告也声明:“凡记内列名各省孝廉过沪,如欲阅看,可遣伻持名片,注明省府,向古香阁取书,奉送一部,不取分文。”(38)《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盛世危言〉》,《字林沪报》1895年8月9日,第1版。事实上,《公车上书题名》中的不少误区都是出版商方面造成的,“香港版”问题尤其严重。不过反观各省乡试题名录这样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文件,当时各报所刊名单也往往错漏百出。
职此之故,笔者认为即便“康党”刊行《公车上书题名》别有政治企图,但作为近代国人爱国救亡精神的象征,该题名仍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遂尝试在“古香阁版”和茅海建、葛真等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资料,对该题名收录的人物一一进行核证。
其间,笔者发现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关于举人们的姓名。时人姓名有原名、俗名、榜名、谱名(按:在谱牒中使用的名字)、派名(按:有些家族因支派繁多,各支派还规定有派名)、更名(按:因避讳、应试或其他原因而改换姓名)等不同说法。如贵州举人俸肇祥,派名“亮柏”;(39)《光绪己丑恩科乡试俸肇祥硃卷》,爱如生“中国谱牒库”。以下硃卷均引自该数据库,不再一一注明。傅夔,派名“师闿”;(40)《光绪癸巳恩科乡试傅夔硃卷》。李益源,光绪丙子中举时用的是原名“熙骏”;(41)《丙子科广西乡试题名全录》,《申报》1876年12月11日,第2版;梁培煐、龙先钰纂:民国《贺县志》卷9,贺县华美商店1934年铅印本,第43页。任承纪,后改名“树滋”。(42)唐承德:《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1997年编印本,第82—83页。又如,湖南举人曾熙,榜名“荣甲”;(43)《辛卯科湖南乡试官板题名录》,《申报》1891年11月15日,第9版。直隶举人张权,谱名“仁权”;(44)《光绪辛卯科乡试张权硃卷》。广西举人文同书,原名“植”;(45)李繁滋等纂:民国《灵川县志》卷5、6,1929年石印本;《电传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广西乡试题名全录》,《字林沪报》1889年10月15日,第2版。江苏举人王禄孙,原名“同曾”(46)《光绪辛卯科乡试王禄孙硃卷》。,等等。第二,举人们的字号。《公车上书题名》原则上是统一登记举人们的“号”,但实际上对于“字”与“号”的区分并不严格,何况有些举人原本就有“字”无“号”,或拥有多个字号。第三,举人们的籍贯。时人籍贯有祖籍、原籍、寄籍、学籍、民籍等不同说法。如直隶举人袁励准(“古香阁版”误作袁励廷),寄籍顺天府宛平县,祖籍江苏武进县;(47)杨钟羲:《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袁君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贵州举人聂树楷,学籍贵阳,原籍思南府婺川县;(48)任可澄等纂:《贵州通志·艺文志十七》,贵阳文通书局1948年版,第95页;《电传甲午科贵州乡试题名全录》,《申报》1894年10月12日,第2版。贵州举人朱勋,寄籍大定府平远州,民籍平越州瓮安县;(49)《电传己丑恩科贵州乡试题名全录》,《申报》1889年10月2日,第2版。广西举人卢荣恩,学籍浔州府,原籍平南县;(50)《光绪己丑恩科乡试卢荣恩硃卷》。江苏举人曹元忠,寄籍苏州府吴县,原籍安徽歙县(51)《光绪甲午科乡试曹元忠硃卷》。,等等。再,若干举人为府城人士,并不能一一具体到县。第四,中举科年。这与举人们的籍贯也存在一定关联。虽然多数举人可见于本省相应年度的乡试题名录,但也有部分举人是在外省应乡试。譬如《公车上书题名》中有36名举人可见于“顺天榜”,包括葛真未能查证的贵州贵筑人周祜。(52)这36位举人分别是吉林德懋,江苏徐普、罗宏洞、濮贤恒、吴廷锡、吴廷燮,山西王仪通,湖南曾纪先,四川杨锐、曾鉴、洪尔振、杨宜瀚、王濬道、湛凤翔、刘乾(“古香阁版”误做“刘轧”),广东左公海、陈大照、潘志和、张元钰、黎宗葆(“古香阁版”误做“黎宗保”)、马銮光、张恩泽、谢晋勋、冯元鼎、杜士琮、王寿慈、关伯麟、黄立权、莫寿彭、梁念祖、梁泮、陈敬彭、颜绍泽,广西林世焘、施献瑄,贵州周祜。
从笔者核查后的结果来看,排除字号不计外,“古香阁版”《公车上书题名》中举人们的姓名、籍贯(或仅具体到府)和中举科年三项皆无误者,只约占总数的一半。在这603位上书参与者中,包括两位同名举人刘文炳,中举科年皆为癸巳(1893):前者(1861—?,“古香阁版”误作“刘元炳”),号蔚臣,江苏上元县人;(53)《大清国事:光绪十九年癸巳恩科江南乡试题名全录》,《万国公报》第59期,1893年12月,第20—21页。后者(1859—1916),字汝彪,陕西陇西县人,曾主讲甘谷、襄武书院。(54)安维峻纂: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9《学校志·选举上》,清宣统元年刻本,第78页;《陇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页。引人瞩目的是,内含6位旗人,分别是吉林德懋和直隶籍的文元、同书、文成、德善、孙同荣。此外,还包括一位进士,即陕西籍的赖清键(1846—1926),他于光绪二年(1876)中举,光绪九年(1883)成进士,旋签分工部,时任工部虞衡司主稿。(55)《赖清键履历》,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7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公车上书题名》之所以仅收录16省、603名举人(不含领衔者康有为),而非“康党”通常所称一千二三百人,且签名举人未及浙江、山东、河南、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等地,原因之一,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言,是因为部分举人在政治压力下中途退出。“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62)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6页。广东同乡也劝林缵统以前途为重,尽快“取回知单”,为林氏所拒。(63)游师良:《“天涯”义士,“戊戌”君子——林缵统传略》,《自治州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2期。此外,还有人指出,《公车上书题名》之所以未收录浙江举人,是因为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的阻挠。“乙未公车上书诸孝廉无一浙江人,由文韶劫持于上,使不得逞,殆亦滑之一端欤。”(64)毅公:《虫天阁摭谈》,苏曼殊等著、马玉山点校:《民权素笔记荟萃·王文韶》,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其二,是因为大批举人因和局已定而撤回知单。未还氏《公车上书记》载:“是夕(按: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65)未还氏:《公车上书记》,清光绪二十一年上海石印书局石印本。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亦称:“同人以成事不说,纷纷散去,且有数省取回知单者,议遂散。”(66)徐勤:《杂记》(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反观同期甘肃举人李于锴等76人的联名上书,也是因为和约批准而中途放弃。(67)李鼎文:《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26页。其三,是因为有些举人不赞成上书内容而拒绝签名。山东举人王丕煦披露:“时大会于松筠庵,传观书稿,内有迁都之议。鲁籍公车多以为非策,不肯署名。”(68)《公车上书纪事》(乙未三〔四〕月),王丕煦:《韬谷诗存》卷1,第5—6页。福建举人邱菽园也现身说法道:“前半迁都、废约、练兵、筹战,词意操切,未策万全。……予初预联名,后即取回名单,诚以主战之不可恃也。”(69)《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邱炜萲:《菽园赘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页。此外,《孙宝瑄日记》也间接反映了部分浙江举人的主和立场。“当甲午中日之役,海内莫不言战,独吾浙人上书言和,且言之最蚤。”(70)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1页。其四,是因为部分举人先期离京,未及赴会。《申报》载:“三江、两湖、闽浙、粤东各省会试诸公,多于出场后束装就道,怱怱言旋,殆虑和议难成,海路梗塞故也。今年会场人数本少,又加以大半先归,遂致会馆、旅邸阒其无人,京师市面益形减色。”(71)《彤廷珥笔》,《申报》1895年4月28日,第2版。《新闻报》也证实:“今年会试,公车人数本少。近缘世变未已,咸有戒心,凡应试之流,出场后,强半来津候榜,都中几为之一空。”(72)《公车回津》,《新闻报》1895年5月5日,第2版。
余 论
1895年康有为发起的“联省公车上书”,虽以流产告结,“康党”却抓住时机,借助《新闻报》和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书局,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灵活的方式,趁着《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内蓬勃高涨的舆论氛围,集中宣传举人们的联名请愿行动,并突出康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从而成功开启了甲午战后宣传维新变法、树立康有为变法形象的历史大幕。其中,《公车上书记》的刊行是关键一环。“康党”之所以将《公车上书题名》一并附在《上清帝第二书》之后,主要目的是烘托康有为个人的政治魅力和能力,塑造其广受拥戴的政治形象,正所谓“红花”还需“绿叶”配。事实证明,此一宣传策略,不但成功塑造了康“维新旗手”的高大形象,为“康党”日后开展维新活动提供巨大便利,也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后世对“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的解读。这与康有为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的情形,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不过就“康党”之外的其他举人而言,当时不但鲜有借此扬名受益者,反有担心与“康党”牵涉过深而改名者。如贵州举人杨锡谟,1898年再应会试时,“恐受惩罚,始更名兆麟”。(73)杨祖恺:《探花公撰联颂扬辛亥贵州反正》,政协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遵义掌故》第1册, 1999年自印本,第263页。
当然,笔者的研究目的,绝不止于澄清参与“联省公车上书”的人员总数和各省名数,更重要的是,通过逐一筛查《公车上书题名》,访求除康有为一派外,当时实际与会人士的相关记载,进而挖掘此次上书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网络和甲午战后的政情与舆情。本文的写作仅仅是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