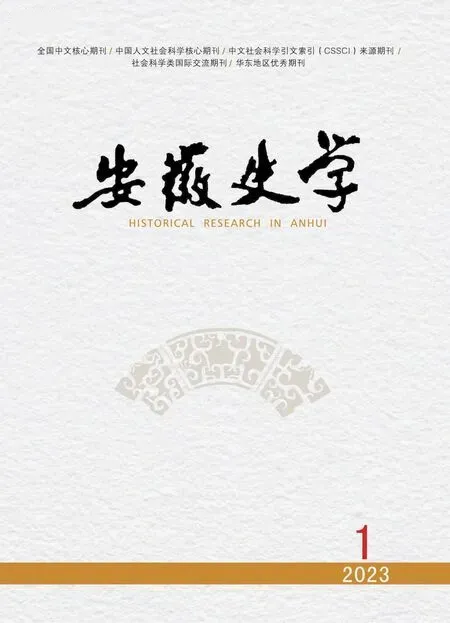民国初年的军队防疫与军阀政治
赵晓华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民国成立以后,迎来政权鼎革的近代中国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一方面,战事频仍,政权更迭频繁,另一方面,水旱等自然灾害不断侵袭,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不断发生。因为军队中“壮夫群处,疫痢丛生”,防疫因此也成为军队卫生事务中最为“重要之事”。这一时期,为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北京政府陆军部颁布了一系列军队防疫法规章程,地方军队也因地制宜,制定了相应的防疫办法,并积极培养防疫人才,宣传和普及防疫知识。同时,军队也成为国家和地方防疫中倚赖的重要力量,在民初防疫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队与地方的联手抗疫过程,体现了这一时期军阀政治的鲜明特点。学界对于民国初年传染病及其防治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对于军队与防疫的关联还较少专门探讨。(1)如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张照青:《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姬凌辉:《难以协调的遮断交通:1917~ 1918年“绥晋”鼠疫防治述论》,《中医典籍与文化》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282页;冯翔:《1917—1918年北方鼠疫回顾与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21年第1期,等。本文主要以1917至1919年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控为中心,希望对这一时期军队防疫措施、军队对地方抗疫活动的参与及影响等进行阐述,从而进一步探析民国初年的疫情防控活动,以及疫情防控中所反映的军阀政治的特点。
一、军队的患疫情况与防疫措施
清末民初的几次瘟疫大流行中,军队均受到了传染病的侵袭,防疫形势严峻。1910年发生的东三省鼠疫中,据陆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统计,第三镇各营因防疫染疫病故的官佐兵夫有150余人,在营染疫病故兵夫达190余人。(2)《奏议录要:陆军部奏撤回调拨防疫军队片》,《北洋官报》1911年第2815期,第2—3页。东三省鼠疫后,军队对于传播卫生知识、防疫知识比较重视。1917年,绥远鼠疫爆发,虽然“各军队卫生人员均能实力防范”,但军队依然受到鼠疫的侵袭。根据陆军部的调查,自1917年12月中旬起,至次年4月中旬止,4个月之间,驻防绥远的北洋陆军第一师军队官兵疫亡46名,绥远军队疫亡45名。(3)陆军部编:《陆军行政纪要(民国九年三月)》,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第276页。另外,这一时期其他地方发生的疫情中,军队也常被波及。如1918年间,湖北岳州一带发生疫疠,驻扎该处军队有“染疫毙命者”。(4)《湖北 十字会解送药品》,天津《大公报》1918年4月6日,第7版。同月,浙江杭州第八团第五连发生猩红热。(5)《浙江 染疫兵实行隔离》,天津《大公报》1918年4月10日,第7版。1919年七八月间,直隶、河南、江苏、安徽、福建及东三省等地发生真性霍乱,“军民传染,死亡甚众”。在廊坊,所驻奉军最先发现真性霍乱的流行,据《大公报》8月8日记载,廊坊所驻扎之军队染病甚众,“近一工日死者已达六十名之多”;(6)《天津防疫之种种》,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8日,第10版。8月20日,又报导廊坊军粮城驻防奉军边防军一千五百余名,“其患染时疫者死毙多人”。(7)《关于防疫之汇志》,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20日,第10版。霍乱当时又称虎烈(列)拉,8月24日,保定东关外军队也发现“患虎列拉者不少,始而兵士染患此症而毙,继又传染于官长而亡”。(8)《保定 官兵疫毙之纪闻》,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24日,第6版。在奉天,疫势猖獗,军营亦发现疫症,病死者络绎不绝。据《大公报》8月11日记载:“小北关炮营军队死亡数人,东关辎重营亦病死二三人,大西关街南马一营疫势最盛,本月一日疫死军队五人,初二日死十一人,初三日死四人,病而未愈者尚有十余人,各区巡警共疫死十二人。”(9)《死亡人数》,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11日,第6版。另从8月上旬至10月下旬,吉林省陆军混成旅患者包括5243名官兵,死者达226人。(10)[日]饭岛涉著,朴彦等译:《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页。
传染病的肆虐,严重影响着军人的生命安全和军队的战斗力。防疫形势逼人,也使得军队对防疫问题高度重视。时人认为,军队之所以容易遭到传染病的侵扰,原因在于:一方面,军队生活本就是“困苦艰辛,身心疲瘁,每超过自然之限制”,民国初年战事频仍,客观环境削弱了士兵对疾病的抵抗力:“在作战时期,两军对垒,血肉相搏,眠食不时,劳动失度,加以气候之变易,风土之各别,南北奔驰,住居无定,时处于反卫生境遇之中,身体对于疾病之抵抗力因而减弱,病菌传染之机会因而增多”。平时训练时期乃战时缩影,困苦艰辛亦不稍减,军人“亦易为传染病所感染”。另一方面,军队为集团生活,人群聚集,“病毒最易传播,若不先事预防,野火燎原,即至不可向迩”。(11)《军队防疫问题》,《军事杂志(南京)》第31期,1931年,第20—23页。为了应对疫情,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队通过制定相应法规、措施,宣传防疫知识等,加强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1.陆军部颁行的军队防疫法规
近代军队防疫法规从晚清即开始制定和建设。1905年,《北洋陆军卫生防疫章程》颁布,包括卫生章程十条、行营卫生章程十条、防疫章程十条。其中,防疫章程十条,从食物、饮水、住房、垃圾处理、疫病的治疗等多方面做了规定。(12)《北洋陆军卫生防疫章程》,《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1905年,第307—310页。1911年,晚清陆军部拟定军队防疫简章十则,通饬“各军官长目兵一律遵守,以期思患预防”。(13)《陆军部颁布防疫简章》,天津《大公报》,1911年2月23日,第5版。1912年,民国成立后即颁布的《陆军部官制》中,明确了防疫事务的管理机构,规定军医司掌“有关于防疫及卫生试验事项”(14)《陆军部官制(附职员表)》,《政府公报》第124期,1912年,第7—14页。,《海军部官制》也规定,军务司掌事务包括“关于防疫及卫生事项”。(15)《海军部官制(附职员表)》,《政府公报》第125期,1912年,第4—10页。1912年3月23日,陆军部颁布《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33条,这较北京政府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要早三年。在传染病的种类方面,该条例明确把传染病分为霍乱、赤痢、百斯笃等9种,以及“陆军总长所特别指定者”。在传染病防控的报批程序方面,如果部队内或附近地方有传染病发生,部队长官须迅速申报其上级长官,如果病势有蔓延之兆,该长官须向陆军总长申报。在病例的信息通报方面,部队的高级医官须向该部队长及军医长迅速申报,军医处长接到报告后,迅速查明病性及流行情况,报告军医司长。在具体防疫措施方面,包括健康诊察,加强消毒清洁,厉行兵士隔离,限制外人出入,必要时禁止交通等。(16)《陆军部颁布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临时政府公报》第46号,1912年3月23日,第10—17页。1913年12月,陆军部又颁布《陆军传染病预防消毒方法》19条和《军兽传染病预防规则》12条,前者对消毒法的分类、适应、应用做了规定,后者对军兽传染病的种类及防控做了规定。1918年3月15日,内务部防疫会拟定《军人检疫办法》,凡成队军人或单独军人,经军医官验明确无疫症,由该长官发给凭单,检验员验明无误,方准放行。(17)《防疫事宜之汇志》,天津《大公报》1918年3月15日,第10版。
此外,陆军部也注意军队中公共卫生的重要性。1912至1914年,陆军部颁行《队附军马卫生员服务规则》《队附卫生员服务规则》《师军医处服务规则》《师兽医处服务规则》《陆军学校卫生员服务规则》《陆军学校军马卫生员服务规则》等,具体规定了军医、卫生员等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职责和规范。(18)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1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69页。
2.地方军队的防疫措施及办法
在陆军部出台一系列军队防疫法规同时,各地军队也制定了具体的防疫措施和办法。其中,有的是对中央条例和法规的细化。如1919年秋,湖南霍乱流行,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也发现疫情,陆军部鉴于廊坊等地驻军已爆发疫情,称“各该军队亟应遵照部颁传染病预防规则,实力奉行”,湖南督军公署在此基础上,另订陆军传染病预防简则,“通令各军队遵照切实奉行”。(19)《省长令拟地方防疫规则》,长沙《大公报》1919年9月8日,第7版。有的是各地军队针对防疫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而定的防疫办法。1918年,各地霍乱流行,吉林驻省各军队制定如下防疫办法:其一,军医配制除痹丹等药剂及消毒药水;其二,每日军队住所消毒一次,所有行李等物曝晒;其三,军营饮食每日由各连司务长检查,务求清洁;其四,遇有染疫军人,由军医切实施治,予以隔离。(20)《吉垣防疫汇志》,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24日,第6版。次年8月,直隶督军曹锟因霍乱异常猛烈,认为军界更宜早加防范,因此制定防范办法六条,主要包括在消毒方面,军衣军装一律检查消毒,军队宿舍、厕所洒扫洁静并撒以石灰,服被每日晒晾。在个人防疫方面,队兵不准用冷水及生冷食物,不准招待亲友入营,以免传染等。(21)《军队防疫之通令》,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23日,第10版。还有的省份制定了军民共用的防疫法规。如为了防治肺鼠疫,山西督军阎锡山制定了《防疫法》《防疫须知》等规章。(22)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1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1页。
3.防疫人才的培养和防疫知识的传播
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即附设防疫学堂。民国成立后,陆军军医学校的军医科开设军阵卫生学、军阵防疫学等课程,为军队培养了一批具备专业防疫知识和技术的医务人员。军队也注重对防疫知识的传播和宣讲。《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第七条第四项称,部队内传染病发生或附近地方有传染病流行之兆,军队应注重卫生宣传,“厉行卫生演说,俾得贯彻预防之意旨,但演说场所须在操场之中”。除了疫情期间注重卫生知识的宣传,军医学校等机构也注重对先进防疫知识的普及、推广和研究。《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兵事杂志》等刊物登载对于各国防疫知识和经验评介的论文,如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俞树棻发表《日英法意四国军阵防疫之近况》等论文,其译著还有《平时战时卫生勤务》《军阵防疫学教程》等。
陆军部认为,防疫知识的宣传推广成效显著。绥远鼠疫时,绥远八县驻扎军队有16000人之众,疫毙者不满百人,防疫成绩“灿然可观矣”。在陆军部看来,除绥远军队间有染疫而亡者,其余各省军队均无疫毙人员,“较之宣统二年东省鼠疫流行时,其卫生知识已有进步”。(23)陆军部编:《陆军行政纪要(民国九年三月)》,第276页。
二、军队对地方疫情防控的参与
民初国家与地方的防疫事业中,军队常常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17年绥远鼠疫中,北京政府委派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前往防疫。有识之士认为,要想抗疫成功,联合军队是关键一步。“此次疫疠,其传播之速,一如昔日之在东三省者,则伍博士等必将有一番坚苦卓绝之事业,然诸医士辈必须得军队之协助,否则无论如何隔绝传染之计划,不能实行也。”(24)《西报纪瘟疫之蔓延》,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7日,第3版。伍连德也指出,清末东三省鼠疫时,军队协助是防控成功的重要原因:“其初瘟疫势盛,无法制伏,及至得军队之协助而后可”,因为“厥后能实行一切命令者,却以军队为最焉”。伍连德因此希望中央防疫委员会会长江朝宗“疏通军队,使了然于情势之紧急,得彼辈联合进行,实属最要之图”,联合军队,“比诸联合医士,尤为切要,盖欲实行必要之方法,端赖彼辈也”。(25)《伍连德医士防疫一席话,肺瘟易于制伏,两月内铲除净尽》,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23日,第3版。从军队来看,也注重与地方政府的联防联控。《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规定,防疫中关于地方事项,应由军队长官与地方行政官协议后处置,军队和地方应互相通报病人的信息、发病场所、发病时日等。(26)《陆军部颁布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临时政府公报》第46号,1912年3月23日,第10—17页。民国初年,军队在地方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参与地方防疫组织、阻断交通、委派军医等方面。
1.参与地方防疫组织
近代以来,军队常被分派和加入到地方防疫机构和组织中。清末东三省鼠疫中,奉天傅家甸隔离防控,即由陆军步队第十二标本部及第一、第二、第三营1048名官兵承担(27)⑤⑩奉天防疫总局编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335、8333、8201页。,吉林全省防疫总局包括63名陆军官兵。(28)⑤⑩奉天防疫总局编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335、8333、8201页。1917年,绥远鼠疫发生,五原、包头、萨拉齐等地疫情严重,军政防疫分局因此成立,该机构由地方长官及驻屯军队之高级军官合办。(29)全绍清:《民国七年第一区检疫事务报告》(附图表),《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年12月,第61页。在山西,山西防疫总局下设警队,因警察不敷分配,由陆军第十团第二连及输送队士兵改编成立急救队和掩埋队。(30)⑨王承基纂辑:《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2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印,第30、130、19页。省会所在地、山西首县阳曲县由姚显仁等20多名军官驻扎,并调用陆军输送队50名、检查队220名士兵沿边驻守,以保省垣安全。据太原人刘大鹏在日记中称:“省城防疫十分戒严,凡入城内者只准由北门而进,余不准入,凡入城之人必须写一券,注其姓名籍贯,现办何事,稍涉疑似,即不准入城”。(31)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5页。另外,驻杀虎口守军在圪针沟设检疫所,检验人数每日从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32)⑨王承基纂辑:《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2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印,第30、130、19页。
2.力行遮断交通
清末民初,实行交通阻断是防疫非常重要的手段,军队在此方面贡献良多。东三省鼠疫时,阻断交通主要就是依靠军队。比如,哈尔滨实行交通隔绝时,陆军步队第十二标前往助防,“该军驻哈之日,正值传染剧烈,与身当前敌者无异”。(33)⑤⑩奉天防疫总局编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335、8333、8201页。1918年1月,绥远分东北、东南、正南三路设点,“各地方自啸日起派兵堵截,暂以两星期为度”,“未经开放以前,无论军民商货一律禁止往来”。(34)《收绥远都统电》,1918年1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防疫事收发电,档号:03-13-030-01-001,第662—663页。本文所列档案的收藏单位和名称完全相同,下文一律简称为“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绥远鼠疫传到山西,山西督军阎锡山饬令由军队负责,组建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阳高县天镇为起点,沿边至河曲县,折而南下,至临县碛口;第二道防线,自灵丘经繁峙、雁门边墙以北各县,经宁武、岢岚、兴县,至黑峪口,与陕西接边之处;第三道防线,自雁门关以南,东至五台与直隶接界之处,西至临县与陕接界处;第四防线,自忻县石岭关、阳曲天门关以南,至正太路沿线娘子关直晋交界。此外,在浑源金龙口、广灵柳涧沟等关口,“均派军分堵之”。(35)⑨王承基纂辑:《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2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印,第30、130、19页。根据曹树基的统计,军队驻防的关隘渡口有48处。驻防军队包括第一混成团二营、三营,步三团二营、三营,步五团二营,骑一团、骑二团,第二混成旅司令部、第三旅、第四旅、宪兵二营和防疫分队。“1918 年的防疫,对于山西的军人来说,不啻是一场战争。”(36)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山西之外,察哈尔也于丰镇设立防疫站,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制定六条军队分队防堵办法。其中,马一营驻丰镇;马二营与第五路步五营驻凉城,防堵由杀虎沟、石匣沟等处来丰要道;马三营分驻双古城、淤泥滩等处,堵截丰绥要道;马四营左右两哨分驻弓沟、张皋两处,遮断赴张大道;步二营分驻麦胡图、天成村,步三营并机关枪连驻马王庙,遮断由丰赴绥行人。另外,陶林、卓资山等地另派军队担任防堵。(37)《田中玉来电(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政府公报》1918年第725号,第20—21页。军队带同防疫医员“设站检验,遮断交通,无论军民商货均须扣留六日,方准入境”,田中玉并请陆军部协调绥远也“禁止军队往来,双方进行,期收速效”。(38)《收察哈尔都统电》,1918年1月19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635—636页。
3.选派军医参与抗疫
应地方所需,北京政府和陆军部选派大量军事医学人员参与抗疫。1918年初,派往绥远指挥疫情防控的伍连德因病辞职,北京政府任命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全绍清为第一区检疫委员。全绍清是伍连德主持抗击清末东北鼠疫时的“得力助手”(39)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 ,湖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 327页。,因当时疫区地域寥广,人员不敷分派,全绍清禀准陆军部,抽调军校医科四年级、医药科三年级学生,组织医队,奔赴疫区。(40)《防疫医队之出发》,天津《大公报》1918年2月2日,第6版。这支军医队伍在疫区历经非常艰苦的工作。据全绍清称,医队在1918年2月1日抵达丰镇后,先是经历了不利交通和恶劣气候的考验:“是时丰镇疫气初发,由丰至绥三百六十里间,死亡枕藉,沿途客店逃亡一空,交通几绝,我检疫人员已入第一防线,冰天雪地,难于进行,商民视为畏途,觅车尤为不易”,接下来又需要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虽然找到车马,“然车夫乘间思遁,看守为艰,以多数防疫人员仅得轿车数辆,余皆粗笨大车,其车夫之肮脏,车间之污秽,均为未曾经见者”。医队就地进行消毒工作,将一百多名车夫“一一施行健康诊断,车夫之衣服,均用福尔马林蒸汽消毒,轿车大车,一律用升汞水洗刷,延迟数日,始获就道,并组织消毒队将宿站之房舍严行消毒”。在恶劣的客观条件下,医队“凌风冒雪,深入险境,起居饮食,悉失常度,行抵鹤千村,适值旧历元旦,每人只用米粥一碗,大有寒尽不知年之景况”。工作环境虽然十分艰难,但是“各员不但毫无困惫状态,且勇往直前,精神百倍,斯亦军人本色”。(41)全绍清:《民国七年第一区检疫事务报告》(附图表),《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年12月,第113页。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筹建成立了一个总事务所,九个分事务所,并建成疫病院、疑似病院、隔离所、消毒所等机构。(42)李斌煜:《校闻一束:(绥区防疫纪实)民国六年岁秒(杪)绥远陡发百斯笃疫症》,《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年12月,第256—261页。
在其他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军医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1918年2月,署直隶省长曹锐因绥远鼠疫蔓延津郡,委派前湖南督军署军医科科长王仲华为直隶防疫消毒部主任。随后,北洋防疫处处长刘国庆特聘军监衔、一等军医正李学瀛为临时防疫顾问,海军医学校教员鲁索望为临时防疫医员。(43)《防疫事宜之汇志》,天津《大公报》1918年2月21日,第10版。1918年,内务部呈请奖励的防疫出力人员中,包括医生38人,其中军医达到16人。(44)《呈:内务总长钱能训呈大总统请奖各区检疫委员所属办理防疫出力人员文(附单)》,《政府公报》1918年第1047期,第13—17页。前述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俞树棻既参加过清末东三省鼠疫的防控,并随全绍清奔赴绥远,1919年后担任中央防疫处第三科科长,在是年廊坊霍乱“发生于军营、延及民间”之时,俞树棻等前往廊坊设立防疫分所,在京城帝王庙设立临时医院,“治愈二百余人”。(45)中央防疫处编:《中央防疫处一览》,1926年自印本,第18页。俞树棻在1921年肺鼠疫防控中殉职于山东疫区,可以说为近代防疫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三、疫情防控中所反映的军阀政治特点
清末民初,随着军国民教育兴起,尚武精神在中国渐受提倡,“军事救国”成为许多热血青年实践爱国热情的重要途径。梁启超认为,处于过渡时代的救国救民的英雄,“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46)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32 页。军人除了奔赴战场,还应致力于社会服务:“况我军人,役身军界,原欲牺牲一身,以普救同胞”,如果“无征役之劳,应尽服务之义”。(47)《救灾义勇军总章》,《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近代史资料》第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8页。民初发生的鼠疫和霍乱等疫病的防控中,军人筑起了抗疫的一道道防线,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杨天宏分析认为,在1922年至1924年的历次民意调查中,军阀得到平均29.20%的支持性投票,这说明当时民意中的军阀“尚属两分,薰莸同器,并未形成整体负面形象”,军阀中一些人也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48)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前述军人在民初防疫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可以增添我们对于民国军人军阀形象多面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民初应对传染病的进程也反映了军队私有化后军阀政治的特点,这一特点对防疫抗疫产生了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军阀政治对中央政府抗疫能力的削弱。民国以来,军事长官兼摄民政的权力,使得军事力量从国家属性变成私人性质。民初防疫的历程体现了北京政府面对军阀力量膨胀所体现出来的无力。从中央来讲,负有管理全国陆军军政之权的陆军部注重在卫生防疫方面建章立制,但是,就陆军部的实权来讲,本“宜有无上权力,冠冕各部,然一进窥其实际,则尚不足以拟内务,遑论财政、交通。盖军权纯粹为经略、巡阅、督军节制,初不服部节制”。(49)沃邱仲子:《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1页。绥远鼠疫的防控中,有人质疑,总统并不能指挥得动各地驻防军官:“迄于今日,此等军官对于总统预防瘟疫之命令,辄置诸不理”。(50)《西报之山西瘟疫谕》,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15日,第3版。伍连德在丰镇防疫时,请求中央政府能授他“实权,统辖一切事宜”,“否则虽以连德之历涉艰辛,及身临危险,恐亦不能收良好效果”(51)《收丰镇伍连德电》,1918年1月9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542—543页。,但是北京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他的诉求。防疫需要群防群控,而地方军阀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保全自己地盘的利益。北京政府决定在丰镇设局检疫,察哈尔都统田中玉赶忙反对,认为“现丰镇尚无疫事发生”,“不宜在丰设局检查,致令丰民受此巨害,且有碍火车之进行”。(52)《收察哈尔都统电》,1918年1月6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529—530页。随着疫情扩大,伍连德认为,绥远都统蔡成勋对疫情蔓延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绥远都统并不信有瘟疫之事,对于一切预防设施均不谓然,伊若同从屡次警告,当时足可防止,乃一切拒绝之”,他强烈要求中央政府调换蔡成勋,“改派一热心辅助连德等之人接充,以图设法将瘟疫之来源歼灭”,否则他自己将结束疫区工作,“不得中央、省中暨军队极充足之协助而望连德等扑灭此险恶之疫疠,何可得乎?”(53)《收伍医官等电》,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550—553页。但军阀当道之下,北京政府权力式微。1月15日后,伍连德因患心疾,“病状务必静养,不宜过劳”(54)《收大同何守仁等电》,1918年1月1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615页。,其绥远防疫之旅不得不铩羽而归。伍连德因此感慨,绥远鼠疫防控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难点,其中之一即是“因军队权力太重,多数人民心怀畏惧”(55)《伍连德医士防疫一席话,肺瘟易于制伏,两月内铲除净尽》,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23日,第3版。,“军人权力甚大,中央政府不敢施行严厉之防疫法”。(56)《北方防疫与官场之状态》,《申报》1918年1月17日,第6版。
其二,防疫中军阀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与争夺。地方军阀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严重的疫情面前不作为,或予以消极对待。绥远鼠疫发端于1917年9月,初由伊盟运输皮毛的马车队车夫、商人传入包头。控制和阻断疫情源头本是防控的重中之重,但绥远都统蔡成勋因为有“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的收入,在疫情发生后,仍不允许禁止羊毛商人往来。10月以后,疫情传入土默特旗、归化、丰镇等地,直到12月,北京政府才得悉疫情详情,而蔡成勋一直“装声作哑,不承认有疫之情形”。(57)《西报论晋官场玩视疫症》,《申报》1918年1月15日,第6版。另外,防疫经费的筹集是保障防疫工作进行的重中之重。在北京政府财政吃紧的情况下,陆军部、内务部根据《预防传染病条例》中规定,希望防疫经费“先由地方筹拨,不敷则由国库补助”。蔡成勋则认为,绥远未办地方自治,防疫经费均由国库支出。随后,陆军部、内务部以山西已经自筹经费,绥远“自应一律会设”,蔡成勋又称,边瘠之地绥远无法与富庶的山西“相提并论”,绥远已经筹拨的十万元,系从军饷中暂移五万元,强烈要求中央将绥远所需经费“迅予核准,如数电汇”。(58)《收绥远都统电》,1918年1月2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664—669页。
地方军阀也有借疫情防控之名而进行权力争夺者。1918年3月2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提到,南京自数日前报纸宣传鼠疫流行,“现宁沪间火车仅开至镇江,自昨日起,轮船交通亦断,南京亦有闭城之说”,阻断交通和封闭南京城的真实原因,并不在鼠疫,而是江苏督军李纯“恐奉军与沪军夹攻金陵,因借此题实行防御。前次蚌埠之疫,亦有人谓为不确,谓系有人欲断绝蚌埠交通耳”。(59)《致罗振玉》,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401页。
其三,军队破解防疫问题能力有限。民国初期,绥远匪患严重,在军队与土匪的交战中,“匪胜兵败之时为多”,于是“兵乃不得不与土匪通声气”。土匪不靖,导致“军队检疫者无法下乡”,极大影响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人感慨:“军队对于土匪可谓无用极矣,对于人民可谓苛虐极矣”。(60)《绥远之三》,《申报》1918年5月27日,第6版。除了土匪的影响,绥远鼠疫防控中的另一个难点是,因地处偏远,风气闭塞,当地人对解剖、焚烧尸体等防疫行为还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因为鼠疫严重,不少外国及留学归来之医士受中央政府邀请或允许,来到疫区参与防疫,囿于习俗之故,民众对于防疫人员产生仇视心理,甚至凌辱、殴打防疫医生。绥远都统与军队对此纠纷无力解决,或者消极对待。蔡成勋对现代医学和防疫知识知之甚少,据北京政府委派的防疫委员何守仁称,“火葬一事,本为防疫要著,而蔡都统竟视为非常,遂致不能实行”。(61)《收丰镇何守仁电》,1918年1月2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674—675页。对于前往绥远的美国医生,持怀疑和抵拒态度的蔡成勋致电北京政府,称“美国人路长乐、伊复宰二名,自称系红十字会大夫,由察来绥欲办防疫事宜”,但是,他们“并无持有证据,到此即要求断绝交通,自认防疫腹地内政,何得任为干涉”,建议北京政府将此二人“劝令出境”。(62)《收绥远都统电》,1918年1月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518—519页。外交部同日回复劝导称:“美国医士路易士等前赴绥属,系辅助本部伍医官查疫,实为热心赞助起见,并无他意”,希望地方官能“以礼貌相接,遇事予以便利”。(63)《发绥远都统电》,1918年1月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0-01-001,第736—737页。就是被寄予防疫厚望的伍连德本人,也称因“地方长官与住民反对,致吾等所乘之专车几乎被伊等围焚,危险万分”。(64)《伍连德自传》,李冬梅主编:《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其四,军阀混战下防疫对战争的退让。民国初年,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常与军阀混战并存,疫情防控严重受到来自战争和政治的双重掣肘。据统计,1916至1918年间,全国有9省发生规模不等的战争。(65)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如前所述,由于巨额的军费支出,北京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力应付防疫所需。1919年,财政部声明,“嗣后各省请款,本部概不应付”。(66)《自决》,《申报》1919年4月22日,第3版。为了争权夺利,扩大地盘,无论是在直系皖系把控的北京政府还是地方军阀看来,疫情防控都要让步于战争。1917年9月,护法战争发生,1918年初,直隶出现疫情,尤以平山为重。此时直隶督军曹锟已被总统冯国璋任命为两湖宣抚使,率部进兵湘鄂。直隶是中央防疫委员会划定的防疫第四区,按照《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军队检疫需由军医官按法检验,给予凭单后,再交路设检验所复行查看放行,曹锟认为程序太过复杂,会“耽延时刻,有误戎机”,因此,陆军部允许其凡属“军队运输关系前方者”,只由军医官按法检验,其余程序一概省略。(67)《天津曹省长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第738期,第27页。严格的防疫规定在战事面前成为一纸空文。因为曹锟率军南下,对直隶疫情无暇顾及,内务部只好致电山西督军阎锡山,以平山与晋省接壤为由,请其“加派弁兵在晋边各口协力堵截”(68)《江朝宗、钱能训致山西阎督军电(二月九日)》,《政府公报》1918年第748期,第19页。,协助防疫。
除此之外,军阀混战助长了鼠疫扩散。1918年,大批奉军南下,让南京鼠疫更为严重:“自北军陆续南来,而直晋间流行之鼠疫亦随以俱来,由浦口而至下关,近更蔓延于城内各区。”(69)《纪南京之疫讯》,天津《大公报》1918年3月25日,第3版。疫情与战乱的双重夹击,导致民不聊生,物价奇昂。为了应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南京当局加紧布防,导致南京城人心惶惶,百姓流离在道:“宁垣鼠疫甚厉,沪宁路今日停开南京至镇江客车。昨晚赶乘夜车之旅客尤形拥挤,其行李箱下关车站堆积如山。”(70)《时事录要 南京军事行动之现状》,《益世报》1918年3月29日,第6版。就是在防疫力度较好的山西,因为疫情而“断绝交通,致使物价腾贵”,时人感慨“草野百姓,十室九空”,“民何不幸而生于斯时耶”。(71)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38、253页。
结 语
军队防疫是民国初年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战斗力,民初陆军部及地方军队在防疫法规的建设、防疫知识的传播方面做了积极努力。在疫情的应对中,军队成为防控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在参与地方防疫组织、阻断交通、加强防疫医疗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一时期的军队防疫活动,也比较具象地反映出北京政府时期防疫事业在制度建设、知识传播、组织动员等方面的进展。但是,如同有的学者所言:“在北洋时代,时代问题就是军阀问题,就是军阀的纷争、割据、战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和社会就无法正常地运转”。(72)翁有为:《北洋时期的军阀纷争与时代主题论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2期。民初疫情防控也集中而具体地呈现了军阀政治的特点,地方政权军事化和割据化削弱了中央政府抗疫能力,防疫过程中常常贯穿着军阀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与争夺,军阀混战助长了疫情扩散,并进一步加大了防疫的难度,疫情防控严重受到来自战争和政治的双重掣肘。凡此种种,又展示了军阀政治下国家防疫事业的困境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