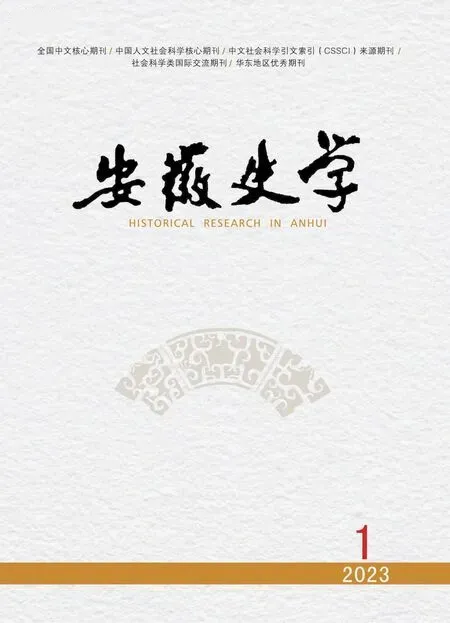从“同频”到“共振”:抗战时期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多维经济互动
刘岩岩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晋绥边区是抗战时期华北三大根据地之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学界对二者的研究,历来著述颇丰,尤其在其经济发展方面,不乏经典之作。(1)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刘欣、景占魁主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晓彪、萧绍良、司俊编著:《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等。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发展进行分别论述,对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则着墨不多。按照物理学的解释:同样频率的东西会共振、共鸣或走到一起。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虽然分别位于华北和西北两大经济系统,但在地理上相毗邻,二者隔黄河而望,地理环境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历史上往来亦较为频繁,抗战时期又同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内部治理和外部应对之策相似,本属“同频”,但囿于主客观诸多因素,在抗战时期一度交流受阻,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理所当然的“共振”。此中原因颇耐人寻味。借助物理学相关概念,并从区域经济学的相关角度切入,对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二者的经贸互动进行深入探究颇为有益。
一、同频之源:抗日根据地之间经济互动的基础
(一)抗战爆发前晋陕两地的商贸传统
抗战时期的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地理上分属华北和西北地区。从经济地理角度分析,因为两地相邻,“晋陕绥一河相隔,疆界毗连”(2)张萍主编:《西北近代经济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页。,且传统商路较为通畅,商业上碛口、河曲等主要市镇向为秦晋交通要道,“为西北与沿海各大城市货物输出入的集散地”(3)⑨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税收工作情况》(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336页。,所以抗战前这两大区域在经济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为诸如盐、碱、甘草、麻油等传统商品的流通提供了基础。于陕西而言,虽紧邻山西,但因其内部按照经济地理层面划分,又分为陕北经济圈、关中经济圈和陕南经济圈。因交通的相对便利,和山西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是陕北经济圈,“而陕北当时与山西仅一河之隔,有多处渡口之便,又因山西境内同蒲铁路连接正太铁路,贯通平(京)汉铁路,可以直达对外贸易的商埠天津”。(4)③王一成、韦苇编著:《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页。基于此,陕北本地的出产如羊毛、皮货等经过山西转运到天津港出口,具体贸易路线上,以陕北的榆林、安边、神木为集中地,“榆林、神木两处集中的货物经米脂、息蜊峪(即螅蛎峪——作者注)、离石过河到山西汾阳达榆次,再由榆次用火车转运至津。而安边所集中的羊毛,则运经宁条梁、石湾、绥德、吴堡、宋家川过河到汾阳而达榆次,然后装车转津。”(5)③王一成、韦苇编著:《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页。通过山西的转运,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出产进入到国际市场,逐步实现了经济外向化的过程。陕西所需产品的进口路线中,山西同样是重要的中转站,“日用品如石油、洋烟、肥皂、火柴、糖,其他杂货如文具、纸张、瓷器、五金等,战前全部由津、晋运来”。(6)⑥张萍主编:《西北近代经济地理》,第246页。
在工业发展水平方面,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前推行“造产救国”,推动了山西重工业的迅猛发展,“仅太原一地,西北制造厂与东北沈阳兵工厂并驾齐驱,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而其他如火力发电厂、炼钢厂、大小型卡车制造厂、机械制造厂、汽车配件制造厂、洋灰厂、各种化学制造厂以及卷烟厂、纺织厂等,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7)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具备一定规模的山西工业在民国时期颇有实力,其生产的商品较为丰富,不但满足省内需要,并且行销多省,其中就包括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如西北火柴厂生产的火柴,西北实业公司晋华卷烟厂生产的香烟,皆把陕西等西北区域作为重要的销场。除了工业品,山西出产的粮食、棉花亦多供给陕北地区。(8)⑥张萍主编:《西北近代经济地理》,第246页。在工业发展水平方面,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前推行“造产救国”,推动了山西重工业的迅猛发展,“仅太原一地,西北制造厂与东北沈阳兵工厂并驾齐驱,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而其他如火力发电厂、炼钢厂、大小型卡车制造厂、机械制造厂、汽车配件制造厂、洋灰厂、各种化学制造厂以及卷烟厂、纺织厂等,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9)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由此可知,抗战前,晋绥地区和陕甘宁地区两地的经济交流,基本以农矿初级产品为主,山西因为在陕西东部,距离东部沿海港口更近,其在陕甘宁经济外向化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二传手”的角色。两地在抗战前的经贸往来传统,为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层面的同频共振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经济因应之策的趋同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有关精神,更名为边区政府。抗战时期,“中共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外,并未建立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并且,“中央主要是从党和军队的角度对根据地进行一元化的领导和管理”。(10)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3页。但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总后方,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实施后,才在其他根据地推行。”(11)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第62页。此两种观点,在陕甘宁边区和地方根据地关系之表述上确有差异,但从求同存异的角度来看,都承认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地位,只是在经济治理的方式上有不同认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同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二者在抗战过程中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斗争任务,既要坚持对敌斗争,又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且两地皆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工商产品需要大量输入,所以大体上处于同一个频率。同时,因为两地都属于传统农业区,经济构成也颇为相似,“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一河相隔都是农业地区,对外来品需要和能输出的货物相差不多”(12)⑨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税收工作情况》(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336页。,所以在经济同频的基础上,理应引起双方深层次的共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二、“共振”之困: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经济互动的障碍
(一)交通和运输条件落后
作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晋绥边区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西面经过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通到大后方。东面是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东南是晋冀鲁豫边区。南面是晋西南。”(13)牛荫冠:《晋西北行政公署向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2年),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看似和各根据地四通八达,但实际上沟通联系起来却很困难,因为除了和西面的陕甘宁边区隔着黄河外,与其它方向的根据地均隔着敌人的封锁线,这就使得晋绥边区三面被敌人包围,处境较为凶险。从根据地分布的物产资源上看,晋绥边区虽然有产粮区、纺织区、煤铁区,也蕴含各种矿产,但因为地处黄土高原,“境内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14)刘欣、景占魁主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第221页。,社会经济条件落后,所以直到抗战爆发,也没有得到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陕甘宁边区对外交通运输同样落后,“考其原因,并不是完全由于运输力量不够,而主要是因为没有建设应有的交通运输设备,未能合理的保证草料的供给,以至有了运输力量不能使用。”(15)《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7页。运输工具的落后亦是大问题,两地位居内地,远离现代交通运输线,既无铁路,也少公路,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极其匮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只有十几辆汽车,“而且由于缺乏配件,能够开动的就更少了,还不能真正用于商业运输。边区马车的数量也极为有限,最多时没有超过二百辆。”(16)邓文卿:《陕甘宁边区的骡马店》,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由于陕甘宁边区交通的落后,隔几十里外的原料就不易利用,“运盐、运粮运费常超过成本”。(17)《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因边区依然是使用牲畜承担主要运输任务,不但运量有限,而且时间成本高,给两地经贸往来带来诸多不便。
(二)日军的抢掠和封锁
抗战爆发后,晋绥边区原本脆弱的生产事业和经济基础在日军反复的“扫荡”下,遭受极大破坏,“特别是1940年一年四次大规模扫荡,使内地兴临各县开始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18)⑦晋绥地区行政公署:《晋西北三年来的生产建设》(1943年),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93、494页。原本薄弱的工矿事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整个生产都走向急剧衰落的趋势,织布几乎完全停止了,造纸的也减到战前的半数以下,煤瓷均比战前减少一半以上,一部分工商业破产,人口转为小农维持生活。”(19)⑦晋绥地区行政公署:《晋西北三年来的生产建设》(1943年),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93、494页。除了对根据地大规模的“扫荡”外,日军还在游击区进行抢掠,至于对边区经济封锁更是异常严厉,1941年的“三次强化运动”,日军按地区实施封锁,“各据点均设有经济班,负责进行查缉,不许物资出据点。即在据点之内其办法也异常严格,违者处死。”(20)晋绥边区行署:《晋绥边区贸易工作材料》(1944年8月29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566页。境况之惨烈,使得原本和陕甘宁边区保持的经济互动颇受影响,想要在经济层面产生共振非常困难。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直接遭受日军侵略,但形势也异常严峻,“日军屯兵柳林,积极准备着进攻陕北”(21)肖劲光:《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西北五省区编写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并出动空军,对延安地区频繁轰炸,给两地正常的经贸交流,带来极大破坏。
(三)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和破坏
无论是晋绥边区还是陕甘宁边区,在抗战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都是重要问题。作为战时名义上一致对外的“友军”,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表现得却不甚友好。针对晋绥边区,国民党军队封锁食盐不准运过来,造成食盐价格昂贵,从1941年每百斤70元涨至1944年的2000元以上。对黄河上游船只和去陕北贸易的商人经常随意扣留甚至迫害。(22)晋绥边区行署:《晋绥边区贸易工作材料》(1944年8月29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568页。如果遇到极端的反共摩擦事件,则损失更大,1939年,山西阎锡山集团挑起晋西事变,一度给晋绥边区的对外贸易带了重大损失,“境内对贸易的市场,大部停顿”;“外来贩货商人减少了。境外商人贩货入境的,一时减到很少”;“外来货物减少了。短期内就很少有外货进来”。(23)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商业贸易发展概况》(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507页。此种损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经济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更是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重点封锁,“正规军五十余万人,各级地方政府税收机关、地痞流氓组织起来的各种便衣队到处都是”。(24)贸易公司:《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封锁材料》(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除了颁布法令禁止货物进出边区,国民党军队直接抢劫没收进出边区的货物,枪杀从事贸易的商民,并根据陕甘宁边区不同地方的特点,针对绥德、陇东、三边地区采取不同的封锁方式。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之严厉,让人瞠目结舌,以至时人惊呼,“国民党和边区虽然同属于一个国家,共同抗日,但在贸易上却比苏德协定期间,法西斯德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关系还要坏。借贷关系固然不必讲,国民党根本就不让物资进来,并断绝了汇兑关系。”(25)贸易公司:《边区区际贸易差额的实质》(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73页。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陕甘宁边区很难对外开展大规模的正常经贸活动,其和晋绥边区虽有地理毗邻的便利,但在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一样处处受限,二者若要实现经济上的共振,仅凭借经济规律这只无形的手是不可能的,只有主动作为寻求突破。
三、“同频”到“共振”的转变:边区政府的因应
(一)基于战时比较优势的两地贸易往来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每种物品应该由生产这种物品机会成本较低的国家生产”(26)[美]曼昆著,梁小民、梁硕译:《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此种理论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不同地区,一个地区在本地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它地区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该地区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抗战时期,由于东中部地区大片国土的沦丧,抗日根据地周边和自身的经济情况也发生变化,原本不是优势的因素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所以,根据战时比较优势理论,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将本地区的特色出产输出到对方,从而实现二者在抗战时期的互通有无。
陕北的传统特产,向有三宝之说,即食盐、甘草和皮毛。战时环境下,“甘草因运量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27)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地区,是边区食盐出口的主力,每年约产盐60万驮,每驮150斤,共9000多万斤。陕甘宁边区150万人口食用的需求为1000万左右,剩下的都可以出口。(28)陈凯:《陇东盐业贸易的反封锁斗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加之抗战以来,东部所产的海盐断绝,西北各省和华北地区对于陕甘宁边区出产的食盐需求量大增,1938年边区食盐运销还只有7万驮,1939年增加到19万驮,1940年为23万驮。(29)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编:《一九四三年的运盐工作》(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第693页。晋绥边区所需食盐,多依靠外部输入,“全晋西北食盐、白碱赖河西供给”。(30)⑥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商业贸易发展概况》(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502、501页。“河西”即是黄河以西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西北地区。由于晋绥边区产盐甚少,所以根据地所需食盐,需要完全从外部购入,全年约需400万斤,具体到不同地区,晋绥边区的三分区由陕边区输入240万斤,二分区由府谷输入约80—90万斤,兴县经神府由神木输入约45万斤。(31)晋绥边区行署:《晋绥边区贸易工作材料》(1944年8月29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571页。由此可知,陕甘宁边区出产的食盐,至少解决了晋绥边区所需的60%。除了食盐,作为棉花重要产区,陕西棉花储备颇丰,陕甘宁边区收购的棉花,“不仅供给了全年机关部队棉花的需要,而且供给了晋西北大部分的棉花”。(32)喻杰:《土产公司工作报告》(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215页。
相较于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经济有一定基础,“晋西北建设的物质条件,自然环境较优于陕甘宁边区。物资丰富(粮食、工业、原料、畜产、森林、药材等)富饶,蕴藏深厚(如各种矿产煤、铁、锰、陶土、硫磺、火硝等)。”(33)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对晋西北经济建设的建议》(1940年6月29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65页。因此晋绥边区农产品在自给的同时,如有合适机会,亦对外输出,“粮食除河曲、宝德自给不足外,其他县份都可以自给。游击区食粮大量运输根据地,一部运往河西”。(34)⑥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商业贸易发展概况》(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502、501页。煤炭是晋绥边区的大出产,“估计全边区产煤达十数万万斤。其中自用一部外,输出数也在近十万万斤。”(35)⑧《晋绥边区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贸易工作综述》(1946年7月10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646页。对外输出的区域除了绥远、怀朔平川、同蒲路东各地以外,渡过黄河向西输出的自是不少,“一、二、三分区从黄河向西输出的炭也不少,只柳林渡口每月即可用炭换回盐一万斤”。(36)⑧《晋绥边区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贸易工作综述》(1946年7月10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646页。
为了使物资交换和商贸往来更加顺畅,步调更趋一致,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于1943年签订了物资交换协定书,“双方议定以绥德分区之螅蛎峪为物资交换地区,由双方派员在螅蛎峪设联合办事处”。(37)⑩《晋西北行政公署、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物资交换议定书》(1943年4月1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408页。照此规定,晋绥边区负责黄河以东采购土产的工作,必须保证按陕甘宁边区需要数字将土产运至螅蛎峪联合办事处,全部交给对方,概不自行出售,亦不向边区内地运送,同时陕甘宁边区停止过河东采购土产,专门在联合办事处收货。(38)⑩《晋西北行政公署、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物资交换议定书》(1943年4月1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408页。这样双方既能保证物资交流的便捷和高效,同时为两区域在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协同打下了基础。为了推动两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944年12月晋绥边区在延安成立“晋绥边区办事处”,并规定:“今后晋绥边区各财经贸易单位与陕甘宁边区财经贸易公司的往来,一律经过晋绥边区办事处;陕甘宁边区部队、机关、学校如赴晋绥边区进行贸易事项,须一律经由晋绥边区办事处的介绍,否则晋绥边区一概拒绝。”(39)《西北财经办事处通知》(1944年12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晋绥边区办事处的成立,进一步扫除了两根据地直接贸易的障碍,有利于二者经贸层面的协同一致。
(二)骡马大会的恢复和发展
从功能上看,北方根据地的骡马大会是传统社会农耕文明中具有经济功能的庙会在抗战时期的调整和发展,其前身的庙会作为农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初,商品交易已成为许多大中型庙会的主要功能,庙会演变成特种定期集市或中小型商品展览会。”(40)刘太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0—1731页。抗战军兴,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骡马等牲畜交易就成了庙会交易的主要形式,“民众对庙会中骡马交易的重视与根据地政府借庙会活跃牲畜、农具市场的初衷不谋而合,因此,在恢复庙会的过程中,有地方政府就将传统庙会直接改称骡马大会或骡马百货市场进行宣传动员。”(41)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受此影响北方各根据地的骡马大会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无论是晋绥边区还是陕甘宁边区的骡马大会,除了具有牲畜交易的基本功能外,在沟通两地经济交流以及密切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7月15日,晋绥边区的兴县举行骡马大会,到会群众和客商达7万人,交易额1300多万元,陕甘宁边区的客商也赶来参会,推动了两地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42)李树萱、晋晓伟:《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大事记》(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44页。陕甘宁边区的骡马大会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延安的骡马大会级别高,规模大,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亲访现场,周边商旅热情踊跃,并吸引了晋绥边区商业机构参加,“而晋绥过载行市部门,永福祥、万瑞祥、晋豫合、德盛玉的四商店联合门市部,以及新上市街上的国货公司,妇女合作社营业部门,购物者均极拥挤”。(43)《延安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403页。陇东的骡马大会会期共10天,场面热闹非凡,“万商云集,贸易鼎盛,与会者不仅有边区各县群众,并有友区人民,包括陕、甘、宁、青、晋、豫等省远近客寄”。(44)《陇东举行骡马大会》(《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406页。骡马大会的恢复和发展,和抗战以来尤其是1943年后根据地经济形势的好转有密切关系,所以能借助传统商品展销会的形式,促进以牲畜为核心的农贸产品的交流,从而密切边区间的经济联系。
(三)两地金融的互动
1940年晋西事变之后,晋绥边区取得对阎锡山斗争的胜利,于5月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其发行的农币在1941年1月成为边区唯一合法的本位币。与之相邻的陕甘宁边区亦有其银行,并在抗战初期发行光华代金券。因为良好的信用,光华代金券甚至流入陕甘宁以外的地区。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实际对敌斗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银行还发行过边币和流通券。无论是晋绥边区还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都需要从外面输入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和军需用品,尤其是医药、军火和日用品还必须从沦陷区或者国统区购来。同时,和国统区地理环境上的紧密相连,也使得被根据地军民称之为“友区”的国统区的法币在边区一度大行其道,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在边区三十一个县市二百十八个区中,有二十四个县八十一个区是与友区犬牙交错着的边境,约占百分之四十的地区人民生活与友区经济密切相联系,因此,他们要使用法币交易。”(45)王思华:《再论如何稳定目前金融》,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边区百姓对法币的选择不是简单靠行政命令就能禁止的,因为边区和“友区”甚至边区之间彼此金融上不能通汇,必须使用对方的货币,所以边区军民一般先在边区银行完成相应的货币兑换,“汇兑工作虽已建立,但范围非常狭小,并只能与陕甘宁边区有来往”。(46)《晋西北货币金融的发展简况及现状》(1942年9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86页。
晋绥边区管理对外贸易汇兑时,虽然给予了陕甘宁边区特殊待遇,“陕甘宁边区基本上以内地论”(47)《晋绥边区管理对外贸易汇兑办法实施细则》(1944年10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418页。,但是因为两边区使用不同的货币,也就是说陕甘宁的边币过了黄河到对岸的晋西北即不能使用,晋西北边区政府发行的农钞到了陕甘宁边区亦不能流通,这就给基层百姓带来困惑,“群众的反映:都是八路军的票子,如何不能互相使用?”(48)《陈希云、刘卓甫、王恩华统一两个根据地的货币之意见书》(1944年2月15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第21页。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老百姓不但对两边区的货币都不信任,边区之间物资交流更多还是使用银元或者法币,并且因为折算的不同,带来新的争端,反而增加了银元和法币的优势,打击了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黄河沿岸,银洋暗流,很难禁绝,以致影响金融,阻碍物资交流”。(49)刘卓甫:《晋绥金融工作报告》(1948年4月2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286页。受战时条件所限,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随着两地银行的合并,才真正实现货币的统一,“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统称西北农民银行”。(50)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1947年11月),杨世源主编:《西北农民银行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四)边区政府层面的沟通和政策的协同
商贸往来、骡马大会及金融互助,都需要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在政府层面进行高效沟通,并从政策方面给予制度保障。为了统一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军委1942年5月13日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两块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和建军工作。(51)《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1942年5月13日),西北五省区编写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册,第241页。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经济工作”。(52)喻杰:《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工作》,西北五省区编写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120师自抗战爆发后,就开始在晋西北地区活动,并长期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所以由师长贺龙负责陕甘宁晋绥联军,自然是最合适人选,同时由其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也有利于统筹两地的各种力量,“这就进一步达到对外贸易的统一,便利于我方价格斗争,增加了财政收入”(53)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35页。,从而有助于具体工作的开展。
财政经济的统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包含了很多具体而且复杂的问题,边区政府首先统一两地的经济政策,“以确定共同努力的方向,然后依此方向,再发展成为具体的合作”。(54)《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上半年财政报告及今后意见提纲(节录)》(1942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页。除了前文所述两地在物资交换的深度合作外,在税收方面也推进统一工作。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为了发展双方贸易,将双方货物过境税取消,在此之后,双方合作更加密切,步调愈加趋于一致,尤其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斗争策略统一同步,且互相配合,“如一区允许进口,一区禁止进口之物资则不得由允进区转入禁进区,否则禁进区得按物资管理规章及办法处理;如允进区需用之物资,又必须经过禁进区时,允进区得托禁进区之贸易公司代为购运,但须得保证不在禁进区销售。”(55)⑨《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陕甘宁晋绥两边区贸易税收之决定》(1945年7月10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421页。此举就规避了敌人利用根据地之间沟通不畅的缺陷,采用迂回的办法,向根据地倾销奢侈品等禁止非必需品的经济侵略方式。同时,两边区还规定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土产品互相销售时一视同仁,“在两区内各地销售,与本区之土产同等看待”。(56)⑨《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陕甘宁晋绥两边区贸易税收之决定》(1945年7月10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421页。
四、被区域分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贸易互动虽然始终在进行着,但是受币制的不统一等因素的影响,双方在贸易上遇到的障碍也比较多。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譬如边区与敌区直接交换的货物而在晋西北方面都是禁止入境的,他就不准运过,这样就交换不成,以致影响与地区的贸易。”(57)②绥德分区:《贸易总结材料》(1944年3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552、553页。此外,不同根据地的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的税收政策以及对一切货物的极端统制也一度给根据地间正常的贸易带来种种困难。1942年,随着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成立,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向着在财政经济上统一为一个整体而努力,双方政府之间也通过系列谈判达成共识,颁布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两地经贸往来的政策,并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总体趋势虽好,“实际上还有些问题没解决(如税收手续问题,收算归款问题,双方贸易配合问题等等)”。(58)②绥德分区:《贸易总结材料》(1944年3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552、553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建设,虽受到区域的分割,也不同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但已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59)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由此可知,毛泽东对于不同根据地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地方根据地好的做法具备在全国推广的价值,这也是新中国经济治理的雏形。问题也随之产生,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空间地理的分割作用下,虽然处于同一频率,但在相互共振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由于根据地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和分布的非均匀性,一方面构成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则导致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下达到各根据地时,因不同根据地斗争形势的不同以及受区域间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实践模式。在战时极端困难的外部环境下,根据地之间商品交易的空间障碍更多,导致交易成本更大,经济效率势必降低,这也是根据地经济即使同频却不容易共振的原因。根据地的区域经济属性,使处于同一频率的不同根据地之间存在一种非均衡力,从而让它们之间战前单一的商贸往来形式的线性流动,升级为战时经贸、金融和政策的多维互动。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中共中央的经济指导,还是根据地政府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模式创新,都在不断的共振中反复调试,进而达到协同统一,从而为日后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宏观治理提供了经验。中央和地方良性的互动、区域经济政策的整合和推动、同一频率经济体之间的和谐共振,对今天区域间经济的协同发展亦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