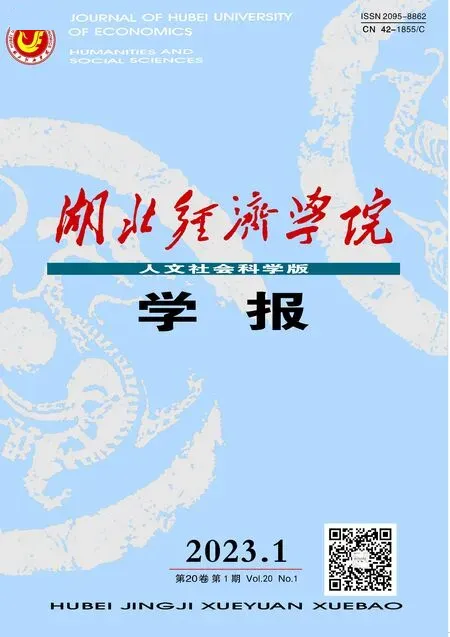网络诈骗犯罪取款人司法定性研究
李 倩,王 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成为犯罪分子青睐的犯罪工具或手段,网络犯罪的数量在不断攀升,犯罪方式、犯罪种类也在不断变化和增多,给刑法的适用提出了不少难题。以诈骗犯罪为例,网络诈骗犯罪正以其成本低、收益大、易得逞等特点而频频发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进化,已经成为环节复杂众多、分工精细明确的“公害”犯罪。诈骗者为了逃避侦查,常将帮助取款行为①独立出来,由此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1]。对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如何定性尚存在不同的观点,司法裁判中也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有的案件中,帮助取款人与网络诈骗行为人之间存在事先的犯意联络,而有的案件中,帮助取款人只是在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负责取款,并没有共谋,对于不同种类的帮助取款人如何界定其刑事责任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以期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网络诈骗”“取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1442份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时间截至2022年3月初),涉及罪名有诈骗罪、集资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罪名。为了对网络诈骗犯罪中取款人的刑事责任做出分析,从这些案件中随机选取了30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其中有21份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8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还有1份一审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二审改判为诈骗罪。根据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区分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存在“事前通谋”。要认定帮助取款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需认定取款人与网络诈骗行为人之间在事前、事中存在通谋,无论取款人是先与网络诈骗行为人一同实施了诈骗行为,钱款到账之后又实施取款行为,还是并没有参与诈骗行为的实行,只按照事先分工在诈骗得手后将赃款取出,都对诈骗犯罪的实施提供了行为上、心理上的帮助和支持,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若帮助取款人没有参与网络诈骗行为的实施,也没有事先通谋,就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由于不同的审判机关对于是否存在事前通谋以及如何认定事前通谋存在不同的理解,才造成同案异判的情况。以下面四个案件为例。
案例一:在羊某博诈骗案中,羊某博在互联网上冒充网警接受被害人报案,并以涉案银行卡需要刷流水激活并紧急将涉案钱款转移至安全账户为由,诱骗被害人将钱款转移到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后指使羊某定帮忙取款,羊某定明知钱款系犯罪所得仍帮助其将约3万元的现金取出,获利2900元。法院认定羊某定明知是犯罪所得仍帮助转账、取现,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②。
案例二:2019年6月初,被告人林某坤纠集被告人林某买,在南靖县一出租房内实施网络诈骗犯罪,通过婚介网站寻找具有感情需求的潜在被害人,伪装成条件极好的单身人员,诱惑被害人与其发展感情,长期的聊天交往使被害人对此感情越来越信任,此时林某坤谎称自己有可以轻松赚钱的门路,诱使被害人测试其本人制作的网上赌场微信小程序,后将赚到钱的截图发给被害人,被害人信以为真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等钱款到账后马上关闭网站,从而骗取大量资金,后林某买帮助取现。林某买明知钱款是林某坤诈骗所得收益仍帮忙变现,被法院认定为林某坤的共犯,构成诈骗罪③。
案例三:2018年3月,刘某1、刘某2与刘某3等五人通过多个微信号添加陌生好友并将他们邀请至其所建的微信群,刘某3充当“理财导师”在群中发送购买彩票方案链接,其他成员伪装成跟单中奖客户,造成中奖假象,取得新入群人员信任后,引诱新入群人员在刘某1等人控制的虚假彩票网站注册、充值,之后通过网站后台操作控制,实施诈骗。陈某与刘某等五人无事前通谋的情况下多次帮助取款,在意识到所取钱款系犯罪所得后,又分两次帮助支取现金共计8.6万元。陈某被法院判决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④。
案例四:2019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王某、李某、任某等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在云南蒙自多次通过POS机帮助诈骗行为人支取诈骗资金4万余元,并按照取现金额收取相应的好处费,法院认为,王某、李某、任某等人的行为属于网络诈骗分工细化(共同犯罪)中的一环,构成诈骗罪的共犯⑤。
上述案例一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例二的定性是诈骗罪,适用不同罪名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存在“事前通谋”,司法实践中“事前通谋”的时间点如何把握?如果取款人连续为同一网络诈骗实行犯取款,刑事责任如何定性?在上述案例三和案例四中,案情也基本相同,判决结果却不同,那么,在没有事前通谋的前提下,取款人连续多次为同一网络诈骗行为人取款的,应该如何定性?下面拟对这些问题作以探讨。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
如果取款人与诈骗行为人没有事先通谋,取款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在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帮助诈骗行为人取款一次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的重点在于取款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明知”包括确切知道和应该知道(推定的知道),或者说取款人对犯罪所得的认识包括必然是以及可能是两种情况。司法实践中,诈骗行为人在向取款人交付犯罪所得赃款时,出于隐蔽考虑,一般不会告知取款人这是赃物,基本上是想方设法隐瞒赃物的性质,彼此心照不宣,这应该是常见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有的取款人会多次为同一诈骗行为人取款,在没有事前通谋的情况下,取款人多次为同一诈骗行为人取款的刑事责任如何认定?笔者认为要分情况而论。“多次为同一诈骗实行犯取款”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诈骗行为人在实施一次网络诈骗并得手后,为了掩盖赃款的来源,会将赃款转移到多个不同的银行卡中,然后安排取款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多次将诈骗所得赃款取出。之后该诈骗行为人由于落网等原因不再继续实施网络诈骗行为,或取款人由于害怕受到法律制裁等原因不再继续实施帮助取款行为。在此种情形下,虽然也属于取款人为同一网络诈骗行为人多次取款的情形,但由于诈骗行为人只实施了一次诈骗行为,取款人的连续多次取款行为都是在为诈骗行为人的同一个诈骗行为提供帮助,事前也没有通谋,只是犯罪既遂后才参与进来的,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第二种情况,同一网络诈骗行为人在实施了多次诈骗行为并都已既遂之后,安排取款人将已经既遂的前几次的犯罪所得分多次取出,这种情况虽然也属于“连续多次为同一网络诈骗行为人取款”的情况,但是由于取款人所帮助的这几次诈骗行为都已经既遂,在不属于事前通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人没有认定诈骗罪共犯的可能,只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第三种情况,取款人在反复帮助同一网络诈骗行为人取款过程中,诈骗行为人继续实施诈骗行为(一边是实行犯诈骗,一边是帮助人取款),如果取款人与诈骗行为人没有事前通谋,帮助取款人是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还是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取款人刑事责任认定的重点在于其主观心理判断。司法实践中,不少案例对于反复为同一诈骗行为人取款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房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中⑥,被告人房石某、房志某就是多次为同一人实施取款行为,法院认定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本案中,介绍房某两人实施取款行为的中间人没有告知二人所取款项为诈骗所得,甚至都没有告知二人所取款项是违法犯罪所得,只是两被告人从取款的次数、数额、方式等来推知这些钱的来源不正当,应该属于赃款。如果取款人只是感觉自己取的款可能是犯罪所得,但并不知道是哪种犯罪所得,“你不说来源,我也不问”应该是更加常见的处理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如果取款人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一种犯罪所得的赃款,就不能认定为上游犯罪(诈骗罪)的共犯,只能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者说,难以从证据方面证明取款人对上游犯罪的性质属于哪一种犯罪有认知,其主观方面只局限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不是诈骗所得),无法认定取款人是上游犯罪的共犯。
三、诈骗罪的认定
(一)“事前”的时间界定
根据《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帮助取款人与诈骗行为人“事前通谋”的,属于事前约定、事后帮助取款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行为人的帮助犯[2]。“事前通谋”的“事前”是成立诈骗罪共犯的主要条件,“事前”如何理解?狭义的理解“事前”应该是指在诈骗行为着手之前进行帮助。实际上,根据刑法理论,帮助犯不仅能在狭义的“事前”提供帮助,也能在“事中”提供帮助,这里的“事”是指实行犯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从诈骗犯罪的发生流程来看,帮助犯成立的时间只存在于“事中”的终点之前,那么,“事中”的终点该如何界定呢?帮助行为可能出现在犯罪预备阶段,也可以与犯罪的实行行为同步进行,也可以在实行行为完成了一部分之后实施,但不能在犯罪既遂之后实施[3]。犯罪既遂之后,由于犯罪行为已经实行完毕,任何其他行为都不会再对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帮助作用,不存在与犯罪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空间,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因此,“事中”的终点是犯罪既遂,也就是说,区分“事中”与“事后”的界限在于犯罪是否既遂。具体到网络诈骗案件上来,“事前通谋”发生在诈骗犯罪既遂之前,在满足其他要件的情况下帮助取款人应被定性为诈骗罪的共犯;若是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就不存在“事前通谋”了,无法认定帮助取款人为诈骗罪共犯,在满足其他罪的构成要件的条件下可以认定为其他犯罪(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因此,诈骗罪的既遂标准就成了决定帮助取款人司法定性的重要因素[4]。
关于诈骗罪既遂标准的争议,存在多种观点,有“控制说”“失控说”“占有说”“失控+控制说”等。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控制说”和“失控说”。“控制说”是指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上支配、控制公私财物为标准判断既遂,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持此观点[5]59-60。“失控说”是指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支配权为标准判断既遂。一般情况下,“控制说”和“失控说”会得出近乎相同的结论,这是因为在传统诈骗犯罪中,被骗财物失控的时间和犯罪人取得财物的时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以至于两种学说的结论没有差别。但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有其不同之处,被害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时间与犯罪人实际取得财产的时间不一定相同,根据相关文件规定⑦,会存在24小时时间差。若取款人在此24小时期间内参与进来,根据“失控说”的观点,此时被害人的财产已经脱离控制,诈骗犯罪已经既遂,取款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根据“控制说”的观点,此时诈骗行为人还没有实际控制财物,犯罪还没有既遂,此种情形下取款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由此,不同的既遂标准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时点怎么认定合适呢?诈骗罪是侵犯财产型犯罪,财产是否遭受实际损失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因素,只要欺骗行为还没有造成现实的财产损失,就只能认定为诈骗未遂[6]523。反之,一旦法益受到破坏即公民的财产受到侵害就应认定犯罪既遂。笔者认为,只要被害人失去对财物完全的、自主的控制就属于财产权已经遭到了侵害,故赞同“失控说”,理由在于:“失控说”不仅与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的立法精神契合,同时也加大了对诈骗犯罪的惩处力度;相反,如果采用“控制说”,当出现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而交付财产却误把财产交给他人的情形时,诈骗行为人就会被认定为犯罪未遂,这既轻纵了犯罪人,也导致被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无法得到对等的法律补偿。因此,从法益保护的立场出发,将“失控说”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应该是较优选择。即被害人失去对被骗财物控制的时点,就是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时点。那么,被害人失去对被骗财物控制的时点如何认定呢?
网络诈骗中被害人失去对被骗财物控制的时点分析。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时点应该是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时点。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的诈骗犯罪相比,财产转移的方式有所区别,网络诈骗中的被骗钱款的转移并不是在现实中以实物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以电子数据传输的方式进行转移,被害人处分自己的财产是将通讯电子数据发送给诈骗行为人,一旦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转账就难以撤回操作,可以认定该财产已经脱离了被害人的控制。有学者认为,即使此时财产已被转出,但是由于必须要经过24小时才能到达诈骗犯的银行卡账户中,被害人有足够的时间发觉自己被骗,并采取报警、联系银行解决等紧急措施来冻结收款账户,避免财产最终进入诈骗犯的账户而挽回财产损失,所以该财物并没有完全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被害人转出财物的时点不能作为财物失控的时点[7]。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理由在于:首先,在现实案件中,诈骗行为人与被害人通常会形成信任关系,被害人基于此种信任关系向诈骗行为人转款,因各种因素而能够在转款后及时发现自己被骗的情况并不多。并且,公民对自己所有的财产的支配权应当是在空间上完全的支配,并且在时间上可以随时依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控制占有的状态,公民的此种权利应当排除他人的丝毫限制和侵害。很明显,在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害人一旦将财产转出,即使犯罪人还没有对此财物形成实际上的控制,但被害人此时已不能随时随意支配或处分该财产,只能依赖于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采取措施才有可能追回这些财产,可见被害人对此财产的控制权已经不再完整,且此种状态与犯罪人的诈骗行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次,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帮助行为是依附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存在的,只有帮助行为借助于实行行为促进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才能要求其为危害结果承担责任,以共同犯罪论处。在被害人转款后的24小时内,即使财产没有进入诈骗犯的账户,帮助取款行为也无法对最后的危害结果有所助益,从这一点上说,诈骗的既遂也不能推迟到转款满24小时。因此,应当认定被害人转移财产的时点为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时点,在此时点之前属于“事前”,事前通谋的,帮助取款人才有成立诈骗罪共犯的余地。
(二)“通谋”的内容分析
“通谋”主要指双方的意思联络。当前我国学界对于“通谋”的含义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仅从形式上进行定义,认为只要双方就实行特定犯罪行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联络即可,不需要就此犯罪所有具体问题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另一种是从内容上进行定义,认为只有双方就具体犯罪在犯罪行为、时间地点、分工、犯罪手段、赃物分配等具体问题进行犯意联络并达成共识,才能构成“通谋”[12]。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观点的划分标准是“通谋”内容的详略程度。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构成“通谋”不应当苛求详细的通谋具体内容,只要帮助取款人和诈骗行为人在犯罪既遂之前进行简单的犯意联络,不管是通过语言沟通或眼神等肢体动作交流,也不管是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形成有关犯罪的合意,只要双方能够在心理上、精神上产生鼓励效果,能够让彼此更放心大胆的去实行犯罪行为,提高犯罪实施成功、犯罪目的达到的可能性,就属于“通谋”,各行为人就必须要对最终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网络诈骗犯罪实施于网络空间,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各参与人之间多通过电信网络联系沟通[13],即非接触式沟通,犯意联络的方式和内容也多存在于网络空间,其表现形式为电子数据证据,由于电子证据具有隐蔽性、易被篡改、易毁灭等特征,并且目前电子证据取证方法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取证能力不能及时跟进,电子取证面临不小的挑战,若不能成功取证,就难以证实帮助取款人与诈骗犯罪实行者之间存在通谋,加上网络犯罪发展趋向专业化,成员之间的沟通会采取暗示、暗语等,即使成功收集到电子证据,取款人也有足够的说辞和理由进行抗辩。若是苛求通谋的具体内容,无疑会加大取证和证明的难度,使诈骗犯罪的共犯人逃脱应有的惩罚。有的取款人经验丰富,反侦查能力强,到案后往往辩称自己不知道他人实施的是诈骗行为,或者他们用某种暗号进行沟通,此时若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取款人和诈骗行为人之间存在具体详细的犯意联络,共同犯罪就难以认定。
从网络诈骗的“通谋”的内容看,应包括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取款人与诈骗行为人事前就实施网络诈骗犯罪的全部内容、整个流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通谋,其中当然的涵盖了对事后取款的通谋,关于事后取款具体的手法、网点的选择、时间的选定等问题都是双方通谋的内容的一部分,此时,双方具有共同的犯意,并且不存在垂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处于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分工关系,属于对等型的事前通谋,根据“实质共犯论”④,双方都构成诈骗罪的正犯[14]。第二种是双方在事前仅就事后的取款行为进行通谋,也就是说双方通谋的内容仅有“帮助取款”这一项,并没有对网络诈骗实行犯起到功能支配作用,属于协作型的事前通谋[15],此时取款人与网络诈骗共犯的通谋对于网络诈骗共犯首先起到心理上的帮助作用,事后实际的取款行为又形成了对网络诈骗实行犯物理上的帮助作用,构成诈骗罪的帮助犯。第三种是双方通谋的内容是“帮助取款”情节之外的一个或多个情节,例如,在事前,取款人与网络诈骗犯罪实施者对犯罪手段、犯罪分工、事后分赃等进行了通谋,并没有对事后的取款行为进行商议和规划,犯罪既遂后,由于降低犯罪成本的目的或基于“越少人知道越好”的心理,其中一方去ATM机将诈骗所得支取出来。此种情况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后实际上取款的人与其他网络诈骗正犯不仅就“帮助取款”情节之外的一个或多个情节进行了通谋,还在行动上具体实施了通谋的内容。此时,事后的取款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不能被单独评价。由于实施了取款的人与诈骗正犯存在事前通谋并且实施了具体犯罪行为,最后会以诈骗罪论处。另一种是事后实际上取款的人与其他网络诈骗正犯仅就“帮助取款”情节之外的一个或多个情节进行了通谋,但由于没有时间赋予行动,或由于临时产生了畏惧心理而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具体实施通谋的内容。在此问题上,本文赞同“共同犯罪意思说”⑨,双方形成共同犯意之后成了同心一体,虽然只有一方实施了正犯行为,但双方成立诈骗犯的共犯。可见,无论双方的犯意联络内容是否包括“帮助取款”,都可以成立诈骗罪共犯。
故此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取款人和网络诈骗犯罪实施者在被害人由于受网络诈骗实施者欺骗而处分财产之前,形成简单的犯意联络,取款人就构成诈骗罪。
注 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取款是指取款人到银行网点或通过ATM机支取现金,不包括提供银行卡或微信提现等情况。因此,不讨论是否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问题。
②参见《羊乃博、羊伟定诈骗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鄂0683刑初551号。
③参见《林振坤、林清买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闽0627刑初20号。
④参见《陈军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陕西省丹凤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陕1022刑初92号。
⑤参见《王涛、李振光、任立新等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591刑初16号。
⑥房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自2019年至2021年5月,被告人房石某和房志某经人介绍为“老杨”(身份未查明)取钱并可获得一定的佣金。两被告人使用自己的银行卡以及别人的银行卡帮助“老杨”转账或取现,并按照“老杨”指定的地点将钱送给其指派的人。被告人房石某共计取现近708万元,转账近307万元,非法获利6000元。被告人房志某共计取现80万元,转账约270万元,非法获利1000元。法院判决被告人房石某、房志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分别判决有期徒刑与罚金。参见《房石某、房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山西省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晋1031刑初79号。
⑦2016年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小时后到账,并且在这24小时之内行为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申请撤销转账或者支付。
⑧“实质共犯论”是从实质上理解实行行为,进而肯定共同正犯。
⑨“共同犯罪意思说”认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的共同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即共同意思主体。共同意思主体的活动,至少有一个人实行了犯罪时,所有共谋者都成为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