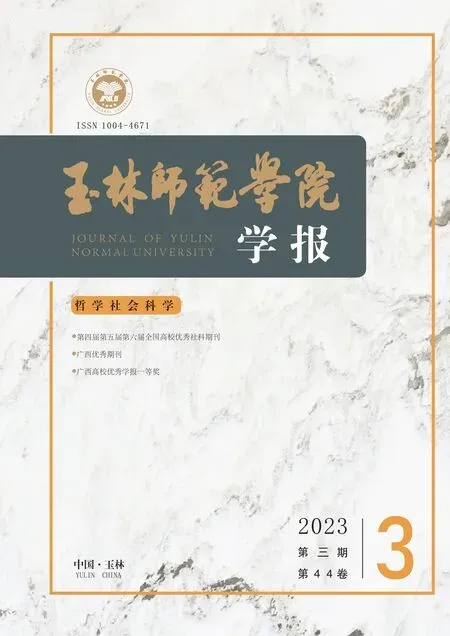向更开阔处突进
——评滕肖澜《心居》
周红兵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一
继2008 年《城里的月光》、2012 年《海上明珠》、2015 年的《乘风》和2019 年《城中之城》之后,滕肖澜于2020年推出了自己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心居》。滕肖澜获得鲁迅文学奖殊荣的是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而在这本《心居》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日子》的影子:外来妹、上海梦、叙事模式以及不入流的个人兴趣。
无论是《心居》中来自安徽的冯晓琴,还是《美丽的日子》中来自江西的姚虹,她们都是上海这座中国最发达城市的外来妹,她们都怀揣着能够在上海扎下根来的“上海梦”,因此,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们同样都巧设心计,嫁给了同样有腿疾但拥有住房的上海男人。当然,她们为“上海梦”做出的“牺牲”,并不是她们两个人的事,更重要的是,她们要用自己的“牺牲”去肩住闸门,好放自己在这段婚姻之前就已经有的孩子进入从而成为新一代上海人。当然,她们两人因此同样都隐藏了自己的上海“前史”:来上海结婚之前都有过一个孩子,姚虹在老家有一个“快十岁”的女儿满月,冯晓琴的弟弟冯大年实际是冯晓琴的儿子,一个是婚内产女,一个是未婚产子,这是她们隐藏在心底深处的最大秘密。两人都很能干,冯晓琴自小就是家乡的能人,妹妹弟弟甚至父母都唯她马首是瞻,婚后更是里外一把好手,将一个复杂的家庭维持得当;姚虹同样精明、能干、坚韧,是刚柔并济能屈能伸的女人。
《心居》和《美丽的日子》都是依托婆媳斗法的叙事框架讲述故事。滕肖澜擅长也偏爱上海日常生活叙事,斗室之内夫妻之间,油盐酱醋家长里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滕肖澜上海日常生活叙事的主旋律。一般来说,擅长历史叙事的长篇小说,总会将目光投注于社会、历史或者现实政治,刀光剑影或者权术智谋,这是男性的角斗场;擅长日常生活叙事的长篇小说,则会将目光投注于家庭、生活和家长里短,而女人之间的斗法,尤其是婆媳、姑嫂或者妯娌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成为一般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也是滕肖澜小说中最重要、最常见的主题。《美丽的日子》里,姚琴要实现自己的上海梦,首当其冲是要搞定“姆妈”甘老太太;《心居》中,冯晓琴婆婆早逝,公公随和,丈夫懦弱,但是丈夫顾磊异卵同胞的姐姐顾清俞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因此,与顾清俞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冯晓琴日常生活的重心之一。无论是“姚虹VS甘老太”,还是“冯晓琴VS顾清俞”,婆媳、姑嫂的日常往还之间,生活中的种种分分合合、家长里短就一一铺陈开来。
当然,《心居》与《美丽的日子》相比,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相同之处就是编织/手办。在《美丽的日子》中,享有这个兴趣的是男主人翁卫兴国,卫兴国最大的爱好便是用竹片纺织些小篮头、小东西什么的,“对别的事不上心,唯独对这个例外,中了魔似的,一弄就是大半天”①本文所引未标明出处的,均来自滕肖澜著《美丽的日子》或《心居》。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滕肖澜:《心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这个被卫老太认为是“搞七捻三的小名堂”却被姚虹发现,在姚虹的开发下,这个小名堂既成为卫兴国在姚虹面前确立男性自尊的艺术,也成为谋取利益的手艺;而在《心居》中,顾士海和冯大年则沿袭了这个爱好,顾士海在黑龙江当知青时,学会了编织,每到心烦意乱时便会拿出竹片编织,在母亲顾老太去世、儿子顾昕入狱之后,更是将此爱好发展成了创收的来路;冯大年不爱读书,唯爱“手办”,在安徽老家时就对读书没了心思,将“一大半精力扑在这上头。自己喜欢,顺便赚点零花钱”,到上海后,既因这项兴趣收获了金钱、澄清了误解,也获得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小老虎、姐姐/母亲冯晓琴的承认,与顾士海成为忘年交。不入法眼的小手段,成为改变人生轨迹的魔法棒。
但是,《心居》毕竟不同于《美丽的日子》,其首要不同之处一望可知,《美丽的日子》是一部十数页、数万字的中篇小说,《心居》是一部长达434页、多达27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度的增加首先意味着人物的增多,《美丽的日子》中除姚虹、甘兴国和甘老太之外,有名有姓有台词有行动的人物就只有姚虹的江西老乡杜琴和卫老太的邻居张阿姨了,其余出现的人物如理发店的师傅、粉摊头的小英、杜琴的孤老房东与丈夫以及张阿姨的那个远亲等,只是隐匿在主要人物背后的“群演”而已。而在《心居》中除了冯晓琴外,还有顾家四代十余口人,第一代顾老太太,第二代的顾氏三兄妹:顾士海、顾士宏和顾士莲,第三代的顾昕、顾磊、顾清俞,第四代小老虎和小毛头,当然,还包括顾士海的妻子苏望娣、顾士莲的丈夫高畅,以及顾昕的妻子葛玥、前女友张曼丽,与顾清俞纠葛不清的施源、展翔等人物,即便是冯晓琴,除了在安徽老家的父母、弟弟外,还有在自己身边的妹妹冯茜茜,这些围绕在顾家周围的人物共同构筑了一道由家庭姻亲关系组成的人物关系图,除此之外,还有老张夫妇、史老板以及顾清俞的闺蜜李安妮、葛玥的父母、舅舅以及她的暗恋者小卢等。这些人物在《心居》中全部都有自己的语言、行动,在他们身上也都可以牵扯出一连串复杂的生活百态。这样粗粗一算,《心居》就比《美丽的日子》多出了十几个人物。
长度的增加,也意味着叙事更为复杂。《美丽的日子》有一主两副三条叙事线索。小说主要写外来妹姚虹嫁入卫家嫁到上海的心愿,从而为自己远在江西上饶的女儿“满月”奠定一个未来的希望,她最大的阻力就是卫老太,因此,姚虹与卫老太之间的交往便成为小说主线,整个小说情节全部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并据此刻划人物;小说还有另外两条副线,一条是姚虹的江西老乡杜琴及其丈夫在上海的遭遇,另外一条则是卫老太隐秘的陈年往事。一主两副的设置使小说于主要人物、事件和次要人物、事件疏密相间,因而更错落有致。《心居》保留了作者关注家庭和女性的一贯本色,冯晓琴是《心居》重点人物,因此,冯晓琴与顾磊的婚姻,冯晓琴对儿子的教育,冯晓琴与公公及公公一大家子人的相处,冯晓琴与顾清俞之间的暗斗,冯晓琴与展翔的合作以及冯晓琴与妹妹冯茜茜、弟弟冯大年的关系是小说重点叙说的内容,冯晓琴在顾家的生存、处世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但在这条线索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其他一些叙事线索,比如顾清俞与展翔、施源之间的情感纠葛,顾昕与葛玥的婚姻,顾士海与妹妹顾士莲的心结,顾士莲、高畅的家庭,还有冯茜茜、冯大年的沪上生活等,总之,顾氏三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爱情婚姻、生老病死同时也是小说关注的对象;当然,除此之外,小说还牵出其他一些人物和事件,比如高畅好友老黄的工伤及善后处理,史老板从足浴按摩到垃圾回收的事业转变等。相对于《美丽的日子》中的一主两支的叙事安排,《心居》则呈多点开花的形式。
二
小说类型复杂多样,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不同的区分,根据小说的叙述范式和容量的差异,一般将小说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到底应该以多少字数为限并无一定之规,“茅盾文学奖”设置的评选规则是版面字数15万字实际字数大概10万字即为长篇小说,以此标准,契诃夫的小说《游猎惨剧》当为中篇,不过在出版的时候却被冠之以“契诃夫唯一的长篇小说”的名义。可见,长度从来就不是衡量艺术的标准,“空间上经验的致密感,时间上经历的漫长感,都是长篇小说的基本要求”。①张柠:《今天的长篇小说应该写多长》,《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美丽的日子》以其对“两代女性情感与生活”的细致刻画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②《美丽的日子》获奖辞:“《美丽的日子》,叙述沉着,结构精巧,细致刻画两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展现了普通女性追求婚姻幸福的执著梦想,她们的苦涩酸楚、她们的缜密机心、她们的笨拙和坚韧。这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美与善、同情与爱的珍重表达。名实、显隐、城乡、进出等细节的对照描写,从独特的角度生动表现了中国式的家庭观念和婚姻伦理。”,在《心居》中,作者同样用心刻画女性,婆媳、姑嫂争斗,妯娌不和甚至骂架,生儿育女,人情来往,家庭变迁和婚姻无常,仍然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桥段,但随着长度的增加,小说也将视野拓宽,时间拉长,小说叙事空间也突进到更为开阔的社会领域,从而获得了时间上的漫长感和空间上经验的致密感。
顾士海的黑龙江知青经历、顾士莲和高畅的结合、施源家庭的衰败和他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展翔的发家史、老张夫妇俩不足为外人道的丁克,都将小说时间跨度拉长,叙事时间拉长的同时,个体命运的起承转合、人生百态、跌宕起伏及亲情的兜兜转转,在小说文本中都被纳入历史的起承转合与柳暗花明中,个人从知青到回城再到今天的人生历史折射出上海的变化和新中国的发展,历史的纵深感便在不同人物的命运史中呼之欲出。顾士海与施源父母的知青生涯,折射出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史,顾士莲与高畅及其同事老黄的个人经历蕴含了改革开放史,展翔、三千金一家及史胖子还有冯茜茜的个人发迹史,浸透的是上海这座“魔都”令人难以置信的“膨胀史”,相对于过去仅仅将视野收拢在个体或者某些家庭这些基本单位的作品而言,《心居》在人物背景、个人命运与历史变迁之间的处理更显示出滕肖澜近来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向,即作者更能进一步掌握现实主义创作的真谛,不仅写出细节的真实,而且还通过人物个体命运的选择和变化来折射出历史的变迁。
如果说美国梦是淘金梦、中国梦是富强梦的话,那么外来妹冯晓琴、冯茜茜两姐妹的“上海梦”首先便是安居梦。无论是冯晓琴、冯茜茜,或者是姚虹还是滕肖澜笔下其他人物,能够在上海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居所,正是她们种种行动的动力:在《美丽的日子》中,姚虹选择卫兴国这个残疾大龄未婚“青年”,卫兴国在上海有房——尽管只是一个亭子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心居》中,冯晓琴嫁给了同样有腿疾但有房的上海男人顾磊;冯茜茜不惜利用女人身份周旋在顾昕及其他客户之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想拥有一套上海住房;顾士莲与其大哥顾士海之间的微妙关系,其源头就在于当初让出的一套房子;即便是顾清俞这样土生土长的上海白领,也需要在住房问题上通过假结婚将利益最大化,她的假结婚对象施源之所以委曲求全甘愿被人骂“卖身”与顾清俞假结婚,相当程度上正是为了让自己的母亲能够拥有一个宽敞明亮的新房;顾家周六的例行聚餐,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买房卖房;葛玥家庭的变化直观地体现在房屋的变化上,葛父降职前,再大的房子也能够买下来住,一旦降职,原先几套房子就只剩下一套自住的两居室,房子与官场浮沉紧密相关;被顾士宏视为“暴发户”、被冯晓琴一口一声叫着“爷叔”的展翔之所以能够活得理直气壮,能够不计成本听从冯晓琴的建议创建“不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房子托底,他不害怕折腾,大不了卖套房就什么又都有了;而顾清俞的闺蜜李安妮第一段婚姻之所以失败,“说到底也与房子有关”。孟子说,应“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①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页。,“产”是中国人的普遍追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住有所居”更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房子不仅是《老娘舅》《家有好大事》或者《金牌调解》这样电视节目的主打内容,也创造了“蜗居”“蚁族”“房改”“房票”和“拆迁户”等这样的时代词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每天上演着买房卖房的戏码。小说以安居为主题,已经触及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话题。
1928年秋,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曾经说:“一个女人要想写作,必须拥有两样东西,钱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②〔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周颖琪译:《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时至今日,我们对空间的追求从未改变,冯晓琴、冯茜茜或者姚虹,她们同样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产证有我的名字,就够了”,“就算痴心妄想,也要试一试”,尽管她们要拥有住房并不是为了能够安静地写作,但这个“痴心妄想”也蕴含着女性对独立与尊严的理解,寄寓着她们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懑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滕肖澜关注的不是住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但她捕捉的是中国女性对于独立生活的向往,是普通百姓平凡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心居》与《美丽的日子》相比,在关注女性的情感与生活之上,更关注女性对独立与尊严的感性理解与现实追求,更关注围绕在这些女性身边的人群对安居即实际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因此,小说在以冯晓琴、冯茜茜、顾清俞、葛玥和其他顾氏家庭成员为对象的同时,也将视野扩展到小说中其他人群,楼下的三千金一家,展翔与“不晚”的从无到有,史胖子的洗脚屋和垃圾回收项目、刘姐的心眼与算计、打工人女儿的优异成绩,顾昕岳父的官场浮沉、顾士宏作为业委会主任在小区里的遭遇等,也在小说中逐一呈现,这样作者就将时代洪流、当代要事、上海难题择要收入,叙事视野拓宽,人物已经溢出婚姻、家庭,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加入,在增加了叙事密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叙事厚度。《心居》实际已经将问题分成两个部分:“心”被“居”所制,同时,“居”又为“心”所动。滕肖澜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写作,她是温情现实主义写作,她看到了红尘俗世的艰辛与追求,他们的哀乐苦痛系于一产,这是普通中国人的追求,也是普通中国人的当世悲喜剧。这样,滕肖澜就将自己的写作从家庭生活的家长里短、婆媳斗法的琐碎中超拔出来,因而《心居》拓宽了滕肖澜小说创作的美学深度与广度。
三
当然,小说的长度、广度和厚度的增加,并没有改变滕肖澜日常生活叙事的另一道底色:温度。温度是作家对芸芸众生的态度,这是基于同情的理解,或者说这是基于理解的同情,是对日常生活鸡零狗碎的留心,是对人生百态世间冷暖的体察,是对普通人家生老病死的关怀,作家的悲悯情怀便完全在温情的叙事中流出。
小说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纳入自己的写作中。小说开始于聚餐,顾家三兄妹三个大家庭十几口人,每周六在顾士宏家雷打不动地聚餐,“民以食为天”,吃历来是中国人的大事,吃既是为了满足人生命存活的必须,又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层面,吃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气息,当传统社会逐渐发展之后,当代社会也逐渐改变了四世同堂围席而坐的吃饭方式,但是顾家却以聚餐的形式维系了传统,通过对聚餐中吃食的准备和餐桌上谈话的细致描绘,作者为读者呈现了上海这座最现代化城市的中国式家庭中最传统的一面,滕肖澜将每场家庭聚餐的家常菜式描绘得活色生香③戴瑶琴:《滕肖澜长篇小说〈心居〉:海派的腔调和格调》,《文艺报》2020年12月14日,第2版。,老百姓的一日三餐中,既流淌着岁月,又浸润着亲情,无论是懦弱的顾磊,还是独立的顾清俞,无论是心直嘴快的苏招娣,还是面淡心冷的顾昕,无论是90多岁的顾老太太,还是只有几岁的小老虎,当他们围绕在餐桌边的时候,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就在字里行间向着读者扑面而来。
“居”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民有所居、居无定所、安居乐业、离群索居、深居简出、饮食起居等等这些词语无不表明“居”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小说以“居”为题,无论是家庭聚餐、日常交往、婚丧嫁娶或是职场沉浮,房子始终牵动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房子催生了欲望和问题,冯茜茜因为想要一间写着自己名字的上海房子而游走在灰色地带,施源因为房子破败不惜“卖身”假结婚,葛父因为房子被降职处理,李安妮因为房子选择结束第一段婚姻,“三千金”一家因为房子问题与展翔打架,展翔因为房子太多而被人视为暴发户,顾士莲与顾士海兄妹之间因为房子问题横亘着一道心坎……但房同样也展现了人情催生了情谊,苏招娣因为装修房子与顾士莲姑嫂情深,顾士莲当年自愿让套房给大哥顾士海当然是出于兄妹之情,展翔为了爱情、为了顾清俞可以牺牲自己的房产,冯晓琴极力劝说展翔成功创建“不晚”,为城市老年人创造了“老有所居”,尤其是顶住压力收容老黄,不仅有家庭情谊,更有社会关怀。
小说之有温度还在于小说对文本中人物命运似乎不忍痛下杀手,笃定地给予人物以“团圆”式的安排。《美丽的日子》中,姚老太太对姚虹的一切手段洞若观火,但她终究选择了和解,这实在是蕴含了对女性这个性别生存不易的体验与同情;同样,在《心居》中也有本可以牵引出无数枝节的叙事线头,但都被作者以温情的、善意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处理了,顾磊去世后,顾士宏对家庭离散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冯晓琴并没有与他们分家产,而是继续留在这个家里守护着,一个本要碎碎的家庭却意外地保留了;施源终究还是获得了来自海外的遗产,这笔境外横财似乎是作者对施源个人及其历经波折已然破碎的知识分子家庭的补偿,这个补偿既是作者对文本中人物的抚慰,也是作者对读者的抚慰;李安妮经历了海外婚姻之后,还是与第一任丈夫破镜重圆,这是一个历经千山万水之后的再组合,尽管双方都带着各自的后代让人看上去那么奇怪,但毕竟尘埃落定;顾士海竟然成为家庭群中最活跃的分子,完全出乎苏望娣意料之外,收获了平静的心境;葛玥怀了二胎,开始为丈夫奔走,当“一向孱弱”的她在昔日的追求者小卢那唱起《我家有个小九妹》或者《桑园访妻》的时候,“那瞬,这朵温室里的花朵,终于迸发出连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力量”①滕肖澜:《小日子有大味道》,《文艺报》2020年12月14日,第2版。,她真正走向坚强、成熟,一股暖流自然也滋润了读者心田。
滕肖澜似乎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对自己文本中的人物痛下杀手、狠手,将人生中残酷真相的帷幕掀开,将人生中的美好毁灭给读者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小说尽管有时候已经揭开了冰山的一角,但却经常是适可而止,最终以友善的方式结束。《心居》的所有情节中,最有可能牵出更大叙事星团的是冯晓琴与冯大年的关系。冯晓琴少年产子,此后离开家乡安徽到上海谋生,嫁给了顾磊之后,又生下儿子小老虎,但是,这段年少不更事的经历,除了冯晓琴与她老实巴交的父母知道外,其他所有人均不知情,顾清俞只是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才将冯晓琴的一切调查得底朝天,也正因为顾清俞对此事的知晓以及知晓后的不便公开,才处处提防着冯晓琴,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顾清俞在与冯晓琴的正面交锋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个惊天秘密抛出,如果不加控制地任由这个晴天霹雳释放的话,必定会使得整个顾家鸡犬不宁,但是,这却是一记闷雷,其意不在使得整个家庭鸡犬不宁,更是意在敲打冯晓琴回归生活正途,不要妄作他想。对于顾清俞而言,她已经达到了敲打的目的,而对于冯晓琴来说,这个晴天霹雳何尝不是一次释放与解脱,压抑在心底多年的秘密一旦被释放,反而能够在心里坦然正视这个秘密,这无异于是一次人性的释放和自由的延展,此后,她向张妈妈的倾诉是揭开压抑后的转移,而将冯大年接到上海,安排其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及对他的调教,更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对于读者而言,我们不必再次见证一次家庭的变故,同时,也会在接下来对冯大年的交代中完成对冯晓琴的同情与和解。这是作者的处理之道,在滕肖澜那里,很多情节从叙事上来说,都可能牵扯到一个个更大的叙事星团中去,牵扯出另外一些发展的可能性,但作者有节制地、熟练地掌控了叙事节奏,并且以团圆、友善的方式完成了叙事的闭合,既没有让叙事溢出作者的叙事意图,又没有给读者以牵强的阅读印象,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些以残酷开头但以温柔结束的人物命运的处理中触摸到作者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态度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