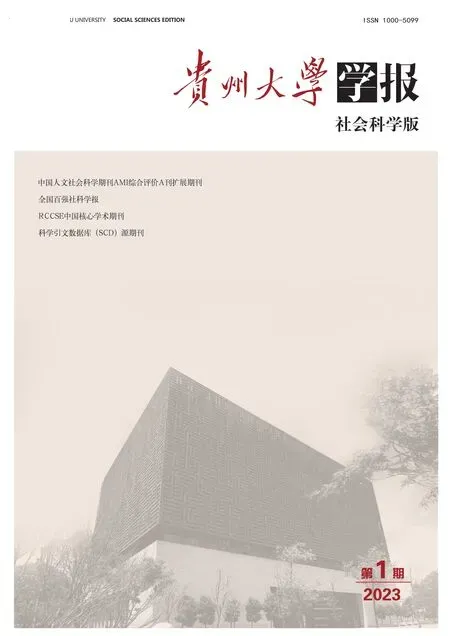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学派
倪梁康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胡塞尔从哥廷根来到弗莱堡后的第二年,布伦塔诺于1917年3月17日在瑞士去世。胡塞尔最后一次拜访布伦塔诺是在十年前。当时,布伦塔诺还住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于1916年再次迁居至瑞士苏黎世,一年后便在那里病逝了。胡塞尔于1919年发表了他的纪念文章《回忆弗兰茨·布伦塔诺》。这篇文章刊登在由布伦塔诺的学生和遗稿管理者奥斯卡·克劳斯撰写的论述布伦塔诺之生平与著作的专著中[1]153-167。但是,这很有可能是胡塞尔根据克劳斯的一个请求而写下了此文。很遗憾,胡塞尔与克劳斯的通信并未被保存下来。同时,刊登在该论著中的另一篇回忆文章出自布伦塔诺的另一位弟子,也是胡塞尔的任教资格论文指导老师卡尔·施通普夫之手。如果不算后来离开学界进入政界的托马斯·马塞里克,那么施通普夫应该是最早与胡塞尔有师生关系和密切思想联系的布伦塔诺学派成员了(1)关于胡塞尔与施通普夫的关系,笔者在即将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反思的使命:第一卷:胡塞尔的生平与著述》的第一幕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全书按胡塞尔的各个时期分为五幕,正文所提各幕均指该书各个时期的相关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胡塞尔本人此前能够获得弗莱堡大学的教职也受益于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的影响。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在1916年聘任胡塞尔为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席教授所给出的理由中,除了胡塞尔本人可以“视作当今最重要的活着的思想家之一和德国最大的严格哲学学派的首领”以外,“他的学术道路的形成得到透彻的指明——‘来自弗里茨·布伦塔诺的业已分布很广的学派’”[2]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
如前所述,胡塞尔自己一再承认,他是由布伦塔诺的学生马塞里克引上了哲学道路,如若没有布伦塔诺,他连一个字的哲学都写不出来,而且他的任教资格论文,最终也是在布伦塔诺的另一位学生施通普夫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与布伦塔诺的其他学生马尔梯、迈农、霍夫勒、特瓦尔多夫斯基、贝格曼、乌悌茨、克劳斯等人都有思想联系,且他们在思想倾向、思维风格、立场方法等方面或多或少带有共同的布伦塔诺印记。这也使得人们有理由为他们——包括胡塞尔在内——贴上布伦塔诺学派的标签,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愿意。
一、布伦塔诺学派
所谓“布伦塔诺学派”,主要是指由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1938—1917)以及他的学生所代表的一个复杂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传统。它由布伦塔诺最亲近和最重要的学生来体现,但也包容了其他较为疏远的学生。目前,被确定的学生通常有以下六位作为代表,他们都可以被视作“20世纪哲学的伟大人物”[3][4]124:
第一位是安通·马尔梯(Anton Marty,1847—1914):布拉格大学教授,语言哲学家、本体论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最忠实的学生;
第二位是卡尔·施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维尔茨堡大学、布拉格大学、哈勒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完形心理学的共同缔造者;
第三位是阿列克休斯·迈农(Alexius Meinong,1853—1920):格拉茨大学教授,对象理论的创始人;
第四位是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布拉格大学教授,完形心理学的共同缔造者;
第五位是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的教授,现象学的创始人;
第六位是卡兹米尔茨·特瓦尔多夫斯基(Kazimierz Twardowski,1866—1938),利沃夫大学和华沙大学的教授,利沃夫—华沙学派的创始人。
除此之外,布伦塔诺的较为疏远的学生以及听众中还包括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教育哲学家和审美学家阿洛伊斯·霍夫勒(Alois Höfler)、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塞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人智学创始人鲁道夫·施坦纳(Rudolf Steiner)等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这里的统计当然是不完全的,而且也不一定确当。无论如何,就笔者在此讨论的布伦塔诺学派而言,其成员中有几位(马尔梯、施通普夫、迈农、马塞里克)已经在笔者即将出版的《反思的使命》第一卷或第二卷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介绍(2)例如:关于胡塞尔与布伦塔诺的私人关系与思想联系,笔者在该书第二卷的第一章“胡塞尔与布伦塔诺:现象学与心理学”中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外,在笔者的《自识与反思》[5]第十九讲“布伦塔诺:心理现象的‘内感知’与‘内观察’”中也有相关的讨论。而关于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学派的关系,笔者在该卷的第八章“胡塞尔与马尔梯:现象学与语言哲学”和第九章“胡塞尔与迈农:现象学与对象理论和完形心理学”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方面更为详细的论述还可以参见:罗林格(Robin D.Rollinger)的《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学派中的地位》(Husserl’s Position in the School of Brentano)[6]。。
在这里,笔者还要补加几位与胡塞尔有关的布伦塔诺学派成员的介绍。他们的著述文章和思想发展或多或少地受到胡塞尔的影响,同样也或强或弱的影响过胡塞尔。
二、奥斯卡·克劳斯
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1872—1942)在上述统计中并未被提及,即在布伦塔诺研究界看来还不算是布伦塔诺的最重要学生。严格说来,克劳斯连布伦塔诺的听众都不算,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他的学生,遑论最重要的学生。但他在布拉格大学学习期间是布伦塔诺大弟子马尔梯的学生,被他引入布伦塔诺哲学中,后来也是其布拉格大学之讲席的继承人,因而可以算是布伦塔诺的徒孙。他为布伦塔诺学派所做的厥功至伟的贡献是对布伦塔诺的思想遗产的管理以及对其遗稿的编辑出版,类似于后来范·布雷达(H.Van Breda)对胡塞尔的思想遗产所做的贡献。
克劳斯与布伦塔诺的第一次相会是在1893年(3)布伦塔诺在1898年5月11日从佛罗伦萨寄给胡塞尔的信中说:“一位布拉格的大学生现在在我这里,一位有才华的马尔梯的学生,他给我带来推动我工作的动力。”(Karl Schuhmann (Hrsg.),Briefwechsel,I-X,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此文献在接下来的正文中简称为“Brief.I,S.18”。)舒曼认为这位大学生是指克劳斯。但从信中,我们还看不出克劳斯是否在佛罗伦萨才初识布伦塔诺。,即在1895年,布伦塔诺从维也纳大学退休的两年前,比胡塞尔认识布伦塔诺的时间晚了近十年。克劳斯于189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以《论价值理论:一项边沁的研究》为题完成了哲学系的任教资格考试。1907年3月15日,他还去佛罗伦萨拜访过布伦塔诺。后者在给施通普夫的信中也表明了自己对克劳斯的推荐意向:“今天有克劳斯博士来访。您认识这个布拉格的有才华、有个性的勤奋年轻讲师。最近他因为一篇就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撰写的出色论文而做出了贡献。我的弟弟以及法学家李斯特对他都有很好的评价。与胡塞尔一样,他并不执着于他的犹太血统,而且他足够明智,不会出于幼稚的任性而使其发展为对庄重高贵之兴趣的障碍。他只需尽可能地防止遭人误解。”(4)布伦塔诺在这里提到的他的弟弟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著名的经济历史社会学家;而他所说的法学家“李斯特”应当是指奥地利裔的德国法学家弗兰茨·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时任柏林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爱德华·李斯特(Eduard von Liszt,1817—1879)是他的父亲,曾任奥地利国家总检察长;而与他同名的著名音乐家弗兰茨·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811—1886)是他的伯父,也是他的教父。[7]83f4
1911年,克劳斯获得布拉格大学副教授的位置。1914年马尔梯去世,克劳斯于两年后接任其讲席教授的职位,并于这年(1916年)与另一位马尔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卡斯悌尔(Alfred Kastil)一同去苏黎世访问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移居到那里的布伦塔诺。他们两人后来自1917年起开始筹划对这年去世的布伦塔诺的遗稿的整理和编辑。从1922年开始就已经有一系列的布伦塔诺遗著得以出版,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克劳斯编辑出版的布伦塔诺的代表作《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三卷本(1924、1925、1928)以及《真理与明见》(1930)等(5)卡斯悌尔也从1922年起编辑出版了多部布伦塔诺遗著,如《耶稣的学说及其恒久的意义》(1922)、《论上帝的此在》(1925)、《范畴理论》(1933),等等。此项工作后来由迈耶-希勒伯兰特(Franziska Mayer-Hillebrand,1885—1978)等人接手,将布伦塔诺的重要遗稿逐步编辑出版。目前,随着布伦塔诺遗稿和新的研究文献的出版,布伦塔诺学派的研究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布伦塔诺曾任教的学校)、格拉茨大学(迈农曾任教的学校)、德国维尔茨堡(布伦塔诺曾任教的学校)和捷克布拉格大学(马尔梯曾任教的学校)都形成了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研究的传统,而且在多地建立了布伦塔诺文献馆。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可谓是层出不穷。。
时至1931年,克劳斯在布伦塔诺的另一位学生、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塞里克的经费支持下成立了布拉格布伦塔诺学会。1934年,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布拉格召开,胡塞尔受邀参会,但并未打算出席,他为此专门致函大会主席莱德(Emanuel Rádl),并写下著名的“布拉格信函”,它可以说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的初稿。当时,克劳斯正担任世界哲学大会的副主席。1939年,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克劳斯遭到逮捕,入狱六周后出狱并成功逃往英国。1942年,他因患癌症在牛津去世。
克劳斯与胡塞尔的关系并不密切,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没有被保留下来。尽管在胡塞尔的书信中对克劳斯时有提及,但从未对其做出过评论。1917年,布伦塔诺去世后,克劳斯撰写了一部题为《弗兰茨·布伦塔诺:关于他的生活与他的学说的认识》[1]153-167的小册子,其中刊载了施通普夫和胡塞尔回忆布伦塔诺的文章,很可能是他们应克劳斯之邀而撰写的。由于当时马尔梯作为布伦塔诺的大弟子已于1914年去世,因而最应当撰写纪念文章的当然是施通普夫和胡塞尔。而迈农、埃伦费尔斯、霍夫勒等为何缺席这个由克劳斯主导的纪念活动,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此时克劳斯对待师长胡塞尔的态度应当还是较为尊重的。只是在七年之后,克劳斯才在他为布伦塔诺编辑出版的代表作《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撰写的长篇“编者引论”中严辞或“恶意”批评了迈农与胡塞尔,将迈农的“对象理论”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称作“布伦塔诺观点的根本对立面”(6)克劳斯的批评可以参见克劳斯(Oskar Kraus)的“编者引论”(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8-9]。,以至于胡塞尔的太太马尔维娜(Malvine Husserl)在其回忆录中禁不住要批评克劳斯“在其布伦塔诺正统派中肯定比教皇本人还要教皇”(7)参见马尔维娜·胡塞尔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平素描》[10]。马尔维娜在此处加引号地提到胡塞尔的“堕落”,应当是出自克劳斯的批评话语,但应当是在其他地方,而非出自他的这两篇引论。。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克劳斯对待迈农和胡塞尔的看法的确来自“教皇”布伦塔诺本人,后者在1916年11月10日致施通普夫的信中也曾批评过“经院哲学化的迈农—胡塞尔谬误”[7]153。
实际上,克劳斯的批评含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一方面一再地证明迈农和胡塞尔仍然停留在老师已经达到的层面上,另一方面又重复地批评他们没有坚持老师的观点。但是,胡塞尔本人似乎对克劳斯的批评从未做过回应,可能也从未打算回应。或许是他意识到在自己与布伦塔诺的基本哲学立场之间确有隔阂,且无法消除,因而不能不做叛逆之举。他在1919年的回忆文章中便感叹自己“并不善于始终做他的学派的成员”[11]346,而该回忆录的全集版编者奈农(Th.Nenon)和塞普(H.R.Sepp)曾概括说:“尽管有相互理解的证明,尽管有胡塞尔将自己哲学立场向布伦塔诺靠拢的努力,在实事上,也在胡塞尔1907年于佛罗伦萨访问布伦塔诺期间的多次对话中,都没有产生任何的亲近,所以胡塞尔强调‘某种疏远,即便不是与我老师的某种私人关系上的生分’,这种疏远‘使一种科学方面的接触变得如此艰难’。”(8)奈农、塞普的“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的《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12]。而且这里需要留意:胡塞尔在写回忆布伦塔诺的文章时(1919年)还没有读到克劳斯的那两篇令马尔维娜产生反感的“编者引论”,它们在1924年和1930年才被公开发表出来。他在回忆录中表达的这些感受,后来只是通过克劳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了而已。无论如何,胡塞尔在这次访问中感受到的“疏远”是真实不妄的,甚至连他否认的“私人关系上的生分”其实也已存在,至少就布伦塔诺那方面而言是如此。这一点在接下来讨论布伦塔诺与胡戈·贝格曼的通信时会得到清楚地表明。而马尔维娜所说的克劳斯“肯定比教皇本人还要教皇”,事实上最终也已表明是不确切的。
三、阿列克休斯·迈农
阿列克休斯·迈农与胡塞尔同为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与他之间的通信没有被全部保存下来,但在《胡塞尔书信集》中还是留有十多封书信往来。迈农可以算是与胡塞尔交往最多的几位布伦塔诺学派成员之一。(其余的几位是在第一幕中提到的马塞里克和在第二幕中提到的施通普夫,以及在第四幕中将会涉及的马尔梯。)
在此前引入马尔梯学生克劳斯对迈农与胡塞尔的批评中,迈农与胡塞尔都被视作布伦塔诺的叛逆者。这里存在一个复杂的三边关系:在马尔悌与迈农之间有学术方面的论争,它通过克劳斯体现出来,而在马尔悌与胡塞尔之间则虽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却并无正面的冲突,但也遭到克劳斯的“恶意”(马尔维娜语)攻击。最后,在胡塞尔与迈农之间有较多的争论发生,它们不仅涉及胡塞尔现象学与迈农的对象理论以及埃伦菲尔茨(Chr.von Ehrenfels)的完形心理学各自观点的解释说明,也关系着他们之间的差异辨析与问题讨论,最终还涉及迈农与胡塞尔各自研究的思想原创性问题,而后一个问题超出了一般学术争论的范围,它应当是导致胡塞尔与迈农关系决裂的主要原因(9)对此可以参见上述《反思的生命》第二卷第九章“胡塞尔与迈农:现象学与对象理论和完形心理学”。。
胡塞尔与迈农的联系在《逻辑研究》之前十分融洽,在许多方面有良好的交流与互动。在《逻辑研究》中,迈农也是胡塞尔考虑、引述和讨论最多的对手,连同布伦塔诺、施通普夫、马尔梯,以及其他一些被视作布伦塔诺学派的心理学家。
严重的分歧在此后的1902—1904年之间便已产生。从遗留下来的几封通信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然充满了怀疑与争议,虽然不失客套与恭敬。也正是在这一年,胡塞尔与迈农之间的通信交往结束了。起因看起来是迈农将自己的长篇论文《关于对象理论》的抽印本寄给了胡塞尔[13]。随后,胡塞尔做了回复和致谢。直至迈农于1920年去世的十六年间,两人之间没有再发生任何有案可查的思想交流了。
不过,在胡塞尔那里可以查到他私下对自己所受迈农影响的反思:在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文库中保存着一本黑色笔记本(编号:X x 5),瓦尔特·比梅尔(W.Biemel)于20世纪50年代将它编辑发表。他在编者引论中说明:“胡塞尔曾在其中摘录过对他留有印象的书,记下重要的著作,并于1906—1908年的关键年代也做过一些私人的、类似日记的札记。”[14][15]438-440笔记开始于1906年9月25日,而且开始于迈农。在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出胡塞尔在此期间正在十分仔细地思考迈农以及其他人对自己思想发展的影响:“自本月初以来我就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我是否做得对呢?我首先研究了迈农《论假设》的书[16],同时我不得不一再地看我自己的旧作并且思考到它们之中去。”[14][15]438-440
在回顾自己从《算术哲学》到《逻辑研究》的思想历程,以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自己的可能影响之后,胡塞尔再次返回到迈农这里:“可惜我无法再判断,迈农的关系理论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于1890年前后就已经读过它。但直至1891年与迈农的通信才导致了对它的更为仔细的研究。但很难设想,除了几个有限的思想以外,它还对我在方法上提供过什么。”[14][15]438-440而后他得出最终的结论:“迈农的书已经无法在表象和判断的研究方面为我提供如此多的东西了,除了一个巨大的兴奋以外,每当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人在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多年来操心的问题时,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我在这部书中仅仅发现一个重要的思想,它是我在《逻辑研究》中没有说出的,尽管我在起草过程中已经有了它并思考过它,但却未敢接受它:将判断向‘单纯表象’的变异转用于愿望和所有其他行为上,我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标明日期的页张(1894年),在那儿我恰好和迈农的立场一致。但当然,我看到了迈农没有看到的巨大困难,而它们阻止我得出结论。迈农的表象概念是完全不明智的,完全不可理解的。显而易见,与迈农的分歧是有必要的并且是无法避免的,撇开这一点不论:总有一天会证明,这些研究领域与最本质认识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14][15]438-440
接下来,胡塞尔记录下自己与迈农之间关系的总体印象:“我们像是两个在同一个黑暗的局部世界中旅行的人。我们当然常常看到同一个东西并且对它进行描述,但与我们不同的领悟力相符合,这些描述也含有多重的差异。”[15]440-441
从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冷静、客观,并未掺杂负面的怨愤和不满的情绪。由此,迈农的这一道坎此时似乎已经被他越过。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后来关于胡塞尔的回忆录中,许多回忆者都提及,胡塞尔在接下来的哥廷根时期和弗莱堡时期都仍然表达过对迈农的抱怨和不满。例如:当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于1913年来到哥廷根时,他已经注意到:“当我的哥廷根岁月开始之时,胡塞尔还没有完全从那种‘优先权之争’(Prioritätenstreit)——尤其是与迈农的争论——的狭隘中走出。”[17]我们还可以从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的同年回忆中得到另一个证明:“当我有一次谈到迈农时,胡塞尔真的愠怒起来。”[18]最后,我们还可以在吉布森(Boyce Gibson)的1928年日记中读到他所记录的胡塞尔在那个时期对迈农的表态以及他对迈农与胡塞尔关系的一种理解,从而为后人了解其中的因缘聚合提供了一个视角:“迈农和胡塞尔都是布伦塔诺的学生。他们曾经关系很好。但《逻辑研究》出版后,迈农很不满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并对此发表了颇具敌意的文章。自此,他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1900年之后,迈农开始写关于‘对象理论’的东西,胡塞尔认为这反映了自己在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在《逻辑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他不确定迈农是否读过此书,但认为他读过的可能性非常大。胡塞尔不认可精神财产这类东西。他慷慨地任由其所有学生从他的思想中充分获益(参看他对海林作品的批评——海林是他在哥廷根的学生,他教了他两年。这个学生比较偏激,但执着且善于表达。胡塞尔曾建议我看看他的书),但在这里他却情绪高昂,强烈反对任何人攫取他自己(胡塞尔)的思想,并说出‘我是一个全新观念秩序的奠基者’之类的话,而且认为自始至终,迈农与其说是原创者,不如说是借用者。”[19]
很显然,胡塞尔仍未从他的怨愤中解脱出来。此时,迈农已经去世了八年。这种情况在胡塞尔那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或许我们可以说,不仅在哥廷根时期,而且很可能在其一生中,能使胡塞尔最耿耿于怀的人便是迈农了。
四、卡兹米尔·特瓦尔多夫斯基
在前面论述英加尔登(Roman Ingarden)时已经涉及布伦塔诺的另一位学生卡兹米尔·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出生在维也纳,并于1885—1889年期间在维也纳大学随布伦塔诺和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n)学习。胡塞尔在维也纳随布伦塔诺学习的时间与此有部分重叠:1884—1885年冬季学期和1885—1886年冬季学期。但没有资料表明他们两人在这个时期就已经相互认识。1891年,特瓦尔多夫斯基以一篇题为《观念与知觉》的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后于1894年以《关于表象的内容与对象的学说》为题完成了任教资格考试。这两部论著后来都正式发表[20-21]。这也是他一生发表的仅有两部专著。在维也纳担任一年的讲师之后,他在利沃夫大学获得教授职位。他被视作波兰现代科学哲学的开创者,也被公认为是“利沃夫—华沙学派”的缔造者。这个学派既是哲学流派,也是逻辑学流派或数学流派。无论如何,布伦塔诺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理想后来通过特瓦尔多夫斯基而在他的一批后来成为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波兰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的确应当说,“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于波兰文化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4]9;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原创性思想家,而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和组织者”[22]。
看起来,胡塞尔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私人联系主要是因为英加尔登的缘故而建立起来的。前面在论述英加尔登时,笔者曾引述过他在回忆胡塞尔的文章中对从利沃夫特瓦尔多夫斯基那里转到哥廷根胡塞尔这里的学习生涯(过渡历程)。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培养了许多学生,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部分以卢卡西维茨(Janukasiewicz)为代表的学生处在B.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和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经验心理学的影响下;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处在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的影响下。英加尔登之所以到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是因为他相信胡塞尔的观点:哲学应当承担本质研究的任务[23]170-171。
按英加尔登的说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与胡塞尔有过多次会面[23]190。但他们之间仅有两次书信往来存世,时间是在1928年,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共同学生英加尔登后来在波兰的工作与待遇问题,并未涉及学术和思想方面的交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信中读到,胡塞尔曾于1927年委托英加尔登,将他于1896年(几近三十年前)为特瓦尔多夫斯基1894年发表的任教资格论文《关于表象的内容和对象的学说》所撰写的一篇书评(但后因种种原因未发表)的副本转交给特瓦尔多夫斯基。后者在回信中特别致谢并提道:“这个书评在历经许多年后也未失去其价值。”(Brief.I,183.)
事实上,胡塞尔的书评后来以另一种形式在《逻辑研究》中得到了表达。他在第二研究中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普遍对象”和“普遍表象”的理解,即“普遍表象的对象是被我们所表象,但它并不实存”[21]106的观点,同时维护柏拉图(Plato)和鲍尔查诺(Bernhard Bolzano)的观念论立场(Hua XIX/1,A 134/B1 124.)。在这里,胡塞尔的确是站在了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的对立面。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则明确地与布伦塔诺站在一边,将普遍表象视作符号表象一样的“非本真表象”。在这一点上,特瓦尔多夫斯基应当属于马尔维娜所说的“布伦塔诺正统派”。
特瓦尔多夫斯基去世于1938年2月11日。此后不到两个月,胡塞尔也于4月8日去世。英加尔登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追悼会上得知了胡塞尔逝世的消息[23]190。
五、安通·马尔梯
不过真正的“布伦塔诺正统派”是由安通·马尔梯来代表的。他是布伦塔诺的大弟子,比胡塞尔的任教资格导师施通普夫还要年长一岁。他于1868—1870年间在维尔茨堡随布伦塔诺学习,1869年便获得神职和教职。但他与布伦塔诺一样,在1872年就放弃了神职,来到哥廷根随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学习,并于1875年完成了博士学业,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语言起源理论的批判》,该论文于同年出版,总计60页,它的完整版也在同年出版,题为《论语言的起源》,总计150页[24-25]。博士毕业后,他在切尔诺维茨(今属乌克兰)大学任教五年,而后于1880年受聘到布拉格德语大学,此后一直在这里任教,直至1914年去世。他通过他和他学生的工作,使布拉格在几十年里保持了“布伦塔诺哲学”的中心地位。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布伦塔诺正统派”称作“布拉格学派”(Prager Schule)或“学圈” (Kreis),与迈农所代表的、可称作“布伦塔诺非正统派”的“格拉茨学派”(Grazer Schule)相对应,或者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相呼应。
马尔梯同样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付诸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布伦塔诺弟子,主要是在第一研究和第四研究中,而且主要涉及马尔梯的语言哲学和含义理论。1910年,胡塞尔还为马尔梯《对普遍语法基础与语言哲学的研究》(第一卷,哈勒,1908年)[26]撰写了书评,并在书评的开篇处对马尔梯的工作领域和思想风格以及他与老师布伦塔诺的关系做了一个出色的概括评价,几乎可以视作对四年后才病逝的马尔梯的预先盖棺论定:“1875年,他以一部杰出的作品《论语言的起源》开启了科学生涯,从那时起,语言哲学的问题便始终占据了他的兴趣中心,他的许多论文(《论无主词命题及语法与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论语言反思、天赋论和有目的的语言习得》,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一著作是献给他那才华横溢的老师及朋友布伦塔诺的。在人们所谓的‘哲学观点’方面——因而不仅是基本的哲学信念,而且还有对待问题的整个方式,以及哲学发问和哲学方法的整个风格——马尔梯都受惠于他。只有在极度紧迫的情况下,马尔梯才在这种风格所允许的范围内修正布伦塔诺的观念。”[27]最后这一点也证明波扎克(Anna Brozek)的确有理由将马尔梯称之为“布伦塔诺的最忠实的学生”[4]124。
胡塞尔与马尔梯之间有十多次的通信往来。关于胡塞尔与他的语言哲学与含义理论方面的思想关联,笔者在《语言哲学的现象学视角——胡塞尔与马尔梯的思想史关联》[28]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六、胡戈·贝格曼
这里还需要作较为详细讨论的另一位马尔梯弟子、布伦塔诺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成员是胡戈·贝格曼(Samuel Hugo Bergmann,1883—1975)。他在胡塞尔与后期布伦塔诺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贝格曼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布拉格老城上的文科中学,与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是同学。他们也包括胡塞尔、弗洛伊德等,都是自几百年来便生活在这个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地区(现属于捷克共和国)的说德语的犹太家族成员。贝格曼先后在布拉格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后来曾于1907—1919年间担任布拉格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他早年便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和该运动的参与者,后来也成为说德语的新希伯来哲学的先驱。1920年,贝格曼来到所谓的“以色列土地”(Eretz Yisrael)或“应许之地”,担任以色列国家与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1935年。自1928年起,他也担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哲学讲师,1935年担任哲学教授,并于1935—1938年间担任该校的校长。
在以色列工作期间,贝格曼在二战前就为介绍和传布胡塞尔的哲学思想做了许多工作,撰写评论和分析胡塞尔现象学的文章,开设相关课题的讲座和讨论课,如此等等。胡塞尔去世后,贝格曼在讲座中还为胡塞尔致了悼词。二战后,他联系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文库,推动并参与胡塞尔的希伯来语文集的编辑校对工作;不仅自己做关于胡塞尔哲学的讲演,同时也邀请犹太哲学家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等去以色列做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报告,如此等等。贝格曼还将自己保存的布伦塔诺手稿誊写给胡塞尔文库备存,如此等等[29]363,366,468,471f,579,655,679,731[30]113,148,205,294。直至战后1949年,贝格曼还在其日记中记录过他的关于盖世太保的噩梦,以及醒来后与胡塞尔哲学有关的思考:“夜里我常常做些沉重的梦,梦见我落入盖世太保之手,而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有一次我醒了过来,为这不是真的而感到高兴,但我很快又睡着了,而后接着噩梦继续做下去。当我再醒来时,我无法再入睡了,便开始接着讨论课的一个对话来思考胡塞尔与康德(Immanuel Kant),而后我明白了以下的问题:康德大致是从主观性出发,但他探问的是,我如何克服它,这样他便走向他的超越的形式。胡塞尔是从客观性出发,并且探问,它是如何系泊在主观性中的。”[30]23
总体上,贝格曼是将胡塞尔视作德语—希伯来语哲学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弘扬和推广,为犹太复国的计划准备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此方向上,贝格曼与当时著名犹太思想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并有密切的交往。他于1929年出版的著作《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之战》题献给他的老师安通·马尔梯,并附有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为其撰写的简短引言[31]。此外,贝格曼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行动在开始阶段受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影响,后者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于1925年正式建立起便在那里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两人之间关系密切。贝格曼也著有关于布伯思想的论著《从基尔凯戈尔到布伯的对话哲学》[32]。
在贝格曼的日记中,他还记录过自己与布伯的一次关于胡塞尔的谈话和感想:“关于胡塞尔,以及他是否能够给出对相对主义的反驳,我们也谈论了许多。布伯认为:‘我拒绝进行这种对世界的加括号。’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回答,因为在胡塞尔那里,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一种研究的方法。”[30]23
与胡塞尔以及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的交往也属于贝格曼1920年赴以色列之前的一个重要章节。作为布伦塔诺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成员,贝格曼与胡塞尔显然时有联系。1908年10月15日,胡塞尔还收到他寄赠的著作《内感知明见性问题研究》[33],并在书中题记:“1908年10月15日得自作者。”(10)Husserl,Hua X: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usstseins (1893—1917),hrsg.von Rudolf Boehm,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9;以下凡引胡塞尔全集均用简称“Hua X,324,Anm.1.”。在后来由施泰因(Edith Stein)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编辑出版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还收录了胡塞尔在阅读贝格曼的这本书后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记录:“无限性——它应当处在哪里?参见胡戈·贝格曼所提到的布伦塔诺的指责,第82页(论述‘内感知’的著述):在他看来,如果‘内感知’在每个时间点上都指向当下之物和过去之物,就会产生一个有无限多维度的连续统:我的内感知是指向当下之物和过去之物的,为它所把握的过去的内感知重又指向当下之物和过去之物,如此等等。”(11)Hua X,S.328.——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胡塞尔全集》本编者波姆(Rudolf Boehm)在这里还附加了一个说明:“在该书相关处的文字是:‘因为不只是我的当下的内感知,而且我的过去的内感知也据此而部分指向当下,部分指向过去,同样还有被这个内感知作为过去来把握的内感知,如此不断地接续下去。这里似乎已经产生出了一个有无限多维度的连续统。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果我们的内感知持续地包含着一个如此之小的时段(Zeitspanne),那么它也就必定包含着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了。’贝格曼在一个脚注中对此解释说:‘这个指责是我于1906年夏从布伦塔诺教授先生那里听到的。’贝格曼:《内感知明见性问题研究》,第82页注1。”(Hua X,S.328,Anm.2.)此外,根据贝格曼致其太太的信,他至少曾于1911年7月20日这天下午在哥廷根拜访过胡塞尔。他在其中还报告说:“这里的哲学兴趣十分活跃。胡塞尔本人就有一个约三十人的紧密学圈,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都想在大学工作。”(12)由于贝格曼的日记与书信出版较迟,因而这次会面并未被舒曼记入《胡塞尔年谱》。[29]4112
但就目前情况看,贝格曼与胡塞尔之间的书信往来应当没有被保留下来。与此相反,布伦塔诺写给贝格曼的数十封长短不一的信函则得以存世,并于1946年被贝格曼编辑发表[34]83-158。这些信函从1906年开始,直至贝格曼因一战爆发而作为军官赴前线参战时中断,但如贝格曼所说:“读者可以注意到,书信往来在最后几年里已经随着学生关系开始松散而不那么密集和温馨了。”[35]83这些信函一方面“表达出被胡塞尔称作布伦塔诺生命的‘原事实’(Urtatsache)的布伦塔诺人格的之伟大、他对自己的哲学使命的信念”等之外[35]83,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布伦塔诺私底下对待胡塞尔的态度和看法。尽管胡塞尔自己已经从布伦塔诺那里直接地意识到,“如果有人走自己的路,哪怕是从他(布伦塔诺)那里分出的路,这会使他多么激动不安。这时他会容易变得不公正,并且在我面前也曾如此,而这是令人痛苦的”[11]471。但布伦塔诺在背后,尤其是在另一位弟子面前,对迈农和胡塞尔的讽刺和挖苦,今天读来还常常会令人咂舌。
如前所述,在回忆布伦塔诺的文章中,胡塞尔记载,1907年在佛罗伦萨拜访布伦塔诺时,他已经感受到“某种疏远,即便不是私人关系上的生分”[11]471。这里所说的与布伦塔诺的“疏远”,主要是因为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在几个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隔阂所致。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似乎默默地将布伦塔诺及其学派视作心理主义的代表之一并予以批判。而关于他与布伦塔诺的其他方面的具体分歧,则首先涉及对布伦塔诺提出的意向性的理解,其次涉及对布伦塔诺所强调的内感知的明见性的理解,再次关系到对布伦塔诺的表象概念的理解,最后是对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的理解。而所有这些意见分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在心理学的经验论与意识哲学的观念论之间的对立立场。
但从外部显露的情况来看,布伦塔诺与胡塞尔之间最大的矛盾焦点和意见分歧在于他们对“心理主义”问题的理解。让布伦塔诺感到恼火的很可能是他在《逻辑研究》之后常常被当作“心理主义”的代表来加以讨论,而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最终要拜胡塞尔所赐。
在1909年6月1日致贝格曼的信中,布伦塔诺便写道:“我很高兴,宇伯维克终于可以从海因策的手中解放出来了(13)“宇伯维克”在这里是指由这位德国哲学史家宇伯维克(Friedrich Ueberweg,1826—1871)撰写的最初为三卷本的《从泰勒斯到当代的哲学史纲要》[36]。后来,该书不断扩充再版。在宇伯维克去世后继续由海因策(Max Heinze,1835—1909)接手编辑扩充。布伦塔诺写信的这天恰巧就是海因策去世的当日。米施接手这部哲学史巨著的扩充再版。。据我所知,米施教授是狄尔泰的女婿。这个婚姻面临诸多困难,女孩的父母对此十分拒斥,但我弟弟(14)弗兰茨·布伦塔诺的弟弟是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带着温暖的同情接受了这对被困扰的人。米施愿意清除那些由格拉茨学派加入的垃圾,这是非常值得夸赞的,而通过与我的布拉格朋友们的接触,他就踏上了正确的道路,会了解到事情的真实状况。”[34]124f
布伦塔诺在这里所涉及的思想史信息十分丰富,消化展开后足以成为一项专门研究的课题。但在此只能就这里的论题扼要论之:布伦塔诺在这里仅仅提到迈农学派加入到哲学史章节中的“垃圾”,即海因策在《宇伯维克哲学史纲要》的第十版中加入的格拉茨学派一章的内容,这一章的标题是“对象理论”;但他并未提及或表示不满的是,也在这一版中,介绍布伦塔诺哲学的一章被冠以“心理主义”的标题(15)参见贝格曼对此的说明[34]124。。因此,我们很难说布伦塔诺认为两个标题中哪个标题更为恼火。但他在这个语境中之所以没有提及胡塞尔,很可能是因为胡塞尔于1907年在佛罗伦萨对布伦塔诺的拜访而使他的火气有所消退。
1906年9月17日,胡塞尔去佛罗伦萨拜访布伦塔诺之前,即在与贝格曼认识第二个月后写给贝格曼的第三封信中,布伦塔诺就已经开始评论他的学生对他的忠诚度,如霍夫勒、施通普夫,尤其是胡塞尔。从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胡塞尔的了解是依据另一位马尔梯的学生埃米尔·乌悌茨(Emil Utitz)的叙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布伦塔诺晚年视力下降,几乎无法阅读。我们甚至可以确定,布伦塔诺没有读过《逻辑研究》。不过这种情况还在他视力健全的时候就已经如此。胡塞尔在回忆录中便写道:“我曾写信请他接受我在《算术哲学》(我的哲学处女作)上给他的献辞,他回信表示热诚的谢意,但同时认真的告诫我:我不应去惹恼他的敌人。尽管如此,我仍将这部书题献给他,但寄去赠书后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回复。直到十四年之后,布伦塔诺才注意到,我的确将此书题献给了他,并在这时才衷心友好地表达谢意;他显然没有仔细地看过它,或在其中以他的方式‘交叉地读过’。他对我来说是高高在上的,而我对他也太了解,所以并不介意。”[11]470-471
事实上,与题献给布伦塔诺,且未真正惹恼过什么人的《算术哲学》相反,题献给施通普夫的《逻辑研究》则恰恰“惹恼”了一些人,而且更多是胡塞尔的师友,甚至首先是他的老师布伦塔诺,他通过其他弟子对胡塞尔的心理主义批判的转述而对胡塞尔抱有不满和怨气。在这里所说的第三封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布伦塔诺在向贝格曼解释内感知明见性问题时举胡塞尔为例来说明:“例如,如果胡塞尔自己感知自己,并且或许以为感知到一个伟大哲学家,那么这个感知就几乎不能被称之为正确的。”[34]85f接下来,在完成了其解释之后,布伦塔诺还写道:“证明这些混乱要比理顺胡塞尔的混乱脑袋容易得多!您的报告对这位突然成名之人的推荐也是非常糟糕的。您的批判是确切的。不过我们在这里打交道的至少是一个好人。”[34]85f
布伦塔诺在这里所说的贝格曼的“报告”,是指后者当时正在撰写和准备发表的论著《关于内感知明见性问题的研究》,该书在与布伦塔诺讨论多次后完成,于1908年发表[33]。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贝格曼在该书出版后曾寄赠给胡塞尔一册。胡塞尔于1908年10日15日收到并在研究手稿中记录下对书中提出的问题的思考。在同一天,布伦塔诺也收到了贝格曼的寄赠,并在这天(1908年10月15日)致贝格曼的回信中写道:“您的论著我至此为止只能匆匆看一下。涉及胡塞尔的部分我让人相对完整地读给我听。”[34]120f看起来,布伦塔诺对贝格曼的胡塞尔批判并不满意,他接下来写道:“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即以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评论这些混乱费解的理论,这些理论既不与真理相契合,也没有在顾及他人意见时去如其所是地把握它们。您在此已经以一种一般说来值得称赞的简洁方式尽力而为之,却也未能使此事变得容易;而我至少不是所有要点上都明白胡塞尔究竟想要什么。”[34]120f
布伦塔诺在这里最后提到的一点是他在对待胡塞尔态度上的问题关键之所在:由于无意或无法阅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本身,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现象学及其心理主义批判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其他学生的转述和批评来了解的。他实际上并不清楚胡塞尔的真实说法与想法。
正因为如此,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不满和怨气即使在胡塞尔与布伦塔诺见面几次并做了当面的解释之后也未见消解。还在1908年10月15日,即在胡塞尔于佛罗伦萨拜访了布伦塔诺之后不久,后者便已经致函贝格曼,并且在讨论“心理主义者”这个负面“绰号”时写道:“这个高贵武器的共同发明者胡塞尔刚来我这里访问过。他滔滔不绝地向我送上一堆谢意和敬意的誓言,而倘若我相信这些仅仅是恭维之辞,那就对他有些不公正了。他也告诉我说:他始终向人们保证,我并不真的属于心理主义者,他似乎在想为我洗清一个可怕的嫌疑。他太太的在场以及在佛罗伦萨初次访问时引发的诸多兴趣而导致的注意力分散,阻碍了一场详尽透彻的讨论的进行。但我还是听到了几个怪诞的主张。看起来胡塞尔似乎带有好的意愿来考虑批评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深入的阐释或许会让他放弃这个立场。”[34]85f
这样一个“深入的阐释”很可能就是布伦塔诺在1911年出版的《论心理现象的分类》(16)该书后来由克劳斯重新编辑并附加了布伦塔诺遗稿,作为《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第二卷于1925年再版。一书的“附录十一:论心理主义”中所做的相关说明:“为了在一个如此严重的控告面前为自己辩护,我必须首先提问,心理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人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个吓人名称,即使在涉及全然不同的事物时也是如此。当我在与胡塞尔的一次友好会面时,以及常常也在其他谈及这个由他新引入的术语的人那里寻求一个解释时,人们对我说,它指的是一种学说,即主张其他不同于人的生物也能够具有与我们的明察恰恰相反的明察。如果就这个意义来理解,那么我不仅不是心理主义者,而且甚至在任何时候都已经对这样一种荒谬的主观主义做了最坚定的抵制和斗争。”[37]
这样一种对“心理主义”的理解显然不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批判的“心理主义”。因而在收到布伦塔诺于1911年出版的三本新书[38-40]之后,胡塞尔于这年的11月22日致布伦塔诺的信中仍然还在解释他三年前于佛罗伦萨访问布伦塔诺时曾做过的解释:“在佛罗伦萨我曾尝试借访问的机会向您澄清我对心理主义批判的意义。也许我的表达过于笨拙了。我不可能像您(从我的不太成功的阐释中)所理解和报告的那样坚持过我的《导引》并对心理主义做过如此定义。”(Brief.I,54.)
就总体而论,“心理主义”的术语问题是造成晚年布伦塔诺与胡塞尔之间隔阂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造成胡塞尔对布伦塔诺的某种冒犯的主要原因。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的起因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布伦塔诺没有阅读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因而他对“心理主义”的理解十分有限,他在1911年11月17日致胡塞尔的信中甚至还在讨论:“心理主义”这个术语究竟能不能说是由胡塞尔“新引入的”。布伦塔诺认为他依据的是胡塞尔在给他的信函中的说法,但其他人则反驳说,老埃德曼早就使用过这个概念,如此等等(Brief.I,53.)。事实上,只要大致地读过《纯粹逻辑学导引》,这个问题就根本不可能被提出来。据此,我们可想而知,胡塞尔在回答布伦塔诺的这个问题时必定充满了内心的苦涩。
这里还需要插入对另一位布伦塔诺学派的成员卡斯悌尔(Alfred Kastil)的说明。他同样是马尔梯的学生,而且如前所述,1916年,他与克劳斯一同去苏黎世拜访布伦塔诺,并于布伦塔诺1917年去世后与克劳斯一起开始编辑出版布伦塔诺的著作与遗稿。布伦塔诺在致胡塞尔和贝格曼的信中一再提到“其他人”或“人们”关于胡塞尔或“心理主义”的说法,或许与克劳斯和卡斯悌尔及其转述有关。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在卡斯悌尔于1950年发表的“布伦塔诺与心理主义”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布伦塔诺在前引“论心理主义”附录中所说的“其他谈及这个由他[胡塞尔]新引入的术语的人”的类似论点。例如:卡斯悌尔在这里对“心理主义”的理解是,“它的意义缺少明确的规定,以至于一个人可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他同时是心理主义者和反心理主义者。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名称应当是一个鄙视性的谓词,而且包含了这样的指责:它的承载者误解了真理的客观性并对真理概念做了主观主义的篡改”。不仅如此,卡斯悌尔还说明:“埃德蒙德·胡塞尔是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但也是将这个指责掷向布伦塔诺的人。”[4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布伦塔诺在“心理主义”问题上的纠结并非他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布伦塔诺正统派的这些解释而形成的。在这点上,布伦塔诺晚年的确是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意义上“盲目的”。
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构成了胡塞尔与晚年布伦塔诺的关系中的一个仅仅具有消极意义的章节。好在他们之间存在的其他一些争议和辨析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们至少可以有助于后人了解他们各自观点的异同,例如:在对待哲学传统的态度方面,在对内感知的理解方面,以及在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差异的态度方面。
我们可以看出,在布伦塔诺与胡塞尔的分歧中,贝格曼原则上是站在胡塞尔一边的,因而尽管他的身份是布拉格学派和布伦塔诺学派中的一员,但其理论立场却很难被归入布伦塔诺正统派,因而他也与他的师兄奥斯卡·克劳斯并不处在同一战线。即使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一再对胡塞尔关于内感知的明见性的看法做出辨析,但就总体而言还是赞成胡塞尔对布伦塔诺的哲学做出的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正:
第一,贝格曼并不赞同布伦塔诺对待观念论传统的态度,包括对鲍尔扎诺以及康德的态度(17)我们可以推测,贝格曼对鲍尔扎诺的研究[42]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他与胡塞尔的距离。。在布伦塔诺的奥地利经验论传统维护者和胡塞尔的德国观念论传统维护者的分歧与对立中,贝格曼基本上站在胡塞尔一边。布伦塔诺在致贝格曼的信中曾写道:“以为哲学思辨与科学并不共属一体,而且恰恰相互对立,这种看法如今已经广泛流行,它与下列看法是相互关联的,即康德以及依附于他的后来德国哲学应当被视作真正的哲学,而如果不与所有这些衰老退化(Entartung)进行激烈的抗争,哲学就没有权利要求重获一个与其他科学相并列的位置,遑论它原有的一切科学之王的位置。”[34]158而贝格曼对此并不赞成,他在这段话后附加了一个脚注说明:“这个讨论,就像与此同时在与我的老师马尔梯的一次通信中就此问题的讨论一样,并不能说明康德和后康德哲学的历史意义。这里也要指出胡塞尔在《弗兰茨·布伦塔诺》文集第159页上就这个问题所做的阐述。”[34]158
的确,胡塞尔在这篇回忆布伦塔诺的文章中一方面准确地再现了布伦塔诺的态度,连同其关于德国观念论的“衰老退化”(Entartung)之说法:“对于像康德和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者那样的思想家,即那些将原初直观和前直观预感的价值看得远远高于逻辑方法和科学理论之价值的思想家,他的评价并不很高。……布伦塔诺,这位完全献身于最严格的哲学科学的苦涩理想(对他来说,这个理想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得到了展现)的人,仅仅把德国观念论的体系看作是一种衰老退化(Entartung)。”[11]466-467另一方面,胡塞尔在这里也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立场和看法:“即便康德和其他德国观念论者并没有为科学严格地处理那些如此有力地感动了他们的问题动机提供多少令人满意的和站得住脚的东西,即那些确实能够对这些动机进行追复理解(nachfühlen)并能够在它们直观内涵中立足的东西,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在观念论体系中涌现出了全新的和最为彻底的哲学问题维度,只有在澄清了它们并构造出它们的特性所要求的哲学方法之后,哲学的最终的和最高的目标才会开显出来。”[11]466-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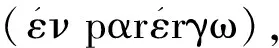
布伦塔诺将近代笛卡尔以降的整个哲学发展都视做哲学的堕落。这一点在前引布伦塔诺1911年11月17日致胡塞尔的信中也清晰地表现出来,他在那里以一种略带讥讽的口吻对胡塞尔的哲学遗产观做出明确的批判性表态:“还请您乐意接收刚给您寄出的三部著述!(19)如前所述,布伦塔诺于1911年发表的三部著作,其中两部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当然它们并不都处在您的较为狭窄的兴趣论域中。不过您很愿意将您的目光加以扩展,而且您没有看错,如果忽略了对以往时代伟大思想家的研究,就无法有所成就。您不久前在贝格曼博士面前所做的一个表述已经充分地透露出这一点,而且我对此只能感到高兴,尽管我也觉得讶异,您如何能够认为,我和其他与我亲近的人不知道以类似的方式尊重哲学前史的价值。但事实上我们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与堕落的时期的区分方面要比您做得更多。”(Brief.I,51f.)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布伦塔诺与胡塞尔的哲学立场不同,导致他们对哲学发展的上升与下降所持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各不相同。
第二,贝格曼相信,布伦塔诺在划分先天的描述心理学与经验的发生心理学时实际上已经使用了某种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方法。他批评布伦塔诺在赋予他的著作以“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之标题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经验”概念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发生心理学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归纳的,并且在此意义上是‘经验的’”;而另一方面,他所倡导的描述心理学也是“经验的”,但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即“描述心理学的分析与一种可以通过增加被观察的案例来获取或然性的归纳无关。正如布伦塔诺自己在他的著作《论伦常认识的起源》中所阐释的那样,描述心理学是可以‘无须任何归纳而一举(mit einem Schlage und ohne jede Induktion)’达到普遍认识的”[43]361f。
实际上,贝格曼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这里需要摘引布伦塔诺的相关原文:“当然,随着对相关的爱或恨的行为的经验,这个总体属的善或恶会在无须对特殊案例的进行任何归纳的情况下一举显露出来。人们以此方式例如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普遍认识,即明察本身是善的。”[44]这个意义上的“明察”,已经不再是布伦塔诺意义上的“经验直观”,而更多是胡塞尔意义上“本质直观”了。这也就意味着,不仅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源自布伦塔诺,而且他的一再受到布伦塔诺批评和讽刺的“本质直观”或“本质明察”的概念最终也可以在布伦塔诺那里找到支点!再扩展一步,我们当然还可以说:布伦塔诺的这个说法就是后来同样处在布伦塔诺影响下的舍勒式“伦常明察”的前身!——不过,这是需要做进一步专门讨论的问题(20)这里还可以追踪贝格曼所受到的鲁道夫·施坦纳的影响。贝格曼很早便在布拉格结识了施坦纳并且终生都在研究施坦纳,尽管他对待施坦纳的态度有变化[45-46]。而在这方面,施坦纳就“精神直观” (geistiges Schauen)的问题很早便与舍勒心有灵犀一点通[47]。如果伽达默尔说“直觉这个关键词在1901年曾是联结两位思想家的桥梁”[48],那么“直观”或“直觉”的概念也应当是联结施坦纳与舍勒的桥梁。。
第三,贝格曼赞成胡塞尔区分心理学(即广义上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与物理学(即广义上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做法。而且他认为布伦塔诺并没有看到这个区分的必要性,因而处在胡塞尔所说的素朴的自然态度的立场上。贝格曼指出,后来的克劳斯恰恰是在胡塞尔的影响下做出了这个区分。他在其纪念布伦塔诺的文章中写道:“描述心理学的对象从属于经验,但它的方法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我相信,布伦塔诺在撰写其《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个区别被布伦塔诺学派意识到了,尤其是被克劳斯所强调。这应当归功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49]362
当然,这个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的要求还应当进一步追溯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对胡塞尔的影响上。胡塞尔在这里将布伦塔诺的严格科学的主张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主张结合在一起,强调精神科学的动机是说明方法的严格性(Strenge),以此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方法的精确性(Exaktheit)划清界限(Hua III,§§ 73ff.)。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同样既受狄尔泰影响也受布伦塔诺影响的海德格尔后来也默默地接受了胡塞尔的这个区分(21)海德格尔在这里实际上更推进了一步:“相反,‘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精确的。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50]21。
如前所述,贝格曼暗示,他与布伦塔诺书信往来在最后几年里不再密集和温馨,是因为学生关系开始松散所致[43]361f。这很可能也是指他自己因为不能附和布伦塔诺的观念和更多站在胡塞尔一边为其辩护的态度,使得布伦塔诺不再有兴趣与他维系和加强这种书信往来。
我们尽可能中立地说,布伦塔诺对待自己的学生胡塞尔的态度和看法或许总体上可以用“不够大气”来标示。毋庸置疑,在与布伦塔诺学派的问题相关的语境中,胡塞尔在对待迈农的态度和看法或许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定义。但在后一个案例上更难找到胡塞尔的动机和理由。或许胡塞尔只是在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而已。而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担心”似乎主要是因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发表后一夜成名以及名声太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类似长辈对晚辈的“少年得志”式的担心。他在1907年5月7日致施通普夫的信中说:“胡塞尔的来访让我非常高兴。但他的新想法是极为奇异的。利普斯、里尔都为此而恭维他。而我担心,如果我向他指明,他正走在歧途上,那么这会有害于他的学术生涯。”[7]134,141[51]接下来,在1909年1月19日致施通普夫的信中,他又写道:“我担心我们的胡塞尔的情况也不好。不应得的赞誉将他越来越紧地束缚在某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上,只要他愿意,我会轻易向他证明它们是完全错误的。”[7]134,141[51]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与胡塞尔有关的马尔梯学生埃米尔·乌悌茨同样属于布伦塔诺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成员。他当时(1906年)是与贝格曼一同去拜访布伦塔诺的,就像克劳斯在十年后(1916年)是与卡斯悌尔一同去拜访布伦塔诺的一样。(笔者在第五幕中还会讨论他在纳粹上台之后为胡塞尔提供的移居布拉格的可能与计划。)但这一部分已经属于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学派关系史的外篇了。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一个贝格曼在1935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的他们师兄弟几人对待胡塞尔的不同态度方面的一段有趣故事:“昨晚我去访问克劳斯和布伦塔诺文库。当克劳斯置身于谈话的中心,闭着眼睛在阐述布伦塔诺对某件事情的反应,而且当他承认胡塞尔的贡献在于:他说出了有一门先天的心理学这个事实,这时他实际上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他关于乌悌茨所讲述的东西尤为有趣:乌悌茨曾如此赞美胡塞尔。对此克劳斯问道:您读过他最近的著作吗?乌悌茨回答说:我可不想因为阅读他的著作而让我对他的敬重蒙上阴影!”[29]410
七、回顾与总结
这里已有必要对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学派的关系做一个全面的回顾总结。尽管这个关系并未随马尔梯于1914年以及布伦塔诺于1917年的去世而告结束,而是延续到更年青的一代人,这一点正如可以从克劳斯在20世纪20年代起对胡塞尔的批评、贝格曼与胡塞尔的关系、英加尔登对迈农的批评[52],以及以后还会讨论的乌悌茨与胡塞尔的关系上感受到。但胡塞尔本人与布伦塔诺本人及其重要弟子的直接联系和书信往来到1916年便已告结束,这年也是布伦塔诺写给胡塞尔最后一封信的年头。
不过,这里所说的“布伦塔诺学派”乃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如果按照目前欧洲的几个布伦塔诺学派研究团队所列出的那些最重要代表人物来确定它的成员组成,那么这个学派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思想阵营,还不如说是对一个师承脉络的标示。当然,这个学术团体的一个共同标识是意向心理学,但在对“意向性”的理解和解释上,他们的分歧要大于统一;此外,这个学术团体的另一个共同标识是“严格的科学”的理想,但在对“科学”以及“严格性”的定义和方法的理解,他们也各持自己的看法。就此而论,“布伦塔诺学派”的含义边界甚至要比现象学的“慕尼黑—哥廷根学派”以及“弗莱堡学派”的含义边界更为模糊,同样也比当时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和“西南德意志学派”的含义边界更为模糊。
虽然胡塞尔本人事实上已被视作“布伦塔诺学派”的重要成员,但他在关于自己“并不善于始终做他的学派的成员”的表达中已经使自己与布伦塔诺及其弟子保持了距离。总体而言,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的对立首先是哲学立场的对立。这个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亚里士多德经验论与柏拉图理念论之间对立的现代延续。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前已经与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和哥德尔(Kurt Gödel)处在一个统一战线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一卷前言中所言:“确切地说,我自身的发展进程引导我,一方面在逻辑学的基本信念上远离开那些对我的学术培养最有影响的人与著作,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其他一些研究者,以往我未能充分地估价他们的著述,因而在工作中也未曾从这些著述中得到足够的启迪。”(Hua XIX/I,A VIIf./B VIIf.)这基本上就意味着从布伦塔诺及其学派、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的脱离,以及同时向弗雷格、鲍尔扎诺(Bernard Bolzano)、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柏拉图方向的靠近。
在这个接近的途中,胡塞尔在哥廷根接受了来自慕尼黑的“利普斯心理学派”的致意,并顺意而认同他们自行改编成为慕尼黑现象学派,而后在哥廷根现象学派的弟子们的合作中开启了早期的现象学运动。统一在这个运动旗帜下的不再是一个师承的脉络,而是一个在方法论的共识:在心理学领域中对本质直观和本质描述的运用。胡塞尔自己的思想列车从“布伦塔诺学派”这一站已经驶到了“慕尼黑—哥廷根学派”的下一站。
但很快,1913年公开表达的超越论还原思想以及由此带来的超越论转向,使得胡塞尔有可能将现象学运动引向一个更接近观念论哲学的方向:超越论的现象学或观念论的现象学。而早期现象学运动的主要成员对这个新的转向或多或少表明了拒绝认同的态度,并或明或隐地不再随胡塞尔同行。胡塞尔逐渐进入思想上的独自行走状态。
我们可以说,在1905—1913年的八年时间里,胡塞尔实际上又完成了一次远离一些人和接近另一些人的行程。如果说以《逻辑研究》为代表的第一次转向意味着穿越了经验心理学而走向本质心理学,这一次的穿越方式是通过观念直观和本质还原来完成的,那么以《观念》第一卷为代表的第二次转向则表明胡塞尔穿越了本质心理学而走向超越论心理学或超越论哲学;而这一次的穿越方式是通过“超越论还原”(Reduktion)或“普全悬搁”(universale Epoché)来完成的。
对于胡塞尔而言,即使本质心理学通过本质直观和本质描述而把握到人的心灵的本质,即心的秩序或心的逻辑,它也仍然是关于在世界中生活的人的心灵的科学,仍然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胡塞尔在二十多年后对这个穿越和转向做出总结和评价:“作为实证科学的纯粹心理学,即一种想要与其他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一样,将生活世界中的人当作世界中的实在事实进行普全研究的纯粹心理学,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种超越论的心理学,它与超越论哲学是同一的。……因此纯粹心理学就其本身来说。与作为关于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科学的超越论哲学是同一的。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Hua VI,261.)
胡塞尔在这里表达出一种彻底的一元论的哲学诉求。他所说的“超越论心理学”或“超越论哲学”就相当于纯粹的、绝对的意识哲学或精神哲学。在这个立场上,他离开慕尼黑学派有一步之遥,而离开布伦塔诺学派则只有两步之距。
但在另一方面,胡塞尔在精神上仍然属于布伦塔诺学派。因为这个学派不仅仅以经验立场上的意向心理学为其统一的共同标示,而且也以严格科学的心理学为其共同理想。正如贝格曼所说:“还在布伦塔诺的青年时代,其主导的理想就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后来胡塞尔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个理想。”[49]349胡塞尔自己在回忆布伦塔诺的文章中也写道:“首先是从布伦塔诺的讲座中,我获得了一种信念,它给我勇气去选择哲学作为终生的职业,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因此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11]463因此,即使后来对于这个意义上的“科学”的理解不一,胡塞尔一生从经验心理学到本质心理学再到意识哲学的发展,始终是而且最终也是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这里的“严格的科学”,不是单纯的“心灵术”或“意识观”,也不是精确的、实证的自然科学,而是严格的“心灵学”或“意识学”,无论这个“学”指的是“科学”还是“哲学”。
如果现在再返回到1917年的语境中,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与胡塞尔在一定程度上同行的还有弗莱堡现象学三人组中的另外两人:施泰因和英加尔登。他们至少一度统一在超越论的观念论的旗帜下。但这已经不是素朴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而是超越论的观念论,而且接下来还可以留意一点:在胡塞尔那里,它也逐渐成为发生的观念论,从而在多重意义上有别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论(22)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论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关系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胡塞尔与柏拉图——现象学观念论的形成与论证》[53]。。这是在胡塞尔思想变化发展中的另一个阶段:发生现象学的阶段——这是笔者仍然会展开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同样处在这个1917年语境中的是胡塞尔的弗莱堡就职讲演。他在开篇谈道:“命运将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劳作置于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之中,它在人类精神生活发生作用的所有领域中都是一个剧烈变化生成着的时代。”(Hua XXV,68.)事实上,这个针对人类精神生活发生作用的所有领域而言的“剧烈变化生成”,同样也体现在胡塞尔的精神发展中。
十三年后,胡塞尔在1930年6月7日致米施的信中就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做出回顾时发出感慨道:“实际上每个自己思考者每隔十年都必须更换自己的名字,因为他那时已经成为另一个人了。”(Brief.VI,281.)据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接下来所做的抱怨:“但对于人们来说胡塞尔就是胡塞尔。”(Brief.VI,281.)
这个抱怨是针对那些没有用发生的眼光来看待他和他的思想的人而发的。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