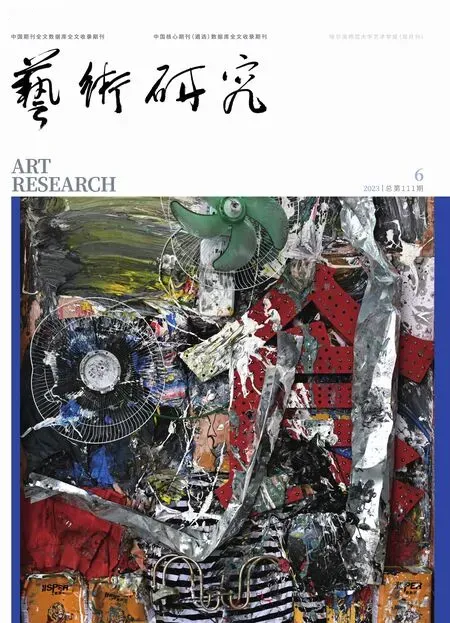从“君形者”看书法中的“形神”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石岳
书法在当代已然被归为了一种视觉造型艺术,不可避免的就要涉及其“形”与“神”的研究,而关于书法“形神”观念的讨论又似乎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命题,古人多以“神采”与“形质”的说法来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也普遍性地认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但具体的对其有所解析却少之又少,这就不妨从《淮南子》中的“君形者”一词中深入讨论。
“君形者”一词见于西汉时期刘安所著《淮南子》中三处:第六卷《览冥训》:“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第十六卷《说山训》:“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第十七卷《说林训》:“使但吹竽,使氐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根据诸多版本的解读翻译来看,这三段描述大多学者都给出了大意相近的解读诠释,唯独在“君形者”这一词组中,解读的方式较为复杂,甚至因为语境语句等原因,同一词组被解译成多种说辞,使得人们可以理解却无法用语言具体描述这一词组的真实含义。又由于长期以来,这一段言论更是被当做艺术学理论中谈论“形神”问题的优秀解读来看待,所以深入地探讨分析“君形者”的具体含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君形者”的基本含义
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形,象形也。”;“者,别事词也。”从许慎的解读中,我们不难读懂每一个字的意思:“君”有主导、统领的意思;“形”即是“象形”,是外形特征的具体把握;而“者”中的“别事词”即指明了其为代词的作用,指代前面所叙述的事物。单纯地从字面意思出发去理解“君形者”的概念,就会出现中华书局版本《淮南子》中的解读:“支配形体生命的生机”或“至精主宰形体”等意义,“支配”“形体”“形体生命”都是根据翻译而来,而“生机”“至精”则是对于“君形”概念的理解后进而做出的主观意识分析,是对到底这是一种什么“者”的直白解答,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诸多学者对于“君形者”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
如果书法本身在创作之时是以某种记录的目的引导书写者完成作品,那么其中的书写目的就是这件艺术作品的最关键核心部分,又或者说是某一种观念思想指引着书写者完成了最终的书写,理所应当的在书写过程中的记录就是一件独立于书写完成品之外的艺术作品,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复制任何一个自我的书写状态,这就使得这样的记录方式具有独一性。而这种观念性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其起到主导主宰作用的先决条件。
对于所谓“形”的出现,最重要的就是形的可观化形式,是人们眼中固有的外化存在。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对于所不能理解的自然事物都会赋予其“神”主宰的概念,诸如“女娲造人”“后羿射日”等其实质上都是对存在的“形”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表达,这也是当“形”不再能满足人类想象需求之后的思维突破。人们也愿意相信在“形”之外,有着更高的主宰者,把这样的理解视作是对于人与自然的解读,这是人的共性与天性。事实上,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后,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看似是政治经济等与生产关系直接产生联系的诸多因素在起着作用,这更像是一种思想家对于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觉醒式认知,大家都希望通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进而寻求到所谓的“天道”“真理”“真知”。同时期的西方伟大哲学家柏拉图也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著名的“三张床”理论,在这“三张床”中,似乎只有“第一张床”在人类还未出现之前就存在的真理的床是主宰“后两张床”的根本所在,而人类永远只能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来建立起与“第一张床”的链接,这与刘安的“君形者”考虑方法虽不想同,但表述的内涵却又有共通之处。
文字作为书法最基本的符号载体,本身就承载着“形”重要作用。而文字的建构又需要分成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文字从本身被建立(亦或者文字从来未被建立,只是存在)起,并没有任何以视觉审美目的需求,只是一种单一的指事代物,甚至不用文字存在,任意的发声都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而一旦抛开文字指示的意思,文字就剩下文字本身了,再无含义可言。如《语言学基础》中提到的案例:“‘猫’字本身只是一个‘猫’字,而‘猫’的意思却是一种四只腿走路毛茸茸的小动物。”文字的图示化存在与指意性一旦分离,彼此之间便再无意义可言,这其中也暗指了实际上“形”只是依附于“神”的表面存在。
归根结底,“君形者”的概念是人对于现有客观存在的不满足,进而对其源流所在提出的哲学问题。不论是东方形神关系的把握,还是西方模仿与被模仿的讨论,“君形者”始终有着不能被言说的深层次含义,这大概就是刘安使用“君形者”一词来进行描述的最终原因。反之,如果刘安对于“君形者”概念的把握使用了某一词语或是直接给出明确如“神”“道”等具象的定义,那么在刘安看来,这极有可能又会被禁锢到“形”的客观存在中,这是我们或是刘安所不能接受的。
二、“君者”对“形”的主宰作用
“君形者”的言论自身就带有强烈的唯心取向,这直接定义了“形”的体现已经是至少“第二”出现在事物的发生发展中,而在之前的“第一”才是主宰着“形”的关键所在。君臣父子的人伦纲常使得古代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都有着等级鲜明的上下级关系,上一级对下一级有着绝对的主宰统领权,在“君形者”这一概念中,很明显“形”处于被主宰的下级之中,这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不谋而合。
“君形”在某种程度上如同“文字”一样,“文”因为其内在含义而成为了统领“字”的“君”,而“字”的表达与客观存在只不过是“文”的一种外化形式。以上,不难看出,作为主宰者的“君形者”是一种具备完整思想、意识的上级存在,而“形”不过是受其支配的“傀儡”。通过对于“君”的主宰意识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得到在中国古代传统艺术中那些更为核心的秘密所在,如: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传承中,笔法与结构之争从未停止,到底二者的支配关系如何,诸多学者书家各执一词。实际上,“形”即外在存在,“结构”亦然,曾有书家言论:“即使是火柴棍摆出合理的结构也是好看的,所以结构先于笔法。”诚然,如果单从“好看”这一范畴出发,此一言论并无问题,形体结构带给人的审美感受绝对是第一性的或是极具冲击力的。但这一言论明显有偷换概念之嫌,书法之所以称之为“法”,自然是拥有了毛笔书写的介入,没有合理的书写方法就不能称之为书法,如果单一将结构即外在“形”置于“君者”的位置上,这明显是一种极端的思想意识,“形”无可“君”,最终就会走向苍白、空洞。同样,反之亦然(笔法统领结构)。
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门艺术像书法一样如此重视法度的重要性,而法度就是“君者”对“形”的主导依据。书法自东汉魏晋时期之后,才正式出现了独立的书法理论研究,法度的规范也才逐渐的显现出来。实践产生艺术,艺术带来审美,审美引人思考,思考形成法度,法度返回来指导实践。所以说在整个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里法度其实是偏向于靠后的过程中才形成的,又或者说法度的出现其实是人为实践后的思维产物,并不是自然客观存在。但同时法度又具备着指导实践创作的作用,相对于主观的创作实践,法度又是客观的。
但是以上所阐述的问题皆是无形的将讨论时期限定在了魏晋以后,也就是书法理论产生之后,对于汉代以前的“书法”我们不可能找到也根本没有任何依据称为“书法有法”,自然的刻画、实用的铸造、简牍帛布上的符号,我们很难将这些没有规律性、缺少规范性的文字用法度一一约束起来。如果说书法的生命力在于独特法度的制约,那么像这些不规范的早期文字又是否可以称之为书法呢?还是说书法的法度其实并不是像上文讨论那样是滞后的,而是在更早的时候法度已经客观存在于这些“书法”之中,只不过后知后觉的是我们罢了。
法度是区分“书法”与“写字”的中间分界线,但这条分界线又显得那么模糊不清。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我们会经常的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商贩手写体的牌匾、个别婴幼儿使用毛笔墨水的涂鸦、从未写过毛笔字的成年人随手涂写,不经意间会使书法专业的人为之一动,但冷静下来观察又觉得离“书法”之距离甚远,甚至都不可以称之为“书法”。反过头来,我们在观察一些初学者或是专业水平不甚很高的书法实践者书写的文字时,尽管最终的成品效果不尽人意,但也不可否认收的是这样的作品只是法度不成熟或者法度不严谨所导致形成的,并没有脱离书法的范畴。这个现象很好地说明了法度的真实存在,并且这里面所涉及的法度概念不能以魏晋之后书法理论成熟以来的法度进行界定,更多的是一种合理的审美感受。法度是人为规定,更是自然存在,一切合理的组织都是建立法度的前提,同时更是法度建立起了“君者”与“形”的重要联系。
不论是结构还是笔法,其实质上,都是外在的“形”的范畴,正因为“君”的主宰意识所为,才形成了具体的可以言明的笔法结构形态,南朝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有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次之即下级,那么“神采”可以认定为主宰统领“形质”的上级,也就是“君”的主宰意识的体现,而“形质”就是这些物化的技法(笔法、结构等),那么书法之核心秘密所在,以上虽未言明,足可见其实际更为深奥,不应为下级的“形质”体现。上文虽然以书法一艺的具体技法来阐述“君”为何物,但事物的核心原理应是彼此相通的。
三、“君者”与“形”的辩证统一
《淮南子》中“君形者”概念的提出,其核心观点旨在阐述“君者”与“形”的主次关系问题。《易经·系辞》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就是作为具体技法“形而下”的“道”之载体,而“君者”则是“形而上”的“天道”真理。虽然“道”决定着“器”,但“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阐释“道”的理念,是“道”的物化,人们只有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器”,才能领悟理解“道”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这本身就是“器”对于“道”的反作用。同理,“君者”在统领着“形”的同时,“形”也在依靠着自身外化的优势尽力的去诠释“君者”的具体意义。
“西施美而不可说”并非是不表现西施的美貌,大概强调的是有些用力过猛所导致的过分重视“形”(美)而脱离了“君者”(说)的范围。但不难想象的是,如果描绘西施不按照所谓“美”的构成去创造,那么得到的就一定不是描绘西施的最初本意,这本身就是“君者”与“形”的辩证统一。
书法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包含在创作的这一完整过程中的,并不可以将二者分割开来讨论。中国古代书法从形制来区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金石铸刻,一类是墨迹文字。墨迹文字多见于东汉魏晋之后,其流传性之广泛与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书法的绝对权力息息相关,其书写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书法的特指意义。而金石铸刻文字显然不具备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优势,甚至在有一大部分的碑刻中书写后的样子无从得知,只能靠刻工的技术将文字还原出来,但这本身已经属于了二次创作的范畴,实际上已经离原作者的创作意图相差甚远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当代看来所谓民间化书法的器物之中:如砖瓦陶器上的刻划文字,完全又是创作者一次性通过刻划行为完成创作,一下子就具备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条件。
西方艺术理论中有“模仿论”之说,意为艺术之起源来源于模仿现实,又有“游戏说”等等,皆为艺术的起源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中国早在东汉时期,赵壹便在其文章《非草书》中有言:“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兴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这一段论述虽然是赵壹为了下文反驳众人追捧草书所做的铺垫,但在其中引用的“东施效颦”与“邯郸学步”无意间暴露了时人在追求草书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以模仿为先导性的书写,这也就是书法创作的最初形态,这与《览冥训》中的“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确有相似之处。
蔡邕在《笔论》中表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一段论述既是表明书写之前的心理状态准备工作又是告诉人们书写之前的行为方式,可以说这是一种蔡邕理解的准备进入到创作的观念,这大概便是“君者”的意义。与蔡邕观点较为相似的还有李世民在《笔法诀》中的描述:“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又如王羲之在《书论》中所言:“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欧阳询《八诀》:“虚拳直腕,指齐掌空,意在笔前......”
“君者”与“形”在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各自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君者”作为“形而上”的“道”,一方面是圣人贤者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感受进而体悟到的,另一方面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传承,不论是自然法则还是人伦规则,“君者”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正是因为“君者”的这种属性,才决定了其虽“形而上”但却不空洞的事实,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属性,“形”才能更准确地寻找到“君者”的所在。其次,“形”的把握一定伴随着的是脚踏实地的技法衍生,过于地将“君者”位置不断提高,最终只会脱离“形”的约束而变成“纸上谈兵”,只有更高级、更准确、更有信息量的“形”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君者”,二者也才能实现真正的辩证统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君形者”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艺思想中极具哲学思辨性的问题汇总,其中既涉及“形”“神”观念的辩证统一,又包含探讨主次关系的发问,是对“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的高度总结。这对于理解书法艺术中的“形神”观念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是沟通书写背后存在意义与书写技艺的重要桥梁。以上笔者草草,未能探之二三,尝试理解“君形者”概念的真实意图是接近书法核心问题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