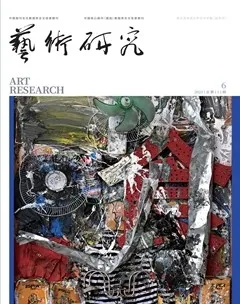社会意识的艺术表达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爱尔兰人》
东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于丽燕 付守丽
马丁·斯科塞斯因其影片中对于社会问题的呈现与剖析,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这说明他的影片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非常适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分析。从马丁·斯科塞斯的新作《爱尔兰人》入手,尝试阐述他对于黑帮题材的回归,以及该部电影中极具特色表达方式,以此来管窥马丁·斯科塞斯影片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艺术表达与美国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密切关联。
一、题材的回归:影像与现实之间的互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爱尔兰人》根据查尔斯·布兰特小说《听说你刷房子了》改编,以黑帮杀手弗兰克·希兰为中心,讲述了他与工会领导吉米·霍法,黑帮头目罗素两人的恩怨纠葛,以一位杀手的视角见证了30 年间美国黑手党的影响与全国卡车工会的斗争兴衰。小说原名本是句黑帮黑话,指的是暗杀成功,血溅四处,故而需要“刷房子”,而影片用以命名的“爱尔兰人”,是片中主人公弗兰克·希兰的外号。片名的改变其实也暗含了导演的意图,影片把眼光聚焦在人物本身,而非他的职业能力。电影用了3.5小时将几个人物串联得立体完整,年迈的弗兰克·希兰孤独地等待死亡,昭示着一代黑帮枭雄的全部落幕。
马丁·斯科塞斯对于黑帮题材的钟爱与回归,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1942 年,他出生在纽约的极度混乱,街头帮派活跃的“小意大利”社区。意大利裔的聚集区自然是渊源于意大利的著名黑帮团伙“黑手党”的天堂。依据斯科塞斯自己的回忆:“在这个地方,居民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法律。我们不会理会什么政府、什么政界显要、什么警察,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经历自然呈现在了他以后的电影中,成了他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重要途径,甚至有的电影情节就源自于他所见的真实经历。即或是黑帮题材之外,如《愤怒的公牛》《谁在敲我的门》等,也都是在关注意大利裔移民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题材选择源于马丁·斯科塞斯的成长经历的社会现实,而对于题材的处理则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思想观念的主观能动表现。他的电影无不个人风格鲜明,最成功的黑帮题材自然也不能外。发迹时期的美国黑帮电影最大特色是“具有传奇色彩”,之后的50年代,则主要聚焦在“警方与黑帮之间的‘黑白对立’、黑帮内部的‘黑吃黑’两种矛盾”,到了科波拉时代,才开始以他意大利裔的视角与个体经历,从黑帮片中“确认自身的意大利传统”。马丁·斯科塞斯为黑帮片打上自己烙印的方法便是改传奇故事为具体写实(他的大部分黑帮题材电影不再具有那么传奇的故事性,而是落脚在具体可见的社会现实),转外在的矛盾的设置为人物内心冲突的刻画(影片着重于对于社会中人物生存、精神状态的深刻把握才让他有“电影社会学家”之名,新片《爱尔兰人》中就对弗兰克·希兰三个时期的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做了细腻的呈现),与科波拉相比,则是由家族史诗变为底层,街头。这种题材的继承与处理方式的变化,让斯科塞斯发扬了黑帮电影,也让黑帮电影成就了斯科塞斯。这次的《爱尔兰人》,虽然依旧是黑帮题材,但较之于之前的那些,内容终归不同,这可以算是时隔十余年,斯科塞斯有了新的内容想要以此来表达。
二、主题的异同:感喟时间与暮年孤独
电影主题的表达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作用的结果。斯科塞斯也说过自己会死在摄影机背后的话,已过古稀的他再痛斥漫威不算电影也改变不了《复仇者联盟4》登顶票房影史。更讽刺的点则在于,斯科塞斯自己的电影反而不再被算作“电影”了。因为他这部新作《爱尔兰人》拍摄过程中因预算超支,最终是由Netflix 公司(全球最大的视频流媒体公司)的资助才得以制作完成,也因此这部电影失去了登陆传统院线的资格,告别了大银幕。这似乎是宣告着斯科塞斯认为的电影的终结,或者说,他在一个不再属于他的时代中的孤独。斯科塞斯电影的这种遭遇和《爱尔兰人》中表达的主旨竟然有了离奇的相似感。影片结尾处,弗兰克·希兰在友人尽去的时代,孤独地等候死亡。这种时间的残酷感和暮年的孤独感,是斯科塞斯先前黑帮电影中所不曾有过的。马丁·斯科塞斯在其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品中的主题呈现,既有源于社会存在的决定影响,也有他主体的能动结果。
先前马丁·斯科塞斯的黑帮电影中,有几个贯彻始终的主旨表达。首先是对于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自我迷失,寻找认同;其次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孤独,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再者就是他宗教家庭背景赋予他电影的,常有一种负罪和救赎意味,他自知:“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是在电影里进行我的忏悔。当然,我还会不由自主地带有宗教性眼光。我在寻找上帝和人之间的联系。”以上述归结的大致三点,对比一下这部《爱尔兰人》,可以不困难地察觉到它与以往斯科塞斯黑帮电影的明显不同。
其一,关于移民身份认同问题。虽然片名《爱尔兰人》指向了主角弗兰克·希兰爱尔兰裔的身份,影片中他也确实在意大利有过四年的战争经历。剧情中丝毫未谈移民身份问题,与其附会这种主角背景设置是马丁·斯科塞斯对于移民身份主题的延续,毋宁说只是为了黑手党头目罗素对他感到亲切并收为所用的故事背景的合理性设置。至于何故让马丁·斯科塞斯放弃了对于身份寻找问题的追索,答案或许需问马丁·斯科塞斯本人,此处的猜想大概是,生命已距幻灭不远,再去追索从来似乎不再重要,眼下的感受与未来更加值得一顾。
其二,关于人的复杂矛盾与孤独问题。这一点片中的确涉及,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重点来呈现,但这种挣扎和孤独已经无关于社会批判与时代审思,而只关于人不由己的选择中的挣扎、痛苦,与时代落幕的终极孤独。影片中军人出身的弗兰克有服从的天性和对生命的漠视,这也是他成为一个专业杀手的原因。但在得知罗素需杀掉自己的好友吉米·霍法时,还是出现了举棋不定是否通报的挣扎,最终他自己动手杀死霍法之后,安慰霍法妻子的电话拨通,他出于歉疚吞吐难言。暮年的时空里,他延续了不关死房门的霍法身上的习惯,可见他一生也未能走出这巨大的歉疚。并且他的歉疚是无法言说、不可忏悔的——保密是杀手必备的素质,这种难言的痛苦也必然导致绝对的孤独感。晚年的弗兰克·希兰无人陪伴,女儿们个个远离他,昔日故友也一一逝去,他只能在生命中独自面对他所有的痛苦与孤独。听到他的律师过世后第一反应是问凶手,而未曾想过癌症。他似乎躲过了疾病灾难与凶杀,但他难逃的是时间的折磨与惩罚。
其三,关于忏悔与救赎问题。影片中虽有涉及,但并非是直接呈现的。弗兰克·希兰几乎是个漠视生命的杀戮机器,仅在杀死挚友后有过痛苦与歉疚。他是在遭受惩罚,但这惩罚却不来自他心中的良心或道德谴责,而源自个人之外,时间、职业以及家人的惩罚,他的个人身上是不存在忏悔与救赎的。但导演聪明的地方就在于设置了女儿佩琦这个人物,弗兰克·希兰内心中缺失的道德与良心都外化到了这个女儿身上,他的女儿仿佛能洞悉他瞒过所有人,甚至瞒过自己的心中罪恶行为,并且以冷漠,断绝关系这最能,也是唯一能惩罚到弗兰克·希兰的方式来惩罚他。从他对佩琦的杂货店老板大打出手起,每次弗兰克·希兰的罪恶都能被佩琦敏锐察觉,佩琦就是一个具象化的良心,静默地越过忏悔而完成对他的惩罚。
三、表达的选择:故事之外的现实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有一条关于人生价值的重要原理。原理指出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即通过自己的活动满足自己所属的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需要。导演作为一种艺术工作者,其人生价值可以说是通过运用艺术的手段创作作品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对于艺术门类的选择、艺术表达技巧的取舍,都是导演实现其价值的具体手段。电影作为一种媒介语言,语言表达层次的技巧正是导演才华的证明之一,几乎相当于评价文学作品时讲的文笔,导演的文笔便是对视听语言的把握,以及细节,意象的设置等等。马丁·斯科塞斯成名很重要的点便在于他对于音乐、光影和剪辑的炫丽地才华横溢地使用上。《出租车司机》中喧嚣迷离的萨克斯和诡谲变幻流光溢彩的灯光,《愤怒的公牛》中凌厉的剪辑,长久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在这部《爱尔兰人》中,视听的才华被自觉地克制,没有用酣畅淋漓的画面表现刺激的故事,而是不疾不徐地把一个跨越了近50年,三条时间线的故事在3.5小时的长度中娓娓道来,几乎有试图阐述一生的漫长的雄心。并且使用了不少前后呼应的意象来隐隐地完成表意,不再具有强烈的震撼性,但却在安静中自含万钧之力。以下便分点阐述斯科塞斯在《爱尔兰人》中的表达技巧。
(一)极具克制的镜头表达
前文已提过,才华横溢的表达技巧曾是马丁·斯科塞斯的风格标志,这在《爱尔兰人》中被完全地遮蔽起来,整部电影在画面上呈现为一种极端的克制。这种大概在片中表现的死亡场景时得到最佳呈现。传统的电影片段在表现杀人的场景时,常常伴有紧张的氛围和让人心跳加速的节奏,通过对音响、景别的控制,给观看者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受人,使人不知不觉地进入剧情中,跟随剧情的变化心惊肉跳。《爱尔兰人》不同,影片中预谋杀人和执行杀人的段落中,镜头如常,毫无节奏变化,甚至景别也没有切换,完全没有特写的强调,只是如常,冷眼旁观式地表现死亡,以至于片中的死亡有一种科恩兄弟式的“突如其来的死亡”感。在弗兰克·希兰杀死霍法的段落中,他还在屋里正常保护霍法离开,接着就在一个平缓的镜头内,他举枪,两枪打死霍法,简单,毫无征兆,也没有任何死亡后的情绪渲染,就如同吃个午饭般自然。这种平静,毫无波动地镜头语言与影片娓娓道来的故事是极具契合度的。整个故事便几乎没有多大的起伏,没有过多情绪的波动,死亡,无论是多大的,怎样人物的,以何种方式的死亡,都不过是生命常然。甚至片中还很戏谑地在每个人物出现的时候直接弹出字幕提醒,此人姓甚名谁,死于何年何月和具体死状。
(二)别有韵味的呼应意象
这部电影中马丁·斯科塞斯插入了不少前后对应的情节来强化形式克制背后的内容表达,外在形式上的克制是讲述这个故事的必须,而不露痕迹的意象设立则是表达尽意的重点了。首先是坟墓的意象,更确切地来讲,是自掘坟墓这一行为的意象。片中弗兰克·希兰年轻时在意大利战场拿枪让俘获的两个敌军掘他们自身的坟墓,当时的他还把不能理解,为何那两个人可以自己为自己掘墓。而影片的最后,他友死亲离,他也不得不自己到棺材店,去给自己挑选棺材,这时没有任何人拿枪抵着他的脑袋,但是他也不得不做当年那两个他理解不了的战俘所做的事——为自己掘墓,拿枪威胁他的,是无形的时间,是命运。他以前以命运主宰者的方式强迫别人做的事,自己终将也不得不做,成为命运的被奴役者,这可否也理解成某种宿命的轮回?另外一个意象是门缝,在他去保护霍法的第一个夜里,他见识了霍法睡觉的卧室留门缝的习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行将就木的弗兰克·希兰,让牧师离开时留出一个门缝,影片就在门缝中的弗兰克·希兰的画面里戛然而止。这里两次门缝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一种呼应,理解成他对霍法的悼念。影片中他手上戴着的戒指是罗素所赠,也符合他对于生命中两个重要朋友的纪念见证。但还可以做这之外的理解,尤其是结尾的那后一个门缝。这里的情节背景是圣诞将至,弗兰克·希兰正盼望女儿能前来看他,为这种不可能的事件抱有丝毫幻想,这可以理解为留门意义之一,他心底及其渴望女儿的关心或者说稍微的挂念,以免女儿偷偷来过自己错过,留门缝以长候。次一种理解就是前文所讲,对于自己杀掉的挚友的悼念,似乎如此可以让霍法在某种程度上存续下去(霍法当年的判定结果是离奇失踪,除杀了他的弗兰克·希兰,在世的再无二人知其下落)。其三,则可以呼应起上面的坟墓意象,这房间大抵将是弗兰克·希兰死亡之处,可以理解为终将或者某种程度上说已然踏进的坟墓,他害怕把门关死,也莫过于想证明自己尚在喘息。
(三)减龄特效之外
影片中画面最大特色就是运用电脑特效再现德尼罗和帕西诺年轻的容颜。这也是影片预算一再超出的原因。电影中要呈现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以及2010年以后三个时空,年迈可以通过化妆来呈现,但青春却只能通过数字技术来复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导演自身对时间,对生命的感慨,这种减龄特效的使用,让影片有了故事之外的时间沧桑感的表达。他们的时代已然过去,导演斯科塞斯,加三个主演德尼罗,帕西诺和乔佩西四个人加起来已经三百多岁了。这种故事之外的时间和故事本身呈现时间的沧桑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让人难免有故事之外的感怀。并且从片中技术的处理来看,这似乎是导演有意为之。影片以特效手段复原了演员年轻时的容貌,但体态上的老态龙钟还是一眼可见的。德尼罗修车时候虽中年样貌,但体态的老迈却无可遮蔽,这没法解释为技术不到位,因为完全可以让年轻演员进行肢体表演,再将面部置换。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就是导演有意为之,刻意提醒观众,即或技术能复原样貌,但那年轻也只是怅惘一梦,时代不复便已然是时代不复了,无可取代和找回。因此,特效的使用有了特效之外的意义,建立了一种奇妙的故事内外的互文,让人感喟于故事之中的时间,也感伤于故事之外。影片感喟的时间,时代,孤独,正是马丁·斯科塞斯本人对于自己生命的时间,对于电影的时代,对于现在的无力的孤独感?
四、结语
对于社会深切关注的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绝佳呈现,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创造价值也是其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时隔十余年,他以一部《爱尔兰人》,重归他最熟悉的黑帮题材,算是对他赖以成名的创作起点的回望。但在表达的要旨上,却一反往昔,转向对时间的执着和感怀。不再留恋恣意的表达才华,而转为极度的收敛与克制,在减龄特效的别样处理下,使影片的故事内外产生奇妙的互文,故事之外的现实,似乎更像其表达重点。而当他这一辈也在风烛残年中消亡后,一个时代的印记也将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