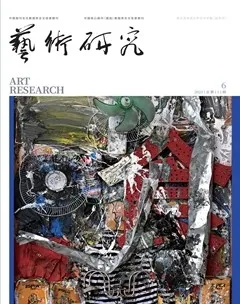《狙击手》:群像叙事、符号表达与类型叙事
江苏师范大学/李 想 新乡学院/曹耀辰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在谈到新主流电影时说道:“新主流电影以正剧题材、精良制作、低起点人物、个体视角、国族情怀、认同想象为核心特征,达成主流价值观、大众国族认同想象的融合,成为重要的电影和文化现象。”纵观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始终存在一条主线,就是特色鲜明的主旋律电影创造,那么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影视理论体系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着革新,从电影《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中所构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到《中国机长》《烈火英雄》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表达,再到《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父辈》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新时代公民话语权体现,不难看出,当下中国的新主流电影发展,其题材更多的是与新时代社会所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这种被大众所接受的主流文化,体现的是创作者们积极迎合时代,主动的创作出反映时代、歌颂时代的电影作品。
一、用群像叙事塑造英雄
“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不再被视为特殊的文化商品,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的工具”。电影从叙事的手段成为了保卫意识形态的武器和工具,从主旋律电影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唯一不变的就是英雄人物形象的背后承载着的一直是家国情怀。从《战狼》《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再到《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悬崖之上》《狙击手》,电影的叙事基本上都呈现出多线多点交叉的表征,必然要依托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串联,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英雄主义电影的核心就是对集体主义的描摹,集体主义就必然要对特定的英勇群体进行塑造,《红海行动》中前往伊维亚执行撤侨任务的海军小分队,《悬崖之上》中的中共地下党和敌特分子的明争暗斗,这种群体的影像化表达都是在个人—集体—国家中对民族形象和英雄群体进行塑造。
(一)启用新演员群体
在电影《狙击手》中,对新人演员的使用更好的契合了张艺谋导演的小切口叙事,在五班这样一个战斗集体中,只有演员章宇被观众所熟知,其余的战士们都是银幕首秀,带着一副生涩的面孔更加贴近史实,同时也给观众一种新鲜的观感。在以往的战争史诗题材电影中,导演们更多热衷的是“数星星”的人物堆砌,各种老戏骨和流量明星轮番上阵,也许是出于吸引更多群体观看以获得高票房,总体来讲,在粉丝经济大行其道的中国电影当下,使用新人演员对英雄人物进行新的诠释,更是技高一筹。抗美援朝战争是青春的战争,电影《狙击手》也为了更好的凸显“青春的战场”。新人演员的加入带来的生动感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正当年少,将这种纯粹感融入到电影叙事和人物刻画中,带来了普通真实的志愿军战士最壮烈的牺牲,这种双重概念的“无名”,却满是力量,虽是新人,但演技却不新,为塑造真实的中国志愿军狙击战士形象,饰演“狙击五班”的年轻演员们提前半年进行封闭训练,从体能、格斗、射击等军事素质各方面严格训练,进行体质、心智与意志的多重磨炼。
(二)冲突双方的群像刻画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需要真实的故事来支撑。在《狙击手》中,五班战士拯救战友的故事就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中“冷枪冷炮”的神枪手群体事迹改编而来。狙击手五班奉命执行解救前线情报员亮亮的任务,班长刘文武带领他的同乡娃儿们即刻奔赴战场,导演将镜头对准敌我双方,在冰天雪地里冷静克制的呈现一场厮杀,作为我国第一部专注描摹抗美援朝战争中狙击手的电影,对每位狙击手的形象刻画是决定影片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后续展开阻击战中,每一个狙击手的牺牲,都有一定的道理和章法,以人换人的班长刘文武,在死去的最后一刻还在向敌人扔着手榴弹,背着铁板搭救亮亮,在牺牲时还在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起名字的胖墩,遭敌人枪击还不忘提醒战友莫暴露的高军,张艺谋将每一位牺牲的英雄们遇难的过程直观地表达出来,目的就在于让后辈们记住,只有这样,我们更能体会到在抗美援朝中战士们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精神。
不同于以往电影中对英雄人物“脸谱化”的描摹,《狙击手》中对战士们的形象塑造则尽显平民化,班长刘文武和战士们更多的是平等的交流对话,扮演的是一种引导的角色,而不是发号施令的导师形象,这就有利于打造一个团结向上的英雄群体,纵观近些年来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这种导师的形象设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主多从,在《悬崖之上》中,为了秘密执行“乌特拉行动”,在由共产党特工组成的人物小队中,分成了两个行动小组,经验丰富的张宪臣自然就成为了决策者,带着王郁、小兰、楚良进行营救任务。由于经验的问题,在一个团队里面更多担当的是决策者和领导者的形象,其他的成员只有执行权利,另一个就是组织领导,《1921》《革命者》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刻画,甚至可以回溯到《战狼》《红海行动》中对营救任务的安排和领导,但是在《狙击手》这部电影中刻画的更多是整个群体,导演叙事的视角就是单一场景——战场,固定时间——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所以在围绕如何突围,如何撤退等重大问题上都是班长和战士们进行沟通交流完成任务。而在对于美军阵营的刻画上,导演并没有刻意丑化、妖魔化美军,有别于早期中国的战争电影中对于敌对势力的夸张的丑化,近年来的新主流军事电影中,更多采用了客观的表达,从人物刻画到整体形象,从纯粹的残酷无情的侵略者,丧失人性的杀人狂到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梦想的敌对阵营中的“普通人”形象,相比于直接扁平化的设定,这样的形象刻画使得新主流电影中的“反派”更加圆满。
二、用符号表达建构意象
“对于电影作品来说,所有的细节、节奏、画面都应该指向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既是电影叙事的整体,也是指电影美学的统一性,好的隐喻式叙事与电影本身一定是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机构整体”。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这种电影叙事和电影美学的统一性体现的尤为明显,运用某种特殊的符号作为影片的意象建构方式,以便传达出导演的特定思想,符号化的表达也可以使得电影的故事讲述增加更多语义的延伸,但是导演的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也不能过于强调隐喻式符号的塑造形式,更应该有一种“以小见大”的观念来引导电影的创作。
(一)物象符号
随着电影符号学的诞生,电影理论由经典电影理论时期进入到现代电影理论时期的新阶段,在符号学家建构的符号化的世界体系中,基本上所有的物象都有着一定的指示意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是由代表价值意义的叙事和代表功能效用的物象构成。物象是真正具有电影化的表意元素,也是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重要特征。在《狙击手》中,雪和望远镜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物象符号体现的就是这个含义。
1.雪
白色的雪和灰黄的土、鲜红的血构成了凄凉残酷的美学风格,在战场上,雪是覆盖在灰黄的土地之上,在弹坑和地道,这些所有战斗过的痕迹。《悬崖之上》是四个字:雪一直下。很有诗意的感觉。这次我觉得不要下雪,地上有雪就够了。在影片表达青年狙击手们牺牲的场景时,地上的雪就显得更为纯洁,导演将雪的“无生气”和血的“有生气”进行有机结合,巧妙的隐喻了在寒冷的朝鲜战场上,五班狙击手营救任务的无比艰辛和战胜对面战壕中的美军力量的来之不易。
2.望远镜
在电影《狙击手》中,破旧的望远镜既是用来侦探敌情的唯一工具,在电影中出现了很多次,也是在影片最后承担起使命与担当的重要意象。“其意义指涉而言,它们既可以是电影中的背景、陪衬,也可以是影片发展的线索,甚至可以是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出现在电影文本中的物象符号,以各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电影的表意”在影片的开头,两名小战士讨论全班唯一一个望远镜给谁的问题,这个时候,望远镜作为的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去串联起战友之间的情谊,而在影片后半段解救被俘的亮亮的时候,班长刘文武选择以人换人,将唯一的望远镜送给小徐,这是任务的交接,是英雄之间的牺牲和成长。
(二)色彩符号
纵观张艺谋所导演的电影,视觉奇观一直是张艺谋的拿手好戏,其在色彩方面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张艺谋式的美学艺术,无论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还是《影》《英雄》等影片,无不展现出了张艺谋突破传统电影对色彩的局限,敢于寻求色彩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从而进行艺术表达的魄力。在《狙击手》这部电影中,张艺谋用国画的风格描绘了一幅萧瑟惨白的战场画卷,以血红和雪白的强烈对比,凸显出战场上的无情,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战场之上,两方势力进行角逐,导演没有用更多的篇幅去具体呈现所在具体的场景,而是通过人物的交锋和事件的具体发展来展示。其多表达出来的美学意蕴也自然更为深刻。电影的色调使用不仅营造了肃杀的氛围,强化了叙事风格,同时作为图像符号隐喻化的表达,也使得整个影片立意高远。
“符号文本的表意不仅与发送者相关,也与接受者相关”。张艺谋导演之所以选取了一个不同于《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宏大叙事,而是选取一个小切入口去对朝鲜战场上的狙击手形象进行刻画,也是着眼于受众的接受域,2020 年是抗美援朝战争70 周年,以反映抗美援朝精神为主题的一大批影片纷纷上线,而张艺谋导演却能够从千篇一律的叙事体系中跳脱出来,敢为人先,使得《狙击手》可以达到一叶知秋的高度,也是充分考虑了当下受众的审美疲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张艺谋在影片的符号文本设置中下足了功夫,青年群体的狙击手英雄,势均力敌的两方势力,单一事件的完整描述,战争题材的技术化表达,将艺术思想、精神追求和市场表达进行有机融合,让当下的中国观众对英雄主义,对抗美援朝精神有一个新的体会。
三、用牺牲与成长来加强类型
作为一部战争片,唯一的主题就是反战,在生与死之间展示势均力敌或者敌强我弱的较量,通过对人物美的描写,再在之后进行摧残来体现战争的残酷无情,从而达到宣传名族英雄,发扬名族气节和反战的目的。不同的是,在此之前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大多都把满足意识形态的需要作为最主要的主题表达,往往或忽略了个人情感的流露,在《狙击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导演将五班战士们的家国情怀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在对五班这个小集体进行具体人物画像时,导演用一种类型加强的策略进行艺术化的塑造,青年狙击手们在牺牲和成长之间完成任务的交接以及灵魂的洗礼。
(一)老英雄的牺牲
在《狙击手》中,电影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老英雄的牺牲,另一个就是新英雄的成长,在对班长刘文武的人物塑造上,导演通过两个侧面进行描摹,这个侧面是通过敌我双方的角度,一个是对面战壕中的美军力量,主要策划者将亮亮作为人质的目的也是为了生擒刘文武,在美军看来,刘文武是一个战无不胜的神枪手,从一开始,刘文武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人出现在银幕中,这也为在后续的影片发展中掌握话语权作了铺垫,而这种话语权的掌握不是一种绝对命令,而是和五班的战士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局和生死攸关的战斗中进行体现,而刘文武也更多地以长兄的形象出现,不同于以往领导者的训诫和指挥,班长的话语以一种趣味的“调侃”进行表达,在战士小徐被炸掉下半身将要牺牲时,班长为了让他减少痛苦,说:“震麻了,脚板还在,雀雀还在,还雄得起”,在教大永用勺子的反光面测距时,更多的也是鼓励和肯定,在最后的牺牲段,班长为了成功营救亮亮和减少五班成员的伤亡,毅然用自己和人质进行交换,在交换之前还在教大永如何突围,这种教导是一种任务的交接,是身份的传递,这种传递是一种力量,是爱国主义的高扬。
(二)新英雄的成长
《狙击手》打破常规的挑战源于剧作的创意和稳健,按照导演张艺谋和编剧陈宇的设想和追求,即在一个几乎封闭的时空中,不依靠外力,只通过故事的内部矛盾形成的张力推动故事叙事。导演对于大永的人物设定就是作为这个内部矛盾存在的,全片观众对大永的印象就是由一个爱哭鼻子的小战士成长为能够担当大任的新英雄,得知同乡的亮亮被俘会哭、战友牺牲会哭、班长批评会哭,而大永的成长正是在这种哭泣中完成性格的塑造和缝合主题的表达,作为一个四川娃儿,在班长的带领下到战场上和美军进行厮杀,这种成长具有双向性,一个是班长刘文武的指导,一个是大永自身的领悟,在集体与个人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简约的空间里,大永凭借着一个勺勺完成班长交付的营救任务,成功地将亮亮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交给上级,成全了集体同时也塑造了个人的成长。
班长的牺牲和大永的成长,在生与死之间,完成主题的升华,时间固定,剧情集中,将这种成长叙述的主题巧妙的串联起来,导演用“点名”的方式将五班的精神永固,开始的班长点名,五班全在,后面的点名,只有大永一人,但其他士兵的喊到,真正的将这种缝合主题所呈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完美地表达出来,仪式性的营造升华主题——五班精神永在,老英雄的牺牲和新英雄的成长,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影片长度中,给观众带来的是具有“中层工业美学”的视听盛宴,以及对前仆后继,英雄杀敌的志愿军战士们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的感慨。
四、结语
在电影《狙击手》中,导演张艺谋摈弃宏大叙事体系,淡化背景,着重对“人”的描述,为我国的战争题材影片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群像叙事和成功的电影符号学的运用,在满足了商业性的同时也不失独特的艺术表达,迈出了新主流电影成熟化和走出形式固化的重要一步。在这样一个电影工业稳步发展、艺术与商业融合逐渐走向成熟的时代,中国新主流电影从国内市场的成功走向国际,在国内导演积极探索、勇敢尝试和党中央大力支持下,也许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