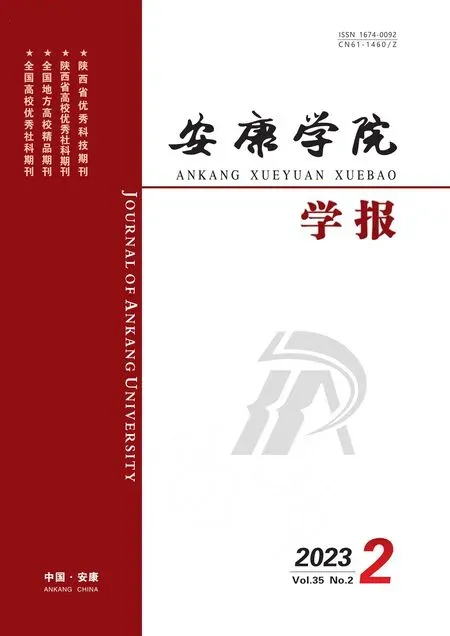克里斯蒂娃的主体间性建构及其理论贡献
王 若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是法国保加利亚裔、犹太裔哲学家。从1965 年至今,克里斯蒂娃的学术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是克氏理论创构的初始阶段,此间她提出了文本间性理论;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克里斯蒂娃借鉴精神分析学,创建了符号分析学;八十年代之后,克氏以文本间性和符号分析为基础,将致思论域扩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致思论题也由“文本与性的政治”转向身份政治、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治[1]。克氏论著看似并非系统化独成一家,但其不乏内在的关联和连贯性,其论思宏旨是关于主体性的,其思想脉络是他异主体性承认、主体间性建构以及主体间性观照下的西方主体性重构。
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为“间主体性”“交互主体性”,是“一个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概念,指涉人们之间的心理关系,通常用来强调人的内在社会性,与唯我论个人经验相对”[2]。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思想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拉康、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思想精英的着力开拓和推进下,经过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致思建构,渐成表征西方文化自觉的显性思维。
克里斯蒂娃作为广涉文本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多产学者,在主体间性创思建构方面也卓有建树。在笔者看来,克里斯蒂娃从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渐次展开的主体间性建构,有着独特的论思进路、内容特征和理论贡献。但是迄今国内学界关于主体间性的研究,却鲜有论及克氏,更缺乏对其主体间性之思的耙梳。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克氏的文本间性理论和符号分析理论,力图厘清其主体间性的建构脉络,进而阐明其理论贡献。
一、文本间性:社会层面的主体间性
1965年克里斯蒂娃作为保加利亚公派留学生来到巴黎时,法国学界盛行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致力于探究与人类相关的诸种事象内部的结构,并将其作为本质和规律加以把握,代表了西方文化的理性崇拜和科学追求。但是,结构主义不仅抛弃了历史和变化这一坐标轴,而且取消了人类作为主体的活动余地;不仅表征着现代社会规则和秩序对人的主体性的压抑,也意味着西方文化对非西方的错认(misrecognization),因为结构主义在搁置主体的同时回避了对近代以来笛卡尔式我思主体的批判和反思,实际上放任了西方理性文化的霸权横行。的确,克氏身为异邦犹太裔女性,在法国这个被认为思想自由和文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里,仍然深深感受到异国、异教、异文化和“第二性”所遭受的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不公。因此,克里斯蒂娃怀着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和革新的学术志向,开始思考主体性究竟如何体现的问题,将结构排斥的东西、创造结构的东西和破坏结构的东西等结构外部的物象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历史和社会的视域下探讨主体,从而开启了她的主体间性建构。
克氏选定文本作为其主体间性建构的切入点。传统文本概念,主要指文学文本,即一个被书写的语言材料填充的完结的、闭合的符义单元;结构主义更是宣称,正是文学文本的封闭性才使人理解了作品的结构,从而把握作品的本质和文学的规律[3]75。在这个封闭的结构主义单元中,实际上作者对文本意义的制造和传达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和中心性。在克氏看来,这种以封闭性结构为核心的传统文学文本,大大减弱了文学应有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活力。于是,克里斯蒂娃在阐释俄国后形式主义代表人物巴赫金(M.M.Bakhtin)的文本“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当时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言说概念——“正是在(预设了对话关系的)语言中人类把自己建构成了主体”[4],坚信人只有在对话中才实现其主体性,于1967年提出了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互文性”或“间文本性”。
克氏文本间性包括三方面的意涵:其一,文本的引文依赖性和立体涵涉性。文本不但意指其他文本,而且的确包含其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证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5]72引文来源广泛和立体涵涉,被引证的文本不仅包括可见的文献、典故和流行语,而且还包括历史传统、社会习俗和意识形态等“无形的资源和影响”。历史文本与当代文本一并参与构成新的文本,所以文本间性理论将文本的历时性或迭代性(Iterability)关联纳入共时性互嵌之中,“互文性把先前的或同时代的话语转换到交流话语中”[6]91。其二,文本之间辩证否定。文本既互涉互构,又互相否定和消解,“在具体的文本空间中,来自其他文本的若干表述彼此交汇、互相消解”[6]91。文本对他文本的引入不是进行简单的摘录和仿写,而是予以否定辩证性回应。换言之,他文本和文本在文本场中作为对立物并置,即巴赫金所说的“双值性”[7]14,在矛盾和交互中生成新的文本和意义。文本在平等对话、交汇融合、参与生成新的意义的同时也消解了各自的历史和存在,新文本的诞生也意味着文本和他文本皆已消解。其三,文本的生产性。文本总是迭替在场,与其他文本在否定性对话过程中参与构成新的文本,所以不存在某一完结、恒定的文本,“文本会永无休止地运行下去”[3]81,此谓文本的“生产性”。
在文本间性话语里,不但他文本、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被引入文本之场,而且作者、读者乃至一般人也被广泛地文本化。在克氏看来,人是互文性的行为者,她本人身上集合着异邦、异教、异质文化和族群的交互和对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互文工厂”。所以,文本间性概念虽然阐释文本和他文本的关系,揭示一切文本的生产机制,但关注的却是主体和异质的他者的关系。借助文本间性,主体将他文本、他文化、他人等一切他者接纳并与之对话,文本成为主体与异质的他性主体的对话之场,所以克里斯蒂娃将间性文本称之为“超语言装置”。这个语言学概念,承载了如此深邃的思想意涵,实质上表达的就是哲学领域中的主体间性,正如日本学者西川直子指出,文本间性就是迁移到文本层面的主体间性,即“不同的复数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的场被打开的事实”[8]59。克氏这种在语言学领域探讨哲学问题的研究路线,与她所尊敬的本韦尼斯特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领域探讨主体问题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这也反映了结构主义在法国盛极未衰之际克氏等学人探索创新和突破的微妙心态。当时结构主义在法国尚如日中天,克里斯蒂娃不可能完全撇开结构来探究主体问题,认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认为这是基础性的)可以用来处理主体问题”,于是“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原译,即本韦尼斯特——作者注)的方式,把它(文本间性)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3]76。
但是,文本间性对主体理解的创新性和革命性足以令人刮目。文本间性理论所阐发的主体间性,消解传统权威主体,将主体多元化、间性化、动态化。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文本间性使得作者成为匿名者”[3]81,作者的位置因为文本间的对话而虚空,取代传统作者的是多个文本的作者之间的对话。在异质、多元的文本空间里,文本的作者和读者在文本辩证互动中形成永不停息的主体化/去主体化。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随着文本被其他文本否定和解构而退场,而其他文本的作者主体又同时登场。所以,传统文本中作者对意义制造和传达的权威性和中心性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读者在文本场域进行跨越时空的意识对话和身份互构。可见,文本间性所演绎的主体间性,彻底地将自我置于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之中,将主体置于间性关系之中进行理解。
克里斯蒂娃通过改造和扩展文本概念的内涵和边界所建构的主体间性,有助于促进当代西方承认其文化整序化成形中所排斥的他者、他群体、他文化,将关注和思维的核心从作者所表征的自我主体、意义独占、西方中心转向读者所代表的他者主体、他文本依赖、非西方互动,因此对西方社会反思和文化自觉意义重大。对此国际学界首位专门研究文本间性理论的学者艾伦(Graham Allen)有确当的评价,“文本间性显然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术语,因为它使得这些理念不证自明:现代文化生活中的多样性,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5]169。
二、符号分析:个体内部的主体间性
20世纪七十年代以及之后,克里斯蒂娃继续沿着多元主体间性的路线进行主体性探讨,但侧重于“言说主体”,聚焦人的“内在”言说(意识),旨在通过剖析主体生产的前生产,追寻主体构建的源动力,以还原主体性生成的完整过程。克氏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中对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性考察;采纳精神分析学理论,揭示意识生产并进入交流关系之前的前生产场景,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相交叉,创立了符号分析学。
在符号分析学中,克氏在文本场域将意义生成的剖面切开,提出了相对于符号态的前符号态,指称个体内部异质的非主体、非意义因素。前符号态的异质因素与符号态的意识命题和逻辑判断虽然二者对立,但同样出现在文本之上。克氏由此发现了个体内部的主体间性,主要意涵包括:
其一,身体性他异的物质性、主体性和革命性。人作为“言在”(言述主体)而非“思在”(“我思故我在”),受到语言结构的必要规范和约束,但还有一个诉求自主运行的无意识世界,“在那里汇聚着我们的感性需求和情欲冲动”[7]22。人出生后经过俄狄浦斯情结的地狱般的挣扎,因为阉割恐惧变成了一个社会化自律的符号态的主体。人变得理性、守规则和尊重秩序,但身体性的永恒欲动并未熄火。“我”主体就是自我与陌生的他者——欲动——的矛盾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一个分裂的悲剧主体:既是理智主体,又是欲望主体;既是历史与社会、文化的主体,又是物质的身体性主体。
基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死亡欲动理论,克氏指出来源于无意识的欲动是有着自主运行逻辑、表现为“无政府性”的否定性力量,这股带着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他异力量,将破坏活动导入“内在”言说(意识)中,使另类的语言活动、排斥性的文本出现,从而制造出“言说的破裂”,使意义非意义化、使人非主体化。身体性破坏作为原初驱力运行不息,使作为意识命题性的主体在破坏和压制、冲击与稳定的调和中不断更新和再造,形成了人的去主体性和再主体性矛盾运动,亦即动态主体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康也曾指出动态主体性就是欲望主体的主体性[3]84。但克氏阐发的身体性他异主体相比拉康有着更积极的意蕴,身体性欲动在破坏和解构的同时表现为一种革命的推动力和创新的原动力,既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也是一种建构性驱动。
其二,个体的内在对话性或内部主体间性。克氏基于承认言说主体的命题性质和逻辑判断性而试图深入研究命题和判断生成中绽露出的、使其变形的异质性他者的形态,而不像德里达那样的解构主义者彻底否认人的主体性和自我的超越性。在克氏的符号解析话语中,符号的指意规则并未被全面取消以追求摆脱任何所指所带来的愉悦,而是在其多元文本空间里,仍存在必要的叙事结构、语法和逻辑。换言之,结构的合理性、法则的规约性和秩序的必要性仍是被承认的,自由主体必须“自由地”遵守法律,“即使是俄狄浦斯法律”[10]42。身体性的无意识主体,显明为一种具破坏力、变革性但同时被掌控、被压制的主体,言说主体就是以一种被掌控、被压制并具破坏力、变革性的他异力量为核心,在身体性和理性的交互作用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主体。因此,在克氏看来,人的身体主体性和意识主体性的内在辩证关系是一直存在的,或言之,对话把人的身体主体性和意识主体性统一于一身。
其三,现代主体的脆弱性。在精神分析学发现“自我之异”之前,西方现代文化一直是以一种压制性的“我思”主体为中心,前符号态的身体性主体被理性主体所杀害。在克氏看来,身体性的、欲动的、物质性的他异主体被杀害所表征的内部主体间性自觉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令人讽刺的悖论:看似无所不能的理性主体,因为对自我之异的陌生和恐惧而暴露出人类自身的脆弱,即自我认识的障碍和面对异己的困难,而走向了主体性危机[10]114。反映在个体身上,“不安的陌异感”可能导致个体精神病症状的出现;在社会层面,人们在遭遇异族、异邦、异文化时,往往惶惶然表现出隔绝和排斥的心态和行为趋向。所以,所谓我思主体实质是缺失内部主体间性自觉的脆弱主体和虚假主体。
符号分析学对前符号态的发现、对潜意识与意识对话的阐发,“打开了主体内在哲学的新篇章”[11]20。通过聚焦言说主体、剖析人的“内在”言说(意识),展示身体无意识的主体性、革命性以及与意识的对话性,完成了个体内部层面或“自我哲学”的主体间性建构,从而呈现出更为完整的主体性生成过程。人作为言说主体,其主体性的实现,不仅通过外部言说即社会性对话,而且有赖于内在言说即自我对话,对话是主体的普遍和永恒属性。正如法兰西学院教授海然热(Claude Hagege)所指出,“如果还存在什么普遍性的话,那么真正的普遍性是‘对话性时刻’,正如很久之前的儿童的体验所表明的那样”[12]。
符号分析学所证成的个体内部主体间性,深化和完善了文本间性所演绎的社会层面的主体间性。在文本间性理论中,克氏消解作者所表征的权威性主体、完结性意义的致思努力,被认为建构了“无主体”的主体间性,因而凸显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旨趣,以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Ihab Hassan)将文本间性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3]。而在符号分析学所建构的个体内部的主体间性,一方面,他异的身体性主体被彻底解蔽,被赋予完全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或破坏性的挑战目标直指符号态所表征的结构、规则和秩序;但是另一方面,克氏也认识到身体性主体的革命性给社会规范和国家标准带来的冲击甚至震动,所以将这种存在于主体内部反抗规制的变革乃至颠覆秩序的力量导入对话和互动的社会关系之中。可见,个体内部的主体间性进一步显明主体的对话属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物质性他异的主体性、革命性或创造性;既一脉相承地消解和颠覆我思理性主体的中心性,也消弭了文本间性理论所带来的“无主体”非议。
符号分析学所证成的个体内部主体间性,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无疑促进了现实政治中被压抑者的复归,非理性因素、非结构物质、非西方文化的主体性承认,因而有着强烈的、普遍的政治进步意义;同时也因为揭示了现实世界里广泛存在的群体间排斥和共同体分裂的内在根源即他异主体的遮蔽和内部主体间性自觉的缺失,因而为破解西方主体性危机提供了思想启示。
三、理论贡献
克里斯蒂娃通过文本间性理论、符号分析学所建构的主体间性,将一元主体碎片化,承认一切被排除的他异物质、力量和文化的主体性乃至革命性,证成主体多元异质化、间性化和动态化的主体间性。可以说,克氏建构了外部社会和内部自我两个层面的主体间性,或曰社会哲学与自我哲学的主体间性,凸显了多元异质、他者承认、辩证互构与动态的主体性。克氏构形的主体间性,对于西方的主体间性自觉和再主体性创构,有着独特的理论贡献,择要而言:对现象学、存在主义主体间性的实质性超越,对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体性理论解困和对精神分析学的颠覆性发展。
首先,对现象学、存在主义主体间性的实质性超越。现象学创始人、奥地利哲学家胡塞尔首开主体间性之先河,最早在认识论领域提出“主体间性”,但是他以先验“自我”为基点,通过类比的统觉构筑了他人的主体性。海德格尔试图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共在”澄明中,证成本体论或存在论的主体间性[14]。但是,海德格尔的“共在”与胡塞尔的“移情与共现”一样,都是在自我意识中构建与他人的所谓主体间性关系。他者是与自我同质的存在,甚至仍是自我主体意识的外在映射。真正的主体间性应该是主体之间平等的对话和互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阐发的主体间性最多只能是“互识”的主体间性。
不同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限于意识领域的狭隘主体观和关联同质的他者的主体间性观念,克氏沿着与胡塞尔逆向的思路展开溯源,以超语言装置的文本作为思考对象,使主体下沉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与异质的他者并置与互构。通过符号分析,发现自我之异的物质性、主体性和革命性以及主体的内在对话性,进一步将主体异质化、间性化、动态化,证成“互构”的主体间性。如果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逻辑是“(我)主体映射间性”,那么,文本间性和符号分析学所演绎的主体间性思路就是“间性产生(我)主体”,在此逻辑中他者的异质性、主体性、革命性或创造性被凸显,他异的主体性得到真正承认。所以克氏的主体间性实现了对现象学、存在主义主体间性思维的“逆向性”和实质性超越,正是在此意义上,克氏说“间文本性取代间主体性,并清除间主体性”[8]59。克氏的主体间性建构也与拉康、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的主体间性理路判然有别,之间的构思歧路比较,将另文论述。
其次,对后女性主义女性主体性理论困境的破解。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引入了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等新兴理论,将女性主义政治主张、社会诉求与其融汇合流,发展到后女性主义阶段。但是,后女性主义在获增新的活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因后现代主义的介入而使后女性主义陷入一种新的理论困境: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男性主体霸权的同时,也在消解渐趋确立的女性主体性;当妇女刚刚登上主体的位置,后现代主义就宣布主体的退隐[15]。
克氏的主体间性建构主要针对以理性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意义、真理等概念和男性霸权为中心的规则、秩序的批判而展开,并没有像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样完全消解主体和否认其超越性,而是通过追溯文本、意识、主体的生产,澄明了读者、身体所表征的他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而将言说主体异质化、间性化和动态化。实际上,克氏由个人他异经历放眼欧洲乃至全球场景,对源于间性思维、对话意识缺失而造成的群体间排斥、社会撕裂和共同体生态恶化深为关切,所以终其一生都在为他异主体性被承认而呐喊和抗争。在诸多他者中,女性的主体性尤其引起克氏关注并着力颇多。克里斯蒂娃借助精神分析学,指出传统宗教和现代文化所压抑的妇女情欲中包含独有的对他者的爱欲,母与子(孩子是第一个他者)之间的关系,闪现着最初始、最本真的人性光辉,是灵长类动物人化的根本驱动,女性主体性就是“爱的主体间性”[11]101。女性主体性的承认、释放和弘扬,不仅可以激活女性的自由与创造力,而且对男性的主体性实现也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克氏建构起一种创造、包容、成就一切他异主体包括男性主体的女性特质主体性。这种女性主体性,既改造和超越传统的男性主体观念,又抵御和免除了后现代主义对主体包括刚刚崛起的女性主体的消解;不仅具有人文主义的母爱伦理,还是一种创造、包容、爱他人的精神特质。
最后,克氏主体间性对精神分析学的颠覆性发展。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被拉康接受之后已经有所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欲动理论虽然对于驱力与本能做出了区分,但是其死亡驱力还是与生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性的发生归因于父性生物性即阉割恐惧。拉康与弗洛伊德有所不同,其理论视域中的驱力不是生物性需求,而是自我追求与外在父权秩序之间永远无解的冲突,人的主体性形成源自自我冲动与父权秩序之间的张力、自由与自律之间的矛盾统一。拉康的主体性建构虽然从生理解剖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但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剖析一样都局限在俄狄浦斯阶段,都与父性关联,女性只是必不可少的配角衬托。
克氏为了探讨主体性生成的更完整的过程,采用符号学的视角锐意探讨前符号态的场景、前语言的意指活动。克氏采纳了精神分析学的欲动理论、拉康的主体理论,但是将主体性生成的探讨追溯到“前俄狄浦斯阶段”,打开了主体生产的前生产母性空间。克里斯蒂娃借用柏拉图的“子宫间”这一概念,指称律动的、前意识、前逻辑、非对象化的母性空间。这个混沌未形的母性空间正是主体性生成的空间,“是在父亲登场以前的舞台上起作用的力量”[8]107。可见,克氏通过发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空间以及对主体性产生的影响,证成女性的特殊主体性,并且表明人的主体性更本真的源头是“母性—诗性”,而不是“父性—逻辑”[16]。这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版本的精神分析学不能不说是一种颠覆性的补充和发展。可以说,克里斯蒂娃正是通过将符号学中的前符号态勾联并融通了精神分析学中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形成了她个人特色的符号分析学,也是“克氏版本的精神分析学”[17]。
四、结语
克里斯蒂娃关于主体性的思考,是沿着与胡塞尔逆向的思路,将主体沉降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领域展开的。克氏发现了被我思理性主体所遮蔽的他异物质性主体及其之间的辩证互动,将主体还原于间性主体关系之中。克氏因此建构了社会外部和个体内部两个层面的主体间性,或称社会哲学、自我哲学的主体间性,呈现了更为完整、更为立体的主体性生成机制,显明多元异质、他者承认、辩证互构与动态的主体性。克氏主体多元化、间性化、动态化的主体间性理论的形成,实现了对现象学、存在主义主体间性的实质性超越,对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体性理论解困,对精神分析学的颠覆性发展。克里斯蒂娃的主体间性致思在西方主体间性思想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克里斯蒂娃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地对西方现代文化整序和形成中被排除的异质的他者重新定位,而且从中汲取可能反哺甚至拯救西方现代文化的力量。克氏的他异主体性抗争和主体间性建构,带有并不隐讳的自身经验色彩和欧洲主体性的特别关照。作为“一个永远处在一种非典型的压力之下的非典型人”[11]3,克氏的论思光谱从个人他异境遇延伸至“欧洲主体的危机”,由他异主体性抗争、主体间性建构发展到西方主体性重建,因而也招致了自我倾向的嫌疑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非议[10]29。另外,在克里斯蒂娃所属的法国先锋派其他成员如福柯、德里达的影响下,其论思创构多采取颇为相似的消解和颠覆理路,“有时甚至对所说主题采取无序的方式论述”[10]43,以至于其思想传播开来后被有些学者划归后现代主义阵营。后现代主义“解构有余,建构不足”的致命缺陷以及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光环遮掩,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克里斯蒂娃本人的知名度及其主体间性思想的影响力。但此类争议和解读并不足以影响对克氏主体间性致思努力的整体肯定,其思想脉络和理论价值也值得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