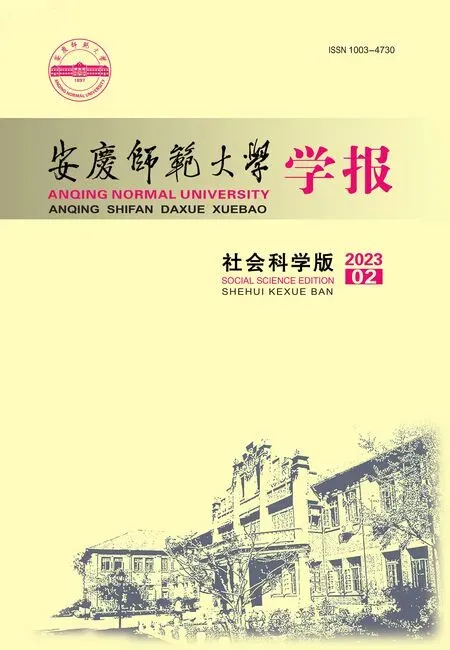方以智与明清之际“格物致知”论的转向
汪孔丰
“格物致知”概念出自《大学》,自西汉时期《大学》编入《礼记》并被推尊为儒家经典后,延续至唐代,其间先哲对“格物致知”的阐释众多,殆以道德修身为主。然自宋明以降,随着理学与心学的崛起,“格物致知”的内涵阐释出现了分歧,大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向:尊程朱派主要是向外求格物以穷理,趋于实;崇陆王派主要是向内求心性以致知,趋于虚。这两者各有偏至,亦各有不足。至明清之际,这两种不同的诠释思想,呈现出明显的融汇贯通的迹象,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学术和学风的发展局面。这种融通态势,在明末清初桐城文人方以智的思想世界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他认为“格合内外,则心物泯也”(《一贯问答》),提出“格物”之“物”不仅有内在心性之义,也有外在物理之义。如此理解与阐释,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余英时曾管窥方以智晚年思想,较早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指出晚明理学家之中,“亦有少数杰出之士,于传统格物之说别生新解,而渐扩大其范围至于天地万物。密之即闻此风而起之佼佼者也”。他又认为方以智未囿于家学与师传的影响,提出的“质测之学”实为格物致知的新解,更指出方氏“诚不愧为中国科学思想史上之新机也”。不过,余先生也强调“晚明诸老,修正宋明儒统,其言有甚峻烈者,然早年染涉既深,心习难涤,故言思之间并不能尽脱旧缚。此亦治思想史者所不宜忽视之点也”。对此,方以智也不例外,其思想中仍有心学熏陶的痕迹,“故密之为质测之学,其含义有极新颖者,然观其通几之说,则又往往依违于儒家格物致知之旧贯”。
嗣后,杨爱东《方以智对传统“格物致知”论的突破》、廖璨璨《方以智的“格物穷理”说及其对明清之际西学的回应》、孙显斌、王孙涵之《方以智〈物理小识〉与近代“科学革命”》、田智忠《一在二中与即用是体——方以智对理学的回应》等文,在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对方以智“格物致知”论的阐释。
本期刊发的《“格致”新说:方以智对传统“格物致知”的贯通》,重新思考了方以智的“格物致知”论。论者认为,方以智面对晚明“崇虚尚无”学风与西学东渐的冲击,基于圆∴的哲学理式,在“格合内外”“心物互格”“不落有无”三个层面重新诠解了传统的“格物致知”说,他在“物”的外延上赋予了西学物理知识,在内涵上融合了外在物理之学与内在心性之学,这就沟通和消解了传统“格物致知”说中的理学与心学之争,体现出鲜明的贯通与超越的思想面向。
需要注意的是,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指出方以智的思想存在“早晚之异趋”的现象,“早年崇实而不甚言虚,晚年蹈虚而仍不废实耳”。由此推之,方以智格物论中的“外在物理之学”与“内在心性之学”,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侧重的。然而,这方面情况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故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此外,方以智提出的“格物致知”论与明末清初学术、学风的关系,当前研究仍不够充分、不够深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相关成果络绎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