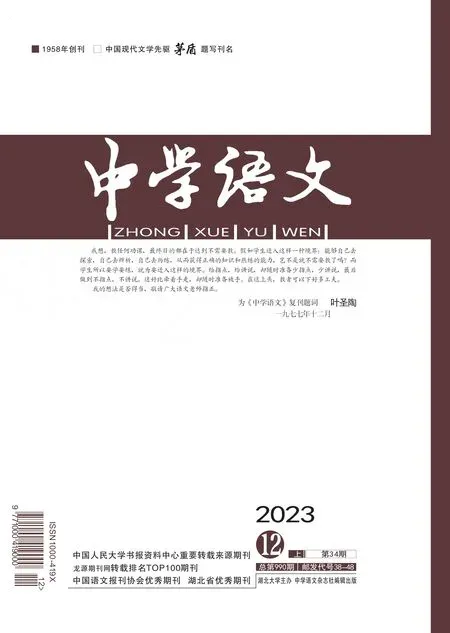吟诵语音与情感表达的理性思考
温育霖 高宇璇
2022 年发布的新课标强调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要求学生认同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1]近年来,关于传统诗词的一些课改实践和电视节目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说明古诗词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间仍有一定热度,可以通过创新形式来传承并弘扬。
不少教师进行诗词吟诵的创新教学实践。然而,不少人过度抬高了吟诵时语音的作用,甚至有所附会。例如,有观点认为平水韵中的东冬韵适宜表现庄严的神态、深厚的情感和宏壮的气概,阳江韵给人以洪亮、浑厚的感觉,适宜表达豪放、激动和昂扬的感情等。[2]不过,“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3],这样笼统的感觉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在历时(不同朝代的语音)和共时(不同地域的方言)上都能成立吗?这几个问题如没有科学、理性的解释,却要学生接受吟诵时“音韵铿锵”“音乐美”之类抽象的描述,恐怕是不妥当的。
诚然,在文学本体上,语音是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应被过度重视。语音的部分作用可以通过专门学科解释,另一部分作用则是抽象的,下文将对前者进行探讨。
一、语言符号的几个特点
1.任意性
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符号系统,语音则是这种符号系统的载体,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即某个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4],只要某个语言社团的成员都认可用某种声音符号去指代某件事物,它们就产生了联系,且这种联系大概率是找不出道理的。这个现象可以在不同的汉语方言和语言中得到印证。以“书”这种事物为例,汉语普通话说shū,英语说book,德语说Buch,日语说hon(本)。至于动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这种情况则更为明显。
这种任意性,在汉语里通常被称为“约定俗成”,是由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任意并不是随意,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要建立联系,其关键是得到同一语言社团成员的认可。语言中也有一些现象不符合语言的任意性特点,这种情况被称为相对任意性,如由象似性、理据性等引发的语言现象。
2.象似性、理据性
模拟猫的叫声,汉语是miāo,英语是mew,语音上有所接近;模拟人的大笑声,汉语是“hā”,英语是ha-ha。这一类拟声词都是以本族语最接近的音节去描摹现实存在的声音,由此成为合法的语言符号。不过,赵元任也指出,“(某些)象声字并不象声……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声音象真声音极了[5]”,这说明拟声词也需要同一语言社团成员认可才可以成立。
语言有依据可循的还有理据性。朱晓农发现汉语方言中的小称变调可以与生物学的“高频声调表示体型小”的说法联系起来,从而能够解释女国音、“美眉”及一些肢体名词、亲属称谓在古代读上声等现象。[6]这一类语音具有象征意义,属于音征词。如李清照的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共14 个字,加点的10 个字的声母在中古时期都相当于普通话的舌尖声母s 或c。频率极高,听感尖细,表示柔、弱、小的感觉,能够引起听者的怜惜、疼爱。
此外,人类的不少语言在称呼母亲和父亲时,其辅音总是与唇音b、p、m 或唇齿音f 有关,元音跟a 之类的低元音有关,如汉语的“母mǔ”“妈mā”“父fù”“爸bà”,英 语mother、father,西班牙语Madre、Padre。这是因为人类最容易发出的元音是a,最容易学会的辅音是双唇音b、p、m。至于唇齿音f,实际上是语音演变后的结果。汉语的f 是遵循重唇变轻唇的音变规律,而英语的f 则是源于原始印欧语格林定律的语音递变定律。这种情况是语言的生理属性所决定的。
王力指出,古代的明母字(相当于现代的“m”声母字,如墓暮幕昧雾霾灭晚冥蒙梦盲)与黑暗相关;阳部字(相当于现代的“ang”韵母字,如阳光朗炳亮王旺昌刚强壮广)与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有关。[7]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本《同源字典》,以古音为纲,利用双声、叠韵的关系以及训诂的根据,将同一个语源的字列举出来,如“理(治玉;治理)”和“吏(治人)”同源,“北”“背”同源等[8]。他还明确指出,古代的声训多数是唯心主义的,没有确切的语言凭据。
由此可见,语言必定是逐步完善的,对一些大同小异的事物或动作,有时候先民会用接近的语音来区别指称,后世随着语音的演变以及词义的引申,又衍生出不同的字音及字形。这一类字就是同源字。这类字的声音如果直至中古时期仍有相近之处的话,那么后世的韵书就会编排在一起,由此给人们一种歧义联想:某韵部字用来表达某类情感。实际上,这个韵部下辖的字必定还有不少与这种情感无关的字,只不过用得少,未被归纳而已。认为某韵部字专门用来抒发某种情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及象似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仍占主导地位,而象似性和理据性处于从属地位。
二、吟诵语音与情感表达
1.语音与情感表达关系有限
如果认为语音与情感表达有较大的关系,即认为语言符号以理据性和象似性为主,任意性可有可无,那么不同的字音就能够用来表达不同的情绪。对于选韵、用韵,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提到:“‘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周济认为“支”“先”韵细腻,而陈少松则与其说法有异,认为先韵各字韵母的韵腹为a,开口度大,且以鼻音收尾,字音比较响亮,给人以悠扬、稳重的感觉[9]。两人之所以说法有异,大概率就是不同语音系统(方言)的影响。陈少松所讨论的是基于普通话语音,而周济很可能是以其时其地的方言(清代吴方言)为讨论基础的。李明孝也认可周济的看法,因为先韵是三四等韵,开口度小,且有介音i[10]。不过,高友工和梅祖麟则认为前高介音i 并无特别的意义,“在古代汉语中一半以上的音节都含有高前介音”[11]。
就取“先”字来看,普通话读xiān,广州话读sin,汕头话读sing,客家话读sen。尽管其语音的源头都从中古汉语的“先”分化而来的,但现代方言的语音各不相同,那么不同方言的使用者对“先”韵的感觉是细腻、宽平还是缠绵呢?
如果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强,而象似性及理据性占主要地位,则某些韵在现代各方言的读法不同,其所表达的情绪也必然不同,那么就相当于否认了诗歌审美体验的同一性——用不同语音系统吟诵,会获得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学体验。但若认为无论用什么语音系统来吟诵文学作品,其所表达的情感都一致,又否定了文学本体需要语言作为载体才能为人们所欣赏的现实。
这一对矛盾产生的缘由是未能考虑每个字的字义及其组合所可能营造的情景、意象和意境。试想,一些老先生用方言吟诵诗文,我们大概率不能听懂他所吟诵的内容,却能感受到他们的基本情感。这种感受必然不是从吟诵中的字音得来的,而是通过吟诵者表情、动作、语调、节奏的演绎得来的。因此,诗韵、词韵中的每个韵部表达什么情感含义,是由韵部内每个字的字义及其所可能营造的情景、意象和意境所决定的,而不是特定语音的堆叠。至于吟诵者要强调字音的作用,很可能是由于个人沉浸于诗歌的美感而情不自禁将这些情感附会于语音,毕竟要呈现诗歌的美需要以语音作为载体。也就是说,字义的组合可以营造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景、意象和意境等形而上的抽象事物,吟诵者通过感受这些才能获得审美体验,但这都需要通过语音作为载体呈现。
2.用韵是诗词抒情的表层媒介
无论是从历时(隋唐往后的各朝代)还是共时(各方言)角度来看,各地读书人读书时用的是各地方言或带有较重方言色彩的官话。作诗词或写韵文时,其平仄及用韵均以一套文学语言为准[12],即后世的“平水韵”,但这种文学语言实际上不是一种活语言,不具备作为口语推广的基础。这可以与老国音来类比:1913 年老国音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除了当时少数的知识分子外,谁也不会说,即便这些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也并不使用老国音。这说明,语音的歧异并不会影响人们的传情达意,也就是说语音与情感表达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更重要的是依靠这些语音及其组合所要表达的字义或词义。
例如,杜牧的《山行》和《泊秦淮》同是押麻韵,韵脚分别是“斜家花”和“沙家花”,但前者表达的是欣喜欢快的情感,后者则是哀伤慨叹;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沈佺期的《独不见》同押阳韵,韵脚分别是“裳狂乡阳”和“堂梁阳长黄”,前者偏豪放、激动、昂扬,而后者则委婉缠绵,孤独愁苦;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均用江阳韵,韵脚分别为“狂黄苍冈郎张霜妨唐狼”和“茫量忘凉霜乡窗妆行冈”,前者豪放慷慨,后者哀怨凄婉。只需留心统计,可以发现同一个韵用以表达不同情感的用例并不少。用韵与抒情的关系是通过归纳得来的,归纳法所推理出来的结论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用某韵既不是抒某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然,从概率上说,用韵和抒情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也是通过作者所想表达的情感及其所选用的字义组合而实现的,不是该韵的语音所决定的,用韵并不能限制作者要表达的感情。因此,作者想要在诗歌中表达的感情是第一位的,通过选用合适的字(字义)来创设情境,构成意象,营造意境,最后通过承载这些字义及其组合的语音表现出来。在选用合适的字时,这些字原来都被归入某某韵中,所以在感性认识上,容易直接将抒情与用韵联系起来,没有看到其本质是选用合适的字所表达的字义,甚至跨过这一步直接与语音联系起来。
文学作品抒情的根本依据是其所营造的意象、意境等,语音(用韵)只是传递这些依据的表层媒介,其本身并非抒情的关键。至于诗词中的平仄,则是编排汉语字调与乐调契合的一种艺术加工手段,也并非抒情的关键,这里暂不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诗词吟诵中的语音并不能直接起抒情的作用,而是由这些语音及其组合所创设的情境、意象和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当然,也有一些音征词可以表达某些特殊意义,但数量有限,且其本身也并不是诗歌表达情感的关键。理性看待诗词吟诵中语音的作用,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遵循的科学路径。
尽管如此,吟诵这一传统的读书方法仍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弘扬、探讨。在现行中小学的教育条件下,是选用普通话、方言还是中州韵吟诵?如何建立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吟诵教学模式?吟诵的师资力量如何培养?还有许多问题,都与吟诵的实践有关,还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