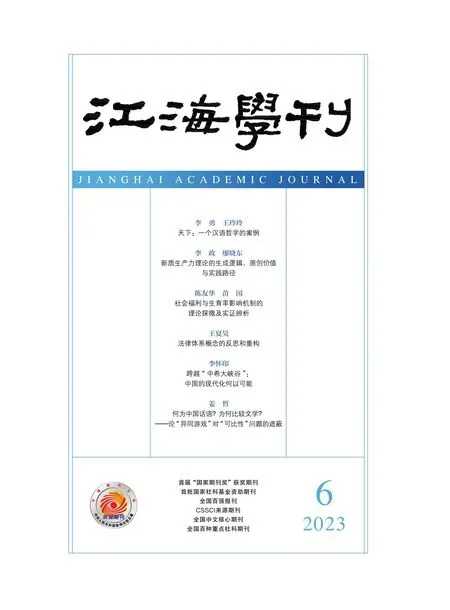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发掘“耻感文化”*
——迈向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人文心态比较研究
王佳鹏
1946年,本尼迪克特(下文简称“本尼”)所著的《菊与刀》甫一出版,就被译为多种文字,并长期畅销不衰。在该书影响下,“日本是耻感文化、美国是罪感文化”几乎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尽管影响广泛,不少学者认可和支持这一观点,或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发展,但该研究在日本和欧美学界还是受到诸多批评和挑战。随着二战后社会变迁和学术发展,日本学界对于《菊与刀》的态度经历了从接受到解构和重构,再到重新分析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对史实和方法的批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对日本耻感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是对问题的解构和重构,近十年则开始对《菊与刀》展开多元文化分析。(1)孙志鹏:《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而在美国,自该书出版至今,评价褒贬不一,比如格尔兹曾批评该书“理论上有些轻率,经验性有些薄弱,道德上有些可疑”。(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页。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更多是对本尼的延伸,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不同于日本耻感文化的面子文化,(3)翟学伟:《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日本耻感文化源自中国,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都是耻感文化。(4)[日]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2期。
然而,在如此广泛的影响和讨论中,不管是支持、修正还是批评,除了观点的争鸣和方法的争论外,很少有人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耻感与罪感这对概念的思想渊源,以及本尼对这对概念的使用与其最初渊源的异同。古典学家多兹在直接运用本尼的这对概念分析古希腊社会时,提出了相似的疑惑,(5)Dodds, E. R.,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17, 26, 28, 43.可惜他并未予以深究。实际上,这对概念并非本尼所独创,也并非完全如多兹所言,与本尼早期著作无关。早在《菊与刀》(1946)之前的《文化模式》(1935)中,本尼就已经开始运用这对概念分析原始文化与美国文化,而本尼所谓的这一区分在人类学中“确立已久”,主要指的可能就是从《文化模式》到《菊与刀》的这十年时间。
本文试图从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角度,追溯耻感与罪感这对概念或“耻感文化”的思想旅行,发掘耻感概念的思想渊源及其流变。正如萨义德所言,“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情形特别值得玩味”。(6)[美]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0页。首先,本文将梳理这对概念在本尼早期著作《文化模式》和晚期著作《菊与刀》中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其次,将追溯这对概念的精神分析渊源及其对心理人类学或文化人格学派的影响,尤其是二者在关注重心和使用方式上的转变。最后,重新评估以精神分析、文化人格学派为代表的西方耻感概念,认为这种罪感文化下的耻感概念作为欧美学者的文化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于是,用这对概念来描述美日文化或东西文化差异时,就会存在很大程度的流变性和不契合性。因此,在社会研究和文化比较中,我们必须以文化自觉的视野来把握和理解特定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意义,避免文化无意识的思想陷阱。
日美文化比较
(一)日本耻感文化与美国罪感文化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设立相关部门,组织跨学科研究,为其内外政策提供依据。其中就包括二战胜利前夕的日本研究计划,该计划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不会主动投降,美国不应直接占领日本,而应保留和利用日本原有机构。本尼将她参与该研究的成果整理成著作《菊与刀》,于1946年出版,并于1949年译为日文,随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影响。通常认为,《菊与刀》的主要贡献在于美日文化比较,提出欧美是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但是这种过于简化的概括经常导致一些误解,似乎耻感在欧美社会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具有重要意义。若进一步追问,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是何为罪感与耻感?耻感对日本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本尼是如何理解罪感与耻感这对概念的?她又是如何利用这对概念来进行跨文化比较的?
本尼在《菊与刀》中用了好几页篇幅来专门讨论这对概念,但只是将其视为美日两种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类学的典型做法并非孤立地看待耻感和罪感,而是将其置于相应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之中,看它们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在副标题“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得到了显著体现,说明耻感文化只是日本诸多文化模式中的一种而非全部。(7)[日]川口敦司:《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合一——读〈菊与刀〉》,《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因此,首先需要在总体上把握《菊与刀》的思路,然后才能理解耻感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的意义。《菊与刀》共13章,如果不算概述研究任务的第1章、讨论日本人战后心理的第2章和提出战后政策建议的第13章,中间10章可大致分为两部分。就像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在结构上包含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两方面一样,本尼对日本文化模式的论述也是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和恩情—义务体系以及二者相互关系出发的。第3—4章主要讨论等级制,第5—10章从静态角度讨论恩情—义务体系,第11—12章则从动态角度讨论自我修养、社会化和文化传承。
首先是日本的等级制。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封建历史和武士社会,使日本人按照性别、年龄、家庭、阶级等不同因素形成了亲疏远近的等级秩序,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日本的等级制尽管学习了中国,但由于长期实行封建领主制而非中国式的郡县制,其家族关系相对淡薄,也缺乏科举制这样的流动渠道,所以“上至天皇、下至贱民”的日本封建等级制极为严格,领主关系比家族关系更为重要。
其次,与等级制相匹配的伦理观念是日本的恩情体系。对于深受封建领土制和等级制影响的日本人来说,每个人生来就对祖先、社会和世界欠恩,而受恩、欠恩、报恩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具体而言,日本人的恩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限的、绝对的恩情,比如忠孝;另一类是在特定时间内可以如数偿还的恩情。第二类又被称为“情义”(Giri),这似乎是日本人特有的,它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社会、主君、近亲、他人的“情义”;另一类是对自己名誉的“情义”,比如受到侮辱、名誉被玷污时洗刷污名、报仇雪恨甚至自杀的义务。日本人特有的“情义”包含很多内容,含义复杂,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将侮辱、耻辱也包括在“情义”内,认为它跟恩情一样。“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在他们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称作侵犯之罪。只要是遵守‘情义’,洗刷污名,就决不能说他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账。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2页。“接受‘情义’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是大都‘不愿意’的。‘为了情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9页。
第二类“对(自我)名分的情义”主要包括隐忍、守本分、对不名誉的反应、对嘲笑和侮辱的回复和报复等。“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荣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10)[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18页。日本人对不名誉的反应,最典型的是遭遇竞争失败时感到蒙羞,比如会失声痛哭,而不像美国人那样可以坦然面对竞争和失败。日本恩情体系的重要目的就是使日本社会处处有礼,主要通过中间人打交道而非直接竞争,以此来减少竞争、失败以及相应的羞耻和耻辱。
于是,在日本等级制和恩情体系下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恩情圈子或义务圈子(circles of obligation)中,既依赖于又受制于这个圈子,缺乏个人自由和独立。不管对天皇、上级,还是对祖先、父母、老师,甚至是陌生人,都要铭记恩情,报答恩情。不平等的、报不完的并构成沉重负担的恩情,使日本人在心理上深感矛盾,一方面是不愿意受恩、感觉自己不配受恩,另一方面则是一旦受恩,又必须努力报恩,这是造成日本人具有菊与刀所象征的那种矛盾性格或暧昧感受(ambivalence)的根源所在。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但更强调对于父母和天皇的绝对忠孝和报恩,不太重视“仁义”,因而不管父母和天皇是否仁慈,都必须绝对服从,这一点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的道德矛盾性。
本尼正是在讨论日本人所面临的各种道德困境时,着重讨论耻感和罪感问题的。她首先对这对概念进行了区分:“在人类学对各种文化的研究中,区别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是一项重要工作”,“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为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1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54页。
然后,她将这对概念运用到美日文化比较中。她在文化比较意义上指出,早期美国清教徒以罪感为中心,现代美国人则为良心所苦恼,罪感不如以前那么敏锐,羞耻感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接下来,她主要讨论了日本耻感文化:“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其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人死之后就不会受惩罚。”(1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55页。
本尼在书中多次直接或间接指出,日本等级制和恩情体系所导致的道德困境或矛盾性是造成日本人对羞耻尤为敏感的根本原因。这不只是说日本人具有更为强烈的羞耻感,也是指出羞耻感在根本上是日本道德困境的体现。日本人对羞耻感本身也有着矛盾的态度,静态地看,日本人似乎在某一方面感到极其羞耻,但在另一方面又毫无羞耻;动态地看,日本人似乎会经历童年的无耻,成年的羞耻,到老年又回归无耻。(1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76—189页。
总之,本尼在《菊与刀》中虽然主要研究的是日本的各种文化模式,但同时她也非常关心美日文化比较:日本等级制与美国自由平等制;日本有条件的恩情关系与美国无条件的爱护关系;日本重视精神与美国重视物质。耻感与罪感作为自我省察性的道德情感,最能凸显二者在文化心理上的根本差异。就日本耻感文化而言,一方面指的是整个日本社会与文化体系下的羞耻心态,另一方面又指第二类恩情或“情义”中的羞耻、耻辱及报复心理,尤其是虽不情愿但必须予以回报的特点。于是,日本耻感文化又可称之为名与耻(name and shame)的文化。此外,跟埃利亚斯、舍夫等从广义或“家族”意义上理解羞耻感一样,(14)Scheff, Thomas J.,“Shame in Self and Society”,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26, No.2, 2003, pp.239-262; Scheff, Thomas J., “Elias, Freud, and Goffman: Shame as the Master Emo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Norbert Elias, eds. S. Loyal, S. Quill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29-242.从用词上也可以看出,本尼所理解的日本耻感也包括了尴尬(embarrassment)、耻辱等感受。(15)[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2页。
(二)评价与影响
《菊与刀》出版后,既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发了诸多争议。首先,争议最大的是方法问题,该书被认为没有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方法,资料来源主要是对日裔美国人的访谈和日本文学、影视作品等资料。并且其访谈也存在一定问题,访谈对象大都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其生活和思想在到美国后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16)Rademaker, John A., “Reiew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3, No.2, 1947, pp.156-158.其次是观点的局限性,本尼过于坚持本质主义,强调行为的统合性和社会规范的决定性,将特定时期特定阶层的社会心理视为日本人的普遍特质,缺乏对历史性、阶级性等因素的充分考虑。(17)Lie, John, “Ruth Benedict’s Legacy of Shame: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in the Study of Jap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29, No.2, 2001, pp.249-261.该书刚出版时就有人指出,其观点或许适用于封建时代的日本,而不是当代日本,通过与西方社会的长期接触,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不同于传统时期。(18)Steiner, Jesse F., “Review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6, No.4, 1947, pp.433-433; Rademaker, John A., “Review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3, No.2, 1947, pp.156-158.本尼在书中也进行了一定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明治维新的分析,但她认为即使经过明治维新,等级制、恩情体系等日本文化模式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明治维新之所以发生,恰恰是由于“封建时代日本那些特殊习俗语境孕育的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由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1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55页。明治维新政治家并未废除等级制,反而试图在国内和国际实现等级制,将天皇和神道教视为民族统一和优越的象征,让人民和国家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其三则是学术伦理问题,该研究主要服务于美国军事战争和占领政策,不够价值中立,因而具有东方主义色彩。
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和局限,但《菊与刀》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文化。在总体上,很多学者也都基本接受了本尼对日本耻感文化的概括,或在其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正和发展。(20)[日]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2期;[日]作田启一:《价值社会学》,宋金文、朱静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6—310页。然而,在有关该书的诸多争论和讨论中,却很少有人去深究耻感与罪感的区分来自何处。古典学家多兹在运用本尼的这对概念时,也提出了相似的疑惑,但却并未给予解答。
原始部落与美国社会
《菊与刀》的巨大影响经常使人们将日本文化与耻感文化等同起来,实际上在此之前,本尼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就已经开始运用这对概念。《文化模式》和《菊与刀》分别是本尼在早期和成熟时期的两部代表作,其研究对象发生了时空上的重要转变,从北美印第安文化转到了日本文化。尽管她将日本文化视为一种古老文明而非原始文化,但其基本观念和方法,以及对耻感和罪感这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前后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我们首先来看她在《文化模式》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这对概念,然后再比较《菊与刀》和《文化模式》两部著作在理解和运用这对概念上的异同。
(一)原始耻感文化与美国罪感文化
作为本尼的早期代表作,《文化模式》比《菊与刀》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人类学作为习俗科学(the science of custom)的基础和作用,并用三个原始部落的文化模式作为范例。本尼指出,人类学作为习俗科学,主要通过习以为常、看似琐碎的习俗及其对人性和人格的形塑作用,来研究文化差异和文化整合,进行文化比较。在对这门学科进行概述后,她具体分析了三个原始部落,并划分了与之对应的三种文化与人格模式。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人主要是日神型人格,强调自我节制和举止适度,看重德行和礼仪,将个性淹没在社会之中,类似于中国文化和中庸之道。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主要是酒神型人格,个体之间充满公开竞争和对抗,傲慢专横,喜欢通过散财宴羞辱他人,极力追求心醉神迷般的迷狂境界。澳洲新几内亚岛南部原始部落主要是妄想型人格,行为反复无常,相互之间充满猜疑、竞争、伤害和欺骗,缺乏严格的政治组织,靠恶毒的巫术和咒语来支配世界。
本尼所分析的三个原始部落和三种文化模式表面上看似乎与耻感、罪感无关,但从词语使用情况却可以看出,耻感和罪感在本尼的早期著述中已经具有重要地位。具体而言,罪或罪感(Guit)在该书中只出现4次。(21)Benedict R., Patterns of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0, pp.117, 229, 238, 239.在这4次中,第1次讲的是以祖尼人为代表的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人没有罪感或罪疚情结(guilt complexes),其余3次讨论的都是现代西方文明。其中,第2次说的是同性恋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罪疚、不适、失败是由于社会传统与其个人之间的不一致所导致的,第3次讲的是18世纪英格兰清教牧师的极端罪疚感,第4次讲的是现代西方思想坚持永恒而绝对的正统梦想,否则生存就变得空洞无物,这种解释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可见,该书4次谈到罪或罪感都说的是现代西方人有罪感,普韦布洛人等原始部落没有罪感。
相对于仅仅出现4次的罪感而言,耻感(shame)在该书中却出现43次之多,还不算与耻感相似的其他词语。(22)Benedict R., Patterns of Culture, pp.102-103, 168-176, 184-194, 209, 212, 221.这43次都是在讨论原始部落的羞耻,尤其是美洲西北海岸文化。那么,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为何会对羞耻如此敏感?在她所分析的三个原始部落中,西北海岸印第安人是本尼及其老师博厄斯长期实地调查的对象,而她对其他两种文化的分析则是以他人研究为基础的。正如后来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一样,本尼的印第安文化研究也是首先讨论整个部落的社会组织体系和文化人格,然后分析耻感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偶尔用西方人的罪感作为比较。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在文化上是典型的酒神人格,这种人格的最显著特征是通过宗教仪式、婚丧礼俗等来实现酒醉迷狂状态,让个体与超自然建立联系。这种文化人格还体现为政治上的缺乏公共秩序和经济上独特而宽泛的财产观念。他们将姓名、神话、歌曲、头衔等非物质的事物都视为财产,每个人一出生就参与到这些财产的竞争之中,尤其是头衔和名号,财富只是服务于地位和名声的竞争。
因而,印第安人不惜通过隆重而盛大的散财宴来羞辱他人,使自己名声显赫。散财宴上的所有宾客都是羞辱对象,其目的是使所有宾客都感到主人带给他们的羞耻或羞辱,如果有宾客要消除自己的羞耻或羞辱,则需举办更为隆重而盛大的散财宴。
可见,不管表现在宗教、礼俗方面还是政治、经济方面,西北海岸部落的酒神人格都极为重视名誉。他们想要极力展现自我的地位、名声和荣耀,同时贬低、嘲笑和羞辱他人。展现自我名誉和贬低他人往往是一体的,也即最有地位和名气之人往往就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他人羞耻或羞辱之人,因而他们在感受上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名誉展示的胜利与失败展示的羞耻:“在西北海岸,人的一切行为完全是由下述需要所支配的,即显示自身的高贵和对手的低下。……他们只承认一种有交错的情感,即摇摆于胜利与羞耻之间的情感。他们中间的经济交易、婚姻、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都是以那种受辱或当众施辱的形式行进的。”(23)[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9页。于是,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对羞耻或羞辱极为敏感,其一切态度和行为的出发点几乎都是为了贬低他人,展现自我优越;同时,他们又特别害怕他人使自己感到羞耻或羞辱。一旦感到羞耻或羞辱,便会十分恼怒,做出极端行为,不是报复便是自杀。
(二)从《文化模式》到《菊与刀》
除了对三种原始文化模式的直接研究外,《文化模式》还论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但并未提到日本文化。本尼指出,西南部普韦布洛人的日神型文化人格更像中国文化和中庸之道。但她并未以类似方式指出,哪种原始文化更像美国文化。相反,她总是比较原始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就西北海岸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比较而言,她指出,在美国文化看来,西北海岸文化人格是一种“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倾向”,“在我们的文明里被看成变态”。(24)[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205页。
倘若比较一下本尼在《文化模式》中对于西北海岸文化与《菊与刀》中对日本文化的描述,可以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相似性。从《文化模式》到《菊与刀》,她对耻感和罪感的分析虽然有一定变化,但在根本上仍以延续为主。首先,她在《文化模式》中已经开始运用耻感与罪感这对概念对西北海岸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比较,这与《菊与刀》对美日文化的比较几乎同出一辙。不同的是,《菊与刀》更加明确地提出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是人类学的重要工作。本尼对于文化差异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文化模式》倾向于以原始文化反思美国文化的束缚性,《菊与刀》则倾向于从美国文化或罪感文化出发,来批评日本耻感文化的不足。
其次,尽管她是在不同时期研究印第安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但描述这两种文化时所用的词语及其含义却高度一致,所描述的内容也十分相似。她指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25)[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55页。这里所谓“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显然是指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可以说,西北海岸印第安文化和日本文化都是以名与耻为基础的文化,两种文化人格都摇摆于羞耻与自豪(shame and pride)、耻辱与荣耀两极之间,于是在文化心理上经常充满矛盾性,而不像日神人格或中国文化那样强调中庸。相比而言,本尼对西北海岸文化的分析更多以文化人格为中心,强调酒神型人格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各方面的表现,而对日本文化的分析则将社会组织上的等级制与伦理上的恩情体系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此外,本尼在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中国。在《文化模式》中,她只是顺带指出,西南部普韦布洛人像中国人,日神型文化像中国儒教。《菊与刀》则更多地论及中日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她指出中国皇帝是世俗之人,日本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日本忠孝虽然源自中国,但只是局限在小家庭中,主要是对外尽忠于封建领主而不是家族和宗族;中国忠孝是以仁为前提的,而日本忠孝则把仁排除在外,强调绝对效忠。对名分的“情义”是日本独有的,中国人听到侮辱或诽谤会将其视为道德低下的小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将对名誉的敏感视为崇高理想的一部分。
耻感文化的精神分析渊源及其潜在问题
(一)从精神分析到心理人类学
不管是早期的《文化模式》,还是后来的《菊与刀》,耻感和罪感在书中的出现似乎都有些突兀。尽管《菊与刀》对这对概念给予了更明确的界定和论述,但二者都没有给出这对概念的直接出处,而是直接运用这对概念来分析原始文化和日本文化,并与欧美文化进行比较。博厄斯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德裔美国人社区,他们比博厄斯本人还要更坚持德国理念主义,而本尼又比博厄斯的其他弟子更加深受德国思想的影响,(26)[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建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尤其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她最初喜欢文学和诗歌,因而在《文化模式》中直接从尼采那里借用了酒神与日神这对概念,并在根本思想和文化观念上追随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给予了她一种从束缚重重的往昔解脱出来的自由感和一个要在未来奋斗实现的目标”。(27)[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2页。
精神分析对本尼和文化人格学派的影响更为明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几乎与精神分析结合在一起,人类学的文化人格学派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彼此交融,本尼跟埃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家在生活和学术上均交往密切。(28)[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第135页。正是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本尼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关注私人感受和道德情感,精神分析特别强调的罪感和偶尔提及的耻感逐渐成为其关注焦点。(29)Modell, Judith, “The Wall of Shame: Ruth Benedict’s Accomplishment 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24, No.2, 1999, pp.193-215.但跟《文化模式》明确承认尼采影响不同的是,《菊与刀》在运用罪感与耻感时,并未给出任何出处,她似乎认为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并将其视为人类学的重要工作,是她自己的独特贡献。那么,在对这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她与精神分析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呢?
从对这对概念基本含义的理解来看,她跟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社会文化学派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将耻感视为他律性和外部评价性的感受,将罪感视为自律性和自我良知的感受,前者重视他人和名声,后者重视自我独立和良知。他们都使用了相似的比喻,认为羞耻犹如大坝或墙壁一样,是一种防御性感受和道德性困境,羞耻感在根本性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恐惧和压力。(30)[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71—176页。尽管基本含义相似,但有关这对概念的关注重点和使用方式,二者则存在很大不同。在关注重点上,精神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罪感,较少关注耻感。(31)Scheff, Thomas J., “Shame in Self and Society”,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26, No.2, 2003, pp.239-262; Lansky, Melvin R. &Morrison, Andrew P., “The Legacy of Freud’s Writings on Shame, in The Widening Scope of Shame, Edited by Melvin R. Lansky, Andrew P. Morris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4, pp.3-40.即使论及耻感,也往往会追溯到儿童时期或人类早期。比如,弗洛伊德从个人成长史和人类文明史出发,强调羞耻的来源是儿童早期的俄狄浦斯情结,或人类早期开始直立行走时因为把敏感部位(性器官)暴露给他人而感到恐惧。社会文化学派虽然对泛性论和俄狄浦斯情结持怀疑态度,但同样认为小孩子先有耻感后有罪感,罪感是比耻感更高阶的道德情感。比如,埃里克森指出儿童在肛门期面临自主与羞耻的矛盾,在生殖期面临主动与罪疚感的矛盾,羞耻感和罪疚感过强是很多心理疾病的根源。(32)[美]爱利克·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高丹妮、李妮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27—253页。
受精神分析影响,本尼也分析了养育模式和日本儿童耻感的关系。她认为日本小孩子幼年时期无忧无虑、不知羞耻,六七岁开始有耻知耻、谨言慎行,小学二三年级后耻感趋于显著,家庭和学校经常使用的耻笑、嘲笑等教育方式更是强化了日本人的羞耻和耻辱,使他们严格抑制自我,遵循“对社会的情义”。“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3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76页。从幼儿到青少年、成年、老年等人生过程的断裂性而非平缓过渡,是导致日本文化人格充满紧张性和矛盾性的重要原因。(3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99—203页。可见,本尼主要关注的是耻感,其次才是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比较,而不像精神分析那样首先关注罪感,偶尔提及耻感。她在使用耻感概念时,虽然延续了精神分析对儿童耻感的关注,但她主要分析的是作为整体的日本文化,对日本儿童耻感的讨论也是服务于日本文化模式的。
在对这对概念的使用方式上,本尼在分析日本文化和原始文化之后,都将其与美国文化进行比较,这一点跟精神分析不同的不只是从微观个体—家庭分析转向社会—文化分析,而且将精神分析的纵向发展思路转为横向比较视野。在精神分析看来,不管是儿童的成长还是人类的文明,都是先有耻感后有罪感,罪感是比耻感更为复杂和成熟的感受,从耻感到罪感、从他律到自律似乎意味着成年和成熟。多兹在本尼和精神分析的影响下,直接运用这对概念来分析古希腊,认为从荷马时代到古风时代经历了从耻感文化到罪感文化的转变,这一观点非常符合精神分析的思路。(35)[爱尔兰]E.R.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王嘉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30—73页。而本尼却是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相对性的角度,对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进行横向比较,更加强调原始文化、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不过,跟《文化模式》相比,《菊与刀》对文化相对性和多样性的坚持似乎有所松动,她认为日本文化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最基本的自由和自尊,承受着耻感的沉重压力,因而美国在日本投降后的主要政策便是在非强制的前提下使其走向自由民主的美国罪感文化。(36)[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214—218页。可以说,本尼对这对概念的使用在总体上以横向比较为主,尽管也暗含着精神分析的纵向发展思路,也即从耻感文化走向罪感文化的趋势。
因此,本尼的耻感与罪感概念源自精神分析,对这对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也跟精神分析基本一致,只是关注重点和使用方式有一定差别。主流精神分析主要关注罪感及其影响,相对忽视耻感,即使偶有提及,主要也是关注儿童耻感,暗示个体成长史和人类文明史是从耻感到罪感、从依赖他人到个体自由的纵向发展过程。本尼及其文化人格学派则主要关注原始部落、日本文化等非西方地区的耻感,儿童耻感也只是整个耻感文化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她又对非西方耻感文化与欧美罪感文化进行了横向比较,其早期的原始文化研究强调以原始文化反思美国罪感文化的繁重压力及其导致的心理疾病,而后来的日本耻感文化研究却又似乎暗含着精神分析的纵向发展思路,并提出了日本文化美国化、耻感文化罪感化的政策建议。
(二)重估耻感概念的意涵
上述追溯、澄清和比较工作,为进一步重估本尼等欧美学者的耻感概念及其对于耻感文化未来走向的判断奠定了基础。在本尼所研究的两种耻感文化中,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逐渐走向了消亡,因而她对原始部落耻感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美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浪漫化的反思镜像。对于日本文化的未来,她认为应努力消除耻感的作用,走向美国式的现代文化,日本在二战后也确实是以美国化为主的,但很快就出现了诸多问题,并开始寻求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发展道路。同时,本尼又指出美国清教徒面临因罪感而产生的诸多精神问题,“在美国,羞耻感正在逐渐加重其分量,而罪感则已不如以前那么敏锐”。(37)[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55页。她似乎不得不在两种观点之间协调,一种是耻感文化给人造成过重的社会压力,因而应该走向强调自由和自尊的罪感文化,另一种则是美国人的罪感似乎正在减弱,耻感反而在增强。从中不难看到本尼等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只是政治的更是思想的,不只存在于他们对于耻感文化发展走向的显性判断之中,而且还存在于耻感概念背后的潜意识之中。
前文已指出本尼的耻感与罪感概念源自精神分析,但还需进一步重估这一概念的潜在意涵。弗洛伊德总体上对耻感关注较少,早期对裸露梦的分析跟耻感有着直接关联,后期则相对忽视耻感,或者最多间接相关,但他不同时期对耻感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在他看来,在人类文明史上,耻感源于直立行走将敏感部位暴露给他人的恐惧;(38)[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89页。在个体成长史上,儿童的耻感源于俄狄浦斯期面对父亲等权威人物时的那种既爱又恨、爱恨交织的感受。面对父亲等权威人物的压力,“为有效地压制[本能所引起的]不愉快,便唤起了相反的心理力量(相反情感),即我前面提到的心理堤坝:厌恶、羞耻与道德”。(39)[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宋广文等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也有学者对弗洛伊德的有关文本进行了重新分析,认为在弗洛伊德那里,不管是早期的释梦还是后来对自恋的分析,都意味着他将羞耻与自我理想、社会压力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个有抱负之人遭到他人否定或拒绝时所感到的羞耻。(40)Lansky Melvin R. &Morrison Andrew P., “The Legacy of Freud’s Writings on Shame, in The Widening Scope of Shame,Edited by Melvin R. Lansky, Andrew P. Morris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4, pp.3-40.弗洛伊德自己就常有这样的体验,比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因为某件事而责备自己——我害怕他人会知道这件事——因而,我会在他人面前感到羞耻”。(41)Freud, S., Extracts from the Fliess Papers(Standard Editio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6, p.225.
总之,弗洛伊德始终将耻感视为一种担惊受怕的恐惧,一种自我在现实中或想象中在他者面前暴露出脆弱、不足、不快因而担心受到威胁或惩罚的恐惧,其结果便是对他者的内化和对自我的克制。这样一种耻感观念不仅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者的观点,也影响了本尼及文化人格学派,而且也是齐美尔、埃利亚斯、理斯曼、波兹曼等许多关注耻感问题的社会理论家的共同认识。(42)王佳鹏:《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从齐美尔到埃利亚斯、戈夫曼》,《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他们之所以对耻感的意涵形成了如此一致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理解是很多欧美学者共同的文化无意识,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独创。
在根本上,这其实是罪感文化视野下的耻感概念,因而它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耻感与罪感的区分问题。在欧美学者的通常理解中,耻感和罪感似乎都是某种恐惧,不同的是耻感更加强调对他人的恐惧,使人形成他律性,罪感则源于对上帝的恐惧,使人形成自律性。这种区分看似自圆其说,但在实际的概念使用中却难以截然区分。弗洛伊德自己就经常将耻感与罪感混为一谈,他对耻感的关注越来越少,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他逐渐把耻感纳入罪感之中了。或者说,他是从罪感的角度来理解耻感的,因而将耻感的基本含义界定为令人恐惧、需要他律。埃里克森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定义耻感的,他指出,“耻感意味着一个人完全暴露在他人面前,并意识到他人的目光”。(43)Erikson Erik, Childhood and Society, London: Penguin Books,1965, p.244.他虽然直言“羞愧是一种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情感,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太容易和罪恶感混为一谈”,但接下来给耻感所下的定义跟弗洛伊德早期分析裸露梦时几乎一样:“羞愧指的是个体完全暴露于他人面前,并且意识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何当我们梦到自己在衣衫不整、穿着睡衣或者‘裤子掉了’时被人注视会感到羞愧难当。”(44)[美]爱利克·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高丹妮、李妮译,第227页。对于本尼来说,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几乎就等同于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而多兹在用本尼的这对概念分析荷马社会时,也指出“它们本身也容易引起误解”。(45)[爱尔兰]E.R.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第32页。
埃利亚斯更是把耻感与罪感混为一谈,他所谓的耻感很多时候更接近于弗洛伊德的罪感。他指出国家的暴力垄断和稳定的社会结构越是将外在强制转化为自我强制,“对于违犯社会禁律的惧怕就越是强烈而鲜明地具有羞耻感的性质”。(46)[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99页。他还直接从弗洛伊德的超我、潜意识来解释耻感的性质和形成:“由社会认可的戒律被培养成了个人的自我强制。对某些情感的强制性压抑以及由这些情感而引起的社会羞耻感已经变成了个人的习惯……由这些情感而引起的快感与由戒律、限制、社会性羞耻感和难堪而引起的厌恶会在他的内心发生争斗。显然,这便是弗洛伊德试图用‘超我’和‘潜意识’,或者一般所说的‘下意识’所表达的情形。”(47)[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203页。
当本尼用这种源自精神分析、以恐惧和他律为基本含义的西方羞耻概念,去研究原始文化、日本文化等非西方文化时,必然面临耻感概念与不同文化的契合性问题,至少很难发现该耻感概念之外的意义。正是从这种耻感概念出发,本尼才认为日本耻感文化是他律性的、令人恐惧的,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代价,放弃了最为基本的自由自尊,承受着沉重的社会压力。(4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203—204页。悖谬的是,这同样也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本尼等欧美学者对罪感文化及其问题的诊断结论,他们似乎都认为西方文化不够自由、过于束缚,罪感过强导致诸多心理疾病,关注异文化正是为了反思罪感文化,促进西方社会的自由。为了回应美国社会宗教式微、罪感减弱、耻感增强的现实,本尼不得不再次强调耻感与罪感概念的不同,重申罪感文化下的耻感概念在其道德体系中是没有位置的:“我们并不指望羞耻感来承担道德的重任。我们也不会在我们的根本道德体系中,对伴随羞耻而出现的强烈的个人恼怒进行控制和利用。”(4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55页,译文有改动。
结语:迈向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人文心态比较研究
19世纪末的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和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文化学派、文化人格学派,在对耻感与罪感概念的运用中,一方面,存在关注重心和使用方式的不同,这些不同类似于从“灵魂”到“心理”的转变;(50)[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第206页;孙飞宇:《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精神分析理性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另一方面,这对概念在根本上似乎又并未发生改变。他们都将耻感视为缺乏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社会性恐惧和他律性压力,这实质上是罪感文化下的耻感概念,或者说其耻感概念有着潜在的罪感意涵。这种耻感概念作为某种文化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后来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从这种耻感概念及其隐含的罪感意义出发,尽管多少有助于理解其他文化,但在根本上却很难达到走出罪感文化、理解其他文化的目的。因而,当本尼将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作为“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并将原始部落、日本社会视为耻感文化时,其背后仍然潜存着罪感的意涵,甚至直接认为其发展方向就是走向罪感文化。
相比而言,耻感概念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则有着不同的意义。中国人的羞恶之心与罪感文化下的耻感概念有着很大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不但不是不道德的,反而是一种深具自主性、道德性的君子美德。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宋朝理学家范浚进一步指出:“耻,入道之端也。”具体而言,中国人的羞耻心几乎渗透在修齐治平的方方面面——人性人格方面的生而有耻、知耻后勇,道德修养方面的行己有耻、有耻且格,齐家治国上的礼义廉耻、耻尤为要。相比之下,罪感文化视野下的耻感则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恐惧和他律,中国文化中的耻感则是一种道德性的仁爱和自律,即使面对社会性的羞耻和耻辱,也是强调含羞忍耻、忍辱负重。可以说,西方罪感文化视野下的耻感文化实际上是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仁与耻的文化,如果将前者简称为耻感文化的话,后者或许可以简称为耻德文化。
中国耻德文化的核心不是恐惧,而是仁爱;不是缺乏自由和自尊,而是充满强烈的自尊和自爱;虽与名望和荣誉有关,但并不十分看重虚名,名誉的地位始终位于仁义之后,最好是名誉与仁义相符,誉不虚出。于是,与欧美思想对于耻感和耻感文化的较低评价相比,中国文化则极为关心作为德性的羞耻心,大力批判无耻之人。近代知识分子更是将中国耻德文化跟近现代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如邹容批评时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康有为在批评中国传统社会的同时还正面强调,公民的重要品格之一是“行己之事知耻”,“行己知耻则风俗日美”,“仁惠之风行,廉耻之俗成,风俗美而大进矣”。(51)《官制议卷八 公民自治》,《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278页。当然,中国传统耻德文化跟等级制有着紧密联系,又受到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的挑战,因而需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尤其是消除其跟等级制之间的关联,激活传统耻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活力,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顿于现代理念和文明秩序之中”。(52)成伯清:《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学海》2018年第5期。
可见,本尼等人所使用的耻感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我们对印第安文化、日本文化等异文化的理解。因此,我们不但要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文化自觉,同时也要对西方的概念及其文化预设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充分理解其渊源、意涵及潜在遮蔽性。正如费孝通所言,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53)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然后才能在文化心态层面上“扩展传统社会学的界限”。(54)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438—465页。费孝通晚年从“志在富民”向“文化自觉”的转变,既是其研究从“经济”和“物质”层面向“文化”和“心态”层面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为了回应当今时代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跨文化沟通问题。
但他主要是“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次,把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55)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并未对具体的心态进行深入探讨和跨文化比较。而从羞耻感或羞恶心这一具体心态入手,以文化自觉的视野比较耻感在中美日等不同文化中的意涵,尤其是重新评估中西耻感概念,批判和反思西方罪感文化视野下的耻感概念,肯定和承认中国耻德文化所具有的道德性和自律性,则可在学术上进一步推进费孝通晚年“点题和开路”的心态研究工作,在实践上促进中西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和理解。简言之,从中国耻德文化自觉出发,对中西日耻感概念进行比较,不但有助于消除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耻感概念的长期误解,而且要求我们怀着“行己有耻”而非“他人即地狱”式的恐惧心态与他者相处,以“化成”一种既“羞己之恶”又“美人之美”的“心态秩序”。
——评章越松著《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