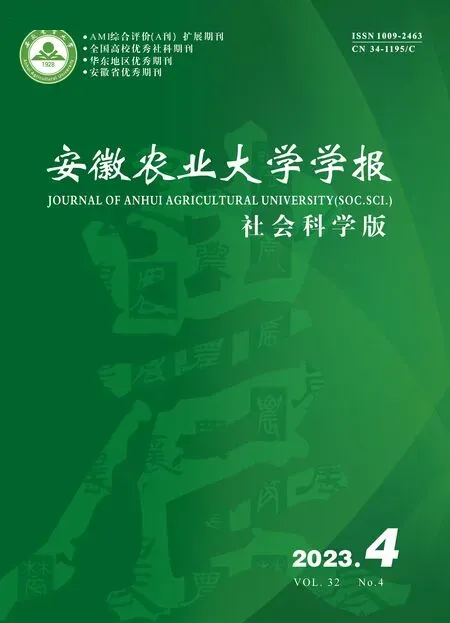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大历史观审视*
吕 岩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1]“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2]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用长远的、比较的、综合的思维来分析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从而把握历史规律。中国作为世界农业主要起源地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运用大历史观审视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揭示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大历史观从人类生产的实践活动出发,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既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创造民族独特文化的前提。提及“农耕文化”必然涉及另外一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农耕文明”,由此我们应当厘清二者的先后关系。一般认为,先有文化后有文明。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3]。所以,广义的文化在人类与自然共生之时已经产生。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随着以农耕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形成,逐步迈向文明社会。中华民族在农耕生产生活过程中孕育出特有的农耕文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的中华农耕文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4]这里的“文化”是广义概念,指的是人类文明处于初始阶段。从自然禀赋来看,中国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青藏高原将东亚大陆分割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在地貌上形成从西向东、由高至低的三级阶梯地形,形成青藏高原及邻近的高寒区、西部干旱区和东部季风盛行区三大气候自然区域,形成中国丰富多样的环境类型。在水资源分布上,青藏高原成为“中华水塔”,黄河、长江养育了华夏儿女。自然禀赋比较优越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心区域,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都有向中心发展的趋向。“由于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各民族的农耕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梯性,有的地区发展程度较高,而有一些地区发展进程较慢,但构成农耕文化的文化链都没有断。”[5]考古学家严文明以大历史观的宏大视角,构建了以中原为核心(花心),以不同时空出现的经济文化类型为花瓣(东夷、百越等文化处于第二或第三层)的差序关系格局,将早期中华文明这种辩证互补性的关系概括为“重瓣花朵”结构,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的紧密的内在结构[6]。
独特的地理环境只是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中华先民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才是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世界各民族在对特定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界分为了“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自在自然”空间才会被延伸、拓展、转变为“人化自然”空间。同时,延伸、拓展和转变并非是任意为之,而是人的实践活动在尊重“自在自然”空间规律性的基础上实现的[7]。中华先民在劳动实践中利用自然环境资源,驯化栽培了不同农作物,形成了区域鲜明的农耕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均以种植粟、黍为特征,红山文化也属粟作农业区;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与湖南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近 7 000年和的9 000年的稻作遗存[8]。从历史维度看,在文字出现之前,农业劳动的经验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后人的加工与演绎,形成了神话与传说。中华文化中关于伏羲驯化家畜、神农氏教人耕稼等远古神话是中国古代人民对农耕生产活动所作出的高度概括与合理想象,是中华史前文化传递的文化符号。
在农耕文明时代,我国文字记载史与农业发展史紧密相连。殷商甲骨文有很多关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描述。“由甲骨卜辞材料可以看出,卜雨、卜晴辞偏多,说明农业是商代最为重视的民生社稷;卜辞中的卜料几乎全部都是牛肩胛骨,反映出商王朝畜牧业发达。”[9]“周之先世,后稷、公刘、大王,皆以农业兴,则著于《诗》,散见于百家之书,其事弥信而有征。”[10]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中华文化就与重视农事相联。秦朝能够最终统一中国与其高度重视农耕息息相关。如秦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全面地学习周代的农耕生产经验以及周代的礼乐文明传统[11]。秦迁都咸阳,将都城从农耕区边缘转移到了农耕区的中心。商鞅颁布的新法有关于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和保护农耕的措施[12]。汉朝继承秦倡导耕战的思想并确立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基本形成了为历代统治者传承的农本思想。农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主题,由此使得农耕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和血脉。
二、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
大历史观看待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但是更要认清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国历史的变迁,统一为常态,分裂为非常态。即使在分裂时期,仍保持着导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历史动力,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朝代的统一时间越来越长。“大一统”不仅是历代王朝对疆域的持续追求,也是农耕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恩格斯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4]坚持从“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出发,是我们认识农耕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格局影响的关键。在农耕社会,人们既需要占据良好的自然资源环境,又需要共同应对严酷自然灾害的挑战。中华民族正是在勇敢应对严酷自然环境以及为生存而不断拓展农耕区域的过程中,孕育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认同和选择了各民族从对抗走向融合的“大一统”政治格局。
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成为多民族国家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大一统”不仅能带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可以动员“集体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和改善耕种条件,从而促进农耕经济发展。最早见于《诗经·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先秦时期“天下观”的核心内容,在这一认知体系中,“天下”是指采用农耕的中原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地区,诸如兴修水利之类的浩大工程,需要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力量才能动员和组织起来。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和排水,这种设施就立刻荒废下去。”[15]
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华夏居中,东、西、南、北分别属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属于“西戎”。秦通过承袭周的农业和文化以及迁都等措施实现了身份转换,并最终由秦王赢政结束春秋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为了获得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嬴政虽自称“始皇帝”,但运用“五德终始说”将秦的大一统与周朝相联系。“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16]秦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原地区的割据状态,废分封立郡县确保了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影响深远的举措得以推行,曾经在诸侯各国管理下的民众被统一整合为“秦人”。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思想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后中华大地在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的历史过程中,“大一统”观念始终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三、农耕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怀
大历史观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从广阔的空间视野来审视和把握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华农耕文明在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世界性融合交流中求变、求新。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兴盛千年。唐宋时期,中国与海外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东南沿海曾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国外珍奇货物源源不断涌入中国。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留下了中华民族与海外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
中国古代从域外引进了大量的农作物,极大丰富了域内种植作物的类型,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对我国的作物引入用“胡、海、番、洋”做了形象的概括,这四个字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所谓“胡”,指的是从丝绸之路引入的作物(如胡椒、胡萝卜等),“番”指的是宋代开设番(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货交易的“番市”)、司(在广州、杭州等地设置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后引入的作物(如番茄、番薯、番木瓜等),“海”指的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作物(如烟草),“洋”指的是清朝中叶后引入的作物(如洋芋、洋葱等)[17]7-12。两宋时期推广的占城国(今越南)的“占城稻”,以及明中期引进的玉米、马铃薯、番薯等美洲农作物对两宋和明清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不仅融合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也吸取了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精华,具有异中求同、兼容并包的融合力,使之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延续能力。
中华农耕文化在与世界交融中逐渐辐射到周边民族和国家,积极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以《氾胜之书》《齐名要术》《农书》和《农政全书》为代表的诸多农学著作。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更是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深刻影响。古代的日本、越南及朝鲜等受到了重农思想的深刻影响,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起源跟我国的重农思想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7]7-12。
四、农耕文化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8]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传承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农耕文化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和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和践行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新道路。在根据地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农耕文化中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信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农耕文化中通过组成分工有序的社会,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忆,让革命群众对马克思主义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革命要求产生认同;农耕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顺天时,量地利”的辩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矛盾的特殊性、适度原则、质变和量变的关系等原理更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农耕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与消除阶级差别、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共同的追求。农耕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都对宣传革命与发动群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以上思想激励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经过不懈斗争实现了独立解放,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通过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热情,从而引发了全民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热潮,为我国推进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生活来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弘扬民族气节的文艺作品。通过宣传下乡、文字下乡等文化实践,重塑乡村文化,使得农耕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将中国农耕文化中的“小康”社会理想与“中国式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揭开了以农村改革为起始的改革开放的大幕。围绕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粮食征购制度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在新世纪一举取消了农业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要从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定位和认识乡村振兴的使命与价值。唯有如此,才能深刻认识乡村在应变局、开新局中的基础作用和“压舱石”功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农耕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之中,让农耕文化精华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结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理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使中华农耕文化迎来了质的飞跃,真正注入了农业现代化的崭新内容。
五、传承农耕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0]当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1]因此,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养分、传承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体现,蕴含着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丰富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确保粮食安全。传统农耕文化注重“民以食为天”,把粮食问题与重农思想、民本思想相融合,并贯穿于施行仁政、实现王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古代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制定了多种律令,集中体现在粮政、仓政和荒政上。例如,雨雪粮价奏报制度、漕粮省际调配、常平仓制度等[2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绿色发展之路等,要把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十几亿人口不仅吃饱还要吃好的问题放在首位,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最质朴的生活理想。纵观中华民族文明史,共同富裕体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从《易经》的“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到《礼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朴素的共富意识与对“天地之道”的探求交织在一起,“为政以德”“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成为封建士大夫的政治信条和德行标准,农家的“并耕而食”、道家的“小国寡民”、儒家的“大同”无不体现着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更高层次的文化复兴为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2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国传统农业一直秉持着以“三才论”为核心的哲学,即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形成重要的农学思想。“三才”论的核心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对于反思工业文明早期因“征服自然”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依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农耕文化追求安定和平的特性,使得中华文明持久稳定的发展向来不依靠掠夺、剥削、压榨其他民族来实现。中华民族也在农耕文化的熏染中形成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贵和尚中的思维方式、厚德载物的宽阔胸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24]
七、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21]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从发展规律来看,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决定了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需要因时而化、因势而变。这就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从中华文明的深远历史根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只有把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之中,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传承发展提升中回应时代之问,才能实现创新发展并发挥其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