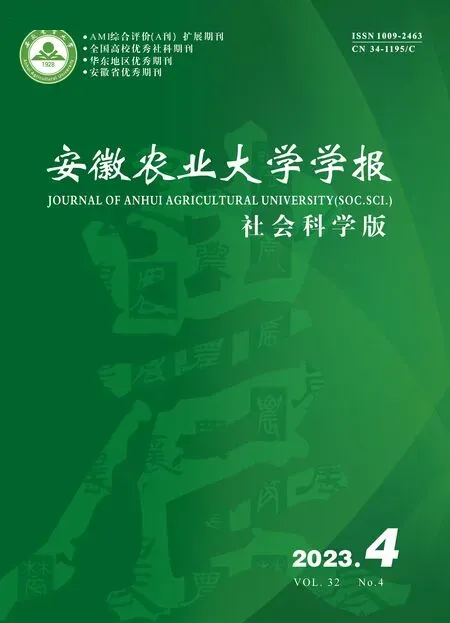论鲍照与道教*
——以鲍照涉道诗歌为中心
吴怀东,王雅娴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的“环境”要素影响论,他说:“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1]在刘宋元嘉时期鲍照的现存作品中,便存在一些有悖于其整体气质的“异格”之作,尤可体现时代思潮与环境对他的影响。如鲍照以善为乐府著名,尤其以拟汉魏古乐府、表现自身价值追求与清刚骨气的作品为人所称许,如《拟行路难》《代出自蓟北门行》,但其乐府中也有部分作品受到吴歌西曲影响,如《吴歌》《采菱歌》,风格清丽婉约,这实与刘宋上层阶级好尚南方民歌的倾向同频共振[2]。又如刘宋时代的“尚释”之风及幕主临川王刘义庆的佞佛行为也影响到鲍照的创作。并非信奉佛教的鲍照也有意地进行过一些佛教题材的创作,以“投主所好”。其实,鲍照还有一类诗歌也属于此种情况,典型的如《代昇天行》《和王丞》《白云》①等诗歌中有关采药、炼丹的描写,表现隐逸、求仙志趣的词汇和概念,运用熟练,这些诗句仿佛出自一个栖身野泽的道教徒手笔,与人们熟知的诗歌史上的鲍照形象迥然不侔。
其实,已有学者发现此现象,但如何认识鲍照此类具有道教意味的书写还需要讨论。苏瑞隆将鲍照放在“六朝人”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进行观察,认为鲍照践行道家服食养生之术,也关注“三玄”,正反映了六朝人流行信仰天师道的文化风尚,“鲍照不是一个相信宗教的人,但他在诗文中偶尔也显露出一些道家看待人生的态度。这似乎是中国文人一贯的态度,在政治上得意时,就抱持儒家入世的态度;失意时就想归隐,抱持道家出世的精神”[3]39-42。但苏教授没有讨论鲍照具体诗文中相关词汇及内涵与道教的综合联系,也未对鲍照接受道教熏染的环境和途径作出具体探讨。罗文卿则以为,鲍照游仙诗作表现的是“寒士情绪”,同时也由于“刘宋时期动荡的时局使得文士们对政治仕途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因此纵情山水,遗落世情者甚多,鲍照虽然才高志远,在理想受挫时,也难免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4]302-304。鲍照此类表现隐逸、游仙情怀的诗作多见于山水诗中,典型代表为“庐山诗”(如《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等),但有的研究者将之与佛教相联系[5-7],或言“这种道教式的联想只是附带的玄外音,而非本诗的主调”[3]199,或仅言其“是对嵇康、张载等人游仙传统的继承和发展”[4]305。可见,现有研究对鲍照这类诗歌书写所反映的思想倾向缺少准确理解,对道教思想与鲍照主体思想的联系的理解亦失之于简单,对其形成背景更缺少考察。故本文试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通过解读相关诗文,结合社会背景,对鲍照与道教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
一、思想与立场:鲍照涉道诗歌的文本分析
据鲍照现存作品统计②,其涉道诗歌,即表现隐逸与游仙内容,并流露出道教思想倾向的作品共有8篇:《白云》,是典型的游仙诗;《遇铜山掘黄精》③,为颇具道教意味的采药诗,且有山水描摹;《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此四篇为带有游仙描写的山水诗;《代昇天行》,为拟代之作;《和王丞》,为鲍照与王僧绰的唱和之作。鲍照另有2首诗也颇具道教意味:《代淮南王》,据汉代淮南王崇信道教本事发散,为拟代之作;《萧史曲》④,是歌咏一位秦穆公时能吹箫作凤鸣的仙士之作。之所以称这些作品为涉道诗歌,主要由于其具备道教文化系统中的三方面内容:其一,神仙传说与成仙方术;其二,饵药服食的养生修炼方法;其三,道教典籍与道家经典中的语汇及典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鲍照未有系统的道教著作,这些涉道内容仅保存于其诗歌中,因此不免零散,但却不容忽视——这正能说明六朝独特的宗教文化环境以及鲍照思想的复杂性与多重性。
(一)玄言的“反动”:鲍照山水诗的道教语汇与“游仙”传承
《白云》诗云:
探灵喜解骨,测化善腾天。情高不恋俗,厌世乐寻仙。炼金宿明馆,屑玉止瑶渊。凤歌出林阙,龙驾戾蓬山。凌崖采三露,攀鸿戏五烟。昭昭景临霞,汤汤风媚泉。命娥双月际,要媛两星间。飞虹眺卷河,泛雾弄轻弦。笛声谢广宾,神道不复传。一逐白云去,千龄犹未旋。
《遇铜山掘黄精》诗云:
土肪閟中经,水芝鞱内策。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矧蓄终古情,重拾烟雾迹。羊角栖断云,榼口流隘石。铜溪昼森沉,乳窦夜涓滴。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蹀蹀寒叶离,灇灇秋水积。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岂怀梁郑客。得仁古无怨,顺道今何惜。
《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诗云:
荒涂趣山楹,云崖隐灵室。冈涧纷萦抱,林障沓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昼烛,地牖窥朝日。怪石似龙章,瑕璧丽锦质。洞庭安可穷,漏井终不溢。沈空绝景声,崩危坐惊栗。神化岂有方,妙象竟无述。至哉炼玉人,处此长自毕。
以上三首诗歌中提到的“炼玉”“炼金”“屑玉”,乃至服食水芝、黄精诸语,都是典型的道教语汇。《抱朴子·内篇·仙药》记载:“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8]196“《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玉屑服之与水饵之,俱令人不死。”[8]204《博物志》卷七记载:“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9]39这些均属于道教饵药服食的养生、求长生之法。此外,鲍照在诗中还抒发了与仙人、灵兽同游的幻想,“命娥双月际,要媛两星间”即欲邀女仙一同徜徉天际;“凤歌出林阙,龙驾戾蓬山”则描写了中国最为经典的瑞兽龙与凤,鲍照即想象出一番驾龙遨游、凤凰和鸣的奇丽景象。葛兆光言,道教为文学提供的意象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神仙与仙境,一类是鬼魅精怪,一类是道士及法术,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对于道教所提供的意象基本上停留在‘简单挪移’的阶段,尚未摆脱它的宗教性质”[10],鲍照如此吸纳、运用道教意象使其诗歌染上了浓厚的道教色彩。
除了直接运用道教意象外,鲍照还对道家经典进行巧妙化用。《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云:“神化岂有方,妙象竟无述。”其中“神化”与“妙象”二词值得注意。“神化”一词屡见于道教经典中,如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曰:“揣渊妙于不测,推神化于虚诞。”[8]284《上清大洞真经·卷四·青精上真内景君道经》记载:“大洞玉经曰:青精上华炁,太微玄景童。神化玉室内,飞羽逸紫空。”[11]东晋名僧支遁也曾写过“真人播神化”(《四月八日赞佛诗》四首其三),而所谓达人、至人、神人、真人,“实际上就是被《老子》《庄子》所概括或已达到老庄所标榜的人生境界的那类人”[12],《庄子·内篇·大宗师》即云:“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13]道教经典《太平经》也如此解释:“人生各自有命: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皆助天治者也。”[14]“妙象”一词,亦可溯源。东晋时期郭璞《游仙诗》即云:“明道虽若昧,其中有妙象。”同样写下很多游仙诗的东晋诗人庾阐《闲居赋》也提到:“至于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居处部四》引)《真诰》中记载一首紫薇夫人所作之诗云:“元(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真诰·卷四·运象篇第四·四月二十三日夜紫薇夫人作》)可见,“神化”与“妙象”并非一般语词,实则有着一定的玄学余韵与道教意味。此外,鲍照《遇铜山掘黄精》中“空守江海思”句,实则化用《庄子》之典:《庄子·外篇·刻意》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15]393鲍照《白云》诗诗题及立意,更是直接取自《庄子·外篇·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15]306《白云》诗云“情高不恋俗,厌世乐寻仙”“一逐白云去,千龄犹未旋”,与《庄子》句意正相吻合。
如果将鲍照此类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可以发现这样的共性——其内容多是山水题材,对山水景物以及登览游历有着细致的描写记录;结构上,是“总分总”或是“分总”的严整模式(首句或先显露隐逸与游仙的主题倾向,或直接以描绘景色为起始,中间部分则为集中的山水景物描绘,尾句便点明隐逸与游仙的题旨),和谢灵运山水诗的固定模式异曲同工⑤。只是谢灵运山水诗继承的是“玄言”余韵,而鲍照山水诗继承的是“游仙”传统,乃至进入道教畛域。若说《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中的“神化岂有方,妙象竟无述”似还带有一些玄言的余韵,那么鲍照在尾句则又话锋一转:“至哉炼玉人,处此长自毕”,回到道教主题——甚至可以说,鲍照的山水诗是对“玄言山水”的“反动”。在中国诗歌史上,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进过程中,鲍照确实发挥了“过渡”的作用,但他又有意无意地将山水诗引到“游仙”与宗教的苑囿中。
(二)宗教的“争胜”:鲍照庐山诗与佛、道二教关系辨疑
《登庐山》诗云:
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茏苁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囋晨鹍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穹岫閟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途,永与烟雾并。
《登庐山望石门》诗云:
访世失隐沦,从山异灵士。明发振云冠,升峤远栖趾。高岑隔半天,长崖断千里。氛雾承星辰,潭壑洞江汜。崭绝类虎牙,巑岏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韬树必千祀。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瑶波逐穴开,霞石触峰起。回互非一形,参差悉相似。倾听凤管宾,缅望钓龙子。松桂盈膝前,如何秽城市。
《从登香炉峰》诗云:
含啸对雾岑,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穹跨负天石。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旋渊抱星汉,乳窦通海碧。谷馆驾鸿人,岩栖咀丹客。殊物藏珍怪,奇心隐仙籍。
此三诗当为鲍照从临川王刘义庆于江州时所作。《宋书》刘义庆本传记载:“(元嘉)十六年(439),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440),即本号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16]1609此三诗应作于其间。既往研究一般将鲍照的庐山诗与佛教相联系,主要因为鲍照此时期所侍奉的幕主刘义庆信奉佛教,且庐山是晋宋间名僧慧远的道场,慧远于此处“创造精舍”,“别置禅林”[17],“讲经论道,撰写文章,培养弟子,邀请西来经师译经,与全国名僧保持密切联系,并与统治阶级上层深相结交,展开了多方面的大量的宗教活动,当时,庐山成了南方佛教的中心,慧远则成了佛教领袖”[18]。但是,鲍照的庐山诗无论是意象还是用典,均不能说与佛教有关联,而具有鲜明的道教意味:“羽人”“隐沦”“灵士”“鸿人”“丹客”所指均是道教中的神仙与修道者;“凤管宾”当为化用王子乔或萧史的典故,《列仙传》记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19]9“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19]11“钓龙子”则指“好钓鱼于旋溪,钓得白龙”[19]23的陵阳子明。这无疑说明,鲍照在面对庐山的奇幻风景时,最直接联想到的便是道教之仙人羽客,产生“游仙”之感。
庐山以烟气云雾蔚为绝妙,历来被诗人歌咏不绝,鲍照的庐山诗中便经常出现“烟雾”的意象或类似描写,如“永与烟雾并”(《登庐山》)、“氛雾承星辰”(《登庐山望石门》)、“含啸对雾岑”(《从登香炉峰》)。鲍照隐逸、游仙诗中的山水描写也屡有“烟雾”出场:如“攀鸿戏五烟”“泛雾弄轻弦”(《白云》)、“重拾烟雾迹”(《遇铜山掘黄精》)。烟雾云气正是山之灵秀所在,若质实地理解,“永与烟雾并”“重拾烟雾迹”则是鲍照想要回归自然、徜徉山水的一种诗意表达,也可以理解为表达归隐的倾向。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鲍照频繁使用“烟雾”意象,在中国诗学一贯重视象征与隐喻的传统中,有学者倾向于将“烟雾”解释为与佛教中的烧香拜佛以及“无常观”之联系[5-7]。其实,“烟雾”与道教关系更密。不只是佛教拜佛讲求烧香,道教亦如此,斋醮焚香即是道教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0],道教敬神要燃香供养,所谓“稽首礼太上,烧香归虚无”(《玉京山步虚词》),做法事时亦常设香炉,如灵宝斋法:“斋人以次左行,旋绕香炉三匝,毕。是时亦当口咏《步虚蹑无披空洞章》。所以旋绕香(炉)者,上法玄根,无上玉洞之天,大罗天上,太上大道君所治七宝自然之台。”(《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道教炼丹时更是烟雾缭绕。传说中的道教仙山往往云烟缥缈,迷离惝恍;仙人出场时常常腾云驾雾,云烟相随,所谓“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郭璞《游仙诗》);仙人及修道者通常不食五谷,而以烟云供养,餐霞饮气。由此联系鲍照于诗中所使用的仙人、灵士的意象典故,则不能不说鲍照眼中烟云迷离的庐山,更称得上是一座奇幻的道教仙山。
道教在庐山的影响早在鲍照之前即已建立。东晋湛方生曾作《庐山神仙诗》,赞美庐山为“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其诗云:“吸风玄圃,饮露丹霄。室宅五岳,宾友松乔。”[21]即便是信奉佛教的僧人慧远,对烟雾朦胧的庐山的初始印象也是“神仙之庐”:“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岩,上有悬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复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计奉在人间近三百年,容状常如三十时,俄而升仙,绝迹于杏林。……百余仞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雾焉。”(慧远《庐山记》)[22]隆安四年(400)仲春之月,慧远与庐山诸道人游于石门,行吟歌咏于庐山胜境的奇秀山水之间,也曾发出“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游石门诗序》)之感叹,慧远所作《游石门诗》亦充满道教游仙之意味:“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驰步乘长岩,不觉质自轻。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端坐运虚轮,转彼玄中经。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23]其中的“灵阙”“太清”“神仙”诸语均为道教语汇。这说明东晋时期玄、释相互影响的倾向,也表明庐山风景超绝人间,宛若神仙洞府,能使观览者天然产生游仙之感。自先秦以来就诞生的浪漫的神仙、仙境想象传统,至此已形成一种思维惯性,也发展成为成熟的宗教形态——道教,而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较晚,体系也未完备,相比之下自然难以使人产生最直接的联想。在鲍照写下庐山诗的二十年后,道人陆修静即于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入庐山修道,“嗜匡阜之胜概,爰构精庐,澡雪风波之思,沐浴浩气,挹漱元精”(《云笈七签·卷五》)[24]27,并于此广聚生徒,庐山道教的全盛局面也确实由此开启。
(三)“拟代”的隐情:鲍照真实思想与创作表现的悖离
如上所述,鲍照写下了不少道情浓厚的游仙诗,并于其中表达出遁世乃至求长生的愿景。问题是,鲍照真的相信神仙之说,甚至信奉道教吗?鲍照在两首拟代体乐府诗中表现出的态度值得注意。
《代淮南王》诗云:
淮南王,好长生,服食炼气读仙经。琉璃药椀牙作盘,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戏紫房,紫房彩女弄明珰,鸾歌凤舞断君肠。朱城九门门九闺,愿逐明月入君怀。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
晋代拂舞歌诗有《淮南王》篇,当是鲍照所拟对象。《淮南王》,其本事为汉代淮南王刘安事迹,《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25]而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第二》“淮南王安神仙”条曰:“淮南王安招募才技怪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才殚力屈,无能成获,……亲伏白刃,与众弃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养士,或颇漏亡,耻其如此,因饰诈说。后人吠声,遂传行耳。”[26]曹植亦言:“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其为虚妄,甚矣哉!”[27]227淮南王成仙之事,在后人看来已是荒诞不经,疾之为虚妄。鲍照此诗即描写淮南王刘安好道家长生之术,服食炼丹,并由此宠幸紫房(道家炼丹房)之彩女,遂致后宫生怨之事。鲍照此诗,正据淮南王本事发散,丁福林即认为“此诗很可能是托言淮南王刘安事,讽谏刘义庆佞佛之作”[28]。刘义庆晚年奉养沙门而“颇致费损”,鲍照诗中的淮南王迷恋道教长生之术而有“琉璃药椀牙作盘,金鼎玉匕合神丹”,此二事正极为相类。按此说则鲍照对过度迷信宗教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他曾为临川王作《佛影颂》,但也并非一味地讨好在上者,而是看到过度迷恋宗教带来的弊端,故而委婉规讽,也不失臣下之礼与义。
《代昇天行》诗云:
家世宅关辅,胜带宦王城。备闻十帝事,委曲两都情。倦见物兴衰,骤覩俗屯平。翩翻若回掌,恍惚似朝荣。穷途悔短计,晚志重长生。从师入远岳,结友事仙灵。五图发金记,九钥隐丹经。风餐委松宿,云卧恣天行。冠霞登彩阁,解玉饮椒庭。蹔游越万里,少别数千龄。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何时与汝曹,啄腐共吞腥。
从“事仙灵”“恣天行”等语以及“凤台”“箫管”所化用的萧史典故来看,《代昇天行》也是典型的“游仙”主题,同时,“五图发金记,九钥隐丹经”则具有浓厚道教修炼的意味。此诗依然是鲍照惯用的“游仙”与道教结合的写法,特殊的是鲍照于此诗中交代了“晚志重长生”的缘故,乃是由于俗情险恶,人世艰难。《昇天行》,鲍照以前有曹植之作。《乐府诗集》收录曹植《昇天行》二首,一为写仙山,一为写仙树,也是典型的游仙风格的作品。《乐府解题》曰:“曹植又有《上仙箓》与《神游》《五游》《龙欲升天》等篇,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与《飞龙》《仙人》《远游篇》《前缓声歌》同意。”[29]可见曹植也有不少作品表现游仙内容。鲍照《代昇天行》中“穷途悔短计,晚志重长生”“何时与汝曹,啄腐共吞腥”,也正合于曹植诗“俗情险艰,当求神仙”之意。鲍照乐府中不乏拟曹植之作,如《代陈思王京洛篇》《代门有车马客行》《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等,曹植可以说是鲍照重要的模拟、学习对象,其诗歌思想自然会对鲍照产生一定影响。虽然曹植写了更多的游仙作品,但事实是,曹植及其父兄并不迷信神仙方术之事[30],曹植《辨道论》即言:“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诚恐斯人之徒,挟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六骥而求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27]228其《赠白马王彪》更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27]366因此,曹植的游仙诸说并非真的企羡长生,而更多是一种“释愁”和“解闷”,并且“是和他固有的强烈的功业意识密切相关的”[31]。
鲍照有着与曹植类似的经历。《南史》本传记载,鲍照曾积极干谒临川王以求见知:“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32]鲍照的《拟行路难》其六自述心曲:“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他的苦闷也多是来源于“士不遇”,如《拟行路难》其十八云:“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数诗》云:“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瓜步山楬文》言:“信哉!古人有数寸之籥,持千钧之关,非有其才施,处势要也。”鲍照是如此积极地求仕进取,正如葛晓音所言:“鲍照毕竟是功名中人。”[33]鲍照有过进取与退守的矛盾,《拟行路难》其六云:“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沈德潜对此即言:“家庭之乐,岂宦游可比。明远乃亦不免俗见耶!江淹《恨赋》亦以‘左对孺人,顾弄稚子’为恨,功名中人,怀抱尔尔。”[34]亲人稚子的家庭温暖尚且使鲍照难平胸中意气,更何况是隐遁避世与鸟兽同栖呢?故而鲍照曾言:“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飞蛾赋》)可见他并不看好隐逸行为——而这正与其诗中描述的隐逸求道内容相悖离。这正与曹植的真实思想与创作表现如出一辙,遂有了异代而“同歌”的《昇天行》。
虽然鲍照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他并非乐于成为栖身野泽、隐遁避世的道教徒,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过度崇信宗教的弊端,但是他却对道教及老庄经典如此熟知,作诗时相关的典故及道教语汇可谓是“信手拈来”,并于诗中扮演着“慕隐者”的身份。虽然一般认为魏晋六朝文士修习道教、成长于天师道的文化氛围中实为常态,但也有必要进行更细致地追究——魏晋六朝时代虽普遍盛行道教文化,流行天师道信仰,而其实也有朝代之异;魏晋六朝文士虽均能受到道教文化熏习,而在接触道教的媒介上也因人之异,个人的家族与地域的成长环境、仕宦与交游的社会经历均是不同的。而作为六朝人的鲍照又有何独特的与道教接触的契机呢?下文试从两方面展开说明。
二、政治与“表演”:鲍照思想与刘宋上层阶级好尚之互动
刘宋帝王及宗室出身于地位较低的士族次门,又以武力发家,于文化方面自然逊色于累世之大族,但其在掌权后尤为重视修养,爱好文义、广延才学之士⑥,由此带来刘宋文学彬彬之盛,并且,刘宋宗室的文化气质与偏好也引导着彼时学术、文风之走向⑦,乃有“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打开”(沈德潜《说诗晬语》)[35]之诗运转关——此即刘师培所谓“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36]。鲍照作为刘宋时期的才学之士,尤以“辞章之美”显拔,历仕于刘宋宗室幕府与宫廷之中,写下不少奉和、奉颂之作,与在上者密切互动,其中尤以歌咏“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16]1610的《河清颂》,及歌颂孝武帝平定京邑的《中兴歌》[37]106-108为代表,其他还有如为临川王所作的《凌烟楼铭》《佛影颂》,为始兴王所作的《代白纻舞歌辞》《蒜山被始兴王命作》等,充分显露其“侍从文人”的底色。为“迎合”在上者,鲍照甚至有意自降文章品格:“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16]1610考察鲍照隐逸、游仙诗创作之缘由,即可以从刘宋上层阶级的活动中寻找到答案。
中国古代王权与宗教关系密切,一方面,王权需要利用宗教稳固人心,加强统治,这是使自己统治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皇权也要对宗教进行管控与限制,防止其破坏社会安定,影响统治秩序。魏晋南北朝时代,如三国时期曹操网罗方士、西晋司马伦依信奉五斗米道的琅琊孙秀称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崇道等,均体现王权与宗教的特殊关系。更特殊者,即帝王本身具有宗教信仰,其在政时为之宣扬,于是举国乃成风习。观刘宋一朝政治与风俗,即为此特点。赵翼于《廿二史札记》中评价刘宋政治特点为“宋齐多荒主”“宋子孙屠戮之惨”[38],而有学者指出:“南朝刘宋朝荒淫暴虐之主辈出,君主行为多怪诞不经,象大肆杀戮宗室及亲属之间乱伦无礼等现象更是千古罕见。……刘裕家族深受南方流行的道教影响,道教是其传身立命之秘缘,他们许多怪诞行为多与此或疑与此有关,刘宋宫廷政治剧变多为道士、道徒的阴谋所致,或是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39]李国荣也说:“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小朝廷,尤其笼罩着巫师仙道的影子。”[40]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家族姻党关系均可体现受天师道之浸染,林飞飞即判断刘宋皇族为世奉天师道之家族[41]。刘宋帝王在宗教政策与文化政策上亦多有对道教的扶植。
鲍照的仕宦经历主要在宋文帝和宋孝武帝朝⑧,因此,要了解鲍照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氛围,尤其需了解此两朝帝王及宗室的相关活动。史载宋文帝刘义隆是一位“留心艺术”的帝王,刘宋所立“四学”之一的“玄学”,即由此而设:“元嘉十五年,……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16]2518-2519《晋书·艺术列传》中对“艺术”有详细解释:“艺术之典,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然而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虽存矣,伪亦凭焉。”[42]2467由此可知,宋文帝所留心之“艺术”,当与“神道设教”、卜谶之术、巫觋鬼神之说有关⑨,而巫觋道和杂术实与道教密切关联,许地山即说“中国古代神道也是后来道家底重要源头”[43]。除了“留心艺术”外,也有证据表明宋文帝笃信仙道之说,《宋书·何尚之传》便记载:“是岁(元嘉二十三年)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16]1898宋文帝亦礼遇道士,著名道人陆修静即受到其重视、延邀:“宋元嘉末,因市药京邑,文帝味其风而邀之”(《云笈七签·卷五》)[24]27,“宋文帝召之于内,讲理说法,不舍晨夜,孜孜诱劝,无倦于时也”(《三洞珠囊·卷一》)[44]。刘宋皇族更是如此,宋文帝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以师事陆修静,“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七十九道部二十)。宋孝武帝刘骏更是对鬼神巫术甚为崇奉,不仅重修蒋山祠,甚至以巫招鬼。《南史·后妃上·殷淑仪传》便记载孝武帝曾让巫者召其死去宠妃的鬼魂之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孝武帝小字道民,其名字亦颇有天师道信仰的意味。林飞飞指出:“孝武宫闱之丑,谓其违礼乱伦、淫乱无度,此盖受到当时道教房中术之影响。”[41]198帝王崇道,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曾因廉俭得到宋文帝褒美的梁州刺史刘亮,“忽服食修道,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道胤,令合仙药。至益州,泰豫元年药始成,而未出火毒。孙不听亮服,亮苦欲服,平旦开城门取井华水服,至食鼓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后人逢见,乘白马,将数十人,出关西行,共语分明,此乃道家所谓尸解者也”[16]1496。由此,刘宋举国上下的风俗可见一斑。
除了崇道行为外,刘宋帝王还存在“慕隐”心理,并多次进行“招隐”活动。《宋书·隐逸·宗炳》记载:
高祖(宋武帝)开府辟召,下书曰:“吾忝大宠,思延贤彦,而兔罝潜处,考槃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伫。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16]2503
《宋书·隐逸·周续之》记载:
上(宋武帝)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慠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16]2505。
《宋书·隐逸·雷次宗》记载:
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16]2518-2519。
《宋书·隐逸·王素》记载:
世祖(宋孝武帝)即位,欲搜扬隐退,下诏曰:“济世成务,咸达隐微,轨俗兴让,必表清节。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风,琅琊王素、会稽朱百年,并廉约贞远,与物无竞,自足皋亩,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难进。并可太子舍人。”[16]2520
《宋书·本纪第六·孝武帝》记载:
大明六年(462),“下四方旌赏茂异,其有怀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当世,或识通古今,才经军国,奉公廉直,高誉在民,具以名奏。”[16]140
《宋书·本纪第八·明帝》记载:
泰始五年(469)九月己未诏:“其有贞栖隐约,息事衡樊,凿坯遗荣,负钓辞聘,志恬江海,行高尘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时以名闻。将贲园矜德,茂昭厥礼。群司各举所知,以时授爵。”[16]181
可见刘宋一代由在上者提倡的风气即为表彰清节、礼遇隐者,嘉奖“怀真抱素”“志恬江海”的品格与行为。鲍照曾和时任秘书丞的王僧绰有过唱和之作,《和王丞》诗曰:
限生归有穷,长意无已年。秋心日迥绝,春思坐连绵。衔协旷古愿,斟酌高代贤。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夜听横石波,朝望宿岩烟。明涧子沿越,飞萝予萦牵。性好必齐遂,迹幽非妄传。灭志身世表,藏名琴酒间。
王僧绰出身于著名的天师道世家琅琊王氏家族,据其本传记载,其人“沈深有局度”,且“谦虚自退”[16]2022,也难怪鲍照会与之言“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性好必齐遂,迹幽非妄传”。鲍照此诗或即为迎合王僧绰所作,同时也不能不说和刘宋时代“慕隐”之风气有一定关系。因此,“功名中人”的鲍照也会偶作“灭志身世表,藏名琴酒间”之语,巧妙地扮演“慕隐者”的身份——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性“表演”呢?
此外,鲍照释褐于临川王刘义庆幕下,于其幕府中任职约有八年之久[37],幕主刘义庆的活动或也对鲍照产生一定影响。史载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以为宗室之表”[16]1609,“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16]1610。刘义庆最著名的文学活动就是编写《世说新语》。据周一良考察,刘义庆正是“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45]。但对于《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学界多有异辞,有学者推断鲍照也应参与到编写《世说新语》的活动中⑩。江左文士以谈玄析理为风尚,并主要围绕《老子》《庄子》《周易》三部玄学经典,《世说新语》即记载了大量江左文士的清谈与玄学的资料。鲍照或也以编写《世说新语》为契机,搜集、了解前代掌故与魏晋道、玄风流,或有心或仅作“游戏之娱”地进行相关诗歌创作,《世说新语》中的相关玄、道内容自然在鲍照的诗歌中留下蛛丝马迹——正如上文提及,鲍照于其隐逸、游仙诗中经常化用《庄子》典故,或与此有一定关系。
总之,鲍照身处于这样崇道的政治氛围与文化风气中,不能不受到道教风习的影响,因此其诗文中出现涉道之语便不难理解了。
三、地域与家族:鲍照与滨海地域天师道联系因由之推测
陈寅恪曾言:“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46]鲍照的道教书写除了受到刘宋朝“在上者之提倡”的影响外,亦可能受到滨海地域天师道之环境浸染。苏瑞隆曾指出,鲍照应受到江南地区蓬勃发展的道教的影响,但其并非道教徒[3]40-41,此论或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实不仅是江南地区,永嘉南渡之前鲍照家族即居于徐州东海郡(故世称其“东海鲍照”),此亦天师道传教之滨海区域。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证,魏晋南北朝时的天师道世家即有东海鲍氏,以鲍靓为代表[47]。魏斌即称以鲍靓为代表的南渡道士为“神仙侨民”,“这些‘流移’于江南的道士们,是神仙知识的重要宣传者”;“东晋初期存在于晋陵、句容的几个仙道传承线索,如魏华存、刘璞—杨羲—许谧父子,鲍靓—葛洪、许迈,紫阳真人周君、清灵真人裴君—华侨,也都可以置于这一背景下理解”[48]。
据《晋书·艺术列传》载:“鲍靓字太玄,东海人也。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稍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南海太守。……靓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42]2482鲍靓还是东晋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丹阳葛氏)的老师兼岳父,“(葛洪)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42]1911。鲍靓和知名道士许迈(丹阳许氏)亦有过交往,“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知之。迈乃往候之,探其至要”[42]2106。据王青《葛洪家世生平五题》一文之说,鲍靓与道士葛洪、许迈的交往活动在镇江丹阳一带展开较为合理,因彼此居地相近。鲍照诗文显示,其家族于永嘉南渡后迁至京口地区(今江苏镇江市),这正与鲍靓侨迁之地一致,即均在今镇江一带。更进一步说,我们甚至不能排除鲍照家族为世奉天师道家族的可能性:中古家族往往聚族而居,同出自东海鲍氏家族的鲍靓信仰天师道,南迁的鲍照家族亦居于京口,鲍照家族与天师道很可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再加上江南地区道教之浸染,风气氛围愈发浓厚,鲍照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只是鲍照一心于功名及进取,故从家族天师道之信仰转型,而更类儒者,这种信仰转型及改宗的例子在六朝并不少见。
若按此说,则鲍照的创作活动更具解释缘由。鲍照曾作有一首《咏萧史》(一名《萧史曲》),歌咏一位秦穆公时的仙人,其诗云:
萧史爱长年,嬴女恡童颜。火粒愿排弃,霞雾好登攀。龙飞逸天路,凤起出秦关。身去长不返,箫声时往还。
诗中描述的萧史能够驻龄长生、不食五谷,爱好攀登霞雾,常吹箫曲乘龙驾凤往返。此诗充溢着浓厚的仙道意味。而鲍照为此作,则或有一定偏好、趣味所在。上文曾推断,鲍照作《和王丞》有“政治性”表演的意图,若鲍照家族世奉天师道,则鲍照对王僧绰所言之“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诸语,当更缘于其二人相同的宗教信仰。
四、结语
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和创作都是复杂的。从思想来看,鲍照身上积极入世之儒家思想的成分更多,但同时由于受到时代思潮、上层社会风气、地域传统的影响,以及仕途挫折的打击,鲍照也偶有道教思想,这种思想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诗歌创作角度看,除了主流的风格以外,也会有“异格”之作,鲍照表现隐逸、游仙情怀、充满道教意味的诗文即是如此。
能够留名于文学史册的作家都有其卓然独标的文体成就以及个人风格、特色所在,如东晋南朝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及颜延之的典密藻丽、谢朓诗的疏朗清逸,而鲍照则以乐府诗体的成就,以及俊逸豪放、奇矫凌厉的诗文风格为代表,但鲍照涉道诗歌也是其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鲍照涉道诗歌创作,不仅呈现出鲍照思想与创作的复杂性,同时也体现了刘宋时代环境的独特性:鲍照的涉道诗歌当与刘宋上层阶级的偏好与提倡有一定关系,体现了刘宋文学“在上者之提倡”的特质以及鲍照“侍从文人”的底色,同时,也反映出江南地区天师道的传播与发展对鲍照的影响。概言之,鲍照这些“异格”之作,既体现了其思想、经历和创作的多面性、复杂性、丰富性,也折射了刘宋时代独特的政治面影、思想脉动,具有发历史之“幽微”的独特价值。
注释:
①本文所引鲍照诗文均出自鲍照、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不一一出注。
②据钱仲联增补集说校本《鲍参军集注》。
③宋本诗题“遇”作“过”。
④宋本题目作“咏萧史”。
⑤林文月提出,鲍照有意追随模拟谢诗句眼之用法、结构,在风格上接近谢灵运诗,在大谢与小谢的山水诗之间扮演过渡的角色。参见林文月《山水与古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第71—94页。
⑥如《南史·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记载:“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595页) 《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记载:“世祖孝武皇帝,讳骏。……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南史》,第55页)《宋书·卷八·本纪第八·明帝》记载:“(宋明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第186页) 《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一》记载:“(临川王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宋书》,第1610页)
⑦唐长孺曾论南朝宫廷文学的产生及其特点与南朝寒人掌机要的密切关系,详见其《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载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第105—107页。
⑧鲍照于宋文帝时期曾先后辗转于临川王刘义庆幕府、衡阳王刘义季幕府、始兴王刘濬幕府,于宋孝武帝时期仕于朝廷,历任海虞令、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安令,随后又为临海王刘子顼所辟,于刘子顼叛乱中被杀害,终于幕府参军一职,并未仕于宋明帝政权。
⑨事实是,刘宋皇室的确有着罕见的鬼神信仰。如宋文帝之子刘劭即迷信巫鬼之说,任用女巫严道育,“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并信惑之。……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宋书》,第2662页)刘劭反叛起兵时,甚至供奉鬼神,“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宋书》,第2671-2672页)宋明帝刘彧也格外迷信鬼神:“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宋书》,第186页)
⑩鲁迅言:“《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64页) 范子烨曾推断:“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其目的正是为了编撰《世说》《幽明录》等著作。”(范子烨《〈世说新语〉新探》,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4期,第118—124页) 曹之也从多方面分析得出《世说新语》成于众手而由刘义庆主编负责的结论(曹之《〈世说新语〉编撰考》,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98年第1期,第29—33页)。丁福林进一步提出:“是《隋志》列于刘义庆名下之著作,除《刘义庆集》八卷而外,它书多出自其手下众文士如鲍照、袁淑等人之手……袁淑自江州始入义庆幕,而之江州前何长瑜已离义庆幕,是二人仅参与以上著述之部分,而鲍照则始终参与其中矣。”(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