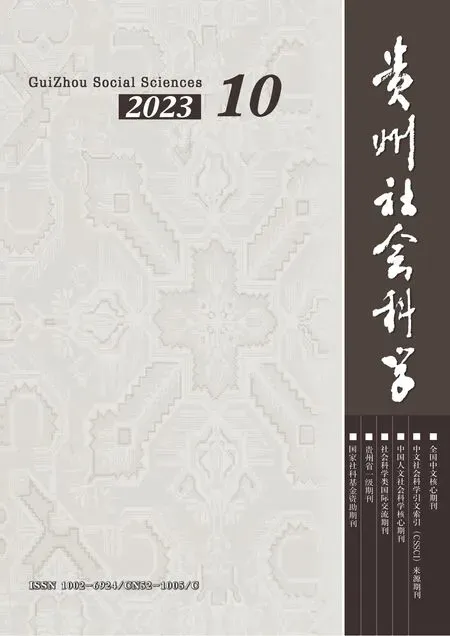论宋代美学的雅俗分野与近代化转型
——以宋代琴学为个案
李晓梦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3)
宋代美学的近代化转型突出地表现在宋琴的“近代化”上。“尚琴”是宋代自上而下的美学运动,古琴之“功能”定位是左右宋琴近代化进程的焦点问题。与皇家审美意识形态“复古”为主的琴治观相比,民间琴家更加关注琴的艺术表现力,后者体现了更为纯粹的审美需求。古琴的下移意味着平民精神世界的雅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将此一“近代”称为“平民发展的时代”:首先是宋代琴人队伍所出现的以平民参与为主要模式的新结构。其次是琴的神圣性降低,传统的乐教功能在宋代遭遇了温和的挑战,突出了追求程式化理性的新要求。再次是系统化、专业化的琴学生态链的塑造以及对个体主义风格的新表现。其结果是,宋代琴学在以节奏、指法等为对象的艺术技法方面呈现出技术化、程式化、标准化的新特征;在琴论与琴词创作等传播方面具有世俗性、娱乐性、广泛性的新特点,它们都昭彰地显明了宋代美学所发生的本质之变与近代化转型。
更值得玩味的是,纯粹审美导向之下的宋琴,在其内部孕育了对其艺术功能转型的要求,在官方与民间、雅与俗之间获得了微妙的平衡。虽有功能定位上的错位,皇家和世俗两股意识形态能量始终相向而行,雅俗并济,互相宽容而没有发生断裂。于是,一股具有“活性”的、强大的“艺术意志”在中国琴史上首次以汹涌的来势,大规模、全方位地突破了古代阶层等级的限制,广泛地席卷了宋人,激活了宋琴艺术与审美的新风尚,并为明清琴学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基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的美学,在宋代所发生的彼此间的交织、互动与摩擦。如至道年间,宋太宗与琴待诏朱文济曾围绕“古琴弦制”的问题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宫廷琴议,君臣二人各执己见、互不让步,太宗以钱财名利诱之,并以加赐文济同僚折辱之,朱氏仍持守初衷。最终还是太宗改变态度,此事方才罢休。此事载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为朱文济人生简历中着墨最多的一笔:
朱文济者,金陵人。专以丝桐自娱,不好荣利。上初欲增琴阮弦,文济以为不可增,蔡裔以为增之善。上曰“古琴五弦,而文武增之,今何不可增也?”文济曰:“五弦尚有遗音,而益以二弦,斯足矣。”上不悦而罢。及新增琴阮成,召文济抚之,辞以不能。上怒而赐蔡裔绯衣,文济班裔前,独衣绿,欲以此激文济。又遣裔使剑南,获数千缗,裔甚富足;而文济蓝缕贫困,殊不以为念。上又尝置新琴阮于前,旁设绯衣、金帛赏赉等物诱文济,文济终守前说。及遣中使押送中书,文济不得已,取琴中七弦抚之。宰相问曰:“此新曲何名?”文济曰:“古曲《风入松》也。”上嘉其有守,亦赐绯衣。文济风骨清秀若神仙,上令供奉僧元蔼画其像留禁中。[1]
在这场宫廷琴议中,朱文济三次反对太宗。其一,朱文济以九弦琴演奏效果与七弦琴无异反对太宗为琴增弦;其二,九弦琴已成,太宗令文济抚琴,文济辞之以不能;其三,在不得不行太宗之命时,朱文济仍然没有妥协,在九弦琴上弹奏了一首只用到七弦的曲子,以示操守。太宗与朱文济争议的焦点表面上是古琴改制的问题,实质产生于二者对古琴属性的不同认知与需要。古琴在历史进程中积淀了复合性的功能,如作为音乐器物,琴所具备的艺术属性,作为上古圣王的治世法器,琴则具有标榜礼乐盛世的政治属性。后者是太宗眼中的琴,因此太宗才以文武王自譬,意在通过始制九弦琴开创大宋王朝的南风之世。太宗屡次折辱朱文济,是因为朱氏的反抗不仅是对太宗乐学素养的挑战,还是对皇权的质疑。
宋太宗制九弦琴以效先王的意图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它奠基于琴的巫术性质,以及舜治时代以南风琴播撒“生养之气”的奇妙效用。这种在人类文化发展早期阶段所形成的,洋溢在音乐审美功能之外、且以超乎现实的巫术效果冠名的行为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原始魔法”[2]39。在早期的音乐进化阶段中,很大一部分原始音乐脱离纯美学享受而倾向于实践目的。它被表述为出于魔法的目的,尤其是辟邪(崇拜)和祛邪(医疗)的需要。据此而言,太宗对南风琴的崇拜与“琴音调而天下治”[3]的琴治思想仍然属于“原始魔法”的范畴。除太宗外,宋徽宗的五等琴、宋仁宗的两仪琴与十二弦琴都体现了宋代皇室“以琴治国”的乐教观念,而以艺为生的琴待诏朱文济则展示了一种“出于纯实践的目的使用传统乐音形式,唤醒人们的纯美学需求”[2]40的另一种音乐原则,它是对原始巫琴功能的祛魅,代表了宋代古琴音乐理性化与专业化的一极。
能否依据人的审美与表现需要改变琴的乐音调式与琴曲演奏技法,是古琴音乐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以艺术史视野区分并判断琴史之古代与近代分野的独立标准。这说明,与魏晋时期小众精英的艺术自觉不同,宋代琴人队伍的结构化变形、传承方式的革新以及琴词结合后琴乐的民间传播,都使宋代古琴在更加广泛地意义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雅俗的重塑与分野过程中,完成了宋代美学的近代化转型。
一、皇贵向江湖:宋代琴人队伍的结构化变形
宋代琴人队伍的结构化变形,是指不同社会身份琴人产生了人数比重上的变化、发挥了与以往历史相比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并造成了宋代琴乐的整体改观。
造成宋代琴人结构化变形的主要力量,源于民间琴人数量的剧增以及为宋代琴学带来的显著影响。许健《琴史新编》载先秦琴人6位,其中伯牙、雍门周为民间琴人,其余为司乐乐官;两汉琴人9位,包含宫中的鼓琴待诏、皇后、大臣;魏晋琴人9名,有建安七子阮瑀、竹林七贤阮籍、嵇康、阮咸等;南北朝琴人4名,皆出自名门,无民间琴人。隋唐琴家9名,民间琴手有李疑、赵师赵耶利、董师董庭兰;而宋代琴家22名,民间琴人则有13位之多,分属琴僧、隐士与浙派琴家三类,如夷中、知白、义海等为琴僧,崔闲为隐士琴家以及郭楚望、刘志方、毛敏仲、徐天民等著名的浙派民间琴人。宋代民间琴人在琴史中的高频提名说明他们在这一时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成为宋代琴学中不可忽略的一支力量。
民间琴人是相对于皇室贵族与士人精英而言的、不处于朝廷体系之中的闲散琴客,不仅包括山林隐士、道士、琴僧、士大夫所养的清客,还囊括了没有被琴史提名的青楼琴伎等。这些看似隐藏在历史浪潮中不为人所见的小角色在宋代突然有了大放异彩的机会,在他们的参与下,宋代琴学在琴论、演奏形式、琴曲内容以及古琴的传播与传承等方面都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如琴论中出现了大量对琴事礼仪的关注与强调、对基础琴礼内容的细节化与程式化规范等,实质是对面向民间琴人的抚琴手册的完善;江西派对民间口占曲调的吸收及其对琴词调子的改创;为琴曲赋艳词的花间趣味以及民间琴人在琴派的建立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如郭楚望之于浙派、崔闲之于江西派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古琴的精英传统,实现了古琴“从皇贵向江湖”的时代转向。
北宋琴僧是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其一者,北宋琴僧队伍形成了连贯的传习链,代际之间具有明显的、可追溯的师承关系,具备系统的有序性。“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4]291,沈括言京师僧夷中学琴于待诏朱文济,又将所学传授给义海,那么可以证明北宋的琴僧脉系并非后世所撰,而是当时就已经有了公认的师承关系。京师僧夷中得朱文济真传后,又有弟子义海、知白,义海的徒弟则全撰写了在琴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则全和尚节奏指法》流于后世,则全有徒弟照旷,照旷的活动年代在政和与宣和年间,可见这支琴僧系统几乎绵延了整个北宋。其二者,北宋琴僧声名远播,知名者众,如宋初“九僧”中有七僧都能琴,此外还有上述提到的京师僧夷中、义海、知白、则全、照旷等。“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4]291,沈括笔下的义海不仅勤奋刻苦,琴艺精湛,还能“得于声外”,有文人士大夫的风度趣味。义海还参与了北宋有名的“韩愈听琴”之争,反对欧阳修与苏轼将《听颖师琴》之琴作为琵琶的解读,后来被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批评,可见义海文论,已进入当时文人的视野。此外,高宗时有《墨庄漫录》载则全的弟子照旷以琴闻名:“钱塘僧净晖子照旷,学琴于僧则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5]《春渚纪闻·琴书杂事》中也云照旷抚奏《广陵散》,“音节殊妙,有以感动坐人者”。对照旷琴艺之高妙的赞美还可见李处权的《听照旷尘外琴》,描写了照旷抚琴时自己难以言表的感受,并以“尘外琴”称赞照旷超凡脱俗的琴艺。不仅如此,朱文济的琴僧徒弟夷中在宋代的影响也很大,时人听琴时会想起夷中、知白的琴艺,“夷中知白骨已朽,后来如师亦稀有”[6]等等。其三者,北宋琴僧与文人士大夫广泛交游,扩大了琴僧队伍的影响力。琴僧知白就与当时很多文人都有交往,如欧阳修在听知白抚琴后作诗《送琴僧知白》:“吾闻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无其传。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知白弹……酒酣耳热神气王,听之为子心肃然。”欧阳修认为知白之琴可以弥补他未曾听过夷中琴的遗憾,不仅归功于知白的高超琴艺,还源于知白对夷中琴学的继承。……除《送琴僧知白》外,欧阳修还在听过知白弹奏《平戎操》后作了《听平戎操》,认为除了知白,没人再能用琴表达出这种令人唏嘘的感受。梅尧臣也有《赠琴僧知白》,诗云:“上人南方来,手抱伏牺器。颓然造我门,不顾门下吏。上堂弄金徽,深得太古意。清风萧萧生,修竹摇晚翠。声妙非可传,弹罢不复记。明日告以行,徒兴江海思。”[7]诗中记录了知白携琴登门拜访梅府,为梅尧臣抚奏一曲后便离开梅府之事,说明知白常以琴与文士结交。琴僧与文人士大夫的广泛交游客观上导致了琴僧的文人化。北宋文人郭祥正曾言“昔年知白师,悟禅兼悟律,能画亦能诗”[8]。他们长期受到文人趣味的熏染,在行为举止、言谈修养方面都受到士大夫习气的影响。琴僧释惠洪与苏轼、黄庭坚都为方外之友,常常“勤田园以供伏腊,玩琴书以娱宾客”[9],宋人许彦周称其诗“颇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类衲子”[10]。琴僧不再囿于寺院清规,虽然身在方外,但却大行世俗之事。琴僧思聪“徽宗大观、政和年间携琴游汴,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11],思聪以能于琴书不但与权贵交好,还能在还俗后为自己谋得官职,侍奉于御前,可见“琴”能够作为琴僧穿梭于不同身份、阶层之间的通行证。
除了琴僧系统外,士大夫门下的琴客也是宋代民间琴人的代表,宋代著名的琴人姜夔、郭楚望、徐天民等都是豪门清客。这一群体为宋代古琴音乐作出的贡献是:一、始终以琴的艺术性为先,关注琴的音律、音调与琴曲艺术性的音乐学问题。如姜夔面对南宋宫廷乐制雅俗杂糅等问题,向朝廷进献《大乐议》:“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箫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12]姜夔对乐制的考量包括了琴的弦质、琴轸调律、琴音合调与琴与其他乐器合奏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是从音乐的演奏实际出发而得出的判断,是以乐人的视野提出的音乐专业问题。二、创立了浙派古琴,改变了琴学家传的传统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演奏风格与艺术语言,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古琴流派。浙派创始人为郭楚望,南宋嘉泰、开禧年间,郭楚望为宋代光禄大夫张岩的琴客,郭楚望有入室弟子刘志方,刘志方又授琴于毛敏仲与徐天民。徐天民将浙派发扬光大,因此有“浙操徐门”之称。他们不仅都是民间琴人,毛敏仲与徐天民还都是南宋司农卿杨瓒的座上琴客。三,编纂琴谱,推动了宋代皇室阁谱的世俗化,为古琴在民间的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张岩的好友韩侘胄家中收藏有秘抄的宫廷阁谱数卷,韩侘胄被陷害后,张岩得其琴谱,与自己平日收藏的民间琴谱合并,成《琴操谱》十五卷。张岩被罢官后,琴谱又交予郭楚望,为其门下弟子传习之用。与此同时,杨瓒及其门客毛敏仲、徐天民也依据该谱每日“朝夕损益琴理”,汇编成《紫霞洞谱》十三卷,共计468曲,成为浙派琴谱之宗。元人金汝砺之《霞外谱考》以及明人朱权之《霞外神品》等,都是由《紫霞洞谱》演化而来,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浙派”使宋代成为琴史上首次出现由民间琴家为主体并历经数代仍有传承的琴学谱系的关键时段,是民间琴学的重要代表。它的重要意义是,使琴学传承谱系能够独立于宫廷之外,琴人有了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摆脱了政治身份的约束,开辟了以古琴艺术为主题的新的发展空间。
从宋代琴人的角度考察宋代美学的发展情况与历史走向是将“感性的人的活动”作为历史的实践,是从根本上挖掘宋代美学生成内在动因的有效途径。在古代封建等级社会中,不同群体所占有的资源依据其社会阶层而划分,琴作为法器、治器、乐器的复合功能属性令其始终掌握在上层建筑的精英群体手中,民间琴人很少能有机会占据主动、掌握话语权、参与琴学的构建,在琴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除了令人瞩目的北宋琴僧系统与南宋的浙派古琴外,与宋代士大夫交游的民间琴人还有被尊称为“处士”的江湖琴士,如王镐、林逋、陈季常、唐异等,他们虽然身隐于山林,但却在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中保存了不少的经典诗篇。苏轼《杂书琴事》是为隐士陈季常所作,范仲淹有《寄赠林逋处士》《与唐处士书》等。这些江湖琴客凭借高超的琴艺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以另一种方式被历史记录下来。此外,宋代道士也活跃在士人阶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苏轼《听武道士弹贺若》等都是听琴诗,魏了翁与刘道士、真德秀与萧守中道士的交往都是道士携琴登门拜访,以琴论道。
从这些民间琴人与士人的交往中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观念是民间庶人难以跨越的屏障,而“琴”恰好可以成为突破阶层壁垒的敲门砖。北宋琴僧系统始于宫廷琴待诏朱文济、浙派琴谱源于皇家秘阁,都有赖于宋代民间琴人向精英群体的靠拢,其实质是民间琴人对上层资源的攫取。对琴艺与琴谱两项核心资源的占有迅速成为了扩充民间琴人队伍的本质动力,改变了以家学与精英阶层内部流转习练为主的传统琴学传承方式,促使了宫廷琴学的民间化,客观上造成了宋代琴学“从皇贵向江湖”的新局面。
二、雅琴落花间:宋代美学中的琴词配伍及其雅俗分野
“调子”是词与曲在琴乐中两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它奠基于同时占有歌辞与音乐的弦歌,《尚书》中的“搏拊琴瑟以咏”就是“弦歌”的原型。孔子整理诗经时,“三百五篇,皆弦歌之”,证明以辞入琴乐是琴人的惯常作法。但音乐与歌辞二者形式的变化组合会决定乐曲体裁出现不同音乐结构的变化,如宋词的前身“曲子词”是先有曲调后填词的口语韵文,句式参差的长短句是曲子词的主要形式,而以长短句入琴乐正是促进“调子”体裁萌发的重要历史背景。“调子”专指以“曲子词”为歌辞的短小琴歌,伴随着宋词的传唱成为了北宋时期盛行的琴歌体裁。“倚声填词”的宋代音乐文学为拥有悠久弦歌历史的古琴提供了革新的契机,并借靠宋词的鼎盛成为了花间趣味的典范,在民间获得了更大的市场。
“调子”对“曲子词”的改造是对后者音乐部分的替换,即将曲子词中的曲调替换为琴调,由于琴的弦乐个性,无论是在音色还是音乐表达的效果方面都会产生变化,是一种有意识的审美改造。在“调子”体裁中,“词”与“曲”的配伍不仅要基于音乐形式的吻合,还要面对雅俗趣味的吻合,这就是说,琴的介入对曲子词造成的变化,不仅是音乐意义上的,更是审美趣味上的。为了与雅琴的韵味配伍,“调子”中的歌辞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使源于民间的曲子词具备琴的雅韵,达到“由俗至雅”的品味提升。
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与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换玉》;三曰《夹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叶下闻蝉》;九曰《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只命曰《贺若》。太宗尝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辇挽,玉鳞背冷清风远。”[13]
关于调子的来源有二说,一为隋代宫廷琴师贺若弼,二为唐代宫廷琴师贺若夷,无论实际如何,都说明调子与曲子词的出现时间基本是一致的,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博金》《不换玉》是典型的民间曲名,是调子主题中曲子词影子的遗存。这则材料透露出的另一信息是,太宗酷爱的这十个宫中调子事实上只剩余其音乐部分,因而需要命近臣重新撰词。这是由于琴调在音乐形态上的复合性,词与曲往往不能同步流传,因此便出现了“倚调声、填新词”的需要。
由于宋太宗的钟爱,《越江吟》琴调被三赋其词,分别为苏易简《瑶池宴》、贺铸《琴调宴瑶池》与苏轼《瑶池燕》,并铸就了以苏易简的《瑶池宴》为正体的新词牌,是自琴调而成词牌的经典个案。不仅如此,琴调赋词与词人对琴调曲趣的体味有关,如苏轼的《瑶池燕》已非苏易简与贺铸所作的宫廷之宴,而是对“莺莺燕燕”的春闺之情的描写:“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揾。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来解幽愠。低云鬟、眉峰敛晕。娇和恨。”苏轼自序《瑶池燕》曰:“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与人云。”[14]“声情相协”是琴调创作的重要艺术原则,由于琴调与曲子词的关系,前者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后者的烟火气息。苏轼将《越江吟》改为艳词便是察觉到了该调子中的“花间调性”,认为闺怨词更能匹配该声调的“怨咽”之感。朱长文亦言北宋琴调:“细调琐曲,虽有辞,多近鄙俚,适足以助欢欣耳。”[15]虽然苏轼的艺术嗅觉如此灵敏,但苏轼仍然对此有所避讳,其原因是琴始终占据着雅乐之器的高位,与艳词不协,因此叮嘱陈季常“勿妄与人云”。可以看到,苏轼面临的困境与朱文济极为相似,他们都坚持琴的艺术立场,只是苏轼身居士大夫阶层,知晓政治利害,处事更为婉转隐蔽些。此外,琴调改艳词方便了士人家中的琴伎与青楼琴伎的传唱演艺。琴与词的艺术创作问题成为琴女与文人交际的热点话题,如姜夔和家伎小红的词曲吟作、名伎琴操对秦观《满江红》的改写等。既迎合了宋代文人的花间趣味,又提高了乐伎的才艺水准,丰富了她们的表演素材。可见拥有特殊职业的琴女群体也以抚琴唱词为媒介,加入到了宋代民间琴人的队伍之中,成为了琴乐的传播者。
另一首著名的琴调是《醉翁操》。与《瑶池燕》相比,《醉翁操》的成调波折得多,是民间琴人与文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音乐作品。首先是撰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其次是受其启发作《醉翁吟》琴曲的沈遵,再次是以《醉翁吟》求词的崔闲,最后是倚《醉翁吟》之声填词成《醉翁操》的苏轼。《醉翁操》定谱后,民间琴人崔闲遍访名人雅士,为其所写的三十余首琴曲一一填词,言“公能各为我为辞,使我它日持归庐山时倚琴而歌,亦足为千载盛事”[16]2635。但崔闲并未携琴歌隐归,而是将其广传于民间,浙派的徐天民、毛敏仲早年就以江西谱为其习琴之根基。同时,崔闲对江西谱的贡献使其成为“江西派”的集大成者。[16]2635琴词创作推动了文人与琴家的新型合作模式的建立,同时夯定了江西琴派以琴歌为主的艺术风格。
雅俗问题是琴词配伍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一方面,琴是宫廷雅乐之首,其格调高古,似乎与尘世不协。另一方面,琴作为乐器,其曲调节奏形式都受到当世的审美风格与趣味的影响。二者的张力来源于历史与当代的时空跨度以及政治与艺术功能诉求之间的隔膜。北宋盛行的调子是琴词结合的产物,其艺术形式决定了其歌辞与旋律可以不断进行对应与更迭,其方法为倚声填词与依词填声。前者是按照琴曲的旋律,即“声情”填词,如《瑶池宴》《醉翁操》等。后者则依据“词情”谱曲填声,谓之度曲,如现存最早的琴歌《古怨》,即是姜夔的自度曲。曲子词进入士大夫阶层后,琴成为了他们提升曲子词审美品味的重要方式,具体路径有三。其一,依琴调填新词,借琴乐的格调表现其词的清雅意境,如《越江吟》《醉翁操》等。其二,自度琴曲,雅化花间趣味。如柳永的《彩云归》、姜夔的《暗香》《疏影》等。其三,将词集命名为“琴趣”,以彰其人之风雅。如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的《山谷琴趣外篇》、晁补之的《晁氏琴趣外篇》等。将琴作为词的雅化工具的结果是,琴雅化了宋词、雅化了花间之趣、雅化了词人,但却造成了琴的流俗:“北宋琴乐之性质,乃一端近雅乐,一端近燕乐,虽不若主流之嘌唱缠声,风靡于众,其与清乐、俗乐此肩并列,词家可任情采之,以歌适之长短句。事实如此,早非一日,特前人未尝着明,而近人复多顾虑,于意不愿承认耳。”[17]琴乐被词家“任情采之”以适其歌,势必会导致琴乐的世俗化,成为与清乐、俗乐比肩的燕乐之类。
在宋代美学的语境下,雅俗问题是宋代民间琴人的集体涌入与其审美趣味对精英阶层造成的冲击、基于意识形态问题对前朝广泛流行的异域音乐进行抵制性的反弹、以及宋人艺术观念在古今转型期发生的应激反应。由此,宋琴的雅俗观表现为三种原则四类形式,三原则为:一、以古为雅,以今为俗。二、以宫廷为雅,以民间为俗。三、以华夏正声为雅,以外邦胡乐为俗。三原则辐射下的四类具体形式分别为:一、以调子的体裁言,以琴乐为雅,以民间文辞为俗。太宗为贺若二调更名表现了第二原则。二、就琴谱而谈,以阁谱为雅,以民间曲谱为俗。浙派琴谱源于阁谱,因此被认为是高雅的文人琴谱,也是基于第二原则的审美判断。三、以抚琴技法论,以简静为雅,以繁声为俗。《则全和尚节奏指法》云:“指法错乱、节奏无度、声韵繁杂,何异筝琶羯鼓之声?”[18]是基于第三原则的审美判断,《太古遗音》有“夫抚琴之法,必资简静……声之曲折,手之取势,缓急失仪,起伏无节,小大乖讹,急慢无度,遂失古人清迥之风,而多鄙吝、琐碎之韵”[19],是基于第一原则的判断。四、本琴曲风格观,以文质兼济为雅,以纤丽明媚为俗。是雅俗三原则共同作用下对琴艺术风格观的影响,如成玉磵《琴论》:“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南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20]819-820进一步言,以江西派为例,其多被批评为“俗”的原因是:其一,江西派琴歌以调子为主,难免夹杂民间曲调口占,因此崔闲才汲汲以求文人士大夫填词,将民间琴歌由口占调子升格为琴乐文学;其二,江西派的琴歌音乐采取复合形式,在声韵协奏方面会增加更多的技术处理手段,因此会有“繁杂”之感。“曰江西者,由阁而加详焉,其声繁以杀,其按抑也皆别为义例。秋风巫峡之悲壮,兰皋洛浦之靓好,将和而愈怨,欲正而愈反,故凡骚人介士,皆喜而争慕之,谓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21]147从袁桷之言观之,江西谱的艺术表现力是非常突出的,不仅指法比阁谱更加繁杂艰深,出现了少见的特殊技法,而且在情绪的表达上也十分具有艺术性。“秋风巫峡之悲壮”与“兰皋洛浦之靓好”是两种对立的主题,是说江西派琴曲的风格十分多样,但都以强烈的表现性为主。“将和而愈怨,欲正而愈反”更是表现了江西派出其不意的高超艺术技巧。江西派的艺术风格源于调子,它对琴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琴曲节奏、句意的重新审定:
凡弹调子如唱慢曲,常于拍前取气、拍后相接。弹调子者每一句先两声慢,续作数声,少息留一声接后句,谓之双起单杀。假如《醉翁吟》“琅然”两声慢,“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至此少息)言”,“惟翁”(此是接下句),他皆仿此。[18]19
可以看到,“双起单杀”是宋代调子节奏的基本形式,并且在调子体裁中,琴曲句逗节次的划分需要参考歌辞内容的句意,这意味着,宋词长短句的断句、长度、结构直接作用于琴的旋律、节奏与织体,使宋琴焕发了新的面貌。由此,以琴的艺术史视野观之,琴词调子的配伍协奏使宋代的江西琴派成为最早突破古琴的传统音乐组织形式、并以古琴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为核心目标且形成有相当影响的民间群体组织。
制约宋琴在艺术性方面持续发展的原因仍然来自于礼乐文明历史背景下宋代音乐美学雅俗观的阴霾,雅俗问题的实质是不同阶层的价值立场。琴调词乐被认为是民间“嘌唱”的变形,虽略胜于民间俗唱,但仍然登不得大雅之堂。以宋代皇室为代表的宋人仍然持有“礼乐魔法”的玄念,对“俗”的抵制事实上出于对国家文明定位的偏离。“方杨氏谱行时,二谱皆废不用,或谓其声与国亡相先后”[21]147,由于音乐与国运之间被认为具有某种联系,北宋灭亡后,江西派便成了“亡国之音”,再也没有了往日“骚人介士,皆喜而争慕之”的盛况。宋元之际的理学家吴澄直称江操为衰世之音,嘲笑江派琴人的不自量力,云:“此关系两间气运之大数,岂民间私相传习之所能变移哉?”[22]这种持有以雅乐为护佑江山万岁的“乐脉观”的宋人还有很多,但这并不能阻断少数已经走在了历史前列的民间琴人的努力。宋琴在与宋词的联结中被注入了新的音乐活力,囊括了更多生活在民间的琴人。在他们的手中,宋琴出现了技术化、表现化的个体主义倾向,古琴的艺术本质在宋代发生了变化,更加接近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艺术。
三、修养贯工夫:宋代琴学生态的程式理性
“修养贯工夫”是指在宋代琴人队伍内部结构变形的背景下,宋代琴论较以往琴学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对琴事礼仪的关注与强调,以及对琴礼内容的细节化与程式化规范。
以《太古遗音》为例,专言琴事礼仪的条目有七条之多,分别为“琴有七要”“琴有五能”“琴有五不弹”“琴有十疵”“弹琴有十戒”“琴有所宜”与“琴有所忌”[19]。具体言之涉及以下六个方面:一、演奏环境。对抚琴环境的要求细言之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就前者而论,《太古遗音》有“疾风暴雨不弹”,后者言有“市廛不弹”“楼阁板壁间不弹”,以及“凡鼓琴,必择明堂、静室、竹间、松下,他处则未宜”等。二、人体姿态。云“不坐不弹”“坐席不正不弹”,头足不可摇动,且头必正、足必齐,目不可斜视、手不可不洁等。三、衣着容貌。“不衣冠不弹”“衣冠不雅、容貌不专者不弹”,总之琴人“容须肃,貌必清”,可以长相古怪,但不能粗俗。四、琴人身份。五类身份者不可鼓琴,武士、商贾、优伶、非中土之人以及百工技匠。五、观众品味。此源于古琴的“知音传统”,因此有“对俗子不弹”。六、学识气度。《学琴四句》云:“左手吟猱绰注,右手轻重疾徐,更有一般难说,其人须是读书”,强调琴人知识储备与文化修养。此外还有“凡学琴,必须要有文章,能吟咏者”“心必要有仁慈德义,能甘贫守志者。言必要有诚信,无浮华薄饰者”等。不难看出,宋代琴事礼仪的要求较以往琴论大有不同,不仅条目更加具体细致,且并未出现针对上层建筑不同等级阶层的用琴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对优伶、商贾、工匠等人的规范,虽然对后者的要求是以否定性的约束形式存在的,但仍然体现了民间群体对宋代琴学的参与与宋代琴学的世俗化。这意味着,宋代民间琴人数量的激增,对重新塑定“琴事礼仪”专题的内容,使其成为指导民间琴人抚琴的的说明手册的要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除了对琴人队伍的民间化的表现之外,宋代“琴事礼仪”专论内容的变化还透露出另一则重要信息,即宋代琴事“礼仪”之“礼”已经不再是外在的、基于制度性的礼仪要求,而转向为以实际演奏效果为目标的艺术原则。《琴有七要》中提到抚琴须于“堂室静密,天朗气清”之时,即源于“俯仰栖阁,周回板壁,左右轩楹,切近喧哗,风狂雨骤”都会影响弹琴的效果,是“夺正声之贼”。如“在楼阁板壁间,则声閧然而不的实;切近喧哗,则声泯灭;在轩栏,则声散而不聚;风燥而声焦,雨润则声浊。按长则池沼闭塞,声不发越。凡面薄则引起板声,而声亦閧閧然;爪长则声枯,指暴则弦迫而声不真全”,是说楼阁板壁间琴声喧闹、不扎实;有噪声的地方,琴声就会被掩盖;在长廊的栏杆处,琴声会不聚合等。而“周回实璧,俯临实几,击打以指面,而附声于甲,则声斯全真矣”,因此要在天气好的时候,在静谧的房间中,将琴置于实木琴几上,才能保证琴的声音不失真,因此《琴有所宜》中才言“凡鼓琴,必择明堂、静室”。不对俗子弹也是由于不谙琴理者,很难专心一致不发出杂音的听琴,声无映对,影响抚琴的心情与效果:“凡为俗奏者,以其不合古人之意,岂能凝神静虑倾耳,以分恬淡之味哉”。这说明,对抚琴环境的要求并非虚玄的旧习,而是对抚琴时声音音响效果的内在追求。
宋代琴论是以贵族修养为标准的抚琴指南,就其修养的不同层次而言分为生活修养、文化修养与审美修养三类。生活修养指琴人的衣冠仪容与行坐姿态,是最低层次的抚琴要求。如成玉磵《琴论》中的“弹琴盥手”[20]831,与《事林广记》所记的“弹琴大病”:“坐无规法,摇头动足”[23]等。文化修养指对琴人“须读书”“能吟咏”的要求。审美修养则有关审美趣味,如“焚香弹琴”“对花弹琴”“对月弹琴”,以及“学琴者,欲得风韵潇洒,无尘俗气而与雅乐称”等。可以看到,这些包括洗手、衣着、仪态在内的贵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都被并入了宋代琴事礼仪的内容之中,成为琴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值得推敲的是,以上提到的三部宋代琴论的作者都是民间琴人,且他们将贵族阶层出于审美品味的特殊抚琴趣味当作习琴的程式。这表现了民间琴人对贵族审美的刻意模仿,如在“焚香弹琴”中直白地标注不可使“浓烟扑鼻”,在“对花弹琴”中要避免“妖红艳紫”,甚至“有腋气口气者不宜鼓琴”等本身就极其俚俗的论调。这说明宋代琴论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已经不是自带雅韵的权势贵胄,而是凡尘烟火中的世人。田芝翁、成玉磵等人试图将贵族的抚琴文化带入民间,从各个方面对抚琴宜忌进行了说明,却只是重现了贵族生活的自然日常。他们的局限是,一方面不屑于传统琴学中出于等级观念对琴人的桎梏,另一方面却希冀通过工夫习养帮助民间琴人实现贵族式的修养,在保持琴的品格的同时壮大民间琴人的队伍,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品格最初正是由居于礼乐文明高位的贵族美学所带来的。
四、余论:宋代美学的近代化转型
宋代美学的近代化是由宋代社会结构的近代化、艺术形式以及行业内部的近代化以及美学观念与意识的近代化所共同构成的,围绕宋琴所发生的在组成宋代琴人队伍的主力琴人的社会身份、琴学礼仪的相关阐释及其程式化、琴人派系及其传承谱系以及琴词调子的艺术新变等方面的变化,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宋代美学所独有的大开大阖之雅俗并济特征。一方面,以皇家与民间为代表的两种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缠与摩擦形成了宋代美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昭彰地表现为雅俗关系的矛盾与对抗。另一方面,复古与新变之间的博弈而非撕裂,始终牵引着宋代美学的发展方向,使宋代出现了相较任何朝代都更加突出的戏剧性的美学演绎,那就是以向历史的回溯为名,实际完成了面向新的历史时代的美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