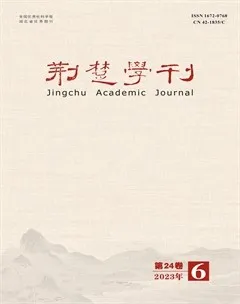电影气氛的发生学与存在论
王 超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无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 抑或是在对电影作品的评价中,电影气氛都被广泛运用。 作为观众,我们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电影气氛的萦绕。 这种萦绕着的气氛往往呈现为无特定方位的、 全感官的感染。 特别是在自己情绪与电影所传递的情绪不同时, 这种感觉会尤其明显。 例如一名观众情绪悲伤时,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喜剧电影, 开始会感觉到自身的情绪与影院的气氛格格不入,但逐渐被周围弥漫的欢乐气氛包围和感染,这种似乎无形无质的气氛如雾一样弥散开来,像浪潮一般一阵一阵地侵袭观众的身体, 改变着观众的情绪。 不同导演的作品带给观众的气氛体验通常不尽相同。 而同一位导演的不同电影作品,呈现的气氛特征往往具有某种一致性,例如小津安二郎电影的沉静哀愁气氛, 希区柯克电影的悬疑气氛,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电影的诗意气氛,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的神秘气氛。 导演的作品独特的气氛, 和他们独特的镜头语言或内容层面的个性标签一样,成为该导演的标志性特征,甚至是其作者性的代表。 通常在类型电影的划分中,诸如恐怖片、惊悚片、悬疑片、文艺片、温情片、合家欢电影等类型, 也是着重从此类电影的气氛进行描述和界定的。
导演郑正秋在1926 年的《导演〈小情人〉之经验(续)》中就谈到了空气,而他的创作观念正是“使人人‘同化’在我一个空气里”[1],此后费穆的《略谈“空气”》一文更是知名。 早期电影人的实践和阐释让“空气”“氛围气”“氛围”“气氛”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概念,堪称“建立在中国影人固有的宇宙观和生命意识之上, 在主体觉醒和整体观照的层面生发出来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电影理论”[2],是当今建构中国电影学派宝贵的理论资源。近几年,随着西方美学“气氛”概念的译介和流行,“电影气氛”重新进入学界视野,然而在讨论中尚缺少从存在论意义探讨电影气氛的发生和概念的研究,所以,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讨论电影气氛的发生和观众感知。
一、从气氛到电影气氛
观众的直觉很容易感受到电影气氛的存在,但难以准确定位气氛的来源, 甚至有时只能感知到朦胧的电影气氛, 无法清晰地识别和分析电影气氛的本体。 电影气氛和电影的画面有紧密的关联,但它并不是画面本身。电影声音也对气氛的建构起到直接影响,可也不能将二者等同。这导致我们虽然常常谈论气氛, 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气氛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大多时候,面对同样的电影,观众知觉到的气氛是相同或相近的, 但确实存在一些情况,观众面对同样的作品,知觉到的气氛却大不相同。例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作品《秋刀鱼之味》(1962),电影开场的前三个镜头,自然光线充足,音乐明朗舒缓,以固定机位拍摄了工厂一排高大、红白相间的烟囱和升腾的白色烟雾。从导演的用意和当时日本观众的感知来看, 电影表现的是日常化的工作背景,电影气氛清新明媚。而在今天的观众看来,这组镜头的气氛则略显怪异,因为光线和音乐虽然暗示了导演积极正面的态度, 但画面内容里的烟囱和烟雾很难触发我们美的感受,直观上给我们的感觉是污染和雾霾。 如此矛盾发生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已经使得观众的审美心态发生了改变。该片诞生于六十年代初,彼时环境问题尚未凸显, 而日本正在经历着二战后的经济腾飞,综合国力迅速发展。 小津电影里工厂、烟囱、 火车、 车站这些常用的意象是工业化的代表, 对于战败后迫切希望看到工业化进程的日本民众来说, 蕴含着美和希望。 今天社会背景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类社会正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 烟囱象征的工业化水平非但不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而给人以落后、污染的印象,让人直觉里产生抗拒。
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六十年代的日本观众还是今天的观众, 他们截然不同的气氛体验都是伴随着各自观影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也许并没有理性的反思介入,而只是他们真实的、下意识的反映。这说明在客体化的电影之外,社会背景与观众的审美心理也对电影气氛产生重要影响。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伊文思的电影《桥》(1928)中表现了桥上行驶的火车和桥下交织的轮船散发的滚滚浓烟,以及巨大钢筋构成的桥,让·维果的《尼斯印象》(1930) 最后一组镜头中反复出现高耸的烟囱和缭绕的烟雾, 这些早期电影在今天看来依然精彩动人, 但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会影响这部分镜头给观众带来的气氛。
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电影气氛既受电影内容的影响,也受观众主观因素的制约,兼具着主观和客观的性质。 在格诺特·波默对气氛的诠释中,气氛这种“介于主客之间的、独特的居间位置”[3]16的特性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波默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 在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精神病学专家胡伯特·特伦巴赫和哲学家伊丽莎白·施特勒克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气氛这一概念。 在西方语境中,“气氛”(Atmosphäre)概念起初来源于气象学术语,意为大气层。在18 世纪后,气氛开始被用作比喻,指“在空气中的情绪”[4]。1950年以来, 气氛才开始逐渐转变为描述审美现象的隐喻[5-6]。 在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气氛”一词,刘向的《说苑·辨物》中有“登灵台以望气氛”,此处的“气氛”指的是表示福祸的云气。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气氛含义, 包含着人的主观情感判断,反而更接近波默对气氛的定义。 胡伯特·特伦巴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将气氛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7]。 施密茨用现象学和身体哲学的方法理解气氛,认为气氛没有边界,居无定所,以情感波动的形式侵袭身体,产生情绪震颤[8]。 气氛是一种“侵袭着的感染力, 是情调的空间性载体”[3]17。相较于前人的研究,波默从本体论角度确立了气氛概念。在施密茨的论述中,气氛相对于物过度的独立性和自由性, 波默则认为审美对象的诸属性是气氛效果的条件,气氛不是无根的、自由漂移的,而是由物或人所创造的,从物或人那里出发的。 波默始终强调的是气氛介于主客体之间的性质,“气氛是某种介于主客之间的东西, 尽管气氛一方面是由客观的环境条件, 即由所谓的营造者所导致的,但就气氛的何所是而言,也就是说,就气氛的特征——比如压抑的或欢快的而言,气氛却是被主观地加以经验的。”[3]4这就是说,气氛本身具有某些客观性要素, 但其特征由主观加以经验而决定。 举例来说,在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孔乙己被人嘲讽,争辩中,“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店内的气氛不是没有来由的,是酒店和众人共同营造的;然而此时众人体验到了欢乐的气氛,但同样的气氛,在孔乙己的体验中却必然是尴尬的、痛苦的。
就气氛的特性而言, 波默认为气氛的根本属性是空间性,因为“气氛显然是通过人或物身体上的在场,也即通过空间来经验的”[3]19。气氛的空间性暗含着主客双方的共同在场的内在要求,“气氛自身是某物在场的领域,是物在空间中的现实性……是知觉者和被知觉者共有的现实性”[3]22。气氛的空间性,不是指物理上的空间,而是一种情感空间,“不是那种按米计算的空间……是一种悬浮的情绪”[9]。气氛的核心并非是对某物理空间的占据,而是空间的情感色彩和其可侵袭性。单纯的某物,或某处物理空间是没有所谓气氛的,只有在与人的相遇中,有了人的知觉和情感参与,主客体共同在场和参与形成了气氛的情感空间。没有与人的相遇,物或空间的存在无法被感知,也就无所谓气氛。
厘清气氛概念的若干要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气氛理论的创新之处, 这对界定电影气氛概念起到了一定的廓清作用。但电影气氛概念的定义,绝非是仅仅给“气氛”概念加上一个“电影”做限定词,让电影成为气氛的来源或类别这么简单。巴拉兹·贝拉认为:“一切艺术存在的权利就在于: 它在自己的领域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表现形式。 ”[10]在对气氛理论的阐释中,波默着重于论述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装潢等作为环境的审美对象的气氛,兼及了光、图像、气味的气氛,对于电影的气氛并未专门涉及, 更没有深入研究。 他所论及的艺术形式均与电影存在着较大差异, 因此也使得其关于气氛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同电影之间存在着隔阂感。此外,波默理论本身的非系统性也使得学者对其展开批评和反思,认为其“有利于我们展开横向的演绎,并获得许多新的认识,但很难在理论纵深上挖掘”[11]53-54。因此,波默对气氛的开创性工作为艺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和领域, 他关于气氛基本特性的阐发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 但若要让“电影气氛”真正获得理论生命力,必须着力于电影的特性,同时与电影文本紧密结合,使其契合电影独特的艺术规律。电影气氛的特殊性,必须立足于电影自身独特的媒介特征和知觉机制。 笔者认为,无论是电影的艺术特性,抑或是电影气氛的本质属性,都必须回到电影的相遇上来。
二、现场的相遇与现场气氛
为了更好地厘清电影气氛与电影的关系,本文引入“相遇”概念作为理论基础,相遇是电影气氛产生的前提条件。“相遇概念是戏剧乃至电影最为重要的元概念。 所谓相遇,就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彼此面对面, 是他们带着各自的性质和特点来打交道, 由此结成一种在他们见面之前没有过的联系或关系。 ”[12]电影气氛,乃至于电影本身,都诞生于相遇中。
考察电影的相遇, 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存在两次重要的相遇——“现场的相遇” 与 “观影的相遇”。 是两次相遇成就了电影,电影能被称之为电影,离不开这两次相遇。 相应的,两次相遇也分别对应了两种气氛,即现场的气氛与观影的气氛。从某种程度上讲, 甚至可以认为电影与戏剧最大的区别, 正在于戏剧的相遇是同一时空关系下的一次相遇,而电影的相遇是分开的,至少存在着两次相遇。 戏剧的生产和接受是同时的、一体的,电影的生产和接受是分离的。 电影的这两次相遇在时间上必然是分开的, 否则即使有摄影机和播放设备作为中介,我们不会把它称为电影,而是称作为直播或什么别的事物, 体育赛事会有多个机位的切换,各类晚会有导演和演员,一些小品和戏剧直播有虚拟的、完整的剧情,观演关系跟电影颇为相似,但是这些都不是电影。
第一次相遇是电影拍摄现场的相遇, 发生在场景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人与世界的相遇。这次的相遇过程通常较为复杂,在导演的统筹下,演员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和任务, 来到被预先设定和布置好的场景里,彼此向对方展开刺激与反应,摄影机则按照一定的形式予以记录。因此,现场的相遇至少包括了演员与演员的相遇、 演员与导演的相遇、演员与场景的相遇、演员与摄影机的相遇等几种类型。 每个要素的变化、每对关系间的反应,都会构成对其他要素的新的刺激, 导致新的变化发生,以此共同构成了一个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些元素和关系共同构成了这一次的相遇。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来, 在这一场相遇中人的意志展开为知觉, 在彼此的刺激反应中不断发展,最终知觉凝结在摄影机里。
一个镜头或一场戏拍摄完成之后, 一次知觉活动宣告结束。拍摄到的素材并不是知觉本身,而是用电影的媒介形式对知觉及知觉形成变化过程的映射,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觉凝结物。知觉活动只存在于当下和现场的相遇中,是流动的、生成的、不能被定型的; 而知觉凝结物则是知觉活动的结果,是可被对象化的客体,同时也是一个可被观众知觉的“召唤结构”。 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认为:“作品刚诞生的那一刻起, 作者的体验便不复存在。 ”[13]14从知觉的角度理解英伽登这一观点,作者的知觉体验在创作中是活跃的, 在作品完成之后则不复存在。 这些知觉凝结物,包括编剧、导演、演员、美术和摄影等诸多部门参与者的知觉,但它不从属于任何单独的个体, 也不是每个人知觉的简单叠加。 “叠加”更接近于一种物理上的累计,而正确的描述则是在相遇里彼此影响、改变和成就,其结果更接近一种“化学反应”。在后期制作中,画面和声音的剪辑,以及加入音乐和特效的过程,从内容层面看,是新元素的加入和旧有内容的改变;从知觉的角度看,既是对既有知觉凝结物的调整和重组,也是新的知觉的参与和反应。
在一百多年的电影发展史中, 电影的内容纷繁复杂,形式花样繁多,而凡此种种,其实都统摄于人与世界相遇过程的复杂性,从本质上讲,反映的都是相遇所凝结的知觉的复杂性。
在人与世界的相遇过程中, 当然也有气氛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现场的气氛。在电影的拍摄现场,所有人都可以感知到气氛。选定和布置好的场景有特定的氛围, 编剧和导演设定的戏剧情境也有氛围。而更能影响现场气氛的,是每一个在场的人,尤其是承担着表演任务的演员,所有人都或有意或无意地释放出自己的气场, 参与着现场气氛的营造。一个敏感的人来到电影拍摄现场,未必需要看到架设的灯光或摄影机, 也不一定要听到演员富有表演性的台词, 仍然能立刻感受到一种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气氛, 让他惊觉自己来到了电影拍摄现场。
于是有一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 此时现场的气氛,是电影气氛么?现场的所有人确实感知到了气氛,这气氛也的确是由电影拍摄活动所引发的,然而笔者仍然要指出,这不是电影气氛。此时人们感知到的气氛,是一种现场的、共在场的气氛,是彼此面对面直接打交道中感知到的气氛, 在此过程中,属于电影的媒介特性没得到体现,属于电影的观演关系未能得以建立, 一个或许以后可以被称之为电影的东西正处在酝酿之中, 却还尚未诞生。 因此,尽管感知到的气氛与电影息息相关,但并不能称之为电影气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而更接近于戏剧的气氛。
三、观影的相遇与电影气氛
电影气氛的真正诞生, 产生于观众与电影的相遇,也即观影的相遇中,我们可以称这次相遇为人与电影的相遇。观影的相遇,本质上是观众对电影的意向性活动。 意向性指意识必然指向意识以外的某个对象,“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Intentio),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 ”[14]胡塞尔将意识的意向结构描述为“自我——思维者——思维物(Ego-Cogitation-Cogitatum)”,“即,自我,其意识活动与客观相关物”的结构[15]。
意向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主客观的统一, 意识不可能是脱离对象的,主观必然与客观相关联。主体通过意向切中(Treffen)事物,意向行为指向意向对象,借由意向行为,意向对象在意识活动中构造出完整的自身。具体到观众的观影活动,是观看行为让观众成之为观众,也让电影成之为电影。作为客体的电影,是一堆胶片,或一份数字拷贝,即使播放,也只是每秒24 帧画面和声音,没有感情,也无法传达单幅图像以外的任何涵义。 在与观众的相遇中,观众的观看赋予了电影以生命。单从客体层面看,电影影像只是一系列单帧画面,之所以能在观众的感知中成为一段连续、完整、动态的近乎于日常视觉感知的视频,从视觉层面讲,是由于观众的视觉暂留和视觉后像机制, 从心理机制上讲,是观众心理上的似动现象。
从物理意义上来说, 电影原本只是平面上的投影,是非立体的、无深度的,但观众观看电影时却可以获得立体感和深度感。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论证了电影的深度感和运动感来自于观众的心理,观众在平面银幕上完全意识到深度,但又不把它完全接受为真实的深度,“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实际的深度……这是由我们自己的活动创造的深度”,“我们获得现实及其全部真实的三维; 然而它又保持了那一闪而过的既没有深度又不丰满的平面暗示”[16]。 并且,由于双眼视差的存在,画面中有远景的衬托,近景的立体感才会更强。知觉心理学家甚至认为人类视网膜只存在高度和广度二维,视知觉本身并不存在深度,是大脑“以背景暗示和对世界的毕生认识经验将二维视觉图像理解成了三维”,“一个三维的世界被一个二维的眼睛所记录,而后再经大脑还原为三维”[17]。
因此, 只有观众的参与才能让电影的单帧画面成为连贯的镜头, 让单独的镜头具备了超越图片的电影化表意能力。进一步讲,蒙太奇意味着依靠对画面的组接和重构, 制造出每个镜头独自出现时所没有的内涵,让镜头成为电影的表意单位。英伽登在研究文学作品时, 将作品中时空段之间的空隙称为“不定点”或“未定域”(Places of Indeterminacy),用来表示“再现的对象中没有被文本特别确定表达的方面或部分”[13]50,他进而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 要主动借助想象补充这些未定域,这种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电影镜头之间的空隙,也类似于英伽登所谓的“不定点”,需要观众的主动填补, 蒙太奇的机制归根结底是观众的心理机制, 区别在于电影的不定点未留给观众专门的时间思考, 观众往往是出于下意识的即时反应予以填补; 文学作品由于阅读节奏由读者自由把控, 其不定点的填充既有迅速带过的即时反应,也可能会有时间停顿做理性思考。 因此,电影依靠蒙太奇来表达单个镜头之外的意义, 这也仰赖于观众的心理。 导演可以通过蒙太奇手段引导观众的注意和联想,在创作阶段就预设了蒙太奇的最终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观众心理的参与;相反,导演正是基于对观众心理的了解和预判,才能进行蒙太奇的创作,乃至整部电影的创作。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电影,必须有观众的参与, 纯粹客体化的电影是无法产生意义的。正如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所言:“一部小说唯有被阅读才算存在。 如果仅仅是印刷字的组合,它就毫无价值。毕竟不比再现于一卷胶卷上的一系列影像更有价值。 小说仅仅‘存在’于读者的意识中;画作应当被看,音乐应当被听。……一切‘客体’都把可感内容和感知它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视作必然。……如果说一部艺术作品的产生需要艺术家,那么,为了艺术作品的存在,还需要观众。 ”[18]电影客体作为一种召唤结构,凝结着第一次相遇中的知觉,等待被观众的知觉唤醒。电影成为了连接观众意识活动和电影创作者意识的特殊中介,是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Intersubjective Intentional Object), 它以胶片或数字拷贝为物理载体,以创作者意识的创造活动为根源,以观众与电影的相遇为正式诞生的标志, 电影只有在与观众的相遇中才真正成为电影。在人与电影的相遇中,演员和演员、演员和场景、演员和导演、演员和摄影机的相遇都已经完成, 第一次相遇的知觉已不再是知觉本身,而成为了知觉的凝结物,它通过电影的媒介形式成为了观众知觉的对象。
观众的感知是一次复活的过程, 在观众的感知中,第一次相遇的知觉得以部分地复活,将单帧的画面复活为动态的影像, 将独立的镜头复活为连贯的表达,观众感知电影的画面和声音,感知电影的场景、光影、表演。在某些时候,观众可以循着这些元素, 想象性地感知到电影创作者的意识状态。之所以强调是“某些时候”,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总能发生, 只有在部分创作者能在影片中展现这种意识状态,而不仅是完全沉溺于表达某种情绪、讲述某段故事或塑造某个人物, 也不是所有观众都能感知到这种意识状态。之所以说观众是“想象性”地感知,是因为创作者创作时意识状态存在于电影拍摄现场,此时已不复存在,观众是凭借创作者凝结为客体的知觉残留物, 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感性知觉,调用了审美经验和知识储备,包括观影经验和对电影的前置理解, 运用想象来还原和感知创作者的意识状态。 对电影的前置理解指观众长久以来形成的对电影的审美趣味, 以及观众对具体观看这部影片的了解和期待, 包括对类型的预判,对剧情、演员、导演的认知等等。因此这种对创作者意识状态的感知,并非直接地感知,而是观众基于影片客观要素的主观想象。 这往往需要一定的观众的想象,绝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自己对电影画面和声音的知觉。 就像现代人看到拉斯科洞穴史前人类的壁画,借此可以“想象性”地感知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图景, 这种想象受到壁画内容的直接影响,但终究并非是真实和直接地感知。
因此,在第二次相遇中,电影得以真正诞生。电影气氛,正是指观众与电影的相遇中的气氛,即观影的气氛。 电影气氛是伴随着观众观影的意向性活动产生的,也是观众知觉活动的产物。胡塞尔认为, 我们无法抛弃人与事物的意向性关系而探讨事物的存在。电影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并且不同的观众可能对同一部电影有着不同的感受, 其奥秘都在这次观众与电影的相遇中,从本质上讲,反映的都是观众与电影的意向性关系。 观众观影的意向性活动不仅仅只是指向电影,更是在构造电影。气氛也正是伴随着构造电影的过程产生的, 并没有客观的电影气氛独立于观众存在然后才被观众知觉到, 而是在观众经验电影的过程中产生了气氛和相应的气氛体验。
四、两次相遇的差异与电影气氛的实质
对比现场气氛和观影气氛, 可以发现两者关系紧密但有着显著的差异。电影拍摄现场的气氛,处在表演和拍摄的戏剧情境之中。 观影的气氛是在观影情境中, 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面对电影时的气氛,此时观众处在银幕之外,借由拍摄和放映设备旁观拍摄现场。在电影观影过程中,拍摄现场的戏剧情境仍然存在, 但只构成了观影情境中被观看的文本,也即观影过程中“客体侧”的一部分。相应地,现场气氛不能等同于观影气氛,而是以特定的形式出现在了观影气氛中的“客体侧”中。 现场的气氛以电影特有的形式,映射入电影客体。摄影机摄录的画面和声音是拍摄现场气氛的残留,是一种机械复制, 现场的气氛经由摄影机和录音设备以特定的光学、 声学规律和特定的艺术手段加以记录和转译,成为电影素材。现场气氛的这种残留,并不是电影气氛本身,而是作为电影客体诸要素之一,构成了电影气氛召唤结构的客体部分。在第一次相遇中电影客体摄录了现场的气氛, 在第二次相遇中电影客体成为了观影气氛的召唤物。因此,电影客体连接起了两次相遇和两种气氛。
从内容上看, 观影气氛和现场气氛这两者有时会很接近,但它们绝不会完全等同,有时可能会差异很大甚至截然不同。 两者出现很大差异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由于观众和角色之间存在信息差,观众通过前文剧情或摄影机的特殊视角, 掌握了超过片中角色的信息。 例如电影《疯狂的石头》(2006)中谢小盟被道哥一伙绑票, 道哥以为谢小盟的翡翠是假的,所以意图用此翡翠调换展厅的翡翠,但观众却知道谢小盟已经借拍照之机用假翡翠调包了真翡翠, 此刻道哥所拿的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真翡翠。 因此道哥一伙的盗窃计划实质上成了以真换假, 表演时他们越是严肃地计划和执行偷窃活动,观影的气氛就越是滑稽可笑。希区柯克在与特吕弗的对话中谈到了如何区分悬念和惊悚, 希区柯克分别举例子予以说明,其中,惊悚是:“我们在火车上聊天,桌子下面可能有枚炸弹,我们的谈话很平常,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突然,‘嘣! ’爆炸了。 观众们见之大为震惊,但在爆炸之前,观众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及其平常的、 毫无兴趣的场面。 ”[19]而悬念则不同,是观众此前已经知道有炸弹快爆炸,并且时间已经不多,如此一来,“原先是无关紧要的谈话突然一下子饶有趣味, 因为观众参与了这场戏。 ”[19]在这里,希区柯克所对比的两种情况, 凸显的正是观众和角色的信息差产生的效果。在观众知晓炸弹,而剧中角色不知道的情况下,原本表演的气氛可能是轻松的、日常的,但观影时的气氛却是紧张刺激、充满悬念感的。
第二,观众存在明显的情感趋向,感情立场更贴近某些角色, 因此对部分场景的现场气氛无法感同身受。 此类情况常见于角色中出现了明显的正反阵营的电影。如影片《投名状》(2007)中,庞青云上任两江总督, 几位朝中大员在围坐笑谈中决断了庞青云的生死, 利益集团的博弈借由庞青云的死重归平衡,现场氛围轻松融洽,但观众所喜爱和自我投射的并非这几位军机大臣, 而是庞青云三兄弟,因此观众感受到的气氛是愤怒和悲怆。此类情况中,为了增强观众与主角的情感共振,电影往往在色调和音乐方面予以修正, 让色彩基调和背景音乐与主角的情绪一致, 强化现场气氛与观影气氛不同产生的戏剧张力。
第三,电影采用了戏说、恶搞、戏仿、拼贴、隐喻等手法, 造成了电影文本与其他文本或外部世界的某些具体社会事件、 历史事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使得影片出现了文本层面和内涵层面的背反,观众需要超越文本的假定性,结合外部语境加以理解。 例如电影《阿甘正传》(1994)大胆地将剧情与历史事件结合,让阿甘见证、参与甚至直接影响了众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些场景从文本层面本身看是严肃的、 自洽的, 但观众看来却有着惊奇、搞笑的气氛。 部分作品甚至本身不是自足的,具有一种“外链式”结构,需要结合其他文本才能理解其内涵。 影片《大电影之数百亿》(2006)出现多个恶搞的桥段,戏仿了《阿甘正传》《黑客帝国》(1999)、《花样年华》(2000)、《无间道》(2002)、《十面埋伏》(2004)、《功夫》(2004)、《雏菊》(2006) 等三十余部电影的经典场景, 观众在观影时不是孤立地关注这部作品,而是不自觉地产生联想,把它与众多场景的原作联系起来, 因此其观影气氛不是由作品本身决定的, 而是受到了仿作与原作关系的影响。 夸张戏谑的模范固然会产生滑稽可笑的气氛, 表面严肃的模仿同样也会营造幽默好笑的氛围。
第四,依靠电影素材的后期加工,配以音乐、音效或对画面做特效处理, 改变了原本的气氛效果。 如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 的结尾,重新踏上娶亲路的孙悟空看到了城墙上的武士和恋人的分别,城墙下一片围观和起哄的群众,该场景原本是戏谑的风格, 主角尤其是周星驰饰演的武士,台词和表演风格都带着故意的夸张。然而当加入了孙悟空的视角后,电影主题曲《一生所爱》响起,电影气氛骤然变得伤感,通过音乐的加入,这对恋人的命运和至尊宝、 紫霞的命运真正产生了对照和呼应。虽然在孙悟空的干预下,这对恋人携手相伴, 但却更唤起观众对紫霞命运的同情和不甘,影片的氛围仍是惆怅的。 此外,很多恐怖片也依靠悬疑、恐怖的音乐和骤起的音效,在原本寻常的场景中制造恐怖氛围, 拍摄现场没有声音的参与则完全没有恐怖感。需要承认,如果电影完全依靠背景音乐和音效来营造气氛, 的确可以制造与现场气氛差异较大的电影气氛, 但也往往会显得较为生硬。
通过与现场气氛的对比,观影气氛,也即真正的电影气氛的性质得以更清晰地呈现。至此,我们借由对电影气氛的发生的考察, 得以在存在论层面发现电影气氛的实质。 电影气氛正是电影在与观众的相遇中,以画面、音响等媒介手段作用于观众的知觉,引发观众的想象和情感反应,在电影场中形成的情感空间。 电影气氛是观众意向性活动的产物,它由电影所引发,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感性知觉和理性思维,唤起了观众的注意、记忆、欲望、想象和情感。 电影气氛并非作为电影的一种元素存在,而是一种电影的感知方式和感知状态。当电影给予的视听信息中出现了明确的元素, 引起观众的相应知觉反应, 这是电影气氛效果的直接体现; 电影的声音和画面中没有出现直接刺激的来源,而是通过诱导观众的联想和想象等方式,间接地让观众产生某种情绪和反应, 这同样是电影气氛的体现。其中,电影场指观众与电影相遇的物理空间,同时也包括了电影放映设备、观众和观看场地在内,电影场以观众知觉的边界为界限。
不同于电影场的“物理空间”属性,也并非当今较为盛行的社会和文化视角的空间, 电影气氛的空间属性是一种情感空间。 空间研究者认为空间既是一种外在的实存, 也是一种内在的感知,“受欧几里得理论的限制,人们认为空间只存在于每个人的骨骼中,是固有的;空间可以通过感官被即刻感知,如手的抓握和人体的运动,以及视觉的穿透力,等等。 ”[20]2电影的气氛空间存在于对电影的感知中,以身体为起点和连接点。意大利神经学家皮耶罗·弗朗西斯·法拉利和斯特凡诺·罗兹认为“我们的大脑会对空间的概念做出多维度的判断,将外部空间同我们的身体联系起来。因此我们身体的维度其实是感知的起点, 也是身体空间结构的起点。”[20]11电影气氛出现的前提是观众的身体性在场,通过气氛与身体的互动,与观众发生反应,波默将此过程称之为身体“收、缩的经济学”[3]18,也即人的对气氛的身体性觉察。
五、结语
波默在论述气氛的诞生时, 将产生气氛的条件表述为人的“身体性在场”或物走出自身的“迷狂”或“出窍”,未强调人与物的相遇,这或许是为了突出气氛既不属于主体又不属于客体的“居间性”, 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免强化了人与物的分离。本文将电影气氛的前提确定为观众与电影的相遇,也即人与物的相遇,明确这一前提使我们对电影气氛的发生学基础表述得更为清晰和完整。 存在论意义上,电影气氛是观众意向性活动的产物,是电影在与观众的相遇中, 在电影场这一物理空间中所形成的情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