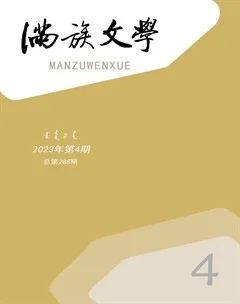松花江的雪,常常是红的
——读舒群《满洲的雪》
熊 阳
西南的三月,暖阳和绿意映入他的眼眸,但并没有进入他的心境。被春风翻动的稿纸拉回他的视线,一晃一晃,一个白色与红色交织的雪夜便在笔尖晕染开来。
一
小说《满洲的雪》的故事发生在北国冰城,白雪飘飞的夜晚肆虐着刺骨的寒风,受难的人们颤抖着,饥饿的枪膛呼号着,他作着成功与失败的两种想象,“独自一人,用一支手枪去威胁一个年青的姑娘”。
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舒群在情节设计方面都倾注了独到匠心。他往往通过故事悬念的制造与揭晓来牵动读者的好奇心与理解力,并借助叙事的“突转”与“发现”来搅动平静的叙事节奏,使故事如海浪般波涌翻折,退潮时也犹有余味。故事从雨文的内心独白引入,有着家国意识和无私信念的雨文需要前往绑架一位年青姑娘朱琳,绑架过程中,二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雨文的行为让朱琳无法相信眼前绑架自己的男子就是自己同情的义勇军,在朱琳看来,他与土匪无异,即使相信了他义勇军的身份,“她对匪贼原有的恶感,立刻移到义勇军的身上”,并用尖刀刺伤了雨文。在路上费尽周折后,雨文才将朱琳——叛徒的女儿带回了租的楼房。绑架的目的主要是勒索叛徒的钱财,但这钱财并非个人谋利,而是为了支援艰苦的前线,朱琳知晓一切缘由后,在与同志们的相处中慢慢将自己融入了同志的行列。然而,赎金交付后,同志们要将朱琳送回,来与去都是不易的,经雨文劝说后,朱琳由雨文护送回家。一切又重归于平静,但却留下了久久不散的波澜。
周立波在1936年曾指出:“他的结构带着传奇式的色彩,常常把全篇的焦点,放置在最后。”如其所言,舒群小说的结尾往往短小精悍、掷地有声,能用简洁朴素的几句甚至一句话来深化回扣主旨,并开拓新的审美想象空间。如《邻家》中的“那天,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独身汉》中“因为我是那一万二千五百万中的一个”。还有一种情况是将情节的重点转折放置结尾而后收笔,戛然而止后是幡然式的领悟,这一领悟并非转瞬即逝的,而是久久萦绕、令人不断回味的。如《奴隶与主人》中车夫将日本人翻落河中;《贼》中最后行窃自家的是自己的父亲。《满洲的雪》结尾的处理属于前者,“你知道朱琳吗?”和“你知道雨文吗?”两个简单的问句,既道出了此次绑架对于二人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显出一种退却未完的状态,二人的轨迹是由聚拢到交叉再到退却的“沙漏状”模式,两句来自对方的询问将这一轨迹再度延长,令读者作二人再次相遇的想象。
舒群早期的作品基本都是短篇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往往抓住人物最突出最本质的特点来书写,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境况相关联,在有限的篇幅内,塑造了诸多鲜明的角色,如失去祖国的朝鲜小孩果里,不堪忍辱奋起反抗的蒙古勇士阿虎太,勇敢刚正的爱国女学生萧苓等等。在中篇小说《满洲的雪》中,舒群则将笔触进一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诸多的心理及细节描写刻画复杂生动的人物个性,并在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思想及命运变化。
二十一岁的义勇军青年雨文,他是“满洲的雪”的化身与使者。廉价破碎的衬衣衬裤套上美好外衣,他在酒店主人面前放荡而无礼,在守门人面前高贵而蛮横,在女仆面前无情而粗暴,在朱琳面前是匪而非军,但这些并不是真实的雨文,这是“以虚伪掩饰灵魂的欺骗,在他也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会在行动之前盼望自己的成功能够为祖国做出贡献,会设想坦然走向刑场报以为祖国复仇的言语,会时刻挂念此次行动对于同志及祖国的意义。他是坚定的义勇军,同时也是善良纯洁的青年。相对危险的任务会让他在院内小路晕眩抖索,相对无礼的行为会让他多次默默道歉,被朱琳刺伤他毫无怨言,并冒着危险护送她回家。担负责任的雨文呈现着正邪两面,正与邪的行为之间构成了相互拆解的张力关系,使得雨文的形象更为深沉复杂,但真实贴切,当邪的华丽伪装褪去,贯穿始终的是雨文干净正直的灵魂。
舒群在塑造朱琳时多次强调了她的弱者形象,“弱者”字样在文本中共出现38次,其中36次是形容朱琳的。“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雨文、父亲以及日本兵相比,朱琳是弱者。但是“弱”并不等于苟且与胆小,在文中它多次与反抗、顽强、勇敢、冒险等词联系起来,展现的是作为弱者的原始强力。对于父亲的看管,虽然“弱者难以行动表示自己的反抗”,但她还是设法给义勇军捐募资金;对于雨文的绑架,“虽然她是一个弱者;但是,弱者被脆弱感情完全操纵的时候,也有一刹那,是最勇敢的行动”,她用尖刀刺伤了雨文;对于日本兵,“如果她不是弱者,她会冲出去,与门外的两个最不道德的醉汉决斗”。这种原始强力“是灵魂内面深度的表现,也是个性和意志自我剧烈冲突与挣扎的表现”,她以不妥协的生命意志冲撞着生理机制的束缚,弱者本弱,但不恐弱,她以尖刀代琴谱,刀刃上折射的是反抗的光芒。
然而当朱琳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下反抗错对象时,带来的则是无尽的忏悔与自责,同时也触动着朱琳思想层面的变化。刺伤雨文后,她目睹了义勇军的拮据,知晓了以钱援国的用途,在父亲与义勇军之间,叛徒与英雄之间,她苦恼着,无助地用一只手的拳头打着另一只手的手掌。见识了日本兵罪恶行径后,愤怒与正义的情绪让她的泪水如断线珍珠般不住地流,这场如“幻灯片事件”般的刺激悄然改变着朱琳的心理归依。在刹那间纷乱不安的心绪中,朱琳对义勇军的好感、对敌人复仇的决心、对祖国的热望以及对父亲的憎恶生发了。在与雨文不舍的离别之后,她的灵魂也有了更大的归宿——祖国。
“作品中的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命运。”“满洲的雪”作为小说标题,不仅营造着朦胧的气氛,同时也承担着隐喻的功能。小说中有多处对“满洲的雪”的隐喻性描写,如“满洲的雪,伟大而圣洁”“满洲的雪,常常是红的”“满洲的雪,是扰着安于满洲睡眠的睡者的”“松花江边被暴风还未打断的旗竿上,又将飘起叛了祖国的旗子,满洲的雪就是为它而怒了的吧”等等。“满洲的雪”在舒群笔下不断拟人化、形象化,带上了情绪、性格与品质,反复的渲染也将其隐喻意义逐渐托出水面:“满洲的雪”既是飘落在东北大地上的白雪,同时也是革命者忠诚的热血,是红与白的交汇,是雪夜的交响。小说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只有绑架这件发生在雪夜的小事,没有冲刺杀敌的战士,只有雨文及几个同志,但实际上,革命者的群体形象一直以“满洲的雪”出现着,呼喊着。“夜深了。快乐的人,已经睡着了。给人以快乐的人们,还未睡成。”覆盖东北大地的雪将故事的视野拉大,正像镜头从近景拉向远景,联结起了所有为东北为祖国奋战的人们,他们抗敌救国的血脉一直偾张着。正是由于适当环境描写的穿插及其隐喻的加持,故事宏大的爱国情感基调才能够奠定,既不流于浅层,也不落入俗套。
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舒群始终关注着战争,投身革命的同时以笔为戎,以小人物为主要书写对象,从侧面反映战争年代的社会面貌,书写战争中的家国意识、流亡意识以及觉醒反抗等诸多牵系国家命运的主题。《满洲的雪》通过或直抒胸臆或细腻敏锐的情感和较为丰富的细节及心理描写将生存、觉醒、流亡、人性等问题悄然覆于纸上,故事结束后留下的是多元深沉的思考。
首先,“生存”在战争年代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容易在宏大情怀中迷失的主题,众多的不幸与悲惨命运大部分根源于生存这一基本问题,典型的如《邻家》与《难中》两对母女的悲哀以及《水中生活》中姐弟三人的不幸。在《满洲的雪》中,舒群并没有单一书写底层民众及义勇军生存的艰苦状况,而是采用对比的形式来凸显生存问题。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是朱琳与雨文,但在绑架路途中,舒群也记述了街上的底层民众,他们是拉手风琴的流浪人,是贫苦的乞讨者,是在风雪之夜徘徊的野妓。文中对于义勇军艰难的生存环境也有诸多叙述,单从绑架勒索钱财这一情节上也足见义勇军的困难。然而,叛国者却极其富裕,饮食起居有仆人照料,屋子华丽得“仿佛是罗马神殿的缩影”,这是“与寒冷而悲苦的世界隔绝的小天地”。贫与富相形之下更见底层人民及义勇军的艰苦,叛国者卖国逐利失却底线的行为也更为令人憎恶。《满洲的雪》中,迫于残酷的生存现实,义勇军选择了绑架勒索叛国者;《贼》中,同样是残酷的生存现实,老张选择了行窃认识的人以便于祈求宽恕。义勇军与老张二者的内心始终被道义与生存二者撕扯缠绕着,雨文一面伪装一面默默道歉,展现出近乎分裂的精神状态;生存让老张无奈选择了行乞偷窃,道义与尊严则让他选择了自杀。舒群以现实主义精神关照发掘着战争年代“生存”问题的多维面向,其笔下众多小人物的命运与归宿如星点般勾画着战争年代的底层面貌。
人民在战争的摧残中承受着生存的压力,生存可以让人麻木于现实,也可以让人从中觉醒。“满洲的雪,是扰着安于满洲睡眠的睡者的”,革命者需要抗争,也亟待叫醒麻木的民众,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朱琳作为叛徒的女儿,虽有一点本能的反抗意识,不至于麻木,但并没有真正地觉醒。“她不曾觉悟自己不过是一个叛徒之女——奴隶的小生命而已。”在绑架事件中经历与同志的相处交流以及日本兵残暴行为的刺激后,她质问着自己“为什么觉悟得太迟迟到现在?”此时,朱琳已然由内而发地呼唤着新的自己。然而,东北大地上,仍有安于东北睡眠的睡者,他们一些是真正的麻木者,是鲁迅笔下一脸麻木看着幻灯片的中国人,一些是失却底线背弃祖国的叛徒,“满洲的雪”扰着他们,革命者的鲜血搅动着他们。呼唤民众觉醒、凝聚反侵略的民族力量是舒群小说创作的一个要义,1938 年舒群在武汉曾与老舍一起参与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协会宣言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一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他始终坚持着以文学之力撼社会之气。
舒群创作《满洲的雪》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并没有在他的故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沦陷,大量东北青年流亡到祖国各地,舒群也是其中之一。常居异乡不免思念故土,这种流亡之苦让舒群创作出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无国籍的人们》这样的作品,以他者的苦难警醒身处家园危难之际的人们。《满洲的雪》以东北为故事发生地,流亡意识中渗入了作者浓烈的乡愁。“飞亡的小鸟,可以飞来了,重新飞往它的故巢。”这是流亡在南方的舒群对东北热忱的盼望。同时,舒群还以大段告白式的话语传达着对东北的爱与思念:“如果有人的诞生地,是满洲,他一旦与满洲离得长久,他会常常呼唤起来:‘满洲,我可爱的故乡!’……满洲是他的朋友,他的母亲,他的情人的怀抱。……尤其是被铁鞭驱逐了的流亡者,只要他记起了满洲,在流亡的途上,他会害了思乡病而疯狂,他会为了归去,不惜牺牲;……满洲,永远是占有着人们的记忆的。”虽然文本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是真挚恳切的话语已经冲破了人称拉开的距离,这般由深沉热烈的乡愁与流亡的痛苦冲撞交融的情感随着作者的笔端与思绪早已跨越千里,飘荡在了松花江上,牵动着流亡在东北以外与封锁在东北以内人们的心弦,呼唤着团结抗敌回归统一的那一天。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写道:“小说就是浸透了人性的……我们可以憎恨人性,可是如果把人性消除或者净化,小说也就枯萎了。”舒群长于在战争的背景下书写人性,他一方面鲜明地刻画了卖国者懦弱顺从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展现了民众及战士们崇高良洁的人性美,但除此两方面之外,他还敏锐地捕捉着善恶交界地带的复杂人性。在战乱与动荡中,一些情况无法简单地用善恶来判断,如短篇《战地》中的刘平向受伤的战友姚中连开四枪,结束了他的生命,随后刘平自己中弹受伤后,也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舒群以极其冷峻的笔调将这一情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的意蕴全由读者品评。《满洲的雪》中“绑架”一事,于法理上是犯罪,于情理上既是给叛徒的一个教训与警醒,也是为了缓解前线将士的困难,而对于被绑者朱琳来说,这是“无辜者的不幸”。舒群在这一复杂事件的处理上,放下了冷峻的书写笔调,着力于雨文内心的愧疚与挣扎,并通过对朱琳的行为补偿与思想启迪将法理与情理的天平向情理一侧倾斜。而支撑情理内核的恰恰是人物展现出的美好人性:雨文判断朱琳善恶不以叛徒女儿身份为基准,对无辜者朱琳始终心存愧疚并祈求原谅,朱琳发觉绑架意图后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歉疚,二者的互谅互解让情理的内核更为质实。
舒群从《没有祖国的孩子》开始,便以文艺的力量影响着社会,济世的情怀始终贯穿着舒群的创作。他的文字晕散向生活各个角落,注重文学艺术性的同时,以其为声,呼唤着沉睡的人民,以其为桨,激荡着抗争的热血。《满洲的雪》是其中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料上新的补充。
——李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