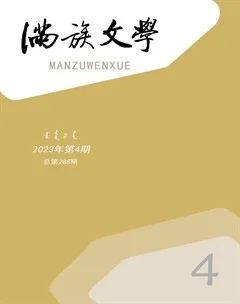写处女作的那些年
徐则臣
晓威兄邀我写写处女作,接到任务后第一件事是查字典。写作二十多年,被人问及处女作也二十多年,每次回答,我都含混其词,回答时就想着必须查查字典,看看“处女作”精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至少在我的回答里,处女作的概念是滑动的,有时指最早的作品,有时又指最早发表的作品,更多的时候我提及的,又是作品中最早为读者所熟悉的那几篇。顺嘴说往往不走心,所以答完了便忘了查字典这回事,稀里糊涂竟过了二十年。这一次晓威兄让写出来,白纸黑字就得慎重了,于是搬出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处女作”:“作者的第一个作品。”简单明了,第一个。继续查“作品”:“指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品。”所以,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处女作即作者的第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品。是成品,不是半成品,烂尾楼不算在内。甚至不甚满意的完成了的创作都不能算,成品暗含了一个意思:这东西拿得出手。拿得出手的文学作品,常规的理解里,发表了应该是算的。若是拿不出手,想来也不会送出去发表,接受众人的检阅。那么,处女作的定义可以稍作完备:作者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作品。
顺手又查了一下百度百科。该百科里在解释这个词之前有一行小字:“比喻个人第一次公开作品”。尽管像个病句,大致意思能明白,相当于“作者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作品”。接下来百度百科对该词作了解释:“处女作(the maiden work),是由‘处女’一词引申而来,进而约定俗成的。它本身带有一种比喻的性质,多用于文艺创作等方面,是指一个作家在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有人误认为处女作指的是年轻女子或未婚女子写的作品,也有人把自己写过的第一篇文章称作处女作,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其后的“概念”一节里,百度百科给了个利落的定义:“指的是一个人初次公开发表的作品。”
结合《现代汉语词典》和百度百科,处女作的概念应该清晰了。但正如百科所提及,“它本身带有一种比喻的性质,多用于文艺创作等方面,是指一个作家在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不厌其烦地征引,是因为我在相当程度上赞成这一义项。日常中,很多作家的确是在这个意义上判定自己的处女作,很多读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作家的创作的。比如余华和苏童,他们谈及早期的作品,多半谈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桑园留念》;读者大多数也以这两个短篇小说作为两位作家的处女作。事实上,这两个短篇之前,余华和苏童都发表了别的小说,只是那些小说很少收进集子里,读者见不到,又少被作者提及,它们便逐渐从两位作家的创作生涯中淡去,以至于《十八岁出门远行》和《桑园留念》成了“理所当然”的处女作。若依百度百科中的条款,这两部小说作为处女作也没错,它们的确分别是两位作家“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
绕了一个大圈,再谈我的处女作就有所本了: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
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篇小散文,在报纸副刊上,稿费不到二十元。钱不多,但对我来说,十几块钱的欣悦与虚荣超过发表本身:我终于可以请同学在食堂里吃小炒了。那会儿念大二,食堂刚设了单灶做小炒,小炒贵,有钱人才吃得起,我没钱,每天刻板地排队打三顿饭。但我被看成可能有钱的人。整天看书写小说,被同学目为作家,作家当然会有稿费,有稿费当然就要请客。他们对我写得怎么样不感兴趣,热心的是稿费,稿费等于小炒。只是那时候太不争气,稿子投出去全是泥牛入海,每天闻小炒的香味而不得,同学们的耐心很快消耗殆尽,再跟他们谈文学只能招致嘲讽。人在阴阳怪气的时候最显文学才华,我便越发地不自信,觉得自己不是写作这块料,他们比我更适合搞文学。
然后,放出去的鸟群中,竟然有一只小小鸟飞回来了。就是那篇散文。题目忘了,内容也不记得,不管他了,稿费到了就行。十几块钱应该也不够炒几个菜,肯定贴了饭卡里的不少钱,那时候食堂里已经可以卖啤酒,他们也不可能仁慈地放过我。我乐得被宰,十几块钱不算多,但有它们做基数,可以让刁钻的诸位同学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我也因此自信了一些,多少有了点写作者的自我认同,于是继续躲在教室的一隅,铺展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精耕细作。
此后又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因为卸掉了请客的压力,记忆更加模糊了。尽管散文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还帮我解了围,多少年里,我依然不认为那是我的处女作。可能跟我要做一个小说家的执念有关,我觉得小说才能算我真正的处女作。就“写作”的正大意识而论,我最早的写作或可追溯到高二。从小说开始。
高二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或者说,我写了第一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东西。好像事关青春期朦胧的感情,题目我还记得,叫《青涩的毛栗》。记得牢是因为誊抄的遍数多。先在演草纸上写完了,再抄到一个本子上,后来把所有习作往一个级别更高的本子上集中,又誊抄了一遍。誊多了,便觉得一无是处,字写得都入不了眼,此后就不再看,那本子也不知扔哪里去了。
中间还写过诗,时值高三。有一阵子每天写一首,在一个书法米字格本子纸页背面,一首诗能写满一张纸。热情很高,每期去县城邮局的杂志铺子里买《诗神》和《诗潮》两本杂志。写了大半年,还是没弄明白分行的规律,很是绝望。后来才醒悟,哪有什么规律,本来就是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因人而异,但那会儿我已经不写了。不写诗,又写起了小说。反复读钱钟书、张爱玲、苏童、叶兆言的小说。在高考前写过中篇和短篇,新历史小说那一路,还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投稿,当然是一去无消息。后来决定当作家,要说不那么突兀,高二高三稀里糊涂的玩票应该算一个线索。
大学一年级暑假之前,我从未动过成为作家的念头,一次都没有。但是我想读的所有法律专业一个没考上,一头钻进了中文系,除了看小说,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大一暑假,我一个人待在学校看书,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我决定做一个作家。很多天里我都在看小说,那个黄昏我终于被小说的魅力彻底说服了。我知道接下来漫长的一生我该干什么了。一点都不夸张。我是很轴的人,轻易不做决定,决定了的事轻易也不会改。从十九岁至今,二十六年过去,从没有动摇过成为一个作家的决心,一次都没有。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写作。或者说,我以一个作家的专业心态开始了写作。同学们看在眼里,我跟他们谈文学,他们跟我谈稿费和小炒。
我的执念,发小说才算发表。大二结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转到南京的一所大学接着念大三大四。南京是个文学之城,作家之多,放在全世界也是奇观。有个相当不负责任的玩笑话:在南京的大街上随便扔块砖头,就可能砸死一个作家。自然是段子,但你要对文学圈足够熟,马路上闲溜达,隔三差五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应该不是难事。我在校门口就看见过毕飞宇,一边走路一边抠胳膊肘上的伤疤,说是踢球摔的,结了疤有点痒。鲁羊、郭平在我们学校教书。我陪过同学去叶兆言家为一家杂志做专访。苏童他们常到我们操场上踢球。朱文和一些年轻的作家会来学校做讲座,有一次我去了,看见朱文戴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我写小说的时候,低我一级的师弟赵志明和李黎也在写,我们同在一个文学社里。在这样一个地方,停止写作是没有道理的。
大三大四那两年的确写了不少东西,但时光漫漶,究竟写了哪些,现在记起来的真不多。基本上都是手写,手稿这儿塞一沓那儿放一卷,最后自己都忘了搁哪里了。电脑那会儿刚时兴,买肯定是买不起,有一回去学校电脑室,用一台电脑打字,没承想电脑还连着网,啥网页没打开过,也被管理员按上网的时长收了费,录入半篇小说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此后再不敢去电脑室打字了。因为是插班生,老师的花名册里没我名字,那是从大一就印好的,所以不必担心老师提问到我,也就是说,本科最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的。除非特别喜欢的课才上,其余时间都在宿舍和图书馆之间穿梭,读书,写作。图书馆在小山包上,现在都能想象出当时每天抱着一摞书和稿纸上下山的样子。写是在图书馆里,看书主要在宿舍,经常整层宿舍楼就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
小说处女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小说,应该就在这个时候。我不擅长资料的归类收藏,也没这个意识,多年后被问起第一篇发表的小说,真有点蒙。这些年多地辗转,蓬飘萍寄,该扔的东西都扔了,不该扔的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反正那时候发表作品的样刊再没见到过。所以小说处女作对我就成了谜。这两年有研究者在做我的创作年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樊迎春老师和江苏师大“徐则臣研究中心”的师生们背靠背爬梳资料,他们在过刊中搜索到的我最早公开发表的小说,都是《青年文学家》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星期五综合症》。他们的专业态度和知识考古的能力毋庸置疑,我的“第一次公开发表”意义上的小说处女作,想必就是这篇《星期五综合症》了。
小说刊发之后我再没读过,手头也找不到样刊和电子版,但我大致想得出小说里写了什么,起码小说里的情绪不会记错。这题目是在学校操场旁边的草坪上静坐时出现在我的头脑里的。插班生,跟谁都不熟,一到周末晚上,同学们逛街的逛街,跳舞的跳舞,谈恋爱的谈恋爱,我就落了单。不喜欢逛街,不会跳舞,也没恋爱可谈,一周看书写作,周五再到图书馆练摊,自己都觉得矫情。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从周六到周四都没问题,一到周五晚上,感觉全世界都放松下来,必须披挂起另一番状态才对得起这个时间。而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到周五晚上自然地心绪不宁,有种被全世界抛弃之感。只要天气尚好,每个周五晚上我都会一个人来到操场边。操场低凹在山下,草坪在小山上,我就坐着,看操场上成群结队的人夜跑,看旁边体育馆灯火通明。不知道哪里传来周末的歌声,再欢快在我听来都凄凉,夜风吹拂,突然觉得两颊清冷,眼泪流下来了。忘了当时都想了些什么,但“星期五综合症”这个题目肯定是坐在操场边草坪上想到的。我似乎记得这个题目出现后,我悲凉地站起来,拍着被草坪打湿的屁股,回宿舍去找纸和笔。
小说发在杂志的1999 年第9 期,写作时间一定比这早得多。投稿就是没头苍蝇乱撞,经常一个稿子在外周游一两年才有面世的机会。感谢《青年文学家》,在一个文学青年不知往哪里去的时候,伸出了救援和鼓励的手。其后我在《青年文学家》杂志又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数字化生存》和《城市里我的一间房子》,分别是2000 年第6 期和2001 年第2期。
我早期的一批作品中,读者朋友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短篇小说《花街》和中篇小说《啊,北京》,两者分别刊于《当代》2004 年第2 期和《人民文学》2004 年第4 期。双月刊第2 期和月刊第4期同一时间出版,因为同时,又同为重要杂志,这个貌似“隆重”的出场让很多朋友有了点印象,加上我之前几乎没在大刊上露过面,很多朋友自然就把《花街》和《啊,北京》当成我的处女作。也没问题,这一中一短两个小说的确算是我早期的代表作,不仅是因为知道它们的读者相对较多,也因为两篇小说分别是我后来两个题材和领域写作的“发轫”之作。《花街》是花街系列小说的第一篇,我第一次在小说里动用“花街”这个地名,从此花街成了我的文学根据地,我的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啊,北京》之后,我写了一系列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三人行》《西夏》《把脸拉下》《逆时针》《居延》《跑步穿过中关村》等。没有《啊,北京》,后面的小说都不会有。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写花街故事和背景放在北京的小说。
发表《花街》和《啊,北京》时,我已在北大读研究生。2002 年进校后,攒了一台自己的电脑,那时候真是年轻,又有澎湃的倾诉欲望,一天噼里啪啦五千字没任何问题,但发表依然有一搭没一搭。《花街》和《啊,北京》之后,终于打开了一点“销路”,所谓的“暗黑”时期算慢慢过去了。到那时候,我已经写了七年小说。
经常有朋友问,那段“暗黑”时期难熬吗?说实话,我从没有熬的感觉。我极少怨天尤人,总认为发不了是自己的原因,如果足够好,金子的光谁也遮不住,所以我反身对自己下手,反复琢磨和修改。那些数不清的琢磨和修改帮我打下的相对结实的基本功,一直惠及至今日。所以我一直感谢那段“暗黑”的学徒期。当然我也感谢《花街》和《啊,北京》这样的“处女作”,它们给那段“暗黑”时期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能够走出去,见证更远大的世界和光。
2023.6.11,远大园
——到壮族花街节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