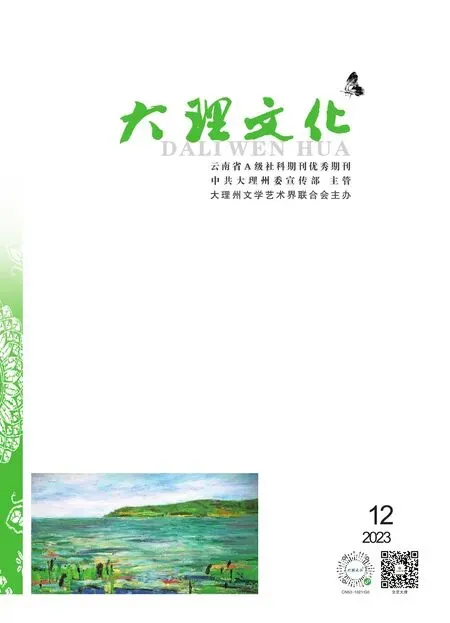扣动泥土的扳机
●刘鹏
记忆·冷杀手
抛开两季丰收不提,清明、谷雨期间的乡土,应该是最肥沃、丰润的。这期间,雨水充足,地气湿润,植物也已抖落春寒,正蓬勃兴旺。这是一个花开花谢两不误的独特节点。乡间泥土理应细腻油滑,像是孩子们酷爱的棕色油泥,还能嗅到独特芬芳。童年里,最爱和村里同龄的孩子一起光着脚丫坡上、坝头到处乱跑,一点也不见土地扎脚。一条路,尽管窄而曲折,但好多情况下,有泥土的地方也就有嫩草、野花,我们就是跑在草甸子上、花衣服上,这些嫩草、碎花豁出了性命,托着我们,像放风筝一般。果不其然,跑着跑着,我就跑出了童年,跑成了城里人。父亲说:“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了……”
在2002 年,我被一所江南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拔走了。初入城市的幸运、自豪的劲儿,藏也藏不住。但不久之后,我发现都市与乡村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我眼里,城市的机械化程度极高,可以理解为机械表。而乡村是一只沙漏。沙漏里面的每一粒沙,都与其他的细沙相互融合,做到不分你我,而机械表里,人不断地被齿轮磨铣。距离产生美,时间给乡村镀金。仿佛在父母电话声里,我嗅到了麦秸秆的味道、稻花香的味道。
几乎每一个节日,都可以成为回乡的理由,而且还能带着荣归的盛势。
回家后,白天可以丢下书本,拿一把镰刀沿着田埂打猪草,举起尼龙抄网去河里捞浮萍,也不必在意疲劳,尽可以挥舞斧头砍下一堆柴禾。这些,都是农村人常常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日常。实在是无事可做,我也喜欢走在湿漉漉的田埂上,喜欢将裤腿微微卷起,但仍被花粉涂抹得色彩斑斓。
4 年过去了,我不得不面临抉择。父母拒绝我回到农村。像我们这样的人,一生之中只能有两次可以与泥土亲近,一次是出生,一次是死亡。我光脚丫子走出泥土,走出乡村,但乡村没有给我提供工作的机会。在2007 年,一个落后的、没有几家企事业单位的乡村,让我没有回去的理由。于是,只能在江南几个城市里摸爬滚打,身心俱疲,回家约等于疗伤止痛。可却没法天天回去,常常回去。久而久之,便再也没有回去的激情了。更不会死撑着拖着疲惫之躯千里迢迢赶回去,吃一口饭?说几句话?更发现城市的好处是,它高效地运转,一如既往的磨砺你,将你驯化。故乡在我身上发生的作用力不断消减,正印证了贺知章《回乡偶记》的说法,是偶尔回乡,偶有所寄。
我们沐浴,更衣。因为,身体和衣服都会沾染尘埃。我们也洗心革面,因为心灵和面目,也都会有可憎之时。然而,沐浴更衣早已成为我们的良好习惯,而洗心革面却渐渐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故乡里一些亲密的人事发生了无法逆转的突变后,才蓦然醒悟:莫把他乡作故乡。这一刻,所有关于故乡曾经有过的痴恋,又都汹涌来袭。这或许就是感情的回潮吧。
针对信息不对称这一导致交易成本增大的诱因,强化信息公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在苗木的竞标过程中,要及时公开招标结果信息,保障农户的利益。同时,应该及时公开造林的数据信息,接受大众的监督,防止已成林再冒领补贴的现象。地方政府应该强化责任意识,保障中央政府造林的基本决策数据的真实性。虽然人的认知和知识技能存在局限,但是保障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失误,从而降低可能的交易成本。
父亲在2014 年10 月离开了我们。父亲的意外离开,震醒了我,也撞碎了我。我忽视了远在故乡的父母,忽视了乡土是会埋葬一些人的事实。
在此之前,乡村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大规模的引进项目,各种企业信息都从父母的口中传递到我耳里,但我都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我站在村口小路上,记忆从无名小路野藤般蔓延向四方。每条岔路,都由绿茵茵的庄稼烘托着,犹如色调饱满的油画,一幅一幅陈列着,展览着。尤其是春日融融之际,夹在路与田之间的沟河涨满水位,一路走,一路蛙噪声声,一群乌黑的蝌蚪,摇着尾巴,扭着腰肢,晃着大脑袋,来来回回地游荡,踏上它们的寻亲之旅。时序微微推移,抵达初夏门槛,蝌蚪已长成四条腿的小青蛙,它们开始进行一场场盛大空前的迁徙,从沟渠河道迁居入方方整整的田块,于是乎,田间地头蛙影麻密,行人无处插足。夜晚来临,月影朦胧,蛙声由远及近,由近至远,笼罩在人家的屋瓦上,弥漫在人家的窗牖上,徘徊在人们的心头上。芒种前后,港汊边上,静默已久的水泵再次咳嗽起来,震得地面处处抖动,环绕田亩的沟渠丰盈,丰盈,再丰盈,我们扛着钉耙,赤脚走上水果蛋糕似的田埂,挖豁口。这时的豁口,只需将沟渠和稻田沟通即可,一块地一般只挖一块小缺口,就可满足整片地的灌溉。当田里的水量足够时,再将挖开的泥土填塞原处,灌溉就算暂告段落。由于水是从通江的港汊里倒灌进来的,像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许多鲫鱼、虎头鲨、泥鳅、黄鳝、龙虾也都会“趁虚而入”,于是乎,功课再重的孩子也会溜出来钓龙虾、下网兜,半个时辰不到,能弄一大碗美味的鱼宴。田垄、村路都水汪汪、油腻腻的,一脚下去,十分打滑。栀子花开时,正是雨季,整个小镇都泡在水中,倘若用一架无人机拍一张大景,或许就像一块硕大无比的海绵吧。
一排排标准化厂房将这个季节的麦子、油菜花、蚕豆挤兑到更远的旮旯。以前每次走到村口,都能看到浩瀚的绿波,每一小撮绿都包藏着一点点小希望、小满足,每次看到这么壮丽的绿浪,心里都感觉到无限憧憬,人们早已熬过了靠天收的苦日子,现在正是坐拥丰年的绝佳时机。生在希望的田野上,连希望都是青翠欲滴的。尤其是那蚕豆花,远远望去,微风拂动,一只只淡紫浅白的蝴蝶翩跹,愈发衬托出和谐与宁谧,即便贫穷与落后,也可以化作记忆中的诗。蝴蝶已经被高高的围墙截获了翅膀,蜜蜂已经被隆隆的车流震裂了鸣膜,它们逃之夭夭。我择枝而栖,也是一种隐性的逃离吗?
母亲说:“该你享福,等你毕业后,家里正好拆迁。”母亲说这话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感波动。但这从吃过大苦的母亲嘴里说出来,总归是意味深长的。
我喜欢看村里人种田,透露出不可言说的神圣。周礼设春官。立春期间,气温、日照、降雨,开始趋于上升、增多,世袭的农村人不约而同穿戴雨衣,扛起锄头,走上草木半枯半黄半睡半醒的阡陌。空气里的丝丝雨气是装扮他们生活的帘幕、锦幔。尽管他们罕有触景生情,略显麻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敏锐、敏感、多心,他们一路走,一路盘算着今年要种些什么蔬菜、瓜果、豆子,要不要把多余的地块开辟出来种点儿果树?儿子爱吃花生、女儿喜食玉米,要不要再照顾一下他们的肠胃?他们一心多用,而且擅长此技。他们一边盘算着,一边还不忘将看到的野草及早拔除。他们偶尔也玩一次多情,怜惜一些迎着料峭春寒开放的小草花,把它们摘了凑到鼻尖上嗅一嗅。乡间的野草花多半是没有香味的,它们太过质朴,但是乡间的儿女们似乎总能领略到独有的滋味。有人会情不自禁地掰一段麦苗咬咬,他能体会到麦苗独有的丝丝甜味,也有人会折一根风中的狗尾草,用细茎剔除牙缝间残留的食物。
他们·断舍离
农村的风物,最养人了。生在城里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农村都是司空见惯的,以前,很多农村人宁愿一辈子守着庄稼,也不愿远走他乡过一种打工的漂零生活。直到有一天,时代变了,需要把土地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促使他们转型。这样的转型,一般只有两种途径,要么打工,要么做小本买卖。从此,原来那些做好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向庄稼地里讨生计的人逐渐转移自己的阵营,大多数人涌入城市,有力的出力做泥水匠,有技术的出技术做木工,上了年纪的则做环卫工、保洁员,城市的街头巷尾、老旧的棚户区簇拥着这样的人——从他们的衣着打扮就能判断出他们的上三代,从他们的语言食性就能猜测到他们的出生籍贯,从他们的举手投足就能摸清楚他们的学识涵养,而从他们的眼神中却又往往懂得他们的无可奈何。他们是城市里无处落脚的种子、无处安居的游民,他们今天也许在这个工地上卖力,明天可能就得去另一个工地讨生活。同样的,他们特别能漂,像浮萍,也许上半年在北京七环外,下半年就到了南京小巷里。他们很难有固定的朋友或同事,唯有亲近老乡,拜托老乡,才可能保住自己的一片小天小地。而那些地摊经营者,要躲避风雨雷电等天气的突袭,还须防范别人占据自己的谋生地盘,否则只能“退居二线”,市口不好、生意艰难。他们特别渴望身边多一些家乡人,平时早晚能够说说话,遇到急难也能搭把手,只有如此,才不至于孤军奋战举步维艰。这就是农民向工、商蜕变必须付出的代价。不事农桑的村庄,日渐清冷,泥土生硬冰冷,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我向远处望去!那里还有一片幸存的麦地。我向那块绿地走过去,一路上听不到鸟语,看不见人影,却有七八只土狗奔跑、打闹,还被青油油的麦苗绊倒,若是往年,一定会有人出来呵斥。走近看,才知道,这仅有的一片麦地,也早已被征收,一块蓝色公示牌兀自竖立在田中,上面写道:“科冕木业二期征用土地”。科冕木业这个名字,在父母给我的电话里,早有提及,我们家的宅基地就在科冕木业一期厂区下面。这家从事木柴加工的企业,相中这片土地的原因主要集中于此处濒临长江,距离泰州港只有一路之隔,离长江不到一公里远,站到厂房的屋顶,泰州港公用码头林立的吊机清晰可见。我想起《诗经》里面一些伐木的篇章,内心却被那些狗叫声刺痛了。
谁会去搭理那些流浪狗呢?以前的乡村,是没有流浪猫狗这一概念的,不久之前,它们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不是阿黄、小花,就是小黑,文雅一点的,也许会叫旺财、招财,或者进宝、富贵、如意。我试图喊一喊这些名字,不知道会有几只应声而至?
它们现在是一个小群体,大家一起流浪,一起觅食,一起被风吹日晒雨淋。它们是一块儿的,而我却被孤立了。我想对它们说:“嗨!知道吗?我们是一伙儿的,因为我属狗……”但我终究没敢说出口。
脚下有一块土坷垃,不知道怎么那么坚硬,竟将130 斤的我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撞上了一棵歪枣树。歪枣树上的刺,深深扎进我的皮肉,刺拔出来,血也跟着流出来。难道这是一种暗喻?拆迁那年,我抡榔头砸窗子时,飞溅的水泥将我的脸擦破;放倒老板车时,老板车上的木屑扎进了我的虎口;最后一次回望废墟时,一块砖头磕破了我膝盖……故乡似乎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彻底决裂,总以流几滴血的方式提醒我:别忘了,你在这里疼过。是的,疼过的地方,确实令人难忘。我仿佛觉得这块麦地,就是我应得的九分田,我当在这里重建小院、栽种蔬菜和三棵挂果的老银杏。
人总是在一低头的刹那间,看见紫陌红尘中自己的影子、故乡的影子,并试图从这里走进故乡的小院。柴门闻犬吠,桃花满蹊径,香风绕树梢。
这个季节,柳絮已经花飞满天了,燕子也从南方归来了。早些年,我家屋檐下、屋内常有燕子筑巢。屋檐下筑巢尚可理解,屋内日光灯下筑巢,却是烦恼不断。
那时,父亲刚刚营造了一个新居,新居结构规模为二层,院子约200 平方米,一面临水,三面环田,东西各有一小径,小径上长满了茵茵绿草,尤其是夏日清晨走上去,且不说露水沾衣,鞋底鞋帮裤管湿漉漉都是必然的。
新居落成后,已是次年春暖花开,燕子们在田间飞舞,在门口的电线杆上停顿,后来竟然有两家燕子选择在我家新房子上衔泥筑巢。一家客气,筑巢在屋外雨檐下,另一家燕子竟突发奇想,把湿润的泥土给衔进了屋内,就在堂屋正中日光灯下筑巢。我的外祖父于是用竹竿捣毁燕巢,巢穴稍有成型,外公就捣毁,燕子继续经营,外公继续破坏,双方就如此这般杠上了,燕子不离不弃不罢休,外祖父最后或许是被它们的倔强打动了,不再拿竹竿破坏它们的家,随它去吧。
燕子泥巢很快就竣工,问题也随之而来。燕巢正好在日光灯的启辉器那儿,启辉器受潮,日光灯开始出现故障,时亮时不亮。我们用竹竿顶一顶敲一敲,灯又亮了。如此反复几次后,再怎样敲打,灯都是黯然沉寂。最后没法,只得再次捣毁燕窝。燕子依旧不气馁,在旁边继续筑巢。筑巢后没多久,小燕子出生。老燕喂食更需勤快,时常是天刚蒙蒙亮,老燕就在堂屋内飞来飞去,呢喃不止,时不时撞击到门框,“哐当哐当”扰人清梦。我们只得赶紧起来,打开一扇偏门,放它们出去。相当烦恼的事情还有一件,它们站在巢穴洞口,屁股往外一翘,就是一堆白加黑。每日,我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清除污秽物。有一日,却见一只雏燕坠落在地,不幸夭折,心里竟然也没有一丝的疼痛感。
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燕子了。燕子是胆小的鸟类,它们始终与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只有在2017 年春天,我去浙江宁波奉化的溪口古镇采风,在一户古朴的民房屋檐下,见到了久违的燕子。起初,是一声呢喃,把我从匆匆的行旅之中吸引。接着,我立足谛听,找了若干地方,终于在一个略高于周边建筑的屋角里看到了它——剪尾的燕子。它们耐得住寂寞。而我看到了它们,恍若他乡遇故知。
横亘于城乡之间的,到底是什么?一扇门?一条路?一场梦境?或者时间?观念?又或者……
当乡村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时,乡村的土路也会改头换面,水泥路、柏油路都会四通八达。那时候,城乡差距越来越小,我再回故乡时,想必也会比现在更为平静。毕竟,昔日坑洼的土路平坦了,再也不会泥泞,不会扬尘,不会断头,不会湿了鞋裤……归根结底,生活像蛇,需要完成一次次痛苦的蜕皮才会促进时代的进步,或者跟上发展的步伐。
母亲是江北人,外祖父当初不太愿意把女儿嫁到洲上,理由正是交通不便。那时候,洲上刚刚因长江泥沙淤积,与泰兴县马甸乡、宣堡乡接壤,母亲每次回娘家时,都得靠一双腿脚走几个钟头。遇上雨天,走到渔业社、平安洲时,根本就走不动了。把女儿嫁到这么个穷乡僻壤,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没有人看好这片沙洲。洲上的人,也没有几个有见识,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认识巴掌大的土地。但现在,汽车能够一路开到扬州、江阴、南京、盐城,乃至更为繁华的地方,一切都仰仗道路。想要脱贫,想要致富,就必须先修路。我在埋怨自然村落被拆、被改造之余,也讨厌自己的见识短浅。“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真是至理名言。
我心底是盼望着故乡发展和富裕的。有一次,坐58 路公交车从口岸回润州花苑,一位从天津来泰州港出差的中年人,忍不住惊叹:“想不到这样一个镇子,竟然有这么宽阔的马路,天津哪有这样宽的路呢?”他是真的大开眼界了!而我听到这里时,心里十二分喜滋滋。我忍不住扭头看窗外,目测道路宽度在50 米开外,道路两旁崭新的路灯排列有序,沿途姹紫嫣红,许多花木我从未见过。这些树木花草的出现,也丰富了家乡的植物谱系。自然生长是野蛮的,而人为地设计规划,带有创新的思想和科学的审美意趣,这无疑是值得点赞的。
应该是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近乎完美的村庄,这是被乡愁和潜意识过度包装过的村庄,已非村庄的本来面目,以至于我们一旦看到车流汹涌,就会觉得太过喧嚣;一旦看到泥土板结,就会觉得乡间小路失去了灵气;一旦看到废墟,就会惊慌失措,觉得生态环境被破坏,乡村文明被割裂,宜居空间被毁灭,等等。静下心来想一想,岂非厚此薄彼,谬之已极?
子弹·温柔乡
如今,我回去得更加勤快了,因为一切都显得那么便捷。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润州花苑楼下的车库门口,陪我86 岁的老祖母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这座叫做永安洲的镇子,现在有另一个更为响亮的称谓:核心港区。借助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昔日肥沃的土地只能生长庄稼,而今日却长出了丰茂的厂房。由于厂房较多,不少乡亲可以哪儿都不去,得以安守这片土地。我回去得勤快了,亲人们似乎也不再觉得我有多么难得一遇。祖母问:“回南京,几个小时啊?”我说:“两个钟头。”她沉吟片刻:“哦——想不到这么近!”
是的,近在咫尺。其实两个钟头还是开得慢,开快一些,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想起一位从老家走出来的作家,他曾坦言自己没有乡愁,半点乡愁都没有,因为家与居住地实在是靠得太近了,根本就无法感受到“望断天涯路”的酸苦。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年持续的疫情影响下,我竟然还能时不时溜回家,何必再谈乡愁呢?乡愁就是一张宣纸,蘸点唾沫星子,点点就破了。像蜻蜓点水——对,我似乎应当让自己变成一只蜻蜓,时常点点故乡的水,足够消解胸中形形色色的块垒。
近两年,我肚量似乎又大了不少。在心里允许发展前的不协调,也允许发展中的局部混乱。好事多磨,没有一蹴而就的完美,有的是不断更新的趋势。或许,《大学》里面的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在此处,再妥帖不过。窥一斑见全貌。以我的故乡为水滴,可以映照到中国千千万万个高速发展的乡村、为脱贫而不断上下求索,锐意突围的乡村。我的故乡是苏北脱胎换骨的水乡,也是中国最为普通却又极不平凡的乡村。
从故乡出逃的我,永远也走不出这片江河厚土。如此想来,也就格外地释然了,不妨常回家看看,与亲朋好友捡几桩新鲜有趣的东家长西家短,略做煎炸焖煮,好好地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