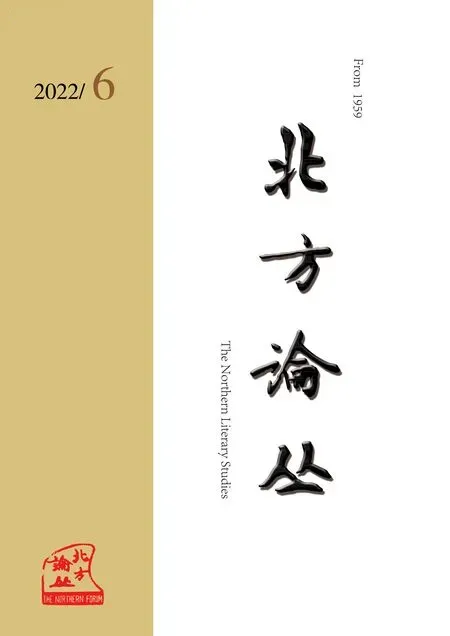茅坤古文观的发展与嘉靖万历时期复古思潮
林春虹
黄宗羲在《明文案序》开篇提出:“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1]17接着又说,嘉靖之盛是因“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而巨子哓哓之口舌,适足以为其华阴之赤土。”“至嘉靖而昆山、毘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1]17-19黄宗羲高度肯定了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的地位,视之为能与众势所趋之七子派相抗衡的“二三君子”。这三人正是所谓“唐宋派”的核心人物,却未包括唐宋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茅坤。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对茅坤以及七子后学等文人普遍持批评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茅坤地位的评价。茅坤一生享年九十,所经历的正是前后七子引领文坛,其评点唐宋文之功虽颇受后人推崇,但其古文观之发展历程、其本人在复古思潮中的地位并未得到中肯评价。在“文以载道”传统思想影响下,今人对唐宋派的认知与定位也往往将茅坤置于次要地位,仅将其视为唐宋派思想的传播者,而忽略其对唐宋派思想建构与发展所作出的更大贡献。以现代文章学的视角看,黄宗羲所强调的“经史之功”并非衡量文章高下的重要因素,撇开“道问学”的束缚,茅坤的思想境界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旨趣。
一、茅坤对唐宋派古文观的接受
“唐宋派”作为一个流派名称,最初是郭绍虞等依据其反七子派的立场并“师法唐宋”而定下来的[2]244-253,这导致其古文观的核心主旨乃至流派的成员认定等问题皆出现一些争议: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将“本色论”当作唐宋派的核心理论;马积高认为唐宋派“仍是南宋以来那些不反对学文的理学家的见解”[3]175;章培恒《中国文学史》说唐宋派其实是“宗宋派”“道学派”[4]248。在流派成员认定上,黄毅对归有光能否归为唐宋派作家表示质疑[5]10-13。这些见解的共同偏颇是将唐顺之、王慎中当作唐宋派的主导人物,而忽略了茅坤、归有光对于唐宋派的意义。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新见解,认为茅坤才是唐宋派领袖人物,唐顺之仅能称作“宋文派”或“本色派”[6]33-44,而且夸大了唐顺之与茅坤的分歧。其实,离开了对前后七子之矫正作用的历史语境,仅就唐宋派谈唐宋派并无多大意义。在李梦阳之前,明代文人本就沿着宋元文章的正统轨迹,形成了典雅的台阁文体,如黄宗羲所说:“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統。”[1]20如果仅从“宗唐宋”来看待唐宋派,那么王慎中、唐顺之与之前的台阁作家又有何不同?或者如马积高所说,唐宋派反而退化到“理学家”的文学见解了?显然,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已不能单从“宗唐宋”的角度来考察,而更应该结合其历史语境,与前后七子相结合而观照。
四库馆臣曰:“梦阳为户部郎中时,疏劾刘瑾,遘祸几危,气节本震动一世。又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7]卷一百七十一李梦阳成为引领时代风气之标杆,这是极力批评他的四库馆臣也无法否认的,其对文坛的最大贡献在于“倡言复古”,转变台阁文体的疲弱文风。台阁作家虽亦追慕古风,但安享太平的他们已失去开国之初的“昌明博大之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李梦阳为矫正日渐冗沓的台阁文风而反其道,却“盛气矜心,矫枉过直”,导致后学“摹拟剽贼,日就窠臼”[7]卷一百七十一,这正是王慎中等人进行矫正的原因,也是王慎中等人重振嘉靖文风的功绩所在。在反七子派盲目摹拟的层面,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立场完全一致,并在学习唐宋文的创作实践上又各有所成,故而他们被追认为“唐宋派”也理所当然。确立了此一前提,再来考察茅坤与唐宋派古文观的关系,方能显出茅坤的独特意义。
茅坤被接纳为唐宋派成员有诸多理由:首先,他积极与当时的秦汉派相抗衡,反对秦汉派“文必秦汉”的观念及其“字摹句拟”的师法行为;其次,茅坤古文观受唐顺之的影响很深,二人的交流较多且基本立场一致,符合一个派系形成的通常规律;再次,茅坤在古文之法与古文之道的平衡问题、古文道统等根本问题上作了深入思考,其古文观本身就可以视为唐宋派古文观的核心内容,唐宋派能够得到后世的认可离不开茅坤的观念阐释及其《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评点工作,如果说王慎中、唐顺之是唐宋派的先锋代表,那么茅坤就是尾翼其后的主力代表。一个历史阶段总有一定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存在往往就是对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最好揭示,秦汉派与唐宋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两大代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嘉靖万历时期文坛的状况。两个流派是在一定范畴上的划分,就两派各自的具体情况来说,其间的复杂性总是难以避免的。秦汉派的主要力量是前后七子,二者之间却存在很大差异性,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历史背景的变化以及地域特征的不同。唐宋派的代表尽管只有四员,他们却各有特点,其间的分歧甚至不亚于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
以现代学术标准判断,唐宋派中,唐顺之受心学思潮的影响十分明显,以哲学家视之并不为过,王慎中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徘徊,代表了一个遵循文以载道传统的儒家文人,而茅坤较纯粹地扮演了一个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从角色辨别出发,其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得到粗略说明:唐宋派本来因文学问题与秦汉派对立,但唐顺之晚年放弃文学,融入心学队伍,这其实意味了与秦汉派理论争执关系的解脱;王慎中古文的道学意味浓厚却不放弃文学修辞,他的身份地位较为尴尬,既难以与心学家相提并论,又难以在文学理论上作出更多抗衡于秦汉派的创新;茅坤从王慎中、唐顺之二人那儿吸收了思想因素,却完全应用于文章学阐释,对秦汉派文论的继承与演变思路最为清晰,所以,若要粗略定位茅坤,那便是他对秦汉派与王、唐二人的折中意义。
茅坤尽管从唐顺之的“本色论”逐渐领悟到由唐宋文上溯秦汉文的奥妙,但他并未随同唐顺之一样转向心性之学,而是始终将“文”当作根本问题,延续了秦汉派以“文”为重心的复古观念。从师法秦汉转为师法唐宋,这对王慎中、唐顺之二人均至关重要,尤其是以宋人之理学议论作为其核心的观念。这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文章法式的改造,而且意味着理学或心学对二人的思想渗透。王、唐二人对曾巩古文的学习尤为得力,其所擅长的古文是序记体以及一些论学体。与王、唐相比,茅坤在这一师法对象的转移中,较少哲理层面的思想阐发,而更多体现为文学观念的更新,为唐宋派古文观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茅坤更关注文学层面的创作规律,对秦汉派文论的继承与反拨思路也因此更为清晰。以思想基础论,茅坤与唐顺之皆以儒家为本,没有根本分歧,不同在于茅坤悟道程度远远赶不上唐顺之深厚,或者说在理性思辨上茅坤所下功夫不多,这就注定了茅坤总带有文人的感性气质,最终在文学是否为人生第一要义的问题上与唐顺之发生分化。因此,茅坤对唐宋派古文观的接受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不断在实践中对之作出理论生发。
二、从法到情:茅坤对秦汉派古文观的提升
一个时代之风气往往是由一些志同道合者相互呼应、共同营造的,李梦阳开启一代新风,在其后百年赢得了大量士人学子之拥戴,但这场声势浩大的复古思潮的内部却并非和谐共进,而是充满了曲折与争辩。嘉靖时期依然处于复古思潮的余波中,但“诗必盛唐”的口号逐渐变得微弱而代之以六朝初唐的模仿,而“文必秦汉”的呼声也渐被“师法唐宋”所掩盖,其间的转变过程正是由唐宋派来实现的。唐宋派的出现与其说是对秦汉派复古理想的反叛,毋宁说是对秦汉派的矫正。李梦阳引领的复古思潮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振兴了当时文坛,终究回归到文是否有益于世的传统载道思想上。七子派呼吁“文必秦汉”,字面上只是师法对象的问题,本质上却隐含了文人的价值观问题,即文学要皈依六经,这是古代文人复古情结的根源所在。秦汉文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其实乃因为它离“古道”未远、与六经最为契合而已。嘉靖前期,何景明、李梦阳等复古中坚力量已先后离世,其追随者固然信守《史记》《汉书》,但往往停留于字句摹拟,缺乏思想的创造与动人的力量。唐宋派力图转变秦汉派的复古方式,出现“弃文入道”[8]70-73的趋势,由此便产生了两种复古模式,即秦汉派倾向于复“古文”,而唐宋派倾向于复“古道”。茅坤的古文观正是在这一转变趋势中渐趋成型。
在折中、整合秦汉派与王、唐二人的基础上,茅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说法“万物之情,各有其至”(以下简而称之“情至说”)。“情至说”在其嘉靖二十六年(1547)写给好友蔡汝楠的信中有详细论述,当时茅坤因受唐龙案牵连被外调为广平通判,精神上的苦闷使他领悟了三年前与唐顺之辩论文章而带来的难题。从文字表述看,它是茅坤对宇宙万物本质的认识,实际上乃是由思索古文创作规律时领悟出来的,明确标志着“情感”进入茅坤的古文思想范畴。茅坤所谓“万物之情”,隐含了万物皆有情的意识,即万物的存在不在理念中,而在各自的情态中。“情”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实情”,但茅坤侧重于指事物的“情态”,即万物都是因其特有之情态而存在:山川因其“寥廓”之情才成其为山川,日月因其“升沉”之情才成其为日月,草木因其“繁翳”之情才成其为草木等等。万事万物在作家笔下,应呈现其各自独特“情态”,而非简单的写实。作家惟有用“心”感受万物之情以致其至,才能写出理想文章。茅坤所说的“心”不是“本初之心”,而是还有一个“大道”的参照点,所以作家之心依然不能违背六经的精神。茅坤的独特性在于,他并非以道论道,从某种虚无的道德规定或抽象的理学辩论去重复“经”的意义,对“道”之内涵也不曾作更多的发挥阐释。他认为作家必须“合之于大道”,但更重要的是“迎之于中”“肆于心”,那就是说,“文”要体现主体的独特心境,即主体的情感境界才是创作的源泉,“肆于心”一词潜在指向了丰富的情感世界,而不是道德世界,这就与唐顺之、王慎中所强调的古人的道德境界有所区别。
茅坤“肆于心”的看法遭到其好友蔡汝楠的质疑。在蔡汝楠看来,茅坤所强调的作家才情乃是有违世教之处,尤其反对情感对文学的渗透,他认为文学不是表现喜怒哀乐,尤其不应该有“太多不安之词”[9]711,力图将好友引上道问学的创作模式。茅坤的情至说并未完全溢出古文传统的范围,但相对于同时代的古文观,尤其正当嘉靖才子重倡“文以载道”之际,却显出一种新鲜而独特的旨趣,以致于竟引起好友的担忧。其间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蔡汝楠局限于古文教化功能,而茅坤转向了古文“言情”功能,教化多为言理而修德,“言情”则多抒情而感物。再与唐宋派的发起人王慎中相比较,茅坤将古文之“理”转向古文之“情”的倾向尤其明显。王慎中所推崇的八大家楷模是曾巩,茅坤在其八大家评点中却屡屡提及对曾巩的不喜爱;王慎中擅长于序、记文,通篇以议论为要;茅坤擅长志、传文,重在跌宕情感之叙写,而序、记文也多重景与事之叙述描绘。
蔡汝楠所谓“不安之词”的个人之情进入古文,对于嘉靖时期的士大夫而言,确实是个不寻常的信号。之前,以台阁体为核心的“有德雍容之象”一直是古文创作的理想追求。但到了嘉靖朝,激扬的复古声势早已打破台阁文学的“雍容缓和”,更何况一次又一次的谏言风波,为其时文坛带来了更多“不平之鸣”。之前最早引发“不平之鸣”的李梦阳其实就是从讽谏奏疏之文开始其政治及文学生涯,他所带动的复古群体充满文章兴邦理想,真正在行动上见证了文章的抒情言志功能。李梦阳之所以让后期文人思慕不已,正是因为他与权势拼死抗争的人生豪情足以打动人心。万历时期葛曦曰:“余少读先生疏,谈时事不避权贵,其拂宸濠于江右,先大夫尝韪之,意其为人凝峻高洁、刚直方正,断乎为古之烈士荩臣,匪直以文章雄视百代。”[10]565苏雨在《空同集序》也说:“世谓昌黎子文起八代之衰,似矣,而不知其挽既颓之世教;人知空同子文振永、成之弱,似矣,而不知其维将颓之士风。”[11]564嘉靖时期的唐顺之、王慎中及其他精英也在当时构成了一定声势,他们因文章而崛起,也几乎因文章进言而受打击。每一个士大夫的创作历程都与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文学的抒情言志功能在其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文章的话语主体从馆阁士人转向郎署士人的过程中[12]113-120,作为弱势群体的郎署士人企图以文章的力量来宣扬其政治理想,但无一例外,全都归于失败。整个嘉靖一朝,皇上所重用的权臣多属擅长献媚阿谀之人,带给正直之音的总是无尽的挫折与苦闷,更不必说还有因直谏而失去生命的沈炼、杨继盛以及远谪边鄙之地的杨慎等人。
有挫折有苦闷,自然有“不安之词”,从朝廷回到日常,被排挤的嘉靖士人大多依然以“诗”来倾吐其个人情绪,而其“文”中却惯于以圣人之“道”来超越个人情感,如唐顺之、王慎中在受挫后皆向“道”求取安心。而在仕途上屡遭挫折的茅坤,并不曾以朝廷之文显名,其独特之处乃在于将“不安之词”有意识地转移到“古文”创作中,这与归有光的创作倾向可谓殊途而同归。与归有光相比,茅坤之文的情感倾向总体上更显粗放,故而其所寄寓之情感虽然激烈却不够细腻,加之茅坤所言之情又与道德追求未能完全剥离,也就制约了真性情的抒发。尽管如此,他对古文情感性的追求,不局限于唐顺之、王慎中所执着的“道”,使其古文观突破了主宰文坛的载道观念。茅坤对唐宋派古文观的这一发展,将嘉靖时期秦汉派所开创的复古思潮引入更深境界,即不仅关注古文外在之“法”,而且更强调古文所蕴含的情感力量,是对秦汉派“师法古文”的提升与开拓。“情至说”的提出折中了前七子与王、唐二人的古文观,使古文的“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再次彰显,对嘉靖万历时期复古思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文统观的确立:复古思潮中古文观的集大成
从“理”到“情”的转移,从复“古道”到复“古文”的倾斜,这是茅坤与王慎中、唐顺之二人的歧异之处,具有了折中流派之争的意义。但茅坤的名气却难以与王、唐二人相比,整个嘉靖文坛依然弥漫着秦汉派与唐宋派之间的争辩。随着王慎中、唐顺之的落职与离世,嘉靖后期文坛的主导力量已经从唐宋派转移到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直到万历前期,王世贞依然占据着文坛盟主之位。李、王二人对唐宋派的批评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对于前七子“复古”的政治意图也不再执着,其时文人的参政热情已不能与弘正时期的文人相提并论。后七子更热衷于对诗文体式技法的探讨,其彼此唱和、互相追捧的作派,又蒙上了一层追逐名誉的功利色彩。在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想中,不仅宗经之道,且宗经之法,其主要偏失则在于将“法”看得过于神圣而抽象。
茅坤虽难以与文坛主流抗衡,但为了彰显唐宋派统绪,他终于在万历七年(1579)完成了一件大事,即出版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写了一篇宗旨鲜明的总序,曰:
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13]490
这段论述乃针对秦汉派而发,茅坤在此明确提出“统”的概念,将秦汉文与唐宋文予以统合,其文统观亦由此确立,为嘉靖初以来的复古思潮作出了理论的概括与升华,实具集大成之意义。茅坤认为文章的兴盛依赖于道学的兴盛,文与道相得益彰,因而在道统、政统的启发下,才有了文统观的产生。同时,茅坤也总是与七子派暗暗较量,企图为唐宋派夺得正统地位。他屡屡将李梦阳等人比作“草莽偏陲”,即“正统”的相对面,指的是虽然才气横溢、雄领文坛,但“不能本之乎六艺”,仅仅工于文词而不能达“万物之情”。茅坤借此将李梦阳等文坛领袖抛下,将唐顺之、王慎中等推尊为文坛的翘楚,同时推行他自己的文学理念,企图成为文坛的领军一族。
茅坤所谓文统,指的是“文必溯六艺之深而折衷于道”,即是否本于六艺、是否折中于道是正统的一个基本评价准则,它与“文以载道”的传统古文观相呼应,但最终着眼点则在“文”本身。“载道”侧重于“道”对“文”的支配作用,仍在文章之功能性层面阐述其性质,经程朱理学“作文害道”观念的冲击,古文几乎丧失其独立存在意义。文统观是从古文的自身属性立论,它为古文提出一个评判准则,使古文的审美本体性得以确立。而且,文统观对载道思想的超越正是明代复古思潮对唐宋复古运动的超越所在,唐宋复古是复“古道”之“道”,以“道统”为重心,而明代复古以复“古文”之“情”为重心,所以才会强调文统观。茅坤在反复言及“六艺之道”时,始终将古文家的才情禀赋相提并论,其文统观立足于文的本体性,只有自成一家的古文大家才得以成其统绪。文章既要承载道的内容,又要具备文章之所以为“文”的本体属性,此为文统观最本质的深层内涵。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完整体现茅坤文统观的八大家评点本[14]52-55,如今已成为最经典的唐宋古文选本。但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迟至清初才有了相对一致的回音。当茅坤于万历初年出版该选本以明确其文统观时,其时文坛却渐趋分化,复古与反复古成为新的流派纷争。公安、竟陵相继出现,以更激进的“反复古”倾向引领了新的风尚,遂使万历文坛呈现多元化创作格局。嘉靖文坛所凸显的古文功能转移,即从“载道”到“言志”再到“抒愤”的转变,在万历文坛的性灵大潮中得以鲜明呈现,并渐行渐远,终至偏离正统轨道。作为一个正统文人,茅坤显然难以适应文坛的风云变幻,反倒从文章习气中洞见了政界兴衰,曰:
我国家文章之运,固不敢遽谓有韩、欧者出,而区区举子业,弘治、正德来,亦稍稍浑融典雅,累累相望。其时学士大夫,亦及以忠厚博大,翊戴中外。嘉靖以下,屡起屡踬;然犹未及如近日诙谐轧扎,甚且踰佚涤滥而放辟邪侈也。……嗟乎!文章之习,与人心气运相盛衰。一二年来,仆窃见庙堂间纷纷多故矣。其所由汉之田窦、唐之牛李相为出入,固其势然;而抑或文运之薄为之也。诸元老执国于上,而公辈翊运于下,得无所以荡涤四海之士,而为之折衷乎?嗟嗟!仆老矣,无所事于世矣,独于此,不能不为扼腕而悲,拊膺而叹,故为舋舋者如此,愿公留神焉。[13]336
这封写给时任翰林院编修黄洪宪的信,大约创作于万历十一年。茅坤所说近日之“诙谐轧扎”“踰佚涤滥”“放辟邪侈”等文风正是万历文坛刚刚兴起的创作风尚,即以颇具个性的书写引领的反复古潮流。尽管茅坤已将古文创作从“载道”束缚中解脱,力求以之“言情”,但从根本上说,他依然强调文为世用的古文传统,对这种与政教传统完全背离的个体书写深致不满。他将文运厚薄与时代治乱相关联,认为文人必须担负起有益于世教的责任,并期望友人以文统振兴国运。以现代眼光回顾历史,彼时茅坤对文运、国运的预见,着实令人唏嘘。其以文统思想扭转文坛风变的意图,使《唐宋八大家文钞》具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意义。然而,“放辟邪侈”之风一旦开启,便难以收拾。《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宣扬的文统思想并未受到重视,其勾、抹、评、点却赢得坊间书商的一再推崇,致使《唐宋八大家文钞》意外成为举业界的新宠,并由此引发出晚明评点之喧嚣与乱象[15]49-53。
各种评点的质量虽高下有别,但数量上的井喷却推动了古代文法观念的成熟。万历时期,士人对古文的认知已从“文以载道”之“道”转移到“文”之自身,传“什么道”已被“怎样作文”所取代。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例,唐宋八大家的“道”并未得到重视,但各家之法却被一再解读,其中就包括茅坤在评点中对各家文法的总结。从“道”到“文”的转移,体现在作家对各种文法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使晚明古文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色。这种状况与茅坤的初衷并不相符,但无形中《唐宋八大家文钞》却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清代文坛继续发扬光大。
四、结语
茅坤“情至说”的提出意味着唐宋派古文观从“理”到“情”的内部转变,并折中了前七子复“古文”与唐宋派复“古道”的两种偏颇,对嘉靖时期古文观的发展与成熟具有重要意义。在李梦阳的复古思想中,既宗经之道又宗经之法,但其偏失在于强调“法度”却忽略作家的主体创造性。王慎中、唐顺之以唐宋文之“道”以扭转前七子之弊端,但又陷入另一种偏颇。茅坤“情至说”的提出,既是对前七子文法观的有益补充,又及时纠正了王、唐二人追求道学境界却忽略作家主体情感的偏颇。茅坤对古文情感性的理论阐释标志着古文体裁像诗歌体裁一样获得了抒发情志的功能。这种古文功能的转变在万历时期有了更突出的表现,即公安派的崛起使古文创作越来越偏离载道传统,变为自我愉悦的个性抒写。茅坤虽然强调创作之主体性,但其主体性仍处于一种潜在的正统规约之中,个体之间有分离性又有皈依性,其古文观在说明“各得万物之情”的同时,也说明各种情感都依附于道学中,原道、宗经意识依然未能彻底摆脱。从显性层面看,茅坤并不属于那种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文坛领袖,但其古文观念与古文评点却有巨大的包容性与持久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从纵向发展上,他统合了中国历史上秦汉派与唐宋派最大的两种文论传统,折中了理与情、道与文、才与法诸种观念范畴;从横向关联上,他整合了吴中重情与闽浙等地重道的地域观念的多样性,将嘉靖、万历之时的复杂多元思想统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富于弹性的文论系统。中国文学思想具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层面,显性的主流层面与潜在的稳固层面,茅坤的古文理论与批评显然属于后者,虽未显赫一时,终当影响深远。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