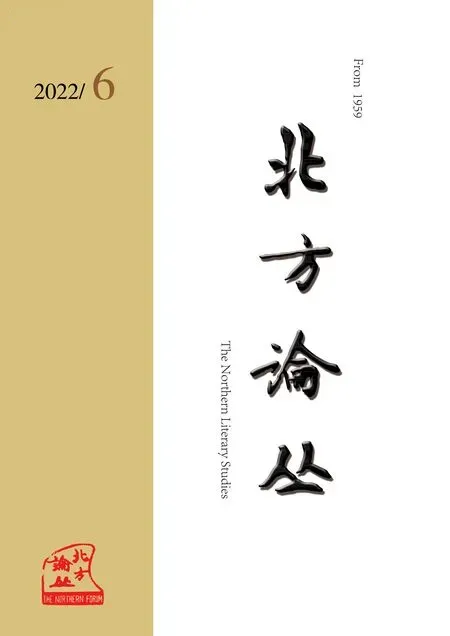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谱系及本土话语建构
薛文龙
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自从20世纪80年代被用于中国研究以来,无论是在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研究方面,还是在法团主义的研究方面都已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主流分析方法。但是,这一西方化的研究框架“更具有空间式的、力量对应的、横向关系结构的视角”[1]3,它更多的是基于西方式国家与社会权力界限清晰、市民社会发达的现实而产生的。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国家力量强大、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十分明显,这使得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无论是作为一种解释模式还是目的建构都存在着难以回避的本土化问题。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力量开始有选择性地从某些社会领域中退出,体制外的社会空间开始扩大,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已然成为现实。但是,国家力量的退出同时也伴随着其对社会领域控制的选择性加强与重构,而相应之下社会的成长仍是不连贯的、碎片化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融合仍十分明显,并未形成二元均势的格局。因此,在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中,探寻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的内在机理、把握中国当代国家与社会形态仍是一个重要议题,为此仍需要重新梳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谱系,并以此为基础来推动本土建构。
一、传统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家国同构”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特征,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与停滞性又为其长久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近代由于受西方化的冲击,传统社会濒临崩溃,但国家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却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加强。单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及各方面社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社会结构分化极低,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方面与传统社会表现出了很强的延续性。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微观单位之间在结构和运作机理方面存在着一种互相对应、互相协调的同构效应,这种同构效应使国家与社会的微观单位之间联系紧密,从而压制个体的权利空间,带有自主性的社会形态无法形成。这种同构效应在传统社会中表现为“家国同构”,而在单位社会中则表现为“单位—国家同构”。
“家国同构”的概念是笔者借用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法式的家庭与国家在内部结构、运作机理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二者形成了一对同构体。金观涛、刘青峰的这一概念主要是强调“宗法制度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组织作用”,意在证明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2]50-54。笔者认为,这一同构效应也是造成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的主要原因。家国同构使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体制化,家庭直接从纵向上与国家政权力量相联接,社会的横向联接被切断,社会难以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而其支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儒家宗法思想
儒家思想自汉代起在历经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被奉为正统思想,并成为上至政权、下至家庭的组织原则,它构成了家国同构效应的思想来源。在儒家思想中,以仁、孝为核心的伦理原则构成了它的核心,宗法道德基于家庭伦理而产生,使家庭中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形成了一套亲疏有别、远近不同的等级伦理关系。在这个关系网中,形成了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对待的差序格局。这套伦理原则从家庭之中被推广出去,也成为传统中国整个国家的组织原则,其关系结构完全对应。君主即为天下的家长,以德治统御万民,国家官僚也被称作“父母官”,由子孝、妇从、父慈伦理观念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与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社会关系如出一辙,君权、父权、夫权相通且相互为用,使得国家与家庭成为一对同构体,君权渗透到家庭之中。这种意识形态表面上是将国家家庭化,实质上是将家庭政治化,使社会自主发育受到抑制。
(二)君主集权官僚制
在传统中国,儒家重伦理、宗法的特征却并没有导致宗族组织的无限扩张,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联结机制,主要借助于君主集权的官僚制来维持。中国传统社会自秦以后便由周朝的“世卿世禄”变为“选贤与能”,天下大小官员的任命皆出自君主,君主集天下大权于一身,成为国家的化身。而庞大的官僚机器则完全依附于君权,成为君主集权专制的维护力量,只在魏晋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贵族政治”。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君主集权官僚制一直得以维持,起自隋唐的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这一体制。君主集权官僚制的顶点为君主,其下为以君权为核心的各司其职管理社会的官员,从而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的金字塔型官僚机器,它使得家庭之外的社会空间完全为国家(君权)所占据,国家与家庭之间直接相连,保证了国家与家庭之间不存在自治性质的“小共同体”形式的组织,“家国同构”完全成为维护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机制。
(三)集权的简约治理
“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一概念是由黄宗智所提出,用以指“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的方式[3]10。传统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官僚机构中主干官员仅占总人口的0.5%左右,因此,官僚机构的末端只能达到县一级[2]33。农业社会低下的效率基础也使得官僚机构难以建立起精确、高效的数目式管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治理主要依赖官僚体系之外的士绅文人来完成。士绅基层由有功名无官职的文人或者退休官员组成,他们是基层社会的精英,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同时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治特征。由于士绅阶层与官僚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以和国家官僚机器实现默契的协调与合作关系,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自上而下的成分居多,而自下而上的成分极少。士绅阶层由科举制所造就,他们本身可以视作是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与渗透。“集权的简约治理”使传统中国在一个庞大的农业经济社会中以较小规模的官僚组织保持高度集权的国家形态,其实质是社会的国家化,它构成了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社会模式的实质运作方式。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效应,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以君主集权官僚制为联接机制,以集权的简约治理为实际运作方式,它将国家政权结构内化为家庭结构,国家成为政教混合体,让行政力量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渗透于社会各处,使社会的微观单位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协调一致。国家与社会纵向联接牢固而彻底,而社会自身的横向联接却受到了极大限制,社会难以发育。因此,“家国同构”实质上是“家国一体”,在这种格局下甚至使个体人格都成为一种“它制它律”的人格[4]181,专制主义得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始终不明显。
二、单位社会中“国家—社会”关系:“单位—国家同构”
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由于西方化的冲击而面临着总体性危机,在经历近百年的社会混乱与探索之后,“单位社会”模式最终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所选中,作为一种现代化方案重新整合中国社会。虽然单位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单位社会的制度基础是单位制,它将社会中一切微观组织如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都变成了单位(在农村中是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其成员相关的社会资源,集政治、社会、专业分工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单位边界的相对封闭与单位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使其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单位之外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复存在,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其程度甚至较之传统社会更为显著。单位成员对单位高度依赖,而国家则通过单位的组织形式直接对社会实行行政化管理。笔者认为,单位社会这一特征的维持主要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微观单位——单位组织之间保持着“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的支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全民主义与革命乌托邦思想
在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也逐渐走向激进。全民主义取向与革命乌托邦思想大行其道[5]165-173,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融入到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单位社会形成和维持的主要思想支撑。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出于对“涣散无力”的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在对社会改造方案的选择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全民主义倾向,加强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的思想观念被反复提及。从晚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群学”的大力提倡,到毛泽东对“民众大联合”的强调,都试图将民众凝聚成了一个整体力量,以彻底克服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的弊病,实现社会重组。这种强调社会整合与动员以提高族群竞争力的理念,不仅成为近代“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单位社会建立后融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体制建设与管理方式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革命乌托邦思想大行其道,亦是单位体制的重要思想支撑。中国文化传统中本身便有诸多乌托邦元素。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所造成的沉重苦难,使得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更加迫切地追求理想化社会形态,寄希望于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将各种问题予以完全解决。而追求理想的平等、公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即在此背景下传入中国,并在本土化过程中与本土的乌托邦元素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在新社会制度的建设中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意识和理想化的追求。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终身雇佣和福利保障、人民公社的大锅饭等都是这一思想意识的反映。而全民主义对于社会动员能力的强调又使得新制度必须将社会成员置于行政化组织之中,这两方面的倾向结合最终使单位成了功能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单位本身便是一个拥有行政结构的小社会,是国家的同构体。
(二)党政相融的科层制系统
中国共产党由于拥有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和严密的组织形态,在争取革命胜利中逐渐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集体。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组织的严密性与高效性很快便体现在对社会的管理上。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在单位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在各级管理层次一般都设有党的组织,党的职能与政府职能高度重叠,党政不分甚至以党代政,使得党对中国社会领导自上而下高度统一。这种管理形态(或领导机制)与现代韦伯式的科层官僚制相契合,使其对社会的管理效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国共产党一直所奉行的“群众路线”,使其在基层社会中拥有庞大的干部数目及影响力。“传统社会官僚人数大约是数万人(不算吏员),国民党官员有70万人,而共产党的官员则高达几百万人的数量级。1953年,拿国家薪水的全国干部总数已达390万。1957年,共产党员人数已达1272万人,到80年代初中国拥有4000万党员、2500万国家干部。”[6]371如此庞大的官员系统与科层制的高效、稳定、精确、纪律严明等优势相结合,则使其对社会秩序的掌控达到了更大的范围。传统社会国家管理机构只能延伸到县一级,而单位社会中的垂直一体化管理机构却在农村延伸到了自然村(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单位),在城市则延伸到了单位。这使得行政体系之外的民间社会消失。这种行动整齐划一、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科层管理制使单位嵌入国家的行政体系之中,将单位与国家直接相连,单位与国家之间的同构效应完全为二者保持一体化而服务。
(三)利益组织化运作
利益组织化运作的概念由张静提出,用以描述单位体制“政行合一”的特点,即单位兼有行政管理与利益传输的双重职能。由于“这种制度化联系渠道(或机制)由两个相互作用的环节构成:即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和合法性供给与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及利益满足)”[7]190,这两个方面是基层社会秩序的核心所在。在单位社会整合中,单位直接隶属于各级政权组织,甚至本身就具有行政级别,单位领导职务本身便是国家行政职务序列中的公职,这使得单位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单位的这种行政色彩使其承担起了维护单位内部社会秩序的责任。而在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也使得资源分配形成了“层级垄断”的格局,单位所需的自愿输入完全依赖上级国家政权,而单位内部成员的资源获得也完全依赖单位的分配,这样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实质上变成了对国家政权的依赖,这种依赖兼有全面性、强制性和政治性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结构不存在自下而上的维度。中国单位社会中的科层化具有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相分离的特征[8]494,这既削弱了单位的外部技术约束,又使单位缺乏内部技术限制。高度集权的行政等级制,使得上级在获得单位信息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单位可借由这种信息不对称在表面的一致性之下产生大量的非正式运作机制。这造成了单位在高度制度化的同时又具有了某种隐蔽的自主性,如灵活地执行上级政策、单位自身运作的弹性等等。单位领导和单位成员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极力争取本单位利益最大化,这使得单位个体成员利益寻求在某种程度上被“公共化”,它与单位隐蔽的自主性相结合,形成了对单位成员要求的反馈机制。这种利益组织化的运作机制,使得单位既是一个行政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场所,单位与国家成为一对同构体。利益组织化运作是单位社会实质的运作方式,构成了支撑单位社会的整体稳定性与一致性的基础。
综上,全民主义倾向与革命乌托邦追求构成了“单位—国家同构”效应的思想支撑,党政不分的科层制构成了“单位—国家同构”效应的联结机制,利益组织化运作则构成了“单位—国家同构”效应的运作方式。单位社会中的“单位—国家同构”效应与传统社会中的“家国同构”效应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传统社会中的“家国同构”实质上是“国家的拟家化”,而单位社会中的“单位—国家同构”实质上是“单位的拟国家化”,二者的同构向度完全相反。但二者在“国家与社会微观单位的同构”这一点上却极为相似,在其同构效应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非正式运作等方面也带有一致性,这种同构效应及其影响在中国社会的整合中拥有深厚的文化与组织基础,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这一特征在后单位社会中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发挥着自身的影响。
三、后单位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同构效应”的消解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的进行,单位外部组织开始萌生、单位人员开始向体制外流动,这些因素促使单位体制开始出现松动。90年代后,随着社区建设的开始、单位自身大量破产、改组,单位社会开始了快速消解的过程,但单位体制却并没有完全消失,之后在社会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反弹(如大型国企),其影响力至今犹在。因此,后单位社会即是指单位社会逐渐瓦解但并未消失的缓慢过程,体制转型与社会转型已经开启但尚未定型、社会整合面临众多问题的时期。在后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被逐渐打破,国家控制方式与社会结构处在持续的、深刻的变动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
后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微观单位之间的同构效应逐渐减弱,社会开始作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主体孕育和发展。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逐渐催生了一个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的市场空间。首先是在农村通过国家(村集体)与个体家庭共享土地产权和产权收益的方式使分散型小农经济的存量又重新释放出来[9]62,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打破了农村公有制经济的统一局面。城市中双轨制的实行使体制外的人群和空间开始增长。国家通过让权放利的方式逐步缩小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与力度,虽然其初衷在于发展经济,但在事实上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90年代中期后,城市中国有企业的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实行也使得单位制的消解开始加速,社会阶层开始形成多元化的结构,民间组织也得到了初步发展。尽管剧烈的社会转型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加大了后单位社会中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难度,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却已然成为现实,这也为“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国家对社会的分类控制
与后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在力量上的非对称地位相对应的,是国家对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如果说后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只是早期经济改革的附带效应,那么90年代以后国家对社会控制方式的调整则更带有主观性和策略性。这一点在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权威主义政府而言,社会组织既是它的制约力量,又是它的辅助力量,而中国政府又在后单位社会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使得政府在面对众多社会组织开始涌现时,可以根据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具体做法上即是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公共物品的种类”来对它们实施不同控制策略的“分类控制体系”[10]73,或支持鼓励,或任其发展不加干预,或坚决取缔,通过这一体系国家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此外,在农村与城市社会之间,国家对于城市社会的控制远强于农村社会。1978年之后,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改革起步早且让权放利的幅度较大,因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农民无法摆脱对于土地的依附关系,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让权放利并不会导致后者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相比之下,国家对于城市社会的控制则较为严格,改革步伐一直较为谨慎。直到90年代初,城市社会中单位体制所受到的触动一直不大,而之后城市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性放权,但分税制改革与2001年以来新双轨制的形成都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自主能力,在城市社会矛盾复杂、人群多元化、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趋势下,国家也仍然能够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对城市社会保持有效的控制。这种国家对社会的持续性控制与后单位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经济性让利放权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方式虽有变化,但却并未形成具有强大内聚力和自组织能力的“市民社会”,社会的发展仍然需要国家力量来统筹引导和管理。
(三)国家对社会的“法团化”治理
后单位社会中国家对社会不同部分的控制,强度虽有所不同,但在控制手段方面表现出将新生社会组织与阶层纳入体制化的倾向,国家对社会呈现出法团化的控制方式。在最初的农村社会改革中,财政包干制与地方分权的实施使得基层政府、地方社区、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之间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互支持协作以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支持、扶植乡镇企业发展,而后者也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益、为社区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各种福利。如:很多乡镇企业与集体企业的主管本身就是地方社区或乡镇的领导人。这种“地方政府法团主义”是早期中国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1978年之后,在中国城市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民间组织总数只有数千个,而到了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已经达到89.4万多个。但社会力量的快速增长却并没有造成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方面,国家虽然无法再完全垄断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全能国家的控制模式正在逐渐弱化,但国家转而运用更加制度化的手段来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如1989年出台的双重管理制度。“政府建立的非政府组织”(GONGO)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高度响应政府指示,受官方支持,拥有丰富的资源。虽然其自主空间逐渐有所增加,但半官方的性质却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在近年来,国家更试图把体制外的维权行为也纳入制度化的框架之内,这种柔性控制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法团化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中国新崛起的社会力量也无法完全独立于政府,它们需要与政府合作以为自身的发展与安全提供保障,它们会主动建立并依赖这种庇护关系,从而形成了“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11]167。因此,后单位社会中国家对社会的法团化控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家与社会双向选择的结果。
综上,后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分离已然成为事实,但二者之间却并未形成对称均等的关系,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分类控制与法团化法团主义治理,不仅使国家在实力与自主性方面对社会保持优势,而且使国家与社会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
四、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本土话语建构
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单位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都十分明显,而其维持机制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微观单位之间的同构效应。可以说,国家与社会的一致性造就了二者的一体化,这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近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后单位社会的形成伴随着国家从社会中的退出、加强与重构,市场化、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等多种不同模式相互激荡其中,使后单位社会纷繁芜杂难以把握。但国家强势、社会弱势和法团模式的盛行等,从本质上说都仍然还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的隐性延续,而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的趋势则是二者通过寻求一致性来获得基层社会秩序的传统治理逻辑的体现。因此,一致性而非对抗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具有较强生命力和现实基础,这应成为思考后单位社会治理的基点所在。
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并未让二者实现真正消除彼此之分的融合。这使得国家力量在渗透到基层社会时,仍需要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互动,才能实现公与私之间的转换,最终将国家意志贯彻其中使国家能力得到体现。因此,这一过程不得不依赖兼有公私、官民性质的协调结构才能够得以实现。从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到单位社会中单位内部幕后解决机制,再到后单位社会中“社会组织法团化”,都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体现。这种带有双重性质的协调结构的存在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能够维持稳定的基础所在。对这一独特结构的考察,是理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特征的关键。在这一方面,黄宗智提出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概念,可视为较早的研究努力。他认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12]260。此后,他又把这一概念修正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并指出“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角色”[3]10。之后,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法团主义在中国研究中的引入与广泛应用,并对这一独特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上述研究中仍是将其看作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市民社会模式的独特结构,所秉持的是一种静态描述的视角,而对这一带有传统、前现代色彩的协调结构,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方面发挥何种作用,则鲜有论及。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在中国后单位社会治理中可能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与其将它看作一种静态的第三领域,不如将它看作一种动态的重层结构,重层结构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但它并非一个与国家、社会并列的独立领域,而是依赖二者而存在。而且它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如果将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的联接看作一个呈上下梯次分布结构的话,那么重层结构便位于其中,而且它会随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互动类型的变化而上下移动,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结构。
在这个“重层结构”的场域中,国家权力与社会都倾向于将自身势力最大限度地向对方渗透,以求获得最大的作用空间。因此,在权力的设计上,双方都出现了将自身“对方化”的倾向,即代表个人权利的公共权力倾向于一定程度上在形式上将自己转化为政府权威,以求将自身意志通过间接的方法影响政府权力,并为自身利益提供保障,即“公共权力的权威设计”。而政府权力则倾向于在形式上转化为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共权力,以求尽量将自身影响向基层渗透,即“国家权力的社会性设计”。二者都体现了当自身作用发挥到极限时,通过间接的方式发挥影响力的权力设计方法。
重层结构能够存在的核心要素,就是权力运作“对方化”的行为倾向。这种权力对方化的倾向往往在民间力量比较弱的社会存在较为明显,因为,面对国家权力的强力扩张,社会力量弱小不得不借助于间接的方式来实现自身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而国家在将权力推进到底层时,需要通过权力“对方化”来渗透,正因为如此,这种权力的重层结构主要存在于社会基层。一般而言,重层结构位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末端,和社会个体权利的顶端。如将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梯次分布结构的话,那么国家力量往往倾向于将这个重层结构向下推,以求使国家力量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而社会力量则倾向于将这个重层结构向上推,以求使社会力量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
正是由于民间力量倾向于把重层结构看作维护自身权力的缓冲带,而国家力量则倾向于将它看作向民间渗透的前进基地,因此这种重层结构中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既博弈又协作的关系。它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重层结构在国家与社会间联接的梯次格局中的移动向度。在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中,国家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逐渐通过制度或组织建设逐渐缩小对社会干预的范围,使重层结构逐渐上移。同时,通过资源下放等方式利用重层结构对社会进行培育和扶植,避免因国家权力的过早退出而造成社会的解组,通过这种重层结构的上移过程,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一个良性平衡的位置上,实现新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以指数、对数函数同构问题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