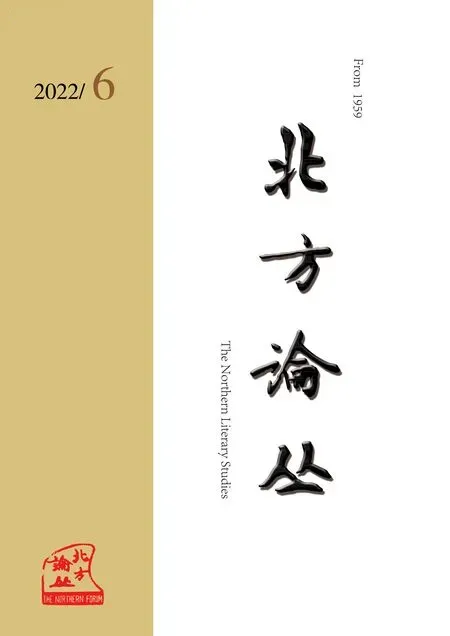两种法律体系的混用及其克服
郭 辉
一种事物能够称之为“某某体系”,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由一系列要素组成,这些要素之间按照特定标准进行有机组合,前后相应,从而形成一个融贯性的整体。法理学课程体系也不例外,理想状态下,该体系应由一系列法学概念、法学原理按照特定标准组合后,形成的前后一致、反映并能解释现实、具有融贯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实中的法理学课程体系永远存在各种问题,比如,该体系究竟应包括哪些概念和原理?这些概念或原理如何界定才能减少争议,并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法律现象,它们之间应如何进行排列组合才显得科学?同一概念在不同地方出现时怎样避免前后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正如宗教信徒在此岸世界长期不断修行,以期达致彼岸世界却永远不能实现而只能无限接近那样,现实中法理学课程体系的发展历程,亦是不断自我修正从而向理想的法理学课程体系无限接近。
本文以“法律体系”为例,说明它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及其原因,并尝试提出修正。在框架结构上,首先,介绍法理学课程体系中的通说对法律体系的界定。其次,指出新时期的法律实践对法律体系的界定与通说之间的张力及学术界对这一张力的反应。最后,针对这种张力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及其可能具有的学术意义。
一、通说:法律体系即法律规范体系
法学界对法律体系的界定也经历过一个过程,不同学者所持见解不同,甚至差异较大。比如有论者将法律体系等同于法制体系,认为法制体系包括宪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1]35-45。也有论者将法律体系的范围扩大,认为“我国学者忽略了法律体系本身是一个母系统,它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基本事实,其构成除了法律规范的部门划分以及划分后的整体性外,还应当包括法律渊源体系(笔者按:即立法体系)、法律的构成体系、法律的规范体系和法律的效力体系,甚至还包括法律的部门分类体系”[2]4-5、21。
但主流观点仍然将法律体系与法律规范联系在一起[3]。理解这一点,可参照英国法学家边沁和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界定法律时所持的观点。边沁认为,法律“是指一个观念对象,其部分、整体或复合体,或者由部分、整体与复合体混合而成的集合体,通过法规得以展示,而不是指显示这些的法规”[4]371。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亦持此看法,他所著《法谚》第38条收录的是“Leges non verbis, sed rebus, sunt impositae”(英:Law are imposed, not on words, but things),意为“法律规定,并非语言,乃系事物”,郑玉波解释为,“在成文法国家,法律虽假文字而表征,但该文字本身并非法律,其所表征之事物,始属法律”[5]19。此即法理学原理中涉及的法律规范与法律语言的关系,前者强调,法律为行为规范,它规制人的行为,这种规制在成文法背景下,用语言(法律条文)来体现,故法律规范与法律语言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法律语言作为法律规范的载体,一如萨维尼笔下的法律之于民族精神那样[6]52。
法律规范按照特定的标准形成的有机整体便是法律体系。几部主流的《法理学》教材也是在此意义上对该概念进行界定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表述为:“所谓法律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划分为若干法律门类,并由这些法律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律规范形成相互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7]317-318朱景文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材表述为:“法律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划分为若干法律部门,形成相互有机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8]285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材表述为:“法律体系,法学中有时也称‘法的体系’或简称为‘法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9]100
这些教材皆将法律体系呈现为一个序列:“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法律体系”。如何把握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的具体内涵?一般而言,可通过“法律条文——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体系(立法体系)”的含义进行。换言之,“法律条文——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体系(立法体系)”是“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法律体系”的外在表现,后者是前者的内容。前者属于“法律条文——法律渊源”系列,属于形式;后者属于“法律规范——法律体系”系列,属于法的内部结构,是内容,两者不能混淆。因此,所谓的法律体系指的是内容。
鉴于两者的上述关系及其指涉的概念序列,将两者混同显然是不应该的,对此,孙国华教授曾指出:
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体系一词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一国或一地区以现行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上层建筑的系统,包括该国、该地区现行法规范的系统(体系)和与这种规范系统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以及在这种规范、意识和文化的作用下的法律实践(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的活动等)。此时,相当于legal system.即法律制度,简称法制。第二种意义上是指法的内在结构,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84页:法律体系通常是指一国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第三种意义是system of legislation 或system of laws。即立法体系。指的是一国法的形式渊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体系(系统)。多数情况下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但往往又兼有第一种意义的含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情况下没有区分第二种含义与第三种含义,即没有严格区别法的内在结构(法的体系)和其外在表现(立法体系)。[10]2-4
对此,他强调,“不应把这几个问题简单地混在一起。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还是法的内部划分,即法的内在结构和内部协调统一的问题”[10]9,“有的同志不仅不区别法的内在结构和其外在表现,而且还把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法律文件的文字表述结构、法律效力体系等,都放到‘法律体系’涵盖的内容中来,恐怕是不妥的”[10]10。进而,“以法的部门划分为标准的立法体系,是近似法的体系的外在表现”[10]6,但须知,近似不是全等,二者不能划等号。所以,他建议为保证概念的精准,在用语方面可以有所变通,“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法的体系或法体系较好,而叫做法律体系就很容易与第一种含义,即整个法律上层建筑系统,或者第三种含义,即立法体系相混淆”[10]4。
一些立法工作者亦持相同意见,比如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认为:“所谓法的体系,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不同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划分为若干门类,并由这些法律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律规范形成相互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10]8
二、立法实践及学界的回应
虽然法学研究对法律规范的界定较为明确,并通过教材的传播而成为常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立法学界的共识,但随着立法实践的发展,传统法律体系的概念面临着无法解释现实的困境。
(一)立法实践:法律体系即规范体系和立法体系的统一
立法实践将法律体系界定为规范体系和立法体系的统一,其标志是2011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已经形成,该体系“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11]1。其实,早在2011年之前,就有立法机关的官员指出了这一点,比如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陈斯喜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成从形式来看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以及规章。从内容看,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包括七个方面:宪法以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0]491-4922010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的李适时在一次访谈中亦指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制定主体及效力的不同,将我国法律体系从纵向上划分为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根据调整关系及方法的不同,将我国法律体系从横向上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等七个部门。”[12]
立法机关对法律体系的界定表明,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法律渊源层面上的“三层次”,其二是法律体系层面上的“七部门”。前者的界定角度是从形式、制定主体和效力、纵向方面,后者的界定角度是从内容、调整关系及方法、横向方面。这种界定明显突破了学界对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的传统界定,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法理学课程体系中是两个不同但又有紧密联系的概念,法律渊源强调的是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律体系强调的是法律的内在结构(即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法律体系),将两个不同的概念置于一个概念之下显然不妥。此外,由于法律渊源涉及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因此,当代我国的法律渊源有哪些,在法理学界争议不大,但为何仅选取部分法律渊源(即“三层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仍有待论证。对法律体系而言,根据不同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等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因此,我国法律体系究竟包括几个法律部门,以及法律部门的名称为何,从不同版本的法理学教材可以看出,学界至今并未统一,从而“七部门”同样具有前述“三层次”面临的问题。申言之,法理学界有关法律体系的学术通说面临立法实践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体系界定的“解释难题”,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第一,形式方面。立法实践将立法体系与法律体系两个概念进行合并或统一,名之曰“法律体系”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在传统法理学课程体系中很难看到。尽管2011年以后的法理学教材吸收了该概念,但如何处理与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之间的关系,尚有待解决。
第二,内容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尽管是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的统一,但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法理学课程体系中的立法体系+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界定的“法律体系”仅包括传统立法体系的三个层次,并未全部覆盖。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性质,排除特别行政区的法渊尚能理解,而将行政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等排除(以及目前的监察法规),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外延上要远远小于传统上立法体系+法律体系。此外,“七部门”亦与多数法理学教材的相应划分不尽一致。
第三,融贯性方面。立法机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法融入传统法理学课程体系。不论是将该概念附在法律渊源或法律体系部分作为一节,还是单独作为一章,即使为了凸显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但面临的难题是,无法与法律渊源和法律体系的概念实现融贯性,因为它既不是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的上位概念,也不是与两者并列的同位概念,既有教材虽然将其放在法律体系框架下单独作为一节,但从内容表述和逻辑关联上,显然不是将其作为法律体系的下位概念。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学术界对立法实践的反映
当立法实践提出了传统法律体系概念不同的界定时,法学界应如何回应?2011年前,法学界一般持否定态度,即“混合式法的体系:不分法的内在结构和这种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研究问题时,最好还是把两者分开”[10]8。2011年以后,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体系的新界定时,对此,却鲜见对立法实践提出质疑的观点,尤其是立法实践的发展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概念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很少有学者进行回应。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的反应涉及学者对自身的三种定位:批判、解释和论证。第一种定位以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为代表,他认为,学术应保持独立,应对政治进行批判[13]75;第二种定位以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认为,二者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学术最好能够保持价值无涉,学者应“为科学而科学”,拥有“无预设前提”,特别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14]28、38;第三种定位是对政治进行合理化论证,类似鲁迅所谓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5]404-406(取其中性意义)。可以说,三种定位指涉的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三种关系,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现实中往往具有混合性特征,即某一种定位可能占主导地位,其他定位占次要地位。因此,针对特定的政治问题,采取上述何种路径,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选择。而三种定位就其自身而言其实并无高低优劣之分,都是从学术角度对政治现象或政治问题的反应,对它们进行武断的价值评判亦不尽合理。一个人为批判而批判,为解释而解释,为论证而论证,都是不可取的。但是,从逻辑角度看,不论哪一种定位,都应符合逻辑,言之成理。
目前,持第一种定位为主的观点几乎没有出现,持第三种地位为主的观点多为政论性文章,缺乏必要的学理分析。据笔者所见,2011年以后持第二种定位为主的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
在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组成时,就是指我国法的内在结构;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组成时,则是指我国法的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即法律渊源。在法学研究中,通常说的法律体系,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法的内在结构,法律部门的构成;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构成的体系不属于法的内在结构、部门划分问题,而属于法的表现形式,即法律渊源,虽然它们也是一个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显然是既包括法的内在结构,又包括其外在表现形式法的渊源在内的有机的统一体。[16]2
该观点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坚守传统对法律体系的界定,即法律体系就是法律的内在结构。第二,这些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即传统观点中的立法体系。第三,从学术角度指出,要想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则既要研究它的内在结构、又要研究其外在表现形式,因为这两个方面形成的对应体系是不同的。第四,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体系的界定,这种回应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描述人大常委会的界定(即包括前述的两个体系的统一体),通过“显然”两字,力图用法理学课程体系中的既有概念来解释立法实践;第二层含义,指出人大常委会虽然将法律体系界定为两个体系的统一,但两个体系毕竟是不同的。可以看出,该观点用学术的语言直面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力图将理论界定与政治实践进行沟通,并用前者来解释后者,客观上起到很好的效果,不过并没有完全解决前文提到的问题。
三、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两种层面的法律体系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将“法律体系”的概念一分为二:即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与作为(立法)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即通说界定的法律体系,是法律规范组成的系统,类似于学者所言的“法学视角的法律体系”[17],尽管客观存在,但仍需要进行法学的建构。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是法律规范体系(即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组成的系统,在特定语境下,其内容可能仅指立法体系,也可能包括法律规范体系和部分立法体系。
发生前文“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实则“借用”了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的名称,这种“借用”,一方面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一词多义,节约交流成本),另一方面体现了语言的局限性(导致概念混乱、造成歧义)。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更多地体现了语言的局限性,最终出现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存“混用”。
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在时间上最早可追溯至1984年,该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努力”的奋斗目标[18]。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19]337在此基础上,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零一零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0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道:“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536、567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8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1]75。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2]42。学术界对前述立法实践领域法律体系进行关注,可追溯至1995年王家福教授为中央领导所做的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的讲座,此次讲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想。该构想虽然被看作法学界“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3],但亦可视为法学界对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的首次回应。
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的发展史说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则就是立法体系或法律渊源体系,并不包括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体系的“形成”由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实现,具有主观性,故要“建设”、要“逐步建立”,而法律体系的“形成”则由“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起主要作用”,其发展是“以社会经济为基础”,“接近于有机的、自然组合起来的系统,是根据社会关系的结构历史地形成的”[8]287。
由此便可明晓,当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尚未形成成熟的“法律体系”,按照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4]20如果考虑到经济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即可理解,在逻辑上,至2010年,成熟的法律体系(即立法体系)即可形成。那么,在此过程中,作为法律体系外部表现形式的立法体系,就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任务,这也是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法律体系”仅指立法体系而非学术层面上的法律体系的原因所在。明确这一点,即可进一步理解,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法律体系”亦指立法体系。从公报中提及的“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标题到相应内容涉及的都是“立法”,形成的是“立法体系”。同样的理由,立法体系只能完善,而作为学术层面上的法律体系不能完善,只能“根据社会关系的结构历史地形成”。
与此相应,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如期形成,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包括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随社会经济发展合乎规律地历史形成,也包括社会主义立法体系随立法机关有意识地逐步建立而形成。形成并不意味着停止,因为社会经济一直在发展,作为学术层面上的法律体系亦随之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能根据客观形势自然演进和变化。但是,立法体系的发展因具有主观性,是在立法机关的主导下进行的,所以要“健全”“完善”“深入推进”和“加强”,正如学者所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大致可以称之为是以立法为中心、以立法机关为主要载体的立法构建”[25]。这可进一步看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内容上仅指立法体系而不包括作为学术层面的“法律体系”,原因在于,完善立法体系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举措(中共十九大报告再一次重申“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主观性,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指涉的也往往是立法体系,而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对某种状态的宣布,该状态是现实存在的,具有客观性。
本文将法律体系作出上述两种层面的区分,其具有的学术意义在于:
第一,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变、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不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文化体制不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不变,那么作为学术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就会无限地趋向成熟,立法体系就会无限地进行“健全”“完善”“深入推进”和“加强”。
第二,根据动作或状态可明确是哪一种法律体系。作为实践层面的“法律体系”在涉及“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完善”“深入推进”和“加强”时,不包括作为学术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作为实践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或“宣告”某种状态时,则同时涵盖作为学术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
第三,这种区分可以继续保证法理学教材关于“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概念不变的情况下,准确把握作为实践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内涵。即一方面,一刻也不能放松“健全”“完善”“深入推进”和“加强”;另一方面,这种“健全”“完善”“深入推进”和“加强”不能脱离实际,这个实际与其说是体现作为学术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内容,不如说就是《立法法》“总则”中规定的“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第三条),“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第四条),“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第五条),以及“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第六条)。
四、余论
可以说,法理学课程体系中每一处概念与原理均凝结着一代代学者的智力成果,是他们付出长期努力与艰难辛苦后达成共识的结晶,这一产物亦体现着人类的文明进展,来源于对法律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并反过来对法律现象进行解释甚至指导对(部门法)法律问题的解决。但另一方面,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这些概念与原理一旦形成,则标示前一阶段思考的终点,同时又意味着新阶段思考的起点。当法律实践出现新变化、新发展,而既有概念和原理无法作出有效回应时,故步自封、教条式地坚守传统概念,或者对此无视的鸵鸟式态度,便注定了法理学课程体系与现实的脱节,此时,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7]3的法理学既无法提供智识进而统领或指引部门法学,反而陷入自身问题都无法解决的正当性危机中。
在此意义上,对法理学学者而言,结合法律实践对传统概念注入新鲜血液进行创造性转化,方能使老树焕发出新枝与嫩芽,这可一方面保持学术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去解释法律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