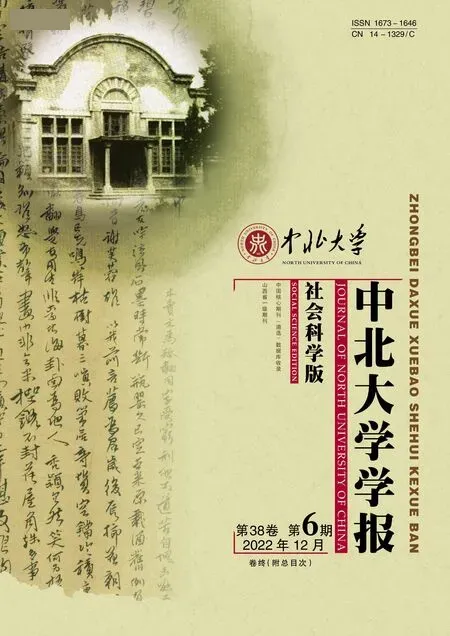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载体初探*
朱冬梅
(徐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4)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文化中极具特色和极富生命力的部分,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载体是指“能够传递、承载家训内容、要素,能为家训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1]。载体在家训传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家训传承的媒介和具体表现形式。传统家训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既有口头语言形式,也有书面文字形式;既有实物形式,也有实践形式;既有长辈自身的行为教育,也有家风的熏陶濡染。
1 语言形式的家训
语言形式的家训是指其内容并非成文的家训著作或诗文,而是训导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的鼓励表扬、批评斥责和讨论交流等形式对子弟进行教育,并经过后人的追记或编纂而得以流传。汉代之前的家训大多以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成文的家训或以文本形式表现的家训数量极少。语言形式的家训主要包括口头训诫、口头遗诫和听训辞三种。
1.1 口头训诫
口头训诫,即口口相授、耳提面命。周代以前,家训没有形成特定的文献著述,多以口头训诫为主。其特点是因事而诫,一事一议,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和针对性。行文以对话的形式为主,是一种口口相传的最大众化的家训范式。此类家训多为子孙追记先人言行,其作者并非亲自动笔者。
西周至秦,我国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家训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文王的《诏太子发》。周文王训诫其子曰:“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向非利?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后戒后戒。谋念勿择。”[2]2-3此外,如周公诫成王“无逸”、孔子的“过庭之训”、敬姜诫子勿“怠惰”、楚国令尹子发母训子与士卒同甘苦等等,皆为口头训诫。先秦时期的家训作品,内容简单而零碎,大多是只言片语或单独成篇的短小文章,还未形成内容丰富的家训典籍,一般保存在子书、史传、文集和类书里。
先秦以后的口头训诫大多以语录式训诫的形式呈现。所谓语录,即训主的言行由门人弟子或家人子弟记录而成。语录式家训不仅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家庭训诫,而且能警示后世子孙。汉代家训主要是一些名臣、名将和名士教育训诫后人的语录,大体上沿袭了先秦时期的语录体家训。如疏广的《告兄子言》、张奂的《遗命诸子》、樊宏的《戒子》和崔瑗的《遗令子实》等,皆为语录式训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家训中仍有语录式训诫存在,如羊祜的《诫子书》、辛毗的《却子言》等均为代表性的家训语录。与汉代相似,这些语录大都十分简短精炼,零星出现在正史相关人物传记中。宋代及以后的家训亦仍有部分作品采取语录体的形式。如北宋范仲淹的家训就是后世子孙追记其言行而成,首句即云:“范文正公为参知政事时,告诸子曰……”[3]422元代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明朝温璜记述的《温氏母训》和明末清初毛先舒的《家人子语》等皆以此形态出现。
1.2 口头遗诫
口头遗诫是指家训的主体在临终之际的口头训诫,由后人加以补录,是家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遗诫类家训在汉代之后开始盛行,其后此类家训层出不穷。如《旧唐书》卷八一《卢承庆传》记载,唐朝宰相卢承庆卒于总章三年,临终训诫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犹朝之有暮。吾终,敛以常服;晦朔常馔,不用牲牢;坟高可认,不须广大;事办即葬,不须卜择;墓中器物,瓷漆而己;有棺无椁,务在简要;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4]1741像这样简短交代如何办理丧事的遗诫,很可能出于后人记录,属于口语体家训文献。
1.3 听训辞
听训辞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的家训。听训词的内容既有父祖长辈的现场训诫,也包括让子弟背诵祖训、家谱和家训歌诀等。在家训发展史上最早采用唱诵韵语对家人进行教诲的是南宋著名学者陆九韶。陆家是一个“累世义居”的大家庭。依据《宋史·陆九韶传》记载,为了更好地对家族子弟实施教育,陆九韶将训诫之辞编成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5]8934“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 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6]196类似的还有浙江浦江的郑氏义门:“每旦击钟二十四声,家众俱兴。四声咸盥漱,八声入有序堂,家长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诵男女‘训戒’之辞。男训云……女训云……”[7]271通过朗诵这些训辞,家长引导子弟、家人认同和遵守家庭规范和家族秩序。
2 文字形式的家训
文字形式的家训是指家训的主体有意识地将自己教育子孙的思想亲自记录成文以便在家庭中流传,而不是由别人记录或追记。文字形式的家训,相较于一时的口头说教,具有不易消失、可反复诵读、代代相传等优势,因而有着更为持久的意义和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最普及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家训形式,为我国传统家训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两汉时期,家训已经由单纯的口头训诫发展到了书面文本形式。文字形式的家训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8]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家 书
家书是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范式。家书往往随事而写,有感而发,语言平易朴素,词意恳切、自然,多肺腑之言而感人至深,极具亲和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更易于被教诫对象所接受。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书信训诫子弟盛行一时。当时,常年在外地为官的父亲和兄长训导家中的子弟,或者在家的父亲和兄长教诫身在异地的子弟,通常以家书的形式进行。如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张奂的《诫兄子书》、司马徽的《诫子书》、诸葛亮的《诫子书》 《诫外生书》、羊祜的《诫子书》、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王僧虔的《诫子书》和徐勉的《诫子崧书》等,都是有名的教子家书。
唐代含有家训内容的家书不少,内容也更加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颜真卿的《与绪汝书》、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与弟莒书》,李翱的《寄从弟正辞书》和李观的《报弟兑书》等。宋代家训以书信形式表达的作品也有一定数量,如苏轼的《与子由弟二则》 《与侄书》、范仲淹的《与兄弟书》和朱熹的《朱子训子帖》等,都是利用书信的形式来教育子弟的家训作品。明清时期,以家书形式呈现的家训更多。现今流传于后世比较完整的有《郑板桥家书》 《史可法家书》 《汤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家书》 《纪晓岚家书》和《林则徐家书》等等。其中尤以《曾国藩家书》影响最大。
2.2 家训诗
所谓家训诗,是指运用诗歌的形式对子孙进行劝诫。古人十分注重子孙教育,并运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家训内容,借诗文抒怀、以文戒子,或直接或委婉,形成了独具特色、脍炙人口的家训诗。家训诗是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家训的特殊化表达方式之一。家训诗往往形式优美,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语言凝练明快,婉曲动人,以物喻理,形象生动,能够使受教育者在极美的艺术享受中受到感化和熏陶,达到预期的教化效果。
以诗训子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汉代以后,家训诗数量愈来愈多,并涌现出了一些家训诗名篇,如韦玄成的《戒子孙诗》、东方朔的《诫子诗》、潘岳的《家风诗》、陶渊明的《命子》 《责子》和《与子俨等疏》等。唐代是诗歌发展的繁荣期,也是家训诗创作的又一高峰。唐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大多都有家训诗留存后世,其数量更是多达千余首。其中比较著名的家训诗有李白的《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 《南陵别儿童入京》、杜甫的《宗武生日》、白居易的《狂言示诸侄》、韩愈的《符读书城南》 《示儿》 《左迁至蓝关示侄儿孙湘》、颜真卿的《劝学》、李商隐的《骄儿诗》、韦庄的《勉儿子》和杜荀鹤的《题弟侄书堂》等。内容涉及修身、治学、立业、爱国等诸多方面,形式生动,语言质朴,情感真挚,鉴赏价值和研究价值颇高,对后世影响甚大。
家训诗到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和杨万里等诗人名家,以诗歌所创作的家训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其中爱国诗人陆游尚存的九千多首诗中,专门训诫子弟或与训诫子弟相关的就达到二百多首,是中国历史上创作家训诗数量最多的诗人。陆游的《示儿子》 《读经示儿子》 《五更读书示子》 《雨闷示儿子》 《示子孙》 《黄祊小店野饭示子坦子聿》 《示元礼》 《示子聿》 《秋夜读书示儿子》和《送子龙赴吉州掾》等都是千古传诵的诗歌名作,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家训诗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明清时期,采用诗歌的形式教诫子弟的文人士大夫数量不少。如明代于谦以《示冕》诗寄予长子于冕勤勉用功、读书治学;吕坤写有《收塞北·示儿》和《望江南·示儿》,告诫其子切勿贪图小便宜,以求得“无私心自宽”;清代魏源写有《读书吟示儿耆》,教导其子知错就改、择善而从。
2.3 格 言
格言既是家训的形式也是家训的载体。以格言为载体的家训风格清新、对仗工整、言约义丰、富有哲理、耐人寻味,能时时给人以警醒,更容易被子孙所铭记和遵循,以达事半功倍之效。
具有代表性的格言体家训主要有北宋林逋的《省心录》、南宋李邦献的《省心杂言》、赵鼎的《家训笔录》、明代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吴麟征的《家诫要言》、陈龙正的《家矩》、明末清初傅山的《十六字格言》、清代金缨的《格言联璧》、胡达源的《治家良言汇编》等。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全文仅522字,却以格言警句的简短形式精辟概括了修身、立德、治家、孝悌、日常规范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内容浅显易懂,言简意赅,对仗工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此篇几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治家之本、家训圭臬而家喻户晓。不但成为许多书香门第、名人绅士的日常座右铭,而且被视为理家教子、整齐门风的治家良策,堪称格言体家训的典型代表。
2.4 家法族规
所谓家法族规,是指由家族长者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用以约束家族成员行为、协调家族内部关系和维持家族秩序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家法族规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是家训文化最为基础与典型的表现形式。家法族规作为整治家庭、家族的法规、训令,其最大的特点是带有“法”的性质,在教化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对家族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成文的家法族规大约形成于唐代。唐末名臣柳玭所著的《柳氏叙训》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家法,有“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之誉。[9]176唐代成熟的家法当属与柳玭同时为官的江州陈氏家族的第七代家长陈崇制订的《陈氏家法三十三条》。该家法明确规定:“恃酒干人及无礼妄触犯人者,各决杖十下。妄使庄司钱谷,入于市肆,淫于酒色,行止耽滥,勾当败缺者,各决杖二十,剥落衣妆,归役三年。”[10]202
对于违犯家规的家庭成员,将分别处以杖责、剥夺衣妆、与雇工一起服役等惩罚。这些规定有效地维护了陈氏大家族的秩序和稳定,使陈氏族人言行有章可循,子孙守继祖业,史称其“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11]224。
自宋代开始,利用宗法族规来辅助教化逐渐增多。正如宋人熊禾所言,同宗族人聚集在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善为家者,必立为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12]798。比较典型的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不但对每一个家庭成员应遵守的家庭规则做出了详细规定,而且还规定对违犯家规者予以杖责、鞭笞、驱逐等不同形式的惩罚。如媳妇对公婆不孝敬,“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13]161。
从宋代开始,还出现了不得葬于祖坟、逐出族谱、开除族籍等精神性惩罚。例如,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在其家训中就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14]256这种精神性惩罚是古代对不肖子弟的一种最严厉的惩罚。
到了清代,这种带有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家法族规数量更多,对族人约束和惩罚的规定更为具体和严格,对族人的处罚方法也更加多样,包括训斥、罚跪、记过、锁禁、罚银、革胙、鞭板、鸣官、不许入祠、出族、处死等共计11种之多。
家法族规作为重要的民间规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不但对维护宗族成员团结、保持宗族兴旺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维护封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2.5 谱 牒
谱牒,又称家谱、族谱、宗谱、祖谱等,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载体,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我国的家训自宋代以后有相当的数量是保存在家谱中的,以家谱为实体进行传承,以祖宗、先贤的名义,垂示后人,勖勉子孙。
据史料记载,宋代司马光、欧阳修、苏询等十分热衷于编修家谱,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欧阳氏和苏氏家谱。但是直到宋代末年,家谱编修还未进入寻常百姓家。正如当时的学者欧阳守道所指出的,现今“世家”,也少有族谱,虽是“大家”,但也“往往失其传”[15]。宋代以后,家谱编修越来越普遍。到明清时期,编家谱撰家训盛行,家训进人家谱,常常累代纂修,并不断添加新的内容。民国年间,整个中国几乎是家家都存有家谱。例如,嘉靖年间安徽的《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崇祯十七年江苏润州的《赵氏宗谱》、嘉庆十三年江苏江阴的《刘氏宗谱》和同治八年湖北金口镇的《刘氏宗谱》等。家谱的修撰从精神上、组织上团结了族众,是维持家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2.6 乡 约
乡约即乡规民约,是指由乡民或村社自主自发所订立的,处理众人生活中面临的诸如治安、礼俗和教育等问题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制度。制定乡约之目的是维护公正良俗的民间社会秩序和实现地方社会教化,是“协和尔民”以成仁厚之俗的重要举措。乡约因与中国传统家训的精神追求一脉相承而具有家训文献的性质。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聚族而居的传统,往往一村一乡就是一个家族,这样地域关系便转化成了血缘关系,乡约也就有了家范的意义。”[16]276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是《吕氏乡约》,由北宋蓝田吕氏兄弟所著。《吕氏乡约》定规约四条,即“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每一条下面又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内容涵盖乡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在于扬善抑恶、扶正去邪、和谐邻里和淳化世风。虽然《吕氏乡约》只是吕氏家族的族约,但其历史影响甚大,深刻影响着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和社会教化。宋代以后,乡约备受关注和推崇,多地出现了以《吕氏乡约》为范本的《乡约》文本。南宋时,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了重编修订,史称《增损吕氏乡约》,乡约的影响更加扩大。
明朝时期,乡约是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吕坤和王阳明等都大力提倡和鼓励乡约教化。特别是王阳明“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17]187,制定出《南赣乡约》,并推广实践。《南赣乡约》要求:“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替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8]125《南赣乡约》在江西南安、赣州一带推行,收到良好效果。据相关县志记载,瑞金县“近被政教,甄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日有渐矣。习俗之交,存乎其人也”[19]38;“人心大约淳正,急公输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20]179清代以后,乡约内容更加丰富,并且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约的推行对于匡正民风、革除陋习、促进社会教化和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2.7 蒙学读物
蒙学即启蒙之学,是指专门针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蒙学读物又称蒙书、蒙学教材、启蒙教材、童蒙课本等,是我国古代专为学童启蒙教育编写的教材。唐宋以来,许多家训文献因具有“厚人伦而美习俗”之立意,而成为私塾蒙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启蒙课本。例如,唐代无名氏的《太公家教》采录经史子籍中的嘉言隽语及民间俗语,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和社会规范教育。由于其文字直白易懂,讲授的内容与儿童年龄相宜,是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传播甚广,其阐述的修身应世思想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随着儿童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革新,宋元时期蒙学教材的编撰和流传更甚。许多家训文献常被用作蒙学课本来教育儿童,甚至还出现了蒙学专书。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不仅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而且形式也更加多样。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蒙学著作当属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教子斋规》。该书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从礼、坐、行、立、言、揖、诵、书等八个方面严格要求儿童的日常行为举止,注重童蒙时期儿童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袁采的《袁氏世范》、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司马光的《家范》和赵鼎的《家训笔录》都曾作为蒙学读本被广泛使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其在社会上的传播范围和影响面。
3 实物形式的家训
所谓实物形式的家训,是指家长通过陈列或展示祖先遗留下来的器物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与价值意蕴,引导教诫子弟、家人。
祖先遗留下来的器物是最明显、最重要的实物形式的家训。如五代后唐名将符存审戎马一生,身上中了一百多剑,他便以此作为家训勉励子孙。史书记载:“临终,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取将相,然履锋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 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百余而示之曰:‘尔其勉哉!’”[21]147他将从自己身上拔下的一百多个箭头积聚起来展示给儿子们看,用这些触目惊心的实物警示子弟今日之富贵来之不易,以激励他们奋勇杀敌、立功报国,维护家族荣誉。符氏家族成员以祖先遗物为感召,奋发图强,符氏家族也因此显赫一时。
王质是北宋名相王旦之侄,也善于运用实物教子。王质有一天在阅读家中收藏的书籍时偶然发现,叔父“文正(王旦)作舍人时,家甚虚,尝贷人金以赡昆弟,遇期不入,辍所乘马以偿之”[22]47。王质持这张借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风,吾辈当奉而不坠。宜秘藏之。’ ”王质还将他父亲做官时因为家境贫穷而向别人索取粮米的借据也保存下来,借以教诫子弟清正为官。“又得颜鲁公为尚书时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遗亲友间。其雅尚如此。故终身不贪。”[22]47
父辈赠予晚辈的物品,其中寄托着长辈的祝愿与希望,也应当看作是实物家训。如宋人高登将砚赠送给儿子们,其意显而易见:“人以田,我以砚。遗尔箕,意可见。”[23]422运用实物教子,比一般的家教更形象、直观,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4 实践载体
传统家训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家庭成员进行训导,使家庭成员在平凡日常中潜移默化地塑造良好品格。传统家训的实践载体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4.1 举行经常的训诫仪式
经常的训诫仪式包括“祠堂读谱”和“会所读约”两种。“祠堂读谱”即族长在祭祀时或重大节日在祠堂向家族众人宣读本宗族的家训家规,讲述家族荣辱盛衰的历史,训诫家族子弟言行不得有违家法族规。祠堂读谱的教化方式在宋代就已出现,到了明清时期更加普遍。如《郑氏规范》详细描述了祠堂读谱的操作规范:每天早晨,家人集中于“有序堂”,让未成年子弟朗诵劝善戒恶及和睦家庭、慈爱子孙等家庭道德内容的《男训》 《女训》;每逢初一和十五聚会时,全家人还要在家长的带领下在祠堂唱念道德歌诀和家规祖训等。通过这种家庭中规范化的训诫仪式,使家人子弟接受系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又如明代文学家许相卿制定的《许云邨贻谋》是其传示家人子弟的一部“家则”。《许云邨贻谋》中对“读则”制度有详细规定:每年岁末,将家族的全体人员集合起来阅读“家则”,对“守身持家有不如则者,众相规警,已亟惩乂”[24]591。众人对违反《家则》的家人子弟进行批评规劝,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是一种教育。
以乡约产生和宗法家族制度完善为前提,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教育实践方式——“会所读约”。所谓“会所读约”,“是指族长在乡或村里的公共场所对族众或本村本乡的异姓村民宣读乡约,宣扬封建道德思想,使族众和村民的言行符合封建道德规范”[25]。“会所读约”是对祠堂读谱的进一步发展。
4.2 接触社会的实践锻炼
让子弟参加实践活动,既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还能提升道德修养,所以,传统家训的作者十分重视加强子弟的实践锻炼。
为了使子弟开阔眼界、通晓人情世故、积累处世经验、增强谋生和治家的本领,《郑氏规范》明确规定:“凡子弟当随掌门户者,轮去州邑,练达世故,庶无懵暗不谙事机之患。”[24]501姚舜牧在《药言》中指出:“盘根错节,可以验我之才;波流风靡,可以验我之操;艰难险阻,可以验我之思;震撼折冲,可以验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验我之量。”[26]414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经过实践的锻炼才能增长真知,发现自身的不足。
清代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也十分注重让子弟在社会的大课堂上去经受风雨,锻炼能力。他的次子林聪彝长期蛰居家中,十分缺乏社会经验,林则徐专门撰写家信一封,要他到广州来历练自己。信中说:“吾儿年虽将立,而居家日久,未识世途,读书贵在用世,徒读死书,而全无阅历,亦岂所宜?……此间名师又多,吾儿来后更可问业请益,以广智识,慎勿贪恋家园,不图远大。男儿蓬矢桑弧,所为何来,而可如妇人女子之缩屋称贞哉!”[27]28-29
5 家长的身教
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原则等对子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以身立范、立教,是传统家训教化的又一重要载体。在家庭环境中,作为教育者一方的家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受教育者。正因为如此,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无论言行,都要起到模范表率作用,以身作则胜于口头训诲。正如明末清初文学家申涵光在《格言仅录》中所指出的:“教子贵以身教,不可仅以言教。”[28]159
赵轨在隋高祖时为齐州别驾。他的邻居家种着桑树,桑葚熟了,落在赵轨家的院子里。赵轨见了便叫家人把桑葚一个个捡拾起来,全部送还给邻居,并教诫儿子们:“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入。汝等宜以为诫。”[29]480送还桑葚事小,但赵轨以自身不贪小便宜的言行给予孩子无声的教育,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曾国藩教训子弟要习劳守朴,自己更是一辈子以此进行检点约束。尽管日理万机,却潜心读书,一日都不落下;虽然历经繁华富贵,却谨慎守持俭省朴实的家风,以节俭朴素为美德。正是这种以身立范与言传身教,让曾国藩的家庭道德教育落地生根。
相比较于家长有意为之的实物家训或文字训诫,家长自身的行为教育淡化或模糊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对立问题,更具亲和力、可信性,濡染更直接、更现实,因而更具感染力,效果自然也更佳。
6 家风的熏陶濡染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30]家风是家庭文化和家庭教育的集中体现,是隐形的“家训”,于无声无息、耳濡目染中影响着家庭成员的道德品格。良好的家风一旦形成,就能成为一种潜在的、无形的道德力量,激励子弟秉承父辈的优良品德。历史上不少家训作者都非常重视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作用。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要求子孙将祖先清白做人、俭省节约、注重气节操守的家风继承下来。他在《示子孙》的教子诗中敦敦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31]1213,要求子孙勤奋努力、恬静淡泊、固守气节、推崇德行。元代名相耶律楚材出身声名显赫的皇族,在写给房孙重奴行的一首诗中,他告诫其孙加强自身修养,不要辱没家风:“汝亦东丹十世孙,家亡国破一身存。而今正好行仁义,勿学轻薄辱我门。”[32]160明清之际的学者、教育家朱舜水通过讲述朱家的清白家风对子弟进行家风教育,他在《与诸孙男书》中说:“汝曾祖清风两袖,所遗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贫,齑盐疏布。年二十岁,遭逢七载饥荒,养赡一家数十口,无有不得其所者。汝伯祖官至开府,今日罢职,不及一两月,家无馀财。宗戚过我门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为嗤笑,非赞美之也。岂但我今日独薄于汝辈?勿怨可也。”[33]387
总之,传统家训文化的载体形式丰富多样,语言形式、文字形式、实物形式、实践形式、家长的身教和家风的熏陶濡染等不一而足,各载体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载体形式的多样化对于家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提高家训教化的实效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对训诫法律属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