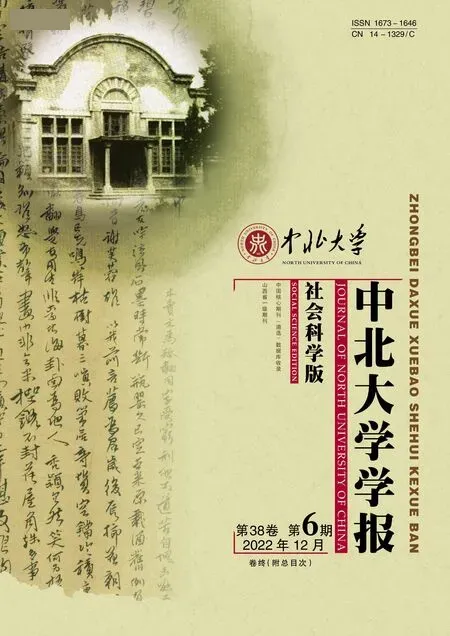民国时期山西汾阳基督教的戏剧与电影活动考察*
张仕林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系,北京 101499)
0 引 言
古称汾州的汾阳在明清时期曾为府治所在地,1912年撤府设县,现为山西省吕梁市属的县级市。作为由山西进入陕西通道上的重要关隘,处在吕梁山脉和太原盆地交界的汾阳在民国时期“代表了山西最富庶的地区,县内居民有二分之一是在外经商的”[1]。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经济发展让这里成为了基督教公理会最早进入中国的内陆地区之一,“光绪八年至十五年间,美国教士冕得禄及唐德先后莅晋,游行汾太平介各地……渐设教堂于汾州”[2]。由基督教公理会汾阳传教站主导的汾阳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23年,是民国时期少数在县级城市建立的城市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基督教的社会服务组织,汾阳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任务是联系青年、宣传福音、发展教会。20世纪2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前,基督教在汾阳的势力达到极盛,各类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机构占到汾阳城面积的八分之一,对一个基层县域的影响一时颇深。[3]以汾阳为中心,基督教的传教范围拓展至了山西中部、陕西西部和内蒙南部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4]
20世纪前期,中国除了科学民主和共产主义两种救国主张以外,基督教救国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基督教是列强入侵的工具之一,主张并不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可。[5]180戏剧与电影“除了是文化商品和工艺以外,也是一种社会力量”[6]2,基督教利用这种充斥着现代性的文化工具冲破中国传统社会并建造新教伦理为新道德主体的社会,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美国拓展其全球化的商业版图。基督教将社会福音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等带入中国,基督教教会不仅在力促中国医疗和教育事业改革中不断赢取吸纳教徒的红利,更是通过戏剧电影等文艺娱乐活动吸引着基层群众的关注。例如,各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在社会服务的同时还设立青年电影院,一方面通过经营收益作为青年会一部分日常运营经费[7],另一方面也通过电影这种知性娱乐实现社会教育。[8]然而,基督教的戏剧与电影活动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内地县域社会基督教的戏剧电影活动研究更是盲点。本文将以民国时期的杂志和报纸为依托,考察民国时期汾阳基督教的戏剧与电影活动及影响。
1 戏剧演出:从精英娱乐到宣教工具
传统中国的百姓若想看剧听曲非到逢年过节不能有之,直到近代口岸通商后营业性戏院才在京沪等城市逐渐出现。在西方传教士和来往商人的影响下,营业性戏院也逐步向内陆地区扩展,看剧听戏成为近代中国城市中的一项时尚活动。民国早期,汾阳东大街十八庵于1916年建立的吉星楼戏院已开始长期演戏,该地在汾阳被日军占领时期还曾放映过电影。[9-10]1934年,汾阳演剧多到成为社会的弊病,“本县演剧筹欵之举,迄今不惟稍减,且有与日俱增之势”。山西正值因旱涝灾害而农村破产的困难时期,社会团体林立,每到成立总以演剧筹款。[10]此时,汾阳“无论何团体演出一天,县政府都能尽得大洋二十元”[11]。另外,汾阳汇海商场内还设有杨小戏园,1936年,汾阳人购买了无线电收音机后曾设座有偿“收音”。[12]
基督教会、西式医院、教会学校等中长期存在着唱诗班等文艺活动,西方学校学生表演戏剧的传统也随着基督教的进入被移植到了汾阳。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基督教公理会主办的汾阳私立铭义中学每年都会利用假日公演话剧,偶尔对外销售门票的收入还会运用于学生会的日常开销。[13]267-2681933年的平安夜,汾阳基督教公理会传教站中传教士们的孩子还表演了《耶稣的诞生》(TheNativityofJesus)情节剧。当夜由于烛光的照耀,节目显示出了神圣的戏剧效果。[14]基督教公理会在汾阳最隆重的内部戏剧演出举办于 1936年底教会非信徒培训课程中,此次演出由基督教公理会汾阳传教站主办,汾阳医院、铭义中学、崇德女校等传教站主导下的各类型教育机构参与,传教士创作了演出的剧本。作为一部历史剧,演出中有很多斗争动作,“最后四个场景都设有‘委员会会议’,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现代使命的主流理念”[15]。民国时期汾阳基督教的戏剧活动大多数还是传教士和汾阳亲西方文化士绅的精英娱乐,很难突破汾阳城墙走向农村,贫苦大众对于这些娱乐文化的接受无论从经济还是渠道上都存在着限制。
戏剧活动出现在公共场合,向教会以外的观众进行表演的可考最早时间为1922年。当时,汾阳崇德女校要在基督教大礼堂内进行戏剧演出,传教士害怕汾阳人接受不了全是女学生的新式戏剧,通过将门票价格定得很高来提高参与门槛,结果仍来了很多人。[16]1931年,崇德女校的学生在招待会上还演出了即兴创作的话剧,“展示了一个乡村家庭通过传教、教学和教育的方式逐渐转变的过程”[17]。
1932年,民族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铭义中学邀请了来自北京的彭姓教育家莅校参观演讲,他在演讲中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受其爱国主义的演讲启发,创建了“铭义中学基督教团契”(Ming I High School Cristian Fellowship)。学生团契不仅发起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寺庙朝圣,还在1933年夏天夜间进行了现代中国戏剧表演来筹款的活动,所得资金都被用于当年在峪道河举行的夏令营中。[18]
在基督教公理会保定传教站的福音戏剧得到宣教效果的启发下,汾阳传教站在铭义中学基督教团契前期实践的基础上,于1933年成立了旅行剧团并于当年秋天开始四处巡演。剧团成立时有12个人,常备节目为《浪荡子》(TheProdigalSon)、《财主和乞丐》(TheRichManandLazarus)等圣经故事的改编戏剧和教会自编自演的《攻击文盲》(AttackonIlliteracy)。[19]旅行剧团的演出地点通常是村里的打谷场、寺庙院子或乡村戏台,“每天三场表演都伴随着情节清晰的演讲,一种深刻的宗教精神渗透了整个世界”,一些时日来看戏的群众约1 000人左右,很多人是“至少步行7英里看演出”,他们甚至会因为《浪荡子》中荡子的回头而感动落泪。节目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以至于乡镇士绅出钱要求旅行剧团在村里多待些时间继续表演节目,他们还赠送给剧团一面写着“社会前沿领袖”的横幅。[20]
1935年,旅行剧团到了顶峰时期,其成员包含19个男教徒和3个女教徒,当年秋天在三个村庄进行了演出,每次演出的内容都相对固定:
早上8点:晨祷。
上午10点到12点:三名团员的宗教主题演讲。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戏剧表演,包括三个故事《浪荡子》《财主和乞丐》《出卖约瑟》;两个表演分别是“家庭改革和基督化”、中国道德剧。
下午5点到8点:关于宗教或团结主题的一对一、小团体谈话。
晚上8点半:晚祷。[21]
1935年,旅行剧团在前两个地方依然选择了当地的寺庙舞台或院子作为演出的场所,寺庙中的和尚或道士对基督教的演讲与演出并没有排斥,形成了一种中西宗教文化共融的独特景观。他们在第二个村庄的演出由当地士绅邀请并支付了剧团从乡村返回汾阳县城的费用,临行之前还赠送了“世界真光”的条幅。一些汾阳乡镇在每年举办秋集期间会由本地商会邀请戏班前来演出,但旅行剧团所到的第三个地方肖家庄镇由于请不起戏班,便采取了让基督教的旅行剧团来代替的计划。最初旅行剧团觉得肖家庄距离汾阳县城相对遥远不愿意过去,但没想到的是在当地演出的五天时间里来了成千上万的当地群众,他们挤在剧团搭建的舞台周围观看演出。肖家庄镇的商人团体为剧团报销了交通、食宿和其他杂项费用,群众不仅对剧团所表演的节目非常赞赏,也为商会“意识到了人们的道德需求”而表达了谢意。由此,基督教公理会汾阳传教站看到了戏剧活动在宣教方面的效果,“旅行剧团”此后便发展成了汾阳传教站每年秋天都会进行的重要传教布道活动。[22]
由于时局变动,汾阳基督教公理会在 1936年以后开始衰落,1938年2月,日军占领汾阳,虽然日美之间尚未有战端,但基督教在汾阳的发展仍被影响。1939年,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汾阳传教站在发往美国的工作汇报中尽管仍有“圣经故事戏剧和反封建计划”,甚至要“发展圣经故事戏剧作为当地传教群体的特殊才能”的想法[23],但迄今仍未发现实际行动的支撑史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征用了美国教会在华的全部财产,基督教公理会在汾阳的资产也未能幸免,其主理下的汾阳医院被迫改为日本军医院。解放战争时期,地处军事要塞的汾阳长期处于国共两军的争执状态。1948年,汾阳解放后,汾阳政府才实施了对基督教汾阳教会的财产的保护政策。[24]90基督教公理会自身的衰落与30年代后期战乱的环境不仅导致了其戏剧活动的衰减,就连其正常的传教活动也力不从心。1939年以后,《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中由汾阳发往美国的汇报也仅剩下在1941年夏天举办的训练课程,汇报人员表示“这些事情并不能有助于福音的传播,整个团队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25]。
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公理会在汾阳还不断购置地产,建成了新旧教堂、汾阳医院、中小学校等机构。1920年,公理会在汾阳东大街改建购置来的两间铺面为二层楼房并开设广智院(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dge),传教士们希望这里成为汾阳的宗教中心和社交文化中心,内设动植物标本以增长群众知识。但是,基督教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普及文化的地方却被长期精神文化生活压抑的汾阳人“注入了‘娱乐’因子”,刚开始对外开放便涌来成百上千的观众,形成了像庙会一样欢闹的场面,以至必须分时段排队才能进入观看。[26]
2 电影放映与拍摄:县域电影事业的起步
相比基督教公理会用戏剧、演讲、圣经研究会的方式来达到宣教目的,汾阳基督教青年会则采取了间接的传教方式,“它不是有形的传道说教,是无形地宣扬耶稣基督的精神,感化青年,使其自愿信教”[5]72,电影放映、赈灾救灾等正是他们的手段。从早期区域电影史的角度看,在1924年,汾阳东正街考院和东关大营盘的驻军部队便曾放映过无声电影。1925年,太原基督教布道会在汾阳峪道河镇举行的夏令营中还放映过《养蜜蜂》《改良麦种》《制作昆虫标本》等教育电影[27]793,鉴于基督教在各地都会举办职业培训班,太原基督教布道会的这次放映有可能是为演讲补充的教育电影播映。
根据对民国时期的相关报刊的考证看,汾阳基督教青年会所进行的电影放映不迟于1932年4月,本月出版的《汾州青年》刊登过这样的消息:
本会专为开通民智,促进会务,联络会友起见,特请太原永明电影社于本月十一、十二日两天,公开演映。除该社每日自行售票百余张,以资开销外,完全由本会赠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会会友。是日会场秩序甚好,观众甚为踊跃,殊颇极一时之盛![28]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汾阳基督教青年会所进行的电影放映是与太原永明电影社的合作放映,售票百余张便达到了开销份额,按照当时每张5角到 1元左右的票价估计,本次放映的成本应在50元~100元之间。当时各城市青年会组办电影院已经成气候,汾阳基督教青年会将剩余的票赠予出去,说明这次电影放映要么是青年会的活动,要么是盈利经营的尝试。直到1933年,《新天津》刊登了一则与汾阳相关的新闻:
本邑素称通商大阜,惟缺少电影院,于是有王相臣、刘俊峰、盛宝华等磋商假青年会大礼堂地址合组一青年电影社,已与太原青年会定立合同,早经签字租用联华影片公司影片,五日一换,每日上映两场。已择于本月二十一日开幕,放映全本《玉堂春》。[29]
类似的消息也出现在1934年的《同工》杂志:
汾阳虽属居民稠密商号林立,但文化的发展究较通都悬殊。近该会会员杨子厚、白少左为促进文化,租借该会部分地址创办青年电影院,借此开拓民智,促进文化云。[30]
两则新闻有创办时间、创办人等方面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惟缺少电影院”和“文化的发展究较通都悬殊”均证明了汾阳在电影院经营上属于空缺状态,汾阳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组建的青年电影院可以确定为汾阳电影院的起点。该影院正式经营时间为1933年5月21日,地点在汾阳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即基督教公理会在汾阳东大街改建的广智院内,第一部放映的电影是联华公司出品的《玉堂春》。其次,《同工》杂志的办刊地点为上海市,各地的消息到达上海后都会延迟,而1934年第129期对于汾阳地方消息的刊登,该杂志还专加了“迟到”二字,可见它与《新天津》上指明的时间出入不大。最后,汾阳的青年电影院由汾阳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主办,股东实际并非少数人,两则新闻在主语后用了“磋商”和“租借”,创办人员的不同体现为发起人和出资人的不同。
《新天津》的新闻中表示汾阳的青年电影院是与太原基督教青年会签订的协议,太原青年会在19世纪20年代存在着“青年会电影社”和“青年电影院”两个电影放映机构。青年电影院创建于1928年,不久便转由罗明佑的华北电影公司接手。[31]时值美国正在进行的电影清洁运动,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响应“英美法各国信徒发起一种反对取缔不良电影誓言”的号召,“征求同志加入”,提倡“电影界对于输入东方各国影片应加改良,并且对于本国影片也要特别注意往善的方面走”[32]。“对上帝心怀赤城”的基督徒罗明佑在华北电影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的经营方针恰是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的转化,他认为电影应该“普及社会教育,使影片到民间去,向中国内地发展……为利用电影宣传辅助国家善政的推行,必要时在各埠设立服务社会的机构”[33]138-139。汾阳青年电影院“开拓民智”“促进文化”等初衷也与联华影业的“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理念有着重叠,在中国内地合并更多的影院加入其放映体系与联华的经营方针并行不悖。由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玉堂春》上映两年后才在汾阳放映,也可以说明汾阳青年电影院在成立之初便被纳入罗明佑的华北电影公司多轮放映体系。
汾阳青年会电影院之所以要商业经营,实际上还有着一定的收入需求,其中既包括汾阳青年会自身的因素,也涵盖着整个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实践经验。1923年成立的汾阳基督教青年会直至1925年才结束会员征求,且“所得者不多”,基本金筹募需要在“时局平定后继续推行,已由西人裴易铎君担任其半,刻孔庸之(孔祥熙)先生已慨助千元”[34]。可见其从创始之处便存在着财务问题,汾阳基督教青年会在公理会传教站的协助下相继创办各类养殖场等农家副业,除了有为当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目的外[35],其实更多还是为了满足青年会的日常财务需求。另外,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除了能够得到北美协会一定程度上的资助外,其大部分经营费用来源还有两种渠道,其一是会员费和社会名流的赞助,其二便是基督教青年会各类文化娱乐事业的经营利润所得。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国内发展规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会,仍然在1915年四川路会所落成以后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亏空,于是在后期决定“每届星期六晚间八时,特开会员家属同乐会,专备有益智游戏,及长片活动、电光影戏,或著名幻术等,藉以联络感情,娱人心目。但每举所费颇巨,因历年定例,凡来观者会员取费一角,非会员二角,意欲稍补漏缺”[36]。由此可见,汾阳基督教青年会的电影院经营,很大程度也冲着盈利目的。不同于早些时间段各类型教育电影的零散放映,汾阳青年电影院的创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汾阳电影事业的真正起步。青年电影院能做到电影“五日一换,每日上映两场”,其实也标志着电影这一摩登生活体验以较为规律和固定的放映方式进入到近代县域社会中,纵然受制于经济、交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青年电影院不可能影响到全县域的人民,但也让当地的部分人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大城市之外经历一番“现代的观影”行动。
电影放映之外,基督教公理会的传教士还拍摄了汾阳的第一部电影《汾州》——一部时长23分钟的无声黑白电影。新中国建立后,铭义中学转制为山西省汾阳中学,该校在百年校庆时的资料收集工作中,意外发现了在卡尔顿大学图书馆收藏室的胶片,该片据传由铭义中学外教克顿所拍。从类型上看,《汾州》是早期电影时期景观电影的集合,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美国传教士、医生、教师在汾阳工作生活的记录,汾阳城墙及娶亲仪式、农民劳作等风土人情,铭义中学童子军训练及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迁徙办学。
《汾州》的镜头相对散乱、剪接处理简单,但镜头中的社会民情和时代风云对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县域社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片中既有干净整洁的教堂、汾阳医院、铭义中学等现代意味十足的景观,又有破旧的古城墙、脏乱狭窄的古街、旧式迎亲等传统走向没落的景象,构建了一种城市景观电影的公共性冲突图景。普通百姓的婚丧嫁娶和铭义中学学生的军训及危难中搬迁办学之间的对比又是“聚焦式互动之外的共同在场中建立起信任”的“世俗的不经意”,在民族特征的识别中召唤着视觉化的现代转型意识。
3 戏剧与电影作为吸引力装置:福音传播与社会教育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中,美国的传教士已经意识到了娱乐活动作为一种传教“吸引力”的存在。英国的约翰·柯文(John Curwen)为提高合唱的水平、加强基督教礼拜和社会改革而开创的首调唱名法(The Tonic Sol-fa)在英伦三岛流传开来后,很快便被传教士引进到亚太地区国家的传教运动中,他们试图用赞美诗的吸引力将其作为一种传播福音的手段,而由此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斐济的赞美诗便是按照首调唱名法进行的记述。[37]近代中国的现代戏剧处于发轫时期,基督教实际早已利用话剧这种新兴娱乐媒介进行了长时间的传教与布道,《救恩》《中华真主》等基督教文学刊物上已经陆续出现了改编自《圣经》的简单剧本。[38]6-8可以发现,首调唱名、话剧等作为一种感染观众的吸引力装置已存在于传教士的布道活动,虽然此时的音乐和话剧暂时还无法被归入“一流的吸引力”之列,但是这些由现代娱乐方式的吸引力装置所组接的“文化序列”(Culture Series)[39]确实间接性地推动了基督教福音在县域社会的传播以及社会教育运动的发展。
汾阳基督教旅行剧团所演出的剧本现已不可见,但可以从山西其他地区传教士所主导的戏剧活动中窥见一斑。《真福吴国盛》这一由教会人员创作的现代话剧在晋南曾长久上演,《公教周刊》还在 1930年和1931年两次连载了该剧的剧本。《真福吴国盛》分为五幕,主要讲述徐姓教友劝说吴国盛入教的故事。相比直接的圣经故事改编,《真福吴国盛》将基督教故事原型与语境转置于中国社会,以朴素的中国民众作为剧作的主要人物形象,在宗教道德和白话口语的表演统一中提升了故事感染力。另外,作为一种话剧表演,“导演、布置、装饰,都开艺术之花”[40],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形式,实际上基督教的新剧对于以农业从业者为主的县域来说都成为了一种震惊体验。在基督教刊物呈现的新闻及当时受众的回忆描述中,可以看到戏剧、电影及展览等活动作为吸引力装置的福音传播影响与效果:
该团为吸引群众接受福音起见,于去年十一月间,在汾文区各地化妆表演各新剧,均系奖善罚恶劝人为善之作。此外并有警惕标语,导人归主。其所演各剧,均能使人发生至深刻之观念云。[41]
山西籍作家马烽也对儿时在汾阳基督教公理会广智院观看动植物标本的记忆深刻:
(广智院)里面有老虎、猴子、狼等动物,虽然不是活的可是真的(标本)。这些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42]
作为吸引力装置的基督教戏剧、展览等活动在促进基督教传播教义的同时,实际上还产生了启发民智、促进社会文化繁荣的作用。随着国家局势的变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汾阳地区的深入发展及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戏剧表演这一吸引群众的娱乐形式在铭义中学学生的实践中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救国与树人的主题越来越明显。“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铭义中学学生就曾与西北军军官教导团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请东北流亡学生作报告并演出抗日话剧。[43]157-165另外,基督教旅行剧团的实践活动也促进了现代新人的培养,增强了县域知识青年走出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如剧团中一个叫许毅的成员于1939年到沪求职,在《青青电影》杂志上刊登了个人广告,表示他“能操国语,曾加入基督教会主办之‘旅行剧团’,对舞台生活颇有经验,对戏剧有特别嗜好,有志投身于影界”[44]。
电影作为基督教青年会重要的健康娱乐活动之一,长期以来就有着以宗教道德感化助长“德育”、以同乐会促进“群育”、以教育电影放映推动“智育”等多重社会教育的功用与目的。汾阳基督教青年会主持下的青年电影院开业便放《玉堂春》,也有着基督教在汾阳长期进行各类型事工的考量。基督教公理会长期关注着汾阳的妇女问题,1922年他们以创办各年龄段女校、举办女性工作培训班等形式领导着当地的女性解放运动,且“在为争取‘教育机会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中预先尝到了胜利的滋味,期待在教会领导下大量的汾阳妇女能有真正的平等”[45]。《玉堂春》是根据京剧《苏三起解》《三堂会审》改编而来,一个以法律判例实践为题的明代故事被包装成民国现代戏,赋之以“妇女问题”标签,认为《玉堂春》“就是隐晦提倡改造现在男子心中的文明,而撤废从来妇女的奴隶地位,建设男女的新社会为唯一目的”[46]。《玉堂春》与基督教之间的共识恰好让电影成为社会教育工具。
与戏剧演出相比,电影对于民国时期汾阳县城的人们更具吸引力,正如早期景观电影所呈现的“杂耍”特征与吸引力。电影《玉堂春》所呈现出的法治意识以及女性“制服丈夫的方法”[47],正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所传播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一,“若银幕上之玉堂春,则着重表情,可使观客领会剧旨之纯洁,警惕人生、指导人生、讽刺人生、规诫人生,可谓无美不备”[48]。
4 结 语
基督教对山西汾阳等县域基层社会的影响可以用汪晖在对中国革命历史条件进行论述时提到的“薄弱环节”所解释。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两种薄弱环节即列宁所说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民族内部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缝隙,其“为中国革命力量在广阔乡村和边缘区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49]的同时,实际上也是西方宗教文化势力深度进入中国社会的条件。基督教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推行戏剧和电影活动,目的绝非是单单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戏剧电影活动作为传教手段与吸引力装置,很大程度上具有着文化侵略和建立文化霸权的目的,通过社会控制达成对市场的占领,他们为中国近代社会所带来的现代科技和生活方式更像是文化与资本入侵的附属品。
在对汾阳基督教的戏剧电影活动所进行的考察中,史料的散佚对研究造成极大困扰,特别是在1934年以后基督教在汾阳式微后,汾阳基督教青年会究竟还有没有继续其他片目的放映,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是,就已有文献资料来看,汾阳并非基督教运用戏剧与电影进行传教或社会教育的唯一一个近代基层县域社会,其密集的网络覆盖到了当时中国非常多的城市和乡村。很多现象看似孤立,实际上牵扯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基督教主导下的青年会及其电影放映所能进行的地域性研究对象拓展也并非只有京沪港或者汾阳,视角与范式可以拓展到政治经济学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后续的研究,除了要对史料继续挖掘,还必须从社会史的基础出发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这些看似被遗忘的独特景象对社会史、文化史、电影史、媒介史的侧面考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汾阳人学习普通话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