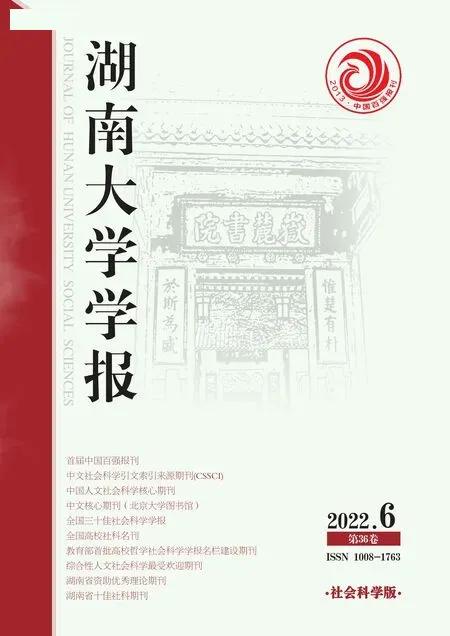论李梦阳之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王菲菲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众所周知,在明代中叶,历经短暂的“仁宣之治”后,从正统到正德年间,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变迁,从政治格局的嬗变,经济秩序的震荡,到农民的武装斗争,以及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厌常喜新”,[1]142-193无疑明代中叶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在学界甚至直接有“明中期变革说”的提法,除此之外其他的诸多学术课题,如“唐宋变革论”“宋元明过渡”“元明变革”等,[2]也都以明代中叶作为一个历史时限的起始点或者终结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阶层处于怎样的状态,面对政治的嬗变,经济的变迁,以及在此影响下所形成的整个社会的风教,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又如何在自己的仕宦生涯中践行这种回应,着实值得探讨。
李梦阳(1472-1530)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繁复的时代中,但当论及其人,很多的学术关注都集中在他“文人”的角色上,如“前七子”的领袖,文学复古运动等等。我们不能否认他所提出的“真诗在民间”“法式”“格调”等对诗文方面的种种贡献,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士人”的身份。诚如廖可斌所言,“复古运动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与政治斗争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复古诸子以文学为手段进行政治斗争,又通过参加政治斗争扩大复古派的影响,推动复古运动的发展”。[3]69可见,对李梦阳而言,其文学上的主张正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形成,这种通过文学手段对时政做出的积极反应,也是我们以他作为考察中心的主要原因。[4]1-26因此,本文将转换研究视角,关注到李梦阳湮没在“文人”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主要从其仕宦经历以及经世层面进行考察,借此挖掘出在时代变迁下当时的士人状态及其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李梦阳自庆阳守制后,弘治十一年(1498)出仕,历任户部主事、郎中、山西布政司、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等职,任职期间曾奉命犒榆林军、监三关招商、饷宁夏军等。[5]112-119基于这样的仕宦经历,其对于当时的教育、经济发展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关于教育以及盐政问题,有着一定的见解和实践。
一 教育实践
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被诏起为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其在任期间,为江西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6]主要集中于社学的建立以及书院的兴修。
首先,关于社学的建立:
南、新二县者,省城县也。今立社学一十六:曰民彝、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沧洲、曰蓼洲、曰通济、曰高节、曰通真,南昌学;曰思贤,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学。[7]380
李梦阳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建立社学,先远后近,逐步扩及全省。社学的设立始于元代,到明太祖时期依然十分重视,但是由于地方胥吏的执行不力,不但未发挥积极作用,反而成为“民众之役”,故逐渐废弃。李梦阳对江西社学的复兴,在明代社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他为什么要复兴社学?除了自身肩负着提学副使的职责外,似乎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他对于家祖礼法等最基本的伦理纲常教育的重视。例如其用《训敦》一文,详细地论述了尊祖敬宗之重要性: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涣也,于是类焉,易曰“类族辨物。”患其乖也,于是睦焉,书曰“九族既睦。”患其争也,于是有大小宗之礼;患其忘也,于是有大宗之庙;又患其弗率,于是有九两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历周、秦、燕、赵、晋、卫诸墟,询故采实,未尝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祸之邪?……览风大江之南东,见其故国遗俗,有百年著土之民。[7]536
如其所论,宗族、家庙等自古即已建立,用以平治天下,“窃惟礼义,人之大闲;纲常,国之命脉”[7]360,而如今却“教衰族散”,未尝不使人悲叹。而更让李梦阳感叹的是士大夫的“教废”:
祀礼,发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广爱敬而交神人也。圣人之意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于祀;严祀立教,莫大于祖考。爱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于祀也忽,故其教废;教废则风偷,风偷则俗恶,故其子孙视其祖考犹秦、越也。吁,甚矣!圣人之微意蔑乎![7]609
在李梦阳看来,祀礼之重在于“祖考”,是为圣人之意,而今士大夫却“于祀也忽”,使得“教废”,最终导致“俗恶”。“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7]348因此作为民之楷模的士大夫“教废”,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教。
除了对于祀礼的强调外,李梦阳对于修谱的行为也大为赞扬。如其在《董氏族谱序》中讲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谱观也……夫自大学教衰也,士不由齐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董之政似君陈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谱而知之也。”[7]490其认为董氏虽不“官政”,却知“家政”,因其“知本”也,同样值得赞扬。而且李梦阳本身也对此作出了实践,其在正德二年(1507)修撰了李氏家谱。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李梦阳对于伦理纲常、尊祖敬宗等基本德行的重视,尤其强调士大夫阶层的实践。这种重视和社学有怎样的关系呢?其在《南新二县在城社学碑》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论述:
社学者,社立一学,以教民之子,所以养蒙、敛才、视化、观治者也。自庠序教废,民之子盖不复教之乡,而辄入其县州府学。其童子事未之习,未知室家长幼之节,而业已学先圣礼乐,讲朝廷君臣之礼矣。按古制:里有序,乡有庠,民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今既不教之乡,以为养蒙、敛才之地,而县州府学,势又不得尽蓄其才,如此而欲视化以观治,难矣!是以治天下者忧焉![7]379
如其所论,社学的教育用以“养蒙、敛才”,主要学习“室家长幼之节”等基本的德行,而如今社学之废使得“童子事”尚未学好,便要讲“先圣礼乐”“君臣之礼”,是故本末倒置。如上所论,家祖礼法等最基本的德行,尤其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至关重要,事关整个社会风教的形成,应该自始便加强教育,加之州县府学不能“尽蓄其才”,所以在李梦阳看来,社学的建立势在必行。其后来甚至规定“非社学生,其勿入其县州、府学”,足以见得他对于家祖礼法等最基本德行教育的重视。有关于此,Sarah Schneewind在讨论明代社学时也有所论述,她讲到明代社学在教学内容上,确实大多强调礼仪实践。[8]100-101还有一点,自李梦阳对于社学的建立中不能明显看出。明代中叶部分社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书院的大量兴修,是在毁掉淫祠的基础上所建立的。[8]76-91因此社学的建立,也利于社会风教的纠正。其次,李梦阳之教育实践还表现在书院的重修与建立。如白鹿洞书院、旴江书院、东山书院、钟陵书院等,[7]382、375、377在此不一一列举。那么他为什么要大量的兴修书院呢?对此其在《东山书院重建碑》中略有论述:
夫士养于学,足矣!奚贵于书院?盖书院者,萃俊而专业者也。夫士群居则杂,杂则志乱,志乱则行荒,故学以养之者,大也。书院以萃之者,其俊也,俊不萃则业不专。业专则学精,学精则道明,道明则教化行……故书院者,辅学以成俊者也。[7]375
由此可知,在李梦阳看来,官学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有限性,使得士人“志乱行荒”。“不患不明而患学不精,不患不精而患业不专,否则不足谓之士,矧谓之俊。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也”[7]376。所谓“业不专”不足以称士,李梦阳十分强调“业专”的作用,此点是基于其对于当时士人间存在的普遍现象而提出的。而书院的作用就在于俊其萃者,使得“业专学精”,最终明道以行教化,是为官学教育最好的辅助者。
另外,李梦阳通过书院的建立以行教化,还基于其对于佛、道信仰之风的排斥。例如,其在《上孝宗皇帝书》“六渐”中的“方术惑之渐”“匮之渐”中都提及佛道信仰之弊端:
而今创寺创观请额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诏葺其圮废,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于彼而为之也……今天变屡见于上,百姓嗷嗷于下,边报未捷,仓库匮乏。信如真人国师,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一试之?且彼能设一醮,噀一法,使天变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无之事,而陛下不察,反听其诱。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7]353
夫钱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则聚于下,公家削则私室盈。今京城内外,千观万寺亦炽矣,顾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动孰匪以巨万计……顾遍察寺观等,敕给费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巨万入者,又何惮而不造寺也。[7]351
由此可知,佛道之信仰,对于“天变”,以及百姓之苦毫无作用,且其修葺之重费又造成财政的匮乏。百姓在皇帝奉佛、道的影响之下,必然信仰成风,而“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7]382。因此李梦阳在江西大量重修、建立的书院中,部分都是将庙、观拆毁,如旴江书院建于东岳庙之上,钟陵书院建于福胜寺之上,筠阳书院也是由寺庙改建而成。这一方面在于风教之施行,而在潜在的层面上也冲击了江西地区的佛、道信仰。
而对于教化施行产生影响的因素,除了佛、道信仰之俗外,还受到当时明代特有的“重贾”风气的挑战,如李梦阳在《旴江书院碑》中明确记载了当地“重贾轻业儒”之土俗:
其言曰:“夫贾,出本而入息,岁有程算相当,即不偶,不甚远。夫儒者,劳费而効逖者也,即中科第,有官职,富田宅衣马,庇耀其族党,然遡其供膳积费,不偿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职也……予既令创是书院,择士集习于中,复书其土俗于碑……莫若从其俗为贾,毋混处以祸吾儒。[7]382
在当地人看来,从商出本即有息,而业儒者费神且出成效较慢,中科第有官职尚且还好,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取得职位,因此二者相较之下,就会选择重商。这种风俗必然是对士人阶层最要害的冲击。于李梦阳而言,建立书院、择士业儒则成为实施教化的必要行为。这种理念并非是基于建昌一地的风俗而促成,更是基于他之前的仕宦经历,尤其是对于明代中期整个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商人势力成长深刻体验下而形成的。关于此内容,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进行详细探讨。
综上所论可以看出,无论是关于社学的建立,还是书院的大量兴修,李梦阳对于士人的培养以及风教的形成都极为重视。因为在他看来,受到当时社会佛道信仰,以及“重贾轻业儒”风气的影响,整个士人阶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士人对于尊祖敬宗、家祖礼法等最基本的德行都已沦丧,而这些所谓的“编写族谱、修建宗祠”活动,正是“属于‘士大夫’的功能”[9]161。这种受社会风气影响而形成的教废及道德沦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士人阶层的地位。加之,官学对士人的培养使得“志乱行慌”,且“业不专”,导致了士人阶层行政职能的下降,“德之经而政之所由行也”[7]499,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阶层的“教废”与“业不专”,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的教化以及政治实践。如其所论,“是故,君子以仁义为竿,以彝伦为丝,以六艺为饵,以广居正位为盘石,以道德为渊……是以君子身处一室,而神游天地矣”[7]381。是故“德以立政,业以广志,征以推信”[7]477,又是学校之要也。他对于士人教育的强调,正是通过学的手段,重新塑造士大夫之德行,以及整个社会的教化。
二 盐政思想
如前所论,李梦阳对于书院的兴修,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对当时社会“重贾轻业儒”风俗的考虑。这种考虑并非仅仅依据江西的现状而萌发,更是基于他对于当时整个商业发展的深刻认识。李梦阳在弘治十一年(1498)担任户部主事,奉命监税三关,故对于当时商业的发展有一定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盐政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其曾上奏《拟处置盐法事宜状》,论及他对当时盐业发展的看法,同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
正所谓“盐者,利之宗而弊之薮也”[7]358,历代以来,盐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明代“恰是处在中国传统官统制盐业向商专卖制移行的重要历史时期”,[10]3出现了官般官卖向商人运销转化的趋势。黄仁宇在讲到十六世纪盐的专卖时,也讲到“十五世纪晚期得到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食盐专卖制度的结构十分微弱,很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弊端百出”,“贯穿十六世纪的这项工作经常陷入周期性危机之中”。[11]237明中叶以前,官卖食盐制度已发育成熟,构成系统而细密的运营体制。明末至清,食盐官卖渐向商卖转型,其制度多有更张,而李梦阳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期,在他看来,当时的盐法遭到破坏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如其所论,“今盐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锥刀之子,举得鼓舌,与官府争低昂。设一无赖子弟攘臂贾众,观望揺撼,需满而应,则轻重之柄岂复在我哉?”可见,明代中叶食盐商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官盐之不行久矣”,而盐商势力的成长,必然造成官方对于盐业操控权的丧失。[7]359
商人势力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李梦阳曾多次提到:
今天下机利莫于盐若货,盐若货散而之四方剧,故盐若货贾尤富……泰者则辄揳妓女,弹鸣瑟,即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矣。夫贾,编户之民也,而一旦音乐、妓女之奉,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则淫侈而易为邪。[7]538
借盐利而成长起来的富商们,无论在衣着、车马均与“大贵人”等同,而商贾为“编户之民”,如此奢侈之行为与其“民”之身份实为不符,这也就是学界所讨论的明代商人固有的特点——“越礼”[12]。因此,商人势力的成长及其越礼的行为,打乱了应有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于士人阶层的冲击。
在李梦阳看来,如若盐政的问题仅仅在于商人本身,“夫太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则易而不畏,此无他,势逆也”。然而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
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縠,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埓也。又畜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借其荫庇。今淮阳仕宦数大家,非有尺寸之阶甔石之储,一旦累赀巨百万数,其力势足以制大贾,揣摩机识,足以蔑祸而固福,四方之贾,有不出其门者亦寡矣。
如此看来,问题的复杂主要在于商贾之家,通过贿赂等各种手段“援结豪贵”,借其庇护,官商勾结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勾结,除了体现在商人想取得庇护外,还表现在部分权贵假借商人之名自己经商,“与民争利”,“今缙绅缝掖,率贵利贱义而务细小,往往诡托贾竖,贩引占窝,逐污辱之利。而权家外属,辄相鼓扇挟制,坚请固乞,志在必获,驾帆张帜,横行江河,虎视狼贪,亡敢谁何。”[7]359不仅缙绅本身贵利望义,甚至其外属也参与进来,借其固有的权势横行。这也就是明代中期盐业发展中愈演愈烈的“官商”现象。[13]溯其本源则要归根于明代初期施行的开中法,致使盐引在整个盐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吸引着权豪“贩引占窝”摄取盐利。如当时正德朝户科给事中尚衡所指出“近来皇亲附马公侯太监家人,开中引盐,诡名包占,凭借声势,强中强支,商人骤守,资本折阅”。[14]282如此看来,所谓的权豪势要之家除了部分缙绅之外,还有皇亲国戚、王府公侯、太监内臣等人,而盐利的最大受益者及操控者,除去部分商人外,则主要集中于他们之中。
在监察盐业的官吏行使职责的过程中,面对这样繁复错杂的关系,“聪察多纷更,恬静多避嫌”,在权势的威胁下,法令之施行实为有限。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难以避嫌,“今运盐使提举等,非坐阘茸不职,不得除拜,是驱之污秽之地,以求自洁之人,亦难矣。人情莫不有义,亦莫不有欲,顾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洁,尚虑污;道之以污,则亦奚所不至耶?”[7]360处于利益纷争如此之多的“污秽之地”,运盐使提举等人欲求“自洁”同样困难。李梦阳在撰写《明故监察御史涂君墓碑》时即讲到一事例:
初,瑾以盐货源也,因遂厚望巡盐御史货,会一御史入货如瑾望,而瑾辄拟人人必厚货如望。及涂君巡盐还,则空手见瑾。瑾怒,下君狱,然犹日望其货来也。久之,货竟不来,瑾愈怒,矫诏:涂祯打三十棍,发肃州卫,永远充军。君坐掠重,寻卒。[7]387
宦官刘瑾因涂君巡盐而望其厚礼,未得逞便将其下狱,及后又将其充军,最终致死。如此看来,盐业行政官吏亦贿赂成风,如此形势之下,部分廉洁的官员想要“自洁”着实困难。
除此之外,在李梦阳看来,盐业的弊政除了在运营销售层面的问题外,在盐的生产方面,同样存在弊端。而这种弊端之生则又归根于盐产地的“土著之豪”,他们“侵夺芦荡,驱役丁灶,盗食原课,逋负动大万数,转相夤缘,设责督稍严,又牵花户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最终导致“场无见积,庾乏故畜,四方来者,持金顿币,得与官府议轻重、争低昂,岂不大可恨哉”!当地豪强侵占产盐之荡地,欺压盐户,使得盐场无积蓄,最终影响盐的生产。正所谓“处必趋之地,持倒置之柄,于是土著者豪,群聚者盗,势亢者奸,力寡者贼,日增月盛,而盐之法坏矣”。[7]359
由此可知,在明代中叶,由于商人势力的成长,官商的形成,以及官商勾结,盐业中吏治的腐败,加之盐产地豪强的侵害,使得“官盐之不行久矣”。国家失去了对盐利的控制,盐法遭到破坏,而商人、宦官、豪强权势之家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针对这一现象,李梦阳同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
李梦阳提出, “今欲处置盐,莫如复祖宗之法;欲复祖宗之法,莫如伐奸、铲豪、弭盗、息贼;欲去此四者,莫如令之必行”[7]359。在此所谓的祖宗之法,即指太祖时期的开中法,明初为了解决边境军需不足问题,利用食盐的专卖权召商输边,既安定了边疆,又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明太祖为了防止官吏从中谋利,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行制裁,“凡监临官吏诡名,及权势之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侵夺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15]371,并且严格执行。而到了明代中叶,“近年以来,法久弊生,世殊时异,冒滥阻坏,废弛殆尽,开中虽多,实用全无”。[16]751-752如前所论,由于权势之家的参与,以及官商勾结等因素,造成明初盐法遭到破坏。在李梦阳看来,恢复祖宗之法实为理想的状态,而这种恢复,不仅仅局限于盐法的恢复,也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如若恢复,则“伐奸、铲豪、弭盗、息贼”成为必然的举措,而伐奸铲盗最根本的问题又在于法令的施行。李梦阳在其《上孝宗皇帝书》中提出的弊政之“六渐”第四即为“弛法令之渐”,可见其对于法令施行的重视。“令之必行”首先则在于皇帝本身,李梦阳借谭景清一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今辇毂之下,不能制一商竖,何以信四方、控海内邪?故曰法行自近始。陛下甘府藏之虚、内用之竭,顾独忍于一商竖,是忘公家之急而辟私幸之门,弃已成之法而长奸盗之资也”。[7]360谭景清为当时一商人,“比以附搭贵戚,假狐虎之威,持风雨空目,冒买补名号,阻遏国利”,而对于如此大贾之抑制,首先则为天子之职责,不能假公济私,以损天子之威。
对于法律政策的执行,具体到盐政实践中,除了皇权的力量,盐业官吏固然是发挥最直接作用的群体,这也涉及李梦阳提出的另外一点措施,“今河东、淮、浙,岁遣御史巡行,意在纠恶兴滞,而新造之士,于法多不甚解,聪察多纷更,恬静多避嫌,及少谙头绪,已复代更矣,窃未见其可也”。在此,李梦阳提出了盐政实践中官吏委派的弊端,也就是巡盐御史的轮换过于频繁,每一次新上任的官吏,对于盐法多有不解,待其“少谙头绪”,却又到了卸任之时,故造成盐法之不行。况且如前所论,盐业官吏们执法的主要对象都是官宦等权势之家,部分官员为了避嫌自保,何谈政令之施行。针对这一问题,李梦阳认为,“愿选贞茂通明御史,清盐如清军,三易岁乃代,仍简风宪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权,略放汉桑弘羊、唐刘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绠坠剔蠧,浚源决流,一切不得阻挠”。[7]360所谓“清盐如清军”,最主要则在于集“权”的问题。无论是执法不严,还是政令之不行,归根结底在于宦官、权贵之家对于盐业的控制,而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选择“贞茂通明”的御史,将权力付之于一重臣,不要经常轮换,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宴,以及本朝成祖时期的周忱等“业专”且集权的士人,这样才能排除权贵之家的各种阻挠,使得政令法律付之于实践。
另外,李梦阳还十分强调士人的基本德行,一方面表现于他在盐业官吏选择方面对廉吏的强调,“运盐使、提举等,悉选补廉吏。如此,而利不兴、国不足、刍饷供亿之费不给,未之有也”[7]360。另一方面,则在于其对于“官商”的谴责,“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与民争利也。”[7]359正所谓“求仁义”,是为卿大夫之本分,而明代中期“官商”之猖獗,是忘本而与民争利也。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他任职江西提学副使时,大量修建书院,强调业儒之教化,主要用以抵挡明代中叶商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冲击。
通过以上对李梦阳之于盐业的分析可以看出,明代中叶盐法的破坏主要根源于商人势力的成长,官、商勾结以及官商的形成,导致盐利掌控于商人、宦官等权贵的手中,加之吏政腐败、私盐盛行,官府失去了对于整个盐业与盐利的控制。如果想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李梦阳看来,首先,皇权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严格执法,限制商人的发展。其次,通过“业专”“贞茂通明”的御史集权施政,才能对宦官、权贵、豪强之家形成限制,解决盐法之弊。最后,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希望士人能够守“义”之本分,严格执法。
三 士人的挑战与自省
通过以上两部分对李梦阳在江西教育层面的经世实践,以及其基于监税三关的仕宦经历而形成的盐政思想的考察,可以明显看出,李梦阳在经世层面对士人阶层的状态以及社会风教等都十分重视,自此也更多的呈现出其作为“士人”的角色。然而这种思想与实践的形成,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士人阶层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与变迁。
在李梦阳所生活的时代的政治环境中,宦官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占主导的地位,无论是以上分析到的盐业、税收等经济方面(1)具体参见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本书收录了宦官对于当时的土地占有,税收(商税、矿税等),织造、烧造、酿酒等手工业各方面进行控制的资料。,还是军事层面,大多控制于宦官手中。如李梦阳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明确指出“且夫锦衣卫,爪牙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团营,兵之精也,内官参之,内兵又其专掌之”,[7]349可见大部分的军权也主要由宦官控制。明代中叶以降,甚至于皇权的运用“完全操之于黄宗羲所谓的‘宫奴’(宦官)之手”,那么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在此时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余英时在讨论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时,也讲到宋明两朝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在明代,“无论是儒学的价值或士大夫的地位在朝廷上更为低落”。[17]273
然而在明代,对士大夫阶层造成威胁和挑战的,并不仅仅集中于政治实践层面上,同时还来自整个社会风气所带来的影响。如以上在论及李梦阳建造书院的问题上,佛道信仰也是其建立书院的考虑因素之一。从明初开始,太祖“在政治上对僧徒的信任也在儒家士大夫之上”[17]272,后来吴与弼曾讲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18]65可见,僧道势力在明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便是在明代特殊历史环境下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势力的成长,无论是在“重贾轻业儒”的社会风气方面,还是官商勾结,以及官商的出现方面,都对士大夫阶层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面对着众多的威胁,明代士人阶层也做出了一定的反抗,最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宦官的冲击,如李梦阳及当时的户部尚书韩文等人草拟的《代劾宦官状疏》[7]356,就对刘瑾等人进行攻击。然而在明代,这种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对抗十分普遍,如此之例举不胜举。但是当大部分士人的视角都转向宦官时,其中一部分士人对于士大夫阶层本身,也做出了深刻的反省,而李梦阳正是其中之一,并且他通过自己的部分仕宦生涯践行着这种反省。
李梦阳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提出的弊政问题,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元气论”:“夫元气之病者,何也?所谓有其几,无其形,譬患内耗,伏未及发,自谓之安,此乃病在元气。臣窃观当今士气颇似之,故曰元气之病。”[7]348他认为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臣为之核心,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士风”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首先,在他看来,当时整个士人阶层对于尊祖敬宗、家祖礼法等最根本德行的丧失,是逐渐放弃了士人阶层特有的“功能”。其次,受明代以来商业发展以及商人势力成长的影响,整个社会出现了“重贾轻业儒”的风气,士人阶层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官商”的出现以及官商勾结,践踏着士人应有的“仁义”。虽然李梦阳本身出身于商贾之家[7]335,自其文集也能显示出他与商人多有交往,但是将商与士放在一起,李梦阳对于商人仍持有很深的传统偏见,认为重贾轻儒的风气“以祸吾儒”。而在明中叶,“四民不分”已经成为一个鲜见的社会现象,如王阳明“古者四民异业而道同”的“新四民论”[9]106,可见在当时社会中,对商人的偏见已经少见,而且士人转业从商的现象也不难发现。但是就在这样的社会风潮中,李梦阳却不受风气之扰,坚持士人应有的“仁义”。最后,李梦阳认为士风的破坏,还在于在宦官权势之家威胁下,官吏的趋炎附势、避嫌、依附、贿赂等行为,影响政令的施行,也使得士人失去了应有的“忠”与“节”。
因此,李梦阳认为士大夫政治的势微,一定程度上是士人本身对于应有的基本德行的丧失导致的。故其在经世实践及部分经世思想中,力图通过社学和书院的建立加强对于士人基本德行的培养,以抵挡佛道信仰以及商业发展所带来的重利忘义之风对士人阶层的冲击。在盐政经世思想中,他则强调通过明御史以掌控整个盐业的发展,通过士人的集权抑制宦官权贵的专权。
四 结 语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例如“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等基本成为对他的主要界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湮没了其在文学领袖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通过对李梦阳经世思想、实践活动以及仕宦经历层面的考察,可以窥探出生活于明代中叶这样一个时代大变迁之下的士人,面对着众多的挑战,他们内心的惶恐,以及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微薄之力重塑士人阶层。因此,无论是关于社学、书院的修建,还是关于治理盐政问题的主张,甚至包括李梦阳在文学上的复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呈现出其对于士人状态的反省,也践行了其作为士人阶层,为了扭转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教,以重振士大夫政治,最终平治天下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