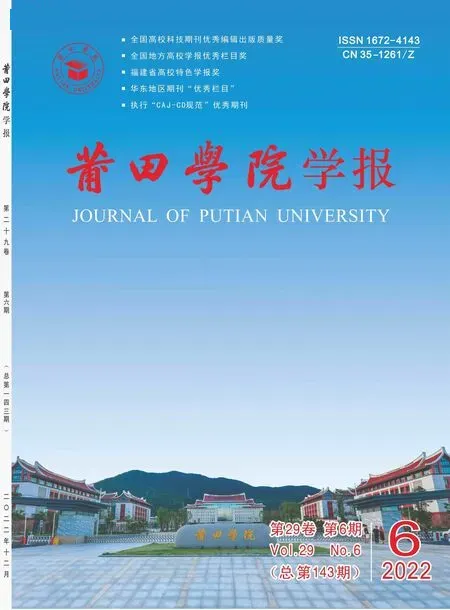同治四年福建南台天后庙御匾颁赐原因辨析
郑永华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
清代帝王给各地妈祖庙宇颁赐的御书匾额,对妈祖信仰的传播和繁荣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2]。 同治四年(1865)清廷给福建天后宫颁发的御书匾额, 对东南沿海妈祖信仰的发展, 同样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此专家学者多有关注, 但由于资料缺失, 有关御匾颁赐的具体原因, 尚只能根据时事进行推测。 最近发现的原始档案, 不仅为这一事件提供确切可靠的答案, 更可借以纠正先前因资料不足产生的误判。
一、 现有档案记载及相关推断
关于同治四年福建天后庙宇获赐朝廷御匾的档案, 学界已寻获 《御赐匾额存档册》 《旨意题头清档》 等档案。 《御赐匾额存档册》 明确记载: “慈航福普——写赐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讨天后庙匾一面。” 《旨意题头清档》 也摘录造办处呈文稿件, 内称: “今为五月初一日由军机处发下福建天后庙匾对一方, 交兵部附本日印封递交闽浙总督一等恪靖伯左祗领, 配做木箱一件, 黑氈马皮包裹, 棉花塞垫, 发报记此, 为此具报等因, 呈明总管, 准行记此。”[3]利用这两件原始档案, 可以确证同治四年经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 清廷曾给福建天后庙宇颁赐一面题字为“慈航福普” 的御匾。 不过学者也注意到, 有关这次御匾颁赐的前期档案, 如左宗棠奏请赐匾的奏折原件以及礼部覆议的题本等等, 均未及发现, “故其事由不详”。 因而关于御匾颁赐的原因及其地点, 也出现了不尽相同的推断。
关于颁赐御匾的具体原因, 由于未见档案记载, 学者只能参考同治四年前后史事进行推测与分析。 蒋维锬先生最先注意到, 同治元年(1862)台湾发生以戴万生为首的民众起事, 清廷命令闽浙总督左宗棠等渡海 “平叛”。 同治三年(1864)初, 清军擒获戴万生, 次年初肃清全台。 可见同治四年左宗棠上奏请求颁赐御匾, 在时间上和他主持台湾 “平叛” 的军事进程相吻合, 可以明确这块御匾是由兵部递送颁发的, 因而左宗棠此次为妈祖庙奏请御匾, “极可能与对台用兵有关”[1]。 稍后, 学者一方面继续强调“左宗棠请匾的时间跟台湾平暴告竣之时正吻合”, 同时补充资料, 认为 《云林县采访册》 将关键的台湾嘉义解围之役中 “北港妈祖大显神威的事迹载入史册”①。 同治二年(1863)三月的《清实录》, 亦有 “即此次嘉义解围, 亦属笨港绅民之力居多” 等记载。 可以再次肯定, 同治四年左宗棠请求给福建妈祖庙宇颁赐御匾, “从历史背景分析, 很可能与镇压台湾戴万生武装暴动有关”[3-5]。
不过也有学者对此分析并不认可, 认为清廷颁赐御匾是出于 “保佑册封琉球使者”。 徐晓望先生较早提出此种看法。 在 《妈祖信仰史研究》附录的 “历代赐封妈祖详情表” 中, 他提出同治四年向福州南台天后宫颁赐 “慈航福普” 御匾, 乃是出于 “保佑册封琉球使者” 的缘故[6]。“历代赐封妈祖详情表” 属附表, 徐先生并未给出详细考证, 也未对已有的 “与对台用兵有关”旧说进行辨驳。 但他提出的 “保佑册封琉球使者” 的看法, 为部分学者征引。 相关论文中,学者或称 “同治四年, 因保佑册封琉球使者,赐福州南台天后宫 ‘慈航福普’ 匾”, 并将之与天津天后宫因护佑出使欧美使节而获赐 “赞顺敷慈” 匾相提并论[7]。 或谓同治四年, “因妈祖保佑册封琉球使者有功, 福州南台天后宫又获得‘慈航福晋’②匾额一面” 云云[8]。
与此同时, 由于档案仅有 “发下福建天后庙匾对一方” 的模糊记载, 关于御匾颁发给哪个庙宇, 也出现了四种不尽相同的说法。 其一笼统称为 “赐福建天后庙”, 即不涉及具体庙宇,仅标明赐予福建省域之内[1]; 其二称赐予 “福建省城庙”, 将范围缩小到福州一城, 但也不确定具体庙名[5,9]; 其三则在对清代天妃封号、 赐匾情况进行归纳的基础上, 认为清代 “有关庇佑使者出访, 多达近十次封号和赐匾, 多以福建南台天后宫为赏赐庙宇, 使节多以出使琉球为多”, 即将同治四年赐匾的对象, 具体明确到福州南台天后庙[6-8]; 其四是认为 “慈航福普” 御匾的颁赐对象, “可能为湄洲、 厦门天后庙”,但仅是推测, 且未给出推测理由[4]。
以上推断, 言人人殊, 没有一致的看法。 至于谈论这个问题的报纸网络科普文章, 更是随处可见, 不胜枚举。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原始资料的缺失。 因而查寻相关档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这不仅有助于推断同治四年御匾颁赐的具体原因, 也可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 原始档案的新发现
笔者近期查阅资料,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名为 “奏请[钦]颁福建省城南台天后宫御书匾额事” 的档案, 正是前人历尽艰辛却始终未获的原始史料。 档案全文行草, 现收藏于 “军机处录副奏折” 案卷内, 其前书 “奏”字, 下注 “左宗棠等, 神灵显应请颁匾由”, 其后又有 “随旨交” “四月二十九日” 等批注。 折内正文, 首称 “闽浙总督臣左宗棠、 福建巡抚臣徐宗幹跪奏”。 由于该档案迄今未见利用, 现将其全文转录如下(其中/表示分行,∥表示抬行,[]表示文字校正):
奏, /左宗棠等, 神灵显应请颁匾由/随/旨交/四月二十九日
闽浙总督臣左宗棠、 福建巡抚臣徐宗幹跪/奏, 为∥神灵显应, 恳请∥钦颁匾额,以酬∥灵贶, 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于同治二年钦奉∥谕旨, 采办米石运赴天津, 五月内购备装兑, 于是月/二十八日放洋开行。 臣徐宗幹先期率领司道, 带/同押运各委员, 敬诣省城南台∥天后宫虔诚祭告。嗣据驻津委员、 候补道耿日椿申/报, 各船先后抵津交兑无误。 押运委员、 候补通/判赵符通、 申其昌回省禀称, 中途遇风, 漂入高/丽国洋面。 该员等呼吁∥天后保护, 望空祈祷,立时反风, 转柁折回, 各米船并/先后归帮收泊, 人船均无损失。 经署福州府丁/嘉玮, 详由藩司张铨庆, 请奏恳∥钦颂[颁]匾额前来。
臣等伏查∥天后, 自宋宣和年间赐 “顺济”庙号, 历元、 明累次加封, 备/载志乘。 ∥国朝∥列圣相承, 叠奉∥加封庙号、 ∥钦赐匾额。臣徐宗幹前在台湾道任内, 详由前任总督/王懿德, 奏奉∥御书 “靖洋锡祉” 四字匾额敬悬庙中, 台洋往返官员/及历年海运米石悉报平安。同治元年台匪滋/事, 调兵运饷两载以来, 风帆顺利。 上年浙江提臣/高连升督带官兵数千, 由海道坐轮船飞驶来/闽, 每船载弁兵千百人, 各带洋枪药袋。 正在中/流簸荡, 一兵偶触火机,衣履皆焚, 风潮当即平/定, 立时扑灭。 又浙省委员由宁波运解火药/五万斤至闽省海口, 验收拨运入城。 甫经交竣, /而该船忽遇暴风起火,回顾犹深悚惕。
凡此化险/为平, 总由∥圣德感孚, ∥神灵效顺。 理合仰恳∥钦颁∥天后宫匾额, 臣等敬谨摹制告谢, 用答∥神庥。 除咨礼部外, 谨合词恭折具奏, 伏乞∥皇太后、 ∥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奉∥旨:钦此!
二月二十五日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所藏的录副奏折, 是清代大臣上奏折片经过御览批示以后, 在颁发返回执行之前由军机处抄录以备查验的档案副件。 因其是奏片的全文抄录, 所以在史料价值方面与奏折原件基本相同。 上述录副奏折抄成于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但其朱批奏折原件, 则成于两月之前的二月二十五日。 档案中抄录有 “四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奉旨” 的提示语, 却未载录谕旨的具体内容。 对照已发现的 《御赐匾额存档册》《旨意题头清档》 等档案, 可知当日代替同治帝批览奏折的两宫皇太后, 很可能是以口头同意的方式, 先交翰林院撰拟御匾文字, 再由造办处等制作, 然后通过兵部驿传系统颁发给福建的。
三、 相关史事的修订与补充
同治四年清廷给福建天后宫颁发的御书匾额, 对于东南沿海妈祖信仰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新发现的原始档案, 不仅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确切可靠的证据, 更可借以纠正此前因资料不足带来的误判, 并对相关史事进行修订与补充。
其一, 该奏折虽然由闽浙总督左宗棠、 福建巡抚徐宗幹两人联衔上奏, 但从正文内容可知,奏折的真正主事者乃是时任福建巡抚的徐宗幹,而非名义上排在第一的闽浙总督左宗棠。 以前有学者因档案中摘有 “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讨天后庙匾” 以及 “递交闽浙总督一等恪靖伯左祗领”等提示语, 而将闽浙总督左宗棠视为此次请讨匾额的主事人员, 其实并不准确。 以此来推测其请匾的原因, 缺乏依据。
其二, 徐宗幹提到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粮船 “放洋开行” 之际, 特地率相关人员 “敬诣省城南台天后宫虔诚祭告”。 因此其奏请 “钦颁匾额” 的对象是位于省城福州的南台天后宫,也就是位于闽县南台冯巷的天后宫。
其三, 虽然徐宗幹在奏折中也提及 “同治元年台匪滋事, 调兵运饷两载以来风帆顺利”,又具体列举浙江提督高连升在海上遇险, “风潮当即平定, 立时扑灭”, 并渲染当时传闻的各种天后显灵事迹。 但他此次为南台天后宫奏请御书匾额的具体原因, 乃是因为同治二年以来福建奉旨采办粮食, 由于天后 “佑护”, 福建粮船通过海运平安运抵天津, 从而为京城急需的粮食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与此期左宗棠率领清军平定台湾 “暴动” 之事并不相关, 与所谓的 “保佑册封琉球使者”, 更无联系。
再查考史事, 同治四年徐宗幹为南台天后宫奏请御匾, 既有具体的现实因素, 还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南台天后宫始建于宋代宣和年间的1122—1123 年, 是福建早期重要的妈祖庙宇之一。 这是因为南台濒临闽江, 自古就是福州重要的水陆码头。 崇祯二年(1629)四月, 浙江巡抚张延登曾奏称: “福建延、 汀、 邵、 建四府出产杉木, 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 南台、 宁波等处发卖, 外载杉木, 内装丝绵, 驾海出洋。”[10]可见早在明朝末年, 福州南台就已成为福建杉木等水运物品的重要集散地。 清代中期以后, 南台逐渐成为福州传统造船业的重地, 林氏 “矮婆厂造船派” 和 “福厂行” 更是远近知名的造船与航海世家。 历经明、 清两代的发展,聚集至南台的商帮日渐增多。 作为与航海密切相关的重要商贸中心, 南台境内的天后信仰随之兴旺。 晚清时期, 南台天后宫更是成为人来人往的商贸会馆场所, 香火更加旺盛[11]。 咸丰七年(1857), 闽浙总督王懿德曾以秋令风汛已过,福州府县官员于漕粮发运时 “虔诣闽县南台冯巷天后宫, 及泗洲铺水部尚书陈文龙庙, 竭诚斋祷, 以期早应京需”, 于米船放洋之后, 陡转南风, 各船顺利抵达天津, “倍形迅捷, 往返极为稳渡, 人船均获平安”, 因而奏请 “钦颁匾额,以酬神贶”。 王懿德称赞天后与水部尚书 “均为海洋正神, 屡著灵显, 凡诸官商航海往返, 无不仰藉神庥”④。 清廷颁发 “风恬佑顺” 御匾后,王懿德等又命令下属在南台天后宫内举行仪式,“敬谨悬挂”[3]。 数年后徐宗幹以天后 “佑助”海运粮船顺利抵达天津为由, 再次为南台天后宫奏请御匾, 固然有趋步闽浙总督王懿德请匾之疑, 但更有 “酬谢” 协助其采办米粮的福建商绅的现实考虑⑤。 这充分显示了南台地区在福州独特的区位优势与信仰传统。 福建督抚大员以奏请御匾等方式介入妈祖信仰, 也进一步促进了妈祖信仰在福州内外的传播与发展, 这也成为观察清代妈祖信仰在官民互动中螺旋式上升的典型个案。
注释:
① 倪赞元纂辑 《云林县采访册》 文称: “同治元年, 戴万生陷彰化, 遂围嘉义, 遣股扑北港。 港民议战议避, 莫衷一是。 相率祷于天后, 卜战吉, 议遂定。乃培土为垒, 引溪为濠。 事方集, 贼大至, 居民迎旌旗出御, 贼不战而退, 时四月也。 自是屡来窥伺,既不得逞, 遂破新街, 焚掠居民。 港人集义勇出,救被难男妇甚多, 兼擒贼二人。 询以前此(不)战之故, 贼称是日见黑旂下兵马云集, 雄壮如神, 故不敢战。 民始悟天后显灵保护, 共诣庙叩谢, 守御益力, 屡与贼战均胜, 前后斩获数百级, 港民受伤阵亡者仅十余人。 然贼势众, 新街未能即复。 七月官军至, 获贼间谍, 与义(勇)分道出击, 大败贼党,狂追十余里, 遂复新街, 并随官军解嘉义围。” 其后更附录 《天后显灵事》, 称 “北港实为海汊, 通金厦、 南澳、 日本、 吕宋等处, 商船萃会[荟], 庙貌尤宏。 神之威灵卓著, 凡水旱、 疾疫, 祷无不应。所尤显者, 惟同治元年显圣退贼事”, 又称七月 “官军至, 义民导之复新街, 解嘉义围。 黑旂所至, 贼尽披靡, 盖神祐也”, “若非仰仗神威, 数万生灵非有官司董率, 三月相拒, 能不有意志所见不同? 乃众志成城, 万夫一心, 摧强寇如拉朽, 则神之功其庸可思议乎?” 载 《中国方志丛书》 台湾地区第32号, 第1 册, 大槺榔东堡, 台北: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83: 106-110.
② “慈航福晋”, 乃 “慈航福普” 之笔误。 因该匾遗失无存, 部分资料与论著将其误录为 “慈航福晋”。 又见蒋维锬. 清代御赐天后宫匾额及其历史背景[J].莆田学院学报, 2005, 12 (4): 81; 以及蒋维锬,朱合浦. 湄洲妈祖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1:501.
③ 录副奏折, 闽浙总督左宗棠、 福建巡抚徐宗幹奏请[钦]颁福建省城南台天后宫御书匾额事,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号: 03-4682-043, 缩微号: 340-0241。
④ 录副奏折, 闽浙总督王懿德、 福建巡抚庆端奏请钦颁天后等庙御书匾额事, 咸丰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九月十六日奉朱批), 档号: 03-4175-142, 缩微号:284-1700。
⑤ 档案所称 “同治二年钦奉谕旨, 采办米石运赴天津”, 乃是由于太平天国兴起之后, 沿运河北上的漕路受阻, 京城粮食供应遽然紧张。 因而筹运粮食,保障京城供应, 遂成为稳定时局的重要举措。 其时主管漕粮的仓场侍郎曾经上奏, 再三强调 “京师为根本重地, 一切饩廪所需, 无不仰资天庾, 必须藏之不匮, 方足以维国计而固人心”, 但 “京仓所入,有减无增”, 上年十二月 “奉旨饬令江苏、 福建各采办二十万石”, 亦多未足额运送, 故请督促主持其事的江苏、 福建两省巡抚, “即将采办事宜实力筹画,一经办有成数, 即饬设法放洋, 务于七月前后次第到津, 俾资接济, 庶京仓储备稍充, 而支放暂可无误。” (见录副奏折, 仓场侍郎麟庆、 宋晋奏请饬各省额运及采办米石迅速运京事, 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档号: 03-4954-007, 缩微号: 368-1209。)对关系京城稳定大局的紧急任务, 接到 “京仓米石急宜设法筹备” 上谕的的福建巡抚徐宗幹, 自然不敢稍有怠慢。 他在招商赴台湾采买粮食受阻的情况下,首先于福建各县购买一万一千四百余石。 (参见录副奏折, 福建巡抚徐宗幹奏为招商购运京仓米石事,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档号: 03-4955-026, 缩微号: 369-0084。) 次年春, “迭奉谕旨” 的福建巡抚徐宗幹又 “遴委妥员, 会同绅士投局招商”, 采买洋米二万石, 并催令押运文武员弁, “依限放洋, 不致迟逾”。 (参见录副奏折, 福建巡抚徐宗幹奏为购定商米运津事, 同治二年四月初三日, 档号: 03-4954-009, 缩微号: 368-1217。)可见徐宗幹对于朝廷交办买粮任务的重视程度。 这无疑也成为他完成任务后即为南台天后宫奏请御匾的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