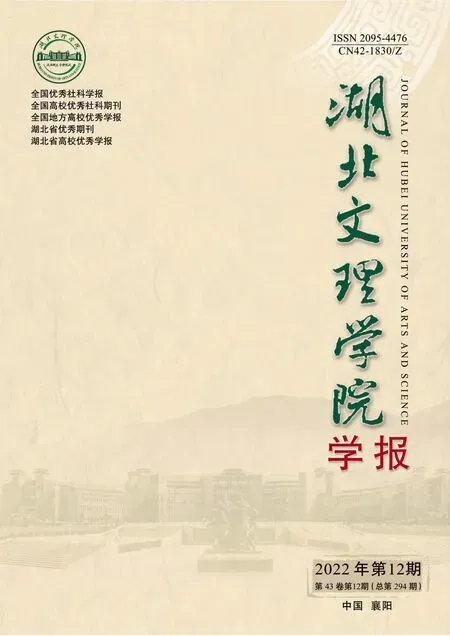《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的文化解读
许中康,许中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写诸葛亮最集中的“大文戏”之一。据陶君起先生的《京剧剧目初探》,京剧、川剧、秦腔、河北梆子等不同剧种均有《舌战群儒》剧目的演出,可见此虽为“文戏”,却有很强的戏剧性与舞台效果,是名副其实的“唇枪舌战”。笔者于此暂不讨论“舌战群儒”的戏剧效果,而把其作为《三国演义》中一个既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在整体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情节单元予以观照,深入探讨“舌战群儒”情节蕴含的深层底蕴,就正于方家。
一、小说虚构“舌战群儒”的用意
若对三国历史稍作考察,我们会发现“舌战群儒”很可能是罗贯中的虚构。“嘉靖本”之前的三国故事中,鲜有与诸葛亮“舌战群儒”相关的故事文本。如欲在历史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的话,那么《三国志·吴主传》中“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1]931,以及《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兵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1]762两处文本与小说中“舌战群儒”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我们在细读相关史传可见,虽然二者在时间和事件发生逻辑上存在某些关联,但史传却对“舌战群儒”只字未提。那么,《三国演义》为何要在历史“可疑的缝隙”中虚构诸葛亮“舌战群儒”呢?虚构这一情节又有何作用?
据笔者所见,叶维四、冒炘两位先生在《三国演义创作论》中对此问题已有关注:“本来‘舌战群儒’在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纯属艺术的虚构。作品为什么要虚构这个情节,为什么在孔明出使东吴后不是写他立即进谏孙权而先插入舌战群儒呢?应当说,这是作者高明之处。‘舌战’不仅写得合乎情理,真实可信,而且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刻画了诸葛亮的博识机敏和政治、外交才能,以致这一虚构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可见小说插入‘舌战群儒’的情节,并非狗尾续貂,而是妙笔生花。从蜀方来说,要求东吴集团与势孤力薄的刘备集团建立抗曹统一战线,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首先要驳倒和说服东吴集团的一批鼠目寸光、软弱胆怯的文官幕僚,才能从思想上分清是非利弊,破除他们的惧曹心理,建立胜利信心,从而进一步坚定吴主抗操决心,建立巩固的联盟。‘舌战群儒’把诸葛亮的政治家形象同一般儒生作了生动而鲜明的对比,充分显示了诸葛亮机智、干练的外交谋略和思辩雄才,也批判了平日只会纸上谈兵、关键时刻却立场动摇、束手无策的腐儒。”[2]220概言之,两位先生认为“舌战群儒”主要有三方面作用,一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刻画了诸葛亮”;二是在小说叙事上,是“建立巩固联盟”的情节需要;三是把诸葛亮与东吴“腐儒”作对比,批判“腐儒”的“只会纸上谈兵、关键时刻却立场动摇、束手无策”。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虽从宏观上对“舌战群儒”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但由于研究者的视野与论述的侧重点不同,对该情节的认识尚不充分。例如对“舌战群儒”到底刻画了一个怎样的诸葛亮形象,以及通过诸葛亮与东吴“腐儒”的对比又强调了何种价值观念等问题尚未深论。刘上生先生从诸葛亮的“才智系统”深度考察,认为“在《演义》中,诸葛亮的观点,兼采儒、道、法、兵、纵横、阴阳诸家”,具有“非正统开放色彩”,是“才、德、性一体的典范”,“以儒用世,以道守身,而又不拘守教条,广泛吸取,兼收并蓄;不以穷经研典为务,而要求具有大则‘匡扶宇宙’,小则‘随机应变’的多方面的实际才能,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这就是诸葛亮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才智特色。”[3]152另外,刘先生在文中也认为“出山后不久,《演义》特地虚构了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面。这一情节的意义,不止在于它是实现孙刘联盟的第一步,一次与东吴投降派的直接交锋,而且在于展示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观念的斗争。作者把东吴投降派完全写成是一批穷研经典的儒生,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笔。”[3]151从上可见,刘先生从诸葛亮的“才智系统”与舌战双方的“知识分子观念斗争”层面对“舌战群儒”进行宏观把握,而这也直接启发了笔者探讨“舌战群儒”深层文化意蕴的思路。
虽然学界对“舌战群儒”已有较多探讨,但梳理相关研究后可见,在小说叙事与文化意蕴两个角度尚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首先,在小说叙事上,“舌战群儒”作为孙刘联盟的过接已是学界共识。但从更宏观的小说结构来说,笔者认为“舌战群儒”故事的叙事功能亦非常突出:一是与“三顾茅庐”呼应;二是与后续诸葛亮故事形成照应。在小说第三十七、三十八回的“三顾茅庐”故事中,诸葛亮一直处于“虚写”的位置,“隆中对”虽然对其“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见识”已有刻画并用“博望烧屯”与“火烧新野”二事来直接验证其才智。但如此种种显然不能与“三顾茅庐”中刘备(包括读者)对诸葛亮的期待相对等。所以,小说如何对“三顾茅庐”中极力渲染“虚写”的诸葛亮之能力予以坐实,似是小说叙事上难以避开的挑战。由此,小说编创者借着历史上刘备军事失利、诸葛亮游说孙权以及东吴士人“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等散乱史实中的一点影子,巧妙地虚构了“舌战群儒”故事。这一情节既在历史事实的笼罩下符合事件的发展逻辑,同时也通过诸葛亮与东吴士人关于理想士人的“舌战”,借诸葛亮之口道出士人群体的“君子儒”理想人格,以诸葛亮口中的“诸葛亮”来验证“三顾茅庐”里众人口中的诸葛亮。当然,这也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论语·为政》中“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为之’”的儒家话语。
笔者认为,小说的这种“验证”叙事并不止此。在“毛本”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大谈“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4]546-547,与“毛本”中诸葛亮所谈的“君子儒”更加重视“道德”方面不同,在较早的“嘉靖本”中“道德”与“才智”很大程度上是平分秋色的:“夫君子之儒,心存仁义,德处温良;孝于父母,尊于君王;上可仰瞻于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治天下如盘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内。”[5]1406于此我们暂不讨论“毛本”对早期版本中“君子儒”内涵进行改动的具体原因,如果我们对小说结构有所了解,则会发现此处诸葛亮口中的“君子儒”的所有特征在其后的小说叙事中几乎都得到一一呼应。道德层面,“忠君爱国,守正恶邪”落实为“白帝托孤”“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在小说中落实为蜀国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人心欢悦,朝野清平”,诸葛亮死后“大名垂宇宙”。才智层面,“上可仰瞻天文,下可俯察地理”在其后的行军布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小说第四十六回诸葛亮“草船借箭”后对鲁肃所说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此处诸葛亮显然是以“将才”自比,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对“舌战群儒”中自比“君子儒”在叙事上的呼应与验证。从这个角度来讲,“舌战群儒”的虚构正是罗贯中试图通过诸葛亮与东吴士人的“舌战”来揭示“君子儒”的内涵,以此落实“三顾茅庐”中虚写的大贤诸葛亮形象,而且通过“君子儒”内涵的前置,逐步展开诸葛亮的“君子儒”素养与精神品格,犹如一幅长卷,诸葛亮的“君子儒”形象随着故事的推进徐徐确立起来。
其次,“舌战群儒”作为“大文戏”,特别是拈出表现士人理想的“君子儒”概念,本身即带有小说编创者自我指涉的意味。小说通过“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的士人楷模诸葛亮之口道出自我期许,来表现对“君子儒”的追慕。正如前人反复论及的“孔明乃《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也。读《三国志》者,必贪看孔明之事”[4]447,“罗氏的《通俗演义》则最活跃的只有一位诸葛孔明而已”,诸葛亮是“《三国志演义》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整部小说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诸葛亮传记”,而这部大传记何尝不是对“君子儒”理想人格的生动演绎呢?
二、“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
“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不仅是“舌战群儒”故事的核心,而且也是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君子儒”与“小人儒”作为对立概念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的“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后世学者对此处“君子儒”与“小人儒”的所指见仁见智,其中以朱熹《四书集注》征引程子与谢氏观点中的“程子曰:‘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与“谢氏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闲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此。’”[6]84影响最大。近代学者对此观点亦有所修正,程树德《论语集释》认为“苟专务章句训诂之学,则褊浅卑狭,成就者小。夫子教之为君子儒,盖勉其进于广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规模之大小言”[7]390,以“度量规模”判别“君子”“小人”;钱穆《论语新解》认为“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8]169,又以“世道”“义理”作为“君子儒”之必备素养;高培华则认为“君子标准加上儒之职业性,就是所谓‘君子儒’”,是具体为以伊尹、周公、姜子牙为楷模的“既为王者臣、又为王者师,‘以道事君’的‘大臣’”[9]等。
笔者认为,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小人儒”在一定程度上与“竖儒”“腐儒”接近。《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骂郦食其为“竖儒”;《史记·黥布列传》中刘邦平定天下“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于此,“竖儒”“腐儒”主要是对“死守章句”而不能“为天下”士人的批评。如元代白珽《湛渊静语》卷二认为“所贵乎儒者之学,以其足以用天下国家也,儒而不适用于世用,特腐儒耳”[10]33;王阳明在奏折中也称“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强调“腐儒”的“才识昧劣”[11]248。除了上述对“小人儒”“才识昧劣”而“不适用于世用”的定性,元代大儒郝经如此评价谯周:“举全蜀奉图籍面缚军门,反社稷以为长策,小人之儒也!昭烈百折仅有此土,孔明不济,继之以死,乃为腐儒所卖,并入仇敌,惜哉!”[12]215把谯周斥为“小人之儒”与“腐儒”,可见“小人儒”又与“卖国”相联系,而具有了道德低劣的意味。
与“腐儒”“竖儒”对立的是“真儒”“鸿儒”“通儒”等。王充《论衡·超奇篇》把“儒”分为儒生、通人、文人与鸿儒四个层次,不过王充眼中最高层次的“鸿儒”尚多侧重“文”的一面。《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载司马徽之言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1]761,超越“儒生俗士”的“俊杰”,就是指不死守章句而“识时务”,且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在作为君主的唐太宗眼中,“君子儒”还应具备更高的素养:“何谓君子儒?真儒是已。《左传》曰用真儒,则无敌于天下,岂唯兴礼乐哉!”[13]88-89在李世民看来,作为“真儒”的“君子儒”具备的能力不应只是“兴礼乐”,而应足以“得此一人,可安天下”。就此来看,《三国志》对“君子儒”应“识时务”的素养要求,在《帝范》中被提升至“无敌于天下”的才能期待。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誉为“得此一人,可安天下”与李世民在《帝范》中“用真儒,则无敌于天下”的对读来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重述与想象,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对“君子儒”一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期待,而是按照《帝范》中对“君子儒”的更高期许来塑造的。
“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是评价士人素养高低的一个传统,体现了两个不同层次士人的人格精神与素养。“君子小人人格理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14]590,是“一种极富特色的政治人格理论”。因此,在讨论“君子儒”与“小人儒”素养层次时,除了注意二者才智素养的区别,还应关注其在政治人格层次上的区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一定范围内,在传统中国,君子形象逐渐衍化成一种道德化的政治人格,得到了普遍的尊崇;小人则作为反道德的政治人格,受到贬斥。”[14]589在儒家文化中,小人人格主要集中于“利”与“私”,而且“喻于利”正是“私”的主要表现。“私”,除了“私己”外,还表现为“与人同逆而旋背之”“有所缘饰而无忌惮”的“反道德”。可为之做一注脚的是,《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得胜头回”中卓文君说:“秀才们也有两般,有那君子儒,不论贫富,志行不移;有那小人儒,贫时又一般,富时就忘了。”[15]44即从“志行”角度着眼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
从上来看,“君子儒”作为士人的理想人格,不断被推向才智与道德至高点;而“小人儒”则逐步固化为死守章句、不识时务,甚至有道德瑕疵的白面书生。这种政治伦理视野中的“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在“舌战群儒”中得到充分演绎。小说通过作为“君子儒”的诸葛亮,以俯视口吻道出二者的本质区别: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4]546-547
小说借诸葛亮之口把东吴士人贬低为“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座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张昭);“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虞翻);“畏惧请降”(步骘);“无父无君之人”(薛综);“小儿之见”(陆绩);“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严畯),或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物”(程德枢)的“小人儒”群像。而诸葛亮却作为“小人儒”的对立面,呈现为“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的“君子儒”的伟岸形象。
三、诸葛亮的“君子儒”素养
《三国演义》不只在“舌战群儒”中叙述了“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在其他回目中亦有类似表述。例如,小说第三十五回中司马徽评价孙乾、糜竺之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称赞“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时,即有意把两种类型的士人作一比较。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作为“君子儒”化身,其言行生动表现了古代士人对“君子儒”在才智与道德方面的想象。以下,笔者将试图通过详细分析小说中诸葛亮的言行,深化学界对古代士人“君子儒”素养的认识。
“君子”作为“君子儒”的概念核心是“一个极富弥散性的整体理想人格”[16]24,在《三国演义》中“君子”(11次)以及与之相近的“大丈夫”(29次)、“仁者”(3次)、“仁人”(6次)频繁出现。那么,在中下层文人编创的《三国演义》中,君子理想凝结在士人形象身上又有哪些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小说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诉求又是什么?
在小说中,诸葛亮的“君子儒”素养在“舌战群儒”中通过批判东吴士人为“小人儒”及以“君子儒”自我定位得到一反一正的表述。
首先,在智谋上,诸葛亮自诩“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并认为“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而非“峨冠博带”的“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白面书生。
其次,在道德上,敢于以“数千仁义之师”对抗“百万残暴之众”,即使失败也会“退守夏口,所以待时”,绝不“屈膝降贼”。另外,“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坚决践行“臣之道”。
再次,在胆识上,当步骘把诸葛亮比作苏秦、张仪一类说客时,诸葛亮却认为苏、张为“豪杰”,因为苏、张“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又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精神接近。
最后,在学识上,诸葛亮认为“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并以“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为标杆,否定了“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的“腐儒”行径。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学识上追求的是“匡扶宇宙之才”而非“寻章摘句”。诸葛亮于此言及的对学识境界的追求让我们联想到第三十七回中司马徽所云的,“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使、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4]462-463在此,“独观其大略”说明诸葛亮学问博杂,而且这种知识素养在第四十六回也有诸葛亮的自我剖白:“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如果说“毛本”中的“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在“君子儒”的士人素养与理想人格的表达上尚显朦胧,那么不妨把“嘉靖本”对“君子儒”的相关表述迻录于此作为观照:“夫君子之儒,心存仁义,德处温良;孝于父母,尊于君王;上可仰瞻于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内。”[5]1406在此,“君子儒”在才智、道德等方面的素养就显豁得多了。
在小说中,诸葛亮的“君子儒”素养充分体现在“三顾茅庐”前后的小说叙述中。蜀汉的草创时期,刘备身边围绕的是孙乾、糜竺等“白面书生”,在这一群“非经纶济世之才”的“小人儒”辅佐下,刘备军事集团四处受挫,辗转寄人篱下。但自从得到“君子儒”诸葛亮的辅佐,刘备军事集团屡次以少胜多击败曹操,联吴抗曹赢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趁机夺取荆州作为根基,实现魏、蜀、吴三分鼎足之势。可以说,小说中诸葛亮辅佐“孤穷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三分天下,正是李世民《帝范》中“用真儒,则无敌于天下”的生动演绎。
作为《三国演义》“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诸葛亮的士人身份很容易与小说编创者的士人身份产生精神共鸣。小说之所以在历史人物的基础上,融入伊尹、姜子牙、张良等人的诸多事迹,并同时依据儒家语录虚构小说情节来塑造“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的诸葛亮形象,无疑表明了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被作为“范型”来塑造的。诸葛亮在小说中是以古代士人的最高理想为标杆创造的产物,罗贯中几乎把所有可以吸纳进士人理想人格的特点都熔铸在诸葛亮形象身上,使之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素养与理想人格的集大成者。
正如上文所言,“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是古代知识分子关于士人素养与人格精神评价的一个区分传统,这一分辨之所以引起历代知识分子的兴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实生活中“君子儒”鲜有而“小人儒”繁多。特别是在鼎革之际,寻求力挽狂澜的“君子儒”呼声明显高涨。在书写乱世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下层文人对乱世中“君子儒”诉求的产物。可现实正如传说中虽“有志图王”却不得已“传神稗史”的罗贯中一样,这种“君子儒”素养从古代士人群体自身来说本就难以企及,更何况在波诡云谲的乱世,就算某些士人具有了“君子儒”素养,要想实现抱负也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对于郁郁无聊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其阶层本身所具有的宿命中的一种常态。现实中成为“君子儒”或者实现“君子儒”的抱负不可得,中下层知识分子转而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其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他如一盏暗夜中的明灯,照耀着古代士人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寻,以及希冀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帝王师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