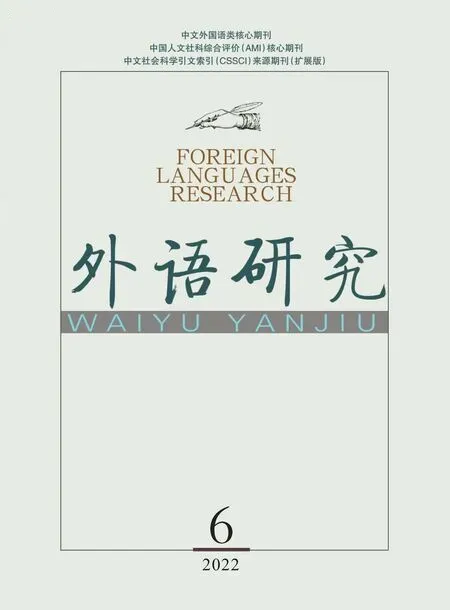语言哲学的语言植物研究法和概念工程及其关联性*
杜世洪 田 玮
(西南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0.引言
格莱斯(Grice)在《言辞之道研究》的“回顾性结语”中说,我应该谈谈我哲学生涯中期之初所取得的,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集体成就,那就是所谓的语言植物研究法(linguistic botanizing)。在当时的牛津大学,这种方法通常被当作概念分析的基础,而在特殊情况下它被当作哲学分析的基础(Grice 1989:376;格莱斯2021:362-363)。无论怎样,作为分析的基础,这种方法旨在对概念进行穷尽性和系统性分析。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概念分析(也叫概念考察)、哲学分析和语言分析这三个术语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具有重叠性,而且拥有共同的旨趣,都追求语言与思想的“澄明性”(clarity)(Soames 2003:xiii;Brandom 2008:213;杜世洪,李飞2013)。不过,语言哲学界多以概念分析来指代实际的哲学活动。一言以蔽之,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是概念分析的一种具体方法。
概念分析或概念考察主要是以语言分析为中心任务的哲学分析,而语言分析是哲学思辨的基本出发点,语言分析是进入哲学思辨的主要通道(Dummett 1978:441-442)。为此,格莱斯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不顾一切,坚定不移地把哲学问题和日常语言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牛津辩证法”(Oxonian Dialectic),堪与“雅典辩证法”(Athenian Dialectic)媲美(Grice 1989:379-380;格莱斯2021:360)。在格莱斯看来,牛津大学的日常语言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微不足道,而且并不会过时。
格莱斯所说的语言植物研究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既然是牛津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那么牛津辩证法与雅典辩证法到底有何异同?语言哲学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个新动态,掀起了“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研究(Cappelen 2018;Burgess & Plunkett 2020;Chalmers 2020;Sawyer 2020;Jorem 2021;Nado 2021;黄远帆2021),那么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与概念工程有何关联性呢?
1.语言植物研究法的基本要义
语言植物研究法这一概念由格莱斯提出,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却鲜有论及。在方法论上,语言哲学研究虽有统一的目标和任务,即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但是似乎还没有“固定”和“统一”的学说与方法(Soames 2003:xiii)。面对这种情况,格莱斯试图用语言植物研究法来概括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常见做法,目的是为语言哲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总结。
为什么定名为语言植物研究法呢?格莱斯举例说,奥斯汀(Austin)要求瓦诺克(Warnock)说出“正确地打高尔夫球”(playing golf correctly)和“恰当地打高尔夫球”(playing golf properly)之间的区别(Grice 1989:376)。要说出这两例语言表达的区别,有一种习惯做法就是对二者做出细枝末节式的处理,即认为二者表达了一致的主题——打高尔夫球,而它们的区别只存在于细节上或者说方式上。
然而,在格莱斯看来,哲学的语言分析并不能终止于此,语言分析不仅仅是针对相似语句进行“微调”的一种工具(ibid.),即并不能满足于就一堆表达与想法进行概念微调,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某个语言表达式所关涉的某个概念区域,进行概念范围勘定以及概念系统化处理。这种工作就像面对两种相似的植物,要区分它们,就不能满足于说出这两种植物的细微差别,而是要弄清它们到底属于哪一种、哪一属和哪一科。植物研究法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具体植物进行“科属种”的分类鉴别,以及对它们的分布范围进行勘定。如此看来,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正是基于植物分类学理念的概念考察。
格莱斯借鉴植物分类学的理念,把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定名为语言植物研究法,这显然具有类比与隐喻性思维特征。在类比和隐喻思维下,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好比千状万态的植物,因而具体的语言表达可被确定为某类,最终可确定为属于某个系统。对具体的语言表达式进行分析,就如同进行植物分类一样,要对具体的语言表达式进行特征甄别与分类。分类的聚焦点就是要观察各种表达式的区别性特征,这些特征往往是细微的,而且这些细微特征却是思维性质的反映。考察语言表达式的细微特征,就是要考察思维性质的可变情况。
既然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犹如植物分类,那么就有必要把握植物分类的发展规律。植物分类经历了三次飞跃:人为分类、自然分类和系统分类(Whittaker 1980:1-3;姜在民,贺学礼2016:229-231)。人为分类主观性很强,分类的依据主要以经验知识为主,根本不考虑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为分类的结果就会不同。随着人们对植物研究的深入,人们注意到了或者认识到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发现了植物之间的各种系统,于是就形成了以植物客观性状为主的自然分类和旨在建立植物体系的系统分类。以此为鉴,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都要聚焦语言表达式的客观特征而进行甄别与分类。
从格莱斯的角度看,语言哲学研究的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在学理上走的正是植物研究法的道路,即按照“明类、知故、晓理”这一基本准则(杜世洪2014),对一个或者一组相似语言表达式的研究,就要先鉴定其类别,再分析其形成原因,勘定其系统归属,最后揭示其相关原理。根据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奥斯汀的例子可作如下分析:
[1]a.playing golf correctly
b.playing golf properly
从句法层面看,[1]中的两个表达式同属一类,即“动词+宾语+状语”,似乎并无实质性差别。二者若有差别,也只是聚焦在状语的词义上,即似乎只有“correctly”和“properly”的词义差别而已。就[1]而言,语言学研究可能会停留在句法描写的技能层面而已。
然而,在语言哲学的视域下,[1]中的两个表达式却彰显着实质性的思维差别。表达式[1a]涉及语言活动或者语言游戏的规则问题,即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打高尔夫球才算“correctly”呢?这规则从何而来呢?如果说规则是一种约定,那么约定的规则就可以更改,甚至会遭到破坏。于是,“playing golf correctly”彰显的道理是,在不违背约定的规则下,就需要“correctly”打高尔夫球。道理就这么简单吗?其实道理并非如此简单。语词“correctly”的意义是由什么给定的呢?它本身有意义吗?语义最小论者会认为,由规则决定的意义(如“correctly”的意义是根据具体活动的规则来确定),其语境依赖性不强,只要符合某种活动规则要求,都可谓“correctly”进行活动。
表达式[1b]彰显的道理却对按约定的规则而“correctly”打高尔夫球形成挑战:如果要“properly”打高尔夫球,那就要按照某种规则进行,这里的问题是,就算“properly”和“correctly”二者享有意义重叠区域,却仍不能肯定断言“playing golf properly”所遵守的规则如同“playing golf correctly”所遵守的规则一样。为什么呢?表达式[1a]指引的是约定性规则,活动性质具有后天性质,所涉及的知识属于人类行为的创新知识;而[1b]一方面要遵守[1a]那样的约定性规则,另一方面还要遵守某种伦理规则或道德规则。然而,伦理道德规则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康德对此颇有感慨。就道德规则而言,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结论章说,他一直痴迷而敬畏的两样东西,一是头顶上面浩瀚的星空,二是内心里面神秘的道德法则(Kant 2015:129)。此外,[1b]中“properly”的意义具有语境敏感性,即“properly”的意义取决于谁和谁在打高尔夫球,而谁才会知情识趣地“properly”打高尔夫球。人不同,“properly”的意义就不同。
对于日常语言表达式,语言哲学家所看到的东西显然不同于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看到的。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倾向于把语言表达式的形态特征或者句法特征当成所谓的语言本体特征,他们所说的语言本体研究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研究,而他们所说的语言的本质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本质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语言哲学集大成者维特根斯坦认为本质是说不清的东西,不过他却断言(2020:166):“本质在语法中表达出来。”日常语言在生活形式中的用法所暗含的活动规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属于哲学语法。
在格莱斯看来,奥斯汀让瓦诺克区分“playing golf correctly”和“playing golf properly”,其目的就是要对二者做出不同的分类,以揭示二者背后的哲学语法规则及其原理:它们在句法上属于同类,而在思维内容上却具有不同的实质。透过语言表达式的表层,去理解其深层思想实质,这就是语言植物研究法的要义所在。
语言植物研究法的要义还体现在概念关系的变化方面。格莱斯认为(Grice 1989:376),奥斯汀对“真的”一组表达式的条分缕析,可作为植物研究法的典型样例。试看例[2]:
[2]“true friends”“true statements”“true beliefs”“true bills”“true measuring instruments”“true singing voice”,etc.
从例[2]来看,语言植物研究法的重要目标就是勘定某个概念的范围,鉴定这个概念的系统以及它在系统中的关系,即要弄清各种从属概念是如何进入某个大概念而形成一个系统。
例[2]展示的是,语言学家或者词汇学家对“真的”一词的认识,不会刻意追问“真的”变化情况。于是,“真的朋友”“真的陈述”“真的信仰”“真的账单”“真的测量仪器”“真的唱声”这些表达涉及“真的”一词,它的用法看似一样。语言学家可能不会感到这几个“真的”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在格莱斯看来,语言哲学家却要突破这种认识,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语言植物研究法。
面对这一组“真的”表达式,利用语言植物研究法,就会发现问题:这些“真的”并不是同样的“真的”,可是它们又是怎样进入“真的”这一大概念的呢?“真的”一词表达的不只是语义内容,它还牵涉着关于“真”的理论,涉及真值条件。即界定“朋友”“陈述”“信仰”“账单”“仪器”“唱声”等的真值条件不同,不可用单一的条件来确定“真的”的不同用法。比如,“真的朋友”和“真的汉子”二者的用法或者说哲学语法相差甚大。对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当然算得上“真的朋友”;对社会有责任担当,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行动的人,算得上“真的汉子”。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可是它们各自为真的条件却复杂微妙。在格莱斯看来,语言植物研究法的宗旨就是要对它们进行甄别与分类。格莱斯认为,在语言植物研究法视野下,单个语词都会涉及多个词汇条目的内容。因此,从单个语词出发,去揭示它所涉及的各种语义特征以及各种语义特征所归属的系统,这是语言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正是牛津辩证法关注的焦点。
2.牛津辩证法与雅典辩证法的异同
格莱斯用“语言植物研究法”来概括他的个人成就,同时他认为这也是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集体成就”(ibid.)。在格莱斯看来,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坚定不移地把哲学问题和日常语言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牛津辩证法”,可与“雅典辩证法”相提并论(ibid.:379-380)。格莱斯的这种认识,旨在强调现代语言哲学具有重要地位。
格莱斯认为,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成就,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完全可以同古希腊哲学成就一样彪炳日月,因为日常语言学派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可算是法古出新,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为此,格莱斯用“牛津辩证法”来概括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成就,把看似细枝末叶的现代语言哲学研究提升到古希腊哲学思辨的辉煌层面,认为牛津辩证法是对雅典辩证法的传承与发展。
格莱斯说,20世纪中叶的牛津和两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腊,二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可用“此牛津”(the Oxford)和“彼牛津”(other Oxford)来做类比(ibid.:378)。在格莱斯看来,“此牛津”指代的是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如奥斯汀、赖尔、瓦诺克等(当然要包括剑桥大学的维特根斯坦、罗素和摩尔等人,因为这里的“牛津”不是位置地域或工作单位概念,而是哲学思想性质概念),而“彼牛津”主要用来指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格莱斯做出如此类比,目的是要说明现代语言哲学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追问精神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旨趣),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哲学地位。
语言哲学容易遭人诟病,“外行”嫌它不科学、不系统,嫌它沉迷于细枝末节的语言表达式的研究(ibid.)。格莱斯认为,这是外行对语言哲学的严重误解。其实,看似细枝末节的语言哲学研究是系统思想的基础。对语言表达式不做细枝末节的分析,其道理正如“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一样。对语言表达式的细微特征不做仔细考察,就好比不对具体的植物物种进行细致的考察一样。外行思考问题喜欢天马行空,大概念来大概念去,他们的思维无法达到精细的程度;他们看得到森林,也看得到树木,就是看不到具体树种的细微特征。外行认识事物习惯于囫囵吞枣,比如他们谈论植物时,也只能把植物说成是植物,却对各种植物的细微特征不做任何深究。同样,不做语言哲学研究的人,很难认识到某些具体的语言表达式背后所隐藏的这样或那样的道理。要知道,人类思维中那些内隐的推理、表征和“话语守诺”(discursive commitment)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表达式外显出来。“彼牛津”的苏格拉底注意到了这些内容,而且擅长于就具体概念(如“正义”)进行追问,反映的是雅典辩证法的精神。同样,“此牛津”的奥斯汀等人也注意到了这些内容,他们虑周藻密,善于就具体语词进行绣花式的精巧琢磨。例如奥斯汀对“假装”的研究,充分展示了牛津辩证法的追问精神。
牛津辩证法和雅典辩证法二者在以下方面异曲同工:(1)二者都倾向于认为,日常语言和哲学思维联系紧密,要从事哲学思辨,就要从日常语言入手。(2)二者都对事实知识和道理知识进行区分,认为事实背后有道理,而道理可以用来解释事实。(3)二者都认为知识本身既包括需要解释的事实,又包括需要解释的道理,认为我们对许多事实既可能熟悉,也可能不熟悉;至于到底是熟悉还是不熟悉,这就需要恰当的解释和道理。(4)要探问解释和道理是否可用,这就要考察它们是否派生于第一原理;然而第一原理却不是现成的,需要探问者进行设计,而如何设计,这本身就需要解释。(5)概念考察不可能一蹴而就,概念考察总是分阶段进行,在任何给定的阶段,考察者都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进行新阶段的研究;概念考察还可能要直接追溯到很久以前一些外行的观点上去,因此这种阶段性、进步性的审查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往往萌生于众人,成熟于智者。(6)辩证法的实用方法之一是系统构建,而系统构建又涉及越来越高的抽象层次,直到第一原理;什么是第一原理呢?大致可以说,第一原理作为解释用的理论,在解释任何给定的数据时,是最小的、概念上最经济的(即牵涉最少概念的)原理。
格莱斯说,上述几点既是对雅典辩证法的总结,又是牛津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与雅典辩证法不同的是,牛津辩证法尤为重视对日常语言的考察。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哲学研究之所以对日常语言特别感兴趣,道理在于日常语言完全可能是某种(尽管不是每种)知识的最终来源。这正是“知识在语言中沉积,意义在语言里彰显,语言构筑起知识之路”(杜世洪2006:26)。现代语言哲学聚焦语言表达式,以意义为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要揭示语言、意义和知识三者共同维系的道理。
奥斯汀和赖尔等人的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并不是始于语言而又止于语言的研究。对此,格莱斯说,奥斯汀和赖尔等人就算不能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并驾齐驱,但至少可以说他二人完全称得上是古希腊哲学的忠实门徒,在概念考察方面,他们技艺高超,热情十足(Grice 1989:379-380)。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的研究手法极具雅典辩证法的特点。格莱斯说,在雅典辩证法中,亚里士多德似乎讨论过以下例子(ibid.:380):
[3]a.“running quickly”or“running slowly”
b.“being pleased quickly”or“being pleased slowly”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例[3a]中所述的“跑得快”或“跑得慢”这样的表达很正常,属于合法表达,而[3b]所述的“乐得快”或“乐得慢”却不正常,属于不合法表达。这里的合法与不合法,不是句法的法,因为在纯粹的句法层面上它们都可接受。于是可以说,语言表达涉及的不只是句法问题,还涉及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出具有“哲学性质的结论”(ibid.):跑步是一种过程,它不同于活动,而快乐则既不是过程,也不是活动,快乐不能用快慢来衡量。
亚里士多德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语言表达式的背后关涉某种哲学道理,在这一点上,这个例子似乎具有明显的说服力。然而,汉语里的相似表达“高兴得太早了”“高兴得太晚了”等却可以接受,甚至“快乐”本身在构词上含有一个“快”字。显然,来自汉语的这种差异,是亚里士多德始料未及而又本应注意的地方。
无论怎样,雅典辩证法和牛津辩证法都是对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的高度概括。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是语言哲学没有统一的学说和固定的方法。然而,在格莱斯看来,这种观点值得怀疑。就算没有统一的学说和固定的方法,牛津辩证法以及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也堪称语言哲学的典型方法或者经典方法。
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种思想派别(维特根斯坦2019:2):理论建设派和理论摧毁派。前者是大多数哲学家尤其是认识论哲学家所推崇的,典型代表如康德、黑格尔等;后者是现代哲学思潮中某些哲学家所注重的,典型代表如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在理论建设派看来,哲学是学说或理论,而在理论摧毁派看来,哲学不是理论,只是活动(同上:17,46)。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也好,摧毁也罢,现代语言哲学注重基于语言事实的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这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家要么属于“概念分析师”,要么继承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遗产而成为“哲学治疗师”。
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多为概念分析师,而格莱斯则属于理论建设派的概念分析师。语言学界特别是语用学界对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和合作原则并不陌生,然而对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却未加注意。从哲学思想上看,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仍然属于他所说的“牛津辩证法”的一种典型方法,标志着现代语言哲学的集体成就。
西方语言哲学发展到21世纪出现了新的动态,一批少壮派哲学家掀起了语言哲学的“概念工程”研究,代表人物是查尔莫斯(David J.Chalmers)、卡佩兰(Herman Cappelen)、柯契(Steffen Koch)、里格斯(Jared Riggs)等。如果说奥斯汀、格莱斯等人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概念分析师”而维特根斯坦是“哲学治疗师”的话,那么,卡佩兰等人则算得上语言哲学的“概念工程师”。
从“概念分析”“哲学治疗”到“概念工程”,西方语言哲学在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从思想性质看,概念工程研究与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以及牛津辩证法存在着关联性。
3.概念工程与语言植物研究法的关联性
从方法论看,牛津辩证法和语言植物研究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哲学思想渊源方面,它们继承的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那么,概念工程研究是否继承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呢?围绕这个问题,我们以格莱斯的语言植物研究法为牛津辩证法的典型方法,以此为参照来对概念工程研究加以关联性阐释。在解释关联性以前,我们先对何为概念工程研究进行梳理。
概念工程这一术语出现于20世纪末,散见于西方语言哲学文献里。直到21世纪初,这一术语逐步获得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关注。2018年赫尔曼·卡佩兰在其专著《修理语言:论概念工程》中明确指出,概念工程是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工程,是对我们的概念使用进行检修的工程(Cappelen 2018:3-4)。2020年赫尔曼·卡佩兰、亚历克西斯·伯吉斯(Alexis Burgess)和戴维·普朗克特(David Plunkett)合作编辑出版了《概念工程和概念伦理》一书,旨在讨论如何评估与改进我们的表征工具(如概念和语词),讨论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使用“应该使用的概念”,以及如何改进我们应该使用的概念(Burgess et al.2020;Burgess & Plunkett 2020:281;杜世洪2021:2)。概念工程研究的这些基本问题指向的仍然是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的基本内容,它的新意在于概念工程研究把概念考察和语言分析推进到系统建设层面上来。
如果说语言哲学的概念分析具有离散性质,那么概念工程研究却是要突出语言哲学研究的连续性。为此,查尔莫斯(Chalmers 2020)在《什么是概念工程以及它应该是什么?》一文中说,概念工程的实际内容包括概念设计、概念实施和概念评估;概念工程实际包括而且应该包括“修补旧概念”“设计新概念”以及“概念工程重建”(conceptual re-engineering);概念工程可分为“异名”(heteronymous)和“同名”(homonymous)概念工程。连续性的语言哲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目的,那就是“修理坏的语言表达”(Cappelen 2018),摧毁思想中、理论上一座座漂亮的纸房子(维特根斯坦2020:21)。
为什么要修补旧概念?为什么要设计新概念?为什么要进行概念工程重建?这三个问题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日常语言的使用所涉及的概念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语言哲学的研究工作就是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连续性和系统性研究,而不能满足于离散性考察。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概念分析和哲学治疗,现在出现了新的研究,这就是概念工程研究。
概念工程分为同名概念工程和异名概念工程(Chalmers 2020)。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因为在现代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同样的哲学论题会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呈现出不同的解释,人言人殊。例如,就指称问题而言,穆勒(又译密尔)的直接指称论、弗雷格的“指称与意义”二分论、罗素的描述语理论(亦作摹状词理论)以及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称论等,它们有共同的指向,可是它们却存在着明显差异。穆勒认为专名具有外延的指称对象而无内涵的表达意义;如果要确定真正的专名的意义,那也只能从它的直接指称对象去确定。弗雷格却认为专名无论有没有直接指称对象,只要有呈现方式,它就会有意义;于是,没有指称对象的空名,只要有呈现方式,它就有意义。罗素另辟蹊径,从知识论角度出发,区分亲知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从而提出真正的专名(如“这”)维系的是亲知的知识,而穆勒和弗雷格所说的专名,在罗素看来都是描述语(亦作摹状词),它们传递描述的知识。克里普克认为,专名的指称存在严格指称,严格指称在不同场合下或者不同语境中都表达同一指称对象。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名称究竟是在指称一个对象,还是在传递该名称所携带的知识。这个问题不是单一维度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涉及多种概念工程研究。
不同的语言哲学家在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会提出新的名称来指代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例如关于语义值和意义观,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卡尔纳普的内涵意义观、弗雷格的呈现意义观、格莱斯的隐含意义观等都属于概念工程研究的异名概念工程。
同名概念工程是指,就同一理论或者同一问题,不同哲学家进行修补性研究或者拓展性研究。他们遵守同一研究范式,但推出的研究成果却不同。例如,就言语行为理论而言,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论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属于同名概念工程。
无论是同名概念工程,还是异名概念工程,它们都可归为概念工程重建。概念工程重建的基础仍然是在既有研究范式下,重新进行概念设计和概念实施。例如语言变异(language/linguistic variation)这一概念,它关涉的是不同言语社群或语言使用者在相同语言事实面前,因受不同语言变量(linguistic variables)的影响而习惯性地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例如发音不同、用词偏好、句式差异等(Labov 1966,1973;Lieb 1993:3-4;Swann et al.2004:177,190)。然而,日常语言使用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现象,即同一言语社群或同一个语言使用者,就同样的对象会特意采用不同的描述,往往是非习惯性的言语表达。曾经“教授”常被当成“人类灵魂高级工程师”,可如今网络语言中“教授”却成了“叫兽”。拿破仑把大英帝国说成是“店老板的国度”(a nation of shopkeepers),而英国人则自称为“伟大的贸易民族”(a great commercial nation)(Forster 1996:3-4)。这类语言使用现象已不是语言变异的问题。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时,就要对语言变异这个概念加以工程重建,于是,“同指异述”(codenotational description)可当作重建后的概念工程研究(杜世洪,李小春2022)。这是基于语言事实的概念工程重建。
近年来,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里,概念工程重建出现了语义最小论者和语境论者关于语义的自身确定性的研究,即语词是否存在确定的不依赖任何语境的意义(黄林慧,杜世洪2018;吴亚军,杜世洪2021;黄乔,刘利民2021)。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争论,但是争论的终极目的不是要废除这个问题,而是要防止谬论传播,促进概念认知进步,构建具有解释价值的理论,为了真问题,争论双方共同寻找最佳答案(Isaac 2021)。这样的理念就是在争论中进行概念工程重建。
叙述至此,我们对概念工程研究有了基本认识。下面就简要谈谈概念工程研究和语言植物研究法的关联性。概括起来讲,概念工程研究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新动向,它是对过去的概念分析或者概念考察的具体方法进行升华。格莱斯概括的语言植物研究法(以及牛津辩证法)是语言哲学研究业已成熟的典型方法,而概念工程研究是在这样的典型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方法。概念工程研究和语言植物研究法二者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首先,二者都以概念分析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都坚守概念分析的基本假设,那就是日常语言中所牵涉的形形色色的概念存在着混乱状况,只有通过概念分析才能达到澄明之境。
其次,二者具有相同的研究旨趣,都重视概念的系统性研究。语言植物研究法强调重视日常语言所关涉的概念及其细微特征,从细微特征入手来勘定概念范围与系统归属。概念工程研究重视概念的连续性研究,避免离散性分析,旨在把概念分析提升到系统构建层面上来,避免语言哲学研究陷入细节研究的坑洼里。这就足以说明语言哲学并非是零敲碎打的研究,也并非毫无用处,相反,语言哲学同样具有哲学发展本有的任务与作用。这一认识是语言植物研究法和概念工程研究共同的发展愿景。
最后,二者具有相同的思想原则,都认为概念具有层级性和系统性。日常语言使用过程出现的认识混乱或者概念不清,完全可能是人们在概念层级上发生错乱而引发争论甚至形成谬论。例如关于格莱斯合作原则的认识,存在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宣称合作不必是原则,另一观点坚持合作必须是原则。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断言,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两个观点聚焦的层面不同,即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具有层级性,不可用基于单一层面的观点来反对另一层面的认识。
上述三点正是语言植物研究法和概念工程研究的关联点。这说明语言哲学研究出现的新动向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既往的研究中进行拓展。虽然语言植物研究法这一名称本身尚未得到广泛认识,但是它所指向的研究却长期存在于语言哲学界。概念工程研究虽然开启了新的研究局面,但是它还面临着内部的困境和外部的挑战。无论怎样,面对日常语言,继承语言植物研究法,开启概念工程研究,都会促进语言哲学研究的发展。
4.结语
语言哲学的概念分析和语言分析常常专注于考察日常语言的细枝末节,从而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就只是沉迷于语言研究,趋于零散和琐碎,而且并无具体方法可言。格莱斯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存在着典型的研究方法,这就是语言植物研究法,而且这也是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集体成就。牛津大学的语言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所取得的哲学成就,可与古希腊的哲学家相提并论,即20世纪的牛津辩证法和两千多年前的雅典辩证法都在西方哲学发展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
语言哲学的发展出现了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和哲学治疗等研究形态。在这些形态中,语言植物研究法作为典型方法旨在聚焦语言表达式的细微特征,以此为出发点重视语言表达式所牵涉的概念范围和系统归属的勘定。21世纪初,语言哲学研究出现了新动向,哲学界开启了语言哲学的概念工程研究。作为新的方法,概念工程研究实质上是对语言哲学既有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概念工程研究与语言植物研究法存在着关联性,它们拥有相同的出发点、相同的旨趣和相同的思想原则。跟语言植物研究法一样,概念工程研究重视语言哲学研究的系统性构建,力图避免陷入语言细节的琐碎纠缠中而忽视哲学本有的任务与作用。不忘哲学的使命,语言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具体学科出现的新概念进行概念分析、诊断治疗、价值评估以及概念工程建设。例如,新文科建设、生态翻译学、体认语言学等这些新生概念,它们本身属于概念工程重建,正需要通过概念分析、诊断治疗、价值评估等来完善相应的概念工程建设。概念工程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修理坏的语言表达,以及摧毁思想中、理论上漂亮但不坚实的纸房子。
总之,语言哲学研究既需要语言植物研究法,又需要概念工程建设。在完成哲学本有的任务以及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语言哲学研究将会出现更多的语言分析师、概念分析师、哲学治疗师以及概念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