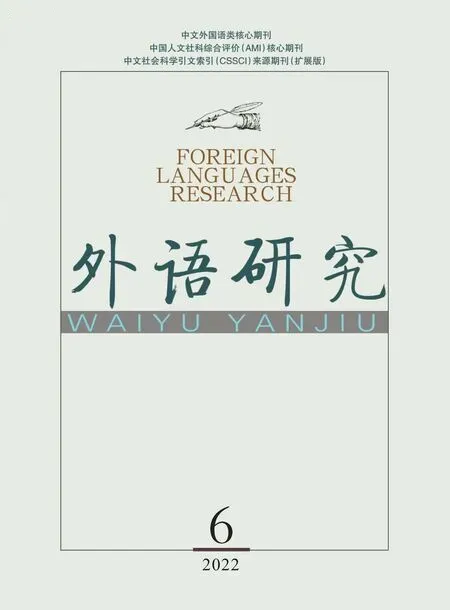美学家朱光潜论翻译*
姜望琪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0.引言
朱光潜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如果说王国维先生是把西方美学引进近代中国的第一人,那么,朱先生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系统最全面地介绍美学,使之在中国得以发展的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开拓者(转引自朱光潜2013:封底)。
同时,朱光潜先生也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一生700多万字的著译,大部分是译作。这不仅因为维柯的《新科学》、黑格尔的三卷本《美学》等译作所占篇幅巨大,即使是《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①等著作也涉及大量翻译,还不算《西方美学史资料翻译》等。
作为美学理论家和翻译实践者,朱光潜先生有其独到的翻译理论。本文旨在挖掘这种理论的内在蕴涵及其价值,弥补我国翻译界的遗憾。
1.译文要尽可能信
朱光潜先生1944年12月发表于(重庆)《华声》第1卷第4期的《谈翻译》(1946年5月收入开明书店为他出版的文集《谈文学》)是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专论翻译的文章,是他1923年发表第一篇译作以来20余年翻译经验的总结。他从文学研究角度入手,讲到翻译的重要,翻译的困难。他指出,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但是我们必求尽量符合这个理想,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不应该疏忽苟且。(朱光潜1988:289-290)
换言之,虽然朱先生认为“信”很难做到,但我们却必须尽量去做,尽可能做好。为什么?朱先生没有说。我猜想,这于他是不言而喻的——译作就得忠实于原作,否则就不是翻译。朱先生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做的。
1925年秋,朱光潜先生开始在欧洲留学,接触到了众多新鲜理论和理论家。其中,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他1927年就开始把克罗齐跟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Beuve,1804-1869)、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一起作为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在1929年动笔的《文艺心理学》里,他也重点介绍了克罗齐的理论。但是,在1932年左右,朱先生发现自己先前对克罗齐的理论有些误解,“恐怕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不起作者,于是决定把《美学》②翻译出来,让读者自己去看作者的真面目。”(朱光潜1989b:129)
朱先生翻译的《美学原理》依据的是Douglas Ainslie 1922年的英译本,但是,他发现英译本常有错误或不妥处。而且,英译本根据的是1909年出版的第四版,所以,朱先生参照克罗齐1922年第五版意大利文本进行了修改。为了保证译文准确,朱先生翻译时多次请教精通意大利文的朋友(王攸欣2011:280)。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学大讨论促使朱光潜先生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④在这场讨论中,他反复阅读了多种马列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撰写了《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等文章,提出了实践论美学观。不过,在阅读马克思著作时,他发现其中有些中文翻译不够准确,于是他参考德文版、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等,对它们进行了修改。例如,他当时就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题目改成了《费尔巴哈论纲》。但是,对这些官方译文的正式批评,要等到大约20年以后。这期间,这些有问题的段落一直在朱先生脑海里打转。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国各方面工作开始重新走上正轨,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朱光潜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变化,于是,他在完成黑格尔的《美学》、爱克曼(J.P.Eckermann)的《歌德谈话录》、莱辛(G.E.Lessing)的《拉奥孔》等以后,就开始细心地校改他认为有问题的马恩著作的译文。
例如,马恩列斯编译局1972年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段是: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作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1972:16)
单纯从字面看,这段文字就让人费解。“感性”能跟“事物、现实”并列吗?“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跟“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什么意义上是对立的?跟“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又是什么关系?这段话几乎每一句都让人不得要领。
朱先生认为,译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原作,所以,译文的不同部分是孤立的,串不起来。以Der Gegentand,die Wirklichkeit,Sinnlichkeit这三个词为例。原文把它们连用,意义上又有联系,就应该在译文中有所体现。第一个词现在译作“事物”,本不算错,英语有时也译作thing。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可以跟下文的Objekts,Objekte一样,译作“对象”。它是与主体(Subjekt)、人类(Menschheit)相对立的,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现有译文分别将其译作“事物”“客体”,下文还用“客观”,完全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割断了。把subjektiv译作“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还容易误解成“凭主观去理解”。下文的“思想客体”“感性客体”也应该相应地译作“思想对象”“感性对象”。
朱先生指出,费尔巴哈是侧重感性认识而轻视理性认识的,现有译文说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这是让费尔巴哈自打耳光了。原文的theoretische在涉及学说或理性认识时,固可译为“理论”,但只涉及感觉或感性认识时也译为“理论”就错了。Theorie本意是看到的事物的形象或道理⑤,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如果一律译为“理论”,就把感性认识排除掉了。一般地说,只是与实践(Praxis)对举时,Theorie应译为“认识”。特别是在涉及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时,不要使读者误以为费尔巴哈也是重视“理论”的。
然后,朱先生又回到开头的那三个词。他说,Sinnlichkeit照字面译为“感性”不妥,因为它指的是具体事物,而不是某种抽象属性。法译作le monde sensible(感性世界),即可用感官直接感知的世界,这就醒豁了。法译文有时把“感性的”改为“具体的”,也便于理解。另外还有“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也是不顾上下文的。Die t覿tige Seite指的就是上下文屡次出现过的T覿tigkeit,为什么不同样译为“活动”,难道这里有“能动”“被动”的区分吗?所以,朱先生建议这一段可以改作:
前此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在内)的主要缺点都在于对对象、现实界、即感性世界,只以对象的形状或直观得来的形状去理解,而不是把对象作为人的具体的活动或实践去理解,即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活动的方面不是由唯物主义反而是由唯心主义抽象地阐明了,——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实在的具体活动本身。费尔巴哈所想要的是和思想对象实在不同的感觉对象,但是他不把人的活动本身当作对象方面的活动来理解。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里只把认识活动当作真正的人的活动,而把实践只理解和固定为犹太人的那种卑鄙的表现形式。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或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朱光潜1989a:408)⑥
这一时期,朱光潜先生分别就准确翻译马恩著作问题在《社会科学战线》《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月刊》《文艺论丛》《文艺研究》《美学》《翻译通讯》等发表多篇文章,后多收录于《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掀起了一场如何准确翻译马恩著作的讨论。
2.译文要尽可能顺
这是译文要尽可能信的另一面。一篇通顺的原文,译得不“顺”,“信”也不复存在。但是,这毕竟是两个方面。好的译文要“信”“顺”兼顾,不可偏废。这一观点,《谈翻译》是通过关于直译、意译的讨论展开的。朱先生认为,“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朱光潜1988:300)。语言跟思想有一致性,语言变了,思想也必然要变。要想尽可能“信”,就要尽可能保留原文的结构形式;而完全按照原文的结构形式组织中文——直译,就可能产生不顺的译文。因此,“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同上:301)。直译、意译都不能过度。好的直译必然包含意译的成分,好的意译又必然包含直译的成分。朱先生的“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同上:300)就是这个意思。
朱先生还举例⑦详细说明了他的具体意思。其中有一段来自Edward Gibbon(1737-1794)的《自传》:
But my pride was soon humbled,and a sober melancholy was spread over my mind,by the idea that I had taken an everlasting leave of an old and agreeable companion;and that,whatever might be the future date of my History,the life of the historian must be short and precarious.
这是一个被动句,如果我们要完全保持原文的结构形式,就会跟中文的常用句式格格不入。最大的难点是:如何翻译the idea?它后面有那么长的修饰语。朱先生的解决方案是把the idea译作动词“想到”,原来那些修饰语就都成了它的宾语。然后,还可以大致保持原来的顺序把它译作:
但是我的自豪不久就降下去,一阵清愁在(我的)心头展开,想到我已经和一个愉快的老伴侣告永别;并且想到将来我的史书流传的日子无论多么久,作史者的生命却是短促而渺茫的。(同上:296)
朱先生说,这里面还有加字、减字,如,直译可能是“无论我的史书的将来的日子是怎样”这个句子就加了几个字使其意思更加清楚;“一阵清愁”前的and及“我的”都可以不译,这样更符合中文的习惯。(同上:299)⑧
朱光潜先生还多次在译者序、译后记里介绍自己如何直译加意译的经验。如,他在《美学原理》第一版译者序里说,“我自己写文章,一般以流畅亲切为主,翻译这书时却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作风以求对于作者忠实。我起稿两次,第一次全照原文直译,第二次誊清,丢开原文,顺中文的习惯把文字略改得顺畅一点。我的目标是:第一不违背作者的意思,第二要使读者在肯用心求了解时能够了解。”(朱光潜1989b:130)
在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译后记里,朱先生又说,“关于翻译的方法,译者所悬的理想是很简单的,一方面要尽量对原文忠实,一方面还要顾到中文的习惯,避免生吞活剥,使读者读起来太费力。不过理想终是理想,译者在一再校改中,还发现许多句法的生硬,许多译词的牵强。他尽了他的能力修正,但是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内容与形式总是分不开的,思想内容是新的,表现形式就不能完全是旧的,熟悉的。不通不忠实,应由译者负责;通,忠实,而有一点生硬拖沓,那就要读者费一点心思了。”(同上:514)
在黑格尔《美学》译后记里,朱先生甚至说,“黑格尔的《美学》是难读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部著作是从作者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及其辩证法出发的。这套体系极端抽象和艰晦,而且有很多矛盾和漏洞。抽象艰晦的思想体系就必然表达于抽象艰晦的语言,黑格尔所用的并不是一般德国人所习用的语言。”何况,该书是根据提纲和笔记编辑的,又未经作者亲自校改,遗漏、重复和错误在所难免。“译起来既有困难,读起来就不会很容易。但是难懂并不等于不可懂。如果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有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多动点脑筋,《美学》这部著作还是可以读懂的。”(朱光潜1990:316-317)
这说明,“通顺、可读”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概念。由于思想内容的不同,表达方式也必然相异。译作既不可能对原作完全“信”,译文也不可能是纯粹的中文;适度的不顺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信”而做出的妥协。
3.要大力倡导翻译批评
朱光潜先生的翻译理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倡导翻译批评。这一点虽然在《谈翻译》中没有明确提出来,却是贯穿朱先生一生著译事业的一个内在特色。从他主张把柏拉图的idea译为“理式”(因为它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的存在,不能译为“观念”或“理念”)(朱光潜1991:288),到他认为把波德莱尔的Les Fleurs du Mal译作“罪恶之花”不够雅驯(这里的mal应译为“病”,“罪恶”是误译)(朱光潜1989a:241),朱先生始终把维护正当译名,批评不良译法看作自己的责任。
在1951年的“五四”翻译座谈会上,朱先生指出,“五四”以来翻译界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性,没有健全的审核制度或批评风气。他提出了很多预防坏译品的建议,其中包括“编译局应领导建立一个健全的批评风气,如现在的《翻译通报》所做的还可以扩大”(朱光潜1993:16)。在1955年合作翻译《萧伯纳戏剧集》时,朱先生甚至在书信中对老舍先生的译文直译痕迹太突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上:38)。
在1957年《关于外语教学的一些杂感》中,朱先生还对翻译教学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认为,学生在翻译方面所犯的错误几乎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公式:不顾思想内容与具体生活情境而呆板地搬运语言形式。如,He shook his head and I did the same被译作“他摇他的头,并且我也做了同样的事”,而不是“他摇摇头,我也摇摇头”。“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语言进行思索(茅盾语)”被译作A good translator on the one hand reads the foreign words,and on the other hand carries on thinking in his own language,而不是A good translator reads foreign language but thinks in his own。(同上:95)
在20世纪70年代末指出马恩著作中的一些翻译错误的同时,朱光潜先生还给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志写信,建议成立全国性机构,解决学术名词译名统一问题。其中,他建议,根据以往《翻译评论》和《出版工作》所积累的经验,重新办一个翻译评论或编译评论的刊物。他特别提到了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终结”这个词的翻译。
[这个词]德文原文是Ausgang,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一是“出路”或“结果”,二是“终结”或“终点”,英文本取第二义作end,中译本也是如此。东德科学院由克拉彭巴哈(Ruth Kplappenbach)主编的新《德语大词典》中Ausgang条下引了恩格斯的这部书名,把这个词解释为时间上的一个“段落”(Abschnit)。此外,我还看到斯屈柔克(Dirk J.Struik)替纽约国际出版局1964年新出版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英译文所写的长篇序言,提到恩格斯的上述著作时,却把Ausgang解释为“出路”或“结果”的意思,足见这个词在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不一致。我疑心Ausgang译为“终结”似不妥,因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恩格斯的全文最后一句话是很明确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怎么能说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时代便已“终结”了呢?
我想一般翻译工作者心中都难免有一些与此类似的疑难。如果有一个公开的编译评论刊物,让编译工作者乃至一般读者提出来公开讨论,那不但会逐步解决一些疑难,而且也会使翻译界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同上:450-451)
在1980年10月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朱先生又讲到马恩著作翻译中的问题,呼吁大家展开讨论。
当读到其他同志讨论译文的文章时,朱先生特别兴奋。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编辑室给朱先生寄来了一位同志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译文进行商榷的文章,朱先生立即抽出时间细读了一遍。并给他们回信,赞赏了这位同志的工作,尽管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朱光潜1993:546-549)。当郑涌同志把自己的《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送给朱先生时,朱先生也很欣赏,称赞了他的成绩,当然也指出了一点问题(同上:636-638)。
特别要提到的是,朱光潜先生强调的翻译批评,并不是对人不对己的。他对自己的译作历来要求更严。他在自己译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愁斯丹和绮瑟》的序里说,“我很惭愧,虽然易稿三次,终于没有把原文的轻妙淡雅的神韵吸收过来”(朱光潜1989b:10)。1979年罗新璋先生重译该书后,致函朱先生。很快得到的答复是:“我本是三套丛书的一名编委,在上海开规划会议时我注意到此书已列入规划,但未提我曾译过此书,因为我有很多的工作待做,找不出时间和精力来改译。现在您既另有译本,千万不要废弃。如果您认为拙译尚有可取之处,可任意采取或修改,作为合译或在序文中提一句就行了。我希望此书可以成为一个青年人和一个老年人合作的纪念碑”(转引自罗新璋2019:21-22)。
在《歌德谈话录》译后记里,朱先生说该书是译完黑格尔《美学》后译的。虽然语言“不像黑格尔的那样抽象,但因为是当时实际谈话的记录,……,译者在这方面对德文的掌握更差。……译者所悬的目标只有两条,一是忠实原文,二是流畅易读。实际做到的当然和理想还有些差距”(朱光潜1989c:538-539)。在维科《新科学》译后记里,朱先生甚至说,《新科学》很艰晦,他开始译时已年近八十。“我既不懂意大利文,又不懂拉丁文,古代史过去在英国虽也学过,但是考试没有及格。……现在总算把这部难译的书译出来了。错误必然百出。”他希望自己的译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来能有人拿出“较好的新译本”。“为着帮助将来的改译者,希望读者发现到这本译文的错误,就立即提交承印本书的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朱光潜1992:267-268)
4.结语
朱光潜先生通常以“美学家”著称,全面论述翻译的又只有一篇《谈翻译》,如果不仔细看,有人会以为他的翻译理论没什么特色。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本文从朱先生的翻译实践入手,揭示了他的美学研究跟翻译的关系,即,正因为他是美学家,所以对破坏美感的误译特别敏感、特别反感,所以他主张译文要尽可能信、尽可能顺。
朱光潜先生翻译理论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倡导翻译批评。特别是在晚年,他反复指出马恩著作翻译中的问题。朱先生是真学者,只相信理性、只相信科学!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唯物辩证法是真理。他从学术角度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⑨所以,他以维护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尽管他的批评对象是官方的翻译者。
注释:
①《朱光潜美学文集》的“作者说明”明确提到“《西方美学史》中绝大部分的引文,都是自己试译的”(朱光潜1993:565)。
②英文名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该书包括原理和历史两部分,朱先生只译了原理部分,所以,改名为《美学原理》。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该书直到1947年才译完。
③苏宏斌在《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撰文《论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兼谈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误译和误解》。他认为,朱先生把克罗齐的intuition译为“直觉”,expression译为“表现”是错误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朱先生的译法是主流观点。而且,朱先生只是在早年的介绍中对克罗齐有些误解,在翻译了《美学原理》,撰写了《克罗齐哲学述评》以后,在《西方美学史》中对克罗齐的介绍无疑要全面和充分得多。这说明,朱先生的译介是“尽可能信的”。至于某些术语的具体译法,朱先生肯定是欢迎讨论的。我们下文将指出,朱先生翻译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倡导翻译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尽可能信”这个目标。
④其实,朱先生在1950年10月就翻译完成了美国犹太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哈拉普(Louis Harap)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说明他当时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开放的态度,是愿意接近和了解的。而且,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他在年近六十之时开始自学俄语,达到了可以借用词典阅读的程度。
⑤在1980年10月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朱先生明确指出,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theoretiker不能译成“理论家”,其词根源自希腊语,表示“看到的东西”;而且这里是指眼睛这个感觉器官。(朱光潜1993:507)
⑥要说明的是,朱先生提供“建议的校改文,本意不是‘示范’,而是供讨论者和校改者参考”(朱光潜1989a:400-401)。
⑦可惜的是,罗新璋的《翻译论集》在收录该文时删除了这些例子。
⑧朱先生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劳动”问题的一段话,其中包含“劳动的内容和进行方式对劳动者[须有吸引力],吸引力愈少,劳动者就愈不能从劳动中感到运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各种力量的乐趣”。他加注说,“‘吸引力愈少’前加‘须有吸引力’五字,为了读起来较通顺”。(朱光潜1989a:434)
⑨1983年,他应邀赴中国香港讲学时,开口就声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朱式蓉,许道明1991:2;王攸欣2011:4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