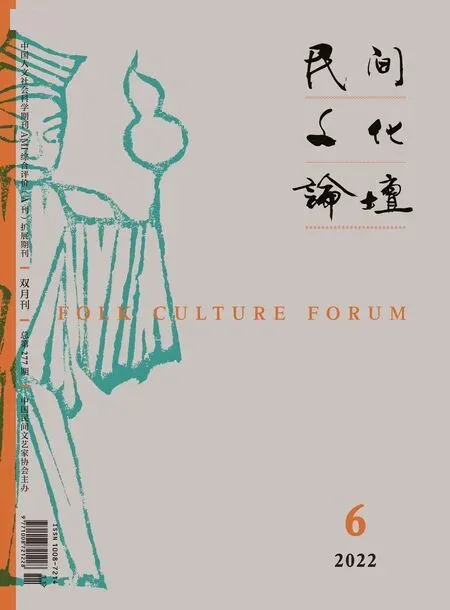民俗摄影的“当下”立场和美学追求
邓立峰
论者常常提及民俗摄影是特殊的摄影门类,因为它内含“学术性”和“知识性”,兼具“文献价值”与“美学价值”,有人甚至称其为“形象历史档案”或“图像民俗学”“图像历史学”“图像民俗学”。①董河东主编:《民俗摄影》,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8年,第84页。类似为民俗摄影树立特殊地位的论断并不少见,按其重要价值,似乎民俗摄影应当成为艺术生产领域或民俗学研究中的“显学”;然而让人感到失落的是,当今民俗摄影却呈现出“热闹中的式微”,并产生了“种种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摄影异象”。②柴选:《民俗摄影的式微的现状与“四化”异象》,那日松主编:《中国摄影批评选集》,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442页。
民俗摄影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现代摄影技术诞生之初,近二百年间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但作为一种经过归类、加以定义的摄影门类,“民俗摄影”还相对年轻——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出现“民俗摄影”的系统性论述,相关研究也在向前推进。然而,在为其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民俗摄影被套上了来自“艺术”与“学术”的双重枷锁,至今仍然面临着范畴界定模糊、拍摄取向不清、美学追求缺失等问题。
一、民俗摄影的范畴界定问题
“民俗摄影”成为学界认可的专门摄影门类,是在1993年中国民俗摄影协会成立之后。冠以“民俗摄影”之名的摄影作品、关于民俗摄影的学术讨论,也随之多了起来。不过,以民俗为对象的拍摄行为却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摄影师大卫·奥克塔维厄斯·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森(Robert Adamson)就拍摄了一系列反映苏格兰地区日常生产生活的照片,算是最早的民俗影像之一。20世纪下半叶,人们更多将摄影技术看作记录工具,广泛应用于对少数族裔、建筑、城市景观及民间风情等的拍摄记录之中。1897年,英国伯明翰区议员班杰明·史东爵士(Sir Benjamin Stone)推动创立了英国国家摄影记录协会(the Naional Photographic RecordAssociation),“为未来记录古迹、古代建筑、民间风俗和其他历史遗迹,形成一个国家记忆库”①[英]凯利·怀尔德:《摄影与科学》,张悦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79页。。20世纪初,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Curtis)完成了二十卷本的《北美印第安人》(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这是民俗摄影史上最常被提及的作品之一。之后的几十年,西方民俗摄影活动不再只聚焦于少数族裔和文化遗迹,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主流人群的生活状态,民俗摄影也达成了拍摄对象的“全覆盖”。
在中国,民俗影像的生产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西方商业摄影师、传教士和殖民官员,如白斯德望(Étienne Albrand)拍摄了贵州居民生活风貌、方苏雅(Auguste François)拍摄了云南居民的城镇生活。到了20世纪20年代,逐渐流行开来的大众画报催生了一批以民俗事象为呈现对象的作品——单单在1926年,《良友》画报就刊载了《北京丧俗一瞥》《山西省小人戏》《福州之水嬉》等系列民俗照片,这说明,民俗事象此时已被纳入社会视觉体系之中,成为视觉消费的对象。与此同时,一些国内外研究者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人类学、建筑学等的考察,拍摄了不少反映当地民风的照片。而像庄学本、王小亭、孙明经这样有专业抱负的摄影师,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拍摄了大量反映当地居民生活状态、穿着服饰、节日习俗的照片……1993年,中国民俗摄影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俗摄影成为一个新的摄影门类并迅速被大众接受”②马有基、吴泳:《民俗摄影中的传统文化及其表现》,《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刊登于1995年第5期《新疆艺术》的《试论民俗摄影》,是最早对民俗摄影进行专论的文章之一,作者将“民俗摄影”定义为“用摄影手段形象地表现民俗事象,它与风光、人像、建筑等摄影一样,都是由内容来确定的一种专业性摄影门类”③雷茂奎:《试论民俗摄影》,《新疆艺术》,1995年第5期。。之后的研究者大多沿用这样的界定,将“民俗摄影”视为民俗文化与摄影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民俗事象为题材进行影像生产的摄影门类。
这样的定义看似简单明了、有具体指向,实则蕴含着范畴的边界危机。当下对“民俗摄影”的界定,混杂了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民俗摄影”和作为民俗研究学科工具的“民俗学摄影”的边界,使民俗摄影兼具艺术生产属性和工具属性,在科学取向、工具价值和艺术追求三个意义层次上产生了矛盾与交杂。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下“民俗摄影”的主要呈现对象,是被视作“他者”的群体或具有文化遗产属性的事物。一方面,说起民俗摄影,最常提到的是柯蒂斯、庄学本、王小亭等人的照片,而他们所表现的对象多是“我群”之外的“他者”;另一方面,人们也常常把“他者”的普通肖像——例如表现拍摄对象面部表情的照片及喝水、饮食等日常动作的特写——视作“民俗摄影”,这类仅仅因为对方的“异域”长相而被拍下来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民俗摄影的教材与摄影集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还要从过往“民俗”的界定标准说起。高丙中指出,在民俗学确定其研究对象的时候,有一个“标准文化”作为参考,在工业时代,现代文化成为评价各种现象的标准,而跟现代文化不尽相同的“古代或异域的文化遗留物”则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今天的民俗学研究同样纳入了主流人群的日常生活,但主流人群和“他者、异己”的二分形态“是民俗学兴起之初就隐含着的内在逻辑”,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④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2—163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者”影像更容易被看作民俗摄影了。
其次,民俗摄影常常被赋予“为历史留存研究文献”的学科属性。一方面,民俗摄影被当成记录和保存文化遗产的工具。民俗摄影“一是可以帮助人类储存民俗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二是可以抢救那些濒临消失的民俗事象,作为现代化手段的形象‘化石’留给后人进行研究。”①雷茂奎:《试论民俗摄影》,《新疆艺术》,1995年第5期。“民俗摄影所拍摄的大量的反映民俗文化的图片,就是一个文化遗产的图片库。”②向先清:《民俗摄影: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俗记忆》,《柳州师专学报》,2010年第3期。另一方面,人们又将民俗摄影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为其赋予“学科边沿性”。“民俗摄影既是民俗学、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又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相联系,有极强的学科边沿性。”③谭巧勤:《关于民俗摄影的考察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这一点与其他摄影门类大不相同:众所周知,现代摄影技术诞生之初就被用于记录和存档工作,其中包括以不同人种为拍摄对象的人类学摄影、记录考古过程的考古摄影、用于拍摄罪犯或犯罪现场的司法摄影,等等。不过,这些摄影门类都有明确的功能边界,媒介本身并没有更多的意义指向;而被用来归类一般摄影实践的纪实摄影,对其界定虽然兼具行为过程和美学形式,但它并不会被视作工具,本身也不具“学科边沿性”;只有民俗摄影与众不同。
第三,民俗摄影被赋予了揭示“本质”的科学要求。在相关论述中,经常可以看到要求民俗摄影实践者通过镜头揭示民俗“本质”。有研究者写道:“民俗摄影着重在于文化的体现,朴实无华,甚至有些显得毫无拍摄章法的民俗摄影作品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更多。当你以做学问的心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在面对即将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时,就已经把摄影的技术‘忘记’了,不在乎用形象语言来塑造美的画面,而关注的是民俗事物的演变、发展过程,希望自己拍摄的内容具有知识性,学术性,希望画面中的环境、人物能够体现出民俗活动的本质意义,这样摄影作品就能反映出称作‘文化’的东西。”④同上。毫无疑问,这样的要求混淆了“民俗摄影”与“民俗学摄影”的功能,也混淆了民俗摄影家和民俗学家的界限。
由此可见,当今对“民俗摄影”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俗学摄影”。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民俗摄影”,应以审美属性和艺术价值为根本追求;而具有学科属性的“民俗学摄影”,则需要在文献留存和研究价值的角度多做考虑。但在当下的论述中,民俗摄影已成为民俗学与摄影艺术边界不清、概念交融的地点,而范畴界定的模糊,也导致了民俗摄影拍摄取向、美学追求的混乱与不定,影响了这一艺术生产形式存在的合法性。
本文认为,应将“民俗摄影”和“民俗学摄影”作清晰界定,并厘清作为影像艺术生产行为的民俗摄影所应追求的美学原则。
二、本质主义思维与民俗“景观化”
如前所述,民俗摄影尝试纳入“文献记录”与“科学研究”等功能,来争取作为独立摄影门类的合法地位,并就此引入了揭示民俗“本质”的科学要求。而在民俗摄影的实践中,不少摄影师也确实抱着揭示“本质”的目的进行拍摄。
长期在滇南地区考察的民间文化专家姜定忠,拍摄了大量具有文献价值的少数民族照片。他在《民俗摄影的方法与理论》一书中提到了其拍摄理念:“对于民俗风情摄影,摆拍比抓拍重要。如果不摆拍,不是有意识有准备地把人物摆进去,你去等几天或者更长时间,也不会有最佳环境、最佳景物、最佳光影、最佳人物同时在一个画面中出现。”同时,处理好民俗民情摄影,要“让作品由表及里,透过表象而最生动、最典型地反映民俗的本质特征”①姜定忠:《民俗摄影的方法与理论》,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5页。。出于这样的理念,他写道:“在拍摄藏族民俗风情时,一定要跟那里的青藏高原结合起来……青山顶着蓝天白云,浓厚的宗教氛围,给喇嘛寺庙增加了高深之感,使那里的天、地、人都带有神圣莫测的色彩……哈尼族居住于哀牢山层层梯田之中,形成了哈尼梯田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其服饰、住房、婚俗、节日,所有一切都带有梯田的神韵,没有梯田的影子,就难以反映哈尼族民俗风情的实质。”②同上,第213页。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资深的摄影实践者,作者的确提供了一种快速入门、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摄影作品的方法。但是,这种以几项“最佳”的组合来“反映本质”的方式,仅仅是契合了拍摄者的“他者想象”——也只有在“他者想象”中,才会有对认知对象“最佳组合”的判断。追求“反映本质”,更容易让拍摄者陷入刻板印象和套式化认知之中。
科学思维往往会为研究对象预设一个可加理解的“本质”,并以研究活动对其进行揭示。民俗活动中,这一“本质”存在与否尚不清楚;而对于民俗摄影,对民俗“本质”的追求,却更容易跟拍摄者脑中的“本质”交杂,产生认知的混乱。致力于呈现民俗“本质”的拍摄活动,的确造成了一些怪象的出现——拍摄者不再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民俗特征,而是为民俗事象和民俗主体预设一个契合刻板印象的“本质”。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在某“摆拍圣地”(如云南东川烟斗老人、福建杨家溪的老牛和农村夫妇),“长枪短炮”围绕着一个孤零零的拍摄对象,这个拍摄对象及其所在的场景,契合了大众对于农民或其他劳作者的想象,可谓是“最佳环境”中的“最佳人物”。据媒体报道,江西婺源秋口镇的“只撒网不打鱼的渔夫模特”,光靠充当被摄对象,每年就有近3万元的收入。③王国红:《婺源:渔夫泛舟当模特撒网摆拍忙创收》,《照相机》,2015年第1期。为了揭示民俗“本质”,一些拍摄者“手动”塑造景观,自动剔除与“本质”不相关的民俗元素。而当拍摄者“手动”塑造的图景契合于大众对民俗的刻板印象时,民俗摄影的景观化就此完成。
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为我们带来了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启示。在德波看来,建立在现代工业之上的社会,本质上就是景观主义社会。④[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由丰富的图像构成的社会图景,使人们屈从于娱乐、消费及意识形态等欲望客体,遮蔽了人们的本真生活和真实渴望。景观具有其自足的“实证性”:“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展开在其自身的普通统一性中,成为边缘的伪世界,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⑤同上,第3页。德波的景观理论所反映的是人与生产方式、政治权力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不过,即使剥离开此一权力系统的运作,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作为社会实践的“景观秩序”。这是一种对现实存在的景观化建构,通过影响着大众思维的本质主义观念,以影像生产的方式使表现对象“部分在场”,达致自足的“统一性”,以促成文化观点或文化产品的流通。
我们熟悉的各类民俗表演,就是将民俗事象“景观化”的重要形式。如今,民俗表演已非常普遍,“各地的摄影节庆活动为吸引参与者,好像不安排点民俗表演就对不起四面八方的来宾;某些特色题材,已成为地方旅游推广的重点项目天天上演,组织拉纤、套马、放牧等‘大型场面’等也称为摄影旅游景点的收费项目之一。”①柴选:《民俗摄影的式微的现状与“四化”异象》,那日松主编:《中国摄影批评选集》,第443页。在民俗影展和相关影集中,经常可以看到民俗表演的照片——一群穿戴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在铺好的红毯或舞台上,或神情庄重地站在祭品前念念有词,或表演着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拍摄者“巧妙地”抓住了“决定性瞬间”,展现了表演者虔诚、投入的神情。
这样的照片看似捕捉到了民俗活动的“本质”,也能满足观看者对民俗活动的想象。但现实是,这类民俗表演本身就是一种“景观化”的建构,依此拍摄的民俗照片更是对于景观的再生产。在今天,这类表演往往由地方政府或商业组织主导,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或娱乐属性,与民俗本身所追求的社会功能相去甚远。不过,民俗表演往往能集合所有契合大众想象的民俗元素,将独一无二的民俗特征集中展现在一个完整的“舞台”上,因此是民俗摄影中常出现的主题。然而,拍摄民俗表演照片时,一些能改变民俗“本质”的信息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景观化图景赖以“自证”的合理性,首先就在于影像内部话语系统的“统一性”,民俗是“民”之俗,表现为民间的自发性与自足性,在拍摄民俗表演场景时,拍摄者会剔除其中象征政治性或商业性的“当代”元素和“外在”元素,这在保证“民间”景观纯粹性的同时,保持民俗的神话色彩。当然,除了影像内部系统的“统一性”,景观化图景存在的合理性,还依赖于影像语言与社会话语的连贯表达,社会大众对于民俗及民俗主体的套式化认知和刻板印象,会使剔除了“当代”元素和“外在”元素的民俗影像显得毫不违和——当身着特色服饰、投入地表演民俗节目的影像出现在大众面前,对该民俗及民俗主体的生活化论述、“他者”想象,与影像本身相联通,两者相互印证,使民俗表演成为民俗“本质”的证明。
基于本质主义思维的景观化生产,使民俗影像成为拍摄者和观看者合谋制造的片段图景,它将被摄对象原本多样的民俗元素和复杂的动态变化简化为“想象-印证想象”的过程,而民俗摄影论者所期待的类似“影像民族志”的成果,往往会演变成民俗活动的“伪民族志”。
三、基于民俗和民俗主体的美学追求
某种程度上讲,本质主义的追求和景观化的塑造,暗合了对民俗“传统”的推崇:将民俗视为“过去”的产物,在拍摄中选取象征“传统”的元素——符合其生存与演变的历史环境的意象,如“历史的”服饰、“历史的”仪式等,而忽视其基于“当下”的动态变化,这看起来更能体现民俗“本质”,也更能契合观者对民俗的历史性想象。
“民俗”与“传统”的密切关联,一直决定着民俗认知的发展,过往对民俗的定义也大多强调“传统”,民俗学研究将“传统”看作是界定“民俗”的特质之一,在一些民俗学者看来,“传统”甚至是“俗”的同义词。②刘晓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但在“传统”逐渐成为解构对象的过程中,人们渐渐意识到,“传统”与“当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叙述的那些“被发明的”传统中,“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导论:发明传统》,[英]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对传统的阐释和构建离不开当下的需求,传统是“被发明的”。
民俗学发展过程中,对“传统”的不断拷问也改变着对“民俗”的界定。近年来,民俗学研究逐渐出现了“日常生活”转向,“民俗”的定义逐渐从一种“实在”转变为一个“过程”。当这一转变发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民俗现象转向实践主体,“从静止的、本质化的共同体转向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不再将民俗视作“客观的、本质化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为人们所意向性地建构的社会文化事实”。②刘晓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
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为民俗摄影树立“当下”立场提供启示:首先,民俗摄影应突破民俗活动的历史性背景及头脑中刻板印象的束缚,展现当下的民俗场景,确立基于“当下”的摄影语言;其次,民俗摄影应将拍摄对象聚焦于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体或个人,突出主体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呈现人在民俗活动中的状态。
我们以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Martin Parr)的纪实作品为例。虽然以传统的眼光看,帕尔很难被视为民俗摄影家,但他的作品中却处处凸显民俗元素。帕尔镜头中的民俗并不是带有“传统”印记的民族风情,而是趣味盎然的“新民俗”。在异域题材系列作品《墨西哥》(Mexico)中,站在墨西哥的土地上,帕尔没有刻意寻找典型民族元素,而是对墨西哥的街头食物、带有墨西哥元素的旅游商品、绿白红三色的物品(绿白红是墨西哥国旗的主色)、人们的街头活动等进行拍摄,反映墨西哥的民风民俗。这些影像显然不具备揭示当地民俗“本质”的能力,却直接地反映了墨西哥民俗文化的混杂性,正是对这一混杂特征的呈现,将当地民俗从“古老”和“神秘”的藩篱中解救出来,彰显了墨西哥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核。
当我们转换观看民俗的目光,将民俗视为“建构的社会文化事实”的“过程”,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基因”,每个人都是民俗的承载者和参与者,人们从事着生产共同意义的群体性活动,民俗在此显露轮廓。以“当下”为本,以民俗中的人、生活为拍摄中心,而不是以追求“本质”为目标、以民俗形式为拍摄对象,这样的民俗摄影更能展现民俗的动态变化,也更能把握民俗主体的存在状态,抓住民俗流变中的精神内核。
除了树立“当下”立场,民俗摄影还应具备美学追求,民俗摄影“合法地”成为独立艺术门类,其最终依据,不是揭示民俗“本质”、保留历史文献的功能,而是对民俗活动美学价值、民俗中个体生命力的充分表现。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蒂娜·莫多蒂(TinaModotti)和路易斯·马尔克斯·罗迈(Luis MárquezRomay)的墨西哥民俗主题摄影作品,来解释这种美学追求。1923年至1930年间,来到墨西哥的莫多蒂用她的相机记录下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女人头顶陶罐出行是具有民间特色的风景,莫多蒂拍摄了多张反映这一习俗的照片。当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不仅可以看到头顶陶罐的女人,还能看到女人开心的笑容、身边赤裸身子的孩子、墨西哥细长的街道及街道两旁铺有砖瓦的房子……莫多蒂很少切割与主题不相关的元素,她将人与环境悉数收入镜头,没有迎合西方观众对于“他者”的刻板印象,而是在表现人与环境关系的和谐形式中凸显人的生命力。相比之下,罗迈的一些墨西哥民俗照片就更体现文献记录的特性。1950年出版的《墨西哥民俗》(Mexican Folklore)刊登了100张展示墨西哥独特民族服装、装饰配饰、仪式用具的照片,这些照片由罗迈拍摄,其中一部分是以定格肖像的特写镜头呈现,着重突出被摄主体,背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类照片中,人的服装、配饰、用具等是照片的主角,人成为模特。从中可以看出“拍摄者-被摄对象”的二元对立,人物“灵魂”缺失,使此类照片的艺术价值大大降低。两相比较,罗迈的此类照片更可归类为“民俗学摄影”,而莫多蒂的照片则更能体现民俗的美学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美学追求,并不是指风格上“唯美”与“矫饰”,也不是单纯追求构图、色彩搭配等的形式主义取向。摄影的机械特性和技术特点,决定了它的强项在于即时抓住生活中的美感;过度追求“唯美”“矫饰”,会使其进入到“想象”的美学感觉,这跟致力于凸显“传统”、塑造“遗存”之感的民俗摄影作品一样,都会使摄影的纪实特质丧失其本性。民俗摄影之美,要从基于当下生活的民俗中寻找其美学价值,反映民俗之美、生活之美和生命力之美。
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就需要民俗摄影者具有“深描”的信念。我们在此借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阐释解释人类学理念时所发展的“深描”概念。格尔茨认为,面对结构“层叠”或“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现象,“首先必须努力把握它们,然后加以翻译”①[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2页。。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深描”,可以建立抽象概念与具体知识之间的关系。其关键点,就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分析,通过那些“在限定情景中长期的、主要是定性的、高度参与性的、几乎过于详尽的田野研究所产生的资料”,可以实现对抽象概念的思考。②同上,第30页。
虽然民俗摄影并不是一种研究行为,但其实践者同样需要以“深描”的信念与方法去理解复杂的民俗结构,建立对民俗更为全面的认知,探求民俗事象背后的人为意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民俗的动态变化以及人在民俗中的位置。当然,“深描”的价值不只在于“深”,也在于“描”,就像格尔茨所说的:“一部具体的民族志描述是否应该引起注意,并非取决于它的作者能否捕捉遥远地方的原始事实……而是取决于它的作者能否说清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能否减少对鲜为人知的背景中的陌生行为自然要产生那种困惑。”③同上,第21页。这样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民俗摄影。民俗摄影实践者不只是民俗的记录者和展现者,还应该理解民俗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用镜头把握民俗深刻的精神内核。
当下被公认具有极高价值的民俗摄影作品,其拍摄者无不践行着“长期”“高度参与”的“深描”理念。无论是庄学本、王小亭拍摄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影像,还是侯登科的“麦客”系列、陈锦的“茶客”系列等等,都可以看出拍摄者对民俗事象高度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为了拍摄四川人的茶习俗,摄影师陈锦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茶客,工作之余每天都泡在茶馆里,和喝茶的人聊天。陈锦谈到:“如果你仅仅作为一个拍摄者、一个猎奇者,那只能拍到茶馆的表象,要真正深入茶馆,必须进入茶客的生活,被他们接纳,融为一体,这时他们才不会把你当外人,会跟你谈家长里短,谈心里话,你拍照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拍的画面才真实自然,才能真正把握茶馆文化的精髓。”④何瑞涓:《陈锦:四川茶馆,品出生活变迁》,《中国艺术报》,2018年12月19日,第23版。更进一步,近年来西方民俗摄影出现了当代艺术取向——一些拍摄民俗主题的摄影师,开始在美学层面寻求与被摄对象的共鸣。例如,英国摄影师帕特里克·萨瑟兰(PatrickSutherland)深入位于北印度的斯皮提(Spiti)地区,拍摄当地民俗文化二十余年,最近几年,他改变了传统纪实摄影的拍摄方式,让拍摄对象摆出他们自己认为“最佳”的拍照姿势进行拍摄,在此,民俗主体成为了可进行文化交流、能在美学层面产生意义交融的对象,对民俗摄影实践有极大的启发意义。①邓立峰:《萨瑟兰与“他我同在”的影像创作》,《中国摄影报》,2022年6月3日,第3版。
与之相对,当下的民俗摄影实践却大多是“候鸟式”的拍摄,生产着景观化的图景。2021年3月,笔者由于工作原因前往位于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正赶上一家塔吉克人家举办婚礼,我们来到婚礼现场,却意想不到地看到了为数众多的“长枪短炮”来到现场,在塔吉克人家里走进走出进行拍摄。打听之后得知,因为时值塔吉克族传统节日肖贡巴哈尔节,很多摄影师、摄影爱好者专门从内地飞到位于国境边陲的塔县进行拍摄,正赶上塔吉克人的婚礼,所以一齐进行了拍摄……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拍摄方式归类为用以收集资料、保存文献的“民俗学摄影”。但如果我们将其看作作为摄影艺术门类的“民俗摄影”,那这种“候鸟式”的拍摄方式能不能真正把握塔吉克婚俗的精神内核?还是仅仅呈现一种“景观化”的少数民族图景生产?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结 语
当今民俗影像生产面临着一个奇怪的现象——打着“民俗摄影”名号的民俗影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但关于民俗摄影的研究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探讨民俗摄影的立论也显老套与空泛。
要使作为摄影艺术门类的民俗摄影更健康地发展,让具有积攒资料、留存文献功能的民俗学摄影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清晰厘定两者的界限,并对其进行体系性阐述。对于“民俗摄影”而言,要界定其边界,首先要区分其与“民俗学摄影”的关系,“民俗摄影”应与“民俗学摄影”有所区别,它具有独立存在的艺术生产价值,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与此同时,民俗摄影要放弃追求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式思维,更侧重于通过镜头描述和呈现民俗活动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在拍摄取向上,民俗摄影应该脱离自身对拍摄对象的想象和价值预设,摆脱“传统”对认知的束缚,以全面的、动态的视野去观察民俗活动及民俗主体,尝试理解当代生活对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要树立以民俗中的人为本体的美学追求,通过镜头展现民俗之美、生命力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