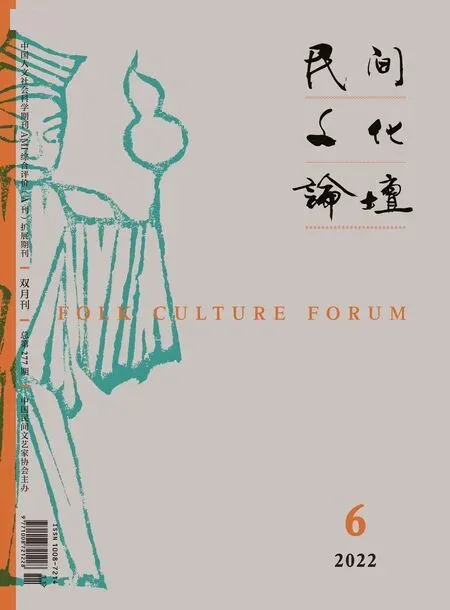刘锡诚《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述评
邢 莉
《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20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刘锡诚先生自1990年以来30篇神话论文的汇集,著作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对于我国神话的研究,下篇是对于神话学者的评述。无论是上篇对各类神话的阐释,还是下篇对于著名学者神话研究的梳理和评估,作者都是在力图探究中华民族神话的特质及其民族精神。这也是他研究神话的目的与初衷。作者研究神话的目的充溢着对文明古国命运的人文关怀,洋溢着一位耄耋老人对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信心和力量。
该论文集建构了研究中国神话的整体思维。①丁晓辉:《神话整体研究·神话学评论——刘锡诚的神话学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1987年10月23日,作者在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提出:中国神话要放到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上来讨论,换句话说,中国神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中国神话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关系,似乎也挖掘得不够。
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一,他认为神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包括经史子集,而且还要眷顾民间文化,包括神话的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他突破了把神话视为文学想象和怪异叙事的窠臼,也不拘囿于用史学话语对神话的阐释。他是位民间文化学家,以民间文化学者开阔的视域研究我国神话,力图从文化史的角度解读神话。其三,他认为,我国神话产生于黄土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然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域的人文创造。其四,我们谈中华民族的认同,首先是文化的认同,而神话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标识之一。他之得以建构从民间文化学角度研究神话的整体思维,是与其学术功力分不开的。他撰写了《中国原始艺术》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两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与其神话研究存在密切的关联。可以说,这三部书是他成为民间文化学者的标识。
刘锡诚先生认为,我国不仅有一个庞大的帝系神话系统,而且也有一个丰富多样的自然神话系统;不仅有一个宇宙和人类起源神话系统,也有一个创造文化英雄的神话系统。在本书的上篇,他研究了我国与世界各民族神话相通的各类神话,又针对我国各个民族丰富的神话呈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例如在人类起源的神话里,他划分了肢体化生型、造人型、卵生型、感生型、石头生人型及其他类型等,归纳出我国神话的丰富形态,突显了我国神话的特色。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神话也有自己的谱系。尽管列出我国神话的谱系尚需要更大的功力和多学科成果的论证,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在质疑和反思我国神话碎片化、历史化、非体系化的结论。他对于中国神话谱系的提出,不仅是中国神话立足于世界民族神话之林的基石,也是探讨中国神话民族精神的动力源。
为了探讨中国神话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他不仅搜集了大量的汉族典籍资料,而且摒弃了汉族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二元论的叙事话语,把多个少数民族的神话包括北方民族的萨满神话和南方各民族的神话纳入了研究视域。在阐释创世神话时,他运用了布依族的《力戛撑天》、壮族的《布洛陀》、布朗族的《顾米亚》、哈萨克族神话《迦萨甘创世》等丰富的资料。我国各个民族的神话产生于多样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历史形态与别样风俗的情境之中。值得探讨的是,我国多个民族都有盘古神话、女娲神话,如果起源于一地,广泛传播的路径什么?传播的动力何在?如果起源于多地,那么为什么多个地域会产生同样的母题?这正是中华神话研究的整体观要阐释的问题。1907年,杨度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他认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①光绪三十三年 ( 1907)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金铁主义说》是他1903年发表在月刊上的一篇主题文章。中国神话整体观的树立,不仅有益于神话本体研究的拓展,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标识之一。
神话是原始社会的遗响,其与原始社会的语言与宗教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中,他涉猎原始社会的祭祀、巫术、占卜、预言等文化范畴。只有这样,才能解开神话神秘的面纱,还原其历史的真面与文化的真面,同时这也为探索中国神话的文化基因做好铺垫。作者认为,祭坛就是神坛,神话往往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在祭祀神祇时的语言表述。在分析鸟神话时候,作者谈到鸟生神话与太阳崇拜的关联,并且引用《尚书.尧典》“寅宾出日”之礼的记载说明神话于祭日仪式的存在。是时,关注神话与仪式的关系的学者尚少,作者凭借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把神话的阐释置于古代的仪式之中。这可以深刻阐释神话在原始生活中的功能和价值。芬兰民间文艺学家劳里·航柯于20世纪70年代在《神话界定问题》一文中谈到界定神话的四条标准——形式、内容、功能、语境时说,除了语言的表达形式外,神话还“通过其他类型的媒介而不是用叙述来传递”,如祈祷文或神圣图片、祭祀仪式等形式。②[芬兰]劳里·航柯:《神话的界定问题》,载[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65页。神话不是讲述的,而是肢体行为,具有渴望的情感并希冀得到可期的目的。刘先生对九尾狐神话的研究别出心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把郑州新通桥和山东嘉祥洪山村两个地方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的九尾狐形象与文献《汲郡竹书》《吴越春秋》的记载相对照,认为在西王母面前的九尾狐是一个沟通天地的巫师。这样得出的结论非常新颖,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他在对我国神话母题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寻求出世界不同生态环境中产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神话母题,另一方面努力分辨中国神话与他者的差异性。例如在阐释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取火神话、洪水神话时,都与其他地域的神话做了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寻求我国神话的特殊性和本源意义。在取火神话中,中国神话不是去天上盗火,而是钻木取火。在分析洪水神话时,他认为,我国与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有相似的避难母题,但还存在世界其他地域不存在的洪水之后再造人类的母题。他认为,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洪水神话中别立一型的。这位民间文化学者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石上,往往使用国内外的大量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其与芮逸夫提出的“东南亚文化区”概念是相契合的。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极具东方特色,对认识亚洲文化史上的神话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揭示了我国原生态神话的本土知识和本土特征。
神话研究之所以被学术界认为是“迷思”,除了“迷思”是对myth的音译,还因为神话叙事具有象征的意义。恩维特·卡西尔将神话定性为“表达符号形式”,他认为只有揭示神话的象征意义,才能理解神话的价值。刘锡诚认为象征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文化模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他有专著《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问世。1996年在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民俗文化国际研讨会”之后,他与游琪女士出版了论文集《葫芦与象征》,讨论的是中国葫芦神话的象征意义,这本书具有广泛的影响。得知美国召开了葫芦神话研讨的国际会议,东方文化研究会认为,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农耕大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世界交流,显扬自己神话的民族精神。在《禹启出生神话及其他》这篇论文中,刘锡诚先生运用汉族的典籍,同时充分利用了佤族、哈尼族、壮族等民族的当代口承神话,阐释了禹启出生于石头的神话背后的象征意义。他认为石头是母体的象征,是生殖的象征,是在奇异的分娩之后已经失去了旧日权力的母系氏族的象征。卡西尔认为,在神话思维中,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①[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神话思维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往往混淆为一。这属于原始思维的范畴,也称为互渗思维。石头和葫芦都是母体的象征,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刘锡诚先生提出,石头是已经失去了旧日权力的母系氏族的象征。虽然这一结论尚缺乏论证,可能会引起争论,而争论是更为接近真知的开启。刘锡诚为白庚胜的《东巴神话象征之比较研究》撰写了序言。他认为,白庚胜对于东巴神话的象征研究超越了民族志的记述和田野工作的简单分析,促进了研究者对方法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们应该借鉴象征的理论,探索神话叙事背后的文化意义。
《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的下篇是对于近代和当代中国神话研究的学术成果的评述,其对我国神话学大家的梳理和综括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同时也书写了他以探索神话为维度而寻求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心。
早期涉猎神话学研究的顾颉刚、闻一多、黄石、丁山、茅盾、芮逸夫等前辈开启了我国神话学建构性的研究。刘锡诚先生指出,中国神话与中国古史混杂在一起。一方面,他认可中国神话的史学特色的独有;另一方面,史学特色又不是他唯一的研究维度。他站在神话学史的高度评述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观。顾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若以建构的角度观,恰恰就是将 “时序错乱”“真伪混杂”的中国古代历史,重新理顺归位——“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②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 273 页。顾颉刚先生早期孜孜不倦地疑古、辨古,欲通过古史辨伪的工作推翻“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一以贯之的高度同一、统一的中国史观,质疑“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①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年7月1日),《古史辨》第一册,第 96—101 页。他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②同上,第99—101页。刘锡诚先生站在探究民族精神的高度评估了顾颉刚先生对我国神话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他认为,顾颉刚先生以渊博的学问在古史“辨伪”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古史学术探索和论争中,阐述了自己的完整的神话理论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创立了一套神话学学术体系,并在顾颉刚的带动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神话研究的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
对茅盾先生关于神话研究的评述中,他指出,茅盾关于神话本质的论述,显然有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子。这无疑应是“重构”中国神话学所要借鉴的。建立中国的神话学派可能要借鉴西方的神话,在接纳、包容西方各个神话学派理论的同时,刘锡城强调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学者研究的视域而探讨中国神话。我国神话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与文化特征,我国的神话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我国的神话学研究也完全可以称为学派,因为近代中国神话研究的成果具有可供借鉴的独特的研究视域、独特的研究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为后学者提供宝贵的借鉴。当然我国的神话学研究能否构成学派要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可,但是这是作者深虑的结果,也是为探究神话与民族精神所做的学术支撑。1990年以来,对于近代神话大家进行研究的论文有之,但对这批神话学大家做系列研究的成果却少见。
论文集下篇还包括关于当代有成就的神话研究者的评述,包括张振犁、潜明兹、萧兵、何新、叶舒宪、杨利慧等学者。刘锡诚给予张振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调查的“中原神话现象”及相关著作极高的评价,他为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保存至今的神话的古朴持久的生命力而拍案惊喜。同时,他充分肯定了萧兵与叶舒宪的科研成果。他认为两位的神话研究成果的思路都是以跨文化研究和原型解读方式重构和复原失落了的古神话,这样的思路与以往的考据法有别,开拓了我国神话研究的新思路。他还指出,叶舒宪与萧兵的不同处在于并不停止在神话的重构(构拟)上,而是希图沟通中西学术研究方法,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背景上建立中国的比较神话学。
本书下篇的另外一组文章,包括《20世纪中国神话学概观》《民俗学神话学:过去、现在和未来——2006年10月2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神话学百年与中华民族精神》等,都是对中国神话学历程的梳理和研究。其研究的框架同样具有宏阔的视野,其评述对象不仅包括中国百年神话学进程中具有卓越贡献的大家,也包括近40年来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后起之秀。通过对神话学百年研究历程的概括,他在继续探讨中国本土神话的内容结构及文化特征。在这组文章中,他再三强调,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最终探索的目标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而在民族精神的发掘与重构中, 神话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象征。民族精神是民族延续最根本的基因,民族基因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
回顾百年神话研究的历程,对于什么是民族精神他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族群融合而成的多民族国家。……从20年代夏曾佑到40年代徐旭生提出华夏民族是由古代华夏、苗蛮、东夷三大集团融合组成的以来,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也就是说,华夏民族、或后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大量的中华古典神话和后来发掘采集的口传神话都显示,神话的文化精神或民族精神是生生不息的……我们的神话学者有责任阐明神话的这种生生不息精神。”我国神话的代表作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都是生生不息精神的显扬,其折射出在中国黄土地的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农耕大国民族精神和文化气派。
神话学是一个涉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以及民间文学的交叉学科。为了阐释和认知“迷思”(神话),学术界展开了“多重证据法”的讨论。其源头要追溯到大学者王国维。刘锡诚先生在研究神话的时候也采用了多重论证的方法。其中包括历史典籍、笔记杂记、考古资料,包括汉代画像砖、古老的岩画、陶器的多种纹饰等,特别值得赞叹的是,他还利用了自己调查或者他人调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他把古典的与活态的、考古的与搜集的、纹饰的与记载的一览尽收,经过分析、比较、质疑而后阐释,尽力得出科学的结论。在研究“葫芦生人”的神话意象时,他甚至运用了学术界对于很多学者感到生疏的沧源岩画为佐证。在《世界树神话》的阐释中,作者运用了山东的画像砖及三星堆出土的“神树花果”的文物为佐证。这部成果重视民族志调查中所获得的可贵的多个民族活形态的资料。叶舒宪认为,多重证据并重的过程,其内在的精神取向就是,破除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态度,以开放的心态大胆地沟通中西,从而“变单向的移植与嫁接为双向的汇通与相互阐发”。①叶舒宪:《中国神话学百年回眸》,《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作者的目的是通过多重证据之间的“间性”,揭示被文字符号所遮蔽的文化之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叶舒宪的著作《中国神话哲学》和《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以神话-原型理论为依据, 对于中国神话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和《空寂的神殿》也相继登上神话研究的舞台。前者探索了神话含蕴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民族精神,后者从文化哲学和神话哲学的角度开拓了研究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之关系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刘锡诚先生再次提出“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的论题。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一直追问的就是“从哪种意义上来说,神话具有价值?”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107页。毫无疑问,这也是作者追问的问题。神话的价值在于民族精神的追问,追问的目的是寻找现代人建构精神家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