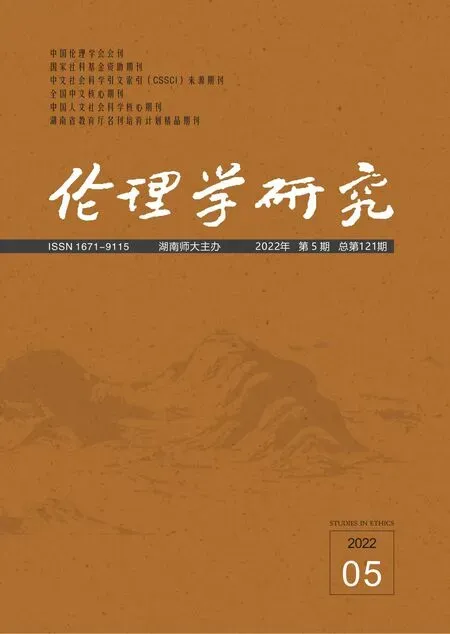自律与公共权威:康德政治证成的伦理向度
黄 各
导 论
政治证成性(Political Justification)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源于如下两点:其一是它能够对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充分的论证,即“可以表明政治秩序能够被视为是有价值的,或者证明国家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1](178);其二是它能进一步对国家和个人的道德关系进行梳理,并对前者是否具备公共权威,即能否“成为其受众(subjects)义务的施加者,并运用强制来推行这些义务”[2](746),进行合理说明。约翰·西蒙斯(John Simmons)等人为了更加清晰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把握,还进一步对证成性(Justification)和正当性(legitimacy)进行了严格的概念区分①很多时候,学者们为了充分说明其观点,都会对概念进行不同意义上的区分。西蒙斯区分这两个概念的目的也是想为其洛克式的“基于同意的正当性观念”进行辩护,并最终捍卫他“哲学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因而,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认可他的概念划分方式,但他对这两个概念所作出的思考却可以激发我们对政治哲学中“元问题的思考”。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进行范围上的界定。此外,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在学界还有一些争论,但在此文中,笔者仍然沿用学界惯有的区分,即用证成性来指代justification,用正当性来指代legitimacy。,以此来为各自的观点辩护。由于这一话题涉及政治生活的核心命题,因而从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神话,到中世纪的高级宗教,再到启蒙时代的理性辩护,人们对其探索从未停息。
近现代以来,学界往往将政治证成的工作与17—18 世纪伟大的政治著作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具有社会契约传统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等人的著作相关联。这些著作中对自然状态的讨论、对公共权威的论证以及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说明,都可以更好地激发研究者们就政治证成的模式、方法与原则进行探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三人都被称为是社会契约论者,但无论是在立论基础、论证方式还是实践指向上都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康德,目前学界对他是否能够归类到社会契约论阵营还存有一定争议①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我所提出的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如在洛克、卢梭、康德那里发现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此外,威廉姆斯和莱利也在其著作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参见WILLIAMS H,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Blackwell,1983,p.94;RILEY P,“On Kant as the most adequate of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ists,”Political Theory,1973,pp.450-470.但在奥妮尔看来,康德法权的原则没有明显提到同意,其也没有把它确立为社会契约的原则。他的很多关于国家权力的合理性的著作,也几乎没有提及社会契约概念。参见O’NEILL O,Constructing Authorities:Reason,Polit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s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171.。康德自己也曾指出:“[公民契约]与任何别的契约(这种契约同样是指向随便某一个必须共同促成的目的的)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其奠立的原则上,却与所有其他契约都有本质的区别(8:289)。”[3](290)②本文中所引用的康德著作,主要参照盖耶(Paul Guyer)和伍德(Allen Wood)主编的剑桥英文版《康德全集》(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参考文献中直接标明的是此版本的页码,而正文括号中标明的是德文科学院标准版《康德全集》的卷数和页码。汉译本则参照李秋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
因此,康德的契约论有何独到之处,其所依赖的奠基性原则是什么,以及它又可以为现当代关于证成性和正当性的探讨提供哪些思想资源,就成了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本文中,笔者首先从康德对国家正当性的讨论出发,分析他对国家(立法者)与臣民之间的权利义务持什么看法,并呈现出他与霍布斯观点的差异;接下来,笔者通过探讨康德政治证成的一个关键要素——公共法权理念,试图呈现康德式(Kantian)证成模式与洛克式(Lockean)证成模式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明晰康德法权状态的基本要求与指向;最后,笔者借助康德道德自律观念所表征的公共性旨趣来论证其政治证成所蕴含的集体自我立法特征,并对这一具备伦理向度的奠基性原则进行合理说明。
一
康德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路主要体现在《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1793)一书的第二部分——“论国家法权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驳霍布斯)”中。在那里,他首先指出:“共同体中的所有人是按照自身即目的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结合只能见诸一个处在公民状态,也就是说构成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之中(8:289)。”[3](290)接下来,他强调了出于自身目的结合所形成的共同体需要受到公共强制性法权的约束,以使每个人都免于受到其他任何人的侵犯。以此形式建立起来的公民宪政体制,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合法自由。因而,这一体制需要恪守如下三个基本原则:第一,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的自由;第二,社会中作为臣民的每个成员与每个他人的平等;第三,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的独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些原则不仅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所立的法,而且唯有依据它们,才有可能按照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建立起国家(8:290)”[3](291)。
因而,在康德所设想的国家和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需按照如下三个程式(formula)来行动。首先是基于相互联合的意志来追求普遍的幸福和自由。在他看来,“没有人能够强迫我按照他的方式去得到幸福,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沿着他自己觉得恰当的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损害他人追求一个类似目的的自由(亦即他人的这项法权),这种自由是能够按照一种可能的普遍法律与每个人的自由共存(8:290)”[3](291)。这即是说,康德所提出的政治体制并非一种父权制的专制主义,而是一个祖国政府(imperium non paternala,sed patrioticum)的体制。在其中,每个人通过共同的意志来保护共同体的法权,而不是让共同体屈服于自身无条件的意愿。其次,除元首外,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对任何其他成员拥有强制性法权:“他有权去强迫,而使自己不屈服于一个强制性法律(8:291)。”[3](292)这亦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其设想的体制中,除了元首可以不受约束并享有执行权以外,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不可能对另一个成员拥有生而具有的特权,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最后是用公共意志来强化国家所施加的法律所具备的权威性。康德强调:“一项公共法律为所有人规定对他们来说在法权上什么是允许的或者不允许的,则是一种公共意志的活动,一切法权都从公共意志出发,因此它自身必须不能对任何人行事不义(8:294)。”[3](294)
如上三个程式(外在的自由、平等、所有人的意志统一)的齐聚构成了康德国家或者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它规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特殊的意志能够为这个共同体立法,人们只能出于普遍联合的意志而立法。康德也将这一立法形式称为“源始的契约”(contractus originarius),并认为它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应当被视为提供实践指导的理性的纯然理念。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康德进一步提出了其政治正当性①在这里,笔者沿用了西蒙斯对正当性所作的定义,将其理解为:国家与国民之间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上的关系,即国家因何让国民遵从责任,并如何用强制力来推行这些责任。的基本方案:“每个立法者要如此颁布自己的法律,就仿佛它们能够从整个民族的联合起来的意志中产生出来,而且每个公民只要愿意是公民,就如此看待他,仿佛他一起赞同了这样一种意志(8:297)。”[3](296)由此,人民是至上的统治者,政治正当性的权威来自人民整体,其不能对自己作出决定的事,立法者也不能作出;同样,人民对于元首也没有强制性法权。
因而,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寻找到康德要将其政治正当性理论与霍布斯的理论区分开来的原因。这首先体现在人们因何走出自然状态的区别上。在霍布斯那里,人们走出自然状态,让渡自身的权利给国家是基于每个人自我保存的需要。若不如此,“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就会一直持续。而在康德那里,人们走出自然状态并非基于霍布斯式的慎思理性,而是需要一个纯然先天立法的前提——所有人普遍联合的意志。在此意志的作用下,才能确立起普遍性规范,以此保障每个人基于法则的自由。瑞雷(Patrick Riley)对此就有十分精辟的概述,他认为:“霍布斯式的政治正当性是源于意愿性的同意,这也是契约和协定的本质,他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有意识产生的行动准则和通过外部引起或决定的行动本身。而康德则认为道德活动不能存在于通过偏好决定意志的对象中,也不能存在于自然冲动中,它只能存在于意志为使用自由而制定的规则和准则之中。”[4](142)
其次,康德认为,人们离开自然状态进入共同体中,需要放弃自己的外在自由,并在共同体中依靠自身立法的意志重新获得自由。在霍布斯那里,“基于保障和平、安全等福祉来证成的公共权威具有无限的强制力,很可能最终以消解每个人所具有的平等自由为代价”[5](20)。由此,国家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利维坦,其元首具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很可能会对其受众的自由进行剥夺。与此同时,康德继续强调,国家公民有权对统治者指令中对共同体有不义之处的东西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故此,他分外看重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因为,通过言论自由所塑造的臣民们的自由思维方式,可以让他们在尊重和热爱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的宪政律法限度内行动。而且各种言论也自行相互限制,以便它们不丧失自由,成为人民法权的唯一守护神。而“霍布斯所认为的国家元首并不因为契约而受人民任何约束,并且不可能对公民行事不义(他可以任意差遣人民)。这一命题在总体上就是令人恐惧的(8:303-4)”[3](302)。
在一年后出版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中,康德进一步用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理念来表征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对权利的诉求,并使之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理念彰显了理性的权威性,而非权力的权威性,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也是基于此,才能在公共领域内恪守协议和约定。因而,康德借助这一理念,让理性的统一在整体世界范围内被公共运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理性观念所塑造的政治权威不仅能够担当其维系政治稳定性的重任,而且能够为自身设定追求世俗秩序统一性的政治理想。”[6](66)而在《走向永久和平》(1795)中,康德还对国家的体制结构作了更为清晰和简洁的表述:“每个国家中的公民宪政应当是共和制的。首先依据一个社会的成员之自由的原则(作为人),其次依据所有成员对一个唯一的共同立法之附属性的原理(作为臣民),再次依据这些成员之平等的法则(作为国家公民)所建立的宪政——由源始契约的理念所产生、一个民族的一切法权立法都必须建立于其上的唯一宪政——就是共和制的宪政(8:349-50)。”[3](322)
总的来说,在康德所设想的国家体制中,立法者(国家元首)与其臣民都处在一种普遍意志的联合中,它要求:第一,构成共和政体的基本宪法必须要求个人的自由;第二,臣民共同依赖或者服从的法则;第三,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不过,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这种视角下,人们又是为何要选择进入到联合所有人意志的共同体之中,并由此确立起彼此间的责任与义务呢?
二
如上所述,“自然状态缺乏合法的公共权威,从而无法保障各方具有恒久性、确定性的所有权,唯有联合意志才具有普遍立法功能,并经由确立公共法权拥有合法的强制权限,由此能够加于每个人对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行动基于公共承认基础上的相互责任或法权义务”[5](19)。因此,康德分外强调人们必须要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法权状态的重要缘由即在于:自然状态一是不具备公共权威的资格,无法在权利产生分歧的时候有合法的强制力进行裁决;二是其所产生的权利(生而具有的法权等)并不能得到最终的确证。因而,这一状态无法保障人们所有权的基本法则,进而无法实现人类共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既是其政治理想的核心要素,也是完成政治证成性的根本保证。早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中,康德就对这种自由进行过说明,在他看来:“一部按照使得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法律而具有最大的人类自由(不是具有最大的幸福,因为最大的幸福将已经自行接踵而至)的宪法,毕竟至少是一个必要的理念,人们不仅在一部国家宪法的最初制定中,而且就所有的法律而言都必须以这一理念为基础(A316/B373)。”[7](397)
正是在此自由理念的作用下,人们意愿进入到法权状态中,并基于公共承认的相互责任确保每个人享有平等的价值。如康德所言:“既然一切法权都仅仅在于将每个他人的自由限制在其自由能够与我的自由按照一个普遍的法律共存的条件上,而且公共法权(在一个共同体中)仅仅是一种现实的、符合这个原则的并且与权力相结合的立法的状态,由于这种立法,所有属于人民的人都作为臣民处在一种一般而言的有法权的状态之中,亦即处在一种依据普遍的自由法则相互限制的任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状态中(8:292)。”[3](293)
在《道德形而上学》(1797)的“法权论”部分,康德更明确地对这种法权状态进行了规定:“法权状态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着一些条件,唯有在这些条件下,每个人才能分享他自己的法权,而这种状态的可能性的形式原则,按照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就是公共的正义(öffentliche Gerechtigkeit)。”[3](450)据此定义,他还进一步区分了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人为状态(status artificialis)与公民状态(status civilis),并认为只有公民状态才能被称为公共法权状态。通过这一状态,康德引出了其关于国家必要性的论证,他指出:“公共法权是对于一个民族亦即一群人而言,或者对于一群民族而言的一个法律体系,这些民族处在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之中,为了分享正当的东西而需要在一个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意志之下的法权状态,需要一种宪政(constitutio)。单个的人在民族中彼此相关的这种状态,就叫作公民状态,而这些人的整体与其自己的成员相关,就叫作国家(civitas),国家由于其形式,作为通过所有人生活在法权状态之中这一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被称为公共体[广义的国家]。国家就是一群人在法权法则之下的联合(6:311,6:313)。”[3](455)
在这里,我们又可看到康德与另一位社会契约论者洛克,在政治证成性方面的差异。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自由状态,但却不是一种放纵的状态,只是某种形式的人际关系[8](480)。若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自然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办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平,并防止外人的侵犯(sec 95)”[9](59)。因而,国家(公共法权状态)是非必需的,如果人们在国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那他们可以退回到自然状态中,因为这并没有伤害到其余人的自由。而康德则认为,国家的证成性(justification),即国家对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实现的必要性蕴含了一种进入公民社会并接受社会所强加的责任的义务。康德打算同时用这种证成性约束我们每个人去服从自己国家的法律,来使具体的国家合法化①西蒙斯同样认为,在康德那里,所有人都对自由拥有一种天赋的权利,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只是具有暂时的权利。只有在公民社会中,这些权利才能得到尊重并被享有。由于权利与他人尊重它们的义务相对应,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种义务离开自然状态并接受强制性法律统治下的公民成员身份。。
从这二者的对比中,我们看到,公共法权状态在康德对国家的证成策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权论导论”中,他还对法权作了明确的阐释:“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与另一方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6:230)”;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普遍法权原则为:“如此外在的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6:231)。”[3](388)因而,在康德的意义上,公共法权状态其实是要让个体依照联合立法的意志确立起法权的普遍原则,并经由共通的自由法权明确共同体中每个人的交互性责任,进而实现最大限度上的平等自由。这种彼此之间相互负有责任的关系与达沃尔(Stephen Darwall)所提出的第二人称立场(我—你的视角)有些类似,尽管达沃尔本人对此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②达沃尔指出,康德道德哲学更多体现的是第一人称的立场。行动者仅仅基于个人的立场而进行自我立法,其关于自律和道德义务的阐释是失败的。相关论述参见DARWALL S,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Morality,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44.。但他对共同体成员间相互要求的表述其实已经暗含了康德法权状态的基本立场:“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来源不是一个人希望或更愿意所有人做什么,而是一个人期望别人做什么,以及我们会同意任何人能够向作为相互负责的平等共同体成员提出的要求,这即是我们对彼此负有责任。”[10](34)那么,在康德意义上的法权状态中,具体到每个行动者,他们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资质与条件,或者说其行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三
我们知道,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中,康德用其特有的自律观念奠定了道德基本原则。在他看来,这一观念能够确立先天的道德法则,并使人们遵从定言命令式的规定,积极履行道德义务。由此,在很多现当代康德主义者眼中,道德自律观念能够使行动者进行自我立法,并以“一种人际间的一致性来选择自身目的”[11](7),从而进入到相互间具有责任的法权状态之中。罗尔斯(John Rawls)即认为,基于自律的独特的人观念是康德式建构主义的独特之处:“一种康德式的学说把法权(justice)的内容与一种特定的人观念联系起来;此观念将人视为既是自由又是平等的,且有能力合乎情理地以及理性地行动,并因此有能力参与到如此构想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中去。”[12](518)奥妮尔(Onora O’Neill)则更为直接地认为,定言命令式中的自律观念是康德完成政治证成的关键,它与如下三个递进的主张高度相关:“第一,定言命令式是实践理性的最高原则,因而也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原则;第二,法权普遍原则陈述了定言命令式的一个限制在公共领域的版本;第三,社会契约的共和主义概念是法权原则的特殊情形,适用于特定的历史境况。”[13](180)
因此,很多学者将康德的自律观念延伸为集体的自我立法,并以此来确立其政治证成中的公共权威。瑞思(Andrews Reath)指出:“当自律被看作是一种对自己制定可普遍化准则的能力时,关于自律的问题就变成了权威性质的问题。在政治领域中,立法权威的标志是通过行使自己的意志为他人创造理性的能力。因而,任何成功地为自己立下普遍有效实践原则的自律行动者都可以同时被所有其他自律行动者视为拥有与他们相关的立法权威。”[14](228)这一论断即是指明了如何从个体的道德自我立法中推证出集体立法的公共权威性的关键所在。不过,这种建立在个人道德自律基础上的论证模式也会引发一定的质疑。弗兰克舒(Katrin Flikschuh)即认为,自律立法者的共和王国并不是一个可信的或者有吸引力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只与伦理上的善良意愿有关……定言命令式只能是自我立法的原则,而不是他人立法的原则。我们不能向其他人规定采取什么样的意志原则,而是只能自问,我们对自己主观准则的评判是否能够被其他人所采纳。”[15](177)
但我们认为,弗兰克舒的这一论断同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一样,对康德自我立法概念进行了误读①弗兰克舒虽然在后续的论证中指出,康德和卢梭所持有的自律观念对个人自律有所超越,但其在分析过程中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现当代自由主义的阐释。而且,他对于自我立法的解读是单向度的,只是通过意志给自己订立法则。而康德的自律观念表明,在每个为自己立法的成员所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公民就应当既是法则的制定者,又是其臣民。在此基础上才能构成共和政体的基本概念。,并模糊了个人自律(personal autonomy)和道德自律(moral autonomy)之间的差异。因为“个人自律仅通过强调人们的自由选择,弘扬了一种以自我主导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这显然与康德彰显纯粹实践理性自我立法的道德自律所截然不同”[16](171)。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其实已经用定言命令式的三个公式②关于定言命令式的种类与数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我在这里采用的是詹姆斯·帕通的分类方法。具体参见PATON H J,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A Stud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Hutchison &Co.,1947,pp.129—198.来表征了自律以及自我立法的运作机制。于他而言,这三个公式表达的内容各有侧重点:普遍法则公式基于一个定言命令式的纯然概念,引导人们去寻求建立道德原则的权威。人性目的论公式将理性本性视为在所有道德原则之后的基本价值,“它以最基本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要成为道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其他人”[17](205)。这两个公式的结合最终指向自律及目的王国公式,自律亦是人的本性和任何有理性的本性的尊严的根据。人们由此能够通过把自己和他人当作目的而得来的敬重感赋予到自身的意志中,以此来完成对道德法则的遵守。
因而,康德式自我立法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理性将普遍立法者的意志与我们自身行动的意志相关联的实践必然性,而不是自己所立之法。这种对于自身来说的立法,是实践理性在积极层面上的自由,它是通过道德法则约束人们的理性来实现的。它表达了道德法则不是被偏好或者外在决定所规定的。正如森森(Oliver Sensen)所言:“如果它是一个能够与道德法则相联系的理性,那么道德法则能够通过外在的决定而成为无条件的。自律的意义即是,它使道德成为自身种类的立法。”[18](270)
康德强调,“自律的概念与自由的理念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而德性的普遍原则由于与自律概念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德性原则在理念中为理性存在者的一切行动奠定了基础(4:452-3)”[3](99)。因而,自律的人格力量乃是实现普遍法则与每个人平等自由内在契合的前提条件。正是在此基础上,所有人才能走进他所谓的目的王国③有学者指出,只要每个人都是理性存在者就能设想一个共同意志,大家都遵守这个普遍的法则就能确定法权范围,以此使所有人的任性能够共存。但我们认为,首先,目的王国公式所表达的意图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理想的道德理念,而是在结合前两个公式的基础上,表征了自由联合的价值向度。其次,康德的政治法权并非只是针对人们的外在行为。外在行为论只是基于“法权论”中初始根据的讨论,而未能结合“公共法权”部分以及整个实践哲学的背景,从而并未清晰呈现出合法强制中各方基于公共承认的道德义务。:“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无论它所服从的是什么样的法则,都必须能够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因为正是它的准则对普遍的立法的这种适宜性,把它凸显为目的自身;现在,一个理性存在者的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理知世界)],作为一个目的王国,就以这种方式成为可能,而且是通过作为成员的所有人格的自己立法。”[3](87)
因而,自我立法并非仅仅出于自我立场确立道德法则,而是基于共同意志确立自身行动的准则。这也是定言命令式中人性公式所彰显的价值取向。每个把自身及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的理性存在者,能够经由联合意志的普遍立法而走进法权状态。在此当中,每个人的自由价值才能得到保障和持存。科斯嘉(Christine Korsgaard)即说明了:“作为目的王国中的一个公民,我必须使你的目的和理由成为我的,因而我也必须用一种它们能够成为你的方式来选择我的目的和理由。”[19](192)只有共同体中所有公民因为共通的自由法权而包含在交互性的责任之中,一种具备集体属性的自我立法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在康德那里,“只有这种形式才使得自由成为原则,甚至成为一切强制的条件,强制是国家本义上的法权宪政所必需的,并且即便在字面上也被最终引导到这种宪政……一切公共法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才能永久地给予每个人他自己的东西(6:340-1)”[3](480)。
由此,康德公共法权状态得以证成的几个核心要素(交互责任、立法意志和平等自由)体现出的其实是自律观念的公共性价值,这也是其政治证成中从个人道德立法到公共权威推证的关键所在。正如他所言:“国家通过三种不同的强制力(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而拥有其自律,亦即按照自由法则自己塑造自己和维护自己。国家的福祉就在于它们的联合……人们需要把其理解为宪政与法权原则最大意志的状态,理性通过一个定言命令式使我们有责任朝着这个状态努力(6:318)。”[3](461)
结语
由于政治证成问题的复杂性,康德所提供的这种模式同样会受到质疑,并引发诸多争论。比如,洛克主义者指出,康德以及现当代的康德主义者似乎在对政治证成性的解释上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通过采取这种立场,它评价制度的维度就被冲淡了,而且变得片面。因为大多数康德主义者的工作都是通过对“合情理的人”这一概念所持的一种独特看法来完成的。而“喜欢孤独与独立胜过喜欢合作,这并非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当代康德主义者对合情理的人的看法似乎被植入了太多的道德内容,而且对此又没有过多论证”[2](765)。政治自由主义者亦会质疑,“一个政治上自律的人将如何回应这样的指控,即他如果接受了他所不想接受的公共法律的话,这是否等于背叛了他的个人自律?”[15](188)
但在我们看来,康德自律理念所蕴含的公共性特征与其法权状态所体现的相互负责理念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些挑战和争论。而且在康德那里,道德自律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般的存在,而不关乎每个公民个人的、现实的合情理性和可接受性。正如伍德所言,“康德并不认为国家是建立在其成员之间的实际契约上的。于他而言,原初的契约反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纯粹的理性观念),只有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我们才能考虑国家的正当性”[20](176)。因而,纵使康德的理论有不完备之处,但其却为一种将道德、法权和政治相互融合的整全式(comprehensive)证成模式提供了可能。这要求人们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契约来构建基本法权规范,而是要以道德上的自由和德性中的完善作为最终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只有如此,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才能形成联合而统一的意志,并由此呈现出兼具平等自由、交互责任和立法意志的政治正义状态,从而更具普遍性地彰显出具有公共立法能力的道德自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