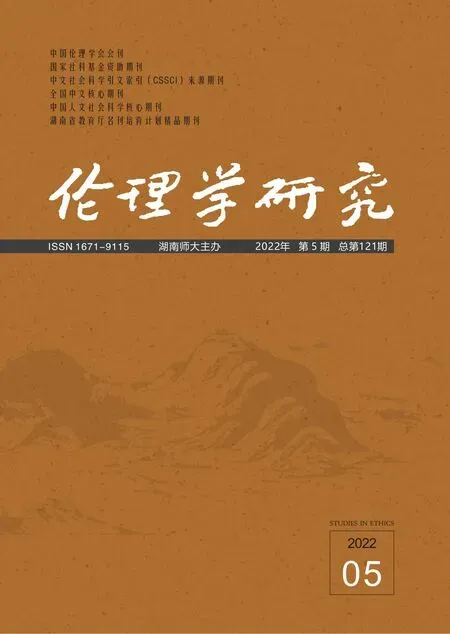伦理与道德:谁是优先战略
樊 浩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不仅是礼仪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在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中,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理论也一直处于欧风美雨冲击的前沿,其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话语、理论和战略中的“无伦理”。无论在伦理学理论还是在伦理道德发展的实践上,“道德”似乎已经取得话语独白的文化霸权地位,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伦理”才作为“道德”的陪衬人或替代性概念在潜意识中偶然出场。“无伦理”不仅潜存现代中国伦理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被同化而面临集体失语的学术风险,而且也是生成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诸多现实困境的重要文化战略误区。根据我们所进行的持续十多年的全国调查的信息,中国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是伦理型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发展遵循与西方宗教型文化截然不同的哲学规律。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首要文化战略,应当也必须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战略。
一、“一体—优先”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战略
这一文化战略有两大要义——“一体”和“优先”,“一体”意味着不是抽象的道德,而是以伦理与道德的辩证互动建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优先”意味着“一体”不是平分秋色,在伦理与道德之间,伦理是战略重心,具有优先的精神哲学地位。这一战略的问题意识是现代伦理学理论和伦理道德发展中“道德”的话语独白和抽象的道德主义,正因为“伦理优先”它才成为“伦理型”而不是“道德型”文化的战略。
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一以贯之的最具标识意义的文化战略和精神哲学理论,这一“中国经验”在传统伦理道德发展中从三个方面得到历史演绎。其一,“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根源性和延绵力的话语,在文明的童年就是由原初社会通向文明社会的一根文化脐带。《论语·季氏》所谓“不学礼,无以立”说明“礼”是“学”与“立”的根本,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学问,孔子向老子求教,问的就是“礼”,“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就是孔子由“学”礼到“立”于礼的精神史进程。礼的哲学本质是什么?是“伦理实体”的中国话语与中国表达,准确地说是血缘、伦理、政治一体贯通的伦理实体。所谓“孔孟之道”在精神哲学形态意义上就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与孟子“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的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范式的一脉相承之“道”,这一精神哲学范式和文化战略在日后几千年的文明演进中不断转化创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礼仁一体,被孟子展开为“五伦四德”,在大一统的进程中被约制为“三纲五常”的名教,到宋明理学则被提升为形而上的“天理”。其二,这一精神哲学规律以某种文化自然律和文化必然律的方式呈现。轴心时代老子与孔子同时诞生,儒家与道家自古至今是中国人精神基因中的一对染色体,然而是儒家而不是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宗,历史现象学的这种图景隐喻两大文化选择规律:儒家与道家共生演绎伦理与道德一体;儒为主流隐喻和诠释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论语》以伦理为重心,贡献人伦原理,《道德经》以道德为重心,提供形上道德智慧。其三,正因为如此,无论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批判,还是后来的文化觉悟,都首先指向伦理而不是道德,陈独秀“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以终极批判的方式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
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文化战略是基于两大中国经验的文化规律和文化自觉: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而非西方“states”文明的文化规律;伦理型文化而非宗教型文化的战略气派。前者使中国走上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以伦理组织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化道路;后者使中国文明具有“不宗教”的文化气派,“以伦理代宗教”。在任何文明体系中,家庭与国家都是两个最基本的伦理实体,然而在中国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中,如何建构家国贯通的伦理实体的体系是文明的基本课题,如何由家及国地建构个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也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首要课题。《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就是中国“国家”文明的伦理型文化战略的体系化的哲学表达。作为“大人之学”起点的“格物”之物,是伦理道德之物,它以“身”的主体性建构为中枢,递次指向知、意、心的道德主体和家国天下的伦理实体。伦理实体是“大学之道”或“大人之学”的终极目标,所谓“修齐治平”就是在家国天下伦理实体的不断建构中达到的个体道德的完成。伦理实现、道德完成的伦理与道德的统一,就是《大学》“止于至善”的“至善”境界,这一境界的根本要求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从实体出发”,即以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的伦理实体的建构为终目标,于是“大学之道”才“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这个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理论体系和战略系统中,“天下”是最具中国标识的伦理实体,它是由家及国的家国一体所生成的非家非国又即家即国的文化意义上的伦理实体,“平天下”之“平”的精髓是通过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达到的“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家”的伦理实体,是由伦理努力达到也是伦理意义上的“平”,因而是具文明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最彻底的“平”,“平”就是伦理实体性的中国话语。在states 的西方文明传统下,不仅所谓“coutry”是诸“state”的“united”,而且个体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也是黑格尔所说的“集体并列”或个体的“united”,因而道德而不是伦理处于优先地位,于是在“united”的“集合并列”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下,追求个体自由的道德与“united states”的伦理认同可能也总是相分离。于是,《大学》以“修身”的“明明德”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亲民”的统一为“至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以道德与幸福的统一为止善。《大学》的至善是修齐治平的伦理与道德一体的此岸的内圣外王之道;康德的至善是借助“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两大公设才能达到的彼岸境界,因而最后精神归宿便只能是“望星空”。
伦理优先与“不宗教”存在某种相互诠释的关系。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金岳霖先生认为轴心时代的最大文化发现是诞生一些“最崇高的概念”,如古希腊的罗格斯、希伯来的上帝、印度的佛、中国的道等,显而易见,把“道”当作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最崇高的概念”有失偏颇。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轴心时代”,如果这个时代贡献了某些“最崇高的概念”,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它不仅是“道”,而且还有“伦”。严格说来,不是“道”,而是“伦”才使中国走上“不宗教”的文化道路,相反,作为以“道”为哲学标识的道家最后却流于宗教,老庄也成为道教之宗。原因很简单,家国天下的“伦”为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世俗而神圣的终极实体和终极关怀,使“不宗教”成为可能和现实。伦、伦理使中国文化与宗教型文化分道扬镳。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就是伦理型文化“不宗教”的战略宣言。
每一种文明都有伦理的构造,只是文化地位不同。亚里士多德开辟了西方文明的伦理传统,然而《尼各马可伦理学》所宣示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取向为后来拉丁化进程中由伦理向道德的型变埋下基因,至康德以“实践理性”为标识的道德哲学的诞生及其高歌猛进,宣告了道德取代伦理的“完全没有伦理的观念”的近代西方传统的最后胜利。黑格尔虽然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建立了伦理道德一体的精神哲学体系,但西方世界故意冷落黑格尔并将他当作死狗打,不仅是一种学术取向,而且是文化基因的自然表达,由此演绎为现代西方文明中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西方伦理道德的文化战略以对普遍准则与绝对道德自由的追求为重心,伦理家园的缔造和精神生命的安顿不是缺场,而是交给了彼岸的上帝。“国家”文明以家与国两大实体为伦理家园,以家与国的伦理实体的辩证互动建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伦理实体既是个体安身立命的基地,也是行为合法性的终极根据和个体的终极关怀,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成为必然和应然的战略选择和文化坚守。
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应然是不断的未然,道德是永远有待完成的任务。正如黑格尔所说,“伦理性的东西,如果在本性所规定的个人性格本身中得到反映,那便是德。这种德,如果仅仅表现为个人单纯地适合其所应尽——按照其所处的地位——的义务,那就是正直”[1](168)。“一个人必须做些什么,应该尽些什么义务,才能成为有德的人,这在伦理性的共同体中是容易谈出的:他只需做在他的环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确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就行了。正直是在法和伦理上对他要求的普遍物。”[1](168)道德就是对于伦理的直道而行,由此可以诠释中国学界曾经长期聚讼的孔子的那个著名命题:“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不少学者批评这一命题是以私德僭越公德。其实无论公德私德,只有在伦理性的共同体中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德是一种伦理义务。邂逅家与国的伦理两难,孔子以“直”肯定亲亲相隐的道德合法性,这里的“直”是父与子在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两种伦理角色发生冲突时所做的“适合其应尽”的伦理性“正直”,孔子所“直”面的是家庭在由家及国的文明体系中的本位地位。在“国家”文明中,家不仅是伦理的策源地,而且是国的基础,如果伦理风尚和道德要求鼓励亲亲相揭,家庭的自然伦理实体必定处于被解构的文化风险之中,最后动摇的是家国伦理实体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亲亲相隐是国家文明体系中的一种重要伦理战略,是冲突背景下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文化战略,具有文明史的意义。“真正的德只有在非常环境中以及在那些关系的冲突中,才有地位并获得实现。”[1](169)“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1](170)离开伦理,离开伦理实体的体系,道德只是“主观意志的法”。
关键在于,必须在精神哲学视野,以及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中才能把握伦理道德的关系及其文化战略意义。黑格尔建立了“抽象法—道德—伦理”的法哲学体系和“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哲学体系,虽然伦理两个体系中的位序不同,但他将伦理道德作为精神世界的两个基本构造并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且一以贯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精神现象学》似乎是一个未完善的体系,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应该有一个由道德世界向伦理世界复归的过程。由此,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体系与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便可以进行文化对话,只是精神哲学的文化形态不同。
二、伦理道德一体战略
根据我们所进行的三轮全国性调查、六轮江苏省内调查的信息①相关调查数据及成果可参看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相关研究成果(https://mdi.seu.edu.cn/hjqk/list.htm),下文亦同。,当代伦理道德发展在文化战略层面遭遇到的最大的中国问题就是“无伦理”。理论上,关于伦理道德的学说被称为“伦理学”,然而无论教科书还是学术著作,一般都把伦理学诠释为研究道德问题的学问,不仅以道德为研究对象,而且以道德为核心甚至唯一话语,伦理学“无伦理”,沦为“道德”的话语独白,在伦理学的学术体系中活跃的也只是道德的明星。既然无伦理,为何名之“伦理学”而不是“道德学”或“道德科学”?答案只有一个,它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本能与文化自觉的学术纠结。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相当程度上代表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战略,“伦理学”是关于伦理的学说,在理论体系上应当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正因为如此才以伦理而不是道德为标识性话语;“道德哲学”相当程度上体现西方传统和现代传统,其中可能“完全没有伦理的概念”,甚至像黑格尔批评康德那样,对伦理加以凌辱。现代中国伦理学在欧风美雨中备受西方道德哲学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内在具有中国文化基因或胎记,形成文化撞击下的学术纠结,纠结的结果,只剩下所谓“伦理学”的话语躯壳,“无伦理”成为伦理学理论的时代印记。更明显也是更深刻的问题出现在实践尤其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战略方面。在实践上,“道德建设”成为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规范性话语,伦理在道德建设中缺场甚至完全被遗忘,于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便只剩下“道德战略”,个体道德似乎成为唯一的对象和内涵。“无伦理”的结果便是调查中所发现的“道德上满意—伦理上不满意”的伦理—道德悖论。道德上满意不只是对道德风尚及其不断进步满意,而且是对价值多元下的道德自由满意;伦理上不满意主要对由此所生成的伦理关系和人际关系不满意。应该说,“无伦理”或伦理缺场是一种跛足的伦理道德发展战略,从以下案例中可略窥一斑。
案例:关于诚信建设。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就是道德信用的缺失,全社会的诚信治理显得尤为迫切,然而随着失信问题被揭露得愈益广泛和深刻,我们猛然发现社会的道德信用度提升缓慢,而伦理信任度却大大下降,甚至出现社会心理上的伦理安全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扶老人难题。自2006 年南京市民彭宇扶老人被讹而成为公众事件之后,到2015 年的十年间仅网络媒体就报道了96 起扶老人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以及社会的关注点都集中于诚信或道德信用②来自东南大学青年学者张晶晶所做的专题信息库统计。。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存在依次深入的三个伦理道德问题:一是“撞没撞”的道德信用问题;二是“信不信”的伦理信任问题;三是“扶不扶”的文明信心和社会风尚问题。社会的兴奋点过多聚焦于撞没撞的道德追责,很少关注到底信不信以及该信谁的伦理信任问题,诚信危机过度渲染的结果是老人跌倒不敢扶、无人扶的文明危机。扶老人难题的严重后果,是一场社会性的伦理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敢扶”的文明信心和文明风尚危机。这种状况有点类似于治疗癌症的化疗,在杀死道德失信的癌细胞的同时,也大量杀伤了伦理信任的优良细胞,形成道德治理下的伦理伤痕,削弱了社会机体的文明体质。
三、伦理优先战略
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文化战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要义就是:在道德风尚的高地上,释放伦理的魅力。伦理与道德,不仅在文化战略中必须同时在场,而且伦理处于优先战略地位。在“后伦理文化战略”中,伦理优先的战略要素有三:伦理认同、伦理公正、伦理关怀。这三大战略要素形成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转化创新的现代体系。
1.伦理认同
伦理认同有两大战略支点:一是坚守“从实体出发”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二是建构坚韧的家国伦理实体和家国情怀,形成“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现代伦理世界和伦理实体的体系。对“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一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的回答必须确立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伦理观和伦理方式,即“从实体出发”。“从实体出发”的伦理精神形态和文化战略表达就是伦理认同,如果以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诊断为问题意识,就是伦理认同先于道德自由。伦理(认同)优先还是道德(自由)优先所对应的问题域不是西方现代理论中的所谓社群主义、个体主义和德性主义等诸流派,而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其核心是伦理实体的认同。在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形态下,伦理认同是关乎文明存续的重大文化战略。“后伦理型文化时代”的伦理认同是三大结构递次推进构成的伦理精神体系和伦理世界体系:家庭与国家的伦理认同;家国一体的伦理认同;家国一体所生成的“天下”伦理实体的认同。三大伦理认同的精髓一言概之: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
家庭与国家在任何文明体系中都是伦理世界的两大伦理实体,但中国传统有两大精神标识,一是以伦理认同而不是道德自由为文化重心建构伦理世界,所谓道德自由总是在伦理实体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伦理境界,这就是黑格尔说的“从实体出发”。二是家庭在伦理实体及其认同中具有一以贯之的本位地位,对伦理世界具有建构性意义,而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的伦理实体。正因为如此,家庭精神与爱国主义总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两大元色,也是伦理道德发展具有基础意义的文化战略。诚然,在家国之间也存在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伦理紧张,但“由家及国”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战略是在家庭精神的基础上生长拓展国家伦理精神和国家伦理认同,“国家”文明的伦理密码不只是家与国两大伦理实体的共生共荣,而是一体贯通,在西方文化中难以调和的两大伦理实体在中国成为相濡以沫的两个文明因子。于是,伦理认同的现实形态就是“国家”,伦理精神形态就是“家国”,它们构成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爱国主义总是深植于自然而深厚的家庭伦理精神,形成坚韧家国伦理纽带。家国情怀是家国一体的情怀,是家庭精神与爱国主义一体贯通的情怀,单一的爱国主义或家庭精神都不是它的全部内涵。家国一体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伦理正果,就是“天下”伦理实体和天下伦理情怀。“天下”伦理实体和伦理情怀基于家国又超越家国,是最具中国标识的伦理实体和中国话语,也是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伦理认同境界,其终极目标是“天下一家”。由此,以家庭精神和爱国主义为结构的家国情怀、天下意识,就成为“国家”文明形态中伦理认同的两个战略支点。
“后伦理型文化时代”的伦理认同遭遇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独生子女时代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伦理认同;文明冲突中的世界意识。独生子女使家庭伦理结构和家庭作为伦理策源地的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使家庭伦理供给具有空前的文化紧迫性,家庭的伦理承载力面临深刻危机,遭遇文化战略挑战。根据我们所进行的全国大调查,2007 年社会大众对家庭伦理最担忧的问题是“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但在2017 年调查中排列第一位的问题已经是“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10 种忧患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的转化,标示着家庭作为文化本位的伦理承载力面临重大危机。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承担终极关怀的伦理使命,本位地位的动摇不仅预示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可能遭遇动摇的危险,更内藏伦理型文化的深刻危机,因为如果家庭不能承担终极关怀的文化任务,人们就很可能到宗教中寻找,老年人在信教群体中的很大比重已经说明这一问题。市场化很可能在创造市场神话的同时陷入“大市场、小国家”的文化误区,也可能出现将国家工具化的倾向。调查显示,在诸社会群体中,企业家群体的国家意识最为薄弱,相应地,公务员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国家意识最强。在2007 年的全国大调查中,国家被排除在最重要的五大伦理实体或“新五伦”的选项之外,在随后的洪涝灾害、汶川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国家充分显示了伦理的力量,在2017 年的调查中国家已经处于“新五伦”之内,不过前三伦都是家庭伦理关系,说明中国家庭本位的伦理认同传统没有根本改变。全球化可能导致抽象的“地球村”意识,但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也可能滋生民族主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天下”伦理认同依然是“全球化”“文明冲突”之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天下”伦理实体的当代表达,是当代中国的“天下”伦理认同战略。由此,家庭伦理精神、国家伦理实体意义的凸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代话语的天下伦理意识,就成为伦理认同的“后伦理型文化”战略。
2.伦理公正
伦理公正是体现“后伦理型文化”时代精神的战略诉求。伦理公正是由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统一、家国关系的伦理公正、以治理腐败和分配公正保卫伦理存在三大支点构成的战略体系。
若干年来,德性论与正义论一直是中国伦理学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我们持续十年的大调查表明,社会大众并没有在德性与公正之间作出像西方那样截然的选择。2007 年的调查结论是“二元体质”,30.0%的人认为个体德性最重要,30.5%的人认为社会公正最重要;在二者发生矛盾时,17.9%的人选择德性优先,19.6%的人选择公正优先,德性论与公正论的选择难分伯仲。2017 年的调查发生了变化,18.0%的人认为个体德性最重要,31.0%的人认为社会公正最重要;51.0%的人认为二者应当统一,当二者出现矛盾时,28.0%的人选择德性优先,23.0%的人选择公正优先。从表面看,已经出现明显分化,公正论选择居主流,但如果将冲突情境下的选择加以整合,优先论对统一论为49.0% VS 51.0%,德性优先对公正优先为46.0% VS 54.0%,虽然公正论高于德性论8 个百分点,但总体上并未出现西方那样的绝对选择,更具表达力的信息是: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德性优先高于公正优先5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德性论与公正论的取向依然平分秋色,或者左右摇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德性论与正义论之争到底是一个西方问题还是中国问题?持续十年调查的信息表明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问题。“正义”本身以及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正义理论,很可能是一个西方话语,中国话语是“公正”而不是“正义”。在伦理学话语中,“正义”是一个具有某种绝对标准即所谓“正”的道德话语,而“公正”则是伦理之“公”与道德之“正”的统一,如果一定要使用“正义”一词,那么完整的中国表达是“公平正义”。伦理公正是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这种统一在现代中西方都遭遇不同的难题,在西方道德话语中就是尼布尔以一部著作的书名所揭示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在中国就是“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根据我们大调查的信息,超过半数的社会大众认为集团不道德造成的危害,如生态危机、企业诚信缺失乃至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等,比个体不道德造成的危害更大。在这些问题中存在深刻的“伦理—道德悖论”:对内,是伦理的实体,包括西方狂热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对外,当这些组织或集团以黑格尔所说的“整体的个体”而行动时,就是不道德的个体。然而现代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只将道德个体当作规约的对象,集团或组织长期逃逸于道德评价之外。为此,“后伦理型文化”战略必须突破关于个体道德主体的传统思维,建立“第二道德主体”的理念和概念,将组织和集团作为道德规约的重要对象,建构“第二伦理形态”或“集团伦理形态”的理论,由此才能在造就至善个体的同时造就至善的社会,超越“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伦理—道德悖论。
在“国家”文明体系下,伦理公正的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课题是家庭与国家关系的伦理公正。家庭精神与民族精神是内在于伦理世界的一对矛盾。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世界的两大元素:家庭精神是神的规律或黑夜的规律,即中国话语的“天伦”;民族精神是人的规律或白日的规律,即所谓“人伦”。民族精神根源于家庭精神,但它誓言要将全民族团结为一个人,因而又压制家庭精神,然而只能侮辱它而不能摧毁它。人的规律在实现之后“就转化为它自己的反面,它发现它的至公正,正是它的至不公正,它的胜利正是它的失败”[2](30)。黑格尔的现象学揭示了西方家国相分的文明路径下家庭与民族之间的文化紧张,但也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问题:伦理公正是伦理世界的基本问题。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建立了家庭与国家之间“乐观的紧张”,但历史已经证明,二者之间的伦理公正及其伦理战略与文明进步息息相关。中国革命的胜利,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土地改革将作为农业国家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还给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实现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伦理革命,因而被称之为“土地革命”;而“文革”时代的一大二公的体制,相当意义上是国家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对家庭权利的伦理压制,于是导致“它的至公正就是它的至不公正,它的胜利正是它的失败”的悲局;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切入点,对家庭的伦理合法性的重新承认,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经济奇迹。任何民族都存在家庭与国家关系的伦理难题,但“国家”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家国关系的伦理公正比任何民族都更加重要,寻找家国之间的伦理公正点或伦理均衡点是文化战略的重大难题和重要支点。
“后伦理型文化”时代“国家”文明遭遇的重大战略挑战,就是如何通过捍卫现实世界的伦理实体推进伦理认同,其战略重心一是以反腐败捍卫国家伦理实体;二是以分配公正捍卫社会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国家权力与财富是现实世界中伦理存在的两种世俗形态。国家权力建构个体与国家的伦理实体性;财富建构社会的伦理实体性,权力公共性和财富的普遍性是生活世界伦理存在的两大现实形态。由于国家权力通过掌握支配权的政府官员体现,财富通过分配实现,因而现实世界的伦理存在期待特殊的伦理条件即官员道德与分配公正。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解构甚至颠覆了国家和社会的伦理实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反腐败和推进分配公正,本质上是一场伦理保卫战,其文化战略意义,就是以保卫伦理存在推进现实世界的伦理认同。我们持续十年的全国性调查表明,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长期在中国社会大众的忧患谱系中位于第一位和第二位,经过多年的努力,反腐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2017 年的调查中,77.9%的人认为腐败现象有较大改善或很大改善,38.8%的人认为对干部的伦理信任度提高了,但“腐败不能根治”依然是居第一位的文化忧患。对分配不公的忧患从2007 年的第一位、2013 年的第二位,降至2017 年的第五位,但依然有77.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不合理”,只是其中有60.3%的受访者认为“不合理,但可以接受”,不合理的判断是主流,只是没有突破伦理承受的底线。从文化战略的维度理解和推进干部道德提升与分配公正,是伦理道德发展必须达到的文化战略自觉。
3.伦理关怀
伦理关怀作为一种伦理优先战略,包括精神家园、弱势群体关怀和老龄关怀三个战略支点。
“伦”与“道”、伦理与道德的重大哲学殊异在于它是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伦”的统一,“伦”是人的公共本质或实体,因而伦理本质上是个体向实体的一场回归运动或世俗性的精神皈依。“伦”是人的精神和世俗的家园,所谓“伦”之“理”就是个体的实体回归之理,也是实体对个体的召唤与关怀之理。以往的伦理学过度关注其教化功能,遮蔽了其作为个体家园的关怀意义,于是实体性的“伦”与本体性的“道”便合而为一,道德僭越伦理,伦理失却其居伦由理的情感享受的家园温度,只剩下尊道贵德的理智满足的抽象道德高度。“后伦理型文化”战略必须回归伦理的家园本性,以伦理关怀建构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实体的坚韧凝聚力和伦理家园的体系,达到黑格尔所说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
伦理关怀以罗素所说的“学会伦理地思考”为前提。伦理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怀伦理,关怀伦理只是伦理的一种形态,伦理关怀以关怀为伦理的本性,在伦理道德发展中赋予其优先的文化战略地位,其中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社会伦理温度和伦理情怀的重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战略有两大着力点,即对于弱势群体的伦理理解和伦理援助。为何关怀弱势群体?是出于伦理的怜悯同情,抑或出于道德的责任感?应该说这两种理解都缺乏伦理上的彻底性,如果一定以同情或同理诠释伦理关怀,那只能说是根源于“伦”的实体性觉悟和伦理良知,在这里福利经济学的补偿理论和政治学的差异公正理论似乎都缺乏彻底的解释力。比如,为什么要帮助残疾人?最彻底的伦理理解是“从实体出发”,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个体作为“人”的伦理实体的一分子,每个人来到世界都内在成为残疾人的风险,一个残疾人承受了其他所有正常人的全部的生命风险,于是对待残疾人的伦理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政策便不是同情怜悯,也不是显示道德高度,而是“感恩”。这才是深邃和真正的伦理情怀。
老龄伦理和老龄伦理关怀是今后相当时期中国战略尤其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重心,因为老龄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几乎无国际经验借鉴的中国问题。家庭伦理是国家文明形态下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之一,传统的孝道不只是一种道德,而是一种“道”的智慧,一种代际伦理和文化战略的设计,其要义一方面是终极关怀,另一方面是人生因老龄走向弱势时的伦理公正和伦理战略,是中国文化设计和提供的自然而神圣的伦理安全系统,不能简单理解为农耕社会的伦理经验。当今中国正走向深度老龄化,最大的国情是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现有文化战略凸显青少年道德教育和伦理关怀,这当然具有合理性,因为青少年是国家和文明的未来,然而正因为如此,对青少年的关心往往具有某种文化本能的性质,就像父母对子女的关爱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天性一样,对待老年人的伦理态度,才真正体现文明的素质和品质,直接影响全社会的文明信心。老龄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而当人们对此有所体验时,便正在甚至已经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因而尤其需要进行高远而缜密的文化顶层设计。当这一群体为社会耗尽全部能量即将退场时,社会对他们的伦理态度及其文化智慧,才是对文明真正的良知拷问,必须将老龄伦理尤其是老龄伦理关怀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
要之,以“家庭精神—爱国主义—天下意识”为战略支点的伦理认同,以“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辩证互动—家庭与国家关系的伦理公正—以治理腐败和分配公正保卫伦理存在”为战略支点的伦理公正,以“伦理家园—弱势群体的伦理援助—老龄伦理关怀”为战略支点的伦理关怀,构成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中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战略重心和文化战略体系。它根源于伦理优先的民族精神传统,但已经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它以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家国情怀和天下意识的伦理认同为基础,以伦理公正的辩证互动建构伦理认同的合理性,以伦理关怀建构伦理的精神家园与现实家园,是伦理的神圣性、合理性、现实性一体互动的伦理优先的现代战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