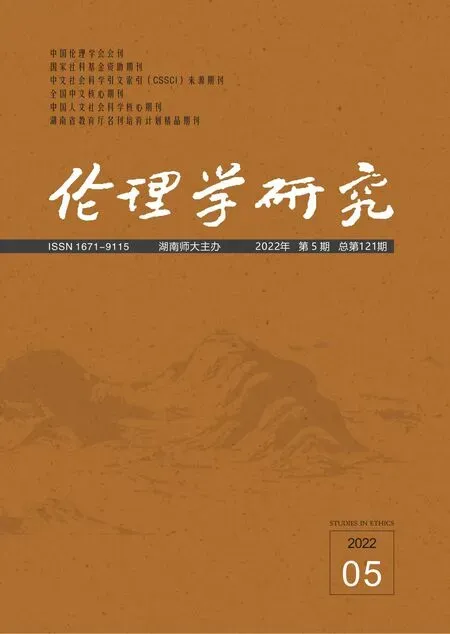合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伦理学论证
——对“诉诸自然”论证的批判
雷瑞鹏
前言
合成生物学被认为是继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之后以基因组设计合成为标志的第三次生命科学革命,给生物技术产业带来了空前的变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能源、食品、药物和疫苗、环境保护等)提供了新的前景。但合成生物学自诞生以来就不断被施以“扮演上帝”“颠覆人与自然关系”等批判性评价。然而学界对于什么是合成生物学仍然存在争议,并未达成共识。欧盟对合成生物学的科学定义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合成生物学的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合成生物学是科学、技术和工程学的应用,目的是促进和加速活的有机体中遗传物质的设计、制造或修饰。”[1](5)合成生物学不同于通过解剖生命体研究内在构造的传统生物学,也不同于通过拼接技术重组DNA 的基因工程,它的最后目标是要致力于“从头开始”“从无到有”地一步步自下而上组装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生物有机体和人工生物系统[2](449-453)。如果说传统生物学的任务是描述生命现象,基因工程的任务是编辑和修饰生命,合成生物学则致力于编写生命软件,设计和制造新的生命形态,实现生物学从“读”到“写”的转变[3](45)。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它使得人类不仅仅能够认识生物、操纵生物,还能够工程化制造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崭新功能的生物,给传统的生命观带来了巨大挑战,包括生命究竟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如何认识生命的认识论问题,以及合成生物学是否拥有伦理上的可辩护性和可接受性的伦理学问题。虽然,所有生物学上的突破性发展都会引起哲学/伦理学争议,但由于合成生物学代表着从“操纵”生命到“创造”生命的颠覆性转变,它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强烈的质疑、争论甚至反对,这极大地影响了合成生物学本身的正当性,其中影响最广泛的两个反对论证为“扮演上帝”的论证和“颠覆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其中,“扮演上帝”的论证我们已撰写了专文进行批判,本文专为批判反对合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诉诸自然的论证。
一、有关诉诸自然的论证
通过诉诸自然的论证否定合成生物学的正当性,主要集中在设计、制造和使用生命有机体是否从根本上改变或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论证包括:合成生物学合成的有机体(synthetic organisms)是不自然的,是人造品,自然的东西与人造的东西之间存在道德意义上的区别;合成生物学犯了形而上学上的错误,使得人在宇宙中处于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合成生物学犯了伦理学上的错误,它贬低生命,过高估计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合成生物学损害或很可能导致损害自然。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诉诸自然的论证,然后加以分析批判。
1.自然或自然物之间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分界线
一些人认为在自然界存在着两类事物,一类是自然的,另一类是人造的或非/不自然的,二者之间存在着道德意义上的区别。合成有机体是“不自然”的,因而是不好的,应该遭到拒斥。环境伦理学中有一种规范性共识:自然之物的价值高于人造之物的价值[4](23-39)。因此,不自然的、人造的东西价值低甚至没有价值,应该遭到拒斥。这一观点在民众中也普遍存在,人们总是排斥不自然的东西,比如欧洲人称转基因食品为“弗兰肯斯坦”食物,人们对将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内感到“恶心”和恐惧等。反之,人们总是更加青睐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才是正常的、安全的、智慧的、神圣的,比如人们普遍认为自然怀孕比辅助受孕更好,农家肥比化肥更好等。总而言之,在他们看来自然的东西比人工的东西更加优越、更值得追求,这就赋予了自然以规范性意义:合乎自然的行为就是有价值的、道德的,不合乎自然的行为就是没有价值的、不道德的[5](96)。按照这一逻辑,科学家从最基本的生物砖开始自下而上构建出具有崭新功能的历史上不存在的合成有机体,用价值较低的人工制品取代价值较高的自然有机体,比以往任何生物技术都更加“不自然”,因而是不道德的,必须加以反对。在当今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先进的时代,人类也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将周围的事物严格区分为“自然的”与“人造的”(或非/不自然的)似乎已经不大可能,而“自然的”与“人造的”之间即使有区别,这种区别也没有道德上的意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有关自然性的观念和论证》[5](94-97)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
2.合成生物学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些人认为合成生物学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形而上主张。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本身或神性的创造者(上帝)已经给宇宙做好了安排,有些领域人类是不应该进入的。例如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米尔德里德·曹(Mildred Cho)及其同事认为,合成生物学通过用DNA 来定义生命,将生命归结为简单的生物学特性,从而威胁到了将生命视为拥有特殊性的观点。合成生物学被指责利用还原论消除了生命的特殊性[6](2087-2090)。德国学者约阿希姆·博尔特(Joachim Boldt)和奥利弗·穆勒(Oliver Müller)认为合成生物学使人类从自然生命的“描述者”“操纵者”变为“创造者”,“这种从‘操纵’(manipulatio)已存在之物到‘创造本不存在之物’(creatio ex existendo)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的根本变化”[7](387-389)。合成生物学似乎在倡导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可以控制自然使其适应人类的需要,而不是人类必须适应自然。这会导致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改变——人们不再尊重和敬畏自然,而是将其当作一张白纸肆意挥洒,自然沦为人类宰制的对象[7](387-389)。英国环境伦理学家李基觉(Keekok Lee)明确地说:“从长远来看,现代科技令人担忧的事情可能不是由于其污染效应威胁地球上的生命,而是它最终能使自然的一切人化(humanized)。大自然作为‘他者’(the Other)将被消除。”为了避免这种结局,“自然之物的本体论范畴必须与人工制品划分清楚,不受它们的侵犯”[8](4)。在这个意义上,合成生物学犯了误解和破坏生命所属范畴的错误,人通过成为创造者对属于这个范畴的生命做了不合适的事情。
3.合成生物学犯了伦理学上的错误
合成生物学产生了一种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它与道德实践的基本概念相冲突。博尔特等认为,合成生物学将有机体描述为机器般的人工制品,对“生命”与“价值”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挑战,最后可能导致削弱社会对更高生命形态的尊重[7](387-389)。他们认为合成生物学改变了人们关于生命和人在宇宙中角色的概念,这是不符合道德的。美国神学家吉拉尔德麦肯尼(Gerald McKenny)在《生物技术伦理学》(The Ethics of Biotechnology)一文中提出,“自然为赐,自然为导,自然为类:回归自然。既然自然是有价值的、道德的,我们应该对自然保持敬畏、谦卑、感恩和惊叹之心”[9](152-177)。
4.合成生物学损害环境
合成生物学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关注,是由于它可能损害环境。这类关注的基石是,环境学家都认为,环境应该被保护,不仅要确保环境有益于人,而且也要由人来保护环境。为此,人类对自然之物应怀有敬畏和感激的态度。美国环境哲学家克里斯多福普雷斯顿(Christopher Preston)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反对合成生物学的。他认为合成生物学破坏了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之间的界限,而传统的分子生物技术则没有,二者的区别在于:传统的生物技术总是从一个现存的有机体基因组开始,通过删除或添加基因来修改它;相比之下,合成生物学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全新的有机体”。因此,合成生物学越过了一条对环保主义者来说最基本、最宝贵的界线:它背离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原则,即通过修改来延续[4](23-39)。
二、对诉诸自然的论证的分析批判
1.根据多元的自然概念无法形成有效伦理论证
自然的概念是一个多元的有严重歧义的概念,根据这一多义的概念形成一个有效的伦理论证,是不可能的。合成生物学的目的是扩展或更改有机体的行为,并把它们设计制造出来以执行新的任务,它或者用原料制造有机体,或者用有机体中已经找到的部件制造有机体。在《自然》杂志中发表的一篇并非反对合成生物学的文章中这样表述合成生物学:首先“利用非自然分子复制自然生物学中本来没有的行为以创造人工生命,其次是“从自然生物学中寻找可互换的部件,组装成具有非自然功能的系统”[10](533-543)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两位作者一下子把原先生物学的“自然性”与合成生物学的“非自然性”对立了起来。这就使一些人认为,合成生物学是在性质上而不是在程度上区别于自然的生物学。后者是为了人的特殊目的而利用遗传材料,如发酵、动物饲养和农业。但合成生物学是为了人的目的合成活的遗传物质的一种新的努力。于是,它就很容易被认为超越了仅仅修改或重组自然给予物(natural givens)而另辟蹊径去创造活的有机体,从而被指责为模糊了有机体与人造物、有机物与合成物、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界限[11](22-42)。
然而,诉诸“自然”和“自然的”概念来形成一个论据,主张对既往的生物技术与合成生物学采取不同的政策,即因为合成生物学致力于制造“非/不自然的”有机体而认为合成生物学与传统的生物技术有性质的不同,而不予批准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应用则存在严重的困难。
因为“自然”这个概念是多元、多义的,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竞相参与制定他们认为合适的“自然”概念,一些学者希望能在“自然”这种多元意义上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论证来反对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应用。例如,美国环境学家詹姆斯·普罗克特(James Proctor)总结了关于自然的五种观点:作为进化的自然、作为突现的自然、作为可塑的自然、作为文化的自然以及作为神圣的自然。普罗克特观察到,前两种观点出现在物理、生命和行为科学之中;最后两种观点出现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神学之中,而可塑的自然则横跨于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12](6)。实际上关于自然的观点比普罗克特列举的要多得多。各种有关诉诸“自然”或“自然的”观点都是事实与信念、描述与规定、情感与直觉的复杂混合物。那么,是否可以使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坐下来,形成大家一致同意的“自然”概念以及“自然”的道德意义,从而形成有效的伦理学论证,将合成生物学与传统生物学加以区分,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有资格作为决策根据的伦理论证,必须经得住分析的考验。然而,诉诸自然和“自然的”论证难以接受精确的分析。理由是一个人对自然的看法往往包含了一大堆难以孤立和单独分析的问题,尤其是当它们主要在直觉和情感层面上发挥作用时。此外,对诉诸自然有多大说服力的判断必须考虑到历史和跨传统的各种解释。对于自然和自然的特定观点,在传统的范围内和跨传统的范围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且传统上被称为“是/应该问题”的哲学挑战使得运用诉诸自然的论据来对合成生物学作出道德判断的努力归于无效。道德判断不能仅仅从对世界的描述中得出。在日常生活中,描述和评价活动是不容易分离的。从斯多葛学派起,自然曾被看作普遍秩序的原点,为道德选择和行动提供辩护。然而,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对混淆经验与道德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这体现在休谟对毫无理由地从描述到规定的论证的批评之中。例如在自然界中既有弱肉强食,又有互惠共生,那么哪一个应该成为我们的道德指南呢?因此在作出道德决定时,我们必然会诉诸一种超越自然的规范性标准,否则就陷入了“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 fallacy)。
虽然诉诸自然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我们需要考虑其中可能的道德意义,然而自然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对自然的许多不同思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引起了人们对在有关合成生物学的政策审议中诉诸自然的论证有效性的关注。很难看到诉诸自然能够发挥论证的作用,从而为全面禁止甚至严重限制合成生物学发展的政策提供基础。对具体研究项目的政策判断,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作出适当的决定,例如考量风险和受益、对社会和人类的福祉、对环境的影响、公平可及等,而不可能依赖不清楚的、模糊的、复杂的、争论不休的自然概念来作出应该鼓励、允许还是禁止合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决策。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诉诸“自然”和“自然的”论证努力,虽然包含一些伦理关注,但对技术决策不能作出决定性的判断,至多仅是某种观点的直觉表达。由于诉诸自然的定义繁多,所以我们不可能提炼出一组有效的原则和合乎理性的论证为支持或反对合成生物学的政策进行辩护。
第二,虽然一些批评者认为合成生物学与涉及基因工程的其他生物技术有本质不同,但这种区别在概念上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从种群生物学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自然给予物(natural givens)与人类文化和技术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少从农业时代就开始了,这就很难在描述当今的自然界时不考虑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互作用。
第三,考虑一下合成生物学是否更类似于其他形态的文化塑造和控制,也是有益的。人们对于后者并无争议。人类文化本身是人类行动能力的自然表现,而人类文化日益增加的技术和科学特性本身似乎并没有在概念上或规范上提出挑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活动已经塑造和重塑了人类生物学。例如,读写能力对人脑的发育和结构有可观的效应,钢琴演奏家和出租车司机的脑会因他们的工作而发生相当大的改变。因此,文化和自然相互作用的事实,已经使试图把文化与自然两个概念完全隔离起来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如上述李基觉的建议,要防止自然“人化”,要将自然之物与人工之物决然分开,恐怕难以实现。
第四,自然概念的多元性提示,使用自然概念的论证只能拥有修辞的目的,而禁不住分析。人们在使用自然这个术语时,其中既包含许多描述性的意义,又有许多规定性的含义。自然既是“上帝荣耀的剧场”,也是因亚当的堕落而变得混乱不堪的领地。自然是值得尊重和保护的荒野,也是造福人类的源泉。这一概念的多元性反映了自然本身既丰富多产,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
第五,为了作出道德判断或政策选择而去确定自然概念意义的努力是徒劳的。我们不能指望如此复杂而歧义的自然概念能够成为一个意义清晰的论证,支持我们对合成生物学采取适宜的政策。试图去规定其意义如此复杂的“自然”概念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多的混乱,需要作更多的澄清。我们对自然界的改变或增添不要以零和的方式来看待。“自然”并没有被人类的创造力削弱,它既是构成我们自己的,又是脱离我们自己的。合成生物学提出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解决,但我们不能囿于自然/人、自然/超自然、自然/非自然的传统二元性而去阻挠如此有前途的合成生物学的发展[12][13](312-336)。
2.合成生物学犯了形而上学方面错误的论证不成立
如上所述,约阿希姆·博尔特和奥利弗·穆勒认为合成生物学使人类从自然生命的“描述者”“操纵者”变为“创造者”,“这种从‘操纵’(manipulatio)已经存在之物到‘创造本不存在之物’(creatio ex existendo)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我们对待自然方式的根本变化”[7](387-389)。批评者认为,宇宙本有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大自然本身安排的还是由神性的上帝在造物时安排的,这个既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容破坏。且不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经排除了这种自然或上帝安排的秩序,这些批评者实际上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阈,超过这个阈就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他们认为传统的生物技术没有超过这个阈,而合成生物学则超过了。那么根据什么说,合成生物学的设计、制造和使用活的有机体超过了这个阈,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呢?我们发现,在合成生物学的语境下没有一个批评者能将他们的这种关注说得非常清晰,反而往往使人难以捉摸。例如反对合成生物学的人提出的理由是合成生物学显示的对生命的某种形而上学的理解是错误的,尤其是他们争辩说,合成生物学通过将生命还原为一种纯粹物质现象(如生物化学现象),进而认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只是各种组成成分的复杂组合,这破坏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在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中,作者们认为,合成生物学通过用DNA 来定义生命将生命归结为简单的生物学特性,从而威胁到了将生命视为拥有特殊性的观点[6](2087-2090)。但海斯廷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格里戈利·凯布尼克(Gregory Kaebnick)指出[14](60-75),从逻辑上讲,在实验室创造一个活的有机体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特殊的性质,因为可以用其他方式赋予它特殊性。如果有一个上帝能赋予沼泽里的生物这种特殊性,那么他也能将这种特殊性赋予在实验室里产生的生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创造活的有机体。在体外受精时,每次配子在试管中结合形成胚胎,生命就诞生了。每一次动物交配成功,生命就诞生了。想必上帝(假定他存在)一直在跟随他们(或它们)。合成生物学改变的是“创造”(或造物)的方法,而不是出现一个新的生命这一基本事实。因此,我们通常在微生物生命中发现的任何特性,也可以在合成微生物的生命中发现。问题在于生命是否有特殊性,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而我们该不该支持合成生物学,那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这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即使认为合成生物学使人如上所述从生命操纵者变成生命创造者,那也说明人在宇宙中的角色有了变化,而人这种形而上学的地位发生改变是否在形而上学方面犯了错误,对此众说纷纭,但生命创造者(或“扮演上帝”)这个标签只是提示,人类正在跨出他们在宇宙中的既定角色以外。人在既定宇宙秩序中的位置应该是什么是一个本体论或形而上学问题,而人应该做什么(如支持还是反对合成生物学)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3.对合成生物学犯了伦理学方面错误的指责站不住脚
如上所述,约阿希姆·博尔特和奥利弗·穆勒认为合成生物学使人类从自然生命的“描述者”“操纵者”变为“创造者”[7](387-389),产生了一种与道德实践的基础概念相冲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将有机体描述为机器般的人工制品,挑战了“生命”与“价值”两者之间的联系,贬低了生命的价值,最终导致弱化社会对更高生命形态——人的尊重;而且合成生物学可能会改变人类关于人的行动能力(human agency)的概念,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的操纵者,而变成创造或改造自然的人,导致人的过度自信。
就合成生命会贬低生命而言,我们可首先指出,没有理由假定探索生命的科学研究将迫使我们贬低生命。在实验室里创造有机体这一事实并不能因此就降低其价值,认为它的价值低于自然产生的有机体。正如美国生命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所说,在宣布合成真菌分枝杆菌之后,其生命的价值并不会因有可能它的功能被理解而受损和贬低[15]。对细菌生命持还原论的观点也不一定导致贬低更高生命形态。当我们合成生命时,合成的生命就会显示生命特有的特性或能力,这并不仅仅是化学变化,也不可能使人们贬低生命的价值。一项关于公众对合成生物学态度的研究提示,人们并不对创造和修改单细胞有机体感到烦恼,即使合成生物学有可能创造和修改更高级生命的形态[16](28)。而且对单细胞生命的态度与对最高生命形态人的态度的联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人们过去曾视动物为机器,这在道德上没有引起任何问题,也没有因此贬低人类生命的价值[14](60-75)。
就生命不同于无生命物体而具有价值而言,需要对“生命具有价值”这种说法作进一步的哲学分析。不同于无生命物体,所有生命形态具有自组织、新陈代谢、生存、繁殖和进化的特性或能力。但这些特性或能力不足以使生命本身具有价值。这里的价值应该是指自身内在的或固有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指外在的工具性的价值。这里的价值也许最好用“道德地位”加以表述,这样能使我们更好地看清“生命具有价值”这种笼统说法存在的问题。当我们说在所有生命形态中人拥有最高道德地位(最高价值)时,这决定于人拥有他们特有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情感、社会关系等能力。当我们说有感受能力(sentient)的动物有不同程度的道德地位(不同程度的价值)时,这决定于它们拥有的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其中一些动物还拥有比人程度低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情感、社会关系等能力。然而,自组织、新陈代谢、生存、繁殖和进化的特性或能力本身不能决定生命具有价值或道德地位,除非你允许生命的价值或道德地位可以是负值的。例如我们能说引致疾病大流行的艾滋病病毒、SARS 病毒、禽流感病毒、新冠肺炎病毒,甚或传播寨卡、登革热、疟疾的埃及伊蚊是有价值或道德地位的吗?显然不能。因此,我们杀灭这些病毒或埃及伊蚊显然不存在道德问题。
就合成生物学会使人类过分自信,即高估我们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能力而言,这似乎本身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至多是一个美德问题(谦逊是美德)。一个人过分自信并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一定就会作出违反伦理规范的行动。但我们可以说,如果你过分自信,你可能会不顾一切地使用你的能力,最终你的行动可能导致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过分自信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那么这是一个与行动后果有关的道德问题,与有关合成生物学如何可能改变我们对自然态度的特殊论证无关。但如果合成生物学家狂妄自大,不但合成单细胞有机体,而且企图合成有感受痛苦和快乐能力的动物以及具有理性和情感能力的人,那就要受到公众的谴责和监管部门的禁止。那时的伦理问题是,我们应该不应该合成有感受痛苦和快乐能力的动物以及具有理性和情感能力的人,这不仅是狂妄自大的问题。如果科学家满足于在实验室或工厂进行合成生物的研究,那么他们的狂妄自大就不一定会引起伦理关注。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科学往往会挑战有关生命以及我们在宇宙中角色的观点。如哥白尼使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消除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截然划分,德国化学家弗里德利希·维勒(Friedrich Wöhler)合成尿素使“活力”(vital force)失去了地位。他们没有使道德沦丧,反之,他们因此而使人类在道德上迈进了一大步[14](60-75)。
4.对合成生物学损害自然的指责至少缺乏经验证据
与上述普雷斯顿断言合成生物学损害自然的指责相反,合成生物学若干成功的案例都不存在或至少没有发现有严重而不可逆地损害自然的问题。例如合成青蒿素使全世界数千万疟疾病人摆脱病魔,并没有发现对环境有明显的损害效应,而且有帮助种植青蒿素植物的地方摆脱作物单一、恢复作物多样性的有益于环境的效应[17](940-943)。需要我们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来应对的人—自然关系问题往往涉及对自然界有可定量的损害,尤其是严重而不可逆的损害。例如将旅鸽(passenger pigeon)杀光了,这一物种就被消灭了;而创造一个有机体不一定起损害作用,尤其是创造出来的有机体留在实验室或工厂、养殖场,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并没有受影响。实际上,合成生物学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例如我们可以恢复旅鸽这一物种,如果我们能够合成旅鸽的基因组,然后将它置于起代理作用的卵中。更不要说,我们可以通过合成生物学让细菌生产干净的能源,生产消除环境污染或吸收二氧化碳的物质,从而减少污染和延缓气候变暖了。
然而,反对合成生物学的学者会进一步说,虽然合成生物学本身不一定损害环境,但它助长了一种损害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即要求自然调整得满足人类需要,而不是使人适应自然。对合成生物学的这一反对意见不能成立,因为人们可以责备所有技术都可能有这种倾向。调整自然适合于人与调整人适合于自然,这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反对合成生物学的这一论证本身不能成立,除非合成生物学使环境更糟。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石油燃料生产和消费的问题是如此巨大且严重,即使我们研究和应用合成生物学产生新的干净的能源,也仍然需要改变人类的行为以适应自然现实。在调整自然以适应人类行为和调整人类行为以适应自然之间不存在二择一的问题。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应用可能对环境有潜在风险,这与研发其他技术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例如利用合成藻类生产燃料,有可能从生态系统中取走营养源,减少环境中动植物的多样性;将本地藻类或微生物种群淘汰或使其受到不利影响,改变水生生态系统及其食物网动力学;将合成或经修饰的遗传物质转移入其他有机体,引起某一藻类微生物株变成对非人有机体致病,触发对环境有害的藻类猛长,产生未知的或新型的与转基因有关的毒素等[18](177-184)。我们对这些可能的环境影响都要进行仔细评估,并采取种种措施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并使其最小化。这与我们研究和应用其他技术时要评估其环境影响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些环境影响不是一个反对合成生物学的理由,而更可能是在研究和应用合成生物学时如何更好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理由。
结语
对于一个新兴的科技领域或学科,我们必须采取适宜的政策。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必须立足于有效的伦理论证。本文着重分析了比较普遍且影响广泛的诉诸自然的论证,指出它不能成为反对合成生物学的有效伦理学论证,根据这个论证来反对合成生物学,否认它的正当性是无效的,不能成立的。
在我们看来,合成生物学的某些领域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鉴于此,第一,合成生物学必须专注于比较简单的有机体,它引起的生物学变化至少比较简单。第二,这些比较简单的有机体完全没有感受能力,更没有意识和自我意识,进行研究不需要它们的知情同意,这样就不存在对研究的监管障碍,从而可加快研究的步伐。
我们认为,在研究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问题时,应该有两个规范性要求:一是我们必须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路径,即从科研实践中鉴定出要解决的规范性或伦理学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伦理问题,然后在哲学/伦理学层面进行研究,继而提出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19](259-273)中指引我们的办法;二是我们要了解每一门新兴科技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9](27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