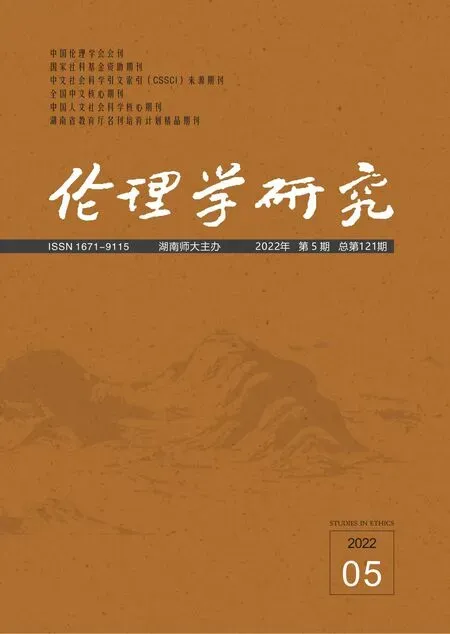儒家仁爱观的志愿服务伦理意蕴
彭柏林,张可人
所谓儒家仁爱观的志愿服务伦理意蕴,意指儒家仁爱观所蕴含的与志愿服务伦理相契合或对志愿服务伦理建设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虽然由于时代局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儒家既没有也不可能提及志愿服务概念,并且也未直接论及志愿服务伦理问题,但只要深研《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就不难看出儒家仁爱观所蕴含的志愿服务伦理思想是较为丰富的、明显的,本文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仁者爱人”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二是“仁义并举”的志愿服务伦理实践模式;三是“天下大同”的志愿服务伦理追求。在志愿服务获得快速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彰显其作用的新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志愿服务发展的实际及其发展趋势,挖掘儒家仁爱观所蕴含的这些志愿服务伦理思想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
细读儒家的《论语》《孟子》等典籍不难发现,儒家仁爱观蕴含着“仁者爱人”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在孔子那里,“仁”最基本的含义即是“爱人”。而在对“爱人”进行具体阐释时,孔子既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1),将“爱亲”视为“仁”之本始,又强调“泛爱众而亲仁”[1](3),从而使“仁”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规定。在“泛爱众”这一层次上,孔子尤重对社会弱者的关心和爱护,《论语·乡党》关于“厩焚”后孔子“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的记载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另据《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特别强调“周急不继富”。所谓“周急不继富”,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为生活陷于困境的他者提供志愿服务,孔子将之视为君子所应具有的道德情怀。不仅如此,孔子还主张行“仁”德于天下,强调“恭、宽、信、敏、惠”,其中的“惠”虽含有多种含义,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是其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含义之一。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无疑包含着为那些处于困境的社会弱者进行道义救助和伦理关怀的意义。当然,这里的社会弱者既可能是熟人圈子的,也可能是陌生人圈子的,而对陌生人圈子中的社会弱者进行道义救助和伦理关怀很显然已具有朴素的志愿服务特性。
在以“爱人”释“仁”的同时,孔子还提出以“忠恕”作为行“仁之方”[2](40)。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孔子那里,“仁”与“忠恕”是内在统一的,“仁”即“忠恕”,“忠恕”即“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仁这个道德范畴包含了多种道德要求,在这些道德要求中贯穿着‘爱人’的道德原则,贯穿着忠恕之道”[3](109)。《论语·里仁》云:“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32)“忠”,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7);“恕”,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07)。这就是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看待,并以自己的愿望、欲求去理解别人的愿望和欲求;当我自己有什么欲望和要求的时候,总要想着我周围的人以至于所有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此,在满足自己的要求和欲望的时候,就应该想着也使别人满足同样的欲望和要求;同样,如果我不喜欢不愿意别人所加于我的一切,就绝不要以这类事情去强加于别人”[3](107)。究极而言,“忠恕之道”在孔子那里乃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所强调的是通过内心反省引导人们领悟与人为善、仁爱他者的价值和意义,履行扶贫济弱的道义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此“忠恕之道”所要告知者,即是仁爱他者、扶贫济困、关怀社会弱者,它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乐的精神”[4](30)。
继孔子之后,孟子对“仁爱”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对仁爱他者、扶贫济弱的内在道德动机作了深入分析和思考,提出了著名的“四心”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5](56)从志愿服务伦理的意义上说,孟子此处所欲肯定者,即是对社会弱者的帮扶和关爱应发自内心的自觉,或为自觉心所本有,而人所本有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是引导人们关心、同情和帮助弱者的力量之源。在此“四心”之中,“恻隐之心”乃“仁之端”,“仁”是这种“恻隐之心”的向外扩充和发展,大凡仁爱之行、慈善之举皆发自于人之内心:“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5](245)正是基于此种道德价值观,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5](85),将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视为“仁爱”的重要诉求。汉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不仅借助天之意志对孔孟所倡导的“爱人”之“仁”作了进一步的强化,而且认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6](315)。宋代以降的儒家倡导以爱己之心爱人,强调以博施济众为己任。张载云:“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7](231)在他看来,扶贫济弱、救人于难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大人所存,盖必以天下为度”[7](163)。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儒家所倡导的这种扶贫济弱之仁中已包含着志愿服务伦理思想的萌芽。
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志愿服务伦理的视角来看,可以说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朴素志愿服务性质的济贫扶弱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撑。“中华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是由诸多原因所致,但其根本原因是道德精神及其永不褪色的价值。”[8](59)蕴含在儒家仁爱观中的这种具有志愿性质的伦理精神,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济贫扶弱观念与行为,乃至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不胜枚举的致力于济贫扶弱的民间志愿者群体以及连绵不绝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济贫扶弱活动。据《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北魏太和七年(483),冀、定二州的老百姓遭受饥荒,一些地方贤良人士自觉自愿地“为粥于路以食之”,使数十万人的性命免于死亡。又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统计,有清一代,由地方社会主持创设的旨在为流丐孤贫者提供志愿服务的民间社会慈善组织普济堂在河南109 个州县建有129 所,在山东101 个州县建有131 所[4](154),等等。这些济贫扶弱活动连绵不断地出现,尽管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与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仁者爱人”志愿服务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诚然,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具有“爱有差等”的局限。儒家所讲“仁爱”与墨家所讲“兼爱”有所不同,虽然它强调“泛爱众”,但这种“泛爱众”是建立在“亲亲”之爱基础上的。换言之,儒家所倡导的是一种“差等之爱”,是按照“爱亲—爱众”即“推己及人”的价值逻辑建构起来的。按照这种价值逻辑,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基本上就只能在自己所属的伦理关系范围内去寻找关系和想办法,而“由于其伦理组织,亦自有为之负责者”,这样“有待救恤之人恒能消纳于无形”[9](311)。基于这种价值逻辑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犹如投入水中的石子所激起的波纹一样是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0](34)。这样,不仅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里没有不分差序的博爱观念,而且也难以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10](47),是以志愿服务所需要的普遍主义的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可以依附的基础。也正因此,虽然在儒家仁爱观中蕴含着“仁者爱人”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涌现了不少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济贫扶弱民间组织及其活动,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最多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在中国古代尚处于萌芽状态。
尽管儒家这种“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具有“爱有差等”的局限性,但只要我们进行深入分析,扬弃其局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以发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倡导儒家的这种“仁者爱人”伦理理念对推进志愿服务的发展从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伦理理念是志愿服务最为深层的道德心理基础。一方面,有没有“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对一个人能否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志愿服务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一个没有“仁者爱人”伦理理念的人,一般情况下,既不可能同情他人的苦难,也不可能有无偿救助他人的动机和热情,从而也难以有参与志愿服务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是激发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与自觉性、调动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仁者爱人”伦理理念是否能够得到普及以及普及程度如何,对一个社会志愿服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社会的志愿服务发展得如何,与这个社会有没有形成仁爱的社会氛围以及仁爱氛围浓厚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缺乏仁爱氛围或仁爱氛围不浓厚的社会,不仅其志愿服务事业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甚至可能没有真正的志愿服务事业。而一个社会的仁爱氛围越浓厚,就越有利于这个社会志愿服务的发展。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推进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就很有必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发展的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的这种“仁者爱人”志愿服务伦理理念。
其次,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这种“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对推进国际志愿服务的发展,从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协同推进方可实现,但无论如何,志愿服务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它可以凭借独有的优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一方面,志愿服务的价值追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志愿服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助行为,而社会互助行为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社会互助行为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并凭借共同体的力量去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和从事生产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1](344)。处于此命运共同体中,“从他者的视角看,我的存在就是为他的。我接受他者的存在,我回答他者的要求,我就是为他者负责的责任主体”[12](86)。志愿服务产生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救助陷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而之所以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除了弱势群体依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走出困境而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外,更重要的在于弱势群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与其他人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志愿服务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均存在的具有国际性的社会现象,是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是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的重要力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志愿服务的价值追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志愿服务可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志愿服务就一定能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志愿服务能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而其中一个甚为重要的方面便是人们能否秉持“行仁德于天下”的伦理理念积极参与到国际志愿服务中去。所谓“行仁德于天下”,从现代志愿服务伦理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秉持“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志愿服务活动。只有每一个人树立了“行仁德于天下”的道德志向,秉持着“仁者爱人”的伦理理念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志愿服务活动,才能够有力推动志愿服务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凝聚起国际志愿服务活动的磅礴力量,促进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而化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使世界朝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3](58-59)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仁义并举”的志愿服务伦理实践模式
儒家不仅强调“仁”,而且强调“义”,主张仁义并举,使人们按照“义”的要求去仁爱他者、帮助他人。孔子曾指出,“见义不为”乃是“无勇”的表现[1](16),他认为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无适也,无莫也”,然而必有所依,那就是“义”[1](30)。所谓“义”,在孔子那里,主要指君子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和应遵守的道德应然或曰“道德律令”。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求仁而得仁”,唯义是从,既不要注重道德的外在价值,也不要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应当像颜渊那样,哪怕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1](51)。这就是说,君子要以履行仁德为最高目的,即使“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1](62),也要乐在其中。反之,虽有追求“仁”的志向,而又以“恶衣恶食”为耻,将个人的私利私欲掺杂其中,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那这样的人是“未足与议”、不值一提的。后来,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贵仁”思想,并将仁义统一起来,提出了“居仁由义”的思想。一方面,孟子认为,“人皆有所不为”即不干不应该干的事情,如果能“达之于其所为”即干应当干的事情便是“义”[5](258),否则便是“非义”。对于“非义”的行为我们应持之以羞恶或憎恶的态度,即所谓“羞恶之心,义也”[5](193)。另一方面,在孟子看来,“仁”是“人之安宅”或“人心”,“义”是“人之正路”或“人路”,如果“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5](124),或“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5](200),那将是很悲哀的事情!这就是说,凡人应当有仁爱之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也是人心须居而勿失的为善之根本;但又不能不加区别地去爱一切人,爱人之心只能施于当爱者,因此需将“仁”与“义”有机统一起来,按照“义”的要求去爱人,即所谓“居仁由义”。换言之,“仁也者,人也”[5](251),每个人都应有仁爱之心,但又不能不分善恶地去爱所有的人或所有的行为,因为人有善恶之分,人的行为也有应当与不应当之别,必须在实行仁爱的过程中注意加以区分,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做到“能好人能恶人”[1](28),爱所当爱、恶所当恶。是故,“义”,“人路也”,是仁爱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去利怀义”,“修其天爵”、保持“良贵”,甚至做到“舍生取义”。从孔子、孟子的这些思想主张不难看出,儒家是主张按照“仁义并举”的实践模式去实行仁爱的,从志愿服务伦理的视角来看,这实质上是提出了一种“仁义并举”的志愿服务伦理实践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就应当把仁与义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既要有仁爱他者的道德情怀,又要顺“理”而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做其所当做,行其所当行,“达之于其所为”。
诚然,儒家的“义”,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等级区分、等级权益的自觉维护和尊重”[14](24),是“遇事按照等级制的精神原则,作正确决断,采取适宜、适当的行为”[14](25),从而使得其“仁义并举”的实践模式具有宗法性特征和确定的界限,而基于这一模式所开展的济贫扶弱等活动则往往具有官办的性质,在封建社会,官吏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济贫扶弱也通常被认为属于官方应当承担的职责。因而,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均将济贫扶弱视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较早地介入和干预。这种情况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济贫扶弱活动的开展,但也导致人们将济贫扶弱仅仅看作是官或绅的道德义务,而对普通老百姓缺乏这方面的道德要求,从而导致民间的志愿服务组织难以兴起,直至明末清初时期才有所改善。
尽管儒家“仁义并举”的这种实践模式存在着宗法性局限,但只要摈弃这种局限,并根据现代志愿服务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就可以发现,儒家的这种“仁义并举”实践模式对如何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是有着一定启迪意义的。首先,儒家强调“义以为上”,不应当将私利私欲掺杂于仁爱的行为之中,否则便是不足为道、不值一提的。很显然,这与现代志愿服务伦理所主张的“志愿服务应当是超功利性的或非权利动机性的”这一道德要求是相契合的。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基于公益的仁爱他者的社会伦理行为,应当始终秉持“义与之比”、唯义是从的道德理念,而不能掺杂有任何功利的计较与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要求,否则志愿服务就将不成其为志愿服务,失去其本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异化为人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其次,儒家主张不能不加区别地去爱一切人,而应当将仁爱之心施于当爱之人。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志愿服务领域,那就是不能不加区别地去为所有的人提供志愿服务,而只能将志愿服务施于那些深陷困境、确实有志愿服务需要的人。最后,儒家强调要按“义”的要求即行为的当然之则去行事,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在志愿服务工作中借鉴和吸取的。志愿服务虽然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志愿服务没有约束,可以随意为之。换言之,志愿服务也有其所遵循的当然之则或“道德律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就志愿服务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6 年3 月1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2017 年6 月7 日国务院第175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志愿服务条例》都对应如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如后者第三条就规定:“开展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志愿服务所应遵循的当然之则,而且只有按照这些当然之则去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才能保证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始终在合义的轨道上运行,朝着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天下大同”的志愿服务伦理追求
除“仁者爱人”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仁义并举”的志愿服务伦理实践模式外,儒家仁爱观中还蕴含着“天下大同”的志愿服务伦理追求。儒家大同理想的提出是与孔子所倡导的均贫富思想密切相关的。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157),希望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很充裕甚至较为匮乏的条件下不要出现贫富悬殊现象。他还认为人不应该“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要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5](118),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毋庸置疑,孔子的这种均贫富思想明显带有空想的性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在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总量比较匮乏而人们所付出的劳动总量或对社会财富所作出的贡献又大致相当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均贫富”的主张,无疑体现了一种关爱社会弱者的志愿服务伦理情怀和追求社会公平的志愿服务伦理价值诉求。
儒家将理想社会分为两个层次,即“小康”和“大同”。小康社会,法制设计合理,道德规范得到有效遵循,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人们所奉行的是合理利己原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15](119),缺乏仁爱利他情怀。到了大同社会,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15](118)。由此可见,儒家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天下为公”、人人为公;二是凡有劳动能力者均应自觉参加劳动,能劳而不劳、劳而不尽其力、劳而为己都是可耻的;三是无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皆有所养;四是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社会秩序稳定和谐。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世界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表达志愿服务伦理的思想,其所主张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充分体现了儒家致力于关爱和扶助社会弱者的志愿服务伦理追求。
儒家“天下大同”这一志愿服务伦理追求在后世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东晋时期的诗人和文学家陶渊明将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凝聚于《桃花源记》之中,展现出了一幅自由平等、同耕共织、安宁和乐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画卷。及至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以丰富的想象勾勒出了一个“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大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人人相亲,社会保障系统高度发达,人们独立自主、自由自在、舒适安逸地生活着,“其乐陶陶,不知忧患”,不仅“老有所长,幼有所恃”,而且“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孙中山认为“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16](36);“大同”理想即是“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即是“人道主义”,其“真髓”就是“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博爱”“得博爱之精神”,是“广义之博爱也”,它“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16](510)。
儒家“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理想社会的企盼,反映了古人对一个有保障、无饥寒、尽人伦的社会的朴素憧憬,尽管具有空想的性质,但其所倡导的诸多理念,如天下为公、人人平等、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与我们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共同富裕观有着诸多契合与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共同富裕观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家这种“天下大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换言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天下大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的应有使命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所应担负的道义责任和义务。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不可或缺的形式和途径,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使社会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分配如何更加公平合理的问题。要保证分配的公平合理性,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队,就必须针对分配领域日益突出的不平衡问题深化分配机制改革,构建一个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完善的分配体系。而在这三次分配中,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通过公益慈善活动来推动和实现的,也就是说,公益慈善是实现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这意味着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公益慈善将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按照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路进行再分配。公益慈善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志愿服务是其中最为重要且最有活力的形式之一,这就决定了第三次分配的开展离不开志愿服务的推动。换言之,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高度重视志愿服务的作用,大力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无数事实表明,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中,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正在而且也必将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