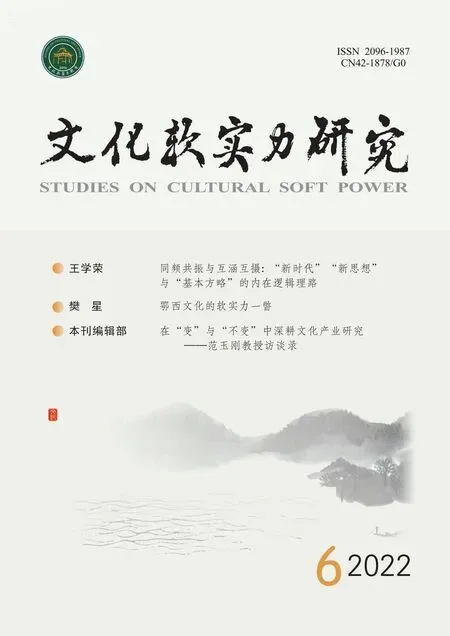评《情感地理学与华语离散叙事》
杜云飞
黎韵孜(Melody Yunzi Li)、小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 Jr.)共同编著的《情感地理学与华语离散叙事》(Palgrave Macmillan,2022)一书以文学情感地理学和空间研究的理论为经,以华语离散群体的叙事为纬,绘制了在不同社会文化、地理空间、情感体验、身份认同和表征实践之间游移不定的复杂集合,各章节的作者从多样的视角与不同的焦点共同讨论了海外华人离散群体对空间/家园的文学表达,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情感和个体经验在文学、电影和视觉文化中的呈现。与史书美从后殖民研究角度以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反对离散暗含的中心主义倾向的研究路径不同,本书的各位作者从离散群体切身体验的地理学诗学的角度出发,向我们展现了文学语言和视觉艺术是如何通过对空间的勾勒而生成一种充满潜力与深度的金石之声。
小罗伯特·塔利的《非一的空间:离散,地形官能症与世界体系》(ThisSpaceWhichIsNotOne:Diaspora,Topophrenia,andtheWorldSystem),这一章更偏重于理论视野的开拓,塔利所谓的“非一的空间”即一种思考离散的空间的方式。离散空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某个他处(elsewhere)或远或近的模糊关联:基本的双重性和杂糅构成了离散空间可供探索的复杂深度。塔利对非一的空间的论述有着清晰的理论谱系,首先借鉴了萨义德所说的流放意识,即流放者对于世界和文化的理解与观察来自至少双重的视角,类似于音乐术语中的“对位”(contrapuntal);而奥尔巴赫的《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中提及的两个拉丁语概念,paupertas(贫穷)和terra aliena(境外之域),也帮助我们去思考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去理解文学的视角,从而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世界的粗暴切割。
值得一提的是,本章标题中Topophrenia一词在目前的中文学界被译为“场所意识”即place-mindness,但这一翻译过度简化了该词中带有精神分析意味的心理内涵,也就是代表“紊乱/失序”(dis-order)及“疾病/忧虑”(dis-ease)的两个方面,因此笔者窃以为“地形官能症”一词能够更完整地标示这一概念中的多重维度。因为离散这一概念则涉及到各种可能的物理移动和心理感受,离散者因其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社会位置也会产生极其异质的情感体验——中产移民、高校教授和底层劳工基于空间所体验的感受必然迥异——所以塔利认为离散群体的地形官能症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异质性地形官能症(hetero-topophrenia)。这种离散意识的模型因其巨大的差异系统,未尝不是一种在当代世界体系内思考微观存在的有益尝试——通过将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视为境外之域、陌生的异域,我们可以摆脱一种中心—边缘的等级制度,从而容纳离散群体多元异质的声音,正如我们在本书其他几章中看到的多层次的离散空间性所展示的原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永恒拉扯的复杂张力。
在第二章中,何淑娴(Elizabeth Ho)从情感地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郭小橹用英语写就的《恋人版中英词典》(AConciseChinese-EnglishDictionaryforLovers)基于个体情感体验对地理象征意义进行女权主义重构的过程,强调了一种后再现式的制图学对于文学阅读的重要意义。所谓的后再现式,也就是不再以社会文化建构、某个领域约定俗成的概念等等再现式的词汇去理解对象,而是一种格外强调行动与互动过程中的感知与体验的经验论。斯威夫特曾对非再现理论做过这样的定义:“行动成为一个关系性和物质性的交叉地带,身体、物、情感、动能、空间、时间等因素都在行动中聚合起来……在非再现理论的视阈中,(复数的)世界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涌现’的状态,或者说世界自身一直处于世界化的过程中。”在本章作者看来,《恋人版中英词典》中女性主人公Z在欧洲这个异域的体验和手绘地图的行为,无疑是一种以情感体验重新绘制再现式的世界版图的尝试,这种向非再现性的转变一方面强调了情感因素在人文地理领域中具备的可供阐释的深度和潜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这部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的性别和性别体验——Z在其所绘制的自反性的地图文本内感受到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自我就是基于情感体验的自我,而她对于欧洲地理的所有认识和感受都来自于她的情感、知识结构和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在欧洲(申根区与非欧盟)所感受到的权力关系,从一个被主流的地理想象边缘化的观察角度强调了情感地理学的重要意义与叙事价值。本文通过对Z的非再现绘图行为进行细读,揭露了众多内嵌在再现式地理学中的权力结构——基于国家边界的政治共同体对外来者(齐美尔所谓“陌生人”)的管制与偏见,以及传统地理学意义上边界、领土产生的视觉效果对人们的认知世界的影响等。本章作者所利用的非再现式的制图学——一种重视经验的空间现象学——无疑在分析情感和地理空间时具有巨大的阐释力。
本书有三章内容关注电影文本,其中第三、四章聚焦的是有关穿越边境的华语叙事。侯小龙(Dorothee Xiaolong Hou)通过将《下海》(2017)和《站街女》(2015)两部电影的影像话语文本和中国“锈带”的语境研究相结合,讲述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性工作者在法国/巴黎和家乡城市之间的差异经历、文化创伤、身体和情感景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电影中呈现的离散群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永久移民,而是短期务工的群体,正如项飙对于短期迁移的研究所指出的,短期移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悬浮”的情况,他/她们暂停了自己的社会家庭关系,投身于经济劳动,同时在政治上处于失语的状态。吴国坤(Kenny Ng)则选取了应亮的《自由行》和白雪的《过春天》两部电影来探讨大陆和香港边境上的迁移景观如何改变人们对于家园和边界的体验与想象。马圣美(Sheng-mei Ma)则通过圣洞(holy hole)的隐喻与道德经诸意象的联系,从女性主义视角祛魅了大众文化和流行影视(包括武侠剧、古装宫廷剧和其他当代影视作品)中的父权神话。
乐桓宇在本书第五章中,通过分析李永平在其作品《吉陵春秋》中塑造的故事空间(想象中的中国)与建构的怀旧乡愁,一方面论述了李永平如何以双重错位置换的异国情调勾描了一处作为精神故乡的充满“中国性”的异国他乡,另一方面又从李永平模仿中州正韵的准文言杂糅地方白话方言的语言风格入手,描述了其乱序排列的故事中重复而破碎的梦境所制造的似曾相识的阅读体验。基于对拉康的公式N+1的阐释和改写,乐桓宇将错置的乡愁视为本源之N基础上的N+1,即基于想象而对本源进行的不间断的重新构建和增殖,因而《吉陵春秋》可被看作是N到N+1的连续序列;而其作品中文学性的似曾相识则源于一种更加飘渺的无根的梦幻性,因而是对原初之物N的缩减即N-1,在某种层面上这一故事又是N-1的不断重现。通过对作品的时空想象和语言风格鞭辟入里的分析,本章作者认为,应该将《吉陵春秋》视作一种基于加减法之上的空间记忆的建构,但是这种对真实本源之N的执迷追求却并未实现李永平所声称的对“纯中文”或“中国性”的寻求,而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浑浊和杂糅。作者的结论似乎认为这部作品存在缺憾,但这种杂糅本身恰恰是文学地理学的景观增殖,而难以企及的纯洁性也许恰恰彰显了语言这一象征秩序无法企及的实在界,对于离散文学而言,“中国性”可能就是先于语言符号存在的无法被象征化的剩余之物。
《在第三空间的文学流亡》中,邱萍(Ping Qiu)解释了哈金在《自由生活》一书中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批判。从霍米·芭芭和萨义德的理论出发,邱萍详述了哈金如何在其文学创作的空间中深化了亚裔美国人研究中的“既非/也非”(neither/nor)的斜杠政治。通过批判将地理空间的理解简化为基于民族国家的空间分割,哈金在其文学叙事构建的第三空间内重新思考了家园、语言和自由等重要的主题。黎韵孜则从哈金与刘柏川(Eric Liu)对纽约唐人街的描绘中,展示了情感地理学的绘图模式与华人移民对空间的体验与认同的挣扎。
在第七章《重绘纽约唐人街》中,黎韵孜基于德塞都《日常生活的实践》的理论——行人在城市中的行动可以挑战社会秩序和权力布置——分析了纽约曼哈顿旧唐人街的边界与位于法拉盛的新移民区的情感空间,也解读了刘柏川和哈金对移民身份认同这一问题的相似表达:通过文化同化进入主流社会,从而摆脱原文化的限制并建立新的身份是常见的认同过程,但文化空间上的距离感和难以根除的文化遗产始终伴随着个体的生命体验。不过本章在分析旧唐人街的空间边界对移民群体进入主流社会的限制时,似乎缺少了一些德塞都理论的批判性,并没有深入剖析刘柏川的话语内含的社会权力机制。
总而言之,《情感地理学与华语离散叙事》一书中作为方法的非表征的空间/地理学,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离散叙事研究中展现了极具潜力的阐释效力,无疑为我们重新理解文学空间和情感地理的结合提供了充满前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