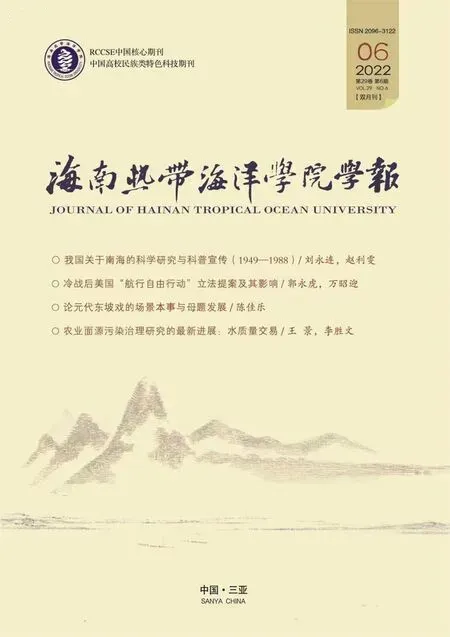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一)
郭 渊
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而言,研究历史的纬度应是价值尺度和行为规鉴,前者主要表现于道德、情感领域,后者则是总结经验,以获得对当下及未来行为的进一步指导。这是历史研究的崇高功能。然而对大多数学者来说,研究的主要指向是具体的历史世界,即在一个由事实、人物和种种偶然性组成的具体历史场景,“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的作用而编织成的网络”[1]。在这一知识网络中,他们能够汲取源于历史的真正智慧,从而获得一定的历史启迪和行为规鉴。南海历史研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钩沉跌宕起伏的南海时空的历史痕迹,为现今开创和平友谊之海提供经验教训。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所说:“对于我们来讲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要懂得记忆,并且要借助记忆而生活。”[2]
如果对南海历史与现实的研究,陷于狭隘的争执、博弈视域之中,即退化为纯粹的纷争现状,那么就难以登高望远,即难以用恢宏的视域审视历史,展望未来,从而更加难以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如何思考历史,决定了我们可能的限度。”[2]对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长远发展而言,谱写南海现实与未来的最强音应是和平与发展。本期所发《我国关于南海的科学研究与科普宣传(1949—1988)》一文叙说新中国成立到海南建省这一阶段南海的科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研究的显著进步,人文学科研究的精深发展。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为以后中国学者研究南海相关问题提供借鉴。
如何能更好地发挥南海历史研究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研究者对南海历史的深度把握与审视,体现在他们广泛阅读核心文献的基础之上。通过钩深致远,研究者必然会带领我们看到不可能通过推理来了解的若干南海历史情节,至于说如何使这种历史经验上升到理性思维,进而成为对南海历史发展方向的把握,不仅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学识、非凡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毅力,还要有敏锐的心灵和通达的悟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海疆建设的规划、投入以及人民建设海疆的热情逐渐提高,关于南海的科普宣传也逐步丰富起来。在此过程中,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科学研究与宣传教育对维护南海主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根据历史经验的总结,南海秩序的建立既有赖于相关国家、国际社会对海洋关系良性运作的建构,更有赖于他们对相关规则、协议的达成与执行。笔者曾著文认为,利益理性是构建海洋法治秩序的认识论基础,缺少利益理性的海洋规范是盲目的法治秩序,而缺少海洋法治的利益理性是片面的利益理性;海洋法治秩序的生成是海洋利益主体理性自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国际海洋秩序建构的趋势[3]。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以及相关国家共同推进南海秩序向前发展,业已形成比较好的多维局面。为使该项工作持续、有效地进行,上述行为主体共同打造全球海洋治理的局面就尤为必要了。本期的《中国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海洋合作的新机遇——“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首批行动方案的思考》一文叙述了“海洋十年”首次召集行动方案的成功,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
近些年来出现的众多著述提供了作者对南海若干问题的深刻洞见。在南海知识系统构建中,我们对相关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对某个历史与现实断面考察得越细致,就越能真正看到南海历史与现实变迁背后的复杂动因,也才有可能把握住看似纷繁复杂事物的本质。《冷战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立法提案及其影响(1991—2021)》,以冷战结束后30年美国国会相关法案文本为依据,指出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立法活动在全球强推美式“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破坏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规范的海洋秩序。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有些学者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他们系统地揭示了南海历史与现实的诸多问题的本质。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建设中,与他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任重道远。《人文社科领域南海问题国际研究动态(1974—2021)》认为,某些欧美学者发表的成果影响力颇大,对中国南海历史及政策存在误读和曲解,这需要我国历史专家多维塑造国际话语权,澄清南海历史真相。
不管南海历史研究是关注于知识的重构还是现象的解释,都必须立足于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而不能凭空想象或推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指出的:“不管历史学家主要关注于重构还是解释,关注于有其自身合理性的过去还是着眼过去能有助于说明现实,他或她实际能做的首先取决于残缺资料的范围和特征。相应地,历史学家对各类研究的表述也必须从那些资料开始。”[4]南海历史研究要将过去特定的语境书写成我们可以理解的情况,尤其是要复原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或人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通过艰苦的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网络,这才有可能明晰这些事件或人物在网络中的位置与功能。换言之,就是要将其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必然以今天的观点来书写南海历史,其中必然有我们的情感与认知,如此才有可能构建一个可塑性的南海知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