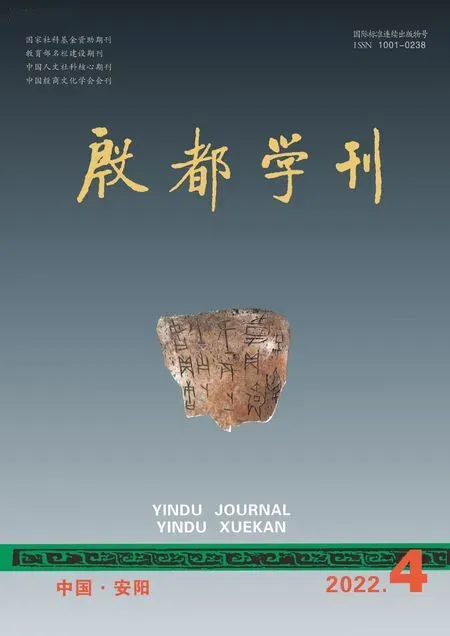传统史学的近代回响
——以吕思勉中国通史著作与赵翼史学关联为中心
王云燕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00)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坛名家辈出,史学家严耕望曾提出“前辈史学四大家”一说,认为:“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1)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四位成就卓著的史学家中,陈垣、钱穆、吕思勉三位都曾对乾嘉学人赵翼的史学予以高评,并深受其史学思想影响。(2)陈垣有言,“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 其中的“瓯北”代指赵翼(字瓯北),认为其史学足以和陆游(代表作为《剑南诗稿》)的诗文相媲美。钱穆十分欣赏赵翼的史学代表《廿二史札记》,称“赵氏非考据家,乃一史学名家。赵著确有其精彩处。余之欣赏此书,以其人极有智慧,颇富哲学味”。吕思勉亦称赞该书“专就正史之中提要勾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三人之中,吕思勉与赵翼之间的学术渊源最为密切。有论者称,“在治史旨趣上,赵翼鲜明的经世意识、宏阔的历史眼光、开明的进化史观、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对民生吏治的关切,都对吕思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3)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第207页。赵翼对吕思勉确有一定影响,但是否如论者所言之广泛和深远,还需借助具体事例加以探讨。
一、吕思勉对《廿二史札记》的认知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恰与赵翼是同乡。有清一代,常州地区人才辈出,涌现出赵翼、洪亮吉、孙星衍等一批知名学者,常州学派更是名噪一时,前辈学人的学术思想对吕思勉学术风格的形成影响颇深。赵翼是他敬仰的家乡先贤之一,在回忆治学经历时曾说: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页。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4)吕思勉述,文明国编:《吕思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页。
赵翼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是吕思勉最早涉猎的史部书目之一,不仅触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还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
吕思勉治学重视考据,提倡“讲史学离不开考据”(5)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93页。。他将这一治学特点归结于赵翼、顾炎武、梁启超三人的影响,自称: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6)吕思勉述,文明国编:《吕思勉自述》,第28页。
他不止一次将《廿二史札记》和《日知录》两书并提,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经历时也说:
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7)吕思勉述,文明国编:《吕思勉自述》,第22页。
由他开列的《古书名著选读拟目》中还将两书归为一类,注解称:“读数卷,以见读书之贯穿事实及钩考有关致用之问题。”(8)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362页。在《怎样读中国历史》这篇专论治史的文章中,又说:
(一)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卷八至十三。(二)赵瓯北先生之《廿二史札记》。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勾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都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9)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392页。
在他看来,两书都是可供现代治史者参考的范本,且有一定相通性。这一论断恰与赵翼的初衷相契合,他治史虽无师承,却私淑顾炎武,《廿二史札记》书前的小引中特别注明:“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1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以自谦的方式表达对《日知录》的追慕、效仿之意。众所周知,顾炎武治学以明道经世为宗旨,尝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1)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下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429页。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对赵翼影响颇深,主要表现为他密切关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问题,流露出强烈的会通古今、以史为鉴倾向。与乾嘉学人大多沉迷于考据的学风相违,他治学不拘泥于狭义的考证,多是在考史中论史,发表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寓经世思想于历史评论之中,形成了个人的学术特色。
与赵翼同时代,以历史考证出名者还有钱大昕、王鸣盛两人。三家的正史考证著作并称“乾嘉三大考史名著”,虽同为正史考证,却同源不同流。吕思勉认为:
清代考据家之书,钱辛楣的《廿二史考异》,最善校正一事的错误;王西庄的《十七史商榷》,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专搜集一类的事实,将其排比贯串,以见其非孤立的现象而发生意义。(12)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371页。
这一说法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梁、吕两人一致认为钱书长于校勘,赵书长于贯串,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史风格。杨树达先生曾将考证派分为两枝,“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西庄书至驳杂,兹据其一部分言之。)”(14)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55页。这一说法较为贴切地阐明了钱大昕与赵翼的学术差异。从史学方法论层面看,治史不外乎考证与解释两途。它们并非对立关系,只是观察视角和思辨程度的不同,在史学研究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就吕思勉本人而言,他虽然重视考证,但反对单纯的考证,明确指出“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15)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526页。。“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6)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750页。。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能以考据和史料为目的,而应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有所发明,在宏观把握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总体情状的前提下,揭示出历史发展、进化之规律,与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有一定相通性。
20世纪上半叶,以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一度占据学术主流,这派学人“差不多都遵奉同一种以材料整理为宗旨的实证范式”。(17)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这种治学范式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发展而来,故有学人将此命名为“乾嘉范式”。吕思勉并不追逐这种以考据和史料为中心的治学范式,他的治学风格属于博通周瞻的一派,追求融会贯通。显然,长于历史解释的赵翼比长于考据的钱大昕更接近他的学术追求。
二、吕思勉读史札记对赵翼史论的评析
清人治学好写学术札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记叙早年游学于学海堂及京师时,尚见“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第58页。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皆以札记体撰写而成,《廿二史札记》更是直接以“札记”冠名。赵翼自叙“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则札记别纸”(19)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页。,积久而成著作。他治史长于综合归纳,对历代大事的钩稽和评论是《廿二史札记》的一大特色,差不多每个时代都提炼出一些与“古今风会之递变”、“治乱兴衰之故”(2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页。相关的专题,不仅便于了解中国历史梗概,且大多抓住了各时代特征,历来为人称道。就治史方法而言,此类条目先借助大量同类史料排比而后得出普遍性认识,与近代极为流行的归纳法如出一辙,梁启超称此方法为“属辞比事”,指明“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2页。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伴随西学的大规模东渐,传统学术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以西方新学理、新方法为参照,整理中国旧籍,阐发旧学新义,成为学术演进的一大趋势,也为民国学人重新发现赵翼提供了历史机遇。当接受了西学的梁启超重新审视传统学术时,最先发觉赵翼史学中蕴含的鲜明治史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归纳法有很大相似性,适时从史学方法论视角对其加以诠释,为时人重新认识赵翼史学开辟了新方向。梁启超的呼吁唤起了学界对赵翼的关注,诸多学人延续他开辟的路径,继续为之揄扬,极大提升了赵翼的史学声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并非始于赵翼,乾嘉学人中精于此二法者也并非他一人,后世却将《廿二史札记》视为比较及归纳法治史的典范。蔡尚思甚至说:“古人读尽全部正史而又能作归纳比较的深入研究者,以此书为第一。”(22)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页。究其原因,在于赵翼熟练地将比较、归纳之法用于宏观问题的历史解释中,擅长“运用考据学家所惯用之归纳方法与比较方法以观察盛衰治乱之原,超越于孤立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发展的通则。”(23)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第378页。这种历史解释倾向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缺少,而近代史学却甚为重视的,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是比单纯考据更高一层次的学术追求。吕思勉认为赵翼史学的可贵之处,恰在于能够“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24)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392页。。由是而论,赵翼史学之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卓越的治史方法,还表现为精辟的史学识见。他眼光敏锐,往往能发现隐藏在纷繁史料背后的问题,有关一代大事的提挈和评论多能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之论。
从民国学人对赵翼史学的接受情况来看,有两种取向较为突出,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对其史法的阐扬,一是对其史论的承袭与发展。就吕思勉个人而言,他不仅欣赏赵翼的治史方法,还钟情于其阐发的史论,可谓两者兼具。有关吕思勉对赵翼治史方法的借鉴,较为人所知(25)详参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李波:《吕思勉与清代常州学术》,《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金顶挑:《吕思勉的历史研究特征及其启示》,西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至于史论方面的汲取,则语焉不详,有必要集中进行探讨。受顾炎武、赵翼等清儒影响,吕氏治史从撰写读史札记入手,“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26)汤志钧:《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学人杨宽曾如是评价他的读史札记:“除了对史实作必要的考订以外,十分讲究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着重于探讨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注意摸索重要典章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其变化原因。”(27)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嵩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页。这与赵翼的治史风格十分接近,细读吕氏读史札记可以发现,其中不乏关于赵翼史学札记的引用和具体评论。从内容来看,大致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赵翼史论的认同与拓展。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多次引及《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两书的史论,并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譬如,《燕史札记》中《汉世豪杰多能读书》一条,称:
《廿二史札记》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历举光武功臣,多习儒术,与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一条并观,可见世变之亟矣。然其所言,犹有未尽者。(28)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第586页。
论者肯定了赵翼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围绕“汉世豪杰多能读书”这一主题,补充《后汉书》的相关史料,就儒学对后世政治的影响展开探讨。又如《唐将帅之贪》一条就《陔余丛考·南宋将帅之豪富》条的观点做出补充:
赵瓯北《陔余丛考》有论宋南渡将帅之富一条,往者读之,未尝不叹息于国家之败,由官邸;官之失德,充赂彰;宠赂之彰,武人尤甚;恢复之无成,未始不由于武夫之贪黩也。然何必宋,唐中叶后将帅之贪侈,恐有甚于宋之南渡者矣。(29)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0册,第842页。
吕思勉不仅认同赵翼关于南宋将帅之富的论说,还进一步延伸到唐代,揭示唐中叶以后将帅的贪侈之习。此外,《京债》、《论金银之用》、《续论金银之用》等条皆在承袭赵翼论说的基础上增益史料,拓展其说,得出更为全面、深刻的见解。
其二,对赵翼史论的辨讹订误。赵翼的史论虽见解独到,却并非精确无误。吕思勉在借鉴赵翼史论时,持一种客观、审慎的态度,不时对其观点进行考辨纠缪。如《汉人多从母姓》一条纠正《廿二史札记》中《皇子系母姓》条的观点,谓:
《廿二史札记》言“汉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为称”,举卫太子、史皇孙为例。实则其以母姓为称,与其封不封无涉。(30)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第491页。
《后魏吏治之坏》一条驳正《北齐以厮役为县令》条的观点,称:
《廿二史札记》谓魏入中原,颇以吏治为意,及其末造,国乱政淆,宰县者乃多厮役,入北齐而更甚。(卷十五)此误也。(31)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0册,第711页。
《魏立子杀母》一条纠正《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条的观点,称:
《廿二史札记》云:“……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遍检《魏书》,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邪?《北史》亦同此误。”今案魏自道武以前,曷尝有建储之事,况云欲立其子而杀其母乎?往史之诬,不待辩也。然云其例始于道武亦误。(32)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0册,第714页。
以上诸例皆为对赵翼观点提出异议者,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吕思勉以赵翼发表的史论为参照,广泛搜集史料,在具体的史实考证中,不仅订正了赵翼的错误,还获取不少新的认知,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对他后来的中国通史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三、《白话本国史》对赵翼史论的承袭
近代史学偏向专题研究,然吕思勉却以通史撰述见长,并凭借出色的通史成绩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是他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因体例新颖、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名震一时。顾颉刚回顾中国通史写作历程时曾言:“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33)顾颉刚撰,王晴佳导读:《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页。如其所言,吕思勉的通史创作一改前人条列史实之弊,多阐发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见解中有不少是受赵翼史论的启发,兹先以《白话本国史》为例,加以说明。
《白话本国史》又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初版于1923年。吕思勉秉承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精神,以进化论为指导,《绪论》中特别强调“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3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在进化史观的统摄下,他叙述历史时不仅重视历代政治兴亡原因的总结,还尽力揭示社会进步之轨迹,意在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和融会贯通,向读者展现社会的整体情状,通览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全貌。赵翼的史论因触及吕思勉感兴趣的内容,被多次引据。例如,西汉初年,开国功臣多出身平民阶层,赵翼在归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经典论断。吕思勉深受启迪,特意指出: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有一段论这事的,题目是《汉初布衣卿相之局》,考据得很精详,可以参看一参看。”(3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177页。
又如谈及魏晋南北朝的学术风气时也备注参考赵翼之论,称:
自隋以前,北方的学者,大抵谨守汉儒的学问。熟精《三礼》的人极多。(参看《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这便是郑玄一派学问。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这并是今文学了。至于南人,则熟精汉学的,久已甚少。(36)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336-337页。
此处以《廿二史札记·北朝经学》一条的观点作为立论依据。叙及南宋与金的和议时亦引据赵翼之史论。关于绍兴和议一事,后人基于各自立场和理解,发表不同的观点,至今聚讼不已。赵翼之说颇具代表性,他提出: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3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86-587页。
他尝试从义理、时势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指明金强宋弱的情形后,断定宋金和议乃时势之必然。其论断备受后人争议,不少学人对此持反对意见。金毓黻据此指出,“南宋与金成相持之势,而得偏安于一隅者,由中兴诸将善战之所致也”(38)金毓黻:《宋辽金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3页。,而非和议之效用。周谷城也认为,“赵说颇带主观成见,且讥嘲义理派,恭维时势派,都是今日的我们所不能同意的”(39)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第218页。。甚至有学人将此称为赵翼的“汉奸哲学”。(40)陶懋炳认为,赵翼的汉奸哲学,最典型的是卷二六《和议》条所云,见氏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仓修良也指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颠倒,而且宣扬了汉奸卖国的反动哲学,其危害性之大自可不言而喻,见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9页。吕思勉则反其道而行之,他非但认同赵翼的主张,强调“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议》条。)”(41)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下册,第409页。,还以此为据为秦桧开脱,为后来《白话本国史》的查禁风波埋下了伏笔。(42)关于《白话本国史》被查禁的原因,可参看王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吕思勉自认为,“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43)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2页。藉此可见,在征引他人观点时是经过一番审慎思考,而非率意而为,以上诸多征引《廿二史札记》的例证足见其对赵翼史论的服膺。除以上直接引用的情况外,书中还有不少参考赵翼观点而未加标注者,大致可归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朝代衰亡原因的总结有相似处。赵翼史论中有不少涉及“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探讨。吕思勉也对王朝衰亡之原因颇感兴趣,他在本书《绪论》中提到:“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他的‘原因’,就可以预测他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 ’的法子。”(4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3页。基于此目的,他特别注重对历代兴亡原因的总结,书中有不少章节专门探讨此类问题。巧合的是,两人的诸多观点不谋而合,最典型的当属对东汉、唐、明三朝宦官之祸的分析。赵翼曾言:“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45)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14页。《廿二史札记》中以宦官为研究对象的条目达15条之多。(46)具体条目包括:《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宦官亦有贤者》《魏以阉人为外吏》《北齐有贤阉》《唐代宦官之祸》《唐宦官多闽广人》《万历中矿税之害》《明代宦官》《魏阉生祠》《阉党》《明代宦官先后权势》《喜宁之擒》《曹吉祥 江彬》。吕思勉论述三朝衰亡原因时也分别提到宦官专权问题,观点多有相似之处。先就东汉一朝而言,吕著认为宦官得以重用的原因是:
宦官的品类,固然是不齿于人的,然而他和皇帝极为接近。从来做皇帝的人,大概是闭置在深宫之中,毫无知识。天天同他接近的人,他如何不要听信。(47)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216页。
赵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国家不能不用奄寺,而一用之则其害如此。盖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嚬笑而售谗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4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13页。
此外,对东汉宦官掌权过程的梳理亦颇为接近,吕著称:
前汉时代……在宫禁里侍候皇帝的,还多用些士人,而且要“妙选名儒,以充其任”。和帝时,邓太后秉政,才把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官,都改用阉人。历代君主,又都和他们谋诛外戚,于是宦官的权力大盛。(49)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216页。
赵书谓:
汉承秦制,以奄人为中常侍,然亦参用士人……和帝践阼幼弱,窦宪兄弟专权,隔限内外,群臣无由得接,乃独与宦者郑众定谋收宪,宦官有权自此始……和帝崩,邓后临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权渐重。(5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11-112页。
前后对照可知,两文在立意、观点、文字表述上十分接近。不同的是,吕著偏向言简意赅的概括性介绍,赵书则列举诸多史料作详细探讨。此处借鉴赵说时,只是有针对性的汲取观点,并不兼及具体史料。
吕著论及唐代宦官专权之弊时,较东汉一朝为详,单独撰有“宦官的专横”一节。《廿二史札记》中也撰有《唐代宦官之祸》一条,两文在选题、立意、史料选取、文字表述方面皆有相近处,借鉴程度较上一例更甚。兹撷取相关内容汇入下表,以资对照。
《白话本国史》与《廿二史札记》文本对照
1.《白话本国史》
(1)然而从中叶之后,也未尝无有为之主,而始终不能振作,则实由于宦官把持朝局之故。宦官所以能把持朝局,又由于他握有兵权之故。所以唐朝宦官之祸,是起于玄宗,而成于德宗的。
(2)唐初的宦官,本没有什么权柄。玄宗才叫宦官杨思勖出平蛮乱。又信任高力士,和他议论政治。于是力士“势倾朝野”。权相如李林甫、杨国忠,尚且交结他。至于太子亦“事之以兄”。然而高力士毕竟还是谨慎的。肃宗即位后,宠任李辅国……代宗又宠任程元振、鱼朝恩,一味蔽聪塞明,以致吐蕃入侵,兵锋已近,还没有知道,仓皇出走,几乎大不得了。然而这时候,宦官的兵权还不甚大。

2.《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
(1)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

(3)……自德宗惩泾师之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以内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全归宦寺。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僖宗纪赞》谓,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案《本纪》,宪宗时,太子宁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丰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遂王宥为皇太子。宪宗崩,宦官陈弘志杀承璀及恽,以皇太子即位,是为穆宗……敬宗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害帝,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江王即位,是为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犹敬宗未有太子,故讨贼立君,亦尚出于正。至文宗在时,已立敬宗子成美为皇太子矣,及大渐,宰相李珏、枢密使刘弘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监国。乃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颖王瀍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则废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恶更非陈弘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马元贽立光王怡为皇太叔,即位,是为宣宗。(时武宗未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马元贽之力也。宣宗疾大渐,以夔王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而中尉王宗实及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实等之力也。懿宗大渐,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刘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渐,群臣以吉王保最贤且长,欲立之,观军容使杨复恭率兵迎寿王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杨复恭之力也。统计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权,尽归宦寺,宰相亦不得与知。且不特此也,宪、敬二帝至为陈弘志、刘克明等所弒,昭宗又为刘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极……文宗欲倚李训、郑注诛宦官,甘露之变,反为仇士良等肆逆,横杀朝士,横尸阙下,帝亦惴惴不保,仅而获免……卒之朝廷纲纪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宋景文谓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筦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52)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 第 452-455页。
注:此据《白话本国史》的段落结构分行,内容相近者用同一类型的下划线注明,引文省略部分是一些具体的事例描述,本文着重探讨的史论部分以“双下划线”标示。
唐代宦官专权的事迹散落于正史的不同纪传,赵翼运用排比、归纳之法将相关史料分类编排,不仅厘清了宦官掌权的始末,还总结出宦官之祸产生的原因:“假之以权,掌禁兵,筦枢要,遂致积重难返。”吕思勉采用相同的方法,选取同样的事例,做出相似的评论,尽管在叙述思路、人物事迹的次序排列方面略有差异,承袭痕迹依旧一目了然。
明代同样存在宦官专权问题,赵翼谓:“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53)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48页。吕思勉也说:“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5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下册,第510页。两人皆认识到宦官专权对明朝政局造成的危害,并就王振、汪直、刘瑾等权阉的种种劣迹做了说明。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类特殊人群,由宦官引发的宦祸是封建皇权政治中的一道奇景。东汉、唐、明三朝的宦祸最为严重,赵翼采用比较、归纳之法,梳理其经过,指责其弊病,分析其原因,由此阐发的精辟史论被后人广为称引,吕思勉也难免受其影响。除以上所述外,有关两汉外戚、唐代藩镇、明末党祸等问题的阐释也与赵翼之论有相似之处,囿于篇幅,不再详述。
第二,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评论有相似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赵翼史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评论历史人物往往不为传统观点所囿,勇于提出独到的见解。比如,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南宋以后,否定王安石的评价一直占据主流,他主持的变法也被视为北宋覆灭的导火索。赵翼虽也知晓“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55)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93页。的主流意见,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变法失败的责任不能强加于王安石一人,“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5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93页。,“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5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94页。。在他看来,宋神宗作为王安石变法的背后支持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不惟如此,他还借考证青苗法之缘起为王安石正名。他经考证发现,青苗法并非王安石首创,在此之前,陕西转运使李参就曾实行该法,指责“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5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95页。的现象。还进一步解释说,青苗法推行的初衷“本以利民”,“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59)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95-596页。换言之,王安石实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为利民,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不肖官吏从中舞弊,才由利民变为害民之策。赵翼的这一论断颇具卓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清末,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时,不但充分肯定王安石的学术人品,还高度评价熙宁变法,至此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彻底转变。吕思勉也高度褒奖王安石:“王荆公是我国有数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数的政治家。”(60)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384页。评论青苗法时他借用赵翼的观点:“‘青苗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所行”(61)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第384页。,又分析了当时反对青苗法的五个理由,指出青苗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奉行不善才会弊病丛生,责任本身不在王安石,不能据此全盘否定他,与赵翼的观点十分契合。
又如评价王伦时,也表现出相似的观点。王伦是两宋之交一个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对金主张议和,又颇受秦桧信任,故遭时人抨击,后世对他也有非议。赵翼对此不以为然,辩驳道:
王伦使金,间关百死,遂成和议。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数犯法幸免之语。不知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6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50页。
前文提及,赵翼反对以义理思想为标准评价宋金关系,强调历史评价必须参酌客观时势。然宋儒多不能正视现实,从义理出发反对议和,并对主张议和者大肆抨击,胡铨等人对王伦的诬陷正是这一现象的直观写照,赵翼对此深为不满,从当时的具体形势出发,极力为其辩诬。他认为宋得以收复河南、陕西之地,与王伦的外交努力关联甚大,还解释说:
设使金不渝盟,则存殁俱归,境土得复,伦之功岂南渡文武诸臣所可及哉!只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毁前议,伦遂被拘于河间。(63)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50页。
他本着知人论世的精神,结合具体时代背景来为王伦辩护,充分肯定了其外交功绩和“历百艰而不顾,而徇国之烈,甘一死而不挠”(6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51页。的民族气节。《白话本国史》中谈及王伦时也说:“王伦的外交,也很为有功,不过《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坏人了。”(6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下册,第412页。与赵翼一样,吕思勉亦不认同《宋史》中对王伦的评价,并对此提出质疑:
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66)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下册,第412页。
这段文字的立意和观点与赵翼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人均认可王伦在外交上取得的功绩,并极力为之辩解,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
以上所举诸例虽未直接注明引用赵翼史论,但借助文本对照可发现,无论是选题、立意、史料采择、观点表述方面均表露出借鉴的痕迹。加之,吕思勉本人对《廿二史札记》推崇备至,文中又不止一次引用其观点,更加证实了两者的承袭关系。事实上,不独《白话本国史》,吕思勉的另一部通史教科书《吕著中国通史》(又名《中国通史》)也深受赵翼史学思想影响,引证赵翼史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且多以明引为主,接下来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四、《吕著中国通史》对赵翼史论的借鉴与发展
《吕著中国通史》创作于抗战期间,与《白话本国史》断代分期式的写作体例不同,该书采取一种新的体例,以政治、文化各自为篇,厘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文化史,通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下册为政治史,按时代顺序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按吕思勉的理解,“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故甚习详。”(67)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页。为此,他采用了这种“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68)吕思勉:《中国通史》,第6页。的新体例。如此一来,既突出经济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又兼顾了政治的发展、变革,可谓一举两得。
与《白话本国史》相比,本书的一大特点是突出社会文化的内容和地位。然而,以往的史实记载主要偏重政治方面,有关社会状况的材料不仅数量相对少,而且零碎,搜集、整理十分不易。赵翼史著中与社会风俗、风气、信仰、制度等相关的条目,因触及著者重视的社会文化问题被屡次征引。与前书不同,《吕著中国通史》中承袭赵翼成果时并不局限于《廿二史札记》一书,还涉及《陔余丛考》,按借鉴内容大致可分为史论征引和史料提取两种情况。兹将其荦荦大者,列举如下:
第一,直接征引赵翼史论者。如第一章《婚姻》论述古代掠婚现象时,引用《陔余丛考·劫婚》一条的观点,称:
古代掠夺婚姻的习惯,仍有存于后世的。赵翼《陔余丛考》说:“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 。”(69)吕思勉:《中国通史》,第24页。
又如第四章《阶级》谈及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时,注明参考《六朝重氏族》一条的观点,原文称: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馀丛考·六朝重氏族》条)。此等限制,直至唐代犹存。(70)吕思勉:《中国通史》,第65页。
稍后,分析门阀衰败的原因时,又将《廿二史札记》中相关的论断汇集到一起,分析道:
这时候的门阀,为什么只剩一个空壳呢?(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做事太无实力。这只要看《廿二史札记·江左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各条可见。(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看《廿二史札记·财昏》,《日知录·通谱》两条可见。(71)吕思勉:《中国通史》,第65页。
谈及种族间的阶级分别时,特别提到了金、元两朝的种族政策,此间又借助《金末种人被害之惨》和《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两条的论说。综而观之,仅第四章一章就先后援引了赵翼两部史著的7条史论。这些条目原本分属于不同的卷次,以独立个体单独存在,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关联。吕思勉独具慧眼,不为原书框架所限,有意识将分散在各处的相关条目汇集到一起,重新布局谋篇,与其追求融会贯通的治史风格一以贯之。除以上几例外,书中汲取赵翼史论的情况尚不在少数,旨在借助赵翼的言论为其论述提供史料依据和论述基础。
尤应注意,吕思勉借鉴赵翼成果时并非盲目吸纳,而是从不同条目中汲取所需内容,按自己意志重新编排,显示出强烈的主体自觉。吕思勉虽出身旧学,治学观念却并不保守,试图立足旧学,融会新知,自言:“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72)吕思勉:《中国通史·自序》,第1页。通观全书,诸多章节中都贯穿着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史学家童书业对此做法大为赞赏,称其“讲文化史,处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同时也处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73)童书业:《介绍一部最有价值的中国通史》,载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89页。此言不仅指明了吕思勉文化史撰述的风格,还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他广泛采纳赵说却不为之所囿的原因。一方面,他需要借助该内容作为论述的史料依据。另一方面,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又为之提供了理论指导,使他能够从全新的视野和高度去审视以往的历史,得出不同的结论。故而吕思勉在沿用赵翼史论的同时也有所质疑和补充。譬如,第十二章《货币》言及后世黄金变少的原因时指出:
从前的人,都说古代的黄金是多的,后世却少了,而归咎于佛事的消耗。(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都如此说。)其实不然。(74)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95页。
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汉多黄金》一条中曾指出,佛教的盛行是汉以后黄金减少的一大原因。《陔余丛考·元时崇奉释教之滥》一条也曾历陈大兴佛事造成的黄金损耗,吕思勉所指盖本乎此。他并不认同赵翼的观点,而是参照社会学的理论,借助对人民生活方式的考察,提出了新见解:
古代所谓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见其多。后世人民生活程度渐高;服食器用,等差渐破;以朝廷所聚之数,散之广大的民间,就自然不觉其多了。(75)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96页。
他重视对生活方式的研究,认为“读史的人,恒不免为有明文的记载所蔽,而忽略于无字句处”(76)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96页。。故另辟蹊径,通过对古代人民生活方式的具体考证,得出与赵翼截然不同的结论,展示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又如,第十五章《教育》中又对《陔余丛考·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一条的观点进行纠正和补充,赵翼谓:
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京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77)赵翼撰,曹光甫点校:《陔余丛考》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8-269页。
吕思勉则指出,赵翼所言颇为失考,称:
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78)赵翼撰,曹光甫点校:《陔余丛考》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6-237页。
此处以《汉书·儒林传》的史料为据,反驳赵翼的“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京师”一说,指出至东汉初年,私家授徒讲学已十分兴盛,纠正其观点的同时,还补充说:“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太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79)吕思勉:《中国通史》,第237页。赵翼对历代史事的评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时代局限,难免存在就事论事的缺陷,显然不能满足新史学家对历史规律和因果关系的追求。因而,吕思勉在承袭赵翼史论的基础上,又借社会科学之助,返观中国历史事实,疏通知远,通观其变,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二,从赵翼史著中汲取相关史料。赵翼的史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他每立一论都广泛征集证据,提炼典型史料,列举多证,便于吕思勉直接从中撷取所需资料。《吕著中国通史》中多次直接挪用赵翼引述的史料,譬如,第九章《兵制》中论及唐代宦官统领禁军造成的危害时,称:
中官之势,遂不可制。“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书·僖宗纪》赞语。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80)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44页。
查赵书原文,确有“《僖宗纪赞》谓,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8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53页。一句。据此可知,引文中的史料并非直接引自《唐书·僖宗纪》,而是据《廿二史札记》转引。又如第十三章《衣食》中先后几次转引《陔余丛考》中的史料。先是在追溯烟草的由来时,引据王肱枕《蚓庵琐语》中的一段史料,后备注:“据《陔余丛考》转引”。(82)吕思勉:《中国通史》,第207页。稍后,叙及衣服的原料时提到木棉,又说有关木棉的介绍“略据《陔余丛考》”(83)吕思勉:《中国通史》,第210页。。叙及古代的服饰时又引述《陔余丛考·马褂、缺襟袍、战裙》条的文献。吕思勉不仅以赵书为媒介转引他书史料,还直接征引赵翼事先归纳好的材料,例如,第二章《族制》叙及历史上的屡世同居现象时直接引用《陔余丛考·累世同居》条的内容。
赵翼史学的内容不限于政治方面,对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皆有涉猎,他将散见于正史各篇的史料摘出,比较归纳,整理成一条条论据丰富的学术札记,为吕思勉的通史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他撰述上册文化史时,正值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之际,能利用的文献资源十分有限,自叹“参考书籍,十不备一”(84)吕思勉:《中国通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在此情形下,很多时候无法引据原书,只能转引他书,这或许是他倚重赵翼史著的又一原因。
综上所言,吕思勉的通史著作确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赵翼史学的成果,除两部中国通史外,由他编写的断代史和历史教材中亦不乏引据赵翼之说的显例。关于吕思勉对赵翼史学的承袭还可做更为细致的考证,本稿仅略举诸例,览其概貌,揭明其旨。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旧杂糅、中西交汇,吕思勉的史著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一方面他尊重传统史学的成果,对乾嘉史学尤其是赵翼史学的借鉴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取鉴传统史学成果的同时又融入新史学的理论,掺入个人分析与考证,更多是借赵翼之说来为其建构的中国通史新体系充当注脚,实现了“旧学”与“新知”的融合。他的通史著作古今通贯,内容周赡,久负盛名,这既源于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继承与发展,又得益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接受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