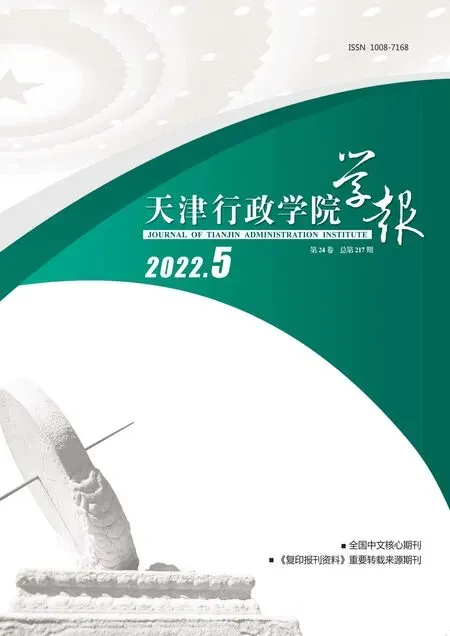公共行政的情感之维
——基于同情的理解
王锋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在理性主义看来,情感低于理性,因而,现代公共行政并没有为情感留下任何空间。作为实践理性,公共行政又不能完全拒绝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同情成为我们理解公共行政中情感主义的切入点。行政管理的公共性本质决定了行政管理者必须具有同情这种情感。然而,仅仅有同情,对行政管理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同情这种自然情感很容易为激情所左右。行政管理需要激情,但被激情左右的行政管理往往是致命的。因而,对行政管理来说,需要将自然情感升华为高尚的情操。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公共行政不能排斥情感,另一方面应造就适宜的空间,使行政管理者所拥有的情感能够顺利转化为情操。
一、理性高于情感:现代公共行政对情感的拒斥
理性代表着去寻找事物的因果规律,这些规律是超越时空的,公共行政也不例外。受理性主义影响,当行政管理完成现代转型后,在工具理性的旗帜下,按照韦伯式科层制建构起来的现代公共行政并没有给情感留下任何空间。在韦伯看来,“就我们的政治和历史科学这一具体的领域而言,这意味着对人的行动加以计算,从原则上说,它不服从任何非理性力量的摆布”[1](p.147)。尽管情感不等同于非理性主义,但至少在那些以科学为使命的行政管理学者看来,如同政治学一样,行政管理应该完全由理性主义支配,行政管理完全是一个由因果律支配的世界。这样一个由因果律支配的世界并没有给情感留下任何空间。
我们非常清楚,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是建立在韦伯所设想的科层制基础上的。在韦伯看来,这种按照职能分工、权责明确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科层制是“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2](p.296)。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迫切需要可预期的、普遍化的规则。而“充分发展的官僚体制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处于‘不急不躁’的原则支配之下。它的特殊的、受资本主义欢迎的特性,使这种可预计性发展得更为充分,它越是‘脱离人性’,发展就更为充分”[2](p.297)。在现代行政管理看来,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相比传统社会的统治行政,由于排除了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且由于科层制满足了现代社会对普遍性和可预期性的要求,行政管理就完全远离了情感等因素的纠缠。
更重要的是,在理性主义的设定中,理性是进步的、高位阶的,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是低位阶的,因而,这里也就不言而喻地预设了理性高于情感。从这种预设出发,行政管理自然就需要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用理性来统一情感。由于这种预设,且由于情感、意志等一直被当作非理性因素来看待,这就意味着情感必然受理性的支配。就公共行政来看,其不仅没有给情感留下足够的空间,而且由于情感在位阶上低于理性,情感本身就被完全排除在公共行政之外,公共行政完全由理性支配。
不仅如此,按照科层制要求运转的行政管理,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实现了从“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变。也就是说,现代公共行政通行的职能分工制即行政管理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进行。基于专业化要求,行政管理被分割成不同职能部门,每一部门承担其职责任务,它们通过分工协作来完成公共行政所承担的总任务。从职能分工出发,我们看到,每一部门实际上只承担与其职责相应的责任,在这里通行的是责任制原则,即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普遍实行责任伦理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韦伯所期望的高效完成行政管理工作的理想。相反,在按部就班的工作中,每一部门都按照其职责来工作,都符合责任伦理要求,最后导致的却是不道德的结果。例如,在抗疫过程中,不同专业部门都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政策,如要求社会成员出示行程码、健康码、核酸阴性证明等,甚至一个组织的门卫都在坚决落实这一政策,对没有核酸阴性证明的人员严格禁止其踏进大门半步。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无可厚非,都在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政策。然而,在责任伦理的要求下这种做法却隐藏着荒诞的一面,那就是,由于没有核酸证明或者核酸证明还没有同步显示在手机中,即使距离医院仅有半步之遥,即使医院的职工,也进不了医院从而获得宝贵的抢救机会。这种荒诞再一次向我们显示,缺失情感的公共行政是一种什么景象!
不可否认,理性在公共行政的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它推动了现代行政管理的确立,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行政管理的职能分工是在理性主义下完成的,满足了工业社会对普遍规则的期待,确立了工业社会所期待的普遍规则的秩序,为工业社会所期待的确定性提供了规则保障和支持。权力是作用他人的意志。统治行政中的权力具有任性的特点,这种任性显然与工业社会所期待的普遍性和普遍秩序不相吻合。因而,当工业社会需要与之相应的管理行政时,理性所代表的普遍化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与限制,这种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使权力本身具有了可预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主义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进步作用。然而,这种理性却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且这种工具理性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理性化行政提供了工业社会梦寐以求的确定性和普遍秩序,但这种确定性却是以失却情感、价值等为代价的,行政管理在管理的名义下获得了确定性,但却没有了对人的关怀。我们知道,公共行政虽然离不开对物的管理,但它主要面对的却是人,用福柯的话来说,是对人群的管理,虽然对人群的管理不同于对人的管理,但行政管理的核心是面对人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在于,理性化行政把人当作物来看待。
我们认为,公共行政需要引入情感。在新公共行政看来,如果没有情感,公共行政仅仅是做好政府工作,而引入情感之后,意味着行政管理对公民和公共行政的热爱,新公共行政称这种热爱为“乐善好施”。新公共行政进一步指出“乐善好施”的内涵,“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3](p.204)。尽管韦伯把科层制设定成一架运转精密的机器,处在这架机器中的行政人员是整个机器精密运转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人不是机器,不论是处于科层制中的行政人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对象,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从行政管理者还是行政管理对象来看,只要把他们当作人来认识的话,就不能排除情感因素。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在人身上既有理性也有情感,既有理性也有非理性。对行政人员来说,尽管我们要求他们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秉公执法,尽可能排除情感因素的影响,但事实上,由于行政管理者是现实的个体,且处于一定的环境当中,这决定了我们无法把行政管理者当作机器,也决定了行政管理者在实际上不可能只是一个“冷若冰霜”的没有同情心的管理者。行政管理者在其工作中展现自己的情感与情绪,这种情感与情绪是其工作状态的显现。这一事实说明,行政管理无法排除情感因素,甚至需要重视情感因素。
从行政管理来看,情感是拉近行政管理者与行政管理对象的黏合剂。有没有情感,怀着什么样的情感,在行政管理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景。管理者有了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热爱和炽热的情感,就能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就能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超越个体和小群体的立场,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来思考并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对人民的热爱,仅仅把行政管理对象看作是无任何特点的普遍化存在,就不会心怀感情,也不会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过,行政管理人员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4](p.322)。既然干部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就要求政府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自觉从维护和实现好人民利益出发进行工作,决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那些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体,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体,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梦想追求构成了对行政管理者的具体要求。对行政管理者来说,他们必须热爱人民,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要求行政管理者关心人民福祉,关注民生。“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4](p.13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关注的是有没有更安全的食品、有没有更好的医疗保障、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教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具体的,那就是办事更方便、环境更美好、生活更舒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p.70)政府就是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
行政管理需要情感,这种情感还需要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进一步升华。悲悯情怀就是行政管理者情感的升华。我们知道,尽管行政管理被设定为执行命令的工具,但管理实践中自由裁量空间的存在,事实上让行政管理者拥有了自由意志的可能。然而,如果行政管理者仅仅满足于获得这种自由意志的权力,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地按照行政纪律的要求服从命令,那就意味着其还局限在科层制所设定的框架内。悲悯情怀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深切关怀。虽然它是抽象的要求,但对行政管理者来说,这种悲悯情怀却是不可或缺的。悲悯情怀意味着行政管理者拥有作为人的高尚情感,他能够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行动,这样的人才符合现实的人的要求。当我们抽离了人的情感因素,把人变成理性的计算者的时候,行政管理者就成了经济人,成了冷若冰霜的管理者。而当行政管理者拥有了悲悯情怀后,他就能够对弱者心生同情,对身处困境者施以援手,而不是仅仅把管理中的规则变成僵硬的教条。
二、从同情到共情:行政管理中情感转化的关键
在公共行政所要求的情感中,同情是最重要的一种情感。同情不是怜悯,尽管不少人把同情等同于怜悯。怜悯是居高临下的,是一种施舍,是廉价的。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看到有人临街乞讨,我们同情心大发,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可是,这种同情是施舍,是强者看到弱者的一种心态,在给穷人施舍的一瞬间,富人或者强者的优越感油然而生。这种同情并不是真正的同情。公共行政所需要的同情是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这种同情是一种移情式的情感,即把自身设想为他人,想象身处其境所可能导致的遭遇,从而能够理解他人的遭遇。对公共行政来说,最容易也是最可能出现的偏差就是把同情等同于怜悯。这是因为,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一般来说,管理者处于强势地位,而被管理者则处于弱势地位。管理者的强势地位往往使他们很容易以怜悯的眼光看待被管理者,甚至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作施舍。显然,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同情,也不是公共行政所需要的同情。
舍勒在论及同情时,曾指出四种同情现象,公共行政所涉及的同情更接近舍勒所说的参与式同情。这是因为行政管理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公共行政所说的同情必然要发生在合适的场景,这个合适的场景就是行政管理所面对的问题或场景。例如,行政管理者面对受到灾难影响的困难群众,悲惨的场景自然而然会引起其“同悲”之心。这就是舍勒所说的参与式同情。在这里,“那(本然)的同感,即事实上的参与,表现为一种反应,即对于在再感觉中所发生的他人感觉之事实和属于此一事实之现象中的价值的反应”[6](pp.13-14)。这就是说,公共行政要求的同情首先离不开特定的情境或场景,即公共行政在具体行政管理实践中所面对的特定事实。
这种同情是“从其他人身上转移给我们的,是由于一种传播而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有的情感,如快乐和痛苦、恐惧和希望、爱与恨、蔑视与崇敬、欢乐的热情和诚挚的庄重,都具有由同情来传播的倾向”[7](p.510)。这种移情必然经过具体情境的传染或感染,行政管理者的同情心才能被进一步激发出来。传染并不一定需要对他人情感的体验性模仿,而是某一行动者进入特定的情境中,不由自主被“卷入” 到由这种情境所创设的气氛或环境中来。例如,在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面对血肉横飞的场景,面对受伤群众,这种情境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痛苦和悲伤,而不是兴高采烈,更不是面无表情地无动于衷。虽然我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但是通过我的再体验,我能够深刻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与快乐。正是这种对他人痛苦的再体验,激发出行政管理者的悲悯情怀,驱使行政管理者采取断然措施抢救受伤群众,挽救他们的生命,而不是推脱,不是拖延,也不是犹豫不决,更不是漠然视之。
移情的关键是使他人的苦乐在我身上产生共鸣。也就是说,他人之痛苦仿佛我的痛苦,他人的快乐仿佛我的快乐。尽管我的苦乐与他人正在遭受的苦乐完全不是同一个事实,但这不妨碍我能体验到他人的这种情感。例如,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正在那里痛不欲生。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这种丧子之痛,这种痛苦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仿佛这位悲痛欲绝的母亲的悲惨境遇正是我所经历的。恰恰是这种共鸣能够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时候的共情与共鸣胜似千言万语,成为不同经历的人们维系情感的纽带。对行政管理来说,虽然我们不指望也不能要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完全平等,但是,“一个人只有理解别人,才能进入周围的生活,才能有意义的生活”[8](p.98)。正是这种强烈的共鸣才能够使我们理解他人,理解他人的处境,理解他人的痛苦。对行政管理来说,这种理解显得更加珍贵。这是因为,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实际地位上的差异,管理者无形之中处于优越地位,这种优越感不足以使他们愿意理解他人,尤其是理解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也难以使他们对他人的遭遇产生共鸣。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同情是带有爱意的情感。这种情感,对行政管理者来说,弥足珍贵:一方面,拥有这种情感,足以证明行政管理者身上还有这种珍贵的、人性的因素,还有这种善的因素;另一方面,对行政管理者来说,没有对人民的热爱,自然也不会对人民正在遭受的痛苦产生同情,进而也就不会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也就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
虽然我感受到的痛苦与他人正在遭受的痛苦是两个不同的现象,对行政管理来说,我们也不可能要求行政管理者去体验或接受他人所有的快乐与痛苦,这在时间与精力上都不现实。问题在于,作为实践性极强的活动,行政管理所面对的具体场景,恰恰需要管理者在面对这些情境时能够在移情过程中产生与他人经历上的一体感。“一体感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这里不仅他人的、有限的感觉过程被不自觉地当成自己的感觉过程,而且他人的自我恰恰与自己的自我被认同为一体。”[6](p.20)作为管理者,行政管理者要时时处处为他人做决定,其行为会对众多的他人产生决定性影响,虽然我们一再要求行政管理者在其行为过程中排除情感等因素的干扰,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管理者没有感情,也不意味着行政管理过程不需要考虑情感的因素。恰恰相反,行政管理者面对的是具体的个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这就要求行政管理者从其管理对象出发,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角度去体验其痛苦与快乐,爱其所爱,恨其所恨。
虽然同情是种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方式,虽然同情包含着双方的平等地位及权利,但对行政管理者来说,其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一方面,同情要求行政管理者站在被管理者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我而为他”。“无我”不等于“无情”,行政管理者的地位和角色决定了其必须心中有大爱,这种爱表现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就是要求行政管理者既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又能以“参与式”的情感体验他人的快乐与痛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感”。另一方面,行政管理的现实决定了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无法像社会关系中的主体那样成为平等主体,哪怕是相对平等的主体。也就是说,行政管理事实上所附带的权力等因素决定了行政管理关系无法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这也就意味着斯密意义上的同情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上的具有自由平等权利的主体,至多只能是在理想意义上对行政管理关系的期待。只要行政管理者手中握有权力,只要权力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所期待的管理关系上的平等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平等。当然,这种相对平等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
对行政管理来说,仅仅有同情是远远不够的,行政管理也不能只停留在对他人苦乐的体验上。作为实践理性,行政管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如何行动,即如何把对人民、对管理对象的热爱与情感转化为行动。当行政管理者面对最初的场景后,就需要把最初的同情转化为冷静的分析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这时候的行政管理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情感了,而是把对被管理者的同情转化为理性行动,这种行动恰恰是对情感的进一步升华。例如,面对血肉横飞的交通事故现场,尽管行政管理者充满对受伤者的同情,可是,只有同情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行政管理者需要在同情的基础上展开理性的分析和处置:受伤者的伤势如何?救援力量如何及时达到现场进行处置?如何调配医疗救护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进行救援?在此基础上,行政管理者采取断然行动,抢救生命,安置伤员,以最大限度减少伤亡,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同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并不是说情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完全理性、没有任何感情地投入到行政管理活动中,固然可以获得行政管理所期望的客观性,可以不为情感所左右,但事实上,没有情感支撑的行政管理并没有带来韦伯所期望的高效率。相反,在责任伦理的要求下,行政管理者执着于岗位要求,在按部就班中完成工作任务,甚至,基于责任伦理的要求,完全坚守自身的职责,而不考虑职责背后还需有的情感与同情。例如,在上海、西安疫情防控中,防疫的刚性要求使得患者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从而失去了生命。这样的事情说明,行政管理活动本身也不完全是纯粹理性的,也需要情感的时时照拂,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不会变得那么偏离人性。
三、从情感到情操:公共行政中情感的升华
对行政管理来说,同情是否就是情感的全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同情是种自然情感,是人类本能的自然流露,也是人类一切高尚美德的善端。然而,“同情自身没有识别能力,它不能成为行为的充分指导。这是因为,一方面,同情以及由此引发的爱与恨,常常以自己的优越感、自爱感为前提与反衬,它可以给别人以帮助、施舍,却难以消除自身的优越感。单纯的同情直接滋生的是怜悯。另一方面,单纯的同情及由此引发出的爱与恨,它们所产生的实际行为自身可能违背社会起码伦常规范,可能是恶”[9](p.339)。这意味着作为自然情感的同情,需要进一步展开,并获得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情感是非理性的,作为一种自然情感,同情甚至有可能转化为激情。如果说诗人需要激情的话,对行政管理者来说,激情则是有害的,甚至会成为一种恶。因为在炽热的情感下,可能包藏着祸心,也可能隐藏着卑劣的心灵和野蛮愚蠢的行为。情感的自然性以及它转化为激情的冲动意味着同情这种自然情感必须受到进一步规定。
就行政管理而言,行政管理者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人们所处的具体道德情境总是具体复杂的,因而,人们的道德情感自然也是复杂的,甚至同一个人对于同一道德现象,可以同时具有数种不同的情感体验。正由于道德情感的这种复杂性,才使道德不那么空洞,不至于仅成为一戒律,才使它具有人性色彩,具有统摄、震撼人心的力量。秉公执法,大义灭亲,铁面无私,公而忘私,这既可以使一个人体验到做人的责任感、正义感、自豪感,但也可能同时伴随着哀怨、痛苦、自愧甚至后悔。”[9](p.339)矛盾冲突的心理体验是情感升华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种冲突交织的选择中,同情这种自然情感由于理性的加入,成为理性的非理性存在。“在各种价值关系的交织中,经过洗礼、锤炼,失去它的自然本性,升华为一种高尚的情感。这个洗礼、锤炼的过程,实质上是理性对各冲突价值的思考、清理过程:或者使恶的让位于善的,低层次的善从属于高层次的善;或者由于具体境遇使然,在多个本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中不得不择其一而行之。”[9](p.340)
显然,经过洗礼后的情感,已经远离了其自然状态,转化为理性化的情感,成为理性的非理性存在,从情感升华为情操。这时的情感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1](p.100)。尽管韦伯这里所说的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但如果仔细追究,韦伯的判断也适用于行政管理。这也就是我们一再坚持的,如果把行政管理关系中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当作人来对待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所具有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情感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身上依然存在。尽管韦伯要求行政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坚持客观立场,保持其对管理活动的客观性,不受情感、意志的左右,但是,这不等于否认行政管理者拥有情感,也不等于抹杀管理对象的差异性,无差别对待被管理者。客观性也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是无差别的管理,而在韦伯所期待的无差别对待背后则是把管理对象当作机器来看待。
虽然我们反对把情感转变为激情,但韦伯这里所说的激情更多地是在情感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也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正如韦伯所说,仅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对行政管理来说,情感是切入问题的起点,可是,当行政管理者需要进一步了解问题的具体情况,如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困难等方面时,激情就让位于理性,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1](pp.100-101)。这种距离就是激情过后的理性沉淀。我们一再提到,行政管理者是为他人做决定,其行为会影响到社会大多数人,因而,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具体的执行行为都必须审慎。韦伯所说的距离感就是此义,即要求行政管理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保持客观理性,这样才有助于行政管理者所作出的决定与行为能够最符合实际情况,也才能最符合民众的要求。
就此看来,理性化的情感,只是情感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非常清楚,即使是理性化的情感,它还是非理性的,只能通过理性的进一步淬炼,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这就是情操,是情感的进一步发展,是理性的非理性存在。在这里,外在约束内在化,理性凝结为人们的自觉习惯,成为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对行政管理者来说,当情感升华为高尚的情操时,也就意味着情感与理性实现了统一,自然情感升华为高尚的情操,转化为理性的非理性存在,转化为行政管理者类似于直觉的反应能力。初看起来,这种直觉似乎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但仔细追究,这是人类长期知识经验积累的结果。正如西蒙所说,“直觉、判断和创造性基本上都是以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识别和反应能力的具体体现”[10](p.111)。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种对人民的责任在这里已经转化为高尚的情操。
公共行政不能不需要情感,缺失情感的行政管理就如同机器一样,虽然可以高速运转,但永远缺失人性的一面。面对他人、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行政管理者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冷漠无情,这是情感的堕落,这种堕落是可怕的堕落,是一种恶。同时,公共行政也不能完全为情感所左右。情感之所以为情感,就在于它包含有情绪的因素在内,而一旦这种情感为仇恨所支配,行政管理者会完全迷失方向,甚至在炽热的情感下做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恶行。“如果情感保证不会使行动的思考变得狭隘,而且有利于实现大范围的长期目标,那情感与理智便是合作关系;而如果情感使得决策制定得过于仓促,并且过分缩小了决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行动备选方案和结果的范围,那情感与理智就是对立关系。”[10](p.80)如果说缺失情感的行为是种恶的话,那么完全为情感所左右的行为同样是种恶。就后者来说,其完全排斥了理性的指引,执着于情感的自然阶段;就前者来说,虽有理性的引导,但这种理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越是执着于一端,其危害越大。
这就提示我们,要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创造有利于情感在行政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能够让行政管理的理性化得到正常发挥,另一方面这种理性化显然不是纯粹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而是包含价值理性在内的更为全面的理性。遗憾的是,我们习惯于技术理性生成的社会环境,也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下的行为反应。殊不知,这样一种由工具理性所塑造的行政环境并没有多少情感因素在内,也没有为情感留下足够的空间。“技术—理性文化中的伦理结构已经没有多少道德选择的余地,也没有抵抗合法权威制造的行政之恶的余地。”[11](p.187)正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行政之恶的根源,艾赅博和百里枫才提出,“由于行政之恶无所不在,公共事务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培养一种对公共机构、权力运用以及普遍文化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11](p.20)。
尽管艾赅博等认为行政之恶无所不在这样的说法有些绝对,但他们对行政之恶产生的根源的认识却是非常清醒的,这就是造就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的文化及其制度。因而,要让情感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维度,就必须对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行政管理进行改造,而改造的重要方面就是承认公共行政的情感之维,并在相应的制度设置中体现出情感,从而有能够让情感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还须注意行政管理者的心灵涵养。在谈及如何修正政治生活的恶时,博洛尔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他说,“最有用最亟须的则是改良道德,用健康的理论和道德信念去涵养人们的心灵。如果要想把社会从腐败的侵袭中与革命的野蛮中拯救出来,就必须使精神的教导在人类的心灵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占有崇高的地位”[12](p.265)。显然,只有健康的心灵,才能也才愿意有这样的情感去面对行政管理,面对行政管理中的人与事。也许,这正是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精神。新公共行政主张,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3](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