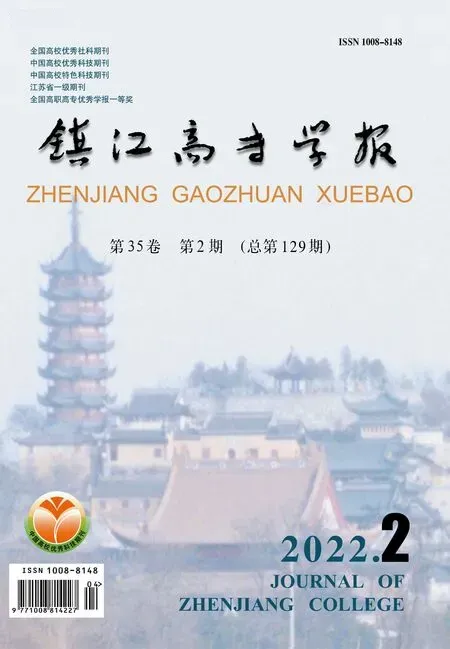论巴金“爱情的三部曲”的革命书写
刘师师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被誉为“人民作家”的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长篇小说“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它们是巴金早期革命叙事的代表作,体现了巴金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性思考。学界对“爱情的三部曲”的研究主要分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第2阶段为“十七年”文学初期到“文革”文学末期,第3阶段为1978年到21世纪初期。“爱情的三部曲”自发表后就引起学界关注。在第1阶段,西方诸多文艺思潮和政治思想被引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即为其中之一,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此时期较有分量的评论文章有老舍的《读巴金的〈电〉》、刘西渭的《〈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等。老舍的文章重点关注作品的理想化书写,刘西渭的文章分析了巴金在作品中表现的对人民的爱及对专制体制的憎。在第2阶段,“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国家的文艺基本方针,此时学界对巴金作品的研究集中于作品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如北京师范大学巴金研究小组1958年发表《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章尖锐批判了扬风、王瑶,认为二人有意淡化了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文革”期间,胡万春发表《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称巴金为“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第3阶段,政治对文艺的影响减弱,学界认为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能在中国特定时代下产生反封建反专制作用,研究者对作品的解析还融入了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文化背景,对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剖析更加中肯和全面。就既有研究成果而言,笔者认为,对巴金“爱情的三部曲”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还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向方面作进一步拓展,如巴金从作品翻译与推介转向作品创作的原因分析、巴金对革命主体现代人格的建构、革命的抒情核心在号召和鼓舞无数革命主体加入革命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等。
1 走向必然的革命书写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巴金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期刊,反封建反专制意识深植于少年巴金心底。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1]71。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统治和专制制度,努力构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巴金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但少年时就对这种腐朽的专制制度暗生不满,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满怀憧憬之情。巴金接受了现代思想文化教育,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青年,他目睹了军阀专制统治倾轧人民的残酷现实,反封建反专制意识逐渐增强。反封建和反专制的革命主题成为巴金文学创作的必然乃至首要选择。
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巴金发现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信仰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双重交锋下,巴金从作品翻译、理论引介等工作转向文学创作。“大革命”失败后,现代知识分子强调文艺创作为政治救亡服务,巴金积极响应。巴金早期革命叙事作品有《灭亡》《新生》《雾》《雨》《电》等,他在这类作品中表现了对中国革命发展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关于作品中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夏志清认为作家在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或多或少会对其日后的写作产生影响。夏志清说:“很多中国作家(巴金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是:在他们未经指导、青春期间所嗜读的书,往往是他们终身写作的灵感泉源和行动方针。”[2]270巴金对现实社会有着清醒认知并且“在理论上承认历史唯物论的内容,把它联系现实斗争,运用它来观察、分析实际的革命运动状况”[3]29,这显然不同于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理念。
“五四”青年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目睹了“大革命”失败后更加专制与黑暗的中国社会,将反封建与反专制的革命事业作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巴金于1931年完成“爱情的三部曲”第1部《雾》,并开始构思第2部《雨》。在“爱情的三部曲”中,巴金生动塑造了众多青年革命者形象。如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制定“土还主义”计划的日本留学归来者周如水;起初在团体中被视为“罗亭”式革命者,后成长为理智的青年革命者的吴仁民;积极向大众宣传先进的文化思想的高志元、方亚丹、蔡维新;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其精神影响和激励诸多革命者的陈真;勇敢无畏的女革命者李佩珠等。巴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革命事业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巴金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空想主义不可避免出现在其笔下革命主体的形象塑造中,但巴金强调革命群体应具备完善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是他革命思想中突出的进步体现。
2 革命主体3类现代人格的书写
如同鲁迅对国民性格弱点的批判,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中亦表现出对革命主体畸形人格的批判,对革命主体独立进取的健全人格,巴金亦予以了高度肯定。正如巴金所言:“我的小说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或她发育、成长、活动、死亡,都构成了他或她的独立的存在。”[1]266关于巴金这里谈到的人格,学者辜也平认为 “包含了人的思想境界和个性气质(即通常所说的思想性格)两个方面的内容”[4]90。巴金在作品中刻画的革命主体现代人格主要分为3类。
第1类如《雾》中的主人公周如水。周如水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青年,他渴望得到美好的爱情,但缺乏实际行动且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周如水极具矛盾的思想性格是当时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在事业方面,周如水起初对改良农村和著书翻译颇有心得,提出了“土还主义”计划,撰写了诸多童话作品,但他的革命热情在面临严峻的革命形势时很快消逝了,作品中巴金借陈真之口对此进行了多番批驳。在爱情方面,周如水虽在国外留学多年,但骨子里其言行仍受封建礼教思想束缚,在爱情方面他不敢违抗父母的婚姻安排,因而拒绝了张若兰。在巴金看来,像周如水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启蒙后“睁开眼睛之后又闭上眼睛,以精神上的麻木去解脱不敢行动的痛苦”[5]167,他们即使有革命理想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无法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中坚力量。
第2类如《雾》中的陈真和《电》中的敏。巴金对此类革命主体热衷以肉身殉道的极端思想与行为给予了批判与否定。陈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为此“抛弃了富裕的家庭,抛弃了安乐的生活,抛弃了学者的前途”[6]109,不需要爱情也全然不顾肺病日渐严重,他是一个完全剥离了自我情感的革命者。敏原本是一个内心平和的知识青年,后逐渐变成一个消极绝望且具恐怖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他未经组织允许私自开展自杀式的暗杀行动。在巴金看来,他们虽然为革命事业牺牲,但其人格存在较大的缺陷。
第3种如吴仁民和李佩珠。他们的现代人格在革命行途中逐渐完善,巴金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厚望。吴仁民在《雨》的前5章是一个思想偏激、易于冲动的革命主体形象。吴仁民与其他革命者在革命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主张跟敌人进行正面斗争,反对李剑虹、张小川等人通过著书与教育来启发民众主体意识的革命方式。他为同伴起草了许多活动计划书,但事实证明很多计划书不切合实际。在《雨》中,吴仁民遇到了熊智君,并迅速沉溺于爱情而无暇顾及团体的革命工作,爱情失败后,吴仁民痛苦表述“爱情是有闲阶级玩的把戏,我没有权利享受它”[6]239。在《电》中,吴仁民已成长为思想成熟的革命者,他能够很快融入团体并有序开展革命工作。吴仁民的性格发展贯穿“爱情的三部曲”。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陷入迷茫与苦闷,但随着在革命道路上的不断磨炼,逐渐自我完善后能坚定信念继续革命。吴仁民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巴金对中国革命道路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性格中固有的动摇性与妥协性的思考。李佩珠在《雾》中被陈真称作“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即指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思想观念进步且日常生活摩登化的知识女性。李佩珠憧憬高志元、方亚丹等青年群体从事的革命工作。在第2部《雨》中,李佩珠开始阅读陈真遗留下来的诸多革命书籍,积极加入方亚丹、蔡维新等人关于革命问题的讨论,她还希冀成为像反抗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妃格念尔那样勇敢无畏的女革命家,“我不想在爱情里求陶醉。我要在事业上找安慰,找力量”[6]215。在第3部《电》中,她积极发展革命团体组织,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坚决阻止陈清等人的冒险行为。在敌人大规模围攻之下,李佩珠冷静将剩余同志转移到城外,总结了失败教训后,及时制定缜密的行动方案。李佩珠已然成长为一个有着崇高的道德情操和完善现代人格的革命者。
3 革命的抒情核心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于2006年提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学术命题,将“抒情”与“启蒙”“革命”视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现代中国处在危机不断加重的境况下,利用革命构建新的社会是众多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革命理想是崇高的,革命过程是波澜壮阔的,同时,革命现实也是无情的和冷酷的,不可避免有流血有牺牲。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会有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显然背后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王德威说:“在革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活动里,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柔软’的面相。在那激昂壮烈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过程里,它有一个非常私密的、碰触不得的核心——或诱人的黑洞。而这个核心,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抒情的核心。”[7]134王德威强调:“革命的能量既源于电光石火的政治行动,也来自动人心魄的诗性号召。”[7]112
在“爱情的三部曲中”,这种“诱人的黑洞”、这种“诗性号召”、这种革命的抒情核心激发了众多革命者同仇敌忾的气势和坚强不屈的意志,激励和鼓舞他们勠力同心、奋力抗敌。陈真目睹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许多许多的人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又看见那些人怎样专制,横行,倾轧”[6]57,在少年时就立下了放弃富裕安乐的人生而献身革命的宏志。为拯救更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他虽受疾病折磨,但全然不顾,他强调“我不再有什么利害得失的考虑了,连生命也不会顾到!那时候只有工作才能够满足我”[6]60。吴仁民面临革命的需要时也挺身而出。他慷慨陈词:“在我的头上,黑暗,专制,罪恶,那一切都仍旧继续着狂欢。这是不能够忍受的!”[6]104巴金在《电》中以李佩珠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团结平等与温暖友爱的革命大家庭,它是巴金对革命群体生活的一种抒情诗意的想望。在革命行进的路途上,革命的抒情核心使得革命主体在历经无数清苦与磨折后仍然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革命激情。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出现“革命+恋爱”模式的革命小说,针对恋爱的欢乐恣意会导致革命主体产生懈怠情绪、爱情与革命会有所冲突等观点,巴金在作品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小说中吴仁民回答了明在弥留之际的询问:“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6]318巴金借吴仁民之口阐述了自己对革命和恋爱的看法。巴金认为爱情与革命并不冲突,革命主体并非禁欲主义者,他抑或她更多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非无欲无求的革命战士而存在。笔者认为,“革命的罗曼蒂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者的精神压力,在号召革命主体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巴金作为深受“五四”运动启蒙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陷入危机时,及时承担起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执笔著书来控诉强权和反抗专制。巴金曾言:“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1]471巴金“不能苦人类之所苦”源于其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出身,但他“悲人类之所悲”的情感使其在革命时代里敢于向专制社会发出控诉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爱情的三部曲”也是巴金“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革命文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