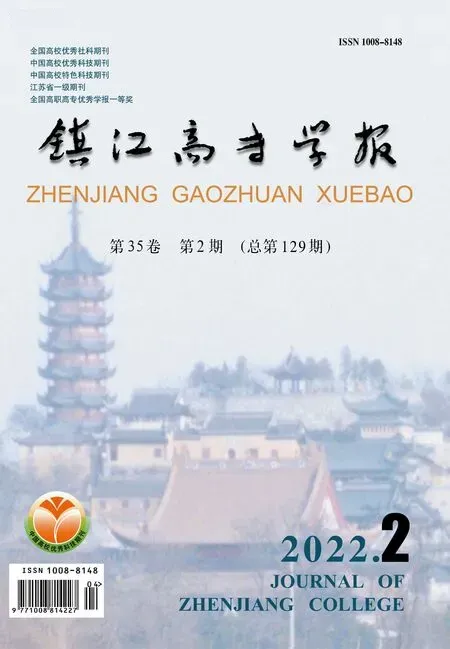“出位”的音乐与城市:论话剧《秋声赋》的叙事策略
闫俊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宋玉高歌“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首开悲秋风气,后又有欧阳修之“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堪称与之唱和。“秋”作为文学意象之一常受到文学家的青睐,田汉的五幕话剧《秋声赋》是现代以“秋”为意象展现抗战时期思想情感的成功之作之一。此剧创作于1941年,讲述了徐子羽、秦淑瑾(徐子羽妻)、胡蓼红(徐子羽情人)等人在抗战烽火中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最终舍弃小我、肩负起救亡图存使命的故事。田汉在《秋声赋》中“把‘诗意的情境,写实的笔法,政治的认识’三者求得统一的处理和发展”[1],使戏剧呈现独特的叙事效果。在戏剧中加入音乐是其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一,不同于其以往作品中音乐仅用于抒情,《秋声赋》中插入的音乐还承担了叙事的功能。此外,地域空间的转换也是《秋声赋》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一,不仅较好地承载了作者不同的情感体认,同时还具有明确题旨的功能。
1 “秋声”行“赋”:隐喻情感与组织结构
美国音乐学家科恩曾论述过音乐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语言,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修辞,甚至有自己的语义。……音乐可以讲述任何事情”[2]22。在戏剧中插入音乐是田汉常用的叙事手法。田汉曾言:“我过去写剧本,喜欢插进一些歌曲:《南归》《回春之曲》《洪水》《卢沟桥》和《复活》等都是如此,那是真正的‘话剧加唱’,这种形式我以为是有效果的。”[3]503话剧是对话的艺术,在对话基础上加上“唱”,使戏剧情节、人物情感与音乐歌曲交融,易产生突出的叙事效果。田汉在《秋声赋》之前创作的话剧中插入音乐,往往是为了营造浪漫诗意的氛围,如《回春之曲》中的《南洋之歌》《梅娘曲》,或是为了更好地抒发情感,譬如《南归》中插入的流浪诗人的自弹自唱。在五幕话剧《秋声赋》中,田汉插入了6首歌曲,数量前所未有,这些音乐除了发挥营造氛围与抒发情感的作用,还承担着隐喻人物内心情感与参与组织戏剧结构的叙事功能。戏剧公演后,一时间 “满城争说《秋声赋》,众人传唱落叶歌”[4]。
1.1 音乐表现人物内心情感
《秋声赋》中插入的音乐能较好地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对刻画人物心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漓江船夫曲》是话剧第1幕开头即出现的音乐。剧中女主人公秦淑瑾曾这样描述刚听到时的感觉:“听着那些船户们排篙子的时候,高声的号叫,那声音发着抖,就像哭着似的,使人家心里怪难过的。”[5]253《漓江船夫曲》生动表现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悲伤凄凉。话剧开场时秦淑瑾正为丈夫的情人胡蓼红要来桂林而感到心忧乃至绝望,“跟了他这么多年,哪一样对不起他?”“临到这个时候他还要这样的害我”[5]254。男主人公徐子羽目睹桂林文化界呈现萧条景象,自身文思枯竭之时又深陷妻子和情人之间的矛盾,痛苦不堪。戏剧还描写了长期漂泊在外的黄志强、徐母等人因生活拮据而痛苦烦恼。可以说,每个人物内心都充满了秋之凉意。时不时穿插在剧中的“风声、雨声、船户号叫声”暗示了剧中人物情绪的波动,将人物内心的悲意放大呈现于读者眼前。
第3幕出现的《落叶之歌》明显有别与前两幕音乐,整体氛围由悲凉沉郁转为激昂奋进。“趁着眉青,趁着唇红,/辞了丹枫,冒着秋风,/别了漓水,走向湘东,/落叶儿归根,/野草儿朝宗,/从大众中生长的,应回到大众之中,/他们在等待着我,/那广大没有妈妈的儿童。”[5]322歌词暗示了胡蓼红心态的转变。被大纯拒绝叫妈妈却又收获了另一群孩子的胡蓼红,终于找到了生命中更有意义的事情,胡蓼红重回长沙积极救助战区孤儿,在这种无私的爱的影响下,秦淑瑾也摆脱家庭琐事的困扰,积极投身慈善工作。
两个女人因为爱上同一个人,在争夺爱情中蹉跎了多年的岁月,如今因为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消除了多年的芥蒂,在无边的秋色中彼此拯救了对方。第4幕的音乐《潇湘夜雨》完美烘托了这种情感。“酸的、苦的、辣的、甜的,一桩桩地溯上了咱们的心房/也难得今宵风雨联床/让咱们谈吧,谈吧/拥着衾儿直谈到东方发亮。”[5]343-344外面下起了雨,“猛然的泪般的秋雨/凄清地敲着纱窗/十几年来/酸的、苦的、辣的、甜的,一桩桩地溯上咱们的心房”[5]343,但房间内的两位主人公心却是温暖而激动的,渴望着“拥着衾儿直谈到东方发亮”。两位女主人公在长沙化敌为友并转危为安,徐子羽在桂林受到感染而重新振作时,剧作也迎来尾声。结尾处的《银河秋恋曲》在壮烈的曲调中暗示剧中人物在经历风雨之后终于重获新生。
1.2 音乐参与组织戏剧结构
戏剧的情节与结构是戏剧的核心。在《秋声赋》中,田汉以“秋声”行“赋”,别出心裁地用音乐参与组织戏剧的情节与结构,既赋予情节的起承转合以音乐的节奏、旋律,又将主要人物的内心情感进行了诗性表达。
剧情尚未开始,音乐《主题歌》便已登场,预示了戏剧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与情感基调。“欧阳子方夜读书,忽闻有声自西南来,/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似山雨将至而风雨楼台,/不,似太平洋的洪涛触巨浪、触崖边而散开。/啊,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但是我们不要伤感,更不用惊怪,/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中、浪涛中屹立起来,/这正是我们民族翻身的时代。”[5]251欧阳修的《秋声赋》云:“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6]8《主题歌》在前半部分借鉴了这几句,在摹古中营造了一种秋日的悲凉气氛,后半部分用“不要伤感”“不用惊怪” “铁一般的坚定”等话语一反欧阳修之“秋意凄切,浸润入骨”的沉闷,用激昂、不屈的语调对艰难的环境进行斩钉截铁的否定,将前文铺开的伤情瞬间扭转,“而走向另一个分水岭”[7]15。整首《主题歌》正如刘平所言:“(开场的主题歌)凄凉中寓示着悲壮,雄浑中孕育着坚定,豪迈中充满着自信。它似乎让人看到了革命的大潮正汹涌澎湃、奔腾呼啸而来,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8]511《主题歌》奠定了整部话剧的叙事情感基调。剧作一开始在一片愁云惨淡的情境中展开,剧中所有人物在出场时内心都或多或少蒙着哀愁与悲凉,但随着情节的发展,3位主人公在各自的事业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从而消解了之前悲凉甚至绝望的心境,走向光明的未来。
话剧《秋声赋》中插入的多首歌曲,往往都处于戏剧冲突的转折点。在第1幕中不时出现的凄婉悲凉的《漓江船夫曲》呼应剧作开头悲凉的氛围与情感基调,在第2幕结束和第3幕出现的《擦皮鞋歌》暗示了戏剧情节的转折。胡蓼红因为大纯拒绝喊她妈妈而伤心难过,恰逢阿春唱着曲调欢快的《擦皮鞋歌》由远及近,这歌声驱散了她心头的悲伤,“我为什么要带着怪可怜的、怪难为情的感情,求着去做一个有爷有娘的孩子的妈妈呢?我为什么不更慈爱的、勇敢地去做那广大的失了爷娘、失了家乡的孩子的妈妈?”[5]318正是在这种欢快曲调的影响下,胡蓼红终于决定回长沙从事抢救战区儿童的工作,“和心里的敌人奋斗”,冲出人生的秋意,迎接属于自己生命的春天。第4幕中的胡蓼红所唱的《潇湘夜雨》在温暖的氛围中将剧情推向高潮,寓示着胡蓼红与秦淑瑾消除隔阂、重新振作。结尾的《银河秋恋曲》宏阔壮美,与剧作开头的《主题歌》首尾呼应。
2 萧瑟桂林与温暖长沙:城市书写与情感表征
文学作品既具有时间结构,又蕴含空间结构,时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申丹、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强调了文学作品中“空间”的重要性:“‘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除了为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动场所,‘故事空间’也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9]362在文学作品中,空间作为场景与背景,是叙事的“容器”,也起到为叙事添砖加瓦的作用。在现代中国,城市无疑是传播现代思想观念与承载叙事的最佳空间。正如罗兰·巴特所言:“城市是一种话语。”[10]93当作家将城市搬进文学文本时,他其实也在为城市进行编码与赋义,创造一种想象性的现实,以此表达自己的叙事旨意与精神诉求。在剧本《秋声赋》中,田汉设置了桂林与长沙两个地域空间作为戏剧情节发展的主要故事空间,在对两个城市的不同书写中表达自己不同的情感。选择桂林与长沙两座城市与田汉的个人经历有紧密的联系。就桂林而言,在抗战中,由于时势的变化,田汉与众多文化工作者不得不在多个城市之间辗转,其中在桂林有长达3年多的旅居体验,对桂林的书写是真实自然的有感而发。就长沙而言,田汉出生于湖南长沙,楚地人民多追求浪漫自由,这便促成了田汉浪漫纤细、敏感善思的个性。同时,楚地自古就有 “卓励敢死、强悍炽烈的士风民气”[11]208,这也对田汉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评价田汉骨子里有一种“扎硬寨,打死仗”的“湖南牛”[12]92性格。可以说,没有长沙就没有戏剧作家田汉,更何况钟情于对故乡的书写是文人一以贯之的传统,田汉也不例外。
2.1 桂林——秋风瑟瑟的异域他乡
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曾言:“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13]126不同的作家以不同姿态介入城市,想象中的城市形象是千变万化的。具体而言,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建构是作家思想观念、文学活动、城市体验、他城记忆与时代语境整合共育的产物。因此,解读作家笔下的城市,不仅需要进入文本,而且需要观照现实。
《秋声赋》写于1941年,彼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抗日战场的胶着与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使整个文坛弥漫着萧瑟的气氛。此时来到桂林,田汉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秋意。“假使上一趟我省识了桂林的春,这一次算充分领略了桂林的秋了。我所谓桂林的秋,当然不只是漓江边的芦花、七星岩前的黄叶,也不只是这名都士女淡雅的秋装。我们来的时候恰逢着桂林文化界摇落的时期,所谓‘落花满地非不好看,但春天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期我除旅中的寂寥感之外,还深深地尝着文化上的秋意。”[14]481田汉在桂林生活时所品尝的这种寂寥的秋意,也无声地渗入剧作中作为故事空间的桂林。剧作一开始,桂林就笼罩在阴雨蒙蒙的氛围里,漓江船户的号叫声更增添了这种悲凉的秋意。此外,房东催缴房租、杂志社没钱出版刊物、桂林文化界的“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的社会境遇,都体现了桂林生活的不易。正如主人公徐子羽所说:“您若在桂林住上两年,又逢着这样连绵的秋雨,你就不是诗人,可也有点儿悲愁了。”[5]277桂林的萧瑟秋意既是客观环境的显现,又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正是在桂林,徐子羽、胡蓼红、秦淑瑾3人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阴雨蒙蒙的天气正暗示着人物内心的苦楚。这种阴雨天气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幕,在主人公都重新振奋而奔赴新征程时,桂林的天气才开始转晴。在一定意义上而言,田汉将自己在异域他乡时的情感体验投射到戏剧中桂林空间的叙写。
2.2 长沙——充满归属感的精神家园
长沙作为田汉与其笔下主人公的故乡与精神家园,在建构中时时与桂林相比较而存在。剧本描写徐子羽在桂林的住所时,呈现的是一幅看似温馨惬意的景象,“窗子颇大,从竹木荫里可以望见象鼻山以及对岸城市山峰。这时是日近黄昏,还可看见二片晚霞”[5]252,但生活于此的人们体验的却并非舒适休闲,而是悲凉的秋意。相反,第4幕才出现的长沙徐子羽的家,即便正处在战火不断、骚乱不止当中,连“墙壁也因不断的轰炸不免剥落了”[5]323,但住在这里的胡蓼红与秦淑瑾感受的却是工作激情与沟通的温暖。在桂林是舒适下藏悲凉,在长沙是艰苦中寻温暖,城市书写与情感表征联系紧密。
在作家笔下,长沙还成为剧中人物精神寄托的载体。在第1幕中,主人公徐子羽一家人因为躲避战火而来到桂林居住,虽在桂林生活了2年,但在闲谈中时时流露对长沙的眷恋。“现在西南的物价当然是长沙比较便宜。”“只要战局稍微稳定些,我想还是带他们回长沙去。”[5]260及至胡蓼红来到桂林,秦淑瑾、徐母同徐子羽吵架之后的第一反应仍是回长沙。在长沙会面临敌军的侵袭与骚扰,但几位主人公在外地遇到困难与不顺时首先想到的避风港还是长沙。在第3、4幕中,胡蓼红重新寻找到的人生方向是回长沙从事抢救战区儿童的工作。这种安排并非作者偶然为之,正是在长沙这一地域空间,胡蓼红与秦淑瑾两位女主人公走出了烦恼苦闷的情感困境,积极投入工作,并且摒弃了以往的成见,互相依靠,一同成长。远在桂林的徐子羽等人,被胡蓼红与秦淑瑾二人在长沙积极奋斗向上的行为所感染,也走出之前的精神困境。可以说,长沙为所有人提供了精神力量,促使大家走出笼罩在桂林城内悲凉的秋意。
不可否认,故乡对多数人而言,既是人生开始的起点,也是永恒的归宿与精神的港湾。对作家而言,故乡既会在其思想与观念的形成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又往往充当着“母性”的角色,引发他们依恋与思念的情感。故乡被赋予的这种身份与符号从古至今都存在于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成为作家一种相对固定的情感表达。所以,当战时桂林的社会状况不能满足田汉的情感期待时,他不得不重塑一个理想城市对象,由此,对故乡长沙的乌托邦式想象出现在戏剧中便是顺理成章了。
3 结束语
话剧作为一种以人物对白为主的叙事体裁,在表意机制与叙事范式上,都需在对话构设上下功夫,而在《秋声赋》中,田汉是在音乐的插入策略方面与地域空间的形塑逻辑方面,都显现了一种“出位之思”(1)“出位之思”源于德国美学术语Andersstreben,指一种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进入另一种媒介表现状态的美学。。这种艺术的“出位”彰显了田汉对话剧艺术新的探索,同时展示了田汉的战时民族国家想象,体现其为民众写剧的目的。
总之,《秋声赋》既是田汉作为剧作家思想与情感的诗性表达,又是贴合民众趣味的抗战话语的真实表达。作家在叙事方面的努力探索使得剧中人物的情感转变更加维妙维肖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将话剧的艺术美感更形象地呈示给受众。同时,田汉积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元素,将现代话剧更进一步民族化与本土化,创作了真正的不失艺术性的大众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