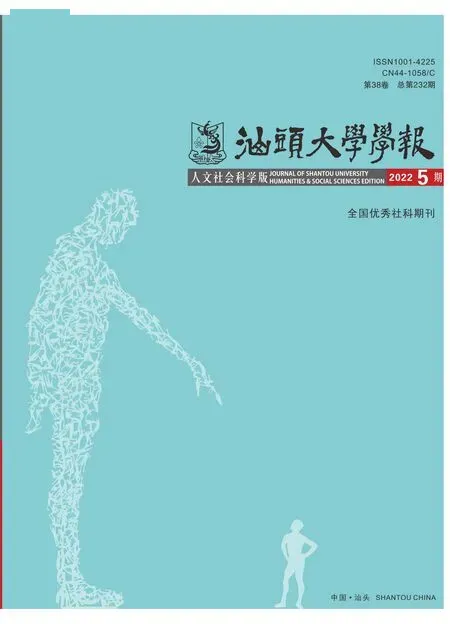情感·创伤·女性:论张翎的小说追问
阮丹丹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作为一个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在创作中融入了异域与中国的多重元素。在跨国叙事中,她逐渐找到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她的每部作品都在讲述一个不平凡的故事,但她并不满足于讲出好故事,而是在故事中不断发出自己的小说追问。情感、创伤和女性是她构架小说的三种维度,也是她在小说创作中着力较深的三个方面。通过这三个维度,她不断在创作中追问如何表现人物命运,如何勘探人性的幽深,以何种视角书写女性。张翎以一种现代主义的眼光和笔法,去书写历史碎片和社会问题,这既是她对现实的介入与发声,也是对小说创作更多种可能性的发掘。
一、用情感线索书写命运浮沉
张翎的情感书写,首先体现在对个人情感的描摹与刻画,尤其关注个人命运的起伏坎坷。他们的爱情经历、情感诉求及婚恋观,从不同侧面映射着张翎对爱情的独特感受,以及对人性的自我认知。
爱情是张翎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不过她倾向于编织一段段不完美的、残缺的爱情故事,将人物置于一种错位的、造化弄人的怪圈中。种种客观因素如跨国恋、革命、战争、灾祸等,使两个情投意合的人不能在一起。正如《雁过藻溪》中的宋末雁和李越明之间难以维系的婚姻关系,最终只能走向离婚。又如《望月》中的踏青,将近三十岁的踏青刚刚感受到初恋的美好,还来不及感受恋爱中细碎和现实的一面,就不幸地离开了人世。作者的意旨不在于书写爱情或婚姻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人物命运转折或人物重新审视生活的触点。
其次,张翎在家庭伦理关系的书写中去展现人物难以摆脱的情感困境,主要表现对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伦理呈现。最典型的是《金山》中扭曲的婆媳关系。麦氏作为故事中方家第一代的女性代表,她是方家最高的权力话语者。儿子方得法跟着村里的红毛去金山淘金,她留在开平负责家庭建设和子女培养。她对于儿子力争迎娶的媳妇六指,始终表现出厌恶和敌意态度。在麦氏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控制欲,她一直站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对六指提出种种要求。直到麦氏去世以后,六指的生活才渗入一丝自由的气息。然而,婚姻的悲剧和家庭的压抑并没有由此结束。麦氏去世之后,六指不自觉地给自己戴上了生活的枷锁。她对待自己的儿媳区氏,又何尝不是一副刻薄的面目。人心的诅咒在这些不幸的女性身上重复上演。
“月圆之夜,最是相思。不知金山之约何日能践?箜山水依旧,红颜老去。唯见玉砚笔中情,寄与金山梦中人。”[1]133这是六指写给阿法的书信,也是她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内心一遍遍重复的声音。对于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期待,都逐渐被养育孩子、伺候长辈等各种现实琐碎消磨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心开始生长出裂缝和杂质,人在现实的境况中不断被打破,生命也由此经历着裂变与可怕的循环。
再次,在个人和家庭之外,民族和国家叙事的部分也值得格外关注。地域的距离并没有给张翎的创作增加隔阂,民族和国家叙事也并未沦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反而为她的写作增添了丰富的维度。她是一个善于沟通历史与当下,跨越异域与本土的作家。在她笔下,跨地域、跨民族的写作,让她在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探寻人的共性和个性。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从一个小地方温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加拿大,肉体离故乡越来越远,精神离故乡越来越近。我主要表现的是人类的共性,而不是表现文化冲突、文化冲撞。”[2]
在民族和国家叙事中,作者将人物的命运置于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的大背景之中,既写出了小人物在时代命运面前的弱小和无力,也写出了他们内心不屈的挣扎和坚韧的选择。如方得法在温哥华给妻子六指的信中这样写道:“若非我大清国力薄弱,民不聊生,吾等何至于背井离乡,有家难归……待吾攒得人头税银两及过埠盘缠,便携汝与锦山来金山团聚。”[1]199读到这里令人不禁感慨,这群金山“红毛”的故事,是值得被看见的,应该被铭记的。他们背井离乡,去异地卖命挣钱,与国家的贫弱有很大关系。他们终其一生所忍受的苦难,正是中国早期穷苦社会之剪影,是彼时中国历史的侧面反映。小说中所讲述的世纪变迁中的方家故事,正是民族故事与家族故事的结合,既有民族发展变迁的历史厚重感,又有传统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细碎感。这两个维度的选择和呈现,恰到好处地糅合了张翎对历史与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密切关系的思考。
此外,在每一段复杂的情感故事中,都有着深刻的寻根意识,贯穿在张翎创作的始终。这里的“寻根”,不仅仅是对故乡的寻找,也是对被压抑自我的认清和解放。她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经历过离乡而后返乡的过程。故乡一开始往往是不熟悉的存在,对于前辈人来说,故乡可能是受伤后要逃离的地方,或是想要改变命运努力挣脱的地方。在后代人的认知中,故乡变成了一种空白或缺失的存在,但由于某些现实的变故或机缘,故乡渐渐成为一个吸引人物发掘生命源头,重新认识自我、找回自我的所在。故乡作为起点,或者作为最终要回去或回不去的终点,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这种寻根的内在冲动,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贯穿在故事的叙事线索中。在离乡—归乡—寻乡的心路历程中,人物一步步完成自己的使命。
对张翎自身来说,温州是她写作的根据地,她看温州的视角比本土作家多了一重距离感。同时,加拿大作为她的常居地,为她的小说创作增添了异域元素和色彩。她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及:“地理位置的阻隔提供了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使人的视野开阔了。离开了本土生活环境,以前束缚我的各种因素,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都大大减弱了。”[3]张翎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围绕着人物和故事的寻根之旅。故事中的人物拼尽全身力气,持续不断地向着回归家园的目标奋进,他们在苦难中慢慢摸索自己的归属所在,在情感困境中寻找自我疗伤的慰藉。也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张翎用情感脉络去展现人物命运,同样也用情感作为连接自我、作品与读者的重要纽带。
二、在创伤记忆中追问人心的安放
在一个个爱恨交织的情感故事中,张翎尤其突出对创伤记忆的书写。她写灾难、战争、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写生育的阵痛,写爱到极致后的怕和畏缩,写飞蛾扑火的“蛾子”所受的伤害。
《余震》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4]张翎要做的就是揭开伤疤,裸露创伤的痕迹,呈现创伤之后人们不同的生活姿态。创伤的痛感是短暂的,但是创伤留在心灵上的痕迹是持久的。如果无法直面伤痛,无法找到与伤痛和解的方式,可能永远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而始终笼罩在创伤的阴影之中。创伤与灾难对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伤害,有很多是难以复原的。如《余震》中的王小灯,在经历了地震中母亲的抛弃之后,她失去了爱和信任的能力,她的生活长期处于害怕失去和保持距离的恐惧之中。
在关于创伤的叙事中,张翎并非集中于创伤本身,而是通过创伤叙事去触碰人性中最深的层次,最隐秘的角落。“极致的残酷里就出现了人性的拷打,拷打中催生了小说的凄婉……我喜欢这样的极致,极致是两端的极限的延伸,一端是飞翔的翅膀,另一端是落地的双足……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5]在日常生活中,创伤是容易被掩盖,是被美好遮蔽的,而张翎要做的就是揭示创伤。张翎的小说显现出一种可贵的向创伤和苦难发问的能力,这是值得文学创作者努力追求的方向。
张翎倾向于写灾难、创伤、死亡,写人的困境,写人在面对生存绝境之后,迸发出来的东西。这是她为人物设置的一种极端的生存状态,也是她选择的一种叙事方式。在一次对谈中她指出:“在我的小说中,死是一种绝境的象征,而不是我真正在写死亡这件事情……我特别爱描写绝境,这确实是真的。绝境当然与死亡有一定联系,我认为,人要被逼到那样的地步,才能够爆发出来一种东西,让自己吃惊,也让周围的人吃惊。”[6]张翎写人的绝境,试图探寻和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的人生体验。通过创伤叙事,写极端生存状态中的人心和人性。
在跨越世纪的个人创伤和家族创伤历程中,人不断地重新认识自我和融入社会,尝试去安放内心与过往的纠结,找到对家园和故乡的归属感。《世界上最黑暗的夜晚》里面,袁导带领的游客,在电梯故障的夜晚聚集在一起,每个人讲述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那些黑暗的夜晚,就是他们生命中最深刻的创伤。“黑暗没有可比性。没有一种黑暗,可以替代另外一种黑暗。只是,什么样的黑暗都可以熬得过去——如果你想熬的话。”[7]实际上,他们讲述自己的创伤,是在向外界倾诉,向别人展示自己生命中的创伤记忆,以得到心理的释放和坦然。当他们熬过最黑暗的夜晚,他们便学会在黑暗中寻找希望,重新找到直面黑暗的勇气和力量。
《金山》中锦绣和阿元的儿子怀国被飞机炸死,怀有身孕的锦绣在教室里被日本人强暴。分浮财时,方家一次死了五个人,疯了两个人。这些死亡和伤害都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一个人的死去,一个家庭的变故,一群人的集体苦难,都被淹没在变革的滚滚浪潮中。这是一个时代的无罪之罪,追究时代的罪状已经于事无补,但他们的死去,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文学就是要听到个体受伤的叹息,看到创伤在个人心灵上留下的印记,感受到个体生命在幽暗中的生长。张翎的小说,就是在挖掘历史背后的故事,从历史角落和细节中探寻普通个体曾经活着的样子。她的创伤记忆书写,也是在寻找一种面对和解决痛苦的方式。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有的痛苦是解决不了了,那你就要找到一个方法带着痛苦生活下去。与痛苦和解,不是说你与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解,有时你不可能和那个原因和解,而是跟自己内心达成某一种和解——这根刺已经长成了肉,除非把肉剜掉,否则你就得带着长成肉的刺继续活下去。”[8]
创伤记忆也是反观当下和定位自我的一面镜子。正如刘小枫指出天主教神学家默茨对苦难记忆的看法:“每一个个体已不可能将历史中的无辜受难者的存在撇在一边去求得自身的自由、幸福和获救。上帝要求我们记住每一位无辜的死者和历史中的每一次罪恶。”[9]在书写这些伤痕累累的人生故事时,张翎并非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者,她的心也跟着人物一起经历着内心撕扯的痛苦,她的笔下总有不忍之心。她说:“我这个人本性上不够强大,我真正忍不下那种疼痛的时候,我会用止痛药。”[3]在一些创伤故事的结尾处,能看到作者给出的“止痛药”。如《余震》中,当王小灯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站在她面前时,她的眼泪在暗示着有一束光亮照进了她内心的黑洞,她终于推开了心里那扇关闭了30 年的窗户。张翎无情地将人物推到绝望的边缘,但并没有无止境地放大绝望。写到极致处,还不忘留有余地。胡传吉在谈文学的“不忍之心”时,有过这样的思辨:“不忍之心,由道德出发,又高于道德,她是善与智的结合。小说的不忍之心,实能度量天下广袤、人心尺寸。”[10]张翎笔下那些富含不忍之心的写作,既是小说的智慧,也是文心的考量。她书写创伤,但没有无限地放大创伤,她要诉说的是创伤绝境中的世道人心。
三、通过女性形象抵达追问的深刻
张翎的小说创作,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她并不是唯女性论,而且不太接受女性主义的标签。她对女性人物的设置和观察,是理解其创作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女性人物的形象和命运,她可以勾连起不同的时空,同时呈现出几代人的命运,注意到人性中难以明确定义的复杂性,从而抵达文学的深刻。
她的小说塑造了一个个鲜明动人的女性形象。《空巢》中的保姆赵春枝,让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空巢老人重新看到生命之光;《都市猫语》里面为了生计被迫沦为洗脚妹的小芬,坚守内心一块干净的地盘;《余震》中因被母亲放弃而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的王小灯,以及坚强到招人恨的母亲李元妮;《金山》里面的女性群像,麦氏、六指、猫眼、延龄等。这些女性形象,都各有动人之处,或让读者为之感叹其命运的不公,或心痛其生活的遭遇。她们身份低微,却有一套定位自我的生命哲学。不论世事如何变幻,生活如何艰难,她们一直在匍匐前行。她们内心的坚韧和决绝,独自承受苦难的能力,都支撑着她们继续生活下去。在人生的修行道路上,她们孤独但不绝情,决绝亦葆有柔情。
在这些小说中,女性不仅作为人物和角色存在,也是架构小说的重要载体。她曾这样表述对《雁过藻溪》中末雁这一人物的构思:“于是我想到一个载体,一个可以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起来的人物,在他(她)身上我可以把那些零碎的印象聚集成一条意向明确的线。”[11]人物在张翎笔下,成为构思整个小说的重要线索,可以串联起她许多零碎的想法。在之后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不断完成故事的讲述,人物与故事一起生长。
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关注张翎写作的女性视角时,不应该落入女性政治的偏狭。她并非单一维度上的女性主义者。她之所以将人物塑造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上,不为与男性形成对立,而是因为对女性内心的发掘可以做到更为细腻,女性命运的曲折可以写到更为离奇的地步。较之男性角色,她更擅长通过女性去探索人性的复杂。
在张翎的女性视角写作中,呈现出更加立体多维的文学图景,表现出对单一的二元对立的女性政治的反拨。女性写作不应只是争夺性别主导地位,而应突出表现在勘探人心的智慧和敏感。张翎的女性视角写作恰好为女性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何彦宏在谈女性文学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内在问题,还是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都要求我们超越既往性别政治的阐释阈限,拓宽眼界,以更广阔的人文主义视野关注我们的女性文学,转换生成和建立一种新的女性人文主义的阐释框架。”[12]张翎的写作,恰恰具有一种广阔的女性人文主义的眼光,她是透过女性命运去观察人物内在的声音,以及内部精神世界中被掩藏和需要释放的部分。
张翎通过女性的人生处境,去追问她们为什么会做出各种不同的人生抉择,去追问生命中缺失的部分在哪里。她将人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挖开来写,放大来写。这些被放大的内心世界,显现出人物日常被隐蔽的面孔。这种主体精神空间里的多个侧面、不同变化,以及自我冲突的历程,都是她建构文本深度与复杂性的重要路径。
她以敏锐的女性眼光,去关注人性中较为幽微隐秘的层面。这些人心的解剖,让文本和故事折射出动人的光辉,达到文学的动情。这样的写作更多地关注于人物的内心,写人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希望与失望、矛盾与困惑、执着与坚决、落在尘埃里的卑微与不甘屈服的尊严等。正如本雅明所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13]这种关注内心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人精神世界的张力。她们是那么渺小、孤立、卑微,但她们的内心又是那么坚韧、倔强、不愿屈服。如《都市猫语》中的洗脚妹小芬,只是一位被生活裹挟、被现实羁绊的柔弱女子,内心却有一块誓死捍卫的净土。她们执拗、偏至,在唯有屈服没有选择的生活中,坚决守护内心的圣地。谢有顺在分析小说人物的“精神洁癖”时曾说:“文学所表达的,有时正是一种精神的偏执,一种片面的真理,它要证明的是,人的内心还有不可摧毁的力量,还有不愿妥协的精神。它试图呈现出一种存在的纯粹状态。”[14]这种不愿妥协,可能就是她们竭尽全力去争取的个体真理。文学的可贵之处,正好表现在对个体真理的展现和追求。
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奏
尽管张翎的小说着力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和命运,但她的创作从来不是天马行空的空想,往往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她从历史画卷和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的灵感,经由文学的想象和创造,创作出一个个令人惊叹和震撼的文学故事。从她的故事、人物中,可以感受到她的文学信念、她对文学的企盼及更多可能性的追求。
从内容上说,她是现实主义的,但从精神上看,她又是现代主义的。她通过现实主义的题材,表达人精神世界的扭曲、变形、裂变和重生。她写人的精神力量,人的内心世界,人曾经可能遭受过的苦难,以及人们在苦难中如何继续生活;她写到人的漂泊与追寻,人的期待与坚守。理想与现实之间仿佛隔着从开平县到金山之间的千山万水,其间有无数个悲剧故事的存在,但等待与希望的灯火永远不会熄灭。
从她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来看,她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心灵上的理想家园。张翎说:“我一直在写,或者说所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可以是东方人到西方寻找,也可以是西方人到东方寻找,但这种寻找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15]在寻找的途中,她不断地摸索和建构小说世界中的精神归属地。她赋予人物受苦受难的能力,看她们受难的极限在哪里。她让人物用尽全身力气去爱一个人,却很少给出圆满的爱情结局。她不只是在寻找理想,也是在寻求文学的现代精神和现代表达。
张翎在创作中对一些基本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探讨,表现出文学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有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对边缘人群内心世界的洞察,对人的精神空间中隐秘部分的勘探。《都市猫语》隐喻了当代都市的人际交往问题。司机茂盛和洗脚妹小芬,原本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合租进入彼此的生活。茂盛一直很好奇小芬到底是做什么工作,但两人基本上没有对话的机会,于是在冰箱便利贴上留言交流。在两人的相处中,猫扮演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两只猫的友谊,一方面打开了两个人沟通的切入口,另一方面也构成对人际交往方式的讽刺与暗喻。再如《空巢》中,对空巢老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也是现实社会亟须关注的精神文明问题。
张翎对文学现实意义的关注,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出国之前她做过几年的车间工人,出国后做过听力康复师工作,这让她接触到许多经历过战争的军人,也让她更多地思考死亡与生命的意义。“我的病人中有一批很特殊的人,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他们的经历,是我这个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同样的灾难落在不同的人身上,会落下完全不同的烙印。这些人的生命体验,让我对灾难、创伤、救赎这些话题产生极大兴趣。”[16]可以说,是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对生命的独特感悟,让她找到了令人感动的细节或瞬间,并由此触发她的文学思考和写作。此外,对写作素材的敏感和留心观察,也时常促使她去关注一些已经被人遗忘的历史角落。《金山》的故事就是她在被岁月土壤掩埋已久的碎片里一点点挖掘出来的。
张翎在访谈中曾这样说过:“许许多多小人物的许许多多件琐事,在枯燥乏味的日期和事件中如星辰跳跃出来,成为闪光点。于是历史被推入背景,人物和故事占据了整个舞台。我没有管‘形而上’的东西,尽可能从概念和套路中跳出来,始终专注在人和人物命运上。”[2]小说本身就是一门虚实结合的艺术,文学的虚构恰恰是艺术的真实。张翎的作品中,较少看到比较明显的文本技巧。她的小说一般都是以故事取胜,讲好故事,讲引人入胜、引人动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她对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做深究和细说,而专注于书写人物命运,勘察人物内心的细微感受,构筑历史变幻中几代人的命运沉浮,用文学揭露历史长河中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人心隐秘角落。
基于现实主义的取材和考虑,完成现代人文主义的思辨,足见张翎深厚的小说功力,以及她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独到见解。为能达到客观实证和主观想象的完美结合,她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和实地调研。她多次谈及自己写作过程中所做的无比烦琐的考证工作:“四十万字的写作有无数的细节,每一个都像刘翔脚下的百米栏一样让人既兴奋又胆战心惊。我需要知道电是什么时候在北美广泛使用的;我需要了解粤剧历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1]5她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糅合在作品中,让故事既有超越时空局限的艺术想象,又有基于历史背景的厚重感与广阔眼光。
正如王安忆所说:“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而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17]张翎既有非虚构的现实取材,又着力打破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探索更多种可能性的想象与创造。小人物的爱恨交织,命运沉浮,建构起有血有肉的活着的文学历史。
结语
张翎的小说创作,不管是表现情感、书写创伤,还是塑造女性,总让人看到她从未停止的小说追问。她追问以怎样的方式能编织出引人共情的故事、以何种笔法去塑造生存绝境中的人物、用哪些细节去表现无法抹去的心灵创伤;她追问人应该如何走出创伤,寻找重生的希望和勇气;她还追问,如何去呈现民族历史中渺小而无助的个体,让更多的人看到被历史淡忘的某些真实存在。还有很多追问,在此难以全数列举。这种追问意识体现出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自觉与自省。这种自觉与自省,是一个小说家在写作上的自我磨砺,也是她对小说这门艺术的深入思考。她的小说追问在向更多的人展现,文学如何从外部表现被遗忘、被忽视的历史、现实和人生,又如何向内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洞察人性的幽微隐秘和复杂多变。这内外两方面的结合与延展,既能引发读者对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又能丰富人们对命运、人性和情感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一种悲悯与共情的感受力。